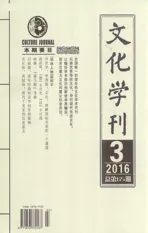文化: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通道
2016-03-16乔世华李秀丽
乔世华 李秀丽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文化视点】
文化: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通道
乔世华 李秀丽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在国际外交关系场中,文化一定是或隐或显的一根贯穿始终的线,对于决策者、当事者产生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并引导和作用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加强对一个国家文化的了解,会有助于我们理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不同国家在解决国际纷争中的角色与选择,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自身寻求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特色之路。
文化;国际关系;民族;传统
19世纪法国史学家和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虽然是一部揭示文学艺术和种族、环境、时代三者关系的论著,但其中有关种族、环境话题的大段讨论对于我们理解某一国家人民品性形成、精神追求、行为习惯还是很有作用的。譬如其中有关于民族差异造成民族精神生活需求和艺术创造也迥然有异的论述:“拉丁民族最喜欢事物的外表和装饰,讨好感官与虚荣心的浮华场面,合乎逻辑的秩序,外形的对称,美妙的布局,总之是喜欢形式。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意事物的本质,注意真相,就是说注意内容。他们的本能使他们不受外貌诱惑,而鼓励他们去揭露与挖出隐藏的东西,不怕难堪,不怕凄惨,一点细节都不删除,不掩饰,哪怕是粗俗的丑恶的。表现这种本能的无数事例中,文学和宗教尤其显著,因为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在这里非常凸出。——拉丁民族的文学是古典的,多多少少追随希腊的诗歌,罗马的雄辩,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路易十四的风格;讲究纯净,高尚,剪裁,修饰,布局,比例。拉丁文学最后的杰作是拉辛的悲剧,写的是君王的举止,宫廷的礼节,交际场中的人物,高度的修养。在雄辩的文体,巧妙的布局,典雅的文采方面,拉辛是个大师。相反,日耳曼文学是浪漫的,起源于斯干地那维亚的古代传说《埃达》和北欧的传说《萨迦》;最大的杰作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现实生活的完全而露骨的表现,包括一切残酷,下贱和平凡的细节,一切崇高而又野蛮的本能,一切人性的特征。”[1]书中还发掘了不同的生存环境对于人类精神启发的作用:“古希腊人中最早熟,最文明,最机智的民族都是航海的民族,例如小亚细亚的爱奥尼阿人,大希腊的客民,科林斯人,爱琴海人,西希翁尼人,雅典人。相反,守在山中的阿卡提亚人始终粗野简单;同样,阿卡内尼阿人,伊庇尔人,罗克利特人,奥佐尔人,出口的海(希腊半岛西侧的爱奥尼阿海)既没有爱琴海的条件优越,人民也不喜欢旅行,始终是半开化的蛮子。”[2]
如此繁复的议论若是换成孟子的“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可能会更简洁些。鲁迅也有过类似的阐发:“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3]自然,这种因环境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肯定不止于敏感的作家,也不会局限于人的“神情”。鲁迅谈到北方人与南方人的性格差异时,大体做过这样的判断:“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4]这就是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是就自然环境对人性情、思想的制约和塑造而言的。鲁迅20世纪初东渡日本留学之初即开始思考中国民族性问题,也一定是受触动于其在东瀛所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有人私下里习惯以地域来区分人群的性格品质——什么“东北人野蛮”“河南人不好”“山东人豪爽”“上海人奸猾”、农村人又如何如何、城市人又怎样怎样……,如此之类的言说或都戴着有色眼镜,难免以偏概全,但多少会有那么点“真实”的影子。进而言之,不同国家的人民也会因为生活地域、环境的缘故而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也因此,不同国家之间或和谐或冲突的关系应该是可以从它们各自背后的文明那里找到一点因由的:以某一国家的文化性格特征作为观察、理解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即使不能全部,也会一定程度上让我们获取一部分“真实”的因子。
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国际政治关系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先后发表和出版有《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文章和著作,就希图用不同区域的“文明”来解释世界冲突,这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对我们理解国际纷争很有启发性。在亨廷顿看来,美苏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所发生的诸种冲突将不会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会是肇始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等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自然,这几种文明也都各有各的代表性核心国家,如代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美国,代表东正教文明的俄国,代表中华文明的中国等。这一观点也许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早在11到13世纪西欧国家对地中海东岸伊斯兰国家先后发动的九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事实,而进入21世纪之后迄今由一部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所发动的诸如“9·11”之类的“圣战”“伊斯兰国”等恐怖袭击事件又恰好可以佐证亨廷顿的“预言”。
综合丹纳、亨廷顿所持的言论和观点,甚至包括来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以及民间百姓的诸种说法,我们似乎可以获得这样的认知:诞生在不同自然环境、地域、种族、国度的人群会因了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别的山水、各异的成长环境而生发不同的性格特征、精神需求,也因此,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或者说外交关系,很可能会因了这“先天”的文化因素而表现出不同的思路和景观来,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纷争还是融合)都一定会呈现出各自国家的文化性格来。显然,不同国家的文化会为我们理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一种有效的策略和思路。
我们可以先拿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一些岛国来说事。虽说国土面积都不大,从前的“大日本帝国”或者今天的“大韩民国”“大不列颠”的称谓,也许会被真正的泱泱大国视为“夜郎自大”,但这“大”在上述岛国国号中的特别强调,是有意味的——岛国会有一种被抛弃于世界之外的感觉,骨子里就有一种渴望得到别国的认同和重视、不甘弱小或被蔑视的气概,甚至有着要用“大”来激发自己国民自豪感的意思。以日本为例,其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立孕育的文化,主要吸纳和接受其他文明的精髓,并转化成自己的文化内涵。譬如“国学”一词固然是来自中国的《礼记》,但在日本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被赋予了日本精神的内涵——“国学”在日本指的是其固有文化和精神。[5]这个事实一面可以看出日本对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化用和拿来,一面也暴露出近代日本国学家的可笑的狭隘来。日本长期孤悬海外,发展空间有限,日本的民族构成相对单一,这有助于其同质性也是单一性文化的形成和巩固,进而强化日本人的集体主义意识。有人曾经把日本形象地比喻成一艘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上行驶的孤船,在台风袭来之时,船上的乘客只有齐心协力共同抗击风浪,才可能避免遭受灭顶之灾。毕竟船上或者说这一团队中有哪个人破坏了整体和谐的话,就必然会令全船人都葬身海底。所以,日本人讲求协作的团队精神是举世闻名的,二战中的日本母亲鼓励作为军人的儿子为天皇而死,战争后期驾驶飞机冲向美国舰艇令美军措手不及也生畏的神风突击队员们,因日本战败而切腹自杀殉国殉战的士兵百姓……数年前,一位日本女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一旦中日再次开战,她将去做慰安妇以鼓舞日军士气——这个“段子”可能比较好地说明了在岛国意识作用下的日本人的危机感、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和牺牲精神。因为是岛国,日本有着强烈的登上陆地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资源的意识,这似乎可以解释其一旦强大就不断向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行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羽翼稍微丰满就迫不及待地炫耀武力,采取吞并朝鲜、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岛国,英国人的“岛国意识”和日本人还有所不同,因为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世界文明国家的核心,英国人一直自视甚高,天生的以及后天造就出来的领先地位和优越感,令他们在很长时间里更愿意以“光辉孤立”的形象现于世人面前,不愿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而是要扮演一个欧洲大国均势平衡者的角色,以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
日本人与生俱来就有着很强的危机感,这与日本的生产空间狭小、自然资源有限有关。相形之下,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种强烈的危机感,民族性格持重、中庸,这可能与中华民族一直地处大陆文明,资源辽阔,物产丰富,地理环境优越,多民族融合共生等有关系。因为迫切的危机感,日本会随时因应形势变化而追随强者、积极地向强者学习:中国强大时,就师从中国积极取经,提出所谓“和魂汉才”,且将自己纳入到亚洲的文化圈中;但到近代当中国衰落、西方列强打开日本国门之时,日本人开始像过去尊重中国人一样尊重西方人,并适时提出沿用至今的“和魂洋才”,“脱亚入欧”成为日本的战略选择;一战之后,西方列强联手制约日本,削弱和否定日本在中国所获得的权益,日本又转向了“排欧主亚”的路线,意图重新称霸亚洲,二战时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正是它这一战略目标的体现。日本在欧亚之间的摇摆不定或者说投机取巧,既是其实用主义性格的体现,也是其要向世界证明自己强势的努力。二战结束后,日本一直积极尾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方针,就有“狐假虎威”的色彩——追随强者,同时证明自己的强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单一性容易令其在现实选择中趋于极端,会如赌徒一般孤注一掷:甲午战争中,日本耗尽海军陆军的所有力量投入战事就是一例,若不是当时的中国统治者无心打一场持久战,日本是不可能由此大发一场不义的战争财的;二战期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向美国叫板,更是其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的淋漓体现。因此,决定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结果的,不仅仅是武器的精良与否、军事力量的是强是弱、得道还是失道一类因素,还应该取决于战争双方所根据和持有的文化,那由“天时”“地利”造就、又在“人和”上表现出来的文化之间或隐或显的较量,应该是重要推手,譬如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能够以弱胜强,其所倚靠和彰显的都是中国文化的力量。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表现为“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6]。因为知耻,意识到自己的缺欠(如资源匮乏),日本的上进心因此被激发,通过学习和研发科学技术,生产出高科技含量、低成本的产品打进世界市场,所谓知耻而后勇,会在二战后迅速成长为经济强国;同样与知耻有关,日本近些年来一直谋求在现行宪法之下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其不甘被忽视、相信实力、追随强者、展示自己强势形象的体现。也还是与知耻有关,日本侵略过诸多亚洲国家,却常常竭力掩盖历史真相,不肯向被侵犯国家人民道歉或缺乏反省的诚意。在这一点上和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战之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战争的反思、对过去战争罪行的真诚道歉,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与德国人冷静、理性的性格、精神有关系。日耳曼民族居住地区纬度较高,多森林平原,土地贫瘠,气候寒冷,饥寒交迫的自然环境助于德国人形成严肃保守、自省谨慎的性格,这似乎可以解释这个国家、民族何以能出现那么多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当然,也正是因为德国人注重理性,其生活中会有较多的顾忌和压抑,一旦情绪失控,就很有可能失去理智、变得疯狂。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德国何以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一战爆发后,德国举国上下欢腾,洋溢着强烈的排外情绪,诸如“一枪干掉一个俄国佬”“一刀捅死一个法国佬”“一脚踩死一个英国佬”“一拳打死一个日本佬”之类的口号随处可见。因为生存环境恶劣,德国人的祖先就要靠征服与掠夺来获取资源,这促成其尚武好战、富有征服欲的性格的形成,“日耳曼”的意思本身就是“令人生畏的战士”,而德国历史上战争频仍也是事实,12世纪中叶弗里德里希家族统治德国之时,就屡屡发动战争,弗里德里希一世曾6次远征意大利,时间长达30年之久,弗里德里希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有一句名言:“不使用武器的谈判就像不用乐器的音乐一般。”在19世纪中后期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德国就有三百多个各自为政互不相服的小国,所谓“一年有多少天,德国就有多少诸侯”。一战期间德国士兵背包里最常见的两本书是《圣经》和尼采所著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也许最能显现德国人尚武与理性这相反相成的民族性格。
再来看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崇尚独立自由、勇于开拓进取的移民精神当然是美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方面,同时,作为美国文明起源的欧洲文明令美国人带有着较浓厚的种族主义观念。所以,美国人一面自诩是“上帝的选民”,而视其他种族尤其是有色人种为“上帝的弃民”,还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利益捆绑在一起,把拯救人类看成是上帝赋予美利坚人民的神圣使命,其在各种国际争端中屡屡以国际警察的身份出现、以“拯救”世界的领导者自居,向其他国家输出其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
当然,像前面这样以国家界限来划分不同区域人群并评说其行事原则、特色的方式,可能会不那么准确。更何况,现代交通、“物流”的畅快,让区域划分变得模糊,也让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人们的交流借镜更加便利,所谓“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7]。但粗略地举说这些事实,并尝试着从不同国家的文化特性来解说国际关系,实在是要说明这样一点:文化,应该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通道。自然,在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交往中,也还会有别的因素胜过文化,譬如利益。19世纪一位西方政治家早就有这样的断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国际关系的复杂有时单纯依赖文化来洞察,显然还远远不够;但文化一定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文化一定在国际外交关系场中是或隐或显的一根贯穿始终的线,对于决策者、当事者产生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并引导和作用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由此形成了国与国之间——事实上是文化之间的冲撞或融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能更多强调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没有提到异质文明之间的融合。其实,了解他国以及自身文化,是为了更好地让不同文化之间发生对话而非对抗关系,能够促进尊重与理解,趋利避害。
民主人士梁漱溟在1946年初赴延安时,曾向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等十位中共领导人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表示自己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深刻的洞察之后,却对中国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即多个政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以及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化等发生疑问。在他看来,中国如是做,“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当然,他也不回避自己的迷茫:“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都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8]这段历史事实很有意味。对中西文化都有了深刻洞察和领悟之后,梁漱溟认为向西方寻求中国发展道路模式是不可行的,但也并没有就此原原本本地要返回东方文化来。这其实说明了:无论是奠基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等诸种文明之上的每一种人类文化,它们都必定各有自己的优长劣短,因此可能并不会存在一种至为完美的文化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普世价值”,东西方文化都会面临着自己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弊端,但这又不能抹煞掉它们各自所创造的多种多样的智慧和成就。一如上世纪80年代一位寻根作家所言:“中西方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极不相同,某种意义上是不能互相指导的。哲学上,中国哲学是直觉性的,西方哲学是逻辑实证的。东方认同自然,人不过是自然的一种生命形式;西方认同人本,与自然对立。”[9]。也许文化就是这样,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和互补中不断前行,而我们当下最要紧的是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一面可以更好地选择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特色之路,一面也会更游刃有余地行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
[1][2]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216-217.322.
[3]鲁迅.“京派”与“海派”[A].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2.
[4][7]鲁迅.北人与南人[A].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5-436.
[5]祝东力.美学与历史[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285.
[6]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
[8]汪东林.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A].中共中央统战部统战理论研究中心等编.相遇贵相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的故事[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23.
[9]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N].文艺报,1985-07-06.
【责任编辑:董丽娟】
G03
A
1673-7725(2016)03-0006-05
2016-02-26
本文系2014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契合性研究”(项目批准号:L14BYY012)、东北财经大学2015年校级科研一般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价值、地位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DUFE2015Y25)的研究成果。
乔世华(1971-),男,辽宁大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