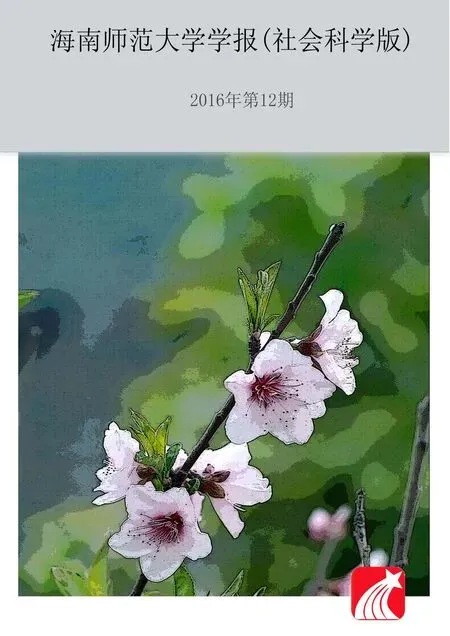论李渝小说中的抒情残体
2016-03-16蒋兴立
蒋兴立
(台湾清华大学南大校区 中国语文学系,台湾 新竹)
论李渝小说中的抒情残体
蒋兴立
(台湾清华大学南大校区 中国语文学系,台湾 新竹)
人们习惯跟随众体的步伐,追逐胜者的身影,渴望迈向成功坦途。但李渝总是勾勒在生命道路上蜿蜒进窄道,或者误入歧途的孤独个体与受创残体。李渝作品中的残体,以生命挫败者的巨大身影,慰藉与导引着世间忧郁痛苦的灵魂匍匐前进。生命赢家的万丈光芒固然闪耀夺目,但走过人生低潮,才会发现生命真正的动人之处,却是那些失败者在深不可测的幽谷以灵魂来回敲打撞击,奋力点燃,照亮黑暗的微弱火花。
李渝;残体;知音
一、前言
李渝(1944-2014)于2009年出版了《行动中的艺术家》一书,内容是其前往香港浸会大学讲授艺术课程的教学内容,封面是马列维奇的作品《拿着红棒子的女孩》,半个手持平衡木的女子,她的另一边在封底,分裂成两半的女人,安静地手持平衡木,凝止于书本的方框中,惟有将整本书打开,才能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自序》的标题是《抒情时刻》,李渝如是说:
人类从不因时空改变而停止过摧残的活动。战争、党派斗争、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等,制造着外在的暴乱;我们的先辈不是被屠戮(像《和平时光》里的父母亲),就是被掏空(像《金丝猿的故事》中的将军)。而进行在内在的暴力,规模也是一样地深广,程度一样地惨淡;20世纪作家、画家、音乐家们自杀和精神失常的数目令人吃惊。公众历史和私人历史都很荒瘠。众体和个体都是一如英国画家培根笔下人物似的残体。时空来到现、当代,蛮荒并不下于古代。错误重复,灾难一再发生,欠缺是一个与生俱来、无法改造的基因。抒情,在我们的时代,还有可能,还有必要吗?抒情,无论它的范畴是什么,大毁坏大失败之后还能持续有效,势必不得不涉及人的再生和重建;它要使人明白,人和世界——外在的和内在的——必须设法互相认识、谅解、协调,而不能达到共存的目的。①李渝:《行动中的艺术家》,第4-5页。
这段话涵盖了李渝创作的核心概念。李渝认为我们置身于一个暴乱的时空中,而这样摧残的活动并未因文明的进步而有所停歇。众体与个体,“群”与“我”都是不全的“残体”,“欠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基因,“抒情”是为了寻找协调与平衡的方式,人与内外在世界的相处,无论是激烈的抗争,或者是疏离的遁逸,都是一场场艰难的战役,如果过程中能出现另一个人让你迎上前去,“不激动不流泪,只是要和他相拥,庆幸有了起死回生,残躯复原的机会”*李渝:《行动中的艺术家》,第5页。,那便是美好的救赎,让被暴力世界毁坏扯裂的残体得以复原保全。等待与寻觅知音,让残躯完整的概念,是李渝小说文本中相当关键的发展主轴,但目前少有论者深入探析。
当下关于李渝小说的学术评论,除了部分综合性的单篇论文研究*详文参见王德威:《无岸之河的渡引者——李渝论》,《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 ,第393-413页;骆以军:《哥德大教堂与曼陀罗》,《印刻文学生活志》第6卷第11期(2010年7月) ,第64-71页。,此外可归纳为四种观察视角:一、探讨现代主义对于李渝的影响;二、分析李渝与夫婿郭松棻或相关作家之间的作品比较;三、从空间书写的切入点挖掘李渝小说中温州街的故事与庭园的深意;四、从画论或心理分析的理论思索李渝小说中忧郁与抒情的力量。*详文参见黄启峰:《主观的真实——论台湾现代主义世代小说家的国共内战书写》,《台湾文学研究学报》第19期(2014年10月),第9-49页;黄启峰:《河流里的月印──郭松棻与李渝小说综论》,台北:秀威出版社,2008年;黄启峰:《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寓言书写:论鲁迅与李渝小说的〈故事新编〉》,《嘉大中文学报》第9期(2013 年 9 月),第155-184页;杨佳娴:《离/返乡旅行:以李渝、朱天文、朱天心和骆以军描写台北的小说为例》,《中外文学》(2005年7月),第133-155页;蒋兴立:《论李渝小说中的庭园书写》,《高师大国文学报》第11期(2010年1月),第119-138页;郑颖:《郁的容颜——李渝小说研究》,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黄资婷:《论李渝小说中忧郁与抒情之力量》,《东亚人文》2015年卷,第49-90页。前述学者对于李渝文本的梳理与研究深具价值,也扩大了李渝作品的影响深度与广度,然而是否还有其他理解李渝小说的可能?文本中是否还潜藏着李渝诠释生命纵深的雪泥鸿爪,等待知音寻幽?本研究意图透过李渝的小说文本、前人论述、艺评画论、访谈数据,思索其文本中所存在的抒情残体,藉由“残体的形貌”“知音与残体”等切入视域进窥李渝的小说文本如何透过残体的抒情,反映现代社会、都市景观中个体的困境?孤独而残缺的个体又如何在荒瘠的生命旅途中寻觅知己,渴求救赎?
二、残体的形貌
李渝1944年出生于重庆,5岁来台,成长于60年代台北温州街,父亲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就读台大外文系时开始创作小说,毕业后赴美攻读艺术,70年代与夫婿郭松棻共同参与北美保钓运动,至1983年以“江行初雪”获中国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回归写作。1997年郭松棻突然中风,她因压力太大,精神崩溃;2005年郭松棻辞世,此后李渝一直难以彻底摆脱忧郁症的纠缠,终于2014年自杀。*参考印刻编辑部:《乡的方向——李渝和编辑部对谈》,《印刻文学生活志》第6卷第11期(2010年7月) ,第74-87页;黄启峰:《河流里的月印──郭松棻与李渝小说综论》,台北:秀威出版社,2008年。如以1997年夫婿郭松棻中风为其创作分水岭,以此为观测脉络,循线追索,会发现李渝中后期的小说虽然延续前期作品的聚焦所在,但人物聚焦逐渐从对“孤独个体”的关注,转变为对“受创残体”的描摹。李渝的小说文本经常出现一个在众体中孤独的个体,她勾勒出台湾不同族群、身份、背景的孤独身影,他们或受迫于无情的政争,或受困于现代都市文明,或受限于自身的理想坚持,在人性、生活、生命的暴力中,趋向一条人烟稀少的道路。李渝之所以聚焦于这些踽踽独行的身影,肇因于她对“孤独个体”的深刻理解与认同,孤独方能高远、成就卓越,进而创造美感的极致,孤独方能提炼灵魂深度,才能鉴赏与体会美的卓越风格。因此李渝致力刻划生命激流中孤高深远的个体塑像,能守住孤独寂寞,才能接近她所信仰的永恒的价值。*李渝曾在艺评中提及,能守住孤独寂寞的艺术家,终能成就优秀的作品。详文参见李渝:《族群意识与卓越风格》,台北:雄狮美术,2001年 ,第V、125页。李渝中后期的小说文本《金丝猿的故事》《金丝猿的故事》(经典版)《夏日踟蹰》《贤明时代》《九重葛与美少年》等作,创作者不再只是书写在人性、生活、生命暴力中坚持自我的孤独个体,前期作品曾出现过失去伴侣、遭遇背叛、内在失衡的人物被更进一步强化,从心灵的破碎到身体的残缺,作者细致描绘受创残体的形貌。
《踟蹰之谷》中的军官,为了国家民族,而使一些生命生灵遭到伤害,数十年积郁,使他在外表上看来冷静敏捷进取,内心却悒闷悲观。静处或夜半醒来,每一张惊恐的脸化为梦魇勾缠他,他担任岛屿开建横贯公路的工程总监,在开路炸山的过程,因内在的濒临疯狂导致外在的行为出错,在炸山意外中失去半条腿,成为残疾之人。自此他退休并居住在这深沉郁结、景观眩妙的峡谷内,以画笔转移悲观的心情。军官的外表逐渐削瘦、狰狞,仿佛山间幽灵,峡谷内也开始出现企图纵身一跃的自杀者,画家往往能看出他们的意念,并要求为他们绘制人像,或能藉此改变他们的命运。一日,画家遇到俊美的小学教员,在为他写生轮廓时,画家忆起自己的年少,为俊美男子绘制人像的时光持续十多年,直至两人都从山谷消失,画家的房舍被改建为饭店,那张美丽而悲伤的人像画则被置放于饭店大厅,任人驻足静观。《寻找新娘》讲述“我”在客户陈女士的请托下,为她寻找艺术家魏虚一张题为“新娘”的画作,魏虚的人物画以“痛苦”为主题,追求丑陋,最可怕的是画作中人物的冷漠,使人隐隐从内心感到惧怕。据说画家有个富有美丽的夫人,支持画家任性的创作,经历一段追索的过程,“我”遇到了已然失去丰美滋润美貌的夫人,在夫人宣称是自己的作品里,“我”发现其中存在魏虚沉重的风格:“黑褐的色调设下陷阱还是深渊一般的背景,人众都陷在深渊里,刀锋锐利划过,刮出点线,割出冷凛空间,于是背景看来也很像监狱或笼牢。”“头部被变形移位得看不出面容,只见参龇的齿牙,扭曲在墙上的,与其说是人形,不如说是兽形,与其说是人物群像,不如说是魅影。”“藏在黑暗里闪烁着的,是双双怯懦又无助的眼睛。”*李渝:《寻找新娘》,《夏日踟蹰》,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 ,第108页。最终“我”并没有见识到传闻中的“新娘”,仅仅与夫人道别。《寻找新娘(二写)》的魏虚更名为卫旭,身份设定异动为“我”与秀玲的老同学,秀玲请“我”寻索卫旭的“新娘”画作,卫旭的画以“受难”为主题,画中人总以索求的目光望着观画者,令人感到焦虑,如阴魂缠附不散。卫旭结过三次婚,第一位夫人是富家千金,第二位夫人精明干练,第三位夫人是他的模特儿,虽没有离婚,但长久一人住在城市某处,仿佛被画家遗弃了。在追寻中,叙事者找到了画家寄居过的空间,目睹卫旭笔下的魅影,并被画中人物那一双双悲哀无望的目光震住。“出没在我们周身的紊乱景象,是不是毕竟由卫旭察觉了呢?他要表现的,是否是我们在生活的路程上,必然会出现的危况,控制不了的失常?我们心底的最隐密晦暗又虚弱的角落,是不是由他描绘出了形状呢?”*李渝:《寻找新娘(二写) 》,《夏日踟蹰》,第118页。“我”终于看见曾经美极了而现在形容憔悴的第三位夫人,也看到了夫人一系列与卫旭风格殊异的画作,故事末尾,“我”决定不提拜访之事,而劝秀玲转而支持其他风格不俗但不得意的艺术家。《和平时光》以聂政刺韩王的历史为原型进行改编,文本交错着两线复仇故事,其一是韩王舞阳命聂政之父铸剑,而后持剑手刃亲生父亲,为名义上的父王报仇,聂政之父铸剑献剑后被舞阳杀害,于是第二则复仇故事则是聂政处心积虑向韩王复仇的过程。史实记载的男刺客聂政被改写为女儿身,一再行刺失败,不惜毁容吞炭,以残容喑声弹奏《猗兰操》,在此大悲之曲的音韵里,聂政与韩王舞阳,“君和臣,敌和我,听者和奏者,复仇和被复仇的双边全体,都在水金色的光里融解”。此首《聂政刺韩王曲》相传是《太平广记·灵鬼志》中魑魅教授嵇康的乐曲,亦是临刑赴死前,嵇康索琴弹奏之音,世称《广陵散》。*李渝:《和平时光》,《贤明时代》,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第165-170页。《待鹤》文中同样穿插着第一人称“我”与第二人称“你”的叙事观点,并在“我”前往不丹寻鹤赏画与治疗忧郁症的双线结构中交错,故事穿插着不丹向导意外坠谷的死亡事件,以及向导之妻在丈夫离世后重生的转折,两条支线各自蜿蜒,却最终曲折相会。《三月萤火》面对工作困境与妻子背叛的“我”与一名甫出狱的男子偶然相识,结为知己,与《夜煦》《从前有一片防风林》般,知己偶遇,错身而过,各自回归自己的生命轨道,但叙事者“我”与《无岸之河》的男学生相同,决定踏上寻觅知己的旅程,末了没有觅得知己,却邂逅另一名规划环岛旅行的少年,在关于海救赎毁灭的思辨中,故事嘎然而止。《建筑师阿比》因图书馆工程受挫,阿比在多重压力下失眠,她决定在周末到印地安乡源的岩穴中驻留。《提梦》描述前半生干戈不断、杀伐无数的巴比尔王,无法入睡而痛苦不堪,他开始铸造遥远童年记忆中的花园。《海豚之歌》的演艺家与海豚都有表演焦虑与上台恐惧,必须吞药度日,最后演艺家鼓动海豚,让它跃回海洋,自己也跳离舞台,向河岸奔跑……作者或者透过双线分裂的叙事结构、“你”“我”分离的叙事主体,或者崩毁与救赎并存的叙事情节,让读者进窥迷惘错综、冲突交织的内在风景。李渝前期小说里,面临生命挫折的孤独个体,到后期多数恶化为残缺病体,残体的增加使病态成为常态。出现裂痕的残躯,如同遭致毁损的精细瓷器,在崩裂化为碎片前,凝止生命的瞬间。这即将崩溃瓦解的残体,是否有缝合复原、裂隙填全的可能?救赎是否存在?残喘的苟延生命,究竟是获致救赎,或是延续毁灭?
文学、音乐、绘画、花园、纯真少女与俊美少年……纯净无垢、臻近完美的人事物,可以被视为艺术,艺术对李渝而言,是作为一种乌托邦的圣域存在。《踟蹰之谷》《提梦》《待鹤》《三月萤火》《建筑师阿比》《海豚之歌》等作,或勾勒杀戮者后半生的罪咎梦魇,或记录失去伴侣、遭致背叛的生命体验,或描写无法适应多重压力的现代生活,残体无法入睡、噩梦连连、生活失序、人生失去固有的形状,如坠深谷,如临狱刑;但文本也安排了生命低谷飞升的可能:《踟蹰之谷》的军官身心残缺,藉由绘画寻找寄托,在年轻男子俊美无垢的脸上,忆起自己的少年时光,画家将己身的悲哀挹注到画像里年轻男子的动人美丽中,从而使自我超脱血染的记忆,获得释放。《提梦》的巴比尔王同样在花园,记起遥远的童年,在源初美好的春天花苑里,使噩梦停歇,觅得宁静。《和平时光》《待鹤》已然逝去的夫婿松棻在“我”的梦中与之相会陪伴,忧郁的尽头出现所待之鹤,虚实交错的结局,在天地晴朗的传奇中凝止,“我”相信群鹤必将飞越千古时空,完成现实与神话的完美结合。《三月萤火》的少年之旅、《建筑师阿比》的印地安乡园、《海豚之歌》艺术家的奔跑与海豚的悠然跳跃……当李渝书写唯美艺术的抒情时刻,时空由原本暴力、紧张、阴郁的炼狱,幻化为安详、圣洁、舒缓、凝止的桃花源,作者不再用世俗平庸的生活节奏,与紧迫盯人的文字枷锁困住人物,跳脱现代化工业文明与沉重黑暗的现实挫折,文本进入一种悠缓宁静的叙事情调。李渝曾在艺评中提到:“艺术家在残忍╱优美,暴虐╱和平,阴狠╱甜纯,腐败╱永恒等等之间来回叩击,陈列出生命的狰狞无奈,也陈述了它的优美庄严。”*李渝:《行动中的艺术家》,第101页。受创的残体藉由孤高美善的艺术让自我得到安适,乐居于内在的静熙国土。
三、知音与残体
在李渝中后期的作品里,她开始探讨知音与残体之间纠结绾合、微妙复杂的勾连。《和平时光》中的韩王舞阳与聂政,渴望报父仇的心思相似,对于哀乐悲曲的体会也同具共鸣,之所以对大悲之曲的乐韵同情共感,是因为彼此的命运使两者对于悲哀的体悟层次相当,原本可以发展为美好的知音,甚至是伴侣关系的两人,却因缘际会变为仇敌,作者将聂政改写为女性,或许是有意透过女性温和疗愈的母性力量,弭平仇恨,抚慰伤痛,恩怨在悠扬乐曲与水金色的温润光晕中和解,作者在结尾引用嵇康《广陵散》的传奇作结,面容残缺的魑魅传授嵇康《广陵散》,鬼魅知己的隐喻强化了小说文本对于“知音”关系的美好想象。但李渝也思索知己对人物的背叛、失约、折磨,《杰作》前半段铺陈一对热爱创作的文学同好春生与夏长的生命发展,故事结尾却暗示着夏长为了自私的文学创作而陷害知己。《三月萤火》中“我”前往寻觅出狱男子,一次知己相约的旅程,而男子却未尝现身。如《三月萤火》故事末了叙事者“我”对于海的思辨,“海可以拯救你,也可以摧毁你”*李渝:《三月萤火》,《九重葛与美少年》,台北:麦田出版社,2013年 ,第129页。。知己与个体的关系吊诡错综,能让个体的生命趋向美好,个体的消失、背叛、折磨也能让个体受伤残裂。《寻找新娘》与《寻找新娘(二写)》叙述艺术家与伴侣之间的爱欲矛盾,艺术家的美丽爱人原是爱慕他、理解他的知己,因此愿意支持艺术家任性的创作,但是只看“时尚和外相的文艺社会”,“辛苦的生活经验”,使得艺术家日子过得困厄窘迫,笔下也未必如意,或许是艺术家对爱侣的折磨,或许是蹇困生活的逼迫,夫人失去了她的美貌,被遗弃在城市中。《寻找新娘(二写)》的修订改写,使得小说的笔调趋于和缓,关于艺术家“残容”画作的叙写不再那么苛刻尖锐,并点明艺术家所画的不只是特殊的变形怪物,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的生命中控制不了的危况与失常,小说里夫人对艺术家的爱是一种知音关系,“我”对艺术家的观察理解,是另一层的知音关系,但两者的结局不尽相同,后者维持了一种距离的美感,前者却在艰困的生活里撕裂磨损。虽然一对因爱与理解结合的知己与伴侣,故事的结局是如此悲哀,然而“有谁能比纯洁的新娘,更能提醒美好时光呢?”*李渝:《寻找新娘(二写)》,《夏日踟蹰》,第124页。文本一写的原句是“有谁能比新娘更能原谅饶恕一切,更能重申纯洁时光呢?”*李渝:《寻找新娘》,《夏日踟蹰》,第111页。二写时,句子被修改了,真正的宽容与饶恕又何须言明?为什么要寻找新娘?是为了重返生命中最优美幸福的时光,是为了寻找安详宁静的力量,曾经是那么美好的知己相遇,尽管之后被生活啮咬得千疮百孔,也能没有忿怨地面对。一写与二写中,夫人都声称人像画是她的作品,为什么不是呢?名作的诞生建构于模特儿给予艺术家的谬思灵感,艺术家才华洋溢的表现,以及最后鉴赏者的理解,环环相扣。二写故事的尾声,叙事者描述夫人“夕光直照窗帘,透进来,十分淡弱,画面黯黯生出一层金,人物绕头有一圈发色比较浅,受光亮起来,便带上一圈光环或花冠像新娘一样了”,“皮肤底下透出一种晕红,使她显得十分细腻精致,纯净秀丽,新娘才有的气貌到底是维持了下来”*李渝:《寻找新娘(二写)》,《夏日踟蹰》,第124-125页。。夫人在受尽伤害与折磨后,《寻找新娘(二写)》让她活得像新娘,以爱与宽宥面对知己与生命。尽管崩裂的伤害是如此痛苦,但是我们的生命因为知己丰富完整,一如艺术必须在鉴赏者的欣赏认同中才能复活重生。《倡人仿生》与《列子·汤问篇》“偃师造人”有几分相似,魏襄王命匠师名巧模仿他嗜爱的倡人柳制作偶人,与本尊一模一样的偶人柳竟与倡人柳灵犀相通,对襄王的宠妃盛姬眉来眼去,导致襄王发现倡人柳与盛姬的私情与背叛,襄王盛努下处斩两人,名巧将偶人柳剖腹摘心,证明玩偶真是无情贱物,才得以存活,时时摘心使偶人色相衰减,四肢齿卡,遂使襄王将之冷落舍弃,消失于历史。千年之后,偶人柳再次现身于美术馆,重新修整上色,复出展览,众人觉得宛如两千三百年前的魏襄王,油然爱慕起他来。偶人柳完美得连本尊都忍不住忌妒,在魏襄王的宠爱中如花初绽,也在魏襄王的猜忌冷落中仓皇失色,终于在千年后鉴赏者的爱慕中残体复原,再现风华。
李渝在《失去的庭园》一文中,自剖小说创作对她的意义:
各种文学形式之间,小说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是因为它能来去在现实和幻想、写实和非写实之间,用后者来弥补、救援前者,呈现人间困境,为弱者说话,提拔沉沦。但是小说也最难写。好的小说得同时具有诗和神话的质量,诗代表了不能翻译的语言、独特的个人风格,是美学的部分;神话代表了迷人的故事,深入的寓意,是思维的部分。此外,写小说又必须仰赖某种非理性的气度或气质,有时需要长期酝酿,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有时却又灵光乍现,不请自来,油然而生。*李渝:《失去的庭园》,《九重葛与美少年》,第258页。
对李渝而言,小说的吸引力在于结合现实与幻想,呈现人间困境,为弱者说话,传达艺术恒久不灭的高远价值。李渝在《失去的庭园》里自问:“小说这么难写,不能写小说已有一段时间,由是问自己原因。”是否是工作的繁忙,与日常庸碌生活的干扰呢?在马勒《第六号交响乐》的提醒下,李渝体悟了原因,是因为她失去了心中的庭园。*李渝:《失去的庭园》,《九重葛与美少年》,第258页。李渝在《都会中的宁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艾斯特庭园》里提到庭园是都会中的一方宁静,她肯定艾斯特庭园保持了艾斯特夫人童年记忆里的宁静,中国庭园精神上的境遇是安详和孤静,若失去了这重要的形上概念,庭园也不过是一方美丽的地点罢了。*李渝:《族群意识与卓越风格》,第159-167页。李渝心中的庭园,能让她在庸碌繁忙、现代节奏逼人的城市生活里忆起源初的美好,保有宁静,安详、孤静、生机蓬勃,而这一座庭园是已然逝去的郭松棻。
一座庭园。……锁上了,用两只手一齐再拉,铁锁和门板相撞发出铿锵的声音,响彻安静的庭园。
放弃了进去的打算,回转过身,走下三、四级阶梯。走下最后一级,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头廊底完全隐没在黑暗中的角落,拥抱着一对年轻的爱人。
头埋在彼此的颈弯里,四只手臂缠绕在肩头,两人的呼吸若不是混淆成了对方的就是已经消失了。
一点声音都没有地紧紧地拥抱着,无顾于世界的骚乱,脱身在时间以外。*李渝:《失去的庭园》,《九重葛与美少年》,第263-264页。
艺术是李渝信仰的美好而永恒的价值,在艺术的圣域,人心能觅得平静与休憩,暴乱与伤痛能被抚平,但艺术创作的过程艰难不易,可说是为了呈现人间困境,为弱者说话,提拔沉沦的奉献。创作者与鉴赏家的知遇,也是艺术呈现的关键环节,失去了最重要的知音鉴赏,艺术创作者该如何顽强地滋长存活?艺术固然是永恒美好的伊甸天堂,但若失去了知音,创作者依旧会觉得寂寞悲哀。知己像海,可以是救赎,也可以是毁灭。知己可以让个体破碎分裂,也可以使残体完整复原,知己的消失、背叛、折磨是如此令人彷徨、忧郁、无助,但是回忆起源初相遇时的青春美好,所有的伤痛都值得被宽宥与谅解。
四、结语
李渝在《地狱天使——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中描述“培根致力于人体变形,夸张呈现人的兽形和兽性,和肉体易腐易败的生理本质”。典型的培根人物有浮肿扭曲的头脸,颜面常不是被咬去一块,便是失去了五官形状,肢体常缺去一部分,血肉模糊,所谓的人形,其实更接近异形、野兽或梦魇。他们总是在冷寂的封闭空间里自残或被摧残,身心忍受着暴力折磨。没有一种劫难比自我格斗、自我凌迟更让人束手无策。*李渝:《行动中的艺术家》,第94-97页。李渝在艺评中对培根的观察理解,未尝不能视为同样被内在忧郁暴力所苦、陷入永无止尽自我拮抗的李渝的自况。郭松棻与李渝,互为创作者与鉴赏家,是彼此最重要的知己,失去了郭松棻,李渝仿佛失去了海洋,感到虚无苍凉。面对一次又一次狰狞痛楚、血肉模糊的自我撕裂过程,苟延残喘并非救赎,更接近是毁灭的延续。李渝评论培根自我凌迟时道,“这样的格斗没有赢者”*李渝:《行动中的艺术家》,第97页。。大多数的时候,人们跟随众体的步伐,追逐胜者的身影,渴望迈向成功坦途。但李渝总是勾勒在生命道路上蜿蜒进窄道,或者误入歧途的孤独个体与受创残体,正如她笔下温州街的失败者照耀着她的人生道路*李渝曾说,少年时,她把温州街“看作是失意官僚、过气文人、打败了的将军、半调子新女性的窝聚地,痛恨着,一心想离开它。许多年以后才了解到,这些失败了的生命却以他们巨大的身影照耀着、导引着我往前走在生活的路上”。参见李渝:《温州街的故事》,台北:洪范书店,1991年,第41页。,李渝作品中的残体,与故事里的边缘人,他们也同样以生命挫败者的巨大身影,慰藉与导引着世间忧郁痛苦、扭曲变形的灵魂匍匐前进。生命赢家的万丈光芒固然令人艳羡、闪耀夺目,但走过人生低潮,才会发现生命真正的动人之处,却是那些失败者在深不可测的幽谷以灵魂来回敲打撞击,奋力点燃,照亮黑暗的微弱火花。
(责任编辑:曾庆江)
A Discussion on Individuals and Injured People in Li Yu’s Novels
JIANG Xing-li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NandaCampusofTsinghuaUniversityofTaiwan,Hsinchu,China)
People are prone to follow the steps of masses, to chase the winners, and eager to achieve success. Nevertheless, Li Yu tends to portray solitary and injured individuals who have gone astray or been struggling hard in daily life. The massive shadow generated by failure stories of frustrated people in Li’s novels is conducive to encouraging and motivating all the suffering souls in the world to plod humbly, for the aureole of life winners is dazzlingly brilliant, but as is aware to individuals going through frustrations in life, the most touching part in life is a weak spark in darkness which is lightened by losers’ incessant and arduous struggle in the unfathomable environment.
Li Yu; injured people; bosom friends
2016-09-01
蒋兴立(1974-),女,台湾台北人,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清华大学南大校区中国语文学系专任教授。
I207.42
A
1674-5310(2016)-12-004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