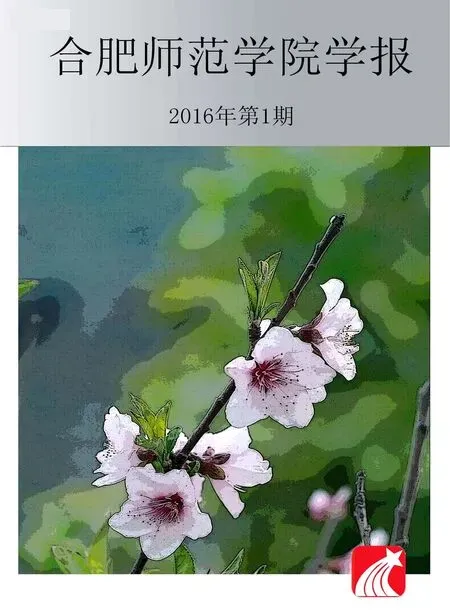孟子的社会实在论思想
2016-03-16邹顺宏
邹顺宏
(铜陵学院 法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孟子的社会实在论思想
邹顺宏
(铜陵学院 法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摘要]经过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阶段之后,儒学在汉朝始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它所构建的社会问题体系构成了其社会认识论的本体基础。孔子之后,“亚圣”孟子在全新的时代氛围中将“天人之际”建基于现实的生活及其社会制度,其社会实在论思想充满了海纳百川式辩证思绪与哲学幽思,这无疑是中国哲学及世界哲学的重大成就。在当代大科学背景下,天-人-民-社-类的辩证关系仍然是科学争议、哲学分歧与文明冲突的核心主题,孟子的社会认识论思想恰是中国古代先贤为全人类所做出的历史宝鉴与珍贵遗产。
[关键词]儒学;孟子学;社会实在论;民主政治
“实在”(Reality)作为既古老又常新的哲学核心范畴,与“存在”(Existence或Being)一词紧密相联;它不仅于历史悠久的东方哲学有着显赫的定位(天象/天道/天地/天理/天命等),在西方古代哲学中也是“对本体论的研究处于首要地位”[1]30。不惟如此,“实在”概念也从来就内蕴于中国哲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中,尤其被儒家学说的“天-地-人-心-…”等深广的知识谱系所发扬彰显。在哲学思潮中,关于“实在”的种种学说纷繁多样,如形而上实在论、科学实在论、自然实在论、批判实在论、内在或外在实在论,乃至各种反实在论等。其中,对于人及其社会的实在论思想可统称为社会实在论,这是与社会建构论针锋相对的理论体系,在现代尤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较突出的典范。社会实在论倾向于强调社会现象、社会制度与社会行动的本真根源及其内在张力,将人及其社会的总体关联纳入到自然主义的框架。
在中国哲学中,儒家的社会观及社会实在论思想自有着源远的学理线索,其在关于社会现象、问题、体制、动力、本体、规律及理想等各层面都展开了自觉而规整的探究。这首先表现在古代先秦儒学中孔子的开创性思想及后来孟子精深的集大成思想中。孟学在宋明理学与实学中得到了两种渐行渐远、南辕北辙式的诠释与发展,其实在论思想遭到肢解与流失。随着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矛盾与争执愈演愈烈,并以西学东渐的比较学理,孟子的社会实在论思想亟需辨证、发掘与弘扬。
一、社会实在论的西方哲学背景
在西方哲学中,在客观/主观、自然/人(社会)、理性/经验、观念/历史等辩证范畴之间凸显着一条纷繁复杂的知识谱系链条,一如康德的墓志铭所昭示的:“头顶璀璨星空,心怀道德律令”。康德指出:“关于由纯粹理性所得知识之起源,即此等知识是否自经验而来,抑或与经验无关而起于理性之问题。亚里斯多德可视为经验论者之重镇,柏拉图则为理性论者之领袖。在近代,洛克追随亚里斯多德之后,莱布尼兹则追随柏拉图之后……并不能使此争议到达任何确定的结论。”[2]531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一方面坚称经验为所有知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则宣扬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他将道德规范置于纯粹理性之侧,在其客观“物自体”与主观认识论的怀疑论之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不可知论立场。此后,黑格尔以其恢弘的辩证范畴体系构建起神秘的唯心主义哲学框架。“凡生活中真实的伟大的神圣的事物,其所以真实、伟大、神圣,均由于理念。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实在”演变成了世界精神的表象,黑格尔赞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他能思维”的观点,思维作为一种后思,“亦即反思。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3]35,39。这种唯心主义路径使西方哲学陷入到神秘而虚幻的宿命论深渊中。
在康德与黑格尔的卓越继承者——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并非基于抽象的观念,而在于其事实实在的、真切的社会关系的统合。随着20世纪之交西方现代哲学的跨时代转换,语言论的基本立场与框架仍然紧密地围绕着“实在”范畴的核心义理。在我国,作为受西学东渐之深刻影响的新儒学研究路径则果断从传统的形而上学束缚中拓展到鲜活的社会问题征候。这在梁漱溟的“生活”儒学、胡适对儒学的实用主义改造、以及当代大陆新儒学的文化研究身份与旅美儒家学者的中西文化共通共荣的艰难理想中显露无遗。现代哲学回归到社会现实的原初定位,这种社会实在论的发展线索进一步体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哲学的更宽泛框架中。在社会理论中,韦伯将理性定位于社会群体的文化传统与精神特质,而涂尔干则深入到群体意识的心理秉性。通过对涂尔干社会思想的专门发展,法国思想家哈布瓦赫(M.Halbwachs)提出历史的实质在于其社会记忆,即群体思维的鲜活的观念系统[4]38。尽管西方哲学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欧美之别(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对垒),在哲学体系中也存在着科学哲学、分析哲学、文化哲学与心理哲学的不同研究趋向,但“实在”概念作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各取一极的解释关键词却衍生出更复杂的争议性问题。这在海德格尔的存有学与普特南的新实用主义等有重大影响力的哲学学说中鲜明表现出来。
实在论作为正反两面都构成为西方哲学的关键概念,体现为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主线。在现代大陆哲学中,海德格尔不渝地追寻存在的终极意义,其形而上实在论美名昭著。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乃是第一哲学范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作为在黑格尔意义上人类本性最本质的语言是存在的核心表征。法国思想家布拉什则针对社会政治地理直接指出社会实在论的实质:“自然提供各种程度的可能性,人在其中挑选。地理提供一块底布,人在上面绘制自己的画图。”[5]44在英美哲学中,以维特根斯坦领航的逻辑经验主义思潮则将经验的最后基础建立在外在世界的本源上;美国实用主义从皮尔士一开始就坚持实在论的基本立场。从皮尔士的形而上实在论、詹姆斯的彻底经验论、杜威的社会实在论,一直到新实用主义的各种实在论理论形态(甚至于罗蒂的反实在论也基于其弱化的物理主义原则),实在论都是其中的主导理论。普特南对实在论要义的规定作如此规定:“世界如其所是地独立于任何描述者的旨趣。”[6]5-6“符号并不内在地对应于对象,也不独立于其使用的情景与使用者。但是,一群使用者以特定方式实际运用的符号在使用者的概念框架中可以对应于具体的对象。‘对象’依存于概念框架。在我们不同的描述图式中,世界被分割为对象集。正因为对象与符号一样地内生于描述图式,我们才能说什么对应着什么。”[7]52在普特南看来,对象(客体)独立于概念框架或观念图式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表明那就是纯粹的语言化或所谓康德式的概念图式;有一些事实仍然有待于我们的发掘与辨别,但是,“人们总是处于特定的言谈方式、语言、概念框架中。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事实’、‘存在’或‘客体’都一样地受制于实在本身(Reality Itself)”[8]36。
二、孟子的社会实在论:“天人之际”
实在论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相较之西方而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中国文字主体的汉字本于“济写实之穷”(朱宗莱语)。“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则谓之字”(《说文解字叙》)。进一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辞》)。其中的社会实在论思路赫显。孟子思想(即孟子学),“在当代儒学运动中,不但是核心的课题,而且它主要是以‘心性之学’的义理性格,进一步被诠释为一套有别于西方的‘道德形上学’”。孟子“述仲尼之意”,从内(心)到(身)外推进了儒学内圣到外王的辩证社会观体系。孟子的社会实在论有着鲜明的逻辑路径,并彰显为“天-人-民-天下”的体系架构。其中,人与民构成为其中的核心环节。
“在儒学中,‘天’这个观念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天’不仅是人之道德实践的根源 ,更是人得以投射到存在,彰显一切存有物意义及价值的根源,在观念地位上,它其实与西方哲学的‘存有’(sein being)一样。”[9]97,154尊天有命的自然主义社会观早在《易经》中就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阐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传》)。这种道德和顺与穷理尽性体现了从“天乾地坤”、“君子自强”、“家国昌盛”以至“天下太平”的朴素辩证法发展要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创儒学,人道以天道为基础、以仁义为核心。孔子之后,诸子百家争鸣,孟子将儒家的“仁心仁术”延绵推演到总体化社会的维度,从深度广度两方面发展了早期儒学的基本思想。就孟子看来,“天”是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表征。“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孟子·梁惠王下》)。即,遵循客观规律才能成就事业,以至保国、保天下。“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对于个人而言,要迎合客观的法则及其社会发展的趋向要求,“若夫成功,则天也”、“其所以行所以止,则固有天命”(《孟子·公孙丑下》)。牟宗三后来对于“天”的界说是:“天是一超越的实体,此则纯以义理言者……在事天上,‘事’字之意义须完全转化为自道德实践上体证天之所以为天,而即如其所体证,而自绝对价值上尊奉之。”[10]136在这里,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完全被康德的超验实在论所涵摄。这种超验实在论后来在西学中演变为影响甚大的形而上实在论,一如皮尔士的经典实用主义实在论理路。傅佩荣对孟子的天道观作了如下的诠释:“孟子并为强调天之主动的主宰性格,反而倾向于把天当做遍在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客观法则:‘道’或‘势’。”[11]27于孟子的人格化的天地理念,其实在论基础是十分鲜明的。
在古代哲学的本体论进路与孔子“天道远,人道弥”的意境下,中国古代儒学比之西方哲学更注重人本的情怀与思考。在天道之后,人道凸显。对于人道,精神义气成为道德教化的焦点。但儒家强调“礼乐”教化,礼与乐却皆是基于天地的结构化功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记·乐论》)。在孟子看来,人不但是天地的精髓,更始终是作为社会的本体与基础,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作为自然生命体的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人与其他动物或禽兽之间的差异在于仁义伦理。首先是基于自然法则的“诚”,所谓“诚外无物”。《中庸》强调“至诚尽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自此,“诚意”成为八纲目的重要一环。孟子秉持了“诚意”的基础功用,而更为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即“正心”的进一步作用。在孟子而言,“仁者爱人”:“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存心养性”又是修身的基础本身,体现了人生的自然发展规则。从辩证的角度看,反过来,经由尽心-知性,最终可以知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伦理内在地具有客观的人本基础时,现实社会中人们可能看到了作为群体社会的自然进化史实,对于很多伦理的形式说教则被讽之主观主义、理想主义的口实,而将这种学说幕后最基本的客观基础忽视了,进而囿于繁衍生息的狭隘框架与视角。但很显然,“一旦人们开始欺诈,德性就随之溃散,协作也戛然而止了”[12]82-83。这一如孟子的反身至诚,修身治国,以及其他一系列富有浓郁道德主义的各种理论。但无论怎么从天道到人道的跨越与转换,孟子继于孔子的“天人合一”观则充溢着实在论的基本义理。后儒中,从梁漱溟到杨国荣,他们对孟子的理性主义与主观主义评述尽管有矫枉过正的本旨,但其过犹不及的趋向则有自反自娱的嫌疑。而在港台新儒学中,唐君毅、牟宗三与徐复观三人对中国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的大力弘扬也同样蕴含了缺失社会实在论的较鲜明立场。
三、孟子的社会实在论:性善论与道德客观主义
孟子以“性善论”为儒学的内在主义取向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基于道德伦理的人性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广泛的阐述。在《道德经》中,对于私欲的压制成为反自然主义的宿命论的基本观点。“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第十九章》)。墨家学派着重于“非攻”、“兼爱”(“爱无差等”的平等主义)。对于儒家,孔子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这种观念后来构成了康德道德律的第一“黄金”律则,但儒家的消极自由观也在其中显露无遗。在之后的宋明理学中,儒家第一要义的“义利之辨”转换为理欲之分。朱熹强调“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力行》)。而戴震受孟子的深刻影响则呼吁“理者存乎欲者”(《孟子字义疏证》)。在孟子看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孟子·公孙丑上》)。人生来就具有契合于自然演化规则的仁心善心。孟子:“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的性善论被后来的王阳明所发扬光大(“良知良能”),在现代则被梁漱溟提升为向上与温情的两大中国民族精神。
在内在道德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通过诚意、正心,再到修身与仁政王道,孟子的伦理观体现为一种卓绝的道德客观主义路径,并始终应承于其社会实在论的基本立场。朱熹总结道:“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论语集注》)。孟子“善推其所为而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梁惠王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观的方法论层面上,孟子不只是采用“从小处入手”的语义上升策略(类似于经验主义的还原论,为社会学中经典的实证方法),他同时也运用了横向类比以及“从大处着眼”的整体主义语义下降方法。前者如“与少乐乐,与众乐乐”,以致“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后者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 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在中国现代化的转换中,传统的礼制因其僵化的意识形态扭曲与封建落后的社会功能而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与西方式的积极自由观以及在资本体制下所衍生的利益博弈普泛规则性局势相对照,孟子的性善论以及儒学的义利观也受到了不应有的实用式曲解、甚至于激烈的批评。但是,经济学家的观念是:“人们必须共存地生活,为此,他们就必须设立社会规则与社会体制”[13]208。在社会学家看来,“鼓励互惠与劝阻欺骗的规则建基于人们善或恶之间的自然倾向。”[14]158-159孟子的性善论是道德客观主义的典范式理论,于其磅礴的社会思想影响与教化功用暂且不论,其基于社会实在论的严密逻辑理路与稳固的学理基础诚然是中国哲学的辉煌奉献。外国学者马克如是中肯地评价道,孟子性善说及其仁义理论的核心是“对于心灵之自然特征的解释及其教化过程中的作用”。[15]103
四、孟子社会实在论:民本民主观与仁政天下的至上理想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在社会实在论层面,作为类种的人群即“民”构成了其中的关键议题。在当代社会理论中,民主是所有学派与思潮都不能规避的基础范畴。新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指出,民主是“解决人类问题的知性之充分发挥的先决条件”[16]1671。于中国哲学而言,“对‘民’的关注,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另一重要之点。相对于以人性理论为出发点的形上进路,关于‘民’的讨论更多地涉及现实的社会政治立场”[17]161。早在《尚书》中就有如此表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虞书·大禹谟》)。在孟子思想中,民本理论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并对后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古代社会中被统治阶级的人民被置于社会首要地位,而视统治阶级为人民的辅佐,这无疑是孟子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宣言。
在孟子看来,王霸之道殊分,基于德治与仁政的王道才是真正的社会律则。平天下(“王”)理想的实现,其秘诀正在于“仁民爱物”(《 孟子·尽心上》)。仁政的第一步就是对于民众疾苦的关心与解决,“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与民同乐、替民分忧解难,构成社会治理的内在机制,“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孟子的社会观中,社会不惟是国土与地理的自然演进,其核心在于民众的力量与和顺的道德状况,推行“仁政”,天下太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这是传统儒学的完整理想。在亚圣孟子的思想中,从民众的基础本位到社会的实在建制,其社会实在论的哲学理念昭然精深。在南怀瑾看来,孟子的王道政治可谓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高理想,即“以大同世界为目标的王道与仁政”。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推行仁义,讲求仁政,期望太平,人民的日子过得好。”在道德的宏大框架中,孟子王道仁政的基石建立在法治、财政、经建等具体的社会制度上,“孟子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罚,财政上做到了薄税敛,农业建设上做到了增加生产,便可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然后进一步再提高教育水平”[18]192,140,136-137。在孔子的思想中,“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在社会治理上,孔子言:“谨权量,审法度,修费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孟子则进一步考究与总结了社会政治的经济实在基础。“夫。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孟子·梁惠王下》)。“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很显然,仁政取决于经界,而经济则服从客观的自然法则。“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强调国家治理的“仁政”,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治理路径:王道与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措施并非有违于法治,而是基于普适道德律则的“省刑罚”、“不嗜杀人”、“及是时明其政刑”与反对“无罪而就死地”。仁政的实在基础在于“薄税敛,深耕易耨”,这样才能自然地达至“仁者无敌”、乃至天下天平。“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所有这些仁政的措施与理念对于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都具有振聋发聩的历史意义,而孟子的社会实在论思想在这里也体现了最高的理想诉求与古代唯物主义的至高成就。
五、结束语: 孟子社会实在论思想的历史意义与时代启示
基于“天-地-人”框架基础的儒家社会观,体现在孟子的“人-家-民-国-天下”路径中。也许,始于与基于“天道”的社会实在论思想在古代哲学中尚存在着神秘主义、甚至客观唯心主义的浓郁色彩。就算在当代社会问题中,自然与社会的两分界说也一样有着难以辨证的复杂纠纷。“从自然向文化的转移不可能是一种从事实向价值的转移,因为自然永远已经是一种价值的条件。…像文化一样,自然的概念模棱两可地在描述性与标准化之间徘徊。”[19]85在孟子的实在论中,“天道”观承载着主观化、价值化的鲜明理念,这也为后世的主观主义与心理主义批评铺就了研究的旨趣与空间。
尽管没能创建起系统的说明体系,但散见于孟子言论中的诸多片段却展示了清晰的社会人本网络,这种网络依托或被统筹于客观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的道德规范中。直至当代的社会行动理论中,社会行动仍然被视为受制于规则的有意义的行为,所有人类的社会行为都依据事实本身而受制于既定的规则,规则与行动之间体现了内在的合理性[20]52。孟子的社会观也并非如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21]78作为具体社会角色的个人始终是孟子思想指向社会的基石。刘述先与墨子刻对于传统儒学“家天下”之封建自然经济模式的批判,无疑有着跨时代的比较意蕴,但是明清以迄的停滞与封闭史实远远超越了春秋义理,其古薄厚今的倾向也只能是哀叹式的悔愿,更何况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内在地有缘于其家庭关系的分崩离析。从社会理论上说,孟子的“家”位并非其社会群系框架的本位,而是实在地构成为其中的辩证环节:“推己及人,由家而国”。
在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原始社会描摹中,“一种强有力的民主精神弥漫于整个机体之中”[22]139。孟子的民本思想无疑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集大成精髓,也如胡适的评价,它是中国民主精神与体制的最大渊源与光辉典范。从民本到民治、再到现代民主,是人类历史的漫长演进。“民主指涉一个社会中的交往的制度化过程,通过这种民主指涉,参与者公开地思考并作出由集体负责的决定。”[23]288但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能孕育民本的至世宣言,孟子亦不愧为现代民主理论的伟大先驱。杜维明曾将民本与民主辨别开来,指出了内圣开出外王的社会困境。诚然,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孟子的社会理念以及“平天下”的大同理想已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情境。现代社会行动的高度复杂化使得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在吉登斯风险社会的意义上,“21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被拖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24]3。这也反映在民主理论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的总体面貌上,中国式儒家民主理念必然构成为地域性当下性民主的身份源泉,并随着海纳百川式的全球文化交融而不断获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与时共进。
“在经济、社会、环境与文化及群体相互依赖的当今世界情势下中,我们也应当在全球社会的总体局势中反思自省。”[25]69对于孟子的思想亦然。杜维明曾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奇迹有着这样的总结:“尽管全球化趋向从一开始就定位于经济与地理政治的角度,但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却持续展现着强有力的影响。”[26]265民主、科学等诸多概念来自于西方,但从其内容上说,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在自古以来的中华文化遍地生根,关于人权的深广内容及核心精神早在孔孟著述及历史文献中无处不提。
“在梁漱溟看来,儒家不仅不能只是被看作一些人们行为的道德箴言,而且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体系。从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人们心中的实际地位而言,儒家无疑是终极关怀层面的信仰。”[27]214几十年的近代化与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历程,儒家思想的命运一波三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核心的儒学在自我批判与海纳百川的进程中浴火重生。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格局中,建基于社会实在论的广义政治文明(包涵生态义理)形成为其中的统摄性的制度框架与保障。内在于孟学的、彰显以王道仁政的社会实在论理论渊源不愧为中国传统思想、乃至世界社会政治理论的重大成就与珍贵遗产!一如唐君毅所言,孟子实乃“中国民本民主之政治思想之宗师”[28]213。
[参考文献]
[1]涂纪亮.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
[3]黑格尔.小逻辑(第二版)[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Maurice Halbwachs.OnCollectiveMemory[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5]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M].杨祖功,王大东.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Hilary Putnam.TheThreefoldCord:Mind,Body,andWorld[M].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
[7]Hilary Putnam.Reason,Truth,andHistor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8]Hilary Putnam.TheManyFacesofRealism:ThePaulCarusLectures[M].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36.
[9]袁保新.从海德格尔、老子、孟子到现代新儒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10]牟宗三.圆善论[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
[11]傅佩荣.孟子天论研究[J].哲学与文化,1984,(11).
[12]Michael Ruse.Evolutionaryethicsandthesearchforpredecessors:Kant,Hume,andallthewaybacktoAristotle? [J].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 Autumn, 1990 ,(8).
[13]James M. Buchanan.WhatShouldEconomistsDo? [M].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79.
[14]Peter Singer.TheExpandingCircle:EthicsandSociobiology[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Meridian Books,1982.
[15]Mark Csikszentmihalyi.MaterialVirtue:EthicsandtheBodyinEarlyChina[M]. Brill, 2004.
[16]Hilary Putnam.AReconsiderationofDeweyanDemocracy[J].The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1990 ,(63).
[17]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8]南怀瑾.孟子旁通[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9]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0]Peter Winch,TheIdeaofaSocialScience[M]. London: Routledge,1962.
[21]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2]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3]詹姆斯·博曼.社会科学的新哲学[M].李霞,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4]柯恩-达努奇.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M].吴波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5]Karen Stohr and Christopher Heath Wellman.RecentWorkonVirtueEthics[J].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002,(39).
[26]Tu Wei-Ming.MultipleModernities:APreliminaryInquiryintotheImplicationsofEastAsianModernity.LawrenceE.HarrisonandSamuelP.Huntingtoneds[M].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Basic Books,2002.
[27]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8]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第一[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责任编辑陶有浩)
Mencius Thought on Social Realism
ZOU Shunhong
(SchoolofLawScience,TonglingUniversity,Tongling244061,China)
Abstract:After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in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nfucianism became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Han dynasty, the social problem system established hence constituted its ontology base of social epistemology. After Confucius, Mencius, the second saint, bas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e and man on people’s life and its social system in the totally new times, his social epistemology contained the dialectical thought and philosophical concern, which contributed considerably to the world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as wel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ga-scienc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among heaven, human, people, society and category still remain to be the main theme of scientific dispute, philosophical dispute and civilization confrontation. Mencius’ thought on social realism is the historical treasure and precious inheritance left by Chinese ancient sages for the whole world.
Key words:Confucianism; Mencius’ theory; social realism; democratic politics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6)01-0057-06
[作者简介]邹顺宏(1968-),男,湖南祁东人,铜陵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收稿日期]2015-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