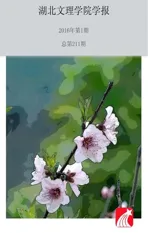从舞台空间形态看契诃夫《海鸥》的创新性
2016-03-16柴德闯朱伟华
柴德闯,朱伟华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从舞台空间形态看契诃夫《海鸥》的创新性
柴德闯,朱伟华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摘要:《海鸥》是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里程碑,创新的内容不仅仅存在于文本话语空间,同样也存在于舞台空间。舞台空间的创新是契诃夫戏剧创新的基础。通过舞台空间的创新性分析,并将之与文本话语空间相结合,才能完整地解释契诃夫戏剧创作中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朱伟华(1954— ),男,江苏无锡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西戏剧形态。
关键词:契诃夫;《海鸥》;舞台空间;戏剧创作
四幕戏剧《海鸥》可以说是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里程碑,不仅是因为这部剧作文本内容上的创新性,同时也包括舞台空间的创新性。舞台空间即剧作家为剧中人物活动所创作的活动空间。《海鸥》这部剧成名是因为这部剧明显的创新,即与传统戏剧的区别十分明显。《海鸥》的首演是失败的,观众认为这不是一部真正的戏剧,而随后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重演,不仅让《海鸥》重获新生,也使莫斯科艺术剧院获得了新生,莫斯科艺术剧院也因此用一只飞翔的海鸥作为院徽,这是世界戏剧史上第一个靠一部戏剧拯救了一个剧院。契诃夫通过对传统戏剧模式的大量摒弃以及新形式的运用,使《海鸥》成为现代戏剧的先驱之作。这部剧淡化了外部冲突(即人与人的冲突),并不是将戏剧冲突排除在戏剧之外,而是将冲突带入内部冲突(即人物自我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之内;放弃了强化冲突的因素,而采用隐喻的对话来表现思想冲突,在人物语言上运用更多的隐喻,在情节设置上抛弃“三一律”等等。[1]在舞台设置上也存在鲜明的创新。纵观契诃夫戏剧可以发现,他的剧本中的舞台空间不像传统戏剧更多的只是提供故事发生空间,也不像现代主义戏剧其舞台空间具有更多的抽象性,而是更好地与文本话语空间相结合,具有语言所不能代替的延伸性。《海鸥》就是其契诃夫式舞台空间的成熟之作,是一部讲述戏剧爱好者或者说写戏剧的人试图创作戏剧新形式的故事,就像契诃夫的自我独白一样,是他对自己戏剧改革的一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看法。
我们通过细读剧本可以发现四幕剧本发生在四个不同的地点,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位置都具有边缘性以及延伸性。第一幕发生在陆地与湖水相接之地;第二幕发生在房子与湖之间的树下;第三幕在餐室;第四幕发生在客厅。三、四幕看似在室内,其实不然,“左右有门”[2]146、“左右各有门通到邻室,正面,玻璃门,通凉台”[2]163这些都表明其发生地不仅仅局限在室内固定的地点,而是延伸到室外,是为了更好地契合剧中人物的话语空间。通过舞台空间的设置可以更好地研究契诃夫戏剧创新的特点。
一、第一、二幕:湖边、树下——开放空间的外展与边缘性
《海鸥》发生在湖边的戏共两幕,即第一、二幕。第一幕发生在花园与湖边的舞台边,第二幕发生在房子与湖边的树下。
第一幕中剧内舞台是没有背景的,而是将湖水、天空当作背景,这种将舞台空间近乎无限延伸的开放性空间设置在传统剧作中是不存在的,连剧中人物特里波列夫自己都说“我是反对目前这样的戏剧的……现代的舞台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和一种格式……在一间缺一面墙的屋子里”[2]110、“应当寻求另外一些形式”[2]111,这不仅仅是为剧中人自己设置的舞台进行的辩护,同样也是契诃夫通过剧中人为自己创作的《海鸥》的舞台空间进行的辩护。通过第一幕中横断着园径的业余舞台的设置可以看出特里波列夫是想要斩断旧形式,希望可以创造新的戏剧形式,不仅在文本话语空间,也在舞台设置上。而阿尔卡基娜则由于身份的原因,极度维护传统戏剧的舞台与文本内容,当看到特里波列夫几乎什么都没有的舞台时发出了“有点颓废派的味道”[2]119的评价。这让她忽略了特里波列夫所设定的开放性舞台空间结构,这是背离传统舞台设置的,开放性的舞台空间设定让外展性的思维得以活跃出现,这是阿尔卡基娜无法理解的。同时她也没有注意到《海鸥》中十分重要的一段独白,妮娜的独白就像是契诃夫自己的戏剧宣言一样。“到现在,大地已经有千万年不再负荷着任何一个活的东西了……”[2]118、“……在我胜利以后,物质和精神将会融化成为完美和谐的议题,而宇宙的自由将会开始统治一切……”[2]119,这是新戏剧形式的宣言,也是契诃夫戏剧创作的意图。阿尔卡基娜在看剧时只关注到了舞台空间的设置“有硫磺的味道……”[2]120、“是为了制造舞台效果的”[2]120,就是因为特里波列夫没有按照传统的戏剧舞台空间进行设置,从而引起了阿尔卡基娜的反对,这也是与人物以后的对话相吻合的。契诃夫将剧中的舞台不是放在传统的室内或放在空阔的室外环境,而是放在了湖边与陆地连接的边缘之地,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演出也许会出现两种结果,接受或者批判,因为这种形式是与传统戏剧背道而驰的。阿尔卡基娜是特里波列夫的母亲,同样也是著名的话剧演员,她所代表的就是传统戏剧的力量。当她看到特里波列夫的舞台空间及对白后表达了她的观点:“他不是自以为是在给艺术创立新形式,创立一个新纪元吗?这一点也谈不上新形式,我倒认为这是一种很坏的倾向”[2]121无疑宣判了特里波列夫戏剧创作的死刑。因为思想的特立独行,使得特里波列夫处于文学世界的边缘,也让他逃离众人,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边缘。契诃夫通过开放性舞台空间的设置,将剧中人物的内心写照印在了舞台上,让观众感受到了特里波列夫思想的边缘性与自身存在的孤独感。这是契诃夫自我的写照,他的戏剧诞生于传统戏剧之中,却背离了传统戏剧的传统,也就会遭到传统戏剧的坚决反对,这也是契诃夫选择陆地与湖边这种边缘性空间的原因。他知道他的戏剧创作会引起强烈的反对。第一幕舞台空间的设置不仅可以更好地契合特里波列夫的心态和地位,同样也更形象地表现了契诃夫戏剧创作时的心态。
第二幕发生在“一座带有宽大凉台的房子,左边一个湖……一颗老菩提树下”[2]129,这一幕中人物对话基本都是在树下的凳子周围进行。对话的内容看似与第一幕基本没有任何的联系,谈论年龄、书目、生活琐事等等,完全脱离了第一幕谈论戏剧的范围,主题似乎偏离到生活琐事当中去了。其实不然,故事发生在“一棵老菩提树下”,在这里,老菩提树也是开放性的舞台空间的代指。代表的是整个俄罗斯的大环境,即包括社会环境,也包括文学环境。剧中人物看似谈论生活琐事,家长里短,其实代表的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的整体态度,他们都是在传统土壤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创作,吸收着传统文学的养分,没有任何的新颖之处,人们笼罩在传统文学的关怀之下生活,安于现状,享受着传统文学给予的滋润。阿尔卡基娜、索林、多尔恩,他们都是在现实环境中接受着传统思想的哺育,虚度着生活,空想着未来,只有一个人除外——特里波列夫,他生活在整个大环境的边缘,使自己具有了边缘性。他手里拿着刚被自己打死的海鸥,放在了树下,“我不久就会照着这个样子打死自己的”[2]137,看似一句玩笑话,其实是在控诉自己在传统的滋养下已经无法生存,无法释放自己的想法,控诉着文学环境的压抑和排斥,控诉着压抑的“老菩提树”,将自己排挤在生活的边缘。“这只海鸥无疑也一定是一个象征了……我太单纯了,不能了解你”[2]138,妮娜用一种传统观念来看特里波列夫的创作,也保持着对特里波列夫的否定。他自己说“突然发现这片湖水已经干了或者已经渗进地下去了。”[2]138湖水干了代表着特里波列夫的生命力流失、活力丧失以及养分缺失的写照,不就是特里波列夫在说自己思想的干枯,被传统思想压榨的无法生存了吗?彻底失望的特里波列夫痛苦地说“人家不喜欢我的剧本,你瞧不起我的才能……他(特里果林)像哈姆莱特那样走路……”[2]138其实就是在控诉着自己的戏剧创新受到了整个环境的排斥,他的结局注定是要失败的,注定是要被禁锢在这片空间,无法逃离。而在特里波列夫痛苦的时候,妮娜和特里果林却享受着传统环境带给他们的美好梦境,一同畅想着未来,因为他们没有发生改变,一直在追随传统。湖边的树就是文学环境的浓缩体,而近在咫尺的湖象征着无限的创作空间,代表着特里波列夫的海鸥却没有能力飞向无限的天空,死在了树下,死在了传统思想的禁锢之下,死在了传统文学的笔锋之下。
我们可以看出,契诃夫创作的边缘性舞台空间以及其所引申出来开放性思维空间,就是舞台空间是一种新的形式,是人物内心的一种写照,也是人物地位的一种体现,他的这种舞台空间设定将特里波列夫的思想以及其所受到的压抑完整地体现出来。不被文学环境所接受,只能游离在边缘。这种空间只有两个结果:也许可以屹立不倒展翅高飞,也许会石沉大海坠入深渊。
二、第三、四幕:餐厅、书房——封闭空间的压抑与内缩性
第三幕中的舞台空间并不复杂,就是餐室,左右有门,一座碗橱,一座药橱,特里果林在吃饭。餐室是内部空间,而前两幕则是外部空间,在第二幕的结尾处阿尔卡基娜在窗口出现对着身处花坛中的特里果林说“我们不走啦”[2]145就是由外部空间向内部空间的过渡。这句看似没有缘由的话其实就是因为特里波列夫的原因。看似感情纠葛,实则是因为特里波列夫写的剧本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因为特里波列夫创作的剧本脱离了传统戏剧的框架,阿尔卡基娜害怕走向新的戏剧形式,从而将自己留在传统文学的城堡里,才会说出“我们不走啦”!由此引出特里波列夫生存与思想空间的内缩。特里果林在餐厅吃饭,并与玛莎交流,特里果林占据着整个餐室,也就是说传统空间依然占据着整个空间,并由外部空间逐渐向内部空间压缩特里波列夫的思想空间,是对特里波列夫的持续性压抑,这种连续性的压抑造成了特里波列夫逐渐的自我内缩。餐室中有一座药橱,在“每一枪都要发射”[3]的契诃夫笔下,是有深刻用意的。当特里波列夫因为压力,因为绝望而自杀未遂时,他的母亲打开药橱为他准备换药,而且还劝他不要再自杀,这似乎在表达了代表传统戏剧的母亲在慢慢地接受特里波列夫所代表的新的戏剧形式,就像打开了一扇可以供他飞翔的窗口时,却又因为特里波列夫对代表传统文学的特里果林的冲击和挑战而破裂。“你们这些死守着腐朽的成规的人,你们在艺术上垄断了头等地位,你们认为无论什么,凡不是你们所做出来的都不合法,都不真实,你们压制、践踏其余的一切!”[2]154这是对环境的控诉以及不满,是对特里果林的不满,也是对传统文化陈旧思想的不满。“绷带待会让大夫给我缠吧”[2]156特里波列夫自己关掉了投向传统文学的窗口,关掉了疗伤的药橱,代表了他没有妥协,自己关掉了传统文学丢过来的橄榄枝,关掉了妥协可以飞翔在传统文学这棵大树下的窗口。当特里波列夫承受住了来自外部世界压力的同时,他感受到了所有人对他创作的不理解,慢慢地让他封闭进了自己的世界。
第四幕发生在“左右各有门通向邻室,正面,玻璃门,通凉台”[2]163的书房里,这一幕开始就是日常生活的琐事开端,就像第二幕的树下一样,而且与第三幕间隔了两年。在对话中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特里波列夫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不安于现状,总试图尝试新的形式,貌似被生活改变了自己。当母亲与其他人玩牌时,他走出了房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被压抑,被无视,不就像被排挤的新形式吗?到这里我们才发现,特里波列夫依然格格不入,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将自己放逐在大环境的浪潮之外。当他回到书房打开窗子说“多么黑呀!我不知道我心里为什么这样不安宁”[2]177来控诉生活,控诉文学对他造成的压抑,希望寻找新的出口时,他的母亲却说“关上窗子,你放进一阵阵的过堂风来了”[2]177。多么可笑的对话,竟然将特里波列夫自认为的新的文学形式当成一阵可有可无却破坏现实环境的无形的风,从而将特里波列夫彻底地摧毁。“我讲过那么多的新形式,可是我觉得自己现在却在一点一点地掉到老套子里去了……在特里果林,写作很方便的,他有一定的格式……多么苦恼啊!”[2]177-178不正是阿尔卡基娜和特里果林在提醒特里波列夫:不要试图改变。特里波列夫在窗口还有另外一种隐喻,两年内,他有了一些名气与成就,却发现自己没有摆脱传统文学的禁锢,没有走出这座充满框架的城堡,一直被束缚在条条框框之中。当他再一次试图从窗口逃离,打破框架进行尝试时又一次被打回原形。“我依然在一些梦幻和形象的混沌世界里挣扎着……我没有信心,我不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2]182,在禁锢着思想的城堡里,一扇窗口似乎无法解脱特里波列夫的灵魂,也就形成了特里波列夫的死亡。在第四幕快结束时特里波列夫从窗口发现了妮娜,以为希望还在,还有摆脱传统的可能,而当妮娜从玻璃门跑出去之后,特里波列夫才真正地反应过来,原来他始终没有脱离传统,始终没有摆脱环境的压抑,没能打开一扇新的窗口,无法像妮娜一样勇敢地逃出窗口,从而失去了自我,走向了毁灭。就像第二幕在树下特里波列夫预言的一样,他选择了自杀来摆脱旧形式。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句话说明人的眼睛是人内心世界的反馈。同样,在契诃夫创作的《海鸥》里,窗口也代表着一条路,一条崭新道路的出口,一条在压抑的封闭空间中自救的路,他诉求着对待戏剧创新时人们应该客观地保留一丝空间给予独特的舞台空间,体会窗口之外广阔的思想意境。
三、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两重空间与两代人的生命轨迹
通过对剧本的舞台空间分析可以看出,每一幕的舞台空间设定都是具有极度契合文本空间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特里波列夫的内心变化以及周围环境的改变,《海鸥》的舞台空间设定是逐渐内缩的。
四幕空间是由室外到室内所代表的外部空间向内部空间逐渐内缩的,第一幕发生在湖边,特里波列夫和阿尔卡基娜两代人的不同思想在广阔的时空中碰撞,代表着传统思想的阿尔卡基娜和特里果林占领着大多数空间,却也能给特里波列夫所代表的新思想可以发挥的空间。特里波列夫可以在广阔的空间中演绎着自己的思想,他并不是在传统思想的滋润下成长,而是在大自然中独立成长,吸收着大自然的养分。此时的阿尔卡基娜也像正常母亲一样既包容也指责自己的孩子,在这一幕中特里波列夫的思想个性很鲜明。到了第二幕,剧情开展发生在湖边的树下,空间被压缩,思想空间也受到了压抑。“树”就是传统思想的缩影,特里波列夫已经被笼罩在传统思想之下,特里果林和阿尔卡基娜所占据的主流地位传统思想和特里波列夫所代表的新思想开始交锋,两代人开始产生真正的分歧,阿尔卡基娜希望特里波列夫回归传统,享受传统文学的滋养。环境对特里波列夫的压抑开始出现,他与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联系逐渐被传统思想所侵蚀,基本上已经无法从大自然中汲取养分,开始颓废,思想个性开始减弱。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压抑,特里波列夫开始寻求庇护,第三幕的场景也就变为了室内的客厅,虽然故事发生地转移到室内,但也存在着与外部空间联系的窗口。客厅虽然是室内,却也还是人与人交流的地方,还存在着思想交流的可能,空间被压缩禁锢得很小。在禁锢的空间里,特里波列夫与阿尔卡基娜的对话依然在阐述着自己的新思想,希望可以得到认可,却引发了新一轮的交锋,阿尔卡基娜的角色发生变化,禁锢特里波列夫的思想,用自己看似权威的传统左右着特里波列夫的世界。特里波列夫在交锋中逐渐退缩,他的思想个性正在加快褪化。第四幕与第三幕之间间隔两年,这里的时间压缩并不是单纯的略过两年时间,而是将特里波列夫与阿尔卡基娜所代表的新思想和传统思想之间的争论放在了幕后,这也符合契诃夫戏剧喜欢淡化人物冲突,注重人物内在冲突的特点,也是与第四幕的舞台空间设定的契合。第四幕发生在由客厅改为的书房,客厅是半开放的空间,而书房则完全是私人化的空间缩影。这时的特里波列夫已经不再是第一幕中思想个性鲜明的角色,而是变得模糊,失去了鲜明的个性,却也不是传统思想的载体,他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狭小的空间内。阿尔卡基娜的回归是宣告特里波列夫失败的讯号,他是被传统思想彻底禁锢在封闭的空间中。书房中的特里波列夫一直做着思想的斗争,新的思想一直在试图反抗,这也是书房中依然存在着与外部空间连接的玻璃门的原因。妮娜的随波逐流也让特里波列夫彻底关上了玻璃门,将自己彻彻底底地封闭在自己狭小的私人空间,并被传统思想压得彻底崩溃,最终走向死亡。
《海鸥》四幕剧从外部空间向内部空间的逐渐内缩,从外部空间中的大自然到内部空间的书房,这是特里波列夫的人生轨迹,也是新生事物所要必须经历的过程,是阿尔卡基娜所代表的传统文学对新生事物的态度,同样也是新生事物思想的变化,是思想受到压抑必然产生的结果。由外向内,是特里波列夫个性消失、生机消散的逐渐外显。思想释放的空间越来越小,致使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就像特里波列夫杀死的海鸥一样,没有了可以汲取养分的天空,被压抑在传统思想的禁锢之下,只能走向毁灭。这种逐渐内缩的舞台空间设置极度符合剧本中人物内心的变化过程以及契诃夫对戏剧创新的担忧。
戏剧是一个需要舞台实现的艺术,戏剧舞台空间是体现戏剧本质的载体。《海鸥》的舞台空间是真正与文本话语空间相吻合的,是契诃夫戏剧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忽略的。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单纯研究文本话语空间是无法对《海鸥》进行全面解读的,需要通过舞台空间与话语空间的结合才能完成对其的创新性研究。同时可以看出通过对剧本舞台空间的创新才是契诃夫戏剧创新性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柴德闯,朱伟华.契诃夫戏剧研究20年——20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文献述评[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5(6):21-26.
[2]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M].焦菊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3]张维嘉.《樱桃园》中的空间[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3):60-64.
[4]黑格尔.美学:第三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叶尔米洛夫.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M].张守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
[6]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夏波.如何认识契诃夫喜剧中的喜剧性[J].戏剧,2014(2):26-34.
(责任编辑:倪向阳)
Innovation of Seagulls by Chekhov from Perspective of Stage Space Form
CHAI Dechuang, ZHU Wei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Seagullsis a milestone in the creation of Chekhov’s drama. The content of the innovation is not only in the discourse space, but also in the stage space. The innovation of stage space is the basis of Chekhov’s drama innovation. Through the innov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ge space, and combining it with the space of the text discourse, we can complete the innovation and uniqueness of Chekhov’s drama creation.
Key words:Chekhov;Seagulls; Stage space; Drama writing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6)01-0058-04
作者简介:柴德闯(1990— ),男,山东潍坊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7-03;
修订日期:2015-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