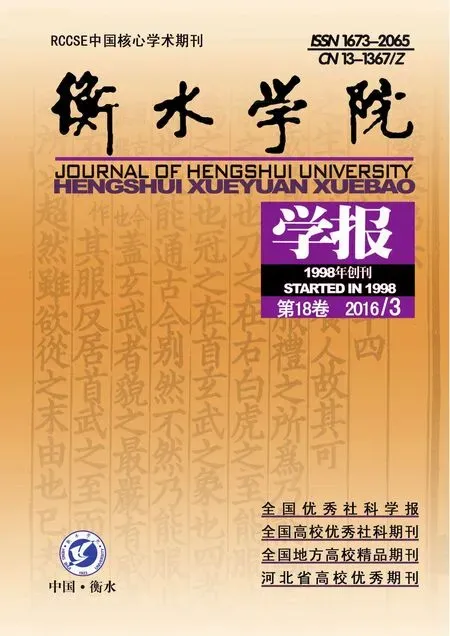“外儒内法”政策形成的内在理路与外部原因
2016-03-16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杨 喜(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外儒内法”政策形成的内在理路与外部原因
杨 喜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摘 要:“外儒内法”政策是汉武至汉宣时期的统治政策,其形成与确立是在顺应儒学转变的趋势下,统治者的有意作为。儒学转变的趋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者,由于礼与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相通,使得出现了礼、法合流的趋势;二者,因为儒家具有兼容百家的特性,使得最终出现折中百家的杂家化趋势。
关键词:王道;霸道;荀子;外儒内法;儒学
秦祚短促,世人多以不行仁政,酷法严苛而亡。前汉继秦而兴,若以统治思想之主流而论,大抵可分为三个时期:1) 自汉高而至文景;2) 由汉武延至汉宣;3) 从汉元直至王莽。汉初承秦之弊,务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推行黄老思想,以巩固初生政权,渐次富国强兵为己务。逮至汉武,援儒以治,改弦更张而兴“有为”。采董仲舒之言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禅明礼,典章大备,扩土封疆,四方莫不宾服。其治国之思想——“外儒内法”,较之秦朝赤裸裸的实行法家之政治又隐蔽许多。刚柔相济,此一思想实乃促成汉朝鼎盛时期之方针。传至汉元,于统治思想有所取舍,则又成一局面矣。本文拟论述之主题乃在探讨其第二时期统治思想之所由及其何以能最终固定之因。
一、言“王道”与“霸道”
据《汉书·元帝纪》载 :(元帝)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德教,用周政乎!”[1]182在此,汉宣帝明确提出前汉之治国思想是“霸王道杂之”。该语不以“法”字加之,却冠之以传统儒家所倡导之“王道”与“霸道”之意,笔者以为此即是汉武以来“外儒内法”思想的直接告白。
对于“王道”与“霸道”的论述,多见于儒者典籍。二者是在相互比较中渐次出现的,大抵以“王道”为早,而“霸道”起初是不为儒者所提倡。其道有优劣之分,亦可以从各自首冠之字“王”与“霸”之不同而意会①。按儒家之意,三代承德而王,礼崩乐坏之际,五霸以力而起②。儒者崇德而不尚力,故齐宣王问孟子以齐桓晋文之事,夫子顾左右而言他,导之以王道[2]14-17。王道之由,自孔子提倡之“仁”发展而来。孟子分析出人之有“四端”[2]79-80,即“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由此而发展出的仁、义、礼、智“四维”则有助于“仁政”的产生。“仁政”即是“王道”,其施政纲领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5。这是有关“王道”的经典论述。
然而,以政治家之眼光看来,治国若依孟子之“王道”所行,则稍嫌迂阔。汉代桑弘羊就曾说到:“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3]温补之药不能济恶疾,必也猛剂,故有荀子之论继其而起。荀子在继承“王道”的基础上,顺应统一形势,从“礼”入手,首倡性恶论,法后王。他认为王者之政是一种用贤罢废,诛恶化民之政治。赏罚分明可以使人归于礼义,处理政事必须用“礼”和“法”,明尊卑等级使之相互制约[4]338-418。在提倡“王道”的同时,他也将“霸道”提出。“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4]472,具体点则是,王者“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霸者“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按谨募,选、阅材技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若禁暴,而无兼并之心”[4]356。荀子似乎比前贤更懂得治理国事,其主张与现实政治更贴近一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章太炎在评价孔孟时有“超出人格”之语,评荀子则言“荀子专主人事,不务超出人格,则但有人趣。若论政治则荀子高于思、孟”[5]。
二、儒学路向之转变
(一) 礼、法合流
“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4]338,荀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发挥了儒家思想最易见功效,又切实可操作的“礼”,从此给政治家们的“有为”提供了一种理论。在孔、孟那里,贵族所专用的“礼”原本被认为是天定的,不可改变的,“礼之端”只能求之于主观的“克己”和“辞让之心”;而荀子论“礼”却是着眼于人类物质欲求的“度量分界”,这已包含有明显的“法权观念”[6]。韩非、李斯被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历来被认为是荀卿的弟子。“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7]253尽管一定程度上与师说宗旨有悖,但不得不说他们也是顺着老师的意思走,只是走得更远了一点。钱穆先生在论及春秋末学术路向之转变时说到:“孔子死后,贵族阶级,堕落崩坏,益发激进,儒家思想暂转入消极的路去,如子夏、曾子等是。从此等消极状态下又转回来,走上积极的新路,便是后来所谓法家,李克、吴起、商鞅可为代表。法家用意,把贵族阶级上下秩序重新建立,此仍是儒家精神。”[8]按其叙述,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多与儒者有着种种师承关系,法家重建治世的精神仍是儒家之精神。冯友兰认为,观荀子《正名篇》的言论,“可知秦皇、李斯统一思想之政策之理论的根据矣”[7]233。《史记·商君列传》里记载商鞅曾以“帝、王道”干禄,在游说不行的情况下又以“霸道”说秦孝公,这才使对方叹服[9]1721。虽不免投机取巧之嫌,却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商鞅可能之前也兼治儒术。葛兆光先生认为按照法度和规则管理社会,其实都是对人性之善端失去信心后的想法。传统的儒者企图希望仪式与象征来增加人的敬畏,理性的自觉来挽救世道人心,在现实的需要与日益膨胀的欲望面前,却终究为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取代[10]164。在一篇论及儒法思想形成的论文中,论者认为儒、法思想的同源是先秦军礼,言之凿凿,可备一说[11]。
从相关研究来看,儒、法两家不论是否真实存在师弟关系,要之,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契合的。葛兆光先生虽然在论述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二者谁影响谁上与上文论点相左,但他同时也承认“我们并不认为儒法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可以认为从‘礼’到‘法’是当时关于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路的自然延伸”[10]169。
(二) 儒家的“杂家化”与统治者的“有为”
前汉的统治在汉初至窦太后时期在名义是奉行黄老无为的(事实上也存在法家思想的伏流),到了汉武亲政便要“有为”,于是儒学复兴。作为君主,汉武帝要求儒家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套修己安人之术,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在其进行暴力统治臣民的同时,又证明其统治之合法性的理论。此后出现的一个典型人物——董仲舒,便迎合了汉武帝的口味。
对于董仲舒,《汉书·叙传》称其为“纯儒”,但扬雄却把他列为讲“灾异”者,并不将其归入“守儒”行列[12]。冯友兰在“治国平天下的哲学主张”一章中指出,在战国末便已开始了“折中主义”思想倾向[13],从此百家互补,开始了杂家化的趋势,前期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这种趋势在此后便一直继续下去,前汉的儒家思想可以实际上称之为“杂家”,以董仲舒为代表。从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的思想来看,确乎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董子利用战国以来阴阳、法、道、名诸家思想,结合孔孟的“法古”“法先王”“任德”“任贤”等政治主张,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汉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需要的思想体系。他强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之言虽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相违,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儒学与君权相互妥协、相互支持的产物。“春秋大一统”“天人感应”说在塑造天子权威的同时,也使统治者默认了圣人的道德权威。于是,便有了“外儒内法”的契机。司马迁将荀孟并列入传,刘向的《孙卿新书》说:“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乎王。”[4]1186可知汉朝人是欣赏荀子的。董仲舒曾“作书美孙卿”[4]1186。其性说,调和荀孟,认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7]24。儒家在名正言顺地推行道德价值的同时,给汉朝的法制建设带来了一种新做法,即在肯定圣贤道德崇高的前提下,以儒家经典来治狱。该做法既没有受到儒者的坚决反对,也没有给统治者叫停,反倒开始盛行起来。“外儒内法”得以推行,似乎得到大家的默许。自从儒学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并作为晋升之阶后,表面上是儒学胜利了,但实际上却使其不得不受到皇权的制约与束缚,为了利益从此便不得不采取实际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一系列的制度化的策略随之而取代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以自由思想为职业的文士不得不承认官僚行政系统的政治正确性。按董子的意思,引《春秋》决狱原是为了慎刑、减刑,仍然是为了推行“仁政”。但先例既开,统治者的意思则又另是一套。在对待刑罚的问题上,历来是主张“性恶论”的,似乎这更能解释罪恶之所以然(荀子倡之,统治者和之)。既然儒学中开始了法家化,一些儒者也便顺应这一趋势。在人治与法治的问题上,荀子是主张人治的,但要靠有道德的君子来操作③。文法吏出现了对经典的歪曲解读,酷吏政治的实行便戕害了这一理想。这似乎符合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坐而论道的前者(儒者)真正进入了实际管理者的后者(法家)的行列,他就很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所以从荀子到韩非、李斯的传续,不仅是任务的师承关系,也是思想史上的理路延续与伸展”[10]169。
儒家的理念在不断地被修改着,儒家法家化半推半就,却仍限定在儒家的框架之内。这既是自身之特性:“古制未完全破坏,儒者通以前典籍,知以前之制度,又有孔子以来所有与各种原有制度之理论。若别家,则仅有政治、社会哲学,而无政治、社会之具体办法,或虽有亦不如儒家完全”“儒家之六艺,本非一人之家学,其中有多种思想之萌芽,易为人所附会。此富有弹性之六艺,对于不同之思想,有兼容并包之可能。”[7]297-298又有后来发展之结果(儒法的某种共通性,使二者渐趋合流),更多的是统治阶层的有意为之。戆直的大臣汲黯就曾经指责过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9]1622
三、后话“外儒内法”
有论者指出汉武帝时期之政策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能静态地、简单地归为“外儒内法”,而应动态地划分为四个阶段[14]。所论有一定道理。然若论及汉武时期之主要政策,其影响之深远,则莫如“王霸道杂之”。公元前 87年,汉武帝崩殂。汉昭帝统治时期,西汉政府在汉武帝晚年《轮台罪己诏》的精神指示下,开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而由此引起了一次大讨论,即盐铁会议。虽然有人认为,盐铁会议“不仅在政治上是终止武帝的战争政策,转入新的休养生息的和平状态的开始和标志,也是思想上终止汉初儒、法合流,重新恢复先秦孔孟思想传统的历史契机”[15]。但笔者却不以为然。因为,在政治上霍光秉政,萧规曹随仍然“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以为能”[15]。及宣帝亲政,霍氏虽一朝瓦解,但就统治方针而言,宣帝却基本上延续霍光秉政时期的为政方略。终于有一天,汉武帝时期潜伏的要求所谓“纯儒”的呼声再次作起,汉元帝便为之响应,故汉宣帝叹曰:“乱我家法者,太子也!”[1]182正是在汉元帝时期,才真正开始了中止儒学法家化的趋势。按照这种做法,似乎他们要走的是思孟一系的路线。然而,此时的儒家却已非“纯儒”,而是杂家化了的儒学。汉元帝二年春二日诏曰:“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咎至于此,朕甚自耻。”[1]189又五年春二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百姓有罪,在予一人。’”[1]194自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所施行“外儒内法”政策,表现出的是国政的好坏由君主与臣子共同负责的态度,但此时却变了。《汉书·元帝纪》“赞”说,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1]196。汉元帝时期纯洁儒术的做法带来的后果是五德始终说,法尧禅舜所引起的统治危机愈演愈烈。
在一篇文章中,有人指出“官僚帝国的本质在于君主与官僚共同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官僚的构成,自秦到西汉:秦政用文吏‘优事理乱’,汉朝取儒生参政,则是为其‘轨德立化’之功。”[15]108笔者以为此论尚有商榷之处:恐怕统治者之意思未必仅仅是立儒以彰德,而汉朝的一些所谓纯粹的儒者也似乎混淆了社会伦理改造之理想(修己安人之道)与政治统治实际要求之界限,所以汉宣帝斥之曰“俗儒不达时宜”[1]182。孔子曾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4]且不说儒家不排斥法家,刑德并用实际也是儒家一贯提倡的治国手段。在政治领域内,与其说是与道德相关联,还不如说是与权力更接近。
注释:
① 案:《说文》对于“王”与“霸”之解说不同于此文之说。《说文》之说“王”采经文家说,多附会之词,“霸”说主要与月相有关。上文所说之“王”与“霸”同《春秋左传》,“王”为三代之“王”,“霸”为春秋五伯之“伯”。
② “孟子将政治体制,分别为‘王道’和‘霸道’两种,‘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引自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6页。
③ “法者,治之端;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出自《荀子校释·卷第八·君道篇第十二》第526页。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98.
[4] 王天海.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 张德美.家族本位视角下的法律儒家化[J].比价法研究,2011(3):12-23.
[6]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108-109.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 钱穆.国史大纲[M].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4-105.
[9] 司马迁.史记[M].郭逸,郭曼,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1] 朱晓红.论先秦军礼与儒法思想的形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22-127.
[12] 扬雄.法言[M].上海:上海书店,1986:34.
[1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2005:163-169.
[14] 周晓露.论汉武帝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兼谈“儒表法里”定位之误[J].北方论丛,2011(2):91-94.
[15] 赵沛.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05-109.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 External Reasons of Contributing to the Policy of “Confucianism as Superficial Thought but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s Practical Thought ”
YANG Xi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1, China)
Abstract:The policy of “Confucianism as superficial thought but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s practical thought” is the ruling policy during the period from Han Wu to Han Xuan. Its for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are a deliberately act of the rulers in the trend of Confucianism transformation. There are two main trend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ne is the trend of combining etiquette and law, which is resulted from the interlinking of etiquette and law in some aspects, and the other is the trend of compromising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which is because Confucianism can be compatible with their thoughts.
Key words:benevolent government; high-handed government; Xuncius; Confucianism as superficial thought but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s practical thought; 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6)03-0040-04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08
收稿日期:2015-10-16
作者简介:杨 喜(1989-), 男,江西樟树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