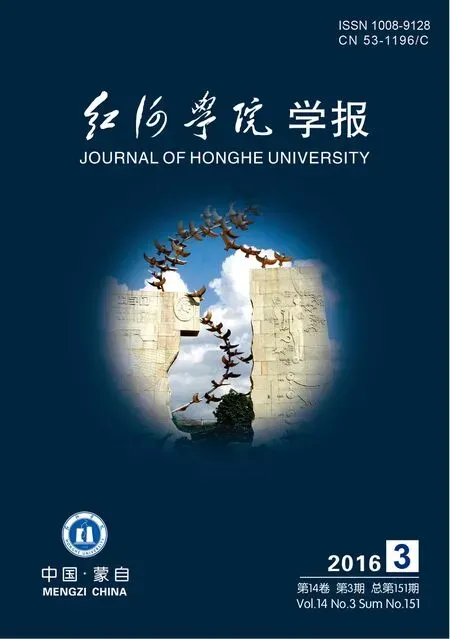抗战时期云南民族文化精神论析
2016-03-16布小继
布小继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抗战时期云南民族文化精神论析
布小继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摘 要:近代以前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土著文化、部族文化到汉族文化的融合期的过程。抗战加速了云南的现代化进程,云南民族文化由此进入到了加速发展期,西南联大等教育文化传播机构的到来、旅滇知识分子带来新的文化思想、日寇入侵激起的云南各族儿女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以及普通民众国家认同感的加强都使云南民族文化获得了新的内涵和质素,其精神体现为以爱国观为主体而付诸的各种实际爱国行动、由“山地意识”走向开放包容多样化文化形态的“高原情怀”以及云南本土文化摆脱封闭自足的特性自觉地与主流文化融合等特点。抗战时期逐步形成的云南民族文化精神,其影响不仅体现在当时和抗战胜利后,还延续至今天的“云南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建设。
关键词:抗战时期;云南民族文化精神;影响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化外之地,沐浴中原文化的时间较短。明清以降,云南民族文化得到了相对于以前的较快发展,近现代尤其是抗战以来,云南成了大后方,1942年5月后滇西又成了前线,这种特性与历史上的云南民族文化有何关系?它对云南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何作用?本文将对此加以探讨分析。
一 近代以前云南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略说
按照楚图南的看法,汉唐以前的云南文化可以算是土著文化时代,而真正的汉族文化在云南统治地位的确立要从明朝算起。明朝时云南并存着至少三种文化,即佛教文化、土著文化和华族文化,华族文化取得支配地位后,前二者渐趋式微、消灭。近代以来,云南的华族文化并没有现代化,比之沿海和中原,是要落后的。[1]显然,楚图南的这一结论基本上是合乎实际的。云南文化发展缓慢、变迁迟滞,既有地处边疆、远离中原核心文化圈的原因,也有世代聚居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封闭性强、汉族文化与之融合同化后产生了新的变异的原因,更有云南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方面的原因。云南由于地处边疆所致的河山阻隔造成了明显的部族群落,这在不少文献中均有记录:
樊绰《云南志》(卷四)“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类种也。”[2]19
元代大德年间李京《云南志略》“金裹两齿,谓之金齿蛮,漆其齿者谓之漆齿蛮,文其面者谓之绣面蛮,绣其足者谓之花脚蛮,彩绘分撮其发者谓之花角蛮;西南之蛮,白夷最盛。”[2]20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羁縻志》,“南中诸夷种类,至不可名纪,然大概有二种:在黑水之外者曰僰,在黑水之内者曰爨”。[2]24即“黑水”是僰(傣族)、爨(彝族)居住的地理分界线。对于“黑水”,一些学者认为是红河。
方国瑜认为,古代统治是以民族集团区域为政治区域,从政治区域可以推知民族集团区域。元代以前属于爨的部族只在红河以东,而其西则以傣族为主要。[2]25元明时期的云南,尽管在政治上臣属于中央政权,但文化上并不能与之同步,部族之间的分隔依然显豁,民族集团的利益是建基于其共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血缘关系和财产分配之上的。其文化诉求并不一致,在汉族文化影响扩散过程中尤其明显。汉族文化的传播与汉族人口的迁徙(包括流放、戍守、屯军)、政府官员对汉族文化的推广、土著民族中的汉化者或汉族文化接受者对汉族文化在本民族中的阐扬等密切相关。但在传播过程中的边际效应也是不言而喻的,即汉族文化在由文化中心向外传播的过程中,距离中心越远,其传播质量和传播效益就会呈现为不断衰减状态直至于消失。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妨认为,云南的部族文化在元代和明代前期依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汉族文化仅处于由萌芽期向融合期逐渐发育成长的状态。只是在明朝后期和清朝,部族文化优势地位才逐渐为汉族文化所取代。正如清人吴大勋所言,“滇虽边徼之地……历代以来,学士大夫之所陶镕而造就之者,又不乏人也。况入圣朝,文治之光华,映照四国,滇之人士,与中原文献之邦,均受涵濡之泽者,百数十年于兹矣。夫以天地之锺灵若彼,君师之教育如此,其谁复以边疆自域,不乐振兴于同文之盛哉!”[3]另有吴应枚对临安府(今建水县)的描述:“临安府学泮池深广,名学海,面焕文山,山顶藜嵩寨,夷人所居。每当大比,于六月星回节,视池中火影,卜乡荐多寡,历科不爽。”[4]即便在偏远的顺宁府(元设,治所在今凤庆县),亦有“其袭现职者为奉天和,执属礼来谒,年已七十矣,言动颇似官场中人。询其世业,旧有田二百余顷,今已耗其大半,家口百余人,支持渐难。然忠厚之流传,或不致失其故物云。”[5]以上诸人或于雍正或于乾隆年间在云南做过官,其述亦有夸饰过誉之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清代云南边疆民族的汉化程度比起明朝已经有了大的提高。按方国瑜的说法,“强不同以为同,所有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一般的文化事业的布置都求一致。”[6]这也是自元代到清代朝廷对云南边疆的控制力逐渐加强的结果。
1906年,留日学生主办的同盟会云南支部机关报——《云南》杂志在日本诞生,其后的五年间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强烈关注云南现状、热切呼吁民众觉醒的政论文。“若我滇……士无新智识,农工商等鄙陋愚蒙,耳无闻,目无见,若聋若瞽。英法人之开矿也,听之;英法人之筑路也,听之。推其所极,势不至为第二缅甸、第二安南不止。呼之不闻,摇之不动,唾之不知耻,剖之不知痛,此环球所未有,天下所罕闻也。如此怪状,何不幸于我滇见之。今不欲云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全省之风气同时并开,全社会之民智同时并启,庶乃有济。[7]又云,“我滇民气素弱,人心不一。一旦有事,以怯懦涣散之民,而与虎狼强敌相抗。是犹以卵御石,以螳当车也。此其可危者一。智识不开,风气窒塞。”[8]由于《云南》杂志发行量大、影响广泛,“甚至在英国、法国,还有人逐期用该国文字译出,以至伦敦、巴黎的报纸纷纷说:‘云南人醒矣,云南人醒矣!’”[9]
留日学生以“启民智、开民性”为当然的主题,把对照先进的工业化强国日本并反观落后闭塞的云南之深刻体悟与呼声传回国内、省内。在归国留学生领导下的在武昌起义前后发生的腾越起义、昆明重九起义、临安起义等军事行动,极大地提升了云南的民气、揭开了云南现代史的新篇章。先进知识分子创建陆军讲武堂以培养军事人才及领导云南边疆民众勇敢反抗满清暴政、声援辛亥革命的的壮举,为民众智慧的开启打开了一扇窗。正是在诸种因素的合力下,传统的土司制度、封建统治在辛亥革命后趋于瓦解,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五四运动”在云南边疆也激起了深远的回响,不仅在省会昆明,就是在其他中小县城如安宁、大理、腾冲、思茅、蒙自、昭通都有学生和群众起来响应,群众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甚至延续到1920 年5月。可见,云南边疆民众的觉醒正是在先进文化的引领和传播下发生的,是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忧虑的结果,民众有了更多的国家认同感。
二 抗战时期的云南民族文化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对云南边疆民众视野和智识的冲击愈发明显,云南民族文化也因之进入到了一个楚图南所说的新时期。云南成了整个国家的大后方,昆明与重庆、桂林一道成了全国的三个文化中心之一。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十一所高校迁至云南,吸聚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国民政府部分军政机关如西南运输处驻留昆明等,使得时代剧变影响下的云南民族文化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和特点:
第一,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先进教育文化传播机构提供了优秀的教育文化平台,云南本土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士大量增加,使得先进文化在云南边疆获得了传承融通的新渠道。以西南联大为例,其迁至昆明的1938年度,全省共有公私立高中、初中学校146所,合计524班,在校男女学生25,691人。当时,云南全省人口约1,152万,中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23%。相对在校学生来说,师资力量则更显得捉襟见肘。当年,全省普通中学、师范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员共2,139人,平均每校不过14.7人。[10]昆明的现代文化氛围甚为淡薄,在西南联大办学一年后,昆明俨然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一座大学城。教育厅长龚自知动员联大的所有毕业生到云南高中教书,联大教员为云南省中学教师提供在职培训,于是有了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全省69所中学的155名教师参与了为期一个月的严格培训,之后双方继续合作,先后举办了为期一年的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1939年)、中学理化实验讲习班(1941年)和中等学校各科在职教员讲习讨论会(1942年)。云南学生考上联大的也在不断增加,联大师范学院以招收云南人为主,本科学生要经过五年(最后一年实习)170个学分的严格训练,[11]75-81还专门开办了培养云南师资的专修科,八年间,联大师范学院共毕业本科学生200余人,专科生80余人,[12]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云南本土的精英人士。1946年,云南的中学(包括公立和私立)已经发展到167所,省立师范学校14所,县立师范学校25所,职业中等学校11所,这些学校的领导及教师十之八九是联大学生[13],正是在以西南联大为主的高校之带动和影响下,云南地方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云南文化的落后面貌。
第二,大批旅滇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与本土不一样的文化思想,改变了昆明乃至于云南的保守、固步自封的民族精神风貌。旅滇知识分子以外来者的眼光和视角看待云南及云南文化,与本土文明和文化产生了剧烈的碰撞。批评家、学者李长之在《昆明杂记》中把“懒洋洋的”昆明人与当时昆明城内外随处可见的牛联系起来的议论,就惹得本土人士在《民国日报》《云南日报》等报纸上撰文攻击之,甚至还有该文引起龙云震怒、作者要被“云绥公署”请去谈话的传言,李长之只好悄悄走之。此事极好地印证了其时云南人的胸怀与气度。之后,许多开明的学者、文人对此发表了看法,进行了批评。比如楚图南就认为“云南更要切实反省,自我批评;何况那些恭维都好像是背熟了的老文章一样,所以这只是反映了云南社会落后、幼稚、无知才有这种需要,需要表面的恭维,无论真心也好,假意也好。至少是在极细微的地方。也就是云南还没有对人尊重和对学术的宽容的雅量。”[14]此次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人尤其是昆明人对外省知识分子的态度。联大师生在旅居昆明的最初一两年,也与云南本土人士有过激烈的文化冲突,这些交锋的结果是双方相互适应,彼此了解的程度加深了,云南对外来人员及其外来文化的接纳情怀也逐渐确立。
第三,日寇入侵激起了云南各族儿女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云南人民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抗战的支持,使得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加速了。早在1934年,云南就有班洪、班老王率领佤山民众抗击英国侵略者掠夺我土地的事迹,1936年又有《佧佤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请求全国人民支持阿佤山民众在与英国人就中缅勘界问题上所持的正义立场的举动。抗战伊始,云南人民便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1937年11月滇缅公路西段开工,1938年8月全线通车,这条战时修建最快的公路,云南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大到常人难以想象。当年亲历现场的记者兼作家萧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我在长达一千公里的滇缅公路上竟连一台推土机也没见到。一条那么长、那么艰险的公路,竟然光靠胳臂拉、肩膀挑,就那么赤手空拳地修了起来。在那些用拉壮丁办法硬征来的千百万民工中间,我还看到七老八十的。吃喝全不管,在那遍地‘瘴气’(恶性疟疾)的地带,连一粒阿司匹林也休想找到。”[15]硬性的摊派拉夫、微薄的报酬、毫无保障的工作和医疗条件,与之相对的却是数不清的悬崖峭壁、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和随时可能的死亡。所以说,这条1941年后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完全是凭借着以沿线各族民工甚至妇孺们为主的云南人民异乎寻常的坚韧与执着、对国家的忠诚与信念甚至还有发乎本能的家园捍卫意识,不惜血肉之躯、不惧个人安危地拼命劳作而建成的。
同样,1937年10月卢汉率领60军(滇军)在台儿庄战场上对日寇的猛烈抵抗,尽管死伤人数超过了投入战斗者的半数,但其英勇无畏之气概使得李宗仁在给龙云的电报中感叹,“六十军将士忠勇奋发”。日本报纸也大发议论,“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16]新编五十八军于1938年7月投入战场后,参加战役二十余次,毙伤敌人五万余人,这在黄声远的《壮志千秋》一书中有详细记述。可见,滇军的战斗力是极其强大的,其背后有龙云政府和云南人民的强力支持,不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富于牺牲精神,体现了云南子弟兵们极好的家国意识和朴素的爱国观念,之后滇军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等重大战役,为云南人民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前方将士的杀敌之功也有后方的一份,以女学生为主组成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深入到了滇军驻地做护理、收容、译电和宣传工作,把家乡父老的问候带到将士们身边,起到了激励、安慰和鼓舞的作用。后方还有捐款捐物、缝制衣服鞋袜支援前方等多种举动。
1942年5月,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沦入日寇之手后,滇西乃至云南人民开始奋起反抗,六十多岁的云南省政府委员张问德于危难之际出任腾冲县长,秉笔书写了正气凛然的《答田岛书》,指斥日军暴行、表明了其本人及治下民众为乡土不惧一死之决心。民国元老李根源在保山金鸡村的抗战动员大会上发表了《告滇西父老书》,慷慨激昂地动员人们起来抗击侵略。两年后松山战役、腾冲光复、驱逐日寇出云南土地,也正是在广大民众的有力支援下得以成就的,云南因之成为了抗战时期沦陷国土最早被全部收复的省份。在军民并肩作战的过程中,云南边地各民族相互支援、共同奋斗,形成了一个以国家利益、乡土利益为核心的战斗团体,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云南民众对国家主体文化精神的认识,即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反侵略精神,以正义对抗邪恶、不服强权与暴力的节义精神和士可杀不可侮的传统士人精神。
第四,普通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通过抗战得到加强。这从当时旅滇文人和本土作家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冰心通过自己从北方到昆明的亲身经历,深刻地感受到了云南大地上所响彻的全面抗战的吼声。沈从文真实地描叙了菜市场上一位姓曾的屠户对区里征兵打战的反应,“我去打仗,保卫武汉三镇。我会打枪,我亲哥子是机关枪队长。”[17]不怕死,为了家国敢于担当责任。李广田《废墟中》的不惧日机轰炸而艰难且一丝不苟地谋生活的木匠夫妇,彭慧《一个战士的母亲》中那个目不识丁却懂得“没有国哪有家”的大道理且在大儿子阵亡后又支持二儿子上战场的老太太,费孝通《鸡足朝山记》中愿意经营好铜矿来为抗战服务的和尚,马子华笔下居住在中缅边境却参加了抗击日本人战斗的佤族,无不充盈着强悍、不服输、不怕死的英雄品性。换句话说,他们恰是广大云南民众的代表,他们对抗战的认识是基于朴素的爱国观,而这种观念又和人们近乎本能的领土意识、家园意识分不开。这些世代形成的民族心理积淀借助抗战这一大事之触发而得到了新的提升,旅滇知识分子传播的先进文化,本土有识之士、开明士绅等的爱国言行与边疆民众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时,就有了前述的遇合,并且被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整合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的云南民族文化精神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保家卫国为主体的爱国观念借助于各民族的团结一心和朴素本色的支援国家的抗战行动得以体现。全民族的抗战使中国任何一个省份都无法独善其身,战争的正义性、残酷性和持久性促使云南边疆地区付出了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和艰辛的代价。有学者认为云南各族人民对抗战的巨大支援至少体现在:(1)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的修建。仅是前者就“完成土方1,989万公方、石方187万公方”[18],民工“死亡人数月二、三千人,受伤近万”[19],1941年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物资为132,193吨,[20]其中汽油占1/3。(2)后勤供应与人力支援。在滇西反击战中,“补给军粮九千一百二十五吨,马料六千五百吨,弹药三千三百四十七吨,连同食盐副食物与装备器材,大约近一万四千吨。在吾国战史上,其消耗数量,不可谓不巨。”[21]在修筑滇缅公路的过程中,征用的民工即达150万人之众,在滇西反击战中,为前方运送粮秣的老百姓也达二三十万之多。其实,抗战保家卫国的过程也是云南人民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的过程,不同民族不再各自为战,而是紧密地围绕抗战建国共同奋斗。云南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在真切的抗战体验和自觉的担当中得到了深化和升华,改写了云南的历史,证明了云南绝不是蛮荒和闭塞的代名词,而是在危难关头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的重要省份。
第二,从自私狭隘、封闭自足的“山地意识”走向吸收接纳先进文化和开放包容多样文化形态的“高原情怀”。云南的交通不便迫使各民族、部落内部必须采用“抱团取暖”的方式坚守住自己的领地,这在封建时代是极其重要的。山河阻隔、地理落差、气候差异也塑造了不少民族保守、闭塞的特性,而对民族、部落以外的事情多半是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征伐、战争是维护自己生存权益的最后手段和必要选择,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势必影响到民族思维,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山地意识”,即某一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自私狭隘、封闭自足,缺少立足于全省、全国的整体观,发生在民族部落之间、民族部落与政府或外来侵略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又强化了基于各自利益的对抗性矛盾,这也愈发强化了民族部落各自为阵的利益观。全民族广泛参与的抗日战争却使得这种矛盾得到了弱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弭,1941年在国家号召捐献飞机的行动中,云南各族人民共捐献了30架,名列全国第一,其功勋不可谓小。由此可见,抗战的发生对云南人民从“山地意识”转向“高原情怀”的改造是不可忽视的,即责任感强、包容、宽厚、有担当、识大体、顾大局。云南人民对优秀文化的吸收接纳一方面体现在昆明等城市对外来人口有了更多的包容,另一方面还渗透进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学生发起的“灭蝇运动”就带动了当地的餐馆老板使用薄纱布遮盖食物,改善了当地的卫生习惯。在联大左派学生的动员下,蒙自、建水等地的青年纷纷参加了云南游击队等等。[11]61-62蒙自这座边陲小城因为联大师生的到来获得了现代文明的更多火种,获得了走向现代文明的更多契机。当然,就云南整体来看,这种吸收接纳与开放包容本身就蕴含着民族精神的巨大进步。
第三,云南本土文化摆脱封闭自足的特性自觉地与主流文化融合。云南边疆在历史上是处于封建王朝统治版图的神经末梢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与外界的交往极少。教育文化的异常落后又令寻常的本土人士几乎无法通过科举考试以出将入相的途径把百姓的声音时时传到朝廷,云南疆域以外形成了一个与己无涉的他者世界。绝大多数老百姓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中,安分守己、辛勤劳作。无论部族群落、土官统治还是流官统治,服从、讲求实际、维系眼前利益是其基本法则,这塑造了边疆各民族天性中的忍耐、顺从等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边疆保守自足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世代承袭的。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爱国行动却是先进理念传播后民众日益觉醒的结果,抗战时期,云南作为大后方这一历史机遇和滇西沦陷与光复中进入云南的兵力超过百万乃至卢汉受国民政府指派入越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等事件显而易见地加速了云南融入主流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本土文化自觉地与国家主流文化融合。
三 抗战时期云南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及影响
综上所述,云南民族文化由自发到自觉,由土著文化、部族文化到汉族文化,由汉族文化的萌芽期、融合期到加速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抗战是这一加速期的重要节点和催化剂,并且塑造了云南民族文化精神。其内涵有以下两点:
第一,云南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不仅是云南部族文化长期演化又融入了中原文化(儒释道文化)的结果,也是云南地方文化近现代变革的产物。当云南学子走出大山,获得了看周围世界的新角度和新体会时,一方面痛感云南的面貌尤其是老百姓自身的麻木,一方面也激发了他们改变云南的雄心壮志,自腾越起义开始的系列运动使云南人民有了亲自参与和改变命运的良机,不断砥砺和成就云南民族文化的基本层面。抗战是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正面回击,而云南文化恰是在其他地域遭受到大肆破坏的时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的。尽管腾冲、龙陵、芒市等地暂时被日军占据,尽管被破坏和现代化进程被打乱是该时期的普遍现象,但抗战为云南提供了赶上国内文化发达地区的可能,如何挖掘出云南的地方文化内涵,建构起云南特色的民族文化是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包括白平阶、马子华、张子斋等人在其作品中关注过的,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精神在军民个体身上的表现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述。[26]抗战中,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回族等各少数民族贡献出了自己的优秀儿女又有自己的英雄人物和杰出代表。超越了族际恩怨、一致对外的抗战实践活动使各民族获得了加深相互了解、促进相互融合与和睦相处的机会。
第二,云南边疆各民族秉持了坚韧和强悍的特性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了抗战的具体实践中,强化了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构成了抗战时期云南民族文化精神中极其优秀和重要的部分。抗战的全民性决定了没有任何人能够置身事外,当北方大片领土沦入日寇之手时,云南的作用和优势得到了凸显——作为大后方,云南派出物资、军队和劳动力,做好相关保障工作;作为前线,云南竭尽全力反抗侵略直至领土光复。云南地方政府动员全省力量全力以赴支援抗战,保障和构筑生命线——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和中印公路等“血脉”的过程,即是云南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不断检验的过程。外来知识分子带来了先进文化,本土人士在克服最初的不适应后多采取积极与之融合的姿态,昆明、蒙自等街头、剧院甚至茶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抗日剧、活报剧、演讲会等轮番上场,一些名剧如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曹禺的《原野》、陈铨的《祖国》、《野玫瑰》和抗战剧《黑字二十八》等也经常在西南联大校内和昆明城内演出,其教育意义和感召力度非同一般。这不仅是对抗战的有力支持,也使包括市民在内的各民族群众心灵受到了洗涤和净化,成了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认同主体文化的缘由,各基层地方的行动亦极好地诠释了云南人民是如何把其吃苦耐劳精神有效地转化成支援抗战并赢得胜利的实际行动的,这又是云南民族文化精神在抗战实践中得到砥砺的最佳体现。抗日战争中滇西地区遭遇到的种种惨状世所罕见,各民族所迸发出的爱国热情和顽强抵抗精神与任何省份相比都毫不逊色,其对强权与野蛮暴力的反抗有着特别的意义。
近现代以来在云南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有力地证明了云南不仅是反抗强权、暴政和抵御外侮的政治、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文化活动的一个高地。抗战胜利后发生的“一二·一”运动、“李闻惨案”、“七·一五”运动足以见证昆明及云南人民对民主、自由、和平、进步所代表的人类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和向往,学生、市民一次次成为了主角,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表达对国是的关心。云南各族儿女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积极配合对滇中、滇西北、滇南的剿匪等也为明证。
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云南作为一个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迄今为止也是民族间相处最为和谐和融洽的省份。这不仅在于有国家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等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规范和约束,还在于云南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力、向心力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成为了民族间和谐相处、友好共存的粘合剂,也是今天云南建设“民族团结示范区”的重要依据和法宝之一。
参考文献:
[1]楚图南.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G]//楚国南.楚图南文选.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624-625.
[2]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绪论二[G]//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3]吴大勋.滇南闻见录[G]//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21.
[4]吴应枚.滇南杂记[G]//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52.
[5]刘靖.顺宁杂著[G]//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55.
[6]方国瑜.云南民族史讲义[M].秦树才,林超民,整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738.
[7]崇实.论云南之社会智识[J].云南,1907(7).
[8]崇实.论云南人之责任[J].云南,1907(3).
[9]谢本书.《云南》杂志始末[N].云南日报,2006-01-19(8).
[10]闻黎明.西南联大与云南中等学校师资培养[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10).
[11]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2]张云辉.国立昆明师范学院[M]//云南省档案馆.建国前后的云南社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72.
[13]张云辉.西南联大对云南文化教育的影响[M]//云南省档案馆.建国前后的云南社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69.
[14]楚图南.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G]//楚国南.楚图南文选.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627.
[15]萧乾.从滇缅路走向欧洲战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64.
[16]云南省档案馆.抗战时期的云南社会[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58.
[17]朱自清.流亡三迤的背影[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83.
[18]徐以枋.抗战时期几条国际和国内公路的修建[G]//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5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45.
[19]谢自佳.抗日时期的西南国际交通线[G]//昆明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6:4.
[20]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9页.
[21]云南省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大事13:上册[Z].云南省志编篡委员会,1985:19.
[22]蒙树宏.云南抗战文学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118-120,132,174.
[责任编辑 张灿邦]
On the Cultural Spirit of Yunnan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
BU Xiao-ji
(School of Humanities,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99,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Yunnan in modern times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igenous culture, the tribal culture and the Han culture.The war accelerat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Yunnan, Yunnan ethnic culture entered into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period, southwest education culture media is coming, Yunnan culture, intellectuals brigade brought the new invasion of Yunnan aroused the patriotic enthusiasm of the children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protect our homes and defend our country and the common people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Yunnan national culture the connotation and quality of the new, the spirit is embodied by patriotism as the main body and put into practical action, by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mountain" to open and inclusive and diverse culture form "plateau feelings" and the local culture of Yunnan from the closed characteristics consciously and mainstream culture fusion etc..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culture spirit of Yunnan gradually formed its influence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victory of the war, but also extended to today's "Yunnan national unity demonstration zone" construction.
Key words: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Yunnan national culture spirit;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6)03-0067-05
DOI:10.13963/j.cnki.hhuxb.2016.03.018
收稿日期:2015-07-01
基金项目:红河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云南边疆抗战文学研究(14bs06)
作者简介:布小继(1972-),男,云南大姚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