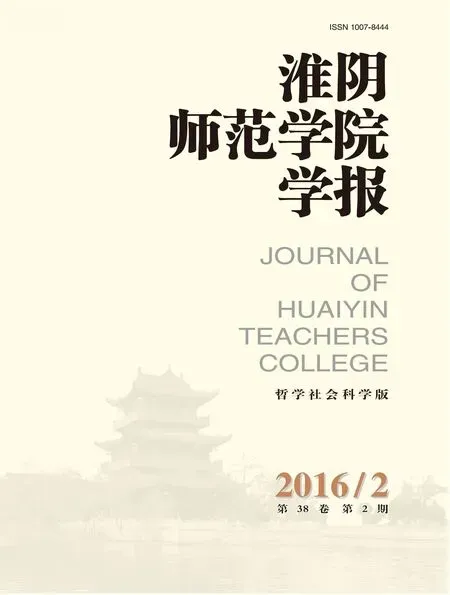从北宋杜诗写本异同看学杜风尚与宋调成熟
2016-03-16王苑
王 苑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从北宋杜诗写本异同看学杜风尚与宋调成熟
王苑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仁宗庆历年间是两宋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时期,宋人大规模学习杜甫便始于此时期,从而形成宋调特色。但是,作家地位的确立首先取决于其作品被阅读的程度,有什么样的作品流传,就决定着什么样的诗人形象,从而决定诗人的地位。而宋人最终选择杜甫作为学诗的共同典范,催生出成熟的宋调,与北宋前期众多杜集广泛流传,且异文多歧有着紧密关联。从中唐到北宋,杜甫形象在不断变化,究其原因,除了时代美学趣尚等因素,也与杜甫作品篇数不断增多完善有关。所以在北宋前期的写本时代,由于杜集没有“真本”,杜集卷帙篇数不等,异文众多,读者心目中的杜甫形象也就呈多元化,有着与“沉郁浑融”主体风格相参差扞格的“豪放俚俗”。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以杜甫诗集从写本到印本的转向及其后果为中心,进一步考察北宋前期尊杜对宋调成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杜集;写本;异文;学杜;宋调
仁宗庆历年间是两宋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时期。庆历新政虽然暂告消歇,但沾溉广远,极大地激励了士风。新型的学者群体涌现,理学思潮初兴。“古文”写作开始获得承认,引起士人仿效。欧阳修入主文坛,拉开文学大变局的序幕。马东瑶先生已撰有相关论文,以实证材料证明宋人大规模学习杜甫始于庆历时期,并具体论述了庆历诗歌如何受杜诗影响,从而形成宋调特色。宋祁、苏舜钦、石延年、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在庆历之际学杜出新,形成宋诗的第一个高峰。[1]
一、北宋前期的杜集写本异文分歧与宋人的采择取向
作家地位的确立首先取决于其作品被阅读的程度,有什么样的作品流传,就决定着什么样的诗人形象,从而决定诗人的地位。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至庆历元年(1041),宋祁、欧阳修、王洙等人编校《崇文总目》,仅载“《杜甫集》二十卷”,与《旧唐书·杜甫传》《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所载的“六十卷”皆不同。[2]王洙利用在崇文院编目的机会,通览“秘府旧藏”和“通人家所有”的多种公私所藏杜集,于宝元二年(1039)将所得各种杜集结集为《杜工部集》二十卷,但未刊刻。20年后的嘉祐四年(1059),王洙所编杜集由王琪增订刊刻于苏州,世称“二王本杜集”,成为以后各种杜集的祖本。[3]杜集的编校刻印充分说明了杜甫在庆历前后深受官方和民间的推崇。
至此,王琪在苏州刻印《杜工部集》前后,在庆历年间,杜集风行全国,杜集的搜辑编校整理在全社会掀起一股读杜、尊杜、学杜的热潮。王洙编校的杜集影响最大。晁公武说宋朝“自王原叔以后,学者喜观甫诗”[4]。南宋叶适《徐斯远文集序》也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5]今从杜集编校亦可证实。北宋后期,蔡启概述本朝诗风嬗变历程时说:
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人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6]
所述虽不够准确,但大致不差。宋人最终选择了杜甫作为学诗的共同典范,催生出成熟的宋调,这个结果约在庆历前后形成,与众多杜集的广泛流传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杜集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问题与特点。如版本众多、篇数不定,多则二十卷,少则仅一卷。且俱为写本,文字差歧之处甚多。所以写本异文的众多,且读者读杜诗篇数不同,对杜甫人格风格就会有不同的判断,从而导致不同的学杜结果。哈佛学者田晓菲研究了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本质,指出手抄本“在文本平滑稳定的表面之下,律动着一个混乱的、变动不居的世界”。因为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失去控制,而且,即便抄手能准确无误地抄写作者的原本,也不能保证流传到后世的文本的权威性,因为文本在离开作者以后会经历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在抄本时代,一个抄写者作为一个特别的读者,可以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地参与文本的再创造,哪怕这作品属于伟大的诗人。田晓菲以韦氏妓“改正”杜诗的故事为例: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阀甚盛。尝纳妓于洛,颜色明秀,尤善音律。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妓随笔改正,文理晓然,是以韦颇惑之。[7]
不同性别、年龄和社会背景的人以其抄写、编辑、改定、修饰、补缺等活动参与了手抄本的创造。写本和印本不同,“由于同一版的印刷书籍全都一模一样,印刷可以限制异文数量的产生;与此相比,每一份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可以产生新的异文,这样一来,比起印刷文本,手抄本就会大大增加异文的总数”[8]。不同的异文会导致不同的诗意,从而塑造出不同的诗人人格和风格。田晓菲在认识中古写本时代手抄本的不稳定性的基础上,细读陶渊明的文本特别是异文,发现后世陶渊明“平淡自然”的高尚形象乃是宋人通过控制陶集异文而创造出来的。这一思路对考察北宋尊杜风尚不无启示。
写本时代,人们所读杜集主要的不同,一是卷数篇数不等,多少不一;二是异文众多,文字不同。试分析其后果。
从中唐到北宋,杜甫形象不断变化,究其原因,除了时代美学趣尚等因素,也与杜甫作品篇数不断增多完善有关。大历年间,杜诗流传多为“戏题剧论”之作,宜乎长时期里人们目杜甫为恃才无礼之人。宋真宗朝,西昆体领袖杨亿,谓其为“村夫子”[9],或与所读杜集收诗不多有关,因为杜甫确有鄙陋之作,尊崇杜甫的苏轼评价其《解忧》就认为:“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真村陋也。此最其瑕疵,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10]宋初王禹偁赞扬“子美集开诗世界”,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极度推崇杜甫的全面成就及对唐五代诗人的影响,这样的认识与其时杜集多见、卷帙丰富是分不开的。庆历前后,苏舜钦、王洙、王安石、刘敞等人广泛搜辑杜诗,杜甫佚诗有大宗发现,杜集臻于完整,而杜甫形象也在此时多样化、崇高化,庆历四年(1044),宋祁主持修纂《新唐书·列传》,《杜甫传》里对杜甫的记载和评价就是这种多样化、崇高化的集中体现。宋祁综合了杜甫同时人、韩愈、元稹、孟棨和《旧唐书》等诸多人的意见,又加入他本人手书杜诗、学习杜诗的体验,于是杜甫的形象成为:性褊躁傲诞,旷放不自检,伤时忠君,诗歌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古今第一;其诗善陈时事,律切精深,世号史诗,光照万代。[11]这反映出庆历前后人们对杜甫人格和风格的认识是多元的、丰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针锋相对的。杜甫形象的日渐丰满、崇高,与杜集版本的日臻完善、杜诗篇目的日益增多是同步的,最突出的时期就在庆历前后。
对杜诗异文的校勘解读也直接影响到北宋诗人对杜甫的学习。据宋人记载,王洙编校杜集时对异文的处理持谨慎态度:今世所传《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辞有两出者,多并存于注,不敢彻去。至王荆公为《百家诗选》,始参考择其善者,定归一辞。如“先生有才过屈宋”,注:“一云‘先生所谈或屈宋’”,则舍正而从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注:“一云‘如今纵得归,休为关西卒’”,则刊注而从正本。若此之类,不可概举。其采择之当,亦固可见矣。惟“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阙字”与下句语不类,“隅目青荧夹镜悬,肉骏碨礧连钱动”,“肉骏”于理若不通,乃直改“阙”作“阅”,改“骏”作“鬃”,以为本误耳。[12]
今传《王氏谈录》系王钦臣记录其父王洙言论的笔记,谈到“校书”时也说:
公言:校书之例,它本有语异而意通者,不取可惜,盖不可决谓非昔人之意,俱当存之,如注为一云作壹(一字已上谓之一云,一字谓之一作)。公自校杜甫诗,有“草阁临无地”之句,它本又为荒芜之芜,既两存之。它日有人曰为无字,以为无义。公笑曰:“《文选》云:‘飞阁下临于无地’,岂为无义乎?”唐郑颢自云:“梦为诗《十许韵》,有云‘石门霜露白,玉殿芜苔青’,意甚恶之,后遇宣宗山陵成,因复职。”公尝笑曰:“此杜工部《桥陵诗》也,颢以为贞陵之祥,而更复缀缉,亦嗤鄙之一也。”[13]
两书记载近似,自属可信,从中可以发现两点,一是王洙所处的时代杜集异文众多,二是王洙处理异文的态度是审慎严谨的,尽可能多地保存异文,以供读者自行抉择。王洙整理的杜集是诗十八卷及补遗二卷,而王琪犹“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多”的表现可能在于王洙保存了很多的异文而未加考辨定夺。这就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丰富多样的杜甫文本,读者对杜甫的解读也就自由多元。嘉祐以后,王琪刻印杜集,对异文采取“义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的处理方法,不可谓不慎重,但也意味着对于他认为“不通”的异文就削而去之,从而导致某些异文消失,毕竟他本人也承认“阅之者固有深浅也”。刻印时裴煜“取以覆视,乃益精密”,也许又对异文作了删汰。但他们并不能保证都校正了杜诗的文字讹误。北宋末《漫叟诗话》校杜甫《秋雨叹三首》其二云:
《秋雨叹》:“禾头生耳黍穗黑”,今所行印本,皆作“木”字。事见《齐民要术》云:“秋雨甲子,禾头生耳”,本当作“禾”。[14]
这条校勘得到后世学者认同。仇兆鳌在“禾”字下注:“一作‘木’字,《漫叟诗话》定作‘禾’。”[15]当代语言文字学家郭在贻亦予以肯定:
按:作禾是,木乃禾字形近之讹。《钱注杜诗》云:“《朝野佥载》:‘俚谚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行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单父人戴寂云:久雨则禾生耳,谓牙蘖卷挛如耳形。王原叔以禾作木,木固有耳,恐非本旨。”[16]
焉知王琪刻印本不是径直删去“禾”字而保留“木”字?因此嘉祐刻印杜集,使杜集异文第一次大量消失,而王安石以己意“择其善者定归一辞”“刊注而从正”的做法则使杜诗异文再次大量消失。《蔡宽夫诗话》谓是王安石编《百家诗选》时所为,误。实则《百家诗选》未选杜诗,应是《四家诗选》,乃安石元丰年间在江宁所编,以杜甫为首,李白居末。嘉祐以后,王安石诗名崇高,蔡启遂以王氏采择为精当,其实古今皆有不以为然者。如蔡启所举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天阙象纬逼”句,王氏径改“天阙”作“天阅”,就遭到同时刘攽、南宋朱熹、明代王世贞的批评,清代王夫之、当代曹慕樊已详列充足理由,证明当从宋代早期版本作“天阙”。即使王安石采择确属精当,删削异文的做法也导致读者对杜诗理解的狭隘化、单一化、定型化,从而禁锢了学杜创新的多元化。
苏轼对待异文的态度也近似王安石。他一方面批评“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似乎是针对政敌王安石而发;另一方面,他又以陶渊明《饮酒》而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句为例,改动原文:
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17]
苏轼是众望所归的大诗人,其观点被广为接受,遂成千古定论。但也许庆历前后的读者所读杜集就有“波”的异文,自宋至明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苏轼,而以“波”字为是。
对异文的采择有时就像阐释的循环。欧阳修记载陈从易的故事:
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18]
对“过”字的选择源于对杜甫伟大诗人身份的尊崇,而对“过”字艺术效果的推重,又反过来加深了对杜甫的尊崇。这是北宋时期读者面对杜诗众多异文所作反应的一个缩影。
二、杜诗异文事例举要与后世歧见中杜甫形象的凝定
杜诗异文中尚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字值得关注。
一是“閒”字。杜甫父亲名閑,閑、閒常通用,因此杜诗中有无“閑”字就关系重大,倘若有,则杜甫会背上不避家讳的恶名。据仇兆鳌注,今存杜诗相关文字如下:
《诸将五首》其一:“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19]1363殷:“音‘烟’。诸本作閒,《正异》作殷。”《宴王使君宅题二首》其二:“泛爱容霜鬓,留欢卜夜閒。”[19]1932鬓,一作发;閒,一作阑;卜夜閒,一作上夜关。《小寒食舟中作》:“娟娟戏蝶过閒幔,片片轻鸥下急湍。”閒,一作开,非。[19]2062
王直方赞成有“闲”字,因为“临文恐自不以为避也”[20],诗人创作可以暂时与世俗礼法不一致。赵令畤以蜀本、王琪本、薛向家本为依据,主张没有。[21]蔡启、周必大也主张没有,以为“北斗闲”本作“北斗殷”,由于避宋太祖父亲弘殷的偏讳“殷”而被改为“闲”。[22]张耒认定杜甫天性“笃于忠孝”,不可能冒犯家讳,故古写本作“问不违”胜过“闲不违”,写本作“殷”字有理,语更雄健。众说纷纭,聚讼不已。今按,现存二王本杜集,相关正文文本及校勘文字如下:
卷一五《诸将五首》其一:“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閑。”[23]291
卷一七《宴王使君宅题二首》其二:“泛爱容霜鬓,留欢卜夜閑。”小字注:“一作上夜关。”[23]313
卷一八《小寒食舟中作》:“娟娟戏蝶过閑幔,片片轻鸥下急湍。”[23]321
“北斗闲”“闲幔”均无异文,“卜夜闲”有异文作“上夜关”,而又以前者为正。古人避讳甚严,王洙参与编撰的《崇文总目》卷一载“《丧礼极义》一卷,唐商价集”。清钱东垣按曰:“本作‘殷价’,避太祖父讳作‘商’。”[24]是以“商”代“殷”。倘若杜甫文本中出现“殷”字,王洙编校时完全有可能径以“闲”代“殷”,但亦可以缺笔形式处理而不必改用“闲”字。从诗意看,“曾闪朱旗北斗闲”本作“殷”是可信的。“留欢卜夜闲”以“上夜关”为较胜;至于“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则本作“闲”才能与“急”对仗。仇兆鳌注引顾炎武云:“‘閒’乃閑暇,于‘閑’字自不向犯。”[25]此说或亦可通,但由于閒、閑常通用,读者阅读时往往会忽略其细微差别。无论如何,庆历、嘉祐之际,二王本流布最广,杜诗中的“闲”字一定影响到人们对避讳文化和杜甫形象的解读,从而增加了解读的多样性。
二是杜甫《哀江头》末尾二句。二王本作:“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无异文。南宋《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三此句下注:“洙曰:一云望城北。”又引黄中立曰:“甫朝哀江头,暮又闻史思明连结吐蕃入寇,欲往城南省亲,仓皇之际,心曲错乱,忘南而走北也。甫家居城南。”黄希、黄鹤补注本同。按所谓“王洙注”,并非出自王洙之手,而是北宋后期人邓忠臣所撰,此条异文校语实为忠臣新校。[26]“忘南北”本自可通,若无异文,则如黄中立那样以常理说诗即可,“忘”字在此处也不可能有歧义;但嘉祐以后异文出来后,特别是杜甫忠君爱国的形象被神化、固化之后,“望城北”尤其“城北”的异文就非同小可了。
南宋陆游与黄中立一样,从普通人面临危险时的正常反应解读:
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舛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惶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27]
王安石既以“望城北”为正,按他的编校体例,其他的异文会被删除。陆游的理解是,杜甫之所以欲往城南却向着城北走去,是因为仓皇避难、不辨方向。训诂学家郭在贻同意陆游的说法,但何以会有“望城北”和“忘城北”两种传本?是由于“望、忘通用,习见于唐人文字”,因此作“望城北”为是,“忘则是望的同音假借”。[28]
清初钱谦益作“欲往城南忘城北”,注云:
兴衰于无情之地,沉吟感叹,瞀乱迷惑,虽胡骑满城,至不知地之南北。昔人所谓有情痴也。陆放翁但以避死惶惑为言,殆亦浅矣。[29]
从杜甫心情极度悲愤激动来解释不分南北的行为,批评陆游的解释是矮化了忠君爱国的杜甫。
今人陈寅恪先生则从更深层次揭示其微言大义:
唐代长安城市之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也。……复次,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多不得其解,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见陆游老学庵笔记柒。)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30]
通过分析长安城市空间结构,揭橥诗人身处危局犹眷念君国之“本意”。但与其说这是作者之“本意”,不如说是读者之“用心”与“深意”。北宋后期以来,苏轼关于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之论深入人心,陈寅恪的解释则以此为基础。陈氏曾在其《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一文中,驳倒以往仅靠文字训诂和句法分析,对乐毅《报燕惠王书》中一段话的解说,而又博取史实,作出最为简易也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总结解释古书之法:“夫解释古书,其严谨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不可仅于文句之间,反复研求,遂谓已尽其涵义也。”[31]不改原有文字、采用习见涵义、旁采史实人情、解释最为简易,这四条阐释原则诚为不刊之论。陈寅恪自身对于杜甫“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亦与此相合。然而,就二王本杜集“欲往城南忘城北”的文字而言,以习见之义“忘记(不辨)南北”来解释“忘南北”,与这四大原则亦不相违。诗人危难之际下笔作诗,也许就是不辨方向的“忘南北”或“望(向)城北”。
以上例子表明,不同的异文会深刻影响到读者对杜诗的解读、对杜甫形象的认知,从而影响到学杜的方向和推陈出新的结果。在庆历前后,杜集仍处于写本时代,在传抄过程中非常容易滋生异文,众多的异文也会被有意识地搜集保存下来。李纲说杜集“传写谬误,寝失旧文,乌三转而焉者,不可胜数”,朱熹说“杜诗最多误字”,都可见出写本时代杜诗异文的丰富。据考查,《全唐诗》异文颇多,而杜诗尤甚,所录杜诗异文多达三千五百余条[32],以致学者呼吁杜集“刻不容缓”地“需要一个新的定本”[33]。由此可以反观北宋前期杜诗异文的特点:丰富多样,流动不居,无权威,无定论,选择自由,解读多元。北宋末,梁子美极喜杜诗,常令人取杜集示客,“有不解意以录本至者,必瞑目怒叱曰:‘何不将我真本来!’”[34]此处“录本”应指“写本”,“真本”盖系印本。然而在写本时代,何为真本?何处觅真本?前引王洙《杜工部集记》说杜集传本“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矣”,刘敞《编杜子美外集》说杜甫的作品,“乱后流传简册伪”,正是说明了北宋前期无所谓“真本”。“真本”既无处觅,“本意”亦幻为子虚乌有。
三、宋调视域下的杜集定本与杜诗学的确立
杜集“真本”的说法出现在北宋后期,其时杜集已进入印本时代,王琪增订刊刻的二王本杜集早已大行于世,成为此后各种杜集的祖本。此本的流通有力地促进了杜诗在全社会的流行,也使杜诗流传从多本并存的“写本时代”进入到定本权威的“印本时代”,许多异文消失了,一些存在异文的文本经过王安石、苏轼等大诗人的解读,也便等于遮蔽了异文,而杜甫众体兼备的文学成就、直陈时事的诗史内容、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忠君爱国的思想境界、忧时忧民的人文情怀等诗人形象,就在印本时代被逐步塑造出来,并日渐定型、神化。从嘉祐到元祐,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先后执诗坛牛耳,此时期的杜诗学也笼罩在他们的阴影之下。王安石称美杜甫家破身危时,在诗中仍“不废朝廷忧”,苏轼敬佩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黄庭坚赞美杜甫“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又称杜甫“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所论皆着眼于政治关怀和道德意识。这些观点直接影响到对杜甫异文的解读与扬弃。四库馆臣指出:
自宋人倡“诗史”之说,而笺杜诗者遂以刘昫、宋祁二书据为稿本。一字一句,务使与纪传相符。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者,固在于是。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耳。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则诗家无景物矣;谓纨绔下服比小人,谓儒官上服比君子,则诗家无字句矣。[35]
以这种单一化、定型化、神话化的形象为基准去对待杜诗异文,必然抹杀了杜甫作品的丰富多样,也限制了读者的解读自由。
而在北宋前期的写本时代,杜集没有“真本”,杜集卷帙篇数不等,异文众多,读者心目中的杜甫形象也就呈多元化。后人多瞩目杜甫的“沉郁”,此时的诗人发现的却是杜诗的“豪”。田锡说“李白、杜甫之豪健”,欧阳修指“李、杜豪放之格”[36],赞扬“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张方平独推“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正如前文所论,《新唐书·杜甫传》集中反映出庆历前后人们对杜甫人格和风格的认识是多元的、丰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针锋相对的。正是这种自由多元的论杜氛围中,西昆体的宋祁和尊韩派的苏舜钦、石延年、梅尧臣、欧阳修诸人皆能在庆历之际学杜而出新,形成宋诗的第一个高峰,宋调终趋成熟。方回指出:“近世之诗,莫盛于庆历、元祐。”[37]这与庆历年间的尊杜热潮密切相关。
庆历以后,赵宋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国内危机日益加深,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关心国事的诗人们逐渐选择了充满忠君忧国精神的杜诗,对杜甫的评价也往往着眼于此。从道德意识出发,宋人对诗歌有“性情之正”的要求,而杜甫全幅人生是仁的境界[38],因而他们对杜甫伟大人格大加赞赏,视杜诗为“明道”“见性”的典范。韩诗多愤世嫉邪、忧穷嗟卑之语,从嘉祐到元祐,人们强调诗歌用以自持自适,对韩诗深感不满,转而以杜诗为典范。
就诗歌嬗变而言,越过韩愈、选择杜甫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诗歌艺术浑融含蓄境界的追求。学韩派强调“意新语工”“意与言会”,在实现明白畅达、工巧新奇的同时,也宰杀了物质世界的浑融感,丧失了内心世界的朦胧美。嘉祐以后,杜甫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诗人们也随之开始了自赎性反思。这种反思从王安石开始。王安石早年作诗好议论,“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皆直道其胸中事”,晚年转学唐人律绝,“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其成就表现为“造语用字,间不容发”与“言随意遣,浑然天成”的高度统一。[39]此中的理论依据源于王安石对杜诗艺术的认识:
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40]
王安石“言随意遣,浑然天成”的进境显然有得于杜诗的“绪密而思深”。黄庭坚一生推尊杜甫,侧重在艺术形式上,更是大张旗鼓地号召学杜,尤其醉心于杜甫晚年到夔州后的作品,心摹手追,推陈出新,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正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所说:“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41]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竞相学习、模仿,杜诗的影响至此达于极盛,宋调的本色至此也臻于极致。苏轼与黄庭坚分别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成就和最大特色。“元祐以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42]因了对杜诗的推崇和学习,中国诗歌取得了第二次大革命的成功。[43]
简而言之,安史之乱后,杜甫漂泊西南,其晚期诗“剥落浮华”,体现出平淡、老健的美,已透露出宋调的风貌。尤其是近体诗,记时事,发议论,写日常生活琐事,用俗字俚语入诗,绝句多对仗,律诗创拗体,皆开宋人门径。[44]其后,从中唐到北宋,有创造力的诗人或先或后、或深或浅、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以杜诗为典范,出以己意,将杜诗中的新变因素发扬光大,共同筑起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二座高峰。
参考文献:
[1]马东瑶.论北宋庆历诗人对杜诗的发现与继承[J].杜甫研究学刊,2001(1):62-73.
[2]钱东垣,等.崇文总目辑释:卷五[M]//王尧臣,等,编次.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册:343.
[3]洪业.杜诗引得序;再说杜甫[M]//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302-349;427-433.
[4]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57.
[5]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一二[M].刘公纯,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214.
[6]蔡启.蔡宽夫诗话[M]//宋诗话辑佚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398-399.
[7]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五一:引唐阙史[M].汪绍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8):2780.
[8]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5-8.
[9]刘攽.中山诗话[M]//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288.
[10]苏轼.苏轼文集:卷六七[M]//孔凡礼,点校.记子美陋句.北京:中华书局,1986:2104.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一:杜甫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35.
[12]蔡启.蔡宽夫诗话[M]//宋诗话辑佚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384.
[13]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笔记:1编:第10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168.
[14]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357.
[15]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17.
[16]郭在贻.杜诗异文释例[M]//郭在贻文集:第1卷:训诂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2:93.
[17]苏轼.苏轼文集:卷六七[M]//孔凡礼,点校.书诸集改字.北京:中华书局,1986:2098-2099.
[18]欧阳修.六一诗话[M]//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266.
[19]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六;二二-二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0]王直方.王直方诗话[M]//宋诗话辑佚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11.
[21]赵令畤.侯鲭录:卷七[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81.
[22]蔡启.蔡宽夫诗话[M]//宋诗话辑佚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394;周必大.二老堂诗话[M]//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673.
[23]宋本杜工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24]钱东垣,等.崇文总目辑释:卷一[M]//王尧臣,等,编次.丛书集成初编本:1:13.
[25]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933.
[26]梅新林.杜诗伪王注新考[J].杜甫研究学刊,1995(2):39-42.
[27]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M].李剑雄,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94.
[28]郭在贻.杜诗异文释例[M]//郭在贻文集:第1卷:训诂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2:91.
[29]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3.
[30]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51-252.
[3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62.
[32]郭在贻.杜诗异文释例[M]//郭在贻文集:第1卷:训诂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2,86.
[33]王利器.杜集释文校例(上)[J].西北大学学报,1980(2):38-46.
[34]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M]//丛书集成初编本.2:69.
[3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1281-1282.
[36]欧阳修.六一诗话[M]//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267.
[37]方回.孙后近诗跋[M]//桐江集:卷四.影印宛委别藏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288-289.
[38]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235-314.
[39]叶梦得.石林诗话[M]//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406-419.
[4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M].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7.
[4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6-27.
[42]刘克庄.后村诗话[M].王秀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26.
[43]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7-51;58-69.
[44]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260.
责任编辑:刘海宁
The Fashion of Learning Du Fu and The Maturity of Song Poetic Style from the View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Manuscript Copies of Du Fu’s Poetr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NG Yuan
(Literature Colle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The Qingli period is influential in Song dynasty. In this period, poets begin to learn Du Fu, and the Song poetic style forms its own characteristic. Howe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sition of a poet firstly depends on how many works have been read. The image and position of a poet are related with his pop works. The final selection of Du Fu as the common model of learning poetry leads to a mature Song poetic style. This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wide spread and disambiguation of variant readings of Du Fu’s poetri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middle of Tang dynasty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reasons for changes of Du Fu’s image are the factors such as age aesthetic interest and the perfect of Du Fu’s numerous works. In the period of manuscript copy of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rare of the true copy and numerous of variant reading of Du Fu’s poetry, images of Du Fu are diversity, which take on a vigorous and flowing style, while not the main style of deep depress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respecting Du Fu to the maturity of song poetic style in early stag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ith the center of Du Fu’s poetry from writing copy to printed copy.
Key words:Du Fu’s Poetry; Manuscript Copy; Variant Reading; Du Fu Learning; the Song Poetic Style
作者简介:王苑(1989-),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2-0227-06
收稿日期:201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