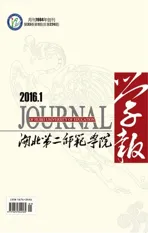质疑苏贾“第三空间”理论的合法性
2016-03-16马征
马 征
(江苏师范大学 法律政治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质疑苏贾“第三空间”理论的合法性
马征
(江苏师范大学 法律政治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试图通过批判理论的地理学化和再度激进化,摆脱历史决定论,激活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但是他在空间转向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在确定的意义上,只是通过一个战斗口号的激进化,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一旦对该理论的前提、核心概念——边缘性进行一次地基清理,就能发现这一后现代激进理论所承载的批判功能和兑现政治承诺能力的孱弱。
关键词:苏贾;第三空间;合法性;地理的不平衡发展;边缘性
在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的过程中,走得最远,也最激进的当属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W.苏贾了。1996年,他发表了《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空间三部曲”的第二部),旨在开辟一种“他者化”的新视野,重新思考与空间相关的概念和空间的意义,消弭二元对立,彰显亦此亦彼逻辑的可能性,并为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三者平衡提供本体论上的依据。苏贾的这种元理论的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深度揭示了空间问题的重要性,并完善了列维——斯特劳斯以降的空间理论的架构,也为中国当代城市化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和反思。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追随第三空间的逻辑,尤需要对这种理论本身、理论谱系,及其政治承诺予以准确的评估。苏贾试图将空间理论的再度激进化以摆脱声名狼藉的历史决定论,通过融入空间视角激活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这一旨趣没有问题,但他已经激进到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并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鉴于此,本文尝试着对第三空间理论的前提、核心概念——边缘性进行基础性分析,以考察该理论自身的承诺和兑现这种承诺的能力。
一、“第三空间”概念及其理论谱系
苏贾的 “空间三部曲”可分为两部分:关于空间的元理论建构和三元辩证法的经验考察。《第三空间》中的第一部分“发现第三空间”分属第一部《后现代地理学》,第二部分“内外洛杉矶”分属第三部《后大都市》。而这两部分恰好表征了苏贾的知识学取向和实践取向(或政治诉求)。在《第三空间》中,苏贾没有给“第三空间”以明确的定义,他承认只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第三空间’是一个有意识的灵活的尝试性术语,力求抓住观念、事件、外观和意义不断在变化位移的社会背景。”[1]2这样,我们要想准确地把握“第三空间”这一概念及其特性就显得非常困难,必须从它所驻足的理论谱系中窥探其秘密;起点是列斐伏尔的他者化理论,接着是瑚克斯的边缘性理论、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最后是作为空间性转向旗手的福柯的异形地志学。
列斐伏尔认为,长期以来,反思性思想及哲学都注重二元关系,但是忽略了始终存在的第三项——他者。他的代表作《空间的生产》正是围绕这第三化展开,而作为第三化的结果或产品,就是苏贾所用的术语“三元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三元结构,而社会空间即是“第三空间”,或谓之“空间三元辩证法”。它要求第三项既包含第一空间(物理空间)和第二空间(精神空间),又超越二者;既超越“二”(二元结构),又超越“三”,每一次第三化,每一个三元辩证法都是一次“趋近”。所以“第三空间”并非一个在“三”面前止步的封闭不前的结构,而是一个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总体,包罗万象的世界都集中于此,且持续地进行肯定性解构,在已知之外不断扩大知识的再生产。由此,可以得出“第三空间”的第一个特性:不断生成的总体性。
苏贾选择瑚克斯的《渴望》作为阐释“第三空间”的亚文本,旨在将我们表征的生活空间重构为养育抵抗的场所,一个真实和想象、物质和隐喻交汇的抵抗一切压迫形式的边缘场所。“这种空间性利用差异构建新的斗争场所,人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彼此联系、互不排斥的反抗社会。”[1]121“利用差异”,首先要承认差异,承认被差异的社会所构成的边缘化和从属地位,然后占据边缘地带,将这些空间开拓成具有彻底开放性的和可能性的空间。而不是作为有色人种简单地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从来都不是惟一的选择,而是被现代主义理论中压迫性结构(中心——边缘)强加给黑人主体而已,[1]124因为边缘始终存在,霸权话语始终存在,这种斗争也就必然会陷入虚无和困境之中。不难看出,瑚克斯所说的边缘并非“中心——边缘”结构中之边缘,而是这种压迫性结构中观念地分化出来的另一种边缘空间,是一种同时在政治和地理两方面主动选择的边缘空间。在此主动选择的边缘中,既可看到中心,亦可看到边缘;既平衡中心和边缘,又作为整体独立于二者构成认识的主干。这种观念性的边缘空间是一种构想出来的被苏贾称之为“刻意的边缘性”,也即苏贾的“第三空间”。看得出,“第三空间”的第二个特性是:主体想象的边缘性。
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作为第三空间理论谱系中的一员,是为了增强“第三空间”的开放性而被援引。其实,瑚克斯的边缘性理论中的边缘已经具有了包容差异的开放性,但是这种边缘的开放姿态,旨在主动选择的边缘背景上构建更大的生存和反抗的社会。作为政治选择的“第三空间”,包含着矛盾、危险和新的可能。这也是一种吁请,承认进步男性和女性的本身,同时又是女权主义的(非简单的反男权,因为这种简单的“反”,并没有逃脱男权的基地,说到底仍是男权的)。而霍米·巴巴的混杂性是各种声音、各种立场的杂糅的“第三空间”,意在超越“文化差异的围堵”,引发一个避免极端政治的谈判新时代。这才是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的要旨,也是霍米·巴巴被苏贾援引的真正原因。苏贾的“第三空间”的确融有这种混合性因子,岂不知它只是缺乏现实空间根基的文化修辞,一个漂浮的隐喻,不仅起不到增强第三空间理论的内涵的作用,反而黯淡了它激进的批判锋芒。这正是“第三空间”的第三个特性——杂糅差异的开放性——在作祟。
福柯虽然作为空间转向的旗手,并没有特别系统的空间理论,他的“异形地志学”是存在于一个生前未打算发表的一次演讲——题为“关于他者空间”。而在《后现代地理学》中,苏贾针对福柯“含糊不定的空间性”,走历史和空间整合的路径而不是解构性路径,表示失望,[2]32并始终提醒福柯,权力与知识之间的那些可能的关系,“根植于权力、知识和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之中,必须始终不要忘记这第三项”。[1]91在这种情况下,福柯为何还被引用呢?那就是“通往空间和空间性思考的新途径,福柯称之为异形地志学,他描述的方式类似于我所说的第三空间”。[1]199其中的核心词“异托邦”正是苏贾想要的东西。所谓异托邦,是指与一般日常生活空间不同的,散落在统一空间之外的异质性存在,是生活空间的镜像,却与日常生活空间并存,如禁地、墓园、军营、监狱、博物馆等等,透过它们,世界及世界的变化一目了然,类似佛家能藏须弥山的芥子。这是一个包容着其他地方的地方,一个包容了被规划整合的统一空间和被统一空间实践所排斥或隐匿的部分(边缘,或后台)的真实存在着的具体场所。不同的场所构成不同的生活空间,不存在被决定论逻辑支配的普遍空间,也不存在非流动的与人分离的总体化空间,人类活动也只有通过描述具体场所中的人的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被把握。这种理论概括被苏贾称为第三空间的微观或地点地理学,也彰显了“第三空间”的第四个特性:充满异质的具体性。
由此,我们可以试着给“第三空间”下一个不完全的定义,所谓“第三空间”,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包含差异的既是构想又是具体的他者——总体空间。这也正是《第三空间》的副标题——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的题中之义。需要说明的是,他者空间的“具体”“真实”并非目之所及的实际场所,它是与此时此地存在的实际场所相反的他者空间,同样需要抽象力和想象力方能把握。
二、“第三空间”理论的前提
第三空间理论的建构与空间转向中的其他大部分理论一样,攻击的矛头是历史决定论,这无可非议,因为历史决定论的确遮蔽了社会批判的空间维度。看得出,第三空间理论的构建不单单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吆喝,而是一场宏大的知识学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和立场的改变。这是苏贾对空间投注过多热情的终极目的。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地基清理,也即前提反思,以探求第三空间理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承载批判视野的功能。
第三空间理论有两个前提:现实前提是地理的不平衡发展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理论前提是列斐伏尔的“他者化——第三化”道路。前者隐含了资本主义本体改变的假定;而后者隐含了历史唯物主义二元论和空间维度缺失的假定。
第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理的不平衡发展的确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方式和原由:晚期资本主义需要借助扩大再生产来缓解资本主义结构所无法负荷的各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借助处处存在但问题重重的空间化过程生产空间并占有空间。空间的生产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品,还是工具,反过来构建资本主义。作为结果的地理(区域和民族)不平衡发展也一样,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支撑着资本主义的延续(分裂出不同阶层的工人阶级)。当然,地理的不平衡发展也构成了威胁资本主义的潜在力量,产生了历史行动和社会变革的地点——边缘。这是一块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边界重叠的肥沃场地,后现代空间批判理论家们从中发现了革命的种子。如此这般,地理的不平衡发展是否就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结构的基础或批判的前提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本体改变的假设,是资本主义真正本体的僭越。因为比不平衡发展的地理更为始基的因素——资本,依然是资本主义的本体,而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形式、衍生物或媒介罢了。就功能而言,虽然资本和空间都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但资本的同一性及其复制的形而上学在制造幻象的能力上远比空间生产出的差异性强大,也更能折射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前途,但需要对资本进行历史现象学上的层层剥离,直至其拜物教意识。也由此,面对一个着了魔的“倒立跳舞”的“只见物不见人”的世界,一厢情愿地通过 “注入”第三项——他者,就想透视其本来面目的,并撼动其根基,只能是一种现象学上的近视。因为地理差异同样被强大的资本逻辑异化了,甚至对它的认识(反思)的本身都“制度化”(吉登斯语)了。以地理的不平衡发展作为“第三空间”理论的前提,看似激进,其实不过是资本逻辑前进中的一个历史性产物,这中反思也不过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反思。
第二,为了解决历史唯物主义二元论问题,苏贾走的是列斐伏尔“第三化——他者化”的道路,从而形成了三元辩证法(这是一个历史辩证法的替代性术语),甚至列斐伏尔在分析马克思的劳动——资本时,也要加上一个第三项,以形成土地——劳动——资本的三元结构。再如中心——边缘——调解,历史——空间——全球性等等。事实上,主客二元分立及其变体,是一个旧形而上学的问题,只要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基地,没有脱离知识论路向,这一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要么只是在封闭意识内完成(如黑格尔的主客同一),要么就是第三条道路的主体构想(如瑚克斯的边缘性理论)。这便是康德所言的“人类理性的耻辱”。马克思终止了旧哲学的基础——意识主体,决定性地开启了生存论路向,以实践或对象性活动来彰显主体性。而与对象性活动密切相关的概念即对象性存在。马克思说:“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对象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对象地’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3]167所以,对象性活动直接就是对象性存在,反之亦然。这种对象性关系正表明了主客体的原初关联,任何存在都是对象性关系存在,而孤立地谈论主体或客体,或主客体统一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历史、地理范畴及其统一问题莫不如此。因此,寻求历史——地理——社会,乃至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实际的空间三者平衡的“三元辩证法”,也是没有必要的。福柯部分地继承了马克思的“幽灵”,他认为人不能生活在内在意识中,也不能生活在抽象空间中,只能生活在各种异质性的场所之中。但是反过来,福柯又把场所(异托邦空间)界定为人类集体的“常量”(没有一种文化在其世界中不产生异托邦)这个超历史的范畴,从而失去他的理论的批判力量。事实上,空间理论家大多陷此囹圄,第三条道路的口号无论喊得多么激进,都无法摆脱在政治实践领域中的调和姿态。当我们明白“第三空间”原理不过是中心——边缘结构之外构想出来的他者空间时,异托邦也不过是一个非历史的想象的“权力的眼睛”,它们的批判锋芒和兑现承诺的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如果撇开作为现代性反抗话语在诞生之初面临的理论条件和情境,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明显地强调时间维度的优越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感慨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其异化现象、内部矛盾和破坏性后果并存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宣称的世俗天国的图景中,而要直接把握社会空间的控制权,以生成为特质的时间,无疑是当时对抗异化的有效利器。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的排斥。毋宁说,马克思的旨趣是空间的,马克思无意去建构一条似自然性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构建在最大限度上只是为资本主义灭亡提供了一个客观条件,之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历史具体”上,也就是空间差异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观点,其关键在于,“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理解的那样。”[4]46“人体”只是一把钥匙,而非透视所有社会形态的万花筒。戴维·哈维十分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他说:“作为一个个体,实际上我并没有把宇宙万物都内在化……主要吸收了那些与我直接相关的东西。”[5]6还是有大量的东西丢掉了,那么“第三空间”这个极具包容性的臆想物是如何做到“一花一世界”的呢?另外,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不同层次上的形式分析,对俄国农村公社的革命和命运的思考,甚至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所表征的也恰恰是空间的旨趣——对“历史具体”的探讨。如果不是这样,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无论是强调马克思发明了症候的拉康,分析《资本论》对象的阿尔都塞,还是差异地理学的哈维,其话语都是不可想象的。
三、作为“第三化”空间的边缘
第三空间理论是元理论冲动的产物,苏贾试图将“他者化”发展成“第三化”,重新平衡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从而构建了一种批判性的元哲学;既延续了现代性之本体论诉求,以期满足真理性需要,又在本体论假设上后现代化,将边缘、外围、残余等他者空间纳入到理论的中心,从而要求获得对地方的定义权,要求边缘作为生产反霸权话语的地点。这种来自他者的声音,部分源自传统的工人运动没能促进彻底的变革。工人阶级的乌托邦空间如此彻底地被资本主义商品化想象所占据,工人阶级政治文化的话语领域被作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大众传媒所统治,潜在的政治抵抗也已官僚化、受惠于并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利益。于是,工人阶级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积累在各个领域中附加的东西,作为革命行动的当事人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因此,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必须寻找新的当事人和实现变革的地点。虽然这种声音很难让人接受,但我们却不能武断地拒绝它。因此,可以理解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建构的旨趣不仅仅是知识学上的空间立场的转向,说到底,还是政治学的。
作为政治的批判理论的第三空间,其核心概念便是边缘,它是包罗万象的全体,不仅包括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还超越了二者,给其他思考模式提供了可能。问题是,作为战斗的边缘是在何种程度上兑现了它的政治承诺的?或者说,作为第三空间之边缘缘何成为历史行动和总体变革的地点的?
前面已经论及,第三空间之边缘是一个比喻性的抵抗场所,即中心——边缘这种压迫性的二元结构之外的“边缘”,是一种反霸权的政治学的“感觉结构”,是一种嵌入其他空间和地方的观念性空间。无论是瑚克斯的作为彻底开放空间的选择性边缘(具体表现为“语言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还是福柯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异托邦(具体表现为身体、监狱等都是权力生产的场所)莫不如是。他们偏好把这样的地方作为川流不息的战场,是因为这里是一个绝不会被消灭的反霸权政治学的安全避难所,永远存在。边缘总会存在和不断产生,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必然,那么边缘之外的想象地点也就随之总会存在。这必将演化成从边缘开始的抵抗事业最终把抵抗变成了边缘的事业,同时也指证了以苏贾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空间理论家(左派)对资本主义内部危机的理论上的测度和实践上的整体改变能力的缺失。倒是左派地理学家哈维突破了这一困境,在“战斗的特殊主义”(雷蒙德·威廉斯)和全球抱负的二者关系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阐释。哈维也主张地方(边缘)斗争的优先权,但是与苏贾等人把第三空间之边缘作为战场不同的是,他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下,详细地阐释了地方何以能够“嵌入”(内在化)外部世界?嵌入了外部世界的地方的动力是什么?以及这些地方如何联系起来形成总体革命?地方被理解为环节,各环节的关系被理解为“流”,“每一个环节主要通过来自所有其他环节的各种各样的冲突结果把异质性内在化。”[5]92但是当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转化的时候,一定有大量的东西丢失了,就像从一种语言转化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一样。这就有必要对所有的环节都进行考察,例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过程(流)的独立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把其他条件内在化了,但是在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运行和社会主义如何实现时,虽然生产环节比其他环节重要,却不能完全忽视其他环节,“实际上,要在生产中把特别的和渴求的变化形式内在化,研究其他环节(如消费)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最明显的例子是,消费者的联合抵制影响生产行为)。”[5]85因此,试图通过“第三化”之边缘作为透视全体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是不可能的。而哈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是确定主要矛盾在特殊历史地理情境中的所在之处,以及它们相互连接是如何可能的?那么,特殊的历史地理情境中的所在之处在哪儿呢?换句话说,可以在什么地方发现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呢?答案是:到处。因为每个地方都内在化了其他地方,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和不满的示威运动。[6]68而让各个地方建立联系的中介或主线是什么呢?哈维说,是阶级斗争。
至此,冠以激进的第三空间之边缘,其困境远不止于此。当它以彻底开放性的名义作为斗争场所时,已经滑进了满足于自身的无窗空间,因为它把来自外部的结果都内在化了。那么这个地方就代表了所有地方,“我”也必定代表着每一个人,这其实等于根本上什么也没说。引申一步,既然都内在化了来自外部的结果,那么除了它自身的内在意志之外,就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动起来。看似有现实的地点为基础,究其质仍不过是乌托邦想象。这是黑格尔哲学在当代语境中畸生的一个怪胎,好一点的话,顶多算是卢卡奇总体革命(意识革命)的变种。更加危险的是,这种比喻性空间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由碎片化和不可解决之差异组成的后现代世界,成为一个似乎在概念上彻底开放的万物汇集的纯粹的点。这是激进之幕下的认同,无疑已经遁入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
那么,为什么看似激进的第三空间理论到了实践的政治领域却成了一枝没有子弹的枪,而在理论领域又成了无批判的形而上学的帮凶了呢?除了苏贾的微观叙事很难承载批判根据的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历史维度的缺失。空间是有历史的,只有当空间与资本合谋时才以“形式”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而且往往是假象),才成为资本主义独有的产物。而资本是没有历史的,如果把资本关系的发展和空间生产的发展这两条不同的逻辑等同看待的话,势必会对当代城市化发展持拒斥态度,结果是要么回到从前,要么落入未来的想象——乌托邦,更别提为城市化发展指明历史出路了。而当苏贾赋予第三空间以不断超越、不断生成的特质时,又在元理论的层面上回到了意识内批判(比喻性边缘)的领域,变成了一种无批判的空间“景观”。其次是经济学视野的缺失。哈维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把阶级斗争、资本积累和差异地理学唯物主义地联系起来之后,产生了颇具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事实上,空间视角和时间视角或其他的视角一样,它必然面对着当下的政治和经济过程,故而,只有具备加强驾驭政治经济问题的能力时,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理论旨趣。
参考文献:
[1]苏贾.第三空间[M].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戴维·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彭雷生
Legitimacy Questioning of Edward W. Soja’s Third Space Theory
MA Zheng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Edward W. Soja’s Third Space Theory tries to get rid of the historical determinism by the geography of the critical theory, and activate Marx’s critique of modernity, but he goes too far in the direction of spac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ean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reconstructed with only one battle cry of radicalization. Once the theory premise, the core concept, is marginally given a ground cleaning, the modern radical theory can find its own weakness in critical function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
Key words:Edward W. Soja; Third Space; legitimacy; unbalanced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margin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6)01-0044-06
作者简介:马征(1978-),男,江苏宿迁人,硕士,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收稿日期:2015-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