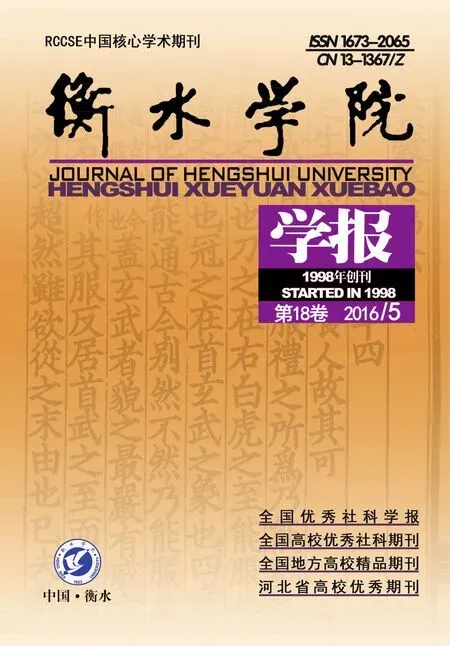熊十力论董仲舒学说中的现代民主精神
2016-03-15姜淑红
姜 淑 红
(淄博职业学院 稷下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314)
熊十力论董仲舒学说中的现代民主精神
姜 淑 红
(淄博职业学院 稷下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314)
熊十力对董仲舒学说重新诠释并加以发挥,认为董仲舒学说中有适应当下社会,并有益于时代发展的微言大义之所在。主要指董仲舒的《春秋》改制、“三世说”和“以元统天”。熊十力分别将三个理论修正扩充为“万世制法”“一统论”和“仁”的理论。熊十力通过改造董仲舒学说而建造的这三个理论体系,对于反对当时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儒学人文意义的彰显也有正面价值,然而这并没有解决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因此也就没有可能找到一条真正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
熊十力;董仲舒;民主精神
熊十力(1885-1968年),原名继智、盛恒、定中, 号子真、漆园、逸翁, 湖北黄冈人。熊十力年轻时爱好读王船山的书,佩服船山的民族大义,后受到康梁维新时印刷的小册子所宣传的“民权”“君民共主”思想的影响,萌发了反清思想,并参与了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熊十力中年时期,时值军阀混战,他认为“革政不如革心”,慨然脱离政界,潜心跟随欧阳渐研习佛理。后由佛归儒,著作了《新唯识论》,之后,熊十力又写了《读经示要》。《读经示要》是熊十力在经历了弃政从文后,重新定下学术救国的目标下著作完成的,他立志挺立中华道统与中华文化精神,因此在书中对儒家民主思想进行阐扬,从而体现他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在《读经示要》中的《春秋示要》部分,熊十力大篇幅引用董子的话说明《春秋》古经中有适合于当下社会之用的大义存在,是“内圣”与“外王”相结合的大学问。熊十力认为中国固有文化就是讲民主自由的,这在董子阐明《春秋》义中多有表述,其中存在改革君权、要求民主等现代精神,因此读经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一、《春秋》改制到“万世制法”
熊十力首先指出,孔子作《春秋》之说首先见于《孟子》,之后主此说者有醇儒董仲舒。熊十力认为董、何于三科九旨说,居功至伟,在《读经示要》卷三中说:“孔子作《春秋》,其说既不便于当时天子诸侯,故不著竹帛,而口授七十子。公羊高亲受之子夏,世传口义,至玄孙寿乃与弟子胡毋生,著于竹帛。同时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广大精微,盛弘《公羊》。其后何休作《解诂》,虽云依胡毋生条例,而义据亦大同《繁露》。故治《春秋》者,当本之董何。”[1]1011可见熊十力对董、何推崇之至。熊十力说董子《春秋繁露》中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孔子作《春秋》并且有深义在,“仲舒作《春秋繁露》有云孔子明得失、差贵贱(贵义而贱利),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大小。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2]241司马迁说:“汉兴五世之见,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既然董子说孔子作《春秋》有贬绝讥刺之辞,那是一定有的,熊十力说两汉诸儒距离古代不远,他们的说法比较可信,而魏晋以后的人以猜测之说降圣人制万世之法的大经为记史之书,肆无忌惮之极。
熊十力认为治《春秋》当本之董、何,《春秋》中有微言大义,但微言与大义颇不同。对于二者之别,《读经示要》卷三曰:“大义者,如于当时行事,一裁之以礼义。微言者,即夫子所以制万世法,而不便于时主者也。如《公羊》之‘三科九旨’多属微言。”[1]1011在熊十力看来,大义一般指适合于当朝统治者的一些思想,如大一统、尊王等,而微言则指变法改制等类。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高高在上, 微言不为其所喜,为免触怒时君,所以一直以口授方式流传。然而时过境迁,到了民国时期,微言不再是禁忌,所以微言便和大义基本上趋同。
熊十力说孔子作《春秋》乃是为万世立法,他说董子对策中有:“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以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2]242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素王呢,熊十力说“孔子《春秋》之作乃通万世而权其变”,使得“仁及未来无量众生而无穷竭”。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假文王以明仁道”,另一层是“假文王以明志”[2]242。熊十力说,孔子本义是作《春秋》为万世制法,但是却被后来的汉儒篡改成“为汉制法”,尤其是汉代的纬书中比比皆是,熊十力说此举无非是为了谄媚时主,但是危害却极其深远,到了清代甚至有为清制法之说。皮锡瑞说:“《春秋》为后王立法虽不专为汉,而汉继周后,即为汉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汉言汉。推崇当代,不得不然。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教,即为清制法,亦无不可。”熊十力严厉驳斥此说:“锡瑞此解鄙陋已极。《春秋》之道,归于去尊以伸齐民。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不容有统治阶级也。人民皆得自由自尊自主,所以致太平。……汉之帝制,清人覆二帝三王之统,皆《春秋》之所以必诛绝而不容宽假也。”
在熊十力看来,古代经书中有值得当代人研读的微言大义存在,这些微言大义如果研究透彻精确,是可以有益于现实政治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孔子作《春秋》乃为万世立法”之说,这就否定了过去延续千年的为一代正统之王立法的说法,对于任何一个妄图借“《春秋》为一朝立法”之理论来行专制独裁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二、“三世说”到“一统论”
《春秋繁露·楚庄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原儒·原学统》曰:“董生受学公羊寿,与胡毋生业,其所说三世义,最符于《公羊传》。”[3]425然而熊十力认为董仲舒的所谓有见三世,提倡君臣恩义,这与《春秋》极端相反,纯是统治阶级之史法[3]425。在熊十力看来,《春秋》改乱制,即是改革君主制度。董仲舒所谓的诛暴君而另外拥戴贤君,所谓易姓更王,称不上是革命。
因此,熊十力对董仲舒的三世说重新加以诠释。熊十力说据乱世有君主,因为此时民众觉悟低下需要君主的领导。而到升平之世,民品已经大有提到,有了自主自治之权利,此时就不应当再有专制君主,但是自从有国家以来,人民习惯于君主的信念,于是仍然有君,但此时是虚君,君权受到限制,只是作为维系群众信仰之用,正所谓“无用之用”。“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而承备具之官,足不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宾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2]258。他解释“无为”为“虚君权”之义,“承备具之官”的意思则是“自中央到地方政区,百官无不备,而各司其职,各治其事”。可见,熊十力以现代西方的君主立宪理解董仲舒学说中的《春秋》升平之世,赋予其现代民主精神。
到了太平之世,“夷狄进诸夏”,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需要说明的是,“诸夏”指的是能服于礼仪而有高尚智慧富于创造之民族,于是全人类没有不平等的担忧。《春秋繁露·俞序》云:“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2]253熊十力说此时的人们都能用功于内,即在内心修养上下功夫,于是仁义之道行而侵害之风气熄灭。《春秋繁露·观德》云:“鲁晋俱诸夏也,讥二名,独先及之。”又《春秋繁露·俞序》云:“亦讥二名之意也。”[2]253因为二名为不合乎礼仪所以讥之。
此外,太平之世,董子还有存三统之说。《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曰:“《春秋》作新王之事,绌夏、亲周、故宋。”熊十力解释说:“统之为言,宗也,一也。言其统一天下之志,而为天下之所共宗也。统以三,《春秋》当新王,一也;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周之道为《春秋》所直接,故亲周,二也。宋者商后,商汤承尧舜禹之道而传至于周以逮《春秋》,故亲周而不得不上及商,是以故宋,三也。”[2]258由此熊十力得出结论说“三统元是一统,一者仁也,《春秋》始于元,元即仁,虽遂世改制而皆本仁以为治,《春秋》当新王,即以仁道统天下也。”[2]259
熊十力的通三统,三统原是一统,即仁统。此说与董仲舒的存三统归于一统也就是大一统,在形式上非常相似,但实质却不同。董仲舒将其视为大义,是就政治来说的,并非真有三统。熊十力将其视为微言,是就文化而言的,借事明义,即以仁道统天下,以此达到天下太平。而继统之人,即不仅指天子,凡能行仁之人,就能维护统之绵延不绝,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熊十力认为孔子作《春秋》制素王之法,孔子之后能继斯统者,并非天子,而是能行仁道之儒,如濂溪、二程等,熊十力亦以斯统自任。熊十力借董仲舒三世说发挥成“一统论”,其说出于董仲舒而超越董仲舒,直接探源孔子,成为后来新儒家春秋学的研究方向。
三、以“元”统天到“元”乃“仁”也
熊十力说不懂得人的生命本体和道德主题,仅仅依一种科学如物理学或生物学中的一种学说去解释宇宙万化之源或生命之源,则未免以管窥天。《春秋》以元统天,董子讲以“元”为本,如《春秋繁露·重政》云:“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尤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2]247熊十力认为董子此语最为深邃,值得后学好好推敲,“董子言《春秋》,首发明元义,以为此经之宗极。与《大易》首建乾元同旨。内圣外王之学,其源底在是也。夫元者,万化之宗主,万物之本命”[2]248但是这仍然只是属于外在的,没有从本体论方面反己体道。故《原儒·原学统》曰:“董生《繁露》,名为说《春秋》,而实建立事天之教。”[3]427由于董子只有宇宙论,而无本体论可言,所以熊十力认为董子乃一“事天之教”者。
熊十力在董仲舒外在“元”论的基础上加以扩展,既言宇宙论,又言本体论,不只就天道,更就人事而言,天道人事兼具,内圣外王并备。熊十力的春秋为万世制法说,既然认为倡导革命,反对君权,那么治法就不能以君臣恩义,而要以仁义为据。熊十力曾举《春秋繁露·仁义法》为“先义后利者,先自正而责人”之例证, 即“《春秋》之所治, 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 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
为仁。”[3]498-499
熊十力认为董仲舒虽知《春秋》特重仁义,然对于二者的关系,却不知其关连及差异之处,以至仁义混而为一,而成君臣恩义。熊十力说:“仁义可以体用言,仁是体,义是用,而义者乃仁之权,两者虽非相即,然亦不离,看似相反,实则不违,诚乃相反相成。”[3]499以仁而言,熊十力认为即使父母之于子,虽必以仁,然犹有义在,以为权衡,方无所失。而董仲舒却说“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唯有仁,而不度之以义,则必流于姑息而反害之,此非《春秋》本旨。以义而言,熊氏认为“义之法,在于正人,必先正我”,[3]499唯有先正我而后能正人,而正我之后亦必进而正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务使人我皆正,所谓达则兼善天下,方是《春秋》外王之教。而董仲舒却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恰恰与熊十力相反,虽亦强调正人必先正我,然正我之后,并不进而正人,己立而不立人,己达而不达人,不能人我皆正,只是独善其身,实非《春秋》本旨。
总之,熊十力扩充了“元”的含义,除了具有万物之本之义外,更赋予其至高意义,即“仁”的意义,即“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既然天地万物为一体,那么就是说人人平等,不该有专制,应当推翻君权。因此,君权不应高高在上,而是人民自觉自主,如此之天地,才是一个人人平等之世界。
熊十力重新诠释了董仲舒的春秋改制、三世说和“以元统天”论。熊十力将董仲舒的春秋为一世制法改为“万世制法”;还将董仲舒的三统说总结为“一统”;在董仲舒的“元”的宇宙论基础上扩充上本体论,即“仁”的理论。总之,熊十力阐释的董仲舒学说是以“仁”为最终落脚点的。熊十力认为《春秋》之道,“内圣”而“外王”,“以仁道统天下”,由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是人的内心觉悟不断升华的阶段,据乱世人们觉悟低,所以需要君主的领导;升平世人们觉悟提高了,可以有自治的权利,所以不再需要专制而应该是虚君;到太平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全人类无不平等,此时应当废除君主。由熊十力的三世历程可以看出他把对个人人性的改造,看成是最根本的东西,他认为只有改造人性,使人的真性即“以宇宙万物为一体”得到切实充分的发挥,世界才能达到民主进而以臻大同。
熊十力对于董仲舒学说民主精神的阐扬,是其儒家民主自由政治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熊十力的儒学思想体系是针对“五四”后思想界反儒学运动而展开的,意图谋划传统儒学的现代化发展。他侧重从儒学的“价值阐扬”上去复兴儒学,彰显儒学特质,克服了“五四”学人对于儒学的片面批判,确立了儒学传统的人文价值意义,然而,熊十力没有从学理上深刻思考儒学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融通关系,而只是用“六经注我”的方式,以“中体西用”的思维来谋求儒学的现代化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往民主自由的现代化之路。尽管如此,我们亦不能否定熊十力以自己独特方式为中国实现民主自由而孜孜以求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1]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三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 熊十力.熊十力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3]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六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Xiong Shil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rn Democratic Spirit in Dong Zhongshu’s Theory
JIANG Shuhong
(Jixia Academy, Zibo Vocational Institute, Zibo, Shandong 255314, China)
Xiong Shili reinterpreted and developed Dong Zhongshu’s theory. He held that there were sublime words with deep meaning in Dong Zhongshu’s theory which could adapt to the present society and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y mainly referred to the system reform i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ory of three times”and “Yuan as the origin of Tian”, which Xiong Shili respectively amended into “system for all ages”, “theory of unification” and“benevolence”. These three theoretical systems that Xiong Shili developed from Dong Zhongshu’s theory had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oppose Guomintang dictatorship and positive value to reveal the humanistic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ism, but this did not solve the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therefore, it was not possible to find a real way to democracy and freedom.
Xiong Shili; Dong Zhongshu; democratic spirit
B26
A
1673-2065(2016)05-0045-04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5.009
2015-06-02
姜淑红(1983-),女,山东潍坊人,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