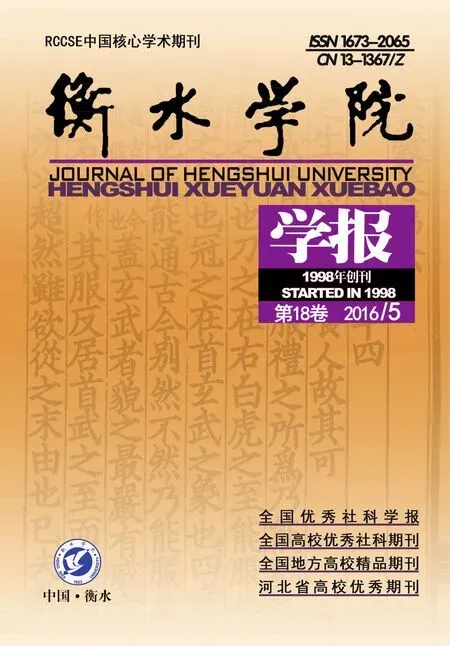儒者使命:面向生活,重建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6-11-17张小星
张小星
儒者使命:面向生活,重建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小星
2016年8月20日至21日,“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举行。会议由山东社科院文化研究所、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等六家单位共同举办,来自北京、上海、香港、重庆、山东等全国各地的近6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生活儒学”的以下方面展开了讨论:思想视域与方法论(与现象学比较)、生活存在论(生活、情感与存在)、变易本体论(形上学建构)、中国正义论(形下伦理学建构)、国民政治儒学(政治哲学);若干特定观念(时间、语言、诠释、历史、社会、宗教等)、“儒学三期”新论(儒学史观)。会议的焦点与热点问题,是对“生活儒学”的理解与评价,涉及生活儒学与形而上学、现象学、传统儒学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生活儒学与形而上学
生活儒学突破了传统儒学的“形上-形下”二级架构,提出了“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或者“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三级架构。这就涉及生活儒学如何定性定位的问题。
傅有德(山东大学教授)认为,生活儒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却是一种“西绪福斯式的形上学努力”。生活儒学尽管区分了形而下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形而上学(关于终极实体、道、性命、心体的学问)和前形而上学的本源论(即生活本身或生活领悟)三个层次,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因为生活儒学的“生活”不是指人的现实生活,而是在逻辑上先于人类、先于世界上任何物质和精神存在的本源状态。这个模式是被怀疑论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所批判过了的。这种西绪福斯式的形上学努力,尽管显示了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且这确实是在做哲学,因为真正的哲学就是一种概念的、逻辑的甚至是诗意的“思想”;但这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Sisyphus)一样,穷其一生致力于将神推下山的石头一次又一次地推到山顶上,这其实是徒劳的,因为自然科学和包括道德哲学(伦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并不一定需要形上学为基础。
对这样的“形而上学”定性和定位,胡波(重庆社科院研究员)表示不同意,指出:生活儒学的基本进路乃是“回到存在而重构存在者”;生活儒学的“生活”其实就是现象学所讲的“面向事情本身”的那个“事情”,既不是纯粹概念思辨的东西,也不是感官经验把握的对象。诚然,生活儒学要重构的存在者就是传统儒学的“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即传统儒学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但是,前此的“事情”“生活”,即由本质直观给出的“存在现象”,跟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所讲的“本体”是有根本区别的,它们是两个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东西。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针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提出的质疑,对于现象学所讲的本质直观所给出的存在是基本无效的。
二、生活儒学与现象学
胡波又指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现象学有很大不同,它不只是要做“解构”的工作,并非止于对存在的终极追问,而且还要在通过“去蔽”而开显出来的生活地基上,重新进行儒学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建构。这并没有西绪弗斯那样的悲壮。生活儒学一方面对既有儒学原教旨主义的形下学和心性论人性论的形上学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而感到非常不满,另一方面身为儒者又必须坚持儒学的根本,这就促使它要去找到一个更原始的基点,来对儒学的形上-形下体系加以重新建构。
涂可国(山东社科院研究员)也指出,生活儒学的形而上学建构,是针对后现代主义而言的,后现代主义要解构形而上学。
谢爱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也对生活儒学与现象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方面,生活儒学无疑地借鉴了现象学的方法,尤其是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借助于现象学的进路,生活儒学突破了传统儒学的“形上-形下”的二元本体论结构,揭示了在传统儒学中长期被遮蔽的、某种更为本源性的东西。但另一方面,生活儒学不是现象学,无意于建立“现象学儒学”的学科体系;对于现象学,生活儒学是在工具论和方法论层面采用的,是采取的拿来主义的态度,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
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也分析了生活儒学与现象学的关系,认为生活儒学所强调的存在论的源发性,这实际上就是儒学的活泼泼的、生生不息的自然“天道”;你可以说它是“存在”,也可以说它是“逻各斯”(Logos),这些都可以在本体论或存在论层面上讲,但落实到“生活”的实处,它实际上就是在讲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活动。这正是“让哲学说中国话”,让中国哲学的研究与思考跳出古代的语言概念、范畴,用我们现代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汉语来说哲学,把我们的古典哲学语言,以及我们这些年来接受消化的外国哲学概念和范畴,换成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汉语语言去说、去思。
三、生活儒学与传统儒学
赵法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认为,生活儒学提出了诠释儒家性情关系的第三种模式。关于性情关系,儒学史上有两个最重要的模式:一个是朱熹的模式。朱熹苦参“中和”十六年,“中和新说”和“中和旧说”有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中和新说”安置了“情”。原来的“中和旧说”,“性”是未发,“心”是已发;中和新说则以“性”是未发,“情”是已发,“心”统性情,这样一来,他就把“情”安顿了。一个是牟宗三的模式。牟先生批判朱熹的性情论,说朱熹将心、性、情三分,理、气二分,其“理”只存有、不活动。在牟先生的模式中,两种思想资源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个是康德的道德哲学,一个是儒家的心学。而生活儒学实际上开出了与朱熹、牟先生不同的另一种诠释先秦儒家道德思想的进路,提出了的“情-性”结构,并对儒家思想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读:比如对“生”“诚”“不诚无物”“万物皆备于我”的存在论解释,展示了原始儒家思想中的现代性内涵;肯定“生之谓性”的意义,把“生”作为“性”的重要特征,生即是性,这个“生”不是一般的“生”,而是“生活”本身,而生活本身是一种情感的存在、情绪性的存在,而且这种情感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情感,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情感,由此开始产生了存在者,产生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情感,产生人的道德情感,由此而产生一种新的性情关系模式,推进了儒家思想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涂可国进一步指出,生活儒学的形下学建构“中国正义论”,代表了上个世纪以来儒家“义利观”研究的范式转换。儒家“义利”概念的研究、儒家“义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主要是立足于“义利观”这个角度,也就是“义利之辨”这个角度,来对儒家的“义”进行一种探索和研究,就形成了“义利”模式。到了21世纪以后,对儒家的“义”或者“义学”的研究,进入另外一种范式,也就是以黄玉顺为代表的“正义论”建构这样一个角度,来对儒家的“义利”进行解释,生成了“正义论”这样一种解释模式。
四、生活儒学与现实生活
针对学界有“生活儒学不生活”的说法,意谓生活儒学只是一种理论建构,而不是将儒学“生活化”、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林存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表示赞成生活儒学的哲学的、包括政治哲学的进路。先要以理服人,而不是拿出一个东西,什么“儒教”,就要别人认同,甚至强制所有人接受。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先得把问题思考清楚,先讲出一套道理来,讲出能说服人的东西,哲学上立得住,理论上有根据,才能说服别人、影响别人。不然的话,就会引发很多让人反感的东西。儒家最根本的精神是什么?是“学”。儒学,儒学,是以“学”为根基,然后让人去学,慢慢感化别人,感动别人,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而不是强迫别人去接受。
林存光认为,生活儒学是“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就是儒学怎么来理解生活,理解生活与儒学之间的关系。儒学一热,这个儒学、那个儒学都纷纷地冒出来,什么政治儒学、心性儒学,还有社会儒学、民间儒学,历史上还有帝制儒学,这些“某某儒学”都是儒学的不同维度、不同面向;但生活儒学与之不同,它事实上意味着对儒学的一种总体的本真含义的理解和把握,而不是用儒学的某一个方面、侧面来限定儒学就是怎样怎样的东西。
傅永军(山东大学教授)进而指出,生活儒学有两个层面,特别值得学界关注:第一、生活儒学超越了“国族叙事”,成为一种淡化了民族及地域视野、而注重思想观念普遍性的儒学体系。在民粹主义泛滥的今天,我们从生活儒学看到的是这种儒学思想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注,它拒斥用“大中华帝国文化安排天下秩序”这样一种狭隘的心态,主张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各种信念、原则进行批判性的审查,培养人们的理性与自由精神,引导人们过一种经过慎思的生活。可以说,生活儒学是一种致力探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负责任的儒学创建活动。第二、生活儒学走出了“儒西对抗”的思维模式。在中国经济腾飞、GDP成为世界第二以及国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我们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中西会通,中国的现代性过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制造儒学与西方学术的对立,不是提倡儒西对话,而是制造儒西对抗,甚至认定儒学的崛起意味着西方学术的彻底衰落。然而,与之不同,我们生活儒学中看到的是儒西对话,包括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尤其是与现象学、海德格尔哲学对话。生活儒学超越儒西对抗,让儒学与西方学术思想辩证地相互诠释,以中国儒学思想和概念会通西方哲学话语,创造出既适合中国儒家哲学的概念、范畴和准则的现代性表达,又能将中国儒家思想和概念带入世界的生活儒学哲学话语系统。生活儒学为中国思想在中国大国崛起背景下,如何避免陷入一种文化上的大中华主义,给出了一种警示,亦给出了一种示范。
任剑涛(清华大学教授)指出,生活儒学属于当前学界“反‘复魅’”“再‘祛魅’”的儒学。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特质的一个基本归纳,就是“以理性祛除巫魅”。这样的祛魅运动,在思想领域中表现为一切宗教和神秘的东西退隐到社会生活的幕后,理性主导社会生活;在政治领域里,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权力的公开化与分权制衡等等。政治的神秘性不再,康德所讲的“人为自己立法”,也就是诉诸理性原则建构政治规则成为元规则。复魅运动的突出特点是,认定现代生活筹划的最大弊端是缺乏神圣价值寄托。因此人对自己立法规则的信从,即因信而行的信从强度是不够的,现代规则因之缺乏权威性。就中国现代儒家来看,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从属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现代性的启蒙传统的“祛魅”运动;而目前蒋庆等“大陆新儒教”则从属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在西方蔚为潮流的清算启蒙的“复魅”运动,包括宗教的复魅和世俗权力的复魅。现代儒学必须是启蒙儒学,即必须回应托克维尔所说的大众民主时代的诉求,这就是说,当前儒学必须“反‘复魅’”,即必须“再‘祛魅’”。
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认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生活儒学在儒学领域的崛起。他对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第一,是从对外的角度,儒学应该和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毫无疑问,在世界上来讲,处于主流地位的思潮是自由主义。儒学的复兴不是自言自语,那么,中国儒学、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和世界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文化展开深度的对话。第二,从对内的角度,儒学的崛起和复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看儒学自身是否够能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创造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儒学的复兴不在讲堂上,不在研究院、研究所,最关键的是能不能落实到生活本身去。而落实到生活,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给爸爸妈妈洗洗脚这些表面上的举动,而应该是创造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克服自由主义局限的、更富有人情味的生活方式。如果儒学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就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一个基础。在这样一个要求之下,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生活儒学,它的意义是特别重大。
责任编校:魏彦红
我校董子学院参与合办“董仲舒与儒家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9月28—29日,“董仲舒与儒家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召开。该会由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和衡水学院董子学院共同主办,由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国学院、先贤先烈英模精神研究院承办,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协办。本次会议是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于2015年10月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学术会议,来自海内外学者60余人参加。我校董子学院魏彦红教授、曹迎春教授、白立强博士、王文书博士、石柱君副教授、卫立冬教授等提交论文并参加了研讨会。
9月28日上午研讨会隆重开幕。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余治平会长首先致辞,余会长在致辞中申明了此次会议选定在孔子诞辰纪念日的“时间意义”和选定于董仲舒终老之地西安的“空间意义”。中华孔子学会李存山副会长代表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张践主任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致辞,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高度评价董仲舒思想研究的重要意义。会议承办方、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刘家全董事长致欢迎辞。衡水学院董子学院执行院长魏彦红教授简要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背景并宣读了中国孔子基金会贺信。大会也收到了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先生的贺信并在开幕式进行了宣读。

参加主题演讲的学者

董子学院参会教师与董学大家合影
在28日上午大会主题演讲阶段,共有6位学者发表学术演讲。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顾问、人民出版社编审金春峰先生首先演讲。他讲到汉朝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读司马迁的《史记》常会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升腾起一股英豪之气,而汉代的那种奋发精神正符合我们当前时代的精神,因此研究汉代思想十分重要。一个民族没有思想的指导是不可能崛起的,董仲舒这样的大思想家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产物。董仲舒与汉武帝一文一武,共同创造了那个时代的辉煌。接着金先生围绕其文章《中国文化的特性与“三统”史观》进行阐述,金先生运用考古材料,将思想史研究与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开创性地提出后世“三统说”之尚黑、尚白、尚赤,是根据陶器而作的系统化的建构。
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存山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董仲舒在中国儒学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开创了秦以后“独尊儒术”和汉唐经学的新格局,而且对宋代的“新儒学”也有重要的影响。董仲舒在中国儒学和文化史上占有堪与孔子和朱熹比肩的重要地位。
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孔子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关于董仲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他主要探讨了董仲舒是否讲过“三纲五常”,以及如何看待“三纲五常”两个问题。刘教授认为,“三纲五常”在历史上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它孕育于先秦而成型于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思想,但尚没有明确把“三纲”与“五常”结合并称,而往往把“三纲”与“六纪”(或五纪)并称,叫“三纲六纪”或“三纲五纪”。将“三纲五常”连称,最早见于汉马融所说。对于如何看待“三纲”的问题,刘教授认为“三纲”并不等同于专制。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曾振宇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民心即天心: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与人文蕴涵》,他首先从天论与天命、天心入手,进而证明“民心即天心”,“民心”在“人道”的具体呈现是仁义,接着从“民心即天心”高度论证制约最高权力如何可能,董仲舒政治哲学如何由此获得非常厚重的形而上根基,最后阐释董仲舒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何为政治之善。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顾问、日本北九州大学邓红教授以《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式历史哲学》为题进行了演讲。他认为作为历史学的春秋公羊学,经过董仲舒之手,已经从历史的范围脱离,朝着政治、法制、民族政策等的方向倾斜而去,最终使得他的春秋公羊学获得了新的哲学内容。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哲学有着天道化、阴阳五行化、实用化、大一统化等丰富内涵。
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张践教授演讲的题目是《秦汉之际的文化选择与董仲舒的历史贡献》,这是其专著《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中着重研究的一个问题。张教授从政治学的角度首先分析了秦王朝“以法为教”的致命缺失。他指出政治权力必须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没有文化基础,权力就是暴政。秦王朝只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权力,没有给权力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外衣。接着,张教授又分析了汉初黄老“不言之教”的利弊得失。汉初统治者选择了黄老之术,但黄老政治的本质仍是法家政治,在建立合法性上仍有极大不足。黄老要求统治者行“不言之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老百姓,可是“不言之教”无法深入百姓头脑。所以为权力寻找合法性、建立政权权威的重任便落到了董仲舒身上。
以上进行主题演讲的6位学者都是学养深厚的董学及儒学研究大家,他们的演讲高屋建瓴、角度新颖,参会的学者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28日下午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举行了第六届“尊师节”暨祭孔仪式,特邀与会嘉宾12人参加。其余人员分两个小组进行讨论。
董子学院魏彦红教授、白立强博士和石柱君副教授参加了第一小组的讨论。魏彦红教授演讲的题目为《董子思想对其故里元明清书院的影响》,她以元明清时代衡水书院的代表作为切入口来谈董子思想对后世家乡书院的影响,指出这些书院都是受董子思想影响、为纪念董子而修建,其学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明显受到董仲舒思想的影响。
白立强博士演讲的题目为《“学”“习”之“说”的道体意蕴及其当代价值》,他认为“学而时习”之“说”内含着深刻的道体意蕴:一方面,“学”“习”分别意味着悟道、行道;另一方面,行道之中自然生成超然物外的“悦感”体验。“学”“习”“悦”三者之间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蕴含着宇宙法则之基于物质世界而又超脱于此的道法律令。此中内含的立身行道、至诚感通、诚者自成、自得其乐的道体法则对于当代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石柱君副教授演讲的题目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当代社会价值研究》,她从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天人合一”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天人合一”思想对衡水湖旅游业发展的启示、对建设北方生态宜居滨湖园林城市的启示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卫立冬教授提交了《倾力打造多个平台,全方位推进董学事业》的文章,该文章全面介绍了衡水学院对董学研究的开展及对董子文化的传播的情况,分别从“一个专栏、三个会议、一套丛书、两个学会、一个董子讲坛、一个董子学院、一个董子研究院、一个孔子学堂、一个国学教育示范基地、一座董子像”等十个方面进行了推介。
董子学院曹迎春教授和王文书博士参加了第二小组的讨论。曹迎春教授演讲的题目为《董仲舒官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她认为董仲舒构建起了一个“道—德—法”的官德有机系统,基础是形而上的“为官之道”,主体是修身爱民的“为官之德”,保障是任贤考绩的“治官之法”,这对当前的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王文书博士演讲的题目为《周辅成和<论董仲舒思想>》。周辅成的专著《论董仲舒思想》在董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盘点建国后董仲舒研究成果,该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绕开的。这本著作是特殊年代里的特殊著作,是董学研究的里程碑,深深地镌刻着时代的烙印。王博士以小见大,从一本董学研究著作入手使人了解到五十年代董仲舒研究的时代风貌。
衡水学院董子学院的6位学者提交的论文选题新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提升,发言获得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这表明董子学院的董学研究队伍已经初步成型,逐渐走向成熟。
9月29日上午6位学者进行了主题演讲。
陕西省孔子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副会长,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刘家全董事长在发言中主要介绍了他的两本著作《中国精神论纲》和《中国文化论章》中关于“三纲五常”的分析。刘先生指出“三纲五常”问题与中国近百年来的命运关系十分密切,百年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就始于对“三纲五常”的批判。而西方虽然也有豪门与平民之分殊,却没有对类似“三纲”的“等级理论”的大肆批判,究其原因乃是中西方文化对人的认识的差异。中国的“三纲”说不平等论,是指的具体人、角色人,西方的自由平等说,是指的抽象人、类人格的平等。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会长、上海社科院余治平研究员演讲的题目为《董仲舒的<春秋>“十指”述要》。余治平先生通过对《春秋繁露·俞序》的解读,认为孔子作《春秋》的根本目的与实质意图就是要通过对春秋时代242年间的历史事件的分析、议论和评判,为后来的圣王明君提供一套治民理国、维持伦常秩序、整合世道人心的基本法则,而这套基本法则的核心内容,被董仲舒概括为“六科”与“十指”。董仲舒的《春秋》“十指”即安百姓、审得失、正事本、明尊卑、着是非、序百官、立教化、达仁恩、次阴阳、顺天意。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李祥俊教授演讲的题目为《从<盐铁论>看后汉武帝的价值观冲突》,李教授认为《盐铁论》一书从辩论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的废立问题入手,附带讨论了汉帝国与匈奴、西南夷等的关系问题,就道义价值与功利价值、价值主体、价值秩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体现出秦汉以降家庭本位的君主专制主义下官僚阶层和民间豪强势力的不同价值诉求,前者沿袭着“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侧重普遍性的价值诉求,后者反映了秦汉新型社会形态稳定后传统家庭、宗族社会以变化了的新形态复归后的侧重特殊性的价值诉求,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正是后汉武帝时代社会政治格局变动的真切反映,而汉昭帝和权臣霍光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的“霸王道杂之”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合理选择。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国民教授演讲的题目为《论孔孟之仁义价值的内在性》,刘教授指出儒家之仁义价值的内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仁义价值是从自然本性中升华而来;第二,仁义价值是从现实世界中发展而来。仁义之内在性表明,仁义不是绝对的普遍原理,而是相对性、特殊性、语境性。仁义之内在性有重要意义:一是个体在继承传统的仁义中不断刻入创新的内容,而保持仁义的鲜活生命;二是重视个体的道德品性和人格的培养。
德州学院常务副校长季桂起教授演讲的题目为《论<楚庄王第一>在<春秋繁露>中的地位及作用》,他认为在这一篇章中,董仲舒从解读《春秋》的有关记史方式、规则与策略入手,阐述了“《春秋》大义”的内涵,发掘了隐含在《春秋》记载中的儒家的历史价值观和政治哲学思想,为整个《春秋繁露》确定了基本的思想脉络,可以视为该书的一个总纲。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国学院王即之副院长演讲的题目为《董仲舒是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家》,他认为无论是从理论体系还是致用功夫考量,董仲舒都远远超越了他之前的孟子、荀子,也是他之后张子、程子、朱子和更多的其他儒家学者所远远不能企及的。
下午与会人员参观了关中书院和位于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下马陵(董仲舒墓)。“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下马陵(董仲舒墓),相传汉武帝经过这里时,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下马步行,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
衡水学院董子学院曹迎春教授参观后写诗一首《拜西安董子墓》:
董生挥袂辞广川,扬鞭千里入长安。
宦海浮沉几十载,青史褒贬两千年。
骄王何足论正谊,强君岂宜谈伸天。
枯冢东望桑梓地,梦魂可曾归故园。
刘贵生副教授和诗一首:
汉武雄才广求贤,仲舒通经方卓然。
三对廷问有大计,两相骄王不平凡。
宦海浮沉由天定,青史褒贬任人言。
埋骨何必桑梓地,此心安处即家园。
两首诗作,表达了故里学者对董子的深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