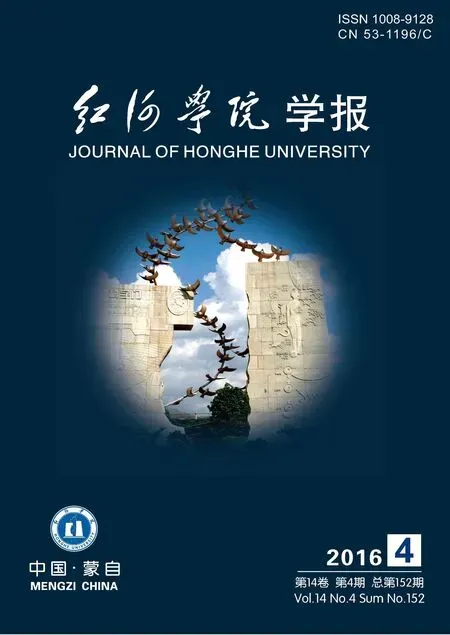解读《德伯家的苔丝》之生态维度
2016-03-15林晓青
林晓青
(三明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三明 365004)
解读《德伯家的苔丝》之生态维度
林晓青
(三明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三明 365004)
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处于全盛时期的托马斯·哈代是一位具有超前的生态意识的作家。在经典之作《德伯家的苔丝》中既有对自然风景的细致刻画也有对工业化生产带来的生态危机的揭示。文章以新兴的生态批评为理论为依托,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切入,解读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旨在激发人们与哈代产生共鸣对自然心怀敬畏,对环境尽心保护。
苔丝; 生态批评;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生态危机
DOI:10.13963/j.cnki.hhuxb.2016.04.017
托马斯·哈代生活在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彼时正值英国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工业革命抵达巅峰状态,当时人们正沉浸在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工商业繁荣的喜悦之中,对工业文明之下的“欣欣向荣”盲目乐观。哈代对此冷静旁观,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狂妄自大、欲望膨胀、对自然索求无度最终危及的是人类生存的空间,陷人类自身于生态危机的深渊。哈代将这份关注与思考投射在作品创作中,因而,无论是在其小说还是诗歌当中都能阅读到他对自然的深切关照。哈代一方面以灵动的笔触展示着大自然无以比拟的美,另一方面以现实主义批判的眼光控诉着人类对于自然的肆意破坏。哈代的远见卓识、深忧远虑成就了哈代生态文学大师的美誉。
当人类在享乐主义的思维模式下不断追求物质文明带来的短暂欢愉之时,伴随着的是大自然被过度消费,在人类对它无限制的开发和利用当中,自然生态危机随之而来。机械化生产代替传统劳动,使人与人之间缺乏有效的情感交流,彼此变得冷漠疏离、关系异化,社会生态危机的出现在所难免。在牺牲自然田园风光以换取城市化进程的过程当中,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心逐渐消淡,人类在自我为中心的路上越走越远,迷失在欲壑难填的困境里,精神生态危机相伴而生。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以及精神生态危机都是生态批评视域之下至关重要的生态维度。生态批评是一个非常庞杂、开放的批评体系,同时兼备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征。“生态批评立足于生态哲学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将文化与自然联系在一起,揭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想象力的危机。其理论内涵为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创作文本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批判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观念,重新构建文学经典。”[1]16《德伯家的苔丝》很好地体现了生态批评视野下的不同维度之中的生态危机,以此为依托解读作品中的生态思想,探析哈代的生态观。
一 自然生态危机:自然的梦幻与幻灭
哈代将自身对于自然的尊崇喜爱诉诸笔端,在哈代的作品里不缺自然的玄远、静谧、柔美与瑰丽奇特,然而这些让人迷恋的无限风光最后往往招致人类的破坏,难以保持原貌。其原因主要在于哈代笔下的风景往往与人物命运息息相关,并不止于单纯地描绘自然景色。“那些令人无法忽略的景色优美时刻,如小说开篇的马洛特村五月节游行跳舞,还有小说结尾处悬石坛上的日出,都让人们相信,哈代未经雕琢的电影表现手法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景色描写。”[2]225其实质上,苔丝生活场地的每一次变化都与所从事的职业及不同的景色相联系。伴随着苔丝的劳动环境越来越恶劣,承担的工作越来越繁重的是机械化生产的参与越来越多,风景遭受的破坏程度越来越严重,作品中自然美景从梦幻到幻灭正是苔丝的命运从生机勃发到黯然消亡的过程。
苔丝出生在田野绿意葱茏、大气清澈透明、景色如诗如画的马洛特村,“这儿距离伦敦虽然不过四个小时路程,它的大部分地区却还是旅游者和风景画家足迹未曾到过的。”[3]8在这片未经开发的土地上生长着未谙世事、天真烂漫、未经雕琢、自然纯朴的苔丝。由于苔丝的疏忽家中赖以生存的老马死于非命,这迫使苔丝不得不离开佳木丰沛的出生地去从事新的谋生职业景色也随之变化:“广阔无垠的景物往四面伸展,背后是苔丝从小生长的青山
坐落在川特里奇的杜伯维尔庄园是“一座纯粹为了享乐而建造的乡间别墅”[3]33这新建的大厦色彩艳丽在温和的自然环境里张扬、突兀与周边的自然景象格格不入。而家禽饲养员苔丝的工作场地在一幢古老的茅屋里,“茅屋所在的场地原是个花园,现在踩得平平的,铺了沙子,成了个方形的广场。”[3]52这里的自然明显已有人为加工的痕迹,按人的需求进行了改建。庄园里还有催熟的草莓与温室里娇艳的玫瑰,他们都无需遵从自然的生长规律,在现代技术手段之下按人的意志开花结果。如果说花床、果园、温室只是年轻的少庄主阿历克对自然生长规律的违逆,那么他对“自然之女”苔丝的侵犯已然注定了自身命运里无可挽回的悲剧。自然对于人类的肆意破坏绝不会无动于衷,她必将对阿历克做出审判,因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4]304-305阿历克看似主导了自然,利用技术手段成功地违抗了自然,但等待他的则是自然的报复,自然之手将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马洛特村到川特里奇,经历的肉体与心灵双重折磨的苔丝已明白了人世之险恶,她回到了家乡,离群索居,在大自然的抚慰中慢慢走出阴霾:“她在寂寞的山峦和峡谷里默默独行,和周围的自然元素化成了一体。她那悄悄闪动的身影化作了景物的的一部分。”[3]85她与自然相处如此和谐,很好地诠释了哈代人与自然理当并驾齐驱,“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大自然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具备疗伤的本领,与自然身心交融的苔丝懂得了过去的终将会成为过去,时间能把一切苦难不幸淹没,并不会因为她的痛苦而有所改变:“树还是照样地发绿,鸟儿还是照样地娇鸣,太阳还是照样地辉煌。她再忧伤,这熟悉的环境也不会因之暗淡;她在痛苦,它也不会因之凋萎。”[3]91人类究其实只是浩瀚自然中渺小的一份子,唯有心怀敬畏,真诚以待,才能独善其身,享受生命的自由与美好。
在自然中汲取了力量的苔丝为了遵循生命的本能去寻求更多的欢乐,第二次离开了家乡,来到了“空气清爽可人、质地轻灵”的泰波特斯从事挤奶工的工作。“佛鲁姆河的水却清澈得如同福音传播者所见到的的生命之河,迅疾得如流云的影子,还有卵石历历的浅濑,整天想着天空潺潺碎语。”[3]105生机勃勃、美丽富饶、迤逦磅礴的牛奶场,让苔丝精神焕发,宛若新生,在这里苔丝度过了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她自然的天性发挥到了极致,连脾气最坏的奶牛在她温柔的手指下都变得百依百顺。年复一年沉浸于各种学问,未曾对自然加以关注的克莱尔在苔丝到来之后,被她的自然本色深深吸引,他不由感叹“那个挤奶姑娘真是个大自然的女儿,多么鲜活,多么天然纯真啊!”[3]121他们倾心相爱,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然而在新婚当夜,苔丝坦承了从前所受过的屈辱,思想被传统的基督道教准则所左右的克莱尔无法体谅苔丝的艰难处境,弃她于不顾,选择远走巴西。这对苔丝而言无疑是重重的一击,婚姻失守的她再次踏上颠沛流离的艰辛人生路。
心灵再次受到重创的苔丝劳动场所再一次发生转移,她从泰波特斯来到了燧石顶,景色再次变幻,初踏上这片土地,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片浅洼地上,有一个残破不堪的荒村”[3]281而且“那儿的凄凉冷落几乎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四面一望连一棵树也没有,在这个季节也没有绿色的草场;除了休耕地便只有萝卜;土地被结扎得十分单调的树篱分成了一大片、一大片。”[3]283在燧石顶苔丝的劳动显得“那么单调、沉闷、毫无变化”[3]313然而繁重的劳动并没有使她屈服,抱着对爱人回归的热切盼望,苔丝自尊自强地与命运抗争,只是冷酷无情的命运再一次将难题摆在了她面前:母亲病重,父亲去世,弟妹衣食无着,家人流离失所,爱人迟迟不归,生活的重重困难再一次把苔丝逼入绝境。在现实困境的步步威逼之下苔丝最终沦为阿历克的情妇,移居桑德波恩。
幡然醒悟的克莱尔追寻苔丝的脚步来到了桑德波恩,徘徊在这个旧世界中的新世界:“他能在树木掩映之中和星光衬托之下看到它高耸的屋顶、烟囱、阳台和塔楼。这也是一个由一幢幢独立的大厦构成的城市……”[3]377苔丝在这新兴的现代化城市里,犹如受困于笼中的金丝雀。阿历克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征服了象征着自然,代表着农业文明的苔丝。然而“哈代还是相信外部世界的物质力量,他不支持,甚至不容许个体的绝对胜利,他反复强调社群的重要和环境的力量”[2]106最终,自然借助苔丝之手终结了阿历克的生命,这是生态文明完成了对工业文明的终极复仇。人与自然若不能和谐相处,那便只能是两败俱伤的结局。
“人类历史长期以来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根基之上的,农业文明的一大特性是人与自然尚且保留着较为密切的亲和关系。”[5]209以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之下,人类不断牺牲乡土田园风光以交换城市的高速发展,这必不是现代化值得推崇的成功经验,而恰恰是人类理应反思之处。随着工业革命影响的逐渐扩大,随着时代的潮流奔流不息向前涌去,大量的维持着农村传统风俗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劳作模式,“只好往大的人口中心逃亡了”。[3]352短短几年的时间,一切面目全非,乡村自然景色分崩离析,苔丝不无凄凉地发现,祖先遗址“周围的丘陵与山坡当年原是园林,现在树木已被砍个精光,土地也分割成了小片。”[3]361。巴西归来的克莱尔再次经过当年第一次遇见苔丝的草场时,惊觉“那里也是一片衰败的景象”。[3]373哈代饱含深情地亲笔毁灭了自己精心描绘的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美景,他以自然风光从梦幻到幻灭的过程无声控诉着工业文明无孔不入式的入侵给农业文明带来的伤害。
二 社会生态危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与弥合
“自然让人曾经是多么幸福而良善,而社会却使人变得那么堕落而悲惨。”[6]16可是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厌世逃避也不能摆脱社会对人产生的影响。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旦失衡,社会生态危机一触即发。《德伯家的苔丝》中,人与人的关系异化有几个方面的体现。一是苔丝与父母的关系上。天下父母心,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但是苔丝的父母亲却把女儿当成摆脱贫困的工具。鼓动她去认亲,一心希望她能嫁给有钱的少爷,她的母亲“几乎是从她女儿出生之日起就在为她自己挑选着乘龙快婿呢。”[3]43只要有钱,爱不爱自己的女儿似乎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苔丝要到有钱的本家庄园里做工了,父亲已经喝起了庆贺的酒,在心里颇为笃定地认为女儿一去将攀上高枝,麻雀变凤凰了。事情并未尽如人意,苔丝遭到所谓的本家阔少爷阿历克的奸污怀孕产子,母亲希望她能以此要挟阿历克缔结婚姻,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但苔丝却选择独自承受一切,她无法跟自己不爱的人共同生活,宁愿选择面对现实社会的责难也不愿屈就于没有爱情的婚姻。
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苔丝与阿历克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上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苔丝到杜伯维尔庄园去认亲,遇见了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阿历克·杜伯维尔,从此活在了此人的阴影之下,开始了悲剧的一生。成长于民风淳朴村落的苔丝对人世之险恶懵懂无知,最终被玩弄女性于股掌之中的阿历克骗取了贞操。她只能问责母亲“太太小姐们知道要防范些什么,因为她们读小说,小说里告诉她们这些花样。但是我是没有机会用那种办法学习的,而你又不帮我!”[3]83家庭贫困缺乏教育机会是苔丝失贞的一个因素,但阿历克的成心纠缠才是主要原因。受了伤害的苔丝选择离去,但命运之神并未就此给她予享受生命的自由,它让苔丝在生活最为艰难无助的时候重逢了阿历克。此时的阿历克已经是一位披着仁慈的宗教外衣,道貌岸然的牧师滔滔不绝地给农民布道,真是多么具有讽刺性的一幕。再见苔丝,阿历克马上抛弃了子虚乌有的宗教信仰露出本来粗鄙恶俗的样子,对她纠缠不休,威逼利诱。苔丝自强自立,绝不依附男人。但是,基于巧合或是必然,苔丝为了家人生计再一次向命运低头,委身阿历克。偏在此时备受挫折明白真爱可贵的克莱尔从巴西归来,欲与妻子再续前缘,阿历克对此冷言嘲讽,触到了苔丝的底线,她一刀结束了这个毁了她幸福的恶魔。而苔丝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付出生命的代价。
另一方面,苔丝与当时的社会也存在矛盾与冲突。苔丝生活在资本主义侵袭农村并强烈冲击固有的风俗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美丽聪慧、善良纯真、勤劳简朴的她对经济拮据的家庭主动承担责任。她处于社会的下层,作为一个无权无钱的农业劳动者,毋庸置疑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与欺凌。这些压迫与欺凌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经济的、权势的、肉体和精神的、还有宗教的、道德的、传统观念的。尽管苔丝大胆反抗传统的道德观念,勇于追求幸福生活,然而她却不能从心理上彻底摆脱世俗道德观念的羁绊。当社会舆论与深植于苔丝内心的传统道德观念跳出来阻止苔丝追求幸福的步伐时,她自己也犹豫了,自我怀疑了,也认可自己是有罪的,是不贞洁的。因而即便她离开故土,时间与空间都将协助她将往事掩埋的时候,她依然卸不下自己身上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只能一再拒绝克莱尔的追求,明明想靠近却只能选择躲闪。虽然苔丝最终听从了内心的呼唤,与克莱尔沐浴爱河,只可惜知道了苔丝过往的克莱尔狠心抛弃了她。她却为了维护丈夫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而委屈自己迁居别处去从事繁重的体力活不能回到泰波特斯的牛奶场工作。“她的返回难免会使她那备受崇拜的丈夫遭到谴责。还有,别人的怜悯她也受不了,别人在她背后对她的奇怪处境的窃窃私语更叫她难堪。”[3]275克莱尔对苔丝的放弃,使苔丝精神上背负了更重的负担,“她害怕城市,害怕大户人家、有钱人家、害怕世故,害怕农村以外的习俗礼数,因为黑色的忧患就是从上流社会来的。”[3]275社会给苔丝造成了内心难以抚平的创伤。哈代赋予苔丝坚强的信念,她始终勇敢地同命运搏斗,然而反抗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最终苔丝从自然中来,回归到自然中去,如梭罗所言:“最甜美、温柔、鼓舞人心的社会,都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7]101苔丝用死亡的方式完成了对自然的回归,找到了内心世界里最温暖舒适的人间社会,再没有嘲笑与伤害,只有安息与长眠。这是社会生态危机的环境之下苔丝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局。
三 精神生态危机:心灵的迷失与回归
在《德伯家的苔丝》的劳动场景中可以看到工业文明简单粗暴地把自然当作原材料,把人当作生产机器,不仅把自然破坏得千疮百孔,也使人的精神世界瘫痪、丧失生命活力。工业文明摧残的不仅仅是自然同时也扼杀人类天性中的美好。唯有回归自然、回归本性,才可以挽救人类。
作品中苔丝的社会身份随着劳动场所的转移而变化,她这样不断迁徙的状态伴随着的是她精神上的飘零,归属感的缺失。肩负养家糊口使命的苔丝原本可以活得顺其自然,在天然淳朴的马洛特村过着虽然艰苦但是精神状态健康、情绪饱满、充满希望,村里“每个姑娘感到外在太阳的温暖的同时,她们的灵魂也还沐浴在各自的小太阳的光中,那是一种美梦,一种纯情,一种习惯,至少是一种渺茫辽远的幻想。”[3]11但是,父亲对财富的渴盼将苔丝推出了马洛特村,让她自此远离自然,走向了居无定所,精神漂泊无依的悲惨人生。
不同于马洛特村,川特里奇从环境到乡民都已然是被工业文明浸淫的状态:“川特里奇一带以它的年轻妇女的轻佻惹人注目,这也许绝妙地反映了大梁子一带的精神状态。这一带还有个历史悠久的毛病:酗酒。附近农庄上的主要话题是:攒钱没有用。”[3]58“吃光、用尽、花完”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极致享乐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了川特里奇的主导。在这样的民风里,天真纯净的苔丝遭遇肉体和精神上的苦难似乎显得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在工业化的社会里,勤劳朴实的苔丝难以找到容身之所,可是当她身心俱伤,回曾经远离城市喧嚣的生养之地时,面对的是物却是人非的无奈。
苔丝在马洛特村默默地将息了两年多之久,这期间工业文明倚仗着蛮横的力量渗透到了这个原本“峰峦环抱,与世隔绝”的原生态村庄,小麦的收割交付于强大的机器,劳动人民机械地重复着捆麦捆的动作“单调得像时钟一样”[3]88麦子收割机强势霸道“机器每走一圈,围着麦地的窄巷便变宽一片,直立的小麦的面积也随着早上时光的消逝而缩小一片。大耗子、小耗子、大野兔、小野兔,还有蛇,纷纷后撤,好像躲进了城堡,并不懂得它们的避难所也寿命有限,也不懂得毁灭正等待着它们。到了下午它们的藏身之地便会缩小到越来越可怖的程度。”[3]87弱小的生命对大型机器心怀恐惧,无处藏身,以死而终,这是机器文明对自然的漠视与扼杀。当人类对自然丧失敬畏心,自然的报复也就开始了,其结果必然是自然生态及精神生态失衡。或许,即便苔丝没有离开马洛特村,她也迟早会以某一种形式被伤害,因为忽视自然生态的工业文明已无处不在,代表着自然的苔丝已无处可逃,滋养着她成长的村庄再不是原来的样子。
辗转流离,像一只失去家园的小鸟在寻找诗意栖居地,始终不能如愿。从马洛特村到川特里奇然后到泰波特斯而后是布莱地港继而来到燧石顶,苔丝的精神负担越来越重,当她抵达燧石顶时,苔丝已经像一只“掉进了罗网的小鸟”[3]290机械化的工作不仅伤害了她美丽的容颜,还滋生了心灵的褶皱“此刻,她身上已没有丝毫青春激情的迹象”[3]280在燧石顶的工作几乎都是协同机器而进行,脱粒机一转动“对她们的肌肉和神经忍耐力都会提出苛刻蛮横的要求”[3]325歇工的时候“由于机器震动得太厉害,她的两个膝盖已经弄得颤颤巍巍的,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3]327无论是切萝卜机还是蒸汽脱谷机,本意是让人民的劳动更加容易,减轻负担的技术发明,其实质上去是让劳动变得重复单调,动作机械化,精神疲乏却得不到片刻喘息的机会。“持续不断的震动透进了她身上的每一根纤维,把她投入了一种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境界,一双手脱离了意识的支配,只是机械的工作着。”[3]333人成了机器的奴隶,失去了自我意识,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了生命活力“原先精力最充沛的人也一个个弄得面无人色、眼圈发黑了。”[3]333在这远离自然的工业文明压迫之下,苔丝的生命逐渐失去了华彩,当她与残酷现实的抗争失败成为阿历克的情妇,也意味着她精神上的死亡,成了只为家人而苟活的无魂之躯。
在生态批评视域中,农业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对自然的一种破坏,“但相较于工业文明而言,由于农业文明中大自然是直接决定人类命运的主宰因素,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呈现出相融相谐的一面。”[1]270农业文明中的人类仰仗自然,对自然崇拜、尊重、顺应自然而动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农业文明下劳作的人民,磨练出勤劳勇敢、艰苦朴素、诚实守信、乐天知命的优良品质。人与自然形成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这种共生相携的关系又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睦友善,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然而工业文明下的人类盲目自大、唯我独尊,怀揣无尽的物欲与征服欲对自然巧取豪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现代社会中自然的衰败与人性的异化是同时展开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不仅伤害了自然,同时也伤害了人类赖以栖息的家园,伤害了人类原本质朴的心。呵护自然同时也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心灵。”[5]55当人类在追求物质享乐主义的过程中忘却人与自然具有整体性,彼此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时,必然迷失本心。其实精神生态并不与物质基础成正比,相反,物质过于丰富并不利于精神和文化的发展,反而是给享乐主义的滋生提供暖房。汤因比在研究文明发生时就指出,艰苦的环境有利于人的精神成长。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长”那就应当对万物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不是站在高处藐视自然、驾驭自然、索取无度。有科学家预测,一旦人类退出地球舞台,只需500年,我们留下的印记就基本上淡渺无痕。大自然有自身的修复系统和繁衍的能力,它并不需要依存人类而存在,相反地,是人类无法离开自然而独立生存。依存自然的人类理应心怀感激,知恩图报,而不是用现代技术设备的强悍逆天而行,以为“人定胜天”。
结 论
“生态文学对工业和科技的批评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工业和科技本身,而是要突显人类现存的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致命缺陷,促使人类思考和探寻发展工业和科技的正确道路,以及如何开创一种全新的绿色工业和绿色科技。”[8]230人类传统的劳动模式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之间应该找到一种更好的平衡,让人民在劳动中感受快乐,而不是被机器压制得喘不过气来。《德伯家的苔丝》激发了我们对自然源于内心的真挚情感,引导我们去探寻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途径,探讨解决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与精神生态危机的办法。哈代深切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联,对社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哈代的生态观里人物不应是人类生存活动的中心,而是一个组成部分,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共生共荣构成适应生存活动的生态体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对自然心怀敬畏人类才能获得幸福,对自然悖逆漠视者最终只能消亡于世。
[1]王喜绒,等.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聂珍钊,马弦. 哈代研究文集[C].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3]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
[5]鲁枢元.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6]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M].王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7]亨利·梭罗.瓦尔登湖[M].田伟华,译.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
[8]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张灿邦]
An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LIN Xiao-q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Sanming College, Sanming 365004, China)
Thomas Hardy with advance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lived in a heyday of Britai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one of his famous work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he not only described the fabulous natural scenery but also revealed the ecological crisis brought by commercial production. The thesis based on the burgeoning theory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to analyze the author's ecological se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and spiritual ecology and anticipate that readers can resonate with Hardy, then harbor an awe to nature and try our best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ess; Eco-criticis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risis
I106
A
1008-9128(2016)04-0062-04
2015-10-31
福建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托马斯·哈代作品中的生态批评研究(JBS14158);三明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A201315/Q)
林晓青(1981-),女,福建三明人,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研究。翠谷,前面是一片灰色的田野。”[3]48这前后色彩的过渡仿若昭示着苔丝从马洛特村到川特里奇的迁移她的人生也将从青葱懵懂走向灰暗惨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