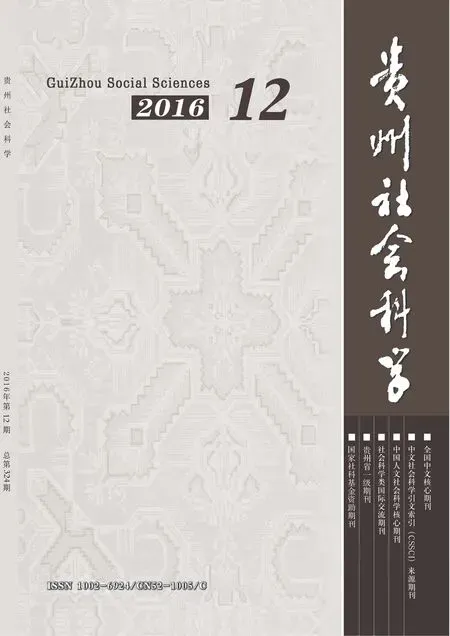中间群体:去边缘化抑或自我边缘化——以贵州屯堡人、穿青人为例
2016-03-15李思睿
李思睿
(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
中间群体:去边缘化抑或自我边缘化
——以贵州屯堡人、穿青人为例
李思睿*
(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
屯堡人和穿青人都是包含有多种民族族群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属于华夏边缘人群,被视为非汉非少数民族的中间群体,形成了一种中间化的心理和认同。在当下新的资源竞争和分配环境中,汉族化和民族化分别成为屯堡人、穿青人不同的现实选择,即“去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的不同生存策略。屯堡人和穿青人的认同核心是历史记忆和地域观念。屯堡地区的旅游发展通过强调屯堡人是“老汉人”的历史记忆,强化了屯堡族群整体认同;同时在屯堡人内部,各个屯堡村寨的“亚”族群成分保持着各自的地域认同。穿青人则因为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存在双重边界,延续了其中间群体的身份和认同,形成一种基于地域观念的民族观。华夏边缘人群通过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汉、非汉或者中间群体的历史进程仍在继续,族群边缘仍在漂移、变动之中。
族群边缘;中间群体;屯堡人;穿青人
在贵州流传着一句话,“穿青大屯堡,屯堡小穿青”,表达着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屯堡人和穿青人居住在相邻的地理位置,具有相似的历史和文化,如移民历史、服饰装束、仪式活动和五显神信仰,同时也存在不少文化差异。[1]如今,屯堡人在贵州被当做一个汉族亚群体,穿青人则是“未识别民族”之一。本文试图通过这两个人群分类的比较,通过对其作为华夏边缘中间群体的历史境遇、到做出汉族化和民族化两个不同现实选择的梳理,分析西南边疆地区的族群关系和族群认同变化。
一、历史境遇:华夏边缘的中间群体
宋元以来,随着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发,先后有不少移民进入贵州。明洪武年间中央在贵州广置卫所,永乐年间在贵州设置布政使司,大量汉族人口移居贵州,引发了汉人移民社会的建构。屯堡、穿青的人群分类及其文化,都是明清移民以原乡文化为基础,在移居地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的重新建构。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屯堡人经历了由汉到苗、从苗入汉的过程,穿青人则成为非汉非苗的边缘群体,两者形成了不同的人们共同体。
屯堡人被学界定义为“清代废明代卫所屯田制后,对分布在贵州省黔中地区(今贵州省平坝、安顺、镇宁、普定、长顺等县市)明初屯军后裔的专称,人口现约三十余万。其特点是他们的入黔祖先大都原籍江南,尽管历经数百年来的社会历史变迁,他们大多数一直聚居在屯堡社区内,至今比较完整地保持着明代江南汉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2]20世纪90年代,屯堡文化在贵州学界曾一度出现研究热潮,屯堡文化被视为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汉民族亚文化系统加以研究,产生了众多“历史实体论”研究取向的作品。[2,3,4,5,6]这些作品将屯堡文化视为一种历史遗存,强调屯堡文化的延续性,使用“老汉人”、“大明遗风”等词汇来形容屯堡人及其文化,用以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写就了作为典范的屯堡人历史。
事实上,明初屯军在贵州六百年间的实际经历并非孤立和静止,而是充满人群互动和竞争的动态历史。屯堡由明代卫所制派生出来,屯堡先民在明代初期作为屯军移民而来,居住在称为“屯”或“堡”的地方,是地位较高的汉人,成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来源。自明清以来,屯堡的发展经历几度盛衰,屯堡曾经作为一种军事化加兵团农业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变革[7],屯堡先民和世居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呈现出动态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处于竞争、对抗、联合等不同状态。在屯堡先民之后到达贵州的清代汉族移民,又将屯堡人视为苗族的一种,称其为“凤头鸡”[8]14;屯堡人则称自己为“老汉人”,称后来的汉人为“客籍汉人”。根据日本学者塚田诚之的梳理,屯堡人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被称为凤头鸡,处于苗汉之间的中间位置,于民国时期逐渐向汉靠拢;总体而言,历史上这一人群经历了由汉到苗,再回归汉的过程。[9]“屯堡人”的称谓在民国时期出现,同时期也有凤头籍、凤头苗等称呼,以及“堡子”的蔑称。
穿青人是中国“未识别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毕节、安顺、六盘水市、黔西南、黔南五个地、州、市所属20多个县。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穿青人人数约67万,其中半数以上聚居在黔西北毕节地区的织金、纳雍两县,每县人数超过20万人。关于穿青人的来源,一种观点认为,穿青人一直是少数民族,祖先是贵州的土著民族“土人”(又叫“里民子”)[10]2,这种观点由地方政府写进作为典范的穿青人“正史”;另一种观点认为,“土人”与“里民子”并非一脉相承,穿青人先民的主体是“里民子”[11]。不过,土人和里民子都是多民族构成的人们共同体,并非一个固定的人群分类。杨然仔细梳理了穿青人族群的发展线索,指出土人、里民、穿青都是在贵州开发过程中,汉化人群标识自己为汉人阵营当中一部分的称呼。穿青人由居住地原有的土人、里民,加入新的人群共同构成,拥有“穿青”这一称号的人们的来源并非单一的汉族移民或当地少数民族,而是多个族群的人们的松散联合体。他认为,穿青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汉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穿青人既不能有效融入主流汉族社会,又不再被少数民族接纳,因此陷入非汉非苗的双重边缘化地位。[12]119
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两次到贵州做民族识别的实地调查,他将屯堡人和穿青人同样纳入“移民后裔与当地少数民族经历长期接触后,受到部分同化的汉移民群体”之列。两者的祖先都是明初随军迁入贵州的移民集团,屯堡先民为有土地的“军家”,驻扎在各个军屯,穿青先民是没有土地的“民家”,成为彝族的佃户。他们被后来的汉族移民视为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如堡子、南族,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汉人,也不是其他“族”,而是京人、穿青、里民子等。他们大多说汉话,穿汉装,并没有民族的特点。[13,14]总之,从历史演变来看,屯堡人和穿青人都是在边疆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不同族群之间互动,通过多重因素建构的结果。屯堡人和穿青人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汉族或者少数民族)成分的族群,而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民族族群成分的人们共同体。长期以来,两者都被视为主流汉族群体和当地少数民族之外的中间群体,他们有着一种中间化的心理和认同。
王明珂指出,在中国西部与西南边疆的汉与非汉之间,有一个漂移、模糊的族群边缘,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的背景中,华夏边缘人群可以通过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非华夏,或成为二者间的模糊状态。他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分配环境背景中,来解释华夏如何形成与变迁。[15]他通过对羌人和羌族的分析表明,在历史中延续的并非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核心与边缘群体互动关系。在近代国族主义之下,族群边缘才转化成汉、羌、藏、彝各民族间的族群界限。[16]10-11同样的,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考察屯堡人、穿青人的历史真实性,加入实体论或建构论的争辩,而是将他们的历史视为华夏边缘变迁史的一部分,关注这些历史主体的形成过程、变迁、互动关系以及现状。族群边缘往往是漂移、模糊的,屯堡人、穿青人因之充满不确定性和文化模糊性。
中间群体可能意味着竞争中的边缘地位,也可以是作出灵活选择、重新阐释的契机。由于族群边缘的漂移和模糊,居住在黔中地区的屯堡先民继续汉化,逐渐建构起关于“屯军后裔”的族群想象;穿青先民向黔西北等地迁移,继续作为不同于汉族和当地彝族的中间群体存续。在民族国家和发展主义的现实语境下,汉族化和民族化分别成为屯堡人、穿青人在新的资源竞争和分配环境中不同的现实选择和生存策略。
二、屯堡人:旅游发展与去边缘化
贵州由于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旅游业成为其利用自身的边缘优势,取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旅游发展也影响了部分族群的存续和认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旅游兴黔”的机遇下,屯堡地区由于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地戏表演、民风民俗等优势,开始发展旅游业。屯堡文化成为地方发展的资源,屯堡人逐渐被学者、政府、市场合谋本质化成为一个汉族亚群体。作为旅游品牌,屯堡文化的价值与其历史遗存的地位紧密相连,典范的屯堡人历史试图通过“结构性失忆”,淡化由汉到苗、从苗入汉的历史记忆,强化“南京人”、“老汉人”的历史记忆。屯堡内部的人们在屯堡这一符号下继续族群建构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通过重修家谱、重塑地戏等方式复述和强化“老汉人”的历史记忆,设定族群边界。
随着研究的深入,大量的研究已表明,屯堡文化并非如旅游口号所宣称的“活化石”、经历600年不变的历史遗存,而是一个文化混合体;屯堡人也并非一个封闭、单一的群体,恰恰是在与其他人群竞争的过程中, 屯堡人才得以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和族群认同。当代意义上的屯堡人是政府、学者、媒体和地方精英共同建构的族群共同体,是以普同性的“屯堡文化”为标准做出的人群的类型性划分,成为学术研究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例子。[17,18,19,20]九溪村是贵州安顺西秀区最古老最大的屯堡自然村寨,被称为“屯堡文化活的博物馆”。笔者在九溪村进行了调研,试图考察旅游发展与族群想象的互动关系。
九溪村距安顺市区27公里,总人口5129人,全村面积12平方公里。根据村里的介绍,九溪人来源于朱元璋大军征南和随后的调北填南,九溪的建立最早大约是在明初“征南”战事结束之后。明洪武年间设屯立堡,军士朱(其始祖朱元正与明太祖朱元璋为同族兄弟)、姚、胡、余、冯、陈、梁、洪、童、吕十大姓最早由江南徙迁入贵州,落脚九溪。后来屯军移民纷至,至清康咸年间,九溪人口近万,为当时最大的屯堡村寨,故有“九溪是座城,只比安平(平坝县城)少三人”之说。九溪的人员构成保留了军士成分,也有明初因其他原因迁入的王、黎、袁、翟、何等姓氏,以及在清代嘉庆年间以经商方式迁入九溪的刘姓、徐姓。明代屯军后裔虽然是九溪人构成的重要部分,但就人口数量而言,并不是屯堡人的主体。不过,由于屯堡先民和当地世居少数民族及后来的汉族移民之间都存在差异和竞争,屯堡人逐渐成为地域性人群共享的人群分类,在历史上成为一个非汉非少数民族的中间群体,保持和维系了屯堡人的中间化心理和认同。
整体意义上的屯堡人和屯堡文化,则是旅游发展的产物,当代的“屯堡”主要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和文化资源继续存在。在整体性屯堡文化的框架下,九溪村按照安顺地区“一村一品、一村一特”的发展格局,发展地方特色人文旅游,重新阐释传统文化,先后成立了屯协会、青年活动中心、地戏队、妇女佛事组织等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把不同年龄组、性别的人群以不同的民俗活动为核心组织起来,重新阐释和延续传统文化,促进九溪村的发展。
九溪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随着当地的旅游发展,一些年轻人开始愿意返乡创业。2015年,九溪村的十多位年轻人成立了“九溪村屯堡民俗活动筹委会”(以下简称民俗会),致力于整合传统资源,希望通过举办具有屯堡意义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传承屯堡文化精髓,发展地方特色人文旅游,促进九溪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九溪的地戏表演队颇有名气,在安顺地区,一般来说一个村寨只有一堂戏,九溪村则有三堂戏。推广地戏是民俗会的主要活动之一,其中一位顾姓成员是安顺地戏交流协会副会长,除了推动九溪村的地戏队外出表演和参加比赛,他还在九溪村成立了少儿地戏队,每周在小学固定授课。他认为,此举除了可以达到传承他小时候由爷爷教给他的技艺之外,还能践行自己“社区教育”的理念,用创新的方式传承屯堡文化。
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是九溪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河灯节。这一天,人们把纸扎的河灯统一摆放到村里的河中,意为送祖先回家;然后烧福包,作为敬奉先人的财物。2015年,民俗会全力打造第十五届“九溪河灯节”精品活动,为准备这一活动,他们争取到了九溪首富的支持,开展了“九溪发展座谈会”等一系列准备活动,邀请学者、文化名人、地方官员共同探讨民俗和九溪的未来发展。此外,民俗会的部分成员还打算参与此后的村委会竞选。
纵观这一过程,典范的屯堡人历史建构了整体性的屯堡人和屯堡文化,屯堡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和旅游品牌,成为有力的象征符号和文化资源。通过运用这一符号和资源,九溪人重新阐释和延续传统文化,目的是建设九溪村,达到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去边缘化的目标。这一过程促进了九溪人的主体性实践和文化再生产,强化了九溪人的屯堡人认同。伴随着村寨年轻人的成长和村寨精英的推动,节日成为社区力量的整合仪式。当地致力于发展民俗文化的各个民间组织,无形中也衍生出了多元的村落社会组织力量。
虽然学界和地方政府致力于书写典范的族群历史,构建集体记忆,划定明确的族群边界,长期复杂的历史进程造成的屯堡人员构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却难以改变。即便如今已有学者写就的“典范”屯堡史,在这一人群内部,各村寨又注重寻找自身的特色,凸显差异,“亚”族群成分依然各自认同,显示了屯堡族群认同的多元性和多层次。与九溪村的情况类似,朱志燕通过对天龙屯等地的考察发现,屯堡文化以及屯堡族群是地域性的区域文化,其认同属于族群地域性认同层次。[20]在屯堡族群整体认同之下,各地着力挖掘自身的地域特色,出现各个屯堡亚群体,通过地方文化表达着自身的地域认同。
三、穿青人:身份政治与自我边缘化
不同于屯堡人通过强调其“老汉人”的历史记忆达到经济地位和族群身份的“去边缘化”,穿青人做出了成为单一少数民族这一“自我边缘化”的选择。居于黔西北山区的穿青人,在政治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少数民族身份成为他们着力争取的资源。20世纪80年代,因不满于被当作汉族,黔西北地区的穿青人多次要求对其身份进行重新识别。经过调查,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在1986年版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问题的重新调查报告》中提出:“穿青”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族。1987年,贵州省公安厅、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发布第36号文件《关于填写居民身份证民族成分等问题的几项规定》,文件规定:穿青人可以享受少数民族待遇。“穿青人”可以成为写在居民身份证上的族群身份,既非汉族也非单一少数民族,其身份依然是中间群体,只不过在当下作为“未识别民族”之一的形态而存在。
典范的穿青史由地方政府参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书写,强调其一以贯之的少数民族特性。在其叙事中,穿青的先民是贵州的土著民族“土人”,穿青人具有独特的信仰、习俗等文化特征。明清以来,穿青尽管族称有变化,一直是少数民族。从明初直到清乾隆以前,在长达四百余年的时间里,穿青与汉人是隔绝的。清末民初以来,大批四川和湖广籍的汉人进入穿青居住地区,穿青人和汉人之间一直充满斗争,是两个对立的群体。至于穿青人的家谱记载和传说祖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祖先是明洪武“调北征南”随军入黔的,则是一种附会。[10]2这一典范历史与典范的屯堡历史正好相反,屯堡叙事淡化自身与少数民族互动的历史记忆,意在通过老汉人的身份争取旅游资源;穿青叙事则淡化自身汉化的历史记忆,这一典范历史也成为如今部分穿青人希望被识别为单一少数民族或“土家族”支系的依据,目的是争取少数民族享有的优待和资源。
在概念上,族群与民族有一定区别。与族群不同,民族不仅是一种人群范畴,而且还是一种人们共同体。它一般是指那些具有自治要求,已被政治疆界化或正在追求政治疆界化的族群,而族群的政治疆界化则往往要以一定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社会经济联系为前提。一般可以用族群范畴来概称、囊括民族,也可以用它来区分民族内部的不同支系,但却很难用民族来概称或区分族群。穿青人民族化的选择,是由少数民族待遇的外部动力和内部族群关系紧张的内部原因共同造就。[21]
纳雍县政府杨先生指出了穿青人的身份政治问题:“如果国家承认穿青人是少数民族,按照现行有关规定,只要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总数的30%以上,该县就可以申请设立少数民族自治县,这样一来,织金、纳雍两个县就能达到申请设立自治县的标准。只要成为少数民族自治县,就能获得国家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多支持。这是全县人民都十分期盼的,所以,穿青人一直在努力争取”。出于这样的发展诉求,地方政府写就了典范的穿青史,致力于追求穿青人的政治疆界化。普通乡民的想法则更为实际和直接,选择成为穿青人有其现实考量。如纳雍县勺窝乡陈姓农民所言:“穿青人一直要坚持是单一少数民族,主要涉及三生(升)的问题。如果国家确定穿青人为少数民族,一是可以多生一个孩子;二是孩子升学可以照顾20分,这对学生考学十分重要;三是有些想升官的,相关条件和要求要比汉族低一些”。
事实上,关于穿青人的身份归属,穿青人内部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大部分穿青人支持维持未识别民族的现状,少部分穿青人认为可以认同为其他少数民族。例如纳雍县张氏族人便认为应该维持原状,保留穿青人身份。“我们张氏家族的每个人从小就是穿青人,在他们眼里,祖宗留下来的身份,不能在我们这些人中被掐断。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身份证上民族一栏就是穿青人。如果我们改族,很容易让穿青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民俗失传;并且更改后的少数民族信仰和生活方式有差异,很容易招来歧视。因此,我们张氏家族的代表在2014年的认同意愿调查工作中,无一人提议要改民族”。前织金县政府官员张先生认为,“在国家不再增加少数民族数量的情况下,穿青人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耐心等待……我们相信,总有一天,穿青人终将被认定为单一少数民族的。二是整体认同。从织金的情况看,我们倾向于整体认同为土家族,不能分化为其他民族。我们平常说,有东土西土,现在的武陵山片区的土家族是东土,黔西的穿青人是西土。但是这个问题我们穿青人内部意见不一致,分歧较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统一”。
杨然在调查中发现,民族化的进程往往和宗族问题、地域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处于这一进程当中的各个集团甚至个人都具有不同的认同意识,而民族化过程有意无意地加强了穿青人整体的意识。[12]119笔者在调研和访谈中也发现,尽管穿青人内部意见各异,但这一民族化过程,也继续强化着穿青人的整体意识和身份认同。例如,纳雍县一位陈姓大学生谈到:“我们一直要坚持穿青人是一个单一少数民族,主要原因在于要增强民族认同,民族归属感。根据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穿青人应该是一个单一少数民族。在上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将共同心理素质解释为民族认同感或民族自觉的认同意识后,我们才理解了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东西。穿青人之所以与彝族、汉族以及屯堡人不同,不仅因为穿青人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还在于穿青人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穿青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文化认同感”。时至今日,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虽然穿青人外在的文化特征不再明显,与汉族无异,但他们依然存在较强的主观认同。
综上所述,穿青人民族观的核心是地域观念,其族群边界的设定与人群活跃的地域范围紧密相关。但这并非意味着穿青人已经成为寻求领土主权的民族共同体,由于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存在双重边界,其身份依然是非汉非少数民族的中间群体,整体上延续着长期形成的中间化的心理和认同。同时,群体内部历史记忆和现实利益的差异,使穿青人的认同策略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性。
四、结语:漂移的边缘
作为历史主体延续的屯堡人、穿青人都是包含有多种民族族群成分的人们共同体。长期以来,两者都被视为主流汉族群体和当地少数民族之外的中间群体,并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中间化的心理和认同。边缘位置往往会带来认同危机,历史和现实中均是如此。边陲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多将自己说成来自中原,且历史久远,如华南客家的宁化石壁村葛藤坑传说、四川移民的湖广麻城孝感乡传说、江西移民的瓦屑坝传说,不胜枚举。这类传说的目的大多在于确立某种正统性的身份,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人群(或族群)逐渐共享了同一个祖先移民传说,从而形成了地域认同。明初卫所制度的设置,对移民传说的产生具有较大的影响,移民传说反映了某种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和移民的生活境遇,在社会生活中多为象征作用,是移居地地域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工具。[22]屯堡人和穿青人的移民传说都始于这一时期,表达的并非是对原乡和原籍地的认同,而是超越地方的、对现居地区的地域认同。这种地域认同也是明清时期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逐渐定型的国家认同的表征。在明清时期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的背景中,他们作为华夏边缘的中间群体,通过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汉、非汉或者中间群体。
华夏边缘的推移、变迁,发生在资源与分配环境的背景中,由华夏对边缘人群的历史与文化书写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行动来体现与达成。在屯堡人和穿青人的历史上,凡是中央在贵州实行政治高压的时期,他们都愿意承认甚至编造自己的汉人身份;与中央政权的亲密程度是判断是否汉人的主要标志,各种文化符号都随着政治认同态度的变化而被解释为汉人或是非汉人的特征。在屯堡先民和穿青先民之后移居贵州的汉族移民称屯堡人为“凤头鸡”(有苗蛮之意)、称穿青人为“通背猴”,穿青人称苗族为“苗子”并沿用至今,各个人群对其他人群存在各种蔑称,形成“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16]314这一族群体系再次印证,古代华夏对蛮夷的歧视推动着整个华夏化的进程,华夏化的过程往往发生在文化、生活习俗与社会身份皆十分接近的人群之间,汉人和非汉只有一个模糊的边界。认同借着邻近人群间的模仿、攀附与相对的区别、夸耀进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文化变迁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
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发展主义的语境下,模糊的族群边缘逐渐向明确的族群界限转化。典范的屯堡史、穿青史可以被视为一些凝聚族群的集体记忆,它们由群体内部部分人士选择和书写,用以凝聚族群情感,设定族群边界,增强族群认同,达到资源竞争的目标。屯堡人的汉族化和穿青人的民族化,表达和反映的是人群自我的界定和当前的族群关系。汉化程度较深的屯堡人抓住了旅游发展的契机,在旅游发展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典范的屯堡史还有外部人士的参与,成为由学者和村落所构筑的知识生产共同体。在屯堡人内部,“亚”族群成分保持着各自的地域认同。穿青人则因为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存在双重边界,延续着中间群体的身份和认同,形成一种基于地域观念的民族观。
屯堡人和穿青人的典范历史,表明了在新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下,汉族化和民族化分别成为两者的生存策略,成为两种设定族群边界的尝试。屯堡人和穿青人族群认同的核心主要基于历史记忆和地域观念。屯堡叙事淡化自身与少数民族互动的历史记忆,穿青叙事淡化自身汉化的历史记忆,表明这些人群通过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汉、非汉或者中间群体的历史进程仍在继续。虽然学界和地方政府致力于书写典范的族群历史,构建集体记忆,划定明确的族群边界,但在与当地其他人群的竞争、互动的动态历史下,边界的设定并非一劳永逸,作为人们自我界定和关系界定的族群,依然处于变化之中。
(本文中凡未注明出处之访谈、论据均来自笔者2015年7月、8月在贵州的田野调查。)
[1] 朱伟华.贵州移民文化形态的留存与变异——“屯堡人”与“穿青人”文化符码比较[J].文艺争鸣,2011(9):131-134.
[2] 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01(4):68-78.
[3] 桂晓刚. 试论贵州屯堡文化[J]. 贵州民族研究,1999(03):78-84.
[4] 周耀明. 族群岛:屯堡人的文化策略[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52-56.
[5] 孙兆霞. 屯堡乡民社会的特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01):46-51.
[6] 吴羽.屯堡文化的时空建构[J].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综合版),2004(03):78-81.
[7] 吴斌.守望的距离——黔中屯堡的历史与文化观察[D].云南大学,2010.
[8] 安顺学院,编.屯堡研究集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4.
[9] 琢田诚之,黄才贵. 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0(01):158-168.
[10] 陈宏枢,主编.穿青人历史与文化[M].织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4.
[11] 李良品.贵州方志中有关“穿青人”及其先民族源和族称的记载[J].贵州民族研究,2011(02):164-171.
[12] 杨然. 穿青人问题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2006.
[13] 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M].北京:三联书店,1951:9.
[14] 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C]//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45.
[1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7.
[16]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7] Tim Oakes,吴晓萍.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3.
[18] 朱志燕. 屯堡族群与族群认同——以天龙屯堡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38-42.
[19] 卢百可(Patrick Lucas).屯堡人:起源、记忆、生存在中国的边疆[D].中央民族大学,2010:2.
[20] 李立.在学者与村民之间——村落知识生产的经验研究、话语分析与反思[D].北京大学,2010:2.
[21] 雷勇.社会历史、宗教生活与族群身份的建构——以黔西北穿青人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12(4):17-22.
[22] 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16.
[责任编辑:明秀丽]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11BMZ010)。
李思睿,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C951
A
1002-6924(2016)12-09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