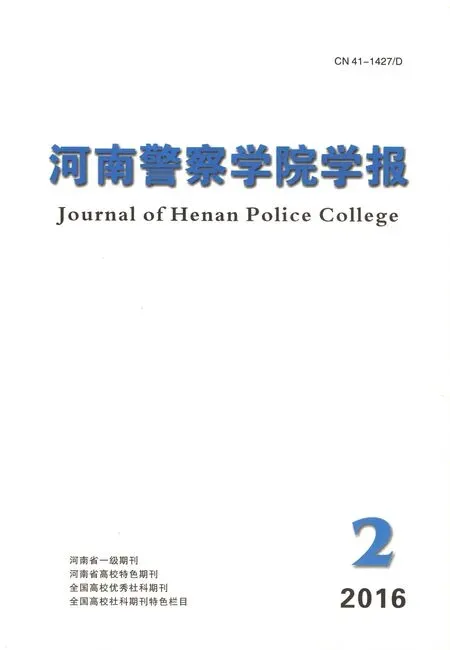行贿犯罪疑难问题解析
2016-03-14胡增瑞卢勤忠
胡增瑞,卢勤忠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行贿犯罪疑难问题解析
胡增瑞,卢勤忠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界分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两罪的区分应遵循意志属性—资金来源—利益归属的进路来判断。从立法沿革及司法实践来看,行贿罪不正当利益要件不可或缺,且其外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无论在主动行贿还是在被索贿的情况下,“谋取不正当利益”都是主观要素而不是客观要素,被勒索而给予财物的也应当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素才可能构成行贿罪。经济行贿只能发生在平等的经济往来中而不是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且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但要以违反国家规定为构成要件。
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要素
司法实务中,对于行贿犯罪的打击明显少于作为其对合犯的受贿犯罪。虽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不说对于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界定困难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不正当利益的界定以及其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归类也同样影响着行贿罪的认定。与此同时,经济行贿与普通行贿在司法实务中的混乱适用甚至是被虚置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实务中对行贿罪的认定困难。
一、行贿犯罪的主体:单位与个人的界分
一般而言,行贿罪的主体是个人而非单位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单位行贿罪,而《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的是行贿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在立案侦查、审查逮捕、提起公诉抑或是审判阶段,对于行贿罪,审查重点及难点之一首先是对其主体的审查,即行贿行为究竟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因为不同主体实施相同的行为,可能涉及此罪与彼罪,甚至罪与非罪的问题。①因为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入罪标准不同,个人行贿入罪数额标准是1万元,单位行贿入罪数额标准是20万元。通常区分行贿主体难度并不大。根据刑法规定,个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为行贿,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是单位行贿。但实践中,单位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是一人公司的负责人行贿,这时的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以及利益归属经常难以区分,不仅司法实践中处理方法不一,刑法理论对此也存在较大争议。概括起来[1],对于两者的区分,有职务关联区分说,②该说认为,单位中自然人的行贿是否与自己的职务相关联,是区分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一个条件。对于此说,并无本质不同的意见,只是在职务关联的程度及范围上存在争议。张明楷教授认为,“单位犯罪一般表现为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以单位名义为本单位全体成员或多数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但也有观点认为对于单位从业人员为本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单位没有制定预防制度或实施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防止他们实施这些行为,在规定单位犯罪的前提下,单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参见李希慧,杜国强著:《贪污贿赂罪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333页。行贿名义区分说,③该说认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单位名义行贿,是区分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一个标准,即以个人名义行贿的肯定不能认定为单位行贿罪;以单位名义行贿的,肯定不能认定为行贿罪。参见吕天奇著:《贿赂罪的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行贿人与受贿人往往是心照不宣,行贿人行贿时根本就不提是以谁的名义,按此标准,显然无法作出区分。贿赂权属区分说,①该说认为,在判断单位行贿意志整体性问题上,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贿赂资金从单位账簿上支出。具体参见窦大勇:《单位行贿罪的司法认定》,载《民营科技》2010年第10期。但是,对于“夫妻公司”,“父子公司”而言,行贿人可能会认为公司的钱就是自己的钱,自己的钱也是公司的钱,形成了公司财物和个人财物混同而不分的情况,按上述标准,也很难区分贿赂资金来源。利益归属区分说。②该说有直接而明确的法律依据,即《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行贿罪的规定处罚。疑问之处在于违法所得是直接归属个人还是包括间接归属个人;既有归属单位的,也有归属个人的,该如何处理。有人认为,如果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有依存关系,则认定为单位行贿罪。参见林亚刚主编:《贪污贿赂罪疑难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也有人认为对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按照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分别处理,对个人认定行贿罪,对单位认定单位行贿罪。参见肖中华著:《贪污贿赂罪疑难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无论何种观点,单独适用的话都不能简单明了地解决行贿与单位行贿的区分问题,以下试举例予以说明。
例1:李某是某土石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股东是李某及其妻子王某。王某从不过问公司的事情,都是由李某一人负责业务及财务等工作。某日,李某为了能承接苏州市某区国有某城投公司土方工程,在工程招标前,找到城投公司的主管人员张某,希望其多多关照,日后将重谢。后在张某的帮助下,李某顺利承接了该公司价值人民币500万元的土石方工程。在李某公司陆续收到上述工程款后,李某将部分工程款转入自己的银行卡上,并从中取出人民币15万元送给张某。某区检察院在初查过程的讨论中对于李某的行为是单位行贿还是个人行贿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某虽然是土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该公司实质上是李某个人所有,其作出行贿的决定也是其个人所为,并没有与其他股东商量,不能代表单位意志,其行贿款也是从自己银行卡支出,是为谋取个人利益,构成行贿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李某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的意志也可代表单位的意志,其行贿是为了让公司承接到工程,利益是归属于该公司的,虽然工程款最终转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上,但也不能否认行贿利益首先归属单位的事实。因此,李某的行为是单位行贿,但是因为行贿数额没有达到单位行贿罪的立案标准,因此李某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根据上述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能单独适用例1而得出正确结论。对于职务关联说而言,李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虽然没有与另外一个股东,即其妻子共同商量行贿一事,但是公司实质上由其一人负责经营,其妻子仅仅是该公司为了满足公司法的相关要求而作为一名挂名股东而已。李某本人的行为,既可以代表公司,也可以说是其个人的行为,因此,依据职务关联区分说是无法区分是个人行贿还是单位行贿的。行贿名义区分说在本案中同样是难以适用的。李某送钱给张某的时候,仅说是感谢其的关照,而并没有说是关照自己还是关照自己的公司。实际上仅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对方足以心领神会。对李某来说,关照自己就是关照公司,同理关照公司也就是关照自己。至于贿赂权属说,这15万元应当是李某公司的财物呢,还是李某个人的财物呢,区分实属不易。实践中,与此类似,有些公司可能根本就没有完整的财务记录,或者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财物和公司财物混同,要想区分清楚行为人是用属于谁的财物来行贿,根本不可能。按照利益归属说,本案中行贿的利益首先归属于李某的公司,进而又归属于李某个人,也可以说行贿的利益直接归属于李某的公司,间接归属于李某。那么《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是否包含间接归属个人的情况呢?对此不无争议。
例2:王某是某知名制药公司的销售人员,为提高个人业绩,多得年终奖金,便个人出资购买2万元购物卡送给某医院药房主任,请其在药品招标采购时关照自己。后王某如愿以偿,向该医院销售了200万元的药品,并在年终因该笔销售获得了10万元的奖励。王某行贿的行为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呢?笔者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应当可以包括利益间接归属个人所有的情况,否则可能放纵例2中的行为,并且也不会置单位行贿罪于虚置的境地,毕竟两者立案标准不同,法定刑亦差异巨大。
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本质上是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关系。根据刑法分则的立法例,其本应当归入同一条文,适用相同的法定刑,只需另外规定对单位犯行贿罪的判处罚金即可。但是,刑法为了突出打击行贿罪,将两者分别规定,并对二者配置了差异巨大的法定刑,致使本该并无实质意义的区分在实践中变得疑难而且复杂。笔者认为,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区分应当坚持以下三个步骤:首先看意志属性。出于个人意志行贿的是行贿罪;出于单位意志行贿的是单位行贿罪。当意志属性无法区分,例如上述例1和例2中的情况,意志重合的情况下应当接下来考察资金来源。其次看行贿资金来源,对于资金来源要从实质上把握,而不能只看表面。实践中,有的行贿人用自己身边的备用金来行贿,表面看起来备用金不是公司的财物,实际上可能是行贿人每年定期以各种名目从单位账上支出,放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如此情况,仍应作为单位资金看待。最后看利益归属。利益归属应当坚持利益直接归属和利益间接归属均可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否则就留给了犯罪嫌疑人巨大的规避空间,从而不当缩小了打击面;同时,也与司法解释不断扩大“不正当利益”范畴进而扩大打击行贿罪的目的背道而驰。
根据上述三个原则来分析前述例1。李某的行贿意志既可以看成是李某个人的,也可以看成是李某公司的;对于用以行贿的15万元,表面看起来是李某个人卡上的钱,实际上来源于单位所直接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因而是来源于单位的;而行贿的利益直接归属于单位,间接归属于李某个人。因此,李某的行为是单位行贿。因行贿额未达到人民币20万元的标准,李某不构成犯罪。同样以上述步骤来分析例2。王某行贿的意志不是单位意志,而是个人意志。王某是个人出资购买购物卡行贿的。王某最终间接获得了10万元的不正当利益。因此王某构成行贿罪。可见,在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没有统一立法前,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利益归属个人理解为既可以直接归属于个人,又可以间接归属于个人,可以严密法网,不会遗漏类似对例2中王某的行为的打击,还可以契合当前严打腐败的需要。
二、不正当利益的规定:限缩与扩大之争
1979年刑法规定只要是行贿或者是介绍贿赂,不论什么原因,一律构成犯罪。①该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实践中不免打击了一些目的正当的行贿,扩大了打击面,如为了要回货款而被逼无奈的行贿。为了适应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5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称《解答》)中首次将谋取非法利益作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要素,适当地限缩了行贿罪的成立范围。②在《解答》中关于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问题中指出“个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介绍贿赂的,应按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三款追究刑事责任”。但是,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又通过用“为谋取不正当利益”③《补充规定》第七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替换了司法解释中的“为谋取非法利益”,变相地扩大了行贿罪的成立范围,因为不正当利益的外延比非法利益的外延要宽得多。此后,在新刑法的修订过程中,围绕何为不正当利益又不断形成新的争议。
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刑法修改小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修改刑法研究报告》中就指出:调查中大部分人认为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不能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限定条件。原因在于:首先,行贿罪的危害性在于严重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无论其是否以谋取正当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这种危害性都不会因此而有所不同;其次,实践中不正当利益与正当利益有时难以区分,造成适用混乱;最后,作为对向犯的行贿与受贿,没有理由只打击受贿行为而放纵行贿行为[2]2639。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呼吁取消行贿罪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要件不同,在刑法修订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却一直主张应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明确规定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法分则修改的若干问题(草稿)》中认为,“鉴于目前社会风气败坏,不少人为了合法利益也不得不行贿,故不能对一切行贿行为都以行贿罪论,必须在行贿罪前边加上‘为非法利益’而行贿这一限制内容”[2]2641。1997年修订刑法最终采纳了折中意见,既没有将谋取利益的范围缩小为非法利益,也没有不当地扩大到正当利益,而是吸收了《补充规定》中的相关内容,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规定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暂时平息了“两高”的争议。
然而,司法实践中随之而来的问题出现了,如何理解与准确界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对此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中争议较大。为此,1999年3月4日,“两高”联合颁发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首次明确了不正当利益的内涵。①《通知》第2条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商业往来活动中,贿赂之风愈演愈烈。为遏制这种势头,2008年11月20日,“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又显著扩大了前述《通知》对不正当利益的界定,为扩大打击行贿犯罪的范围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②《意见》第9条规定:“在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2012年12月26日,“两高”在《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继承了前述《意见》中对于不正当利益界定的同时,又在第12条第2款中再一次扩大了不正当利益的范畴,③增加规定“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首次将在相关领域谋取竞争优势的行为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到,“将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在此之前,只有较大的市而不是设区的市才有最低一级的地方立法权。随着《决定》的出台,可以预见的是拥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将大大增加,地方政府规章的数量无疑也会大大增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外延肯定会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扩大,为当前的反腐败形势再添一把力。
梳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立法及司法沿革可以发现,在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从无到有,期间虽有争执,但随着各种腐败犯罪情况的不断出现,为严控腐败形势,“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的内涵与外延又不断扩大,增大了其犯罪构成的涵摄面。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目前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决不会取消,反而会不断扩张其外延,以扩大行贿罪的适用范围。这既符合我国的国情,也是当前高压反腐的刑事政策需要。
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要素还是客观要素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的主观要素还是客观要素,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分歧较大,一种观点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犯罪的主观目的,而且行贿犯罪是指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为其特别构成要件的犯罪,是目的犯[3]。持同样观点的论者认为,“为谋取”一语明显属于主观目的的范畴。《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是该条第一款的补充性规定,同样也应当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主观要件;同时,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是行贿罪的基本犯罪构成,第三款的规定是行贿罪的修正犯罪构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这两款规定中之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是一致的,都属于其主观方面的要件[4]。第二种观点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既是主观要件又是客观要件。如张明楷教授认为,如果认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主观要素,则当行为人已经获取不正当利益后,为了不正当利益酬谢国家工作人员,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时,就会被排除在行贿罪之外。如果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解释为既可能是主观要素,也可能是客观要素,该种行为才可认定为行贿罪”[5]。
笔者认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主观要件要素,但其属于行贿罪的动机,而不是行贿罪的目的。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希望通过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活动,它反映要达到某种愿望的意志。而犯罪动机则是推动或者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内在推动力量)。行贿者的目的是要收买国家工作人员,而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6]。行贿者首先产生行贿动机,这个动机既可能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可能是为谋取正当利益,如为按期拿到工程款,行为人在上述动机的驱使下进而采用金钱或其他财物收买的方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客观上形成了钱权交易,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不可收买性。同时,笔者认为,张明楷教授用以证实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属于客观要素的观点的案例④2009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许某受他人委托替他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过户手续,为少缴纳契税及相关滞纳金等费用,找到时任平顶山市房产管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兼平顶山市房地产产权产籍监理所负责人、党支部书记的吴某某,吴某某利用其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给相关人员打招呼,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事后,许某向吴某某行贿人民币6万元。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2010)郏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许某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394页。恰恰证实了该要件属于主观要素。该案中,被告人许某事先对国家工作人员有请托,请托的内容是“少缴契税及相关滞纳金等费用”,该请托显然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受请托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请托后,为许某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事后,许某送钱给国家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该案中,许某只是在谋取到了不正当利益之后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但其事前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已经进行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请托,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动机很明确,只是事成之后给予财物罢了,其实质仍是以钱买权。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的内涵。根据该款规定,从逻辑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是行贿。”①司法实践中也持同样看法,如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五)项中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已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是否构成行贿罪取决于是否实际获得不正当利益这一客观结果,如果不考虑主观方面的话,得出这样结论显然是一种客观归罪,与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认定犯罪所坚持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相违背。主观上有犯罪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犯罪的行为,只是因为客观原因而未得逞,这更符合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而不是不构成犯罪。因此,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只能理解为是该条第一款规定的例外规定,而不是补充规定,其应当符合第一款规定的基本内容,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但因为客观方面存在些许不同,即“被勒索而给予财物而不是主动给予”,同时“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所以排除了犯罪构成。如此规定依据何在?笔者认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内涵应当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本应构成行贿罪,但毕竟是被勒索给予财物而不是主动给予,同时又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使得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客观危害性均显著降低,没有达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符合《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不认为是行贿罪。所以,可以认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暗含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主观要件要素而不是客观要件要素的意思。
四、谋取不正当利益:能否适用经济行贿
一般认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是经济行贿,也就是经济往来中发生的行贿行为,而不是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行贿行为。经济往来的范畴是什么,司法实践中其实并不容易准确界定。以袁某行贿案为例(例3):被告人袁某系国家注册建筑师。2010年5月,其通过同学沈某某(泰州市路灯管理处主任,另案处理)的介绍,与负责拆迁安置房开发建设的泰州市海陵房产开发公司经理刘某某(国家工作人员,另案处理)相识,并委托沈巧龙向刘某某索要其使用的银行卡号,于2010年6月14日向该卡存入人民币4000元,同年9月18日向该卡存入人民币20000元,又于2011年3月12日向该卡存入人民币100000元,总计人民币124000元。在刘某某的帮助下,未经招标程序,被告人袁某以挂靠单位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揽了泰州市迎春东路安置小区海曙颐园的规划设计项目[7]。检察机关以行贿罪(经济行贿)提出公诉得到法院的认可(从判决书中法院同意检察院看法可以推断出来)。法院认为:“被告人袁某在经济往来中,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予以支持。”在本案中,检法两家均认为未经招投标而因行贿直接承揽设计工程的行为属于在“经济往来”中。如此一来,那《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将被虚置。到底该如何界定“经济往来”?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往来活动包括生产、经营的各种活动,既包括国家经济管理活动,又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的直接的经济交往活动[8]。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往来活动只限于行为人代表本单位与外单位或个人从事经济交往活动,也即限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交往,不包括行为人代表单位所进行的经济管理活动,凡是行为人在履行经济管理职能过程中收受或者索取贿赂的,都不算是经济受贿行为[9]。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如果经济往来既包括经济管理活动,又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那么《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区分设置第一款和第二款就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了。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经济管理活动,其本质上和国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并无实质差别,都是一种行使公权力的管理活动,是国家工作人员行为公务性的体现。而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交往,体现的是一种平等关系,而不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是经济往来中的回扣、手续费,而不是经济管理中以回扣、手续费名义出现的行贿和受贿。因为回扣本身只产生于商品贸易流通过程中的买卖双方,手续费、辛苦费、劳务费等则是因一定的劳务关系,由接受劳务的一方支付给提供劳务的一方的报酬。主要产生于推销商品、采购原料、联系企业经营有关业务等活动中。实践中,在银行信贷、发包工程及工程验收、决算等过程中以所谓回扣、手续费名义出现的行贿受贿问题,虽然打着回扣、手续费的招牌,但严格说来,因其具有经济管理的内容与特征,不应属于经济行贿范畴,只能属于一般行贿范畴[10]。因此,在例3中,袁某为了直接得到设计工程,多次给予具有将工程以何种形式进行发包决定权的刘某某以财物,这显然不能当成是经济往来过程中给予财物,而是属于经济管理过程中给予财物。在此过程中行贿罪的认定应当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而非第二款的规定。因此,在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管理活动过程中行贿的应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而在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平等经济交往过程中行贿的,应当适用该条第二款的规定。
那么《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要求要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素,该条第二款因为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是否也要求具备这样的要素呢?刑法理论中,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行贿的构成要件也应当包括“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是行贿罪的必备要件[4]。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行贿并不要求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经济行贿具备行贿罪的特殊构成要件体系,从逻辑角度看具备独立的存在价值,也不像一般行贿行为发生在社会生活领域而是发生在经济往来环节[11]。也有论者认为,经济行贿是行贿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就属于行贿,不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罪要件[10]。司法实践中上述规定给司法实务者造成巨大的困扰,同时也是司法实务中的一个难点。笔者认为,理论与实务中对此问题纠结的根源在于一是没有深刻理解“经济往来”的内涵,二是没有认真研究法条规定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与“违反国家规定”的异同。如前所论,只有在严格区分行贿犯罪中社会管理、经济管理与经济往来的具体类别归属的前提下,讨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否属于普通行贿与经济行贿的构成要件才具有针对性。实际上,经济行贿的构成要件要求比普通行贿应当更严。因为,从立法本意来看,犯罪构成要件宽严的决定性因素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大,则构成要件要求宽;社会危害性小,则构成要件要求严。普通行贿发生在双方不平等的社会及经济管理过程中,在这种情形下行贿人处于相对更弱势的地位;而经济行贿发生在双方平等交往的经济活动中,在这种情形下行贿人处于相对较平等的地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行贿人要求要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才构成行贿罪,那么处于相对平等地位的行贿人不更应当具备这样的要件吗?按此逻辑,经济行贿中也应当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
但实际上,根据前文对“不正当利益”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外延其实相当丰富,并且呈不断扩大趋势。①根据《解释》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与此同时,经济行贿中“国家规定”的内涵相比“不正当利益”要严格得多。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11〕155号)中规定,“根据刑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刑法中的‘国家规定’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其中,‘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应当由国务院决定,通常以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制发文件的形式加以规定。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制发的文件,符合以下条件的,亦应视为刑法中的‘国家规定’:(1)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同相关行政法规不相抵触;(2)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或者经国务院批准;(3)在国务院公报上公开发布。”对比上述规定同样可以发现,经济行贿的构成要件要求比普通行贿的要求要严格得多。纠结于经济行贿是否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并无实际意义,它不是一个“有”或者“无”的问题,而是由刑法在不同层面作出了不同的安排,即在经济行贿中,只要证明行贿人违反哪一个具体的“国家的规定”,并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回扣、手续费,就足以认定其构成行贿罪,而不需要证明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五、结语
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区分应遵循意志属性—资金来源—利益归属的进路来判断,个人决定进行行贿,资金也来源于个人的,行贿利益也是归属于个人的,才可认定为行贿罪。从立法沿革及司法实践来看,不正当利益外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也是契合了当前高压反腐的要求。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主观要素不是客观要素,被勒索而给予财物的也应当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素才可能构成行贿罪,否则不构成犯罪。经济行贿发生在平等主体的经济往来过程中,而不是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并且其构成要件之一为违反国家规定而非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1]董桂文.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界限之司法认定[J].人民检察,2013(12):30.
[2]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3]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分则篇(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2.
[4]赵翀.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要件[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2):102.
[5]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94.
[6]卢勤忠.“谋取私利”是行贿罪的目的吗?[J].法学,1990(4):20.
[7](2011)兴刑初字第304号[J].人民司法·案例,2012 (4):66.
[8]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1981.
[9]杨兴国.贪污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释[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16.
[10]郭晋涛.论行贿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6):33.
[11]金永华,解杰.行贿犯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刑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J].人民检察,2011(2):20.
(责任编辑:刘 芳)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Bribery Crime
HU Zeng-rui,LU Qiu-zh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The boundary of bribery and corporate bribery is the difficulty in judicial practice.We need to follow the order of will attribute-the source of funds-attribution of interests when distinguishing these two crim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evolu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the illegitimate interests is an indespensable element of the crime of bribery,and its extension is constantly expanding.No matter in active bribery or extortion bribery case,to seek illegitimate interests is subjective factor rather than objective factor.Those who are blackmailed to give properties shall also be subject to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of illegitimate interests that may constitute the crime of bribery.Economic bribery can only occur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action,but no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management,and its constitutive element is the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but not to seek illegitimate interests.
bribery;corporate bribery;to seek illegitimate interests;subjective factor
D924
:A
:1008-2433(2016)02-0110-07
2016-02-06
胡增瑞(1979—),男,安徽固镇人,华东政法大学2013级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经济刑法;卢勤忠(1965—),男,浙江上虞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经济刑法、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