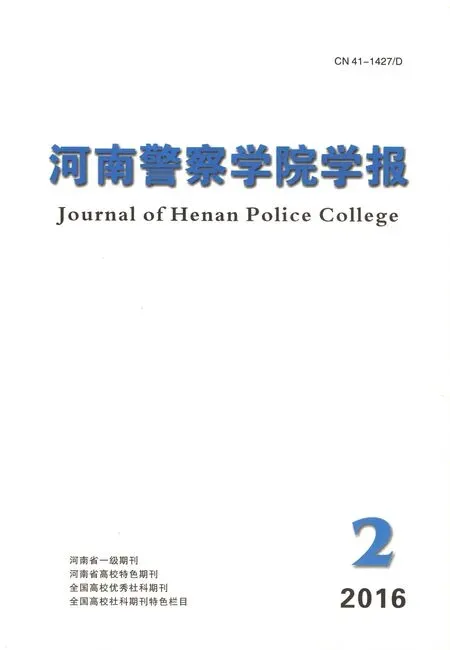政商交易“6.0时代”的刑事困局
——以刘汉案为切入看企业家贿赂犯罪的升级
2016-03-14赵军
赵军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政商交易“6.0时代”的刑事困局
——以刘汉案为切入看企业家贿赂犯罪的升级
赵军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企业家贿赂犯罪手法的升级与反贿赂法的演进一直处于紧张的持续互动之中,非法政商交易已开始向脱离传统贿赂之“财物”/“财产性利益”属性的方向发展。然而,过度犯罪化的努力不是应对贿赂犯罪不断升级的最佳路径选择,通过坚实的“前刑法制度构建”确保公权力不被滥用,才是解决政商交易问题的关键。
财产性利益;不正当好处;非法政商交易
2015年2月9日,随着刘汉、刘维被执行死刑,这件被媒体称为“党的十八大后依法查处的性质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刑事案件”终告段落。然仔细梳理该案所涉15项罪名,①二审法院认为,为偿还刘汉境外赌债兑换外币的行为不具盈利目的,非法经营罪不成立,其他罪名无变动。参见搜狐新闻:《刘汉二审宣判维持死刑判决,个别罪名发生变化》,http://news.sohu.com/20140808/n403234176.shtml,访问时间:2015年6月15日。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保护伞”之间、犯罪企业家与贪腐官员之间通常触犯的贿赂犯罪却未见踪影。2015年6月11日周永康案的判决亦显示,无论是周本人直接收受的财物,还是其子周滨、其妻贾晓晔收受的财物,均与刘汉及其企业无关。②参见新华网:《周永康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5-06/11/c_1115590304.htm,访问时间:2015年6月15日。由此,当初为媒体广为报道的发生在刘汉、周滨之间的“利益输送”,并未进入现实司法程序的审查范畴,这一让普通民众颇感蹊跷与“意外”的结果值得细究。
一、非法政商交易的司法“缺席”
刘汉当初为与周滨建立关系,高价收购了周滨夫妇位于四川茂县的一个旅游项目,这让周滨夫妇顺利从这个开发前景堪忧的项目中脱身并获利颇丰。之后,周滨投桃报李,利用其特殊身份所具有的影响力,为刘汉相关经营活动提供了帮助。③参见财新网:《刘汉与周滨的两次商业合作》,http://china.caixin.com/2014-03-13/100651130.html,访问时间:2015年6月15日。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据此,向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却能够利用其“影响力”“办事儿”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刘汉向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周滨“行贿”,是不构成犯罪的,即便周滨能够利用其特殊的影响力为刘汉谋取不正当利益。①该法律漏洞已被《刑法修正案(九)》弥补。该修正案第四十六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从周滨一方分析,接受刘汉方面通过高价收购旅游项目所输送的利益,也难以成立影响力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受贿罪及影响力受贿罪中“收受财物”的方式虽有相关司法文件细述,但面对具体案件的“新情况”,“认定死角”依然存在。“两高”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以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对那些通过“交易”具有“市场价格”的财物而实施的普通贿赂犯罪,该规定的规制效果较好,但面对“交易”无明确价格参照的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所达成的利益输送却力所不逮。刘汉与周滨夫妇之间围绕某“旅游项目”的非正常交易就属于这种情况——所涉公司并未上市,其实际价值无从计算,无所谓“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贿赂犯罪难以成立。
刘汉案中还有一些与贿赂犯罪危害性相当的政商交易未受刑法评价,这其中就有发生在刘汉、刘维与原德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刘学军之间的交易。2001年下半年,刘学军受命侦查一件凶杀案,在获取刘维是该案重要犯罪嫌疑人的线索后,不但不深入展开调查,反而多次接受刘维等人的吃请。2007年,刘学军主动向刘维提出:刘汉若帮其当上德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主要领导,他就把凶杀案卷“烧掉”,后刘学军如愿当上刑侦支队政委。②参见荆楚网:《聚焦刘汉刘维涉黑案公审:3名“保护伞”认罪》,http://news.cnhubei.com/xw/2014zt/lhsh/201404/t2885779.shtml,访问时间:2015年6月15日。无论该情节的证据状况如何,最终的调查结果达到何种程度,帮助职务升迁与非法职务行为之间的交易都会因不符合“钱权交易”这一贿赂犯罪的“本质特征”而难以成罪。③刘学军滥用职权或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犯罪性另当别论。
可见,刘汉集团所实施的非法政商交易“缺席”司法判决,虽在普通民众“意料之外”,却在现行法律“预料之中”。这种“之外”与“之中”的矛盾,凸显了非法政商交易升级与现行法条的冲突。
二、企业家贿赂犯罪手法的升级
企业家贿赂犯罪手法的升级与反贿赂法的演进处于某种紧张的持续互动关系中。为获取某项经营利益,企业家贿赂贪腐官员的“1.0版”与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实施的、原始形态的、“一事一议”的、以普通财物(钱款)为贿赂物的“典型钱权交易”并无太大区别,这也是刑法中贿赂犯罪基本构成要件的“初始犯罪学原型”。
显然,这种原初形态的“1.0版”贿赂犯罪,并不适合企业经营者用来长期维护某些重要的政商关系。这不仅因为“直来直去”的钱权交易较易暴露和认定,其过于明显的“犯罪外观”也会让处事谨慎的官员心生警惕。于是,意欲寻求官员长期关照的企业家不得不对“典型钱权交易”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包装”。他们或通过与官员的长期“交往”、透过“世故人情”的“礼尚往来”展开“人情化”的贿赂,或通过官员的“特定关系人”/“关系密切者”对官员实施“间接化”的贿赂,这便是以“人情化”/“间接化”为特征的“2.0版”贿赂犯罪。在该“版本”的贿赂犯罪中,如何准确区分正常“礼尚往来”与贿赂犯罪的界限,如何确凿证明官员对“特定关系人”或“关系密切者”收受财物行为的“明知”或“共谋”,成为刑事认定的难点,贿赂犯罪由此获得了某种“掩护”或“伪装”。
尽管如此,“红包”里的钱毕竟还是钱。以现金为主要形式的贿赂,一则“铜臭”太重,有损领导威仪;二则价值有限,不方便大额行贿,也不方便收受者存放,查处风险较高。由此,更为隐蔽、更具文化附加值、更难精确估价、更难认定确切“受贿故意”的“雅贿”开始在政商圈流行。古董字画、奇石文玩,真假莫辨,其实际价值天差地别,很适合政商通融勾兑时的“举重若轻”,也很利于政商交往的“圈子化”和持续化,此即以“文明化”为特征的“3.0版”贿赂犯罪。
“文化”固然无价,但包裹在“文化”外壳内的“文明化”的贿赂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鉴定价值的。而且,与现金之类的种类物相比,作为特定物而存在的艺术品、收藏品,在法律程序中更利于侦查的展开及司法的认定。为摆脱贿赂之“物品”属性所带来的刑事风险,政商交易开始转向以财产性利益为中心的、以“去财物化”为特征的“4.0版”贿赂犯罪。在这一“版本”中,作为“贿赂物”而存在的、具有实体形态的财物(当然也可表现为银行账户中的资金或公司的股份等)被安排旅游、吃喝、娱乐、保健、美容、出国考察、参加学术会议等更为隐蔽的财产性利益所替代。在语义上,这种“去财物化”的“贿赂”与刑法条文明定的“财物”存在一定差异,一度在某些领域和行业成为犯罪企业实施贿赂犯罪的重要选项。①如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部分贿赂行为即以此种形式完成。参见人民网:《揭开跨国药企商业贿赂利益链》,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715/c1004-22194208.html,访问时间:2015年6月18日。
伴随最高司法机关对贿赂犯罪中“财物”的扩张解释,以财产性利益为贿赂物的入罪判例不断出现,贿赂犯罪随之向“交易化”的“5.0版”迈进。在这个“版本”中,行贿人通常会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或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财物。这种贿赂因介入了“交易”而变得隐蔽、复杂,加之市场行情的变动性以及交易主体对交易标的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在具体案件中要认定交易价格与市场明显背离以及交易双方的贿赂故意,并不容易。尤其当“交易对象”不存在确定的“市场行情”时,司法上的认定便成为一项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此一来,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前景不明的经营项目收购,乃至于收藏品的流转,就成为完成非法政商交易相对“安全”的操作模式。
不过,这种“安全”也是相对而言的,“交易”中数额过巨的价差很容易被发现。刘汉高价收购周滨夫妇旅游项目就遭到过公司内部高管的质疑,类似情况在刘汉的关联公司低价获取云南某优质矿产的过程中也发生过。违背市场行情的反常操作本身未必能够成立犯罪,但却容易成为深查贪腐犯罪的线索。发展到这一阶段,非法政商交易的升级必然向脱离传统贿赂之“财物”/“财产性利益”属性的方向发力,传统贿赂犯罪“钱权交易”的“本质特征”被淡化、否定,政商交易由此进入“6.0时代”。在这一最新“版本”的“贿赂犯罪”(这已非现行法意义上的“贿赂罪”了)中,原来与权力进行交换的“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被“非财产性利益”所替代,这些“利益”可以是这些年经常在公共空间中讨论的“性贿赂”,也可以是刘汉、刘维案中的职务晋升,还可以是任何能够满足“受贿人”某一方面需要的非财产性“好处”。当然,用这种方式“行贿”,需要有相当的处事手腕和综合实力——给领导安排“女明星”交往,为官员解决职务晋升、文凭学位、子女出国留学等重大问题,都要以足够深厚的人脉资源和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正因为如此,往往只有那些与官员结成紧密的“利益同盟”,甚至达到“地下组织部长”级别的企业家才能进入这个政商交易的“6.0俱乐部”。从这个意义上讲,犯罪企业家是推动政商交易乃至整个贿赂犯罪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三、社会反应的路径选择
如上所述,企业家贿赂犯罪由最初的、“典型”的“1.0版”逐步发展升级为晚近“变异”的“6.0版”,这其中既有人际互动、社会变迁及犯罪手法自我改进、更新的推进作用,更有法律现实规制、演化的促成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应对犯罪之社会反应重要内容的法律规范,经历了一系列调整与扩张。贿赂物由“财物”扩充至“财产性利益”,受贿主体由自然人、国家工作人员扩展至单位、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特定关系人”或“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限制功能不断软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法律上的调整与变化都是为了应对不断升级的贿赂犯罪,而这种调整与变化又反过来促成了贿赂犯罪的进一步升级,这几乎成为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作为最新的立法动向,《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规定,这为处罚向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即便如此,对“高版本”(“5.0版”以上)的政商交易仍难以有效规制。这是因为,无论怎样扩张、修补,我国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都难以脱离其“源头模板”的限制。这个“源头模板”有两个彼此关联的本性:一是“钱权交易”,二是“计赃论罪”。即便是“财产性利益”,那也是“钱”的变体,可以折算成金钱;即便介入了某种形式的“交易”,成交价格与正常价格的差额仍可作为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依据。可一旦借以输送利益的标的价值无从计算,或者“贿赂物”被置换成某种不能折算成金钱的非财产性利益,现行刑法贿赂犯罪的规制力便失效了。“6.0版”及部分“5.0版”的政商交易即如此。刘汉方面为刘学军职务晋升所提供的帮助,属前者;刘汉、周滨之间通过无法确定准确价值之非上市公司股权或前景不明之商业项目的转让实现利益输送,属后者。
为有效应对这些高版本的非法政商交易,突破我国贿赂罪犯罪构成要件“源头模板”的限制,是一种合乎逻辑也有国际法依据的路径选择。《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所规定的“贿赂”都是“不正当好处”,该术语能够涵盖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及非财产性利益在内的所有非法利益。如果将我国刑法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扩张至这两个国际公约的水平,上述“高版本”政商交易所引发的法律适用难题将迎刃而解。不过,这一扩张会带来新的难题。将能够“计赃(折算)论罪”的传统“(变相)钱权交易”与绝无折算可能的非财产性利益与权力的交易,规定在一类犯罪中,可能会带来定罪量刑方面的混乱与失衡。譬如,受贿10万元与帮助提拔为正处级干部,究竟孰轻孰重?行贿100万元与性贿赂领导100次,谁的危害性更大?不能准确计算价值差额的不正常交易如何量刑?如此等等。显然,尽管都属于“不正当好处”,但财产性的贿赂与非财产性利益的“贿赂”在危害程度的判断基准上存在重大差异,强行将两者整合在一起,未必是最佳选择。
进一步分析这个没有太多限制的“不正当好处”,会出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疑问。若以性换权是贿赂,那以陪伴(跳舞、打网球、聊天……)、友谊(很多官员其实没多少真朋友)、赞美(拍马屁)、情感慰藉(很多官员的内心其实很空虚)、良好的人际关系体验换取权力的不当行使,是否也是贿赂?若帮助职务晋升可以构成贿赂罪,那为了换取权力的不当行使,帮助官员提高艺术品鉴赏水平、提高文化修养、提高摄影技巧、提高高尔夫球技、提高衣着品位,是否也可构成贿赂罪?尤其是在贿赂罪之“谋利要件”不断弱化的背景下,把这些“非财产性利益”统统纳入犯罪圈,官员正常的人际交往还存在吗?正常的政商关系还存在吗?正常的社会管理以及正常的企业经营活动还存在吗?这些疑问似乎在提示我们: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固然必要,但过度犯罪化的努力或许不是应对贿赂犯罪不断升级的最佳路径选择。严防政商不当交易、合理管控政商人际交往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如何保证公权力本身不被滥用,而这需要坚实的“前刑法制度构建”。在此意义上,在政商交易进入“6.0时代”的当口,我不得不再次站在“少数派立场”——贿赂犯罪刑法条文的升级需慎之又慎。
(责任编辑:刘 芳)
The Criminal Dilemma of Version 6.0 of the Trading between Politics and Commerce——Taking the LiuHan Case as a Breakthrough to View the Upgrade of the Entrepreneur-Bribery
ZHAO Jun
(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The advance of the entrepreneur-bribery crime manners and the evolving of the anti-bribery law has been in a tense and sustained interaction.The illegal trading between politics and commerce ditches the traditional bribery of property or property interests.However,the undue criminalization is far from the best option to elevate the countermeasures of bribery crime.It is the solid“foundation of pre-crime regulations”making the public power not be abused that is the key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rading between politics and commerce.
property interests;undue advantages;illegal business transaction
D924
:A
:1008-2433(2016)02-0023-04
2016-01-15
赵 军(1969—),男,湖北宜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犯罪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秘书长,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犯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