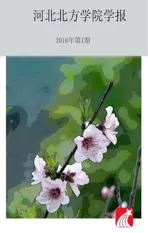歌颂暴力的美学——浅析《伊利亚特》战争观念的内涵
2016-03-14崔鸣华
崔鸣华,高 方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7)
歌颂暴力的美学
——浅析《伊利亚特》战争观念的内涵
崔鸣华,高方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7)
摘要:荷马在《伊利亚特》一书中对战争场面的直接描绘充斥着浓重的血腥气息,最直接地体现了暴力和死亡的力量。他将战争中表现的暴力作为美的事物进行歌颂,暴力因此被纳入美的研究范围中,成为暴力美学。歌颂暴力的美学是其在史诗中表现的一种独特的战争观念,核心是将对暴力的批判转变为一系列动作的欣赏和场面的铺排。经过净化后,战争、暴力及杀戮终将展现为人性的光辉。
关键词:《伊利亚特》;暴力美学;战争观
《伊利亚特》所反映的战争观念不同于其他军事作品,荷马在书中以欣赏的目光歌颂英雄,褒奖战争,对战争场面的直接描绘充斥着浓重的血腥气息,最直接地体现了暴力和死亡的力量。他将战争中表现的暴力作为美的事物进行歌颂,暴力被纳入美的研究范围中,成为暴力的美学。暴力美学的出发点是形式化的体验,将暴力本身作为审美的对象,其研究主要集于战斗场面,重点发掘打斗和杀戮等暴力手段的形式美感,试图营造一种令人兴奋的主观感受。在暴力美学的运作下,死亡的恐惧和暴力的血腥得以清除,并逐步升华为对英雄力量的崇拜与人性觉醒的赞美。从生存经验出发,暴力美学构建起人类力量的完美形态,彰显英雄的个人魅力与人性的普遍光辉,体现了古希腊人的审美道德。因此,暴力美学将道德评判的权力交给读者,并给予其纯粹的欣赏视角。从暴力美学的角度出发,《伊利亚特》战争观念的特别之处在于战争是歌颂暴力的美学。
一、暴力的渲染与死亡恐惧的消除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广泛地采用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发展理念,其要义在于无论个人还是种族为求生存和繁衍,必须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不断改造自己以适应环境的挑战和社会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迈向文明的同时也不断地深化对暴力的认识。供需矛盾形成的冲突演变成一种竞争,而暴力则成为战胜对手的有效手段。暴力的出现具有特定的合理性,它作为人类的原始经验沉淀于个体的记忆中,并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具体体现,而荷马正是这样一位善于将暴力表现在具体文本中的渲染者和赞美者。因此,从暴力美学的角度出发,对暴力场面的渲染和死亡恐惧的消除成为作者欣赏战争暴力之美的前奏,也是《伊利亚特》战争观念所表现的内涵之一。
(一)暴力场面的渲染
《伊利亚特》一书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多倾向于精细化和具体化,以显示作者在暴力场面的构建上所进行的精心安排。作者常用铺叙手法对血腥的战斗场面大量着墨,细致渲染血流漂杵、脑浆飞溅及尸体横陈的战争场景。小说描述特洛亚人反攻阿开奥斯人时,“他们相逢,来到同一个地点的时候,盾牌、长枪、身披铜胸甲的战士的力量相互猛烈地冲击,有突出装饰物的盾牌彼此靠近,爆发出一阵阵大声的喧嚷。杀人者和被杀者的呻吟和胜利呼声可以同时听见,地上处处在流血”[1]170。荷马通过描摹战士生死搏杀的详细画面,展现了其刻意处理过的暴力形态。一方面,荷马在描写两军交战时,常常会出现这样一幅景象:旁观的牧羊人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阵亡将士身上流出的鲜血逐渐汇聚成了溪流,从高处坠落到深潭中时就如同瀑布一样能听见它的轰隆声①。作者通过夸张的手法将暴力场面高度形象化和场景化,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表现出战争的残酷。另一方面,身披华丽战甲的士兵纠缠在一起,刀剑碰撞与盾牌相抵,不时发出刺耳的响声和痛苦的哀嚎,直接展示了施暴的全过程和血腥的效果,渲染了暴力带给人的感官刺激。此外,这类场景在文本中不断出现,高度形象化的场面持续渗透到人的思想中,改变了暴力的刻板印象,并使之成为可以接受的事实。
(二)死亡恐惧的消除
荷马真实地再现了血流漂杵的战斗场面。他将暴力以一种日常的甚至是略显称赞的方式表现出来,用鲜血铺就的风景将野蛮和崇高交织在一起,表现了暴力的形式美感,使读者在刺鼻的血腥中感受到战争的撼人心神和死亡的高贵气质。
古希腊人认为,死亡所展示的高贵气质最终消除了人对死亡的恐惧。一方面,古希腊人将死亡视作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即死亡是人的命运。“天父取出他的那杆黄金天秤,把两个悲惨的死亡判决放进秤盘,一个属于阿基琉斯,一个属于驯马的赫克托尔,他提起秤杆中央,赫克托尔一侧下倾,滑向哈得斯,阿波罗立即把他抛弃。”[1]507除了神,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死亡的结局。尽管英雄赫克托尔强健有力,但仍然不能逃脱命运的支配。古希腊人憎恶死亡,却从不回避死亡。所以,他们在埃莱夫西斯建立了供奉冥王哈迪斯的神庙,以此昭示死亡是“他者”操纵的力量,和凡人无关。这样,令人战栗的死亡可以堂而皇之地被转换为坦然面对的现实。对古希腊人来说,在死亡面前,暴力的实施者和受难者处于同样无辜的地位。“从来没有人如此苦涩地讲述人类的悲惨,悲惨甚至使人类再没有能力感觉悲惨。”[4]他们受制于命运的捉弄,不能自已。因此,看淡死亡。另一方面,既定的死亡使人感到解脱,脱离死亡束缚的人往往更倾向于生命的狂欢,战场或斗兽场成为发泄剩余激情的主要场所,其中蕴含的暴力常常与死亡如影随行,战斗中的种种暴力直接导致了更多的死亡。“整个原野满溢着洪水,水上漂浮着无数精美的铠甲和被杀死的青年的尸体,阿基琉斯抬膝跨步,迎着水流前进,任河神波涛汹涌,也难把他阻挡,雅典娜给他胸中灌输了巨大的力量。”[1]487暴力是一种毫不掩饰的伤害性力量,战争中它必然会伤及性命,循环往复的过程越多,其结果也越惊人。它的魔力在于将活生生的个体杀死,更甚者将人看作暴力的工具,使其变成活着却没有思想的物。因此,处于战争中的战士不在乎死亡的结果,“让赫克托尔杀死我吧,特洛亚人中他最优秀;高贵之士杀人,杀死高贵之人”[1]486。阿基琉斯不避死亡,他认为死亡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既然如此,何不将短暂的人生变成流光溢彩的传奇,而成就自我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战争中纵情厮杀,成就一番事业。因此,对阿基琉斯来讲,暴力不仅是不需要避讳的负面因素,反而成为强大的力量和保卫灵魂的盔甲。
“恐怖、痛苦、疲倦、杀戮、消亡的同伴,人们相信,除非力量的酒意前来淹没这一切,否则它们不可能停止折磨灵魂。”[4]命运控制下的战士不得不屈从于恐怖、杀戮或者死亡。这意味着古希腊人必须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消除对死亡的恐惧,用暴力的形式将生命投入战场,化作狂欢的肉体。暴力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成为战士们争相追逐的对象。
二、形式化的快感体验
荷马歌颂英雄和战争。他正视战争中存在的血腥暴力,战争场面的铺排更加强化了暴力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强调的暴力场面“不按照真实来表现,经过艺术化加工与设计来展示攻击性力量,展示夸张的、非常规的动作;追求形式快感,不强调特定的‘意识形态结论’……”[3]简而言之,就是将各种武备兵器及各式武打动作结合起来组成新的视听元素来表现暴力场面。
当特洛亚人冲击阿开奥斯人坚固的营垒时,“佩里托奥斯之子,强大的波吕波特斯掷出长枪击中达马索斯的同颊头盔,头盔没有能挡住投枪,投枪的铜尖却一直穿过了他的头骨,里面的脑浆全部溅出,立即制服了进攻的敌人”[1]274。作者有意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景——战场之上的波吕波特斯掷出投枪刺穿达马索斯的铜盔,使读者仿佛能够听到投枪接触盔甲的一瞬间爆发出的金属卷曲的响声,表现了英雄的武力超群和力大过人,显示出英雄施展的暴力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脑浆飞溅”生动形象,将血腥暴力的场景转换成为可视的形象,使读者在感官上形成一种刺痛感。“投枪刺穿头骨”与“脑浆溅出”这两幅画面组接在一起,实际上是将人的力量和血腥的暴力结合到一起。在战争中,暴力具有突发性,但是,从投出标枪到刺穿头骨致人死亡是一系列连贯的动作,在形式上体现了力量的美感。将暴力的场面分解并关注其动作上的变化,实际上是对人的力量做夸张化的处理,以突显英雄气势之磅礴与精神之伟大。
生存和死亡一直都是人类深感困惑的问题。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人类受到求生意志和赴死意志的双重压迫,并在双重迫力下寻求解脱之道,其最终结果是从十分敏感的内心生发出由衷的悲剧情结,而古希腊人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典范。即便是最血腥与最残酷的景象,他们也能够承受,并将之表现为“希腊式的快活”[2]304-305,而“希腊式的快活”②集中反映了古希腊人内心的痛苦和冲突,从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激发出的人生悲剧感化为萌动于外的艺术冲动,其目的是为了挽救人的灵魂与肉体。因此,《伊利亚特》对战争流光溢彩的描绘表现的是希腊人的好战心态,在战争中他们都得以平和。“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当时也这样临面冲杀到一起,没有人转念逃逸。双方狂勇如狼,进行的同等的杀戮,制造呻吟的埃里斯看着心满意足。”[1]239在常人看来战争是恐怖的,但是,“埃里斯”对于死亡并不感到恐惧反而感到满足,这表明战士欣赏暴力且热爱战争,只有身在战场,他们才会感到满足,杀死敌人或者被敌人杀死都能宣泄和抚平内心的矛盾,实现“希腊式的快活”。“心满意足”一词真切地反映了古希腊人内心的纠结与萌动,他们将灵魂的寄托与精神的支柱表现为一种酒神与日神纠缠的情结——光明与黑暗、狂喜与痛苦以及理性与痴迷,并通过表现这些情结来装饰华丽的战斗场面,进而将血腥的暴力转变成一种形式的美,从而掩盖了暴力的实质。
古希腊人的悲剧情结暗示是“希腊式的快活”的另一层含义,即隐藏在人潜意识中的死亡意志以及通过这种意识表现出的狂欢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中的暴力、杀戮甚至英雄都是人在寻求狂欢精神的具体表现。战争成为古希腊人实现死亡意志的重要场所,他们通过暴力或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以此来平息内心的死亡冲动,并通过敏锐的目光透视自然的残酷和人类社会可怕的毁灭性进程,以艺术的方式否定求生的意志。“让我们一起去进攻船只,如果你们有人被击中遭到不幸,被死亡赶上,那就死吧,为国捐躯并非辱事……”[1]353赫克托尔率军袭击阿开奥斯人的船只前,鼓励特洛亚的战士们勇敢地面对战争,奋勇拼杀,不惧死亡。“阿开奥斯人和特洛亚人围绕着这条船面对面凶狠搏杀,现在他们已不再是远远地等待对手投掷或者放射枪矢,而是近在咫尺地怀着同样的热望,用锐利的铁钺和板斧,两端带刃的长枪及锋利的长剑疯狂地面对面砍杀。许多精美的黑柄长剑从战士手里掉落到地上,或者连同他们的肩膀被一起劈下,鲜血染黑了泥土。”[1]361这一段描述真实地再现了交战双方围绕船只进行激烈搏杀的场景,在激烈的战斗中,以个体消亡为终点,并通过暴力的手段最终完成了狂欢仪式的全过程,也使读者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解脱和自由的快感。同时,这也印证了尼采的观点——随着生命的消亡,附加于其的一切苦难都将化为乌有;虽然人与自然终将融为一体,但个体会在周而复始的毁灭中感到由衷的欢乐。
借助暴力手段毁灭个体成为古希腊人寻求精神解脱的方式。《伊利亚特》描绘了一场迷狂的战争,它解除了个体的枷锁,复归原始的自然,就像酒神狄奥尼索斯纵情狂欢,打破一切禁忌,忘却自我的个体与世俗追求,在令自己痛苦甚至毁灭的迷狂中得到欢乐。荷马找到了一种调和内心冲动的方式,并将其纳入战争观念中。他将暴力形式化,成功地寻找到暴力所表现出的力量之美,通过“希腊式的快活”消解暴力的负面因素,使其成为纯粹的审美,完成了古希腊人内心狂欢化的过程。
三、人性的光辉
荷马不惜笔墨描绘英雄争斗的具体场景,称赞战争中的勇士,反映了其独特的战争观念。当暴力被当作一种美来看待,战争便不再是令人恐惧的杀戮机器,“通过特殊手段对有关暴力的作品进行改造,使得人欣赏时不自觉地采纳了另一个价值系统”[3]。循环往复的动作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③,通过夸大血腥的场面吸引注意力,激发读者的思考进而产生怜悯与认同。荷马歌颂英雄,欣赏暴力。因此,在暴力迸发出的一瞬间所表现的是充满人性光辉的美学。
首先,《伊利亚特》塑造的英雄形象表现出完整的人的特点。他们充满荣誉感,为了城邦利益而奋斗;同时也极看中个人荣誉。当阿伽门侬私自占有了阿基琉斯的女奴时,阿基琉斯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愤而退出战场,致使阿开奥斯人节节败退。虽然阿伽门侬向阿基琉斯表示歉意,但是“他不愿平息怒火,更加充满火气,蔑视你本人,拒绝接受你的礼物”[1]504。对物质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即使是英雄也不能逃脱物质利益的诱惑。阿伽门侬的贪婪与阿基琉斯的任侠使气都是最真实的人性,荷马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让读者看到了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暴力美学强调,“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平凡也好,艰辛也好,幸福也好,痛苦也好,其背后都存在着苍白的现实”[5]。阿开奥斯人以帕里斯拐走海伦为借口发动了特洛亚战争,帕里斯希望能以两倍的财富平息这场战争。但是,阿开奥斯人想要的不仅仅是海伦,更是整个特洛亚城的财富、女人以及奴隶④。虽然暴力美学聚焦于动作的形式,但它旨在还原事件的真实,引起人们的注意。荷马从不隐藏希腊人发动战争的目的,读者从他的表述中能够感受到阿开奥斯人对于财富的渴望,并且更深刻地认识到战争中的暴力和杀戮都是其抢夺财富的手段。
其次,英雄透过神灵看到了死亡的必然命运。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出对死亡本能的恐惧。赫克托尔下定决心在特洛亚城下决一死战,但当“阿基琉斯来到近前,……如同一团烈火或初升的太阳的辉光。赫克托尔一见他心中发颤,不敢再停留,他转身仓皇逃跑,把城门留在身后……”[1]477荷马写出了英雄的恐惧。因为没有战士能够克制对死亡的恐惧,即使是英雄在死亡面前也会胆怯。小说中,荷马只是记叙了一个事实,“它不直接激发观众的主动性,而是需要通过观众思考来得到结果”[3]。读者通过文本了解世界的真相,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不仅没有成为英雄身上的污点,反而成为他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最好诠释。但是,英雄毕竟不同于一般人。他们虽然恐惧死亡,可是,当需要履行使命牺牲生命时,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犹豫。阿基琉斯不顾母亲劝告,执意要上战场。“我心里明白,我命定战死在此。远离心爱的父母;只是,我必要把特洛亚人杀个够!”[1]26“把特洛亚人杀个够”带有明显的主观复仇色彩和浓重的暴力倾向。阿基琉斯通过暴力手段为好友报仇,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将赫克托尔杀死后,没有听从赫克托尔的临终请求,而是粗暴地侮辱了对手的尸体。荷马毫不掩饰阿基琉斯的残暴,侮辱赫克托尔尸身的举动令人恐怖。读者在一系列动作中感受到的不仅是阿基琉斯的怒火,还有对死去的赫克托尔的同情和怜悯。“怎么?那道路宽阔的特洛亚城,我们为它历尽艰辛,如今却要放弃它?”[1]239奥德修斯不同意阿开奥斯人撤退。他不在乎海伦和特洛亚城本身,他认为敌人的存在迫使它接受一切不愿接受的东西。他希望通过摧毁敌人来消灭外部世界的压迫,从而自由地接受一切,使自己得到拯救。阿基琉斯也面对相似的处境,他被仇恨所驱使,暴力成为他寻求自由的方式,摆脱外在迫力的过程也是暴力改造其价值体系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人性的种种特征。
最后,英雄必然走向死亡,因为他们从不满足于对力量的追寻和渴望。暴力带来的刺痛感使死亡成为令人敬畏的情感,暴力的实施者和接受者——英雄则成为他们敬重的对象。在战争中,“人性”得以苏醒,英雄显示出人应该具有的在现实社会中的生活和追求,而这些都将在施暴与受暴的过程中完成。
任何事物都具有美的因素。通过人文价值的关照,即使是暴力也可以转变成美的事物。因此,荷马所歌颂的暴力也被纳入欣赏的范围内。荷马关注英雄,通过描写整个施暴过程表现力量的美感;通过将暴力进行形式化的处理,提取其中的美感,暴力的恐惧得以净化,成为纯粹的审美过程。此外,荷马将暴力合理化,即肯定了人的力量,深刻反思人性的幽暗,进一步发现人性的光辉之处。从暴力美学角度来看,《伊利亚特》所蕴含的战争观念通过表现暴力构建起人类力量的完美形态,消除了死亡的恐惧,彰显了英雄的个人魅力与人性的普遍光辉,体现了古希腊人的审美态度。暴力美学强调将道德评判的权力交给读者,进而创造了一种纯粹的审美态度。从这点出发,《伊利亚特》所讲述的战争及暴力并不可怕,因为战争、暴力及杀戮终将展现为人性的光辉。
注释:
①“被杀人的痛苦和杀人的人的胜利欢呼混成一片,殷红的鲜血流满地面。有如冬季的两条河流从高高的山上,从高处的源泉泄到两个峡谷相接处,在深谷当中把它们的洪流汇合起来,牧人在山中远处听得见那里的响声,呐喊和悲声也这样从两军激战中发出。”
②“希腊式的快活”一词源于尼采对于古希腊艺术的本质、作用以及与人的关系的看法。尼采认为,悲观主义确实是真理,现实世界对于每个人来说的确是残酷而无意义的。为了活下去,我们需要用艺术这种谎言来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为了肯定人生,我们需要悲剧世界观,用审美的眼光看待现实世界的生成、变换过程,把现实世界艺术化,把人生的苦难化作审美的快乐,把人生的悲剧化作世界的喜剧。
③荷马在《伊利亚特》一书中的写到了两军交战的情景,英雄之间相互决斗的场景则更加常见。脑浆、鲜血、骨头等使用频繁,以此形成一种重复循环的视觉体验,延长了读者的感受过程,使之形成了一定的欣赏心理。
④帕里斯在特洛亚人大会上宣布,不愿交出妻子海伦,但愿意支付双倍从阿尔戈斯带回的财富。消息传到联军中,狄奥墨得斯说出了出征的目的:“‘如今不要让人接受帕里斯的财产或者海伦;人人知道,连傻瓜也知道,特洛亚城从此处在毁灭的边缘。’他这么说,阿开亚人个个欢呼。”
参考文献:
[1]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马国新.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尹洪,冷欣,程辉.试论“暴力美学”及其特征[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8,(2):97.
[4][法]西蒙娜·微依.《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J].吴雅凌,译.上海文化,2011,(3):71,76.
[5]张炜.灵魂的冲撞——电影暴力美学的启示[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1):44-45.
(责任编辑张盛男)
Aesthetics of Violence——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War inIliad
CUI Ming-hua,GAO F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Kashgar University,Kashgar,Xinjiang 844000,China)
Abstract:Homer’s explicit description of the bloody scenes in war in Iliad most directly reflects the power of violence and death.He sings so highly of violence in war as a thing of beauty that violence has become part of the aesthetic research,called aesthetics of violence.Aesthetics of violence,which sings of violence,is a unique concept of war conveyed in Iliad.Its core is to turn violent criticism into the appreciation of a series of action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scenes.After being purified,war,violence and killing are displayed as the glory of human nature.
Key words:Iliad;aesthetics of violence;the concept of war
中图分类号:I 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6)01-0076-05
作者简介:崔鸣华(1988-),男,山西大同人,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喀什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课题项目(KSGRI2015018)
收稿日期:20151017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60106.1532.036.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6-01-06 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