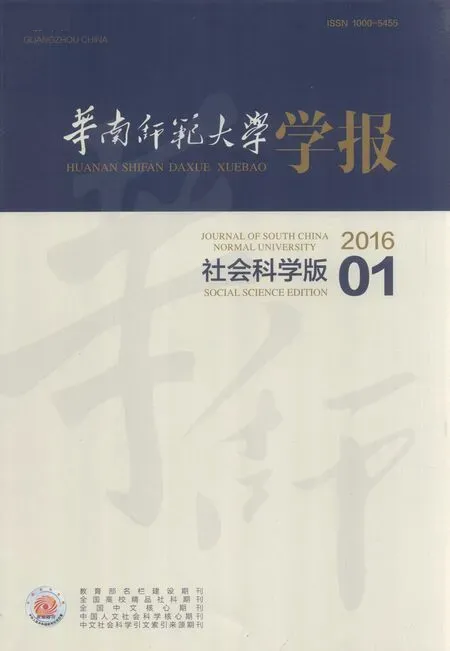陆游与唐诗史“盛唐”观念之建构
2016-03-11吴光兴
吴 光 兴
陆游与唐诗史“盛唐”观念之建构
吴 光 兴
【摘要】钱钟书《谈艺录》指出陆游为宋代诗人中“学太白最似者”。陆游“入蜀”途中、仕蜀期间对李白、杜甫、岑参的专题研习,是他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陆游的文学新思想(“文气”说、“雄浑”品目等)继往开来,也为宋末唐诗史“盛唐”观念之建构开了先河。
【关键词】陆游“盛唐”“文气”说李白杜甫岑参
说到唐诗史,人们耳熟能详的无过于将三百年唐诗史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阶段的“四唐说”了。本来,分段落叙述历史演变,以“前、后”“前、中、后”或“初、中、晚”为次序分期,符合人类认识的常规,若非“盛唐”横亘在其中,“四唐说”也就没有多少特别的意义了。因此,“盛唐”观念之建构,实为“四唐说”之关键。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盛唐”观念还产生了一定的模式、标准作用,“盛宋”“盛明”甚至“盛汉”之类的概念都屡见不鲜。一个“盛”字,神奇建构了一种强盛时代、高尚人格、伟大文学之间的特殊关联,也创造出一种文学史认知、叙述模式。其意义不可谓不大。
“诗必盛唐”的口号是明代人喊出来的:“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卷二八六《文苑·李梦阳传》。但是,明确的“盛唐”概念可以溯源至宋末,以严羽《沧浪诗话》尤其著名。若论“盛唐”观念之建构,则更可以自严羽的时代向前追溯,本文将重点关注南宋中兴诗人陆游(1125—1210)在唐诗史“盛唐”观念建构历程中的角色、作用等问题。
一、“前陆游”时代的唐诗史叙述
讨论陆游之前的唐诗史叙述的问题,首先要辨析“唐诗”的王朝史、文学史界限之分别,也可以称为狭义、广义“唐诗史”之区别。古代帝制时代,“唐诗”即唐朝之诗,起武德元年(618)、迄天祐四年(907)是严格、标准的说法。但是,如果以文学发展为本位,又可见唐朝初年的文学与南北朝大体一脉相承,而唐朝诗风的流衍更至北宋中叶才被完全遏止,“泛唐诗”或“大唐诗”的概念就要复杂一些。这些必须心中有数。
“前陆游”时代的唐诗史,唐人的自我认识足资参考。对于唐诗史的演变,一方面,唐人的叙述多举年号论时期,如龙朔、景龙、开元、天宝、大历、贞元、元和、长庆、大中、咸通云云。另一方面,众说纷纭,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尽管如此,质其实质,对于唐诗史演变的共识,在唐人之中也是客观存在、可以稽考的。大体而言,“律诗建制”“元和诗变”可以视为唐诗史内部两座最大的“路标”。后人有将唐诗概称为“唐律”的,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告竣的“律诗之建制”,对六朝文学成功总结,又创造了文学新体制,唐人普遍视为唐代文学的门户。而“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见《全唐诗》卷四四六,第5000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作为唐诗史内部最大的革新,“元和诗变”同样具有划时代地位,“白居易的时代”不仅笼罩晚唐百年,而且延续至五代、宋初,北宋中期才真正被终结。总之,唐人视野中的唐诗史分为前、中、后三期,沿用比较流行的称呼,景龙之前的前期可曰“初唐”,元和之后的后期可曰“晚唐”,唯景龙之后、贞元之前的中间百年一段,因“四唐说”流行之后“盛唐”“中唐”概念的干扰,称为“唐中期”稍为稳妥一些。*拙著《八世纪诗风——探索唐诗史上“沈宋的世纪(705—8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主要表出的就是唐人相关历史认识的问题。唐人对开元、天宝时期文学成就有多种认识与论述,但是,作为一个文学时代、文学典范的“盛唐”观念或概念并无建构的迹象。
唐诗史叙述的新阶段的来临,在于唐诗“盖棺论定”“大唐诗”时代被终结的时期。经过几代“韩愈知音者”群体的连续努力,“古文”终于获得了文体的正宗地位。北宋中叶庆历、嘉祐、元祐年间,以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不仅创造了更具活力的宋代“古文”,而且,堪与“唐诗”分庭抗礼的“宋诗”也走出了一条新道路。北宋诗文革新的一个特征是继承韩愈的事业,在韩愈经典化、普及化的历史条件之下,相关的历史认识受到韩愈话语的极大影响。落实在唐诗史叙述方面,一者,作为唐天宝至贞元时期复古思潮的集大成者,韩愈文学趋向复古,与唐诗“清丽居宗”的基本价值异辙*宋人尊为典范的韩愈的话语,在唐诗的言论世界属于“非主流”。,因此,宋人论唐诗,在“古—今”这一维度上,右古左今为基本立场。二者,韩愈并尊李杜,这一点对宋人影响也大。例如,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曰:“既观坐长叹,复想李杜韩。愿执戈与戟,生死事将坛。”(《宛陵集》卷四六)当然,在诗歌世界,宋代“杜甫典范化”超过韩愈,然而,杜甫文学古今兼综、门庭广大,且杜甫活跃在唐中叶,时代偏前,唐诗史叙述方面,能够奉为信条的不刊之论反而不特别多。简而言之,宋人的唐诗史叙述“与韩愈合辙”的“近古”特征,值得重视。这也是陆游认识、叙述唐诗史的一个前提。
至于贯穿全部宋诗史的“晚唐”话题。如上所述,从文学本位的“大唐诗”角度观察,北宋前期流行“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其状态与唐诗史上流派纷陈的“晚唐”时期一脉相承;以此为例,可以说北宋诗文革新正是因反抗“晚唐”而起来的。代表宋诗高峰成就的江西诗派将“晚唐”悬为厉禁。黄庭坚《与赵伯充书》曰:“学老杜诗,所谓刻鹘不成尚类骛也。学晩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黄庭坚:《与赵佰充书》,见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五《向背》,第154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从宋诗的立场看,作为“晚唐”的“天敌”,它对“晚唐”多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架势。然而,当江西诗派的作风普遍蔓延之后,批评者竟也操起“晚唐”作为利器。文学史上的陆游,恰好置身在“晚唐”起而与江西诗风较量的潮流之中。总之,宋诗史上、宋人口中的“晚唐”首先应该当做一个活的概念来看待,其次才与“唐诗史”相关。从时序、逻辑上看,“晚唐”似乎也先于系统、完整的唐诗史观而存在。
陆游之前的唐诗史叙述,除了唐人的认识已为陈迹,宋人之中也已大致达成偏尚“复古”的基本倾向,而“晚唐”更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二、陆游对唐诗史的认识
观察陆游对唐诗史的认识,还要顾及更大的环境因素,如古文复兴、理学流行、士大夫主人翁意识高昂、宋诗粗具与唐诗分庭抗礼之势。新社会、新文化、新文学构建出宋人评论唐诗的总体氛围、言论平台。不赘。
陆游对唐诗史的认识,以他本人的写作生涯为参照,分别以乾道六年(1170)入蜀、淳熙十六年(1189)罢官归隐为标志,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陆游的早期生涯,又可以他十八九岁拜师江西诗派著名诗人曾几*按:于北山认为陆游始师曾几于绍兴十二年(于北山:《陆游年谱》,第38—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孔凡礼则说是绍兴十三年(孔凡礼:《孔凡礼文存》,第156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两存俟考。为标志,分作两个小阶段。
陆游出身于士大夫官宦世家,自高祖陆轸始,数代人通过进士、门荫途径而出仕。家世文学、藏书也有几代积累。祖父陆佃为王安石门生,官至尚书左丞,有小学著作《埤雅》、别集《陶山集》等。陆佃长于七言近体,《四库提要》评论陆游文学成就与家学有关系:“(陆佃)以七言近体见长……厥后,佃之孙游以诗鸣于南宋,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虽得法于茶山曾几,然亦喜作近体。家学渊源,殆亦有所自来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陶山集》。陆游少年时代在乡校的老师之一、族父陆彦远更是王安石学术的坚守者。陆游在《斋中杂兴十首(其一)》中曰:“成童入乡校,诸老席函丈……从父有彦远,早以直自养。始终临川学,力守非有党。”*陆游:《剑南诗稿》卷四三,第647页,中国书店1986年版。可见,少年陆游的文学启蒙,受王安石趣味的影响必不小。北宋文学诸大家之中,在宋诗与唐诗立异、努力走出自己道路的历程之中,王安石为文工丽,对唐诗的同情、继承比较多,编有《唐百家诗选》。宋人胡仔引《后山诗话》曰:“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宋)胡仔编:《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二《东坡五》,第2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因此,接近唐诗规范的美文、抒情方面,陆游“文学少年”时代应受到过一定训练。十八九岁从师曾几之前的陆游,对包括“晚唐”在内的唐诗史具备基本的认识,也是合乎情理的。
师从曾几(1084—1166),是陆游文学生涯中的大事件,《剑南诗稿》以《别曾学士》为压卷第一篇,寓有深厚敬意。江西诗派发展至两宋之交,吕本中(1084—1045)、曾几成为极具影响力的领袖。吕本中去世稍早,青年陆游很荣幸亲身接奉文坛前辈曾几。曾几除了给予陆游以指导,还夸奖陆游诗的风格源自吕本中。*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四《吕居仁集序》,第81页,中国书店1986年版。“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陆游:《剑南诗稿》卷二《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第37页。成为诗坛正统的衣钵传人,对陆游的揄扬之深、激励之大可想而知。因此,江西诗派的基本规范、吕本中的“活法”理论、曾几“轻快”“活泼”*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文风,自然影响到陆游早期的创作、思想。
总结早期陆游的文学思想与观念,可得如下要点:一者,作诗主工丽。《示子遹》自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剑南诗稿》卷七八)作诗求工,为王安石、江西诗派所同趋。陆游诗对偶工切的特色,应与入门之初习得的写作方法有关。二者,思想重渊源、求脉络。陆游自述:“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然譬于农夫之辨粟麦,盖亦专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机杼如是、边幅如是,自《六经》《左氏》《离骚》以来,历历分明,皆可指数。”*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三《上执政书》,第70页。这似乎又与陆游儿时耳濡目染与父辈往还的南渡故老的馀论有点关系。《书叹》诗曰:“大驾初渡江,中原皆荒芜。吾犹及故老,清夜陪坐隅。论文有脉络,千古著不诬。”(《剑南诗稿》卷七)三者,对于唐诗(含“晚唐”)持开放态度。一方面,王安石、吕本中论文于此有一定契合*作为江西诗派领袖,吕本中倡“活法”与“悟入”理论,引谢脁名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为证,又主张学习李白、苏轼,其中包含取法唐人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有时代因素方面的关系*陆游的上一代、南渡之初诗人群体表现较多对唐诗的向往,参见[日]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第196—198页,郑清茂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
落实到唐诗史认识方面,前期陆游的唐诗史观,大体融会了王安石“荆公新学”、更新的(非“原教旨”)江西诗派(吕本中、曾几)诸方面因素而成。以陆游对王维的态度作为一个例证,能够看得稍清楚。《跋王右丞集》曰:“余年十七八时,读摩诘诗最熟。后遂置之者几六十年。”(《渭南文集》卷二九)作为唐诗史上的“开元文宗”,王维是唐诗最具有典范资格的诗人之一。十七八岁,正当陆游成为江西传人前一二年,读王维诗最熟;接着,就搁置近六十年。证明陆游早期的前半段比较热衷唐诗。他之爱读岑参*“予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六《跋岑嘉州诗集》,第158页。、欣赏许浑*“若论风月江山主,丁卯桥应胜午桥(按:指裴度)。”陆游:《剑南诗稿》卷八二《读许浑诗》,第1113页。,大约属于类似语境。在此条件之下,建构“盛唐”观念的迹象不明显。
陆游文学生涯的“中年”,是他自述中一再提出的概念。前揭《示子遹》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广大。”(《剑南诗稿》卷七八)《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曰:“我昔学诗未有得……四十从戎驻南郑……诗家三昧忽见前。”(《剑南诗稿》卷二五)陆游将“中年”与“从戎南郑”联系起来,指斥的是乾道八年,四十八岁的他从事于汉中宋金前线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事,本年冬,王炎召回,幕府解散。陆游从戎,前后总共不足一年。
近人朱东润论“陆游诗的转变”,指出应该结合《东楼集序》的自述,将陆游诗风转变的标志定在乾道六年(1170)十月到达夔州的时候。“这一年是陆游的早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分水岭。后此在淳熙十六年(1189)陆游六十五岁被劾罢官,退居山阴,这一年他的晚年时期开始了。晚年是中年的延长,因为生活不同了,在作品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3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展读《东楼集序》,乾道九年、陆游入蜀第四年在蜀中自述他本人“巴蜀之缘”的缔结:
余少读地志,至蜀汉巴僰,辄怅然有游历山川、揽观风俗之志。私窃自怪,以为异时或至其地,以偿素心,未可知也。岁庚寅,始泝峡,至巴中,闻《竹枝》之歌。后再岁,北游山南,凭高望鄠、万年诸山,思一醉曲江、渼陂之间,其势无由。往往悲歌流涕。又一岁,客成都、唐安,又东至于汉、嘉。然后知昔者之感,盖非适然也。到汉、嘉四十日,以檄还成都。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则不敢,欲弃则不忍,乃叙藏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阴陆某务观序。(《渭南文集》卷一四)
可见以庚寅岁(乾道六年,1170)始“入蜀”之年为陆游文学生涯新阶段的开端,诚为不诬。下迄淳熙五年(1178)“出蜀”,首尾九年的“巴蜀之旅”客观上构成陆游诗风升华的关键因素。陆游《遣兴》曰“西州落魄九年余”(《剑南诗稿》卷一一),《舟过小孤有感》又曰“千篇诗费十年功”(《剑南诗稿》卷一○),诗人自我认识中,也将巴蜀生涯独立看待。出蜀东归之后,迄止淳熙十六年(1189)罢官乡居之前,诗风仍然大体相承。以故,乾道六年至淳熙十六年(1170—1189)这前后二十年构成陆游文学生涯的“中期”。
对于陆游“中期”诗风之嬗变,历来的解释重视自然、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近人则多曰“现实主义”)。以江山之助论文章,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认知习惯之一。陆游本人也有这方面观点的例证,如《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其二)》曰:“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剑南诗稿》卷五○)指山水游历能够激发出文章之妙。
笔者在此冒昧补充一个浅见:巴蜀风情、梁州戎阵固然似乎催生了陆游新诗风,然而,按之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求学进益的定律,对于文学阅读方面的因素也应给予重视。陆游高才积学,四十六岁入蜀之前,按理,文学名家必然早已广泛涉猎。然而,按之书籍常读常新的机制,再取陆游本人六十年不读王维的例证,可知某个时期、以什么方式阅读哪些作家作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作为观察点,陆游入蜀途中、在蜀期间对于李白、杜甫、岑参的“体验式阅读”“凭吊式理解”,对于陆游中期新诗风建立的意义,就不容人不认真思考、玩味了。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指出,一般宋人对李白尊而不亲,学李白学得成功的例子不太多,陆游是其中学得最像的。曰:
放翁颇欲以“学力”为太白飞仙语,每对酒当歌,豪放飘逸,若《池上醉歌》、《对酒叹》、《饮酒》、《日出入行》等篇,虽微失之易尽……而有宋一代中,要为学太白最似者。*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第12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钱先生列举的四首七古作品,其中三首均为蜀中之作(《剑南诗稿》卷四《池上醉歌》、卷五《对酒歌》《饮酒》),《日出入行》(卷十三)为东归后不久的作品。似乎可见陆游在蜀受李白影响之一斑。受钱先生观点的启发,笔者注意到《入蜀记》中引述李白诗句数量之众,以及一路上陆游边泊舟、边凭吊的独特阅读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入蜀记》自乾道六年(1170)六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一日,近四个月的日记中,引述李白诗句、事迹等共计32处,这委实是个突出现象。李白是蜀人,终于江东;而陆游的行程却是自江东出发,前往巴蜀;一路上阅读李白诗句、凭吊李白遗迹,看起来多么像“李白诗风溯源之旅”。这一种阅读方式所得的体会与理解,必然与众不同。入蜀之后,陆游先后在夔州、成都、东川等地任职,游历杜甫故地,又可以用同样方式阅读杜诗;他至南郑从军、至嘉州任职,又可以同样阅读岑参诗。总之,陆游首尾历时九年的“巴蜀之旅”,是一个“与李白、杜甫、岑参结伴而行”的特殊人生、文学旅程。以现场体验式阅读的新读法为线索,诗人边读边走、边走边读、边读边写。陆游“中期”诗风之转变,看起来具有这样一种特殊语境。
在经历过“韩愈普及化”的宋代言论环境之中,“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全唐诗》卷三四○《调张籍》),“李杜”已成文学“神主”,置论空间一般有限。下面重点讨论陆游在蜀对岑参的评论与尊崇。乾道九年(1173)夏,陆游摄知嘉州事,岑参曾任嘉州刺史并卒于蜀。为了纪念这位前任先贤,陆游于郡斋壁上绘岑参像,又刻其遗诗《岑嘉州诗集》。《跋岑嘉州诗集》曰:
予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往在山中,毎醉,归倚胡床睡,辄令儿曹诵之;至酒醒,或睡熟,乃已。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今年自唐安别驾来摄犍为,既画公像斋壁,又杂取世所传公遗诗八十余篇,刻之以传知诗律者。不独备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乾道癸巳八月三日山阴陆某务观题(《渭南文集》卷二六)
陆游又有《夜读岑嘉州诗集》曰:
汉嘉山水邦,岑公昔所寓。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
常想从军时,气无玉关路。(原注:公诗多从戎西边时所作。)至今蠧简传,多昔横槊赋。
零落财百篇,崔嵬多杰句。工夫刮造化,音节配韶頀。
我后四百年,清梦奉巾屦。晩途有奇事,随牒得补处。
群敌自鱼肉,明主方北顾。诵公天山篇,流涕思一遇。(《剑南诗稿》卷四)
一则曰“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再则曰“笔力追李杜”,在陆游心目中,“李白、杜甫、岑参”已经结合为一个“笔力”雄壮、风格“豪伟”的文学典范共同体。陆游读诗的识力令人佩服,唐代中期的文学史上,“天宝左翼思潮”之中确实活跃着一个偏嗜复古、擅长七古歌行、当时属于“后起之秀”的诗人群体。笔者曾经指出:“高适、岑参、杜甫、李白等人,在‘飞动’等题目之下,其实是未尝不可以视为一个文体、诗风的共同体的,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追求壮丽、壮美风格的时代风尚,与后人概括的‘盛唐气象’尤有契合之处。”*吴光兴:《八世纪诗风——探索唐诗史上“沈宋的世纪”(705—805)》,第17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陆游学岑参的作品,亦颇有其例。*参见胡明:《陆游的诗与诗评》,载《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4期。
总之,与中年“宏肆”*赵翼《瓯北诗话》(卷六)评陆游诗风“三变”为少工藻缋、中务宏肆、晚造平淡。亦参见齐治平:《陆游传论》,第91—97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豪迈诗风一致,陆游“中期”的文学思想、唐诗历史认识,亦进入新境界。新地域、新生活、新气概、新想象、新诗风、新文论。陆游以“李白杜甫岑参”为典范而建构的与唐诗“选择性契合”,符合唐宋以降复古思潮的大趋向,堪称唐诗学术史的一个创新,也是“盛唐”观念建构的重要基础。
与高举“李杜岑”比较,陆游猛批“晚唐”的动作在文学史上更为旗帜鲜明、令人瞩目。口诛笔伐“晚唐”的同时,陆游从“晚唐”的获益又似乎并不少于其他诗人,这一矛盾现象也成为评论家感兴趣的话题。下面试综合唐诗接受、宋诗建构的视角提出几点解释:
一者,略如本文第一节叙述所及,从宏观历史因革的角度看,“晚唐”本是宋诗矢志超越的对象,“挑战—应战”的关系架构之中,宋人对“晚唐”持批评态度是比较自然的。大家都记得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序》中有关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生怕听到父亲打胜仗的消息的绝妙比方。“晚唐”、宋诗,正类似皇帝、太子间天然矛盾的关系。而陆游笔下的“晚唐”概念的动态范围亦值得注意,他尽管常常指“大中以后”为“晚唐”,但是,有时也将“元白”(元稹、白居易)以及贾岛姚合的诗风算作“晚唐”*参见莫砺锋:《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这个“动态游移”的“晚唐”之存在,其根源亦在于所谓“晚唐”是从宋代往前逆推的,以宋人熟悉的韩愈话语设定的“李杜”为“极限”。宋人曰“晚唐”,指与宋代接界的唐诗史的“末一段”而已,多数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唐诗史分期的观念在胸中。
二者,以《剑南诗稿》首冠《别曾学士》为例,陆游对曾几、江西诗派的感情明白无误。宋代文化讲道统、文统、正统,宋人重视派性,陆游之斥晚唐,应有继承诗派传统这方面的原因。*参见齐治平:《陆游传论》,第88页。发声批评“晚唐”,实际上并不表示与晚唐“隔绝”,所以,陆游批晚唐与学晚唐,也不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为陆游所继承的吕本中、曾几以下的江西革新派诗人,其寻求革新的有些思路,正取法于晚唐诗、唐诗。
三者,在南宋前期诗坛,江西、晚唐两派诗风激烈竞争已趋白热化之际,陆游没有像杨万里那样正面肯定晚唐诗的价值,这一现象倒是启发了我们的思路。证明即使面对江西末流弊端显现,陆游也无法服膺晚唐诗的典范。观念典范的碰撞,正好激发了诗人思想观念的创新,豪迈闳肆的“李杜岑”模式,以及“诗家三昧”“诗外功夫”等观念才应运而生。
四者,陆游所论晚唐,如果与他论王维、《中兴间气集》等联系起来观察,尤可以见出与“唐律”语境逐渐剥离、隔绝的宋人新唐诗史观的建构轨迹。以宋人当中流行的贾岛、姚合“晚唐”诗风为例,姚合编《极玄集》在唐宋两代都很有影响,入选诗人被姚合赞许为“诗家射雕手”,其中位居开山第一位的是“开元文宗”王维。《极玄集》其他20位入选诗人,除祖咏外,皆为大历诗人;19人当中,有钱起、郎士元、韩翃、皇甫曾、李嘉祐、皇甫冉、刘长卿、灵一、戴叔伦9人曾经入选大历末年的《中兴间气集》;《极玄集》中的剩余诗人多数是大历后进,《中兴间气集》编选时,尚没有机会入选。王维、《中兴间气集》、“晚唐”三者之间,在唐诗本身的语境之中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唐诗、宋人也常称“唐律”,是以律诗为主流、典范的。而陆游的诗论,对三者抱有程度不同的排拒心理。嘉泰元年(1201),陆游《跋王右丞集》曰:
余年十七八时,读摩诘诗最熟。后遂置之者几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昼无事,再取读之。如见旧师友,恨间阔之久也。(《渭南文集》卷二九)
陆游十七八岁之后几乎六十年不读唐诗典范王维的诗。而六十岁时(淳熙十一年,1184)《跋〈中兴间气集〉》对该集的恶评,也可以反映部分心态:
评品多妄,葢浅丈夫耳。其书乃传至今。天下事出于幸不幸固多如此。可以一叹……议论凡鄙……唐人深于诗者多,而此等议论乃传至今,事固有幸不幸也。然所载多佳句,亦不可以所托非其人而废之。(《渭南文集》卷二七)
稍微认可了所载“佳句”,然而“评品多妄”“议论凡鄙”的结论稍显严厉*传世的唐元和间诗选《御览诗》经陆游手跋,该集主要选录大历、贞元诗人,陆游《跋》仅作了文献史料的揭示,未评论诗歌价值方面。。再结合陆游对“晚唐”的一贯贬斥,足证明陆游胸有定见,对唐代律诗主导的文学价值不能够充分赞同。
五者,宋人有关唐诗的论述受唐殷璠、司空图影响,论者多有留意。比较而言,首要的仍是“韩愈化”言语环境的基础作用。韩愈代表的复古思潮在唐代文学史上处于边缘、非主流的地位;同时,也是勇敢发言、积极挑战、志在颠覆的革新力量。经由这一套话语的教育、熏陶,宋人心目中的唐代文学史逐步呈现为具有一定颠覆性的状态,以复古为基调*陆游有个“近古”的观念,参陆游:《入蜀记》第四,见《渭南文集》,第287页。的“新版唐诗史”逐渐建构,陆游在这一历史潮流之中是个“弄潮儿”。
陆游人生与文学生涯的“晚期”,自淳熙十六年罢官至嘉定三年去世(1189—1210),二十年的光阴,主要是在家乡山阴度过的。陆游晚年诗风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思想观念方面与中期大体一贯,变化不大。他的论诗名篇,许多出自晚年定论。
综本节上述,陆游对唐诗史的新认识,突出体现在他“巴蜀之旅”时期对“李白杜甫岑参”典范的塑造,这也为他猛烈批评“晚唐”诗的做法建立了一个理论支点。这样一种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历史认识,对于宋末“盛唐”观念的建构起到了奠基作用。
三、陆游文学思想中的“盛唐”元素
宋末严羽(1192—卒年不详)是文学史上“盛唐”名称的制造者、“盛唐”理论的最早宣布者。但是,理论家的理论,与历史上的传统观念之间的关系,要有所辨别。理论以文本为据,而观念更多属于深藏在历史表象、理论文本之下的“散乱”资源。以“盛唐”的理论文本来说,严羽至明代复古群体“独领风骚”;然而,追踪“盛唐”概念所标示的文学典范之流行,其建构、传播、阐释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本文从文学观念史研究角度进入,探讨陆游思想中的“盛唐”元素,因此,以“盛唐”观念为主题,并不完全按照相关元素在《沧浪诗话》中的轻重位置来安排。
陆游思想观念之中的“盛唐”元素,参考他处身其中的文学环境及其创作,若非为“江西诗风”补偏,即是救“晚唐诗风”之弊。细绎之,约有如下数端。
第一,“士气”“养气”与“盛唐气象”。
这方面的核心概念为“气”。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韩愈曰“气盛言宜”(《答要翊书》)。孟子、韩愈的“复兴”与经典化,一定程度上是点燃宋人“气”的观念的火种。“气”的观念,代表新型士人社会士大夫的主人翁意识,弥漫、流行在宋代文人胸怀言语之间,几乎成为一种信仰的符号。宋人语境的“气”,连缀成词如“正气”“气节”,超越了传统一般的“气质”,由士大夫的主体性,上升至兼容个人、士类、国家、天地等为一体的一种至大、至刚的超越的精神、意志。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陆游曰:“周流惟一气,天地与人同。”*陆游:《剑南诗稿》卷八四《宴坐二首》(其二),第1147页。“气”本是贯天、地、人的。与国家治乱也有关系,“文章有废兴,盖与治乱符。庆历嘉祐间,和气扇大炉”*陆游:《剑南诗稿》卷七《书叹》,第119页。。陆游的眼光更多地落在人“气”方面(即“士气”),又常与“文章”专业联系在一起,如:“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陆游:《剑南诗稿》卷二一《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第362页。又如:“尔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陆游:《剑南诗稿》卷一三《谢张时可通判赠诗编》,第225页。前揭“谁能养气塞天地”句中的“养气”二字整合《孟子》成词,是陆游自吕本中、曾几继承下来的重要主题*参见于北山:《陆游年谱》,附录三。,其《傅给事外制集序》曰:“某闻文以气为主,出处无媿,气乃不挠。”(《渭南文集》卷一五)又《曾裘父诗集序》曰:“(曾裘父诗)所养愈深,而诗亦加工。”(《渭南文集》卷一五)由此,立身行事,以培养士气,树立人格,文学才能达到崇高境界。陆游《上殿箚子》对苏轼的评论将“文气”说的义蕴发挥得淋漓尽致:
臣伏读御制《苏轼赞》,有曰:“手抉云汉,斡造化机。气高天下,乃克为之。”呜呼,陛下之言,典谟也。轼死且九十年,学士大夫徒知尊诵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于“气高天下”者,今陛下独表而出之。岂惟轼死且不朽,所以遗学者顾不厚哉!然臣窃谓天下万事,皆当以气为主,轼特用之于文尔……盖气胜事则事举,气胜敌则敌服;勇者之斗,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气胜之耳。(《渭南文集》卷四)
苏轼取得文学的最高成就,奥秘在哪里?照陆游的理解,如宋孝宗《苏轼赞》所言,苏轼“气高天下”而已。
严羽《诗辨》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律,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沧浪诗话》)将“气象”列为诗法之一。移“气象”以论诗,注重诗歌意象与诗人精神面貌之间的联系。鉴于陆游在南宋后期诗坛的巨大影响力,由他推广其波澜的新时代的“文以气为主”之说的流行,可以视为“盛唐气象”品题出世的观念意识方面的基础之一。
第二,“雄浑悲壮”索源。
严羽论盛唐诗有“雄浑悲壮”之目,其《答吴景仙书》曰:“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沧浪诗话》附录)“浑厚”“雄壮”二目,亦可合并为一“雄浑”,于陆游极有渊源。
陆游《周益公文集序》原原本本将“文人之才”分为二类:一是为国家作册命公文的御用文人;一是著文论、吟诗赋的“自由文人”。而“自由文人”的“雄浑”之才竟然可以溯源于形而上的天,曰: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异。将使之发册作命,陈谟奉议……若夫将使之阐道德之原,发天地之秘,放而及于鸟兽虫鱼草木之情,则畀之才亦必雄浑卓荦,穷幽极微。又畀以远游穷处,排摈斥疎,使之磨礲龃龉,濒于寒饿,以大发其藏。故其所赋之才与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于其间者,虽不用于时而自足以传后世。此二者造物岂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渭南文集》卷一五)
如此,“雄浑”乃天赋文人的素质,“理之自然,古今一揆”。无怪乎陆游论诗,以“雄浑”为崇高品目矣。《白鹤馆夜坐》曰:“袖手哦新诗,清寒媿雄浑。屈宋死千载,谁能起九原。中间李与杜,独招湘水魂。自此竞摹写,几人望其藩。兰苕看翡翠,烟雨啼青猿。岂知云海中,九万击鹏鹍。”(《剑南诗稿》卷八)屈原、宋玉、李白、杜甫等“雄浑”风格的古代典范,呈现的是“九万击鹏鹍”的气势。陆游推崇宋代诗人梅尧臣,其《读宛陵先生诗》曰:“欧尹追还六籍醇,先生诗律擅雄浑。”(《剑南诗稿》卷一八)诗人感叹自期,其《江村》曰“诗慕雄浑苦未成”(《剑南诗稿》卷六三)。
以“雄浑”为风格极致,其他如“弘大”(《剑南诗稿》卷七八《示子遹》)、“豪伟”(《剑南诗稿》卷四《夜读岑嘉州诗集》)、“磊落高格”(《剑南诗稿》卷一五《记梦》)等,皆派生而出的特征。熟悉了陆游“雄浑”品目的系列论述,回顾《沧浪诗话》有关“盛唐”“雄浑”的论断,似乎只是从陆游相关思想原则敷衍、推广开来的。当然,陆游思想也有前辈渊源、当代语境方面的关系。
第三,以“李杜”为“晚唐”药石,自“元和”拾阶而上。
陆游的唐诗史叙述,上文专节论述重点关注到“李白杜甫岑参”典范与“晚唐”问题。
推崇“李杜”原本是宋人当中流行的常言,唐诗人物“座次”方面,陆游的创新点在于“巴蜀之旅”时期将岑参排进李杜的阵容。由“李杜”而“李杜诸公”而“盛唐诸公”(《沧浪诗话》),逻辑上看,形成一个序列;由“李杜”而“盛唐”,由两位齐名的典范诗人进而展开为文学史的一个时段,更堪称历史认识的飞跃。
陆游的推崇李杜与批评晚唐,常常联系在一起。如《记梦》曰:“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蒿。晩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剑南诗稿》卷一五)而抨击晚唐诗,进而对元和诗不满意,似乎也顺理成章。历史上的晚唐诗风,诚然就是由“元和诗变”引导而出的。《偶观旧诗书叹》曰:“可怜憨书生,尚学居易稹。我昔亦未免,吟哦琢肝肾……幸能悟差早,念念常自悯。”(《剑南诗稿》卷七一)陆游庆幸自己迷途知返,不再学元稹、白居易了。《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则以“元白”与“晚唐”为等而下之:“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剑南诗稿》卷七九)《示子遹》晚年定论,“元白”“温李”(温庭筠、李商隐)都不在话下:“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剑南诗稿》卷七八)这些都是以陆游心目中“李杜”典范为标准作出的历史评价。
批评江西诗风,又不满意晚唐诗风者,理论上可以通过阐发“李杜”典范来找出路。这或许就是陆游诗论对“盛唐”观念建构的启示。
上承江西诗派衣钵、下开江湖诗派风气,作为南宋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枢纽”人物,陆游创作生涯的“中年之变”,是他自己及历代后来人都认可的重要契机,不仅助力他的写作生涯翻开新的一页,而且,文学思想观念也几乎壁垒一新,激发出包括“诗家三昧”“诗外功夫”等光芒四射的重要论题。他对唐诗史的相关论述,他传承并进一步丰富的宋人传统的“文气”说、“雄浑”品目等,以及他对晚唐诗的批评,则为宋末唐诗史“盛唐”观念的建构积累了极其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王建平;实习编辑:杨孟葳】
【收稿日期】2010-09-1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6)01-0021-08
(作者简介:吴光兴,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