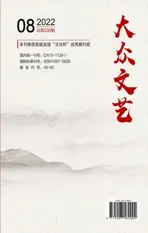一个从未走出密室的酷儿
——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的一种解读
2016-03-11钱少武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521000
钱少武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521000)
一个从未走出密室的酷儿
——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的一种解读
钱少武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521000)
《雨天的棉花糖》中同性恋者红豆生在异性恋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这种文化霸权一方面不断强化红豆与生俱来的性取向,一方面却又挤压以至剥夺红豆所能拥有的生存空间。
密室;酷儿;红豆;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
毕飞宇199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抒写了一曲有同性恋倾向的男性的悲歌。这曲悲歌产生于异性恋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语境中。小说人物红豆孤寂痛苦、茫然无助灵魂影射的,无疑是文本的一种非常明显的主题。
一
在小说的叙事语境中,红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酷儿。叙事人几乎以肯定的叙述,从气质、欲望、情趣、言行甚至生理等多方面交代了生理性别为男性的红豆的女性性倾向虽有后天影响的成分,但本质上却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红豆天然的性倾向并不必然对他的命运造成不利的影响,只是他偏偏生在一个男、女界线分明,同性恋既不为人所熟知同时又绝对不为人所接受的时代,这就使他具有了命定的悲剧性。出于繁衍需要而成为规定性的异性恋文化霸权一方面不断强化红豆与生俱来的性取向,一方面却又挤压以至剥夺红豆所能拥有的生存空间。
虽然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性别都是某种模仿和近似”1,不同生理性别之间并不存在质的不同,但是由于异性恋文化强调人的生理性别的差异,并赋予不同性别以不同的社会意义,所以现实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超然于异性恋文化潜在而巨大的影响之外。异性恋文化语境中性别差异暗示对红豆的影响可说是无处不在。它们强化了处于专制地位的异性恋文化关于女性特征的不容受到任何挑战的规定性叙述:女性是柔弱美好,温婉含蓄的,需要得到两性世界中占支柱地位的男性的宠爱和保护。红豆想做女性的欲望使他在扮演女性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开始由对女性身份的向往和模仿逐步走向适应和自我认同,这些无疑在客观上助长甚至完成了他通过遗传得来的酷儿性倾向。
异性恋文化张扬男性的阳刚气质,而军人身份不光是这种气质的合法的拥有者,他们所经历的战争更是为这种气质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场地。小说中红豆的父亲钟情于战争。战争使他成为英雄的同时,也助长了他的适合异性恋需要的男性身份和男性意识:酗酒,暴躁,好发脾气。“父亲”角色对红豆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压迫性存在。红豆在父亲那里得到的不是尊重和保护,而是蔑视和屈辱。对男性特征鲜明的父亲的异常反感,无疑潜在强化了红豆对自身女性气质、欲望的认同。这不仅导致了红豆与他父亲截然不同的战争感受,甚至也是他悲剧性地拥有战俘身份的深层原因。
二
不可否认,让红豆同性恋欲望现实对象化的,正是他所生存的异性恋文化世界,因为在“禁止在男人的脸上挂上‘女人的泪水’”,要求男性“对世界采取一种更富进攻性、情感上更为纯一的姿态”的强制性的异性恋文化世界中,“这种使得男人难以抵御女性化情感的感情上的需要和依赖”,让同性恋者红豆很自然地“转入到了同性社交和单一男性关系的领域。”2作者在文本中反复渲染红豆拥有的女性化的性倾向的先天性,凸显他成长过程特别是背负“战俘”身份后渴望在两性关系中得到理解、保护的情感需求,显然是想强调,红豆将“我”视为现实中情感依赖和性幻想的唯一对象,其实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作者并未单纯地建构红豆和“我”双向的同性之爱,而是把它与“我”的异性恋爱和婚姻的进程交织在一起,凸显异性恋文化强大压迫性的同时也凸显了同性恋的隐秘性和复杂性。小说文本所展示的异性恋文化世界中上演的同性之爱是默默存在,从未公开的,明显属于暗恋性质。爱恋的两个主体都极力遵循现实中的异性恋文化规则。红豆虽具有天然的同性性取向,但他还是深知同性之爱是有违异性恋社会规则的,是非常态的,所以他在和“我”交往时,显然都在控制自己的言行,力求使它们不逾越男人间交际应有的规则。和红豆相比,“我”在隐藏自己的性取向这方面做得更成功。“我”在言语上从未流露出对红豆的如同异性般的爱。
虽然如此,文本世界中红豆和“我”的同性之爱还是无形中对异性恋爱和婚姻形成了冲击。如筹办婚事期间不情愿地成为同性恋者恋情尴尬见证者的弦清既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又要保全彼此的名声,她透过目光传达出的和“我”之间的“纵深距离”,让“我”感到“害怕”。作者让异性恋文化价值取向以温情而合理的方式张扬其威权的力量,显然是为了凸显红豆和“我”的同性之恋的生存之难。
但这并不是“我”终结和红豆恋情的唯一原因。“我”对红豆的同情、喜欢自始至终都有“我”的保护性心理因素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一因素,“我”绝不会抛弃弦清而和红豆在一起,因为弦清更需要保护。基于异性恋规则而生发出的男性的保护行为其实也无形中增强了“我”对异性恋规则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红豆之间若即若离的同性恋倾向,实质上也是异性恋的一种变化形式。
三
小说中,曹美琴的出场和退场无疑都是为了展示红豆这个同性恋者的心理世界服务的。如果说“我”和弦清的婚礼击碎了红豆的同性恋梦想,那么他主动走进高中同学曹美琴的生活,与其说是遵循异性恋规则的积极的尝试,不如说是红豆对自己同性恋倾向的努力矫正。尽管叙事文本明显暗示了红豆从曹美琴那里渴望得到的并不是“性爱”本身,而是和曾经喜欢的异性一起做事,进而寻求他从母亲那里不可能得到的母亲般的理解、关爱与呵护。如果曹美琴能够做到这点,再配以成功的性爱,就有可能治愈红豆的同性恋倾向,帮助他成为一个男人,或者至少可以唤醒他作为男性的某些意识。不过,作者并不想讲述一个违背他对同性恋认知的故事。他笔下的曹美琴本身就是一个男性化的女性。和红豆在一起的所有细节,都暗示她总是具有传统异性恋文化所认知的男性对女性才有的引诱、放纵和强烈的支配欲望。对于红豆,曹美琴看重的恰恰是性爱,她主动、贪婪的索取式方式,反倒让红豆的胃“在这样飘香的日子里”发了病,而且只要一想到性事,他的胃就疼得厉害。红豆反感和讨厌的也许并不是性爱本身,而是曹美琴悖离异性恋文化所规定的女性角色的行为方式。从这一点来看,红豆可以说既是异性恋文化的受害者,同时又是这种文化价值取向的实质维护者。
《雨天的棉花糖》用了大量篇幅叙写红豆的自杀。如果说文本世界中红豆背负的与他同性恋倾向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战俘”身份令他痛感压抑和焦虑,那么曹美琴的反目和“我”的渐行渐远显然使他陷入了几近走投无路的极度孤独、绝望的境地。小说对顽固坚持“杀了”红豆“我就是我了”宏伟梦想的红豆自杀行为的的舒缓叙述,体现出红豆对自身难以消失的同性恋倾向的长久的困惑和憎恨,以及他一步步走向自杀选择的被迫和无奈。故事结尾处作者借助红豆死前念念不忘他在战俘营所用的数字编号和死去时手指指着二胡这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象征性地揭示了红豆自身携带的同性恋倾向就是他难以挣脱的人生牢笼,而红豆心灵的全部诉求则始终停留于密室之中。
注释:
1.[美]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340.
2.[美]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