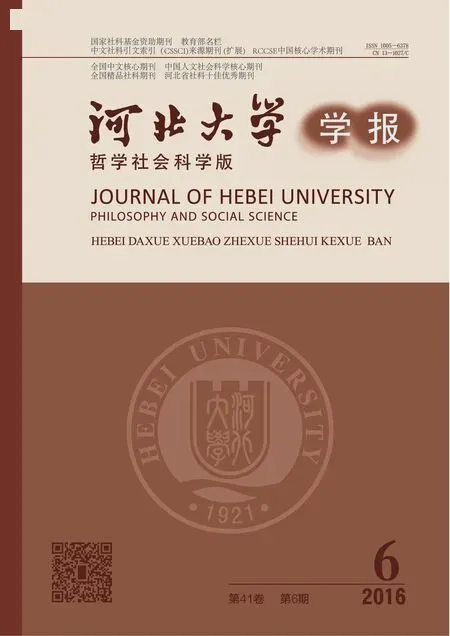匡山书院与“南宫义举”的由来与价值
2016-03-08许怀林
许怀林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西 南昌 330022)
宋史研究◎教育部名栏◎
匡山书院与“南宫义举”的由来与价值
许怀林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西 南昌 330022)
泰和县地处吉泰盆地核心区,自古以来是粮食农业发达之区,为发展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朝廷科举与民办书院相互为用,促进文化教育逐步发展。南唐时期罗韬在家乡创办匡山书院,开风气之先。南宋中期泰和县人士率先实施“南宫义举”,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是社会文教事业的大进步。泰和“南宫义举”的首创地位,依史有据,无可怀疑。“义举(约)”形式的赞助发展为设立“贡士庄”,为扶贫而起的襄助进而对全体赴考者的资助,改自费赴考为官费赴考,是文教制度上的完善,对发展书院教育与维持科举事业有积极效益。
农业经济;匡山书院;南宫义举;贡士庄
古代的国家管理,是统治阶级的职责,获得官位、掌握统治技能是极少数人的特权。我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被科举制取代,是政治特权从金字塔尖向下移动的继续,在向社会开放进入仕途的大门,士族权贵垄断文化知识、把持官僚队伍的旧秩序在破除,让平民家族(历史用语是“庶族”)有了熟习儒学知识,力争为官,挤进社会上层的一线希望。
书院,是庶族为子弟求学而设置的园地,它铺就一条通往科场的道路。有财力设置专供子弟读书园地的庶族,到了唐朝时期还不多;能够胜任教学,认识古文字的音义、能看懂经史典籍的人,同样很少。
科举义约,是家族或社区以群体力量,资助举子解决科考旅费拮据困难,使通往科场的小路平坦一些。在挑担走路、乘船航行或骑马坐轿的古代,进京赶考,旅途跋涉,要耗费漫长时日,而所需的巨额银钱,也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开支得了的。
那些率先开办书院的家族,毅然担起传播知识重担的儒士,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种子,殊为珍贵。本文以南唐时期创办的泰和县匡山书院、南宋时期出现的泰和“南宫义举”为个案,陈述他们宏传文化、赞助考试的榜样事迹,评议他们的垂范作用。因为时隔近千年,人事记录残缺,不免传说失误,对关于“科举义约”创始者的讹传,一并做出必要的考证。时下的热门议题之一是“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为求温故知新,必先真切把握传统事实,撰写此文即出于此意,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一、兴旺的农耕生产与匡山书院的创办
泰和位于赣江中游的吉泰盆地核心区域,土地宽平,水流充足,稻耕农业发达,早已是粮食充足之地。南北朝时期,陈霸先攻夺梁朝政权,自始兴(今广东韶关)出发,进入江西境内,在泰和、庐陵一带迅速筹集到50万担食粮,军队无缺粮之忧,威势大振,遂能打败敌兵,攻下建康,建立陈朝[1]。到了宋代,吉泰盆地已是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产量尤为丰足,江南每年“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至于民间商贩出境的粮食就更多,“不知其几千万亿计”*曾安止《禾谱序》,见泰和县石山乡匡原村光绪三十四年刊《匡原曾氏重修族谱》。泰和县农民栽培的水稻品种多达50个,我国最早的关于水稻品种和稻田耕作技艺的专著《禾谱》,就是泰和人曾安止撰著的。农田垦辟充分,平衍沃野耕种完了,进而开垦山丘,“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尝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曾安止《禾谱·序》)。元丰五年(1082年)黄庭坚出任泰和知县,下乡看到的山村实情是“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上大蒙笼》)。
百姓相对温饱了,必然进而重教,把发家致富的追求,定格在耕读结合的途径上,兴办私家书院,致力培育子弟,朝科举出仕的目标奔跑。在这方面,泰和人罗韬于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创办匡山书院,为社会作出了榜样。罗韬,字洞晦,家有田产,自己又有为官的知识和经验,他的匡山书院可供读书和住宿,有学田供书院开支费用,在泰和本地是私家书院之开先者,在江西乃至全国也是领先之一,有很大的风标意义。
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处于政局分裂之中,罗韬不愧是眼光远大的学者。他虽以文学被南唐聘为端明殿学士,不久即急流勇退,请病归乡,在家建书院聚徒讲学,把人生追求转移到培育后辈上面。对其行动,后唐明宗下敕书赐匾,予以表扬:
朕惟三代盛世教化每由学校,《六经》散后斯文尤托于士儒。故凡闾巷之书声,实振国家之治体。前端明殿学士罗韬积学渊源,莅官清谨。纳诲防几之鉴,允协朕心;赏廉革蠹之箴,顾存扆席。寻因养病,遂尔还乡。后学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善,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可无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风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题,俾从游之士乐有瞻依,而风教之裨未必无小补焉!
在官学教育废坏,社会教育非常衰微的背景中,罗韬自觉肩负“士儒”的使命,创办书院教学,传播“斯文”,培养后人,确有振聋发聩,表率民风的社会效益。
明朝人曾皋评论罗韬创办匡山书院之举,极言其收徒育人传播文化的作用:
匡山之有书院也,肇自后唐长兴间。是时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亦无讲于学者,洞晦罗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圣人之学为己任。朋来自远,书院筑焉。圣殿经阁,埓今学宫。明宗嘉而赐额,于鑠哉!五季稀有事也。历宋而元,四百年无恙……先生生而笃修潜养,淡于声利,惠政在郡,清节在朝。辟地匡山,延收四方,启愚发覆,吐词为经。[2]
社会上还没有兴学之议、讲学之人的环境中,罗韬独能筑书院,收徒教学,自然是“启愚发覆”,使愚昧者觉醒,知识不被埋没。曾皋指出的罗韬毕生作为,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南宋时乡人发起对科举考试的资助,正是效法他“惠政在郡”的具体表现。
当“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亦无讲于学”的五代时期,罗韬就率先垂范。在宋朝有了兴学政策,士大夫开始了讲学活动的时候,泰和民众办书院的积极性更高,全县共计8所书院中,县城的龙洲书院属官办,其余7所均为私家办。它们是匡山书院、文溪书院、柳溪书院、云津书院、林山书院、南熏书院、石冈书院。民间涌动着以农耕支持读书,求官位保护家族的热潮,有学力参与科举考试的士人必然众多,由此催生出科举义约,首创于泰和,是历史的必然。
二、朝廷科举与民间书院的相互促进
罗韬退出官场办书院,自然不是空洞地为书院而办书院,进入匡山书院读书的人也不是只为读书而来,应该都是在科举出仕的巨大吸引力推动下而来的。朝廷的选官制度改为从地方读书人中考选,候选人群的范围必然比前代由世家大族推荐时扩大,中选者的优秀程度相应提高。因此,读书士人为求得官,拥进科举考场。所以,唐太宗看到新科学子从考场鱼贯而出,非常得意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3]“学而优则仕”早已是读书人的理想目标,社会公认的价值取向。实施了二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逐渐强化了百姓对朝廷的向心力。从民间来看,追求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只有读书应考,力争出仕,藉官位获取权势,才能保守财富,提高家族地位。于是,江州“义门”陈氏在唐末创办了“东佳书堂”,内分蒙学与进修备考者两个层次,不仅自家子弟在此读经史,习诗文,“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间”[4]。这些非陈氏的人来“东佳书堂”肄业,不是迷恋“子曰”“诗云”,而是要备考出仕。他们达到了目的,故成为“名士”。匡山书院“延收四方,启愚发覆”,也是要培养有为政施治能力的官僚后备队伍。
民间办书院,投资教育,企求的是科举回报。科举考试制度,让朝廷能够在更大的知识群体中选拔官僚,有明显的统治效益。于是,科举取士为朝野所认同,得以持久地坚持下来。很明显,书院的生命力来源于对科考入仕的追求,并非它的教学制度与传习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环境需求的产物。到了清末,时代变了,社会改弦更张,一纸命令,书院就结束,成了历史文化的认识对象。朝廷科举与民间书院相互为用,推动社会教育逐渐发展,促使文化向社会下层扩展,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文明的大进步,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科举,有逐级考试选拔的程序,先要经过县级考试推荐,参加地方大行政区的考试筛选,中选者称“举人”。举人再集中到京城会考,合格者最后还要朝考(殿试),中选者称“进士”,才能任命为官。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考试关,是极大的幸运和胜利。但是,要支付参与考试所需的路途费用,却非易事。古代交通原始,动辄几十天,家境若非足够富裕,定然有捉衿见肘的困难,得到举荐资格却因盘缠紧张而难于赴考。为了这个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人生际遇,当事人必然竭尽心力借贷营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地方官员为着政绩考虑,也希望本地多有人中举。于是,发动社会力量捐助资金,解除贫寒举子赴考之困的“义举”。
为什么要迟到南宋才出现,而不是跟随科举制度同时面世?这里面有不同的利害关系。设计考选官吏的制度,是朝廷的需求;有无能力参与考试,是民间个人的条件。科举制起始阶段,上接魏晋九品中正制,那是掌握在士族门阀手中的荐举办法,有资格被荐举者无不是世代公卿权贵,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根本不存在贫穷一说。这个金字塔上层人群,世代享受文化教育特权,科举考试初期的参加者主要是这些人,故而隋唐科考中还有旧士族残余。唐朝晚年以来的频繁战乱,使士族门阀阶层急剧衰退下去。进入宋代,平民地主——庶族阶层迅速发展起来,家境富裕了,有能力参加考试的人比以前增多。加上宋朝进一步修订科举制度,录取名额不再是一二十人,而是几百人。这就更加吸引普通富裕人群追求科举,尽可能把子弟挤上仕途。获得进京赴考的众多学子中,难免有比较贫寒的成员。为旅费而卖田负债,甚至无力上路、痛失赴考机会的事也有发生。一方面是科举日益受到社会看重,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则是赴考费用导致的困难,问题积累到南宋中期,乡绅们终于酝酿出了合力资助的良策。
三、自愿集资助考的“南宫义举”及其首创地位
我们目前所知,南宋江南西路吉州泰和县倡行的“南宫义举”,内容清楚具体,实施的时间最早,确是这桩文化公益事业的创始者。
泰和县社会集资助考义举,开始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发动这次义举活动缘由和操作办法,知情人周有德写《南宫义举记》曰:
士风之厚薄,大抵以义为轻重。而西昌壮邑,素号多士,三岁大比,应诏者不下二千人。其相与友助,相与讲习之意,已乐见于平昔,及登籍天府,观上国之光,实众歆艳其荣之时,岂可于道里之费而使家自为备乎,此今日义举所由兴也。义举之约,以千人为率;每人日出一文,约三岁,得钱一千有奇。壬子科,绍兴士子大比,郡以十二日揭榜,吾邑题名者十人,皆以义举。月既建亥十有五日,序乡饮于学,邑宰赵公、丞姚公、尉梁公及乡老与焉。义举之领袖者咸在。集钱得四十四万八千有奇,析而送之。于斯时也,县官之劝驾既勤,乡里之饯举甚宠,士气大振,礼文可观,古者宾兴之意复见于今日矣。乡举里选三代所尚,县次续食两汉仅见。自科举法行,是意微矣。膺荐之士观光上国,道里远者以数千计,裹粮资费,贫则未免资人介则必至鬻产,因仍积年,无有宽其忧者,于是令道州司法严公万全、乡先生周公英彦合谋其男琰有德偕乡贡进士陈忱三人总其事,率乡里同志为义举,计日集钱,积之三岁,以侑其行,士得不困。戒行之先,乡老饮饯于学。是日,壬子良月望日也。请于邑侯赵公师奭,公欣然主盟,复行古礼,且曰歌鹿鸣之诗,序燕贤之仪,公家常制,未足为盛观,公等崇乡里之义,行乡饮之礼,举百年之旷典,新一时之美化,真盛事也,当捐公帑百千以助斯举。士益感公厚意,谓三代两汉遗风今日见之。越明年,谭一飞实中乙科,调章贡户掾,陈嗣宗次之,调衡州茶陵簿,皆由此其选。虽未应龙洲之谶,而来者为可知。况义举自吾邑始,今天下闻者类欲效之,夫岂无益。凡预是举者佥曰盍识之以诏后来云。(弘治志)*道光《泰和县志》卷三二《艺文·记》。宾兴,是周代的制度。《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郑玄注:兴,犹举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即地方荐举的贤能者,给予宾客待遇,官费送往朝廷。 续食,汉代郡国每年派遣上计吏进京报告财政收入,汉武帝命各地选送“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与上计吏偕行,“县次续食”,官府供应往返饮食。后世借用为举人赴会试者之称。
道光县志编撰者注明转录于弘治县志,然此志已经失传,无法判断这段转录文字的完整性。仅此而论,事件的原委交代很清楚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冉棠《重修泰和县志》摘要记述周有德之记文,并补写了绍熙三年之后简况,可以和上段资料相参认识。但原书无存,只在同治县志中有转载:
按弘治志,西昌南宫义举始自宋绍兴壬子。约曰:西昌壮邑……厥后庆元、嘉泰以次举行。而倡是举者,邑人严万全、周英彦、陈忱也,乡贡进士周有德书其事。乙卯科,曾有凭记。戊午科,知县卓洵复益以公帑之钱,严万全记。辛酉科,知县赵汝謩书其事于乡饮所。
其后不复继矣。……(冉志)*同治《泰和县志》卷七《宾兴》。
标题为“南宫义举”,义举,公正合宜的行动,有自觉的意愿。南宫,是古代权贵居留的所在,可以是皇宫、官署、皇室和王侯子弟的学宫等的代称。古人认为朝廷中央的尚书省象列宿之南宫,故称尚书省六部统称南宫。隋唐实行科举考试,进士考试多在礼部举行,故又专指礼部为南宫。在这里就是指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会试。所以,周有德这篇《南宫义举记》,写的是资助会试的举动,即是“科举义举”的记录。
为了准确把握此文内容,有必要先进行一些文字考辨:这篇记文在转载刊刻中造成一些文字差异,影响了对情节判断理解。最为紧要的是起始时间,同治县志中作“始自绍兴壬子”,是文字讹误。按:“绍兴壬子”,即是绍兴二年(1132年)。以周有德记文中写到的人事来检验,应是绍熙壬子(1192年),要晚60年。会出现这点误差,应是“熙”与“兴(繁体‘興’)”的字形相近所致。这样考辨之后,可知文中“壬子科”“壬子良月”的干支时间,都是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与前后语意完全符合。
周有德记文提到“邑宰赵公”“请于邑侯赵公师奭”,查道光《泰和县志》卷十四“宦绩”:赵师奭,“绍熙元年知泰和县事,辟潢舍,益庖廪,作兴士类……按:师奭传,旧志作绍熙,原志作绍兴,误。”正好与乡饮之事相互印证。乾隆志补充写的“戊午科,知县卓洵复益以公帑之钱,严万全记。辛酉科,知县赵汝謩书其事于乡饮所”,在“宦绩”所记官员中也有呼应:卓洵,“庆元间以朝奉郎知泰和县”;赵汝謩,“嘉泰中,来知泰和县事。”有了年号界定,“戊午科”“辛酉科”就确知是庆元四年(1198年)、嘉泰元年(1201年)。人物、时间、事件三者协调,参与其事的诸人任官时间,进一步证明发起“义举”只能是绍熙,写作“绍兴”是不对的。
另外,有的文句遣词造句难于理解,如:“壬子科,绍兴士子大比”,此处“绍兴”二字不可理解;“令道州司法严公万全……”,这里的“令”很费解,义举本是人们的自发行动,不应该是执行“命令”的行动,而且究竟是谁下此命令,也没有交代。这两点要存疑。
接下来的“严公万全、乡先生周公英彦合谋其男琰有德偕乡贡进士陈忱三人总其事”,出现的人名不止三人,语意也难明辨,该是刊刻时有讹脱。同治县志转载时写作“邑人严万全、周英彦、陈忱也,乡贡进士周有德书其事”,意思就清楚明白了,可以据此理解。
再有“贫则未免资人介则必至鬻产”,意思为贫者难免要向别人借债,至于卖家产抵债,但“资人介”三字不明晰。我主观倾向理解为请人中介担保,才能借到钱,而偿还债款和中介费,必将卖掉家产。
“虽未应龙洲之谶,而来者为可知。”“龙洲之谶”,是关于科举的民间预言。南昌、新建、丰城三县有“三洲联,出状元”谶语,说是碰上三县的赣江沙洲连成一片了,就预兆本地要出状元;福建建州也有“淮尾沙圆,宰相状元之谶”[5]。这种谶语虽然是虚幻迷信,却不乏心理暗示、鼓舞斗志的作用。泰和县的“龙洲之谶”是同类意思的预言,据县志记载,福建同安僧定光,来庐陵参西峰豁禅师,到泰和过怀仁渡时,水暴涨,定光于是念偈语,水退,起沙洲,即为龙洲,他又留下偈语曰:“龙洲过县前,泰和出状元;龙洲接金鱼,泰和出相儒”。此类传言寄托着人们的理想追求,虽然没有兑现状元,但谭一飞、陈嗣宗两人已中进士得官,表明资助义举确实有效,故“来者为可知”。
四、“南宫义举”的意义及其首创地位的认定
《南宫义举记》是一篇记实的文章,由此可以知道南宋吉州泰和县社会文教方面的几点具体内容。
1.社会教育发达,儒学水准高。“西昌壮邑,素号多士,三岁大比,应诏者不下二千人。”泰和县古名西昌县,位于赣江中游吉泰盆地的核心,小农经济兴旺,魏晋时代就是江南的粮食主产区,生活相对富裕的人群庞大,他们投资教育、培育子弟的欲望自然普遍迫切,形成追求由科举而出仕,从农户上升为官户的社会潮流。经由科举选拔人才,是全国范围的文化实力大比拼,而泰和县每次能够选拔出二千人参与,是全国少有的盛况。
2.发动义举的原因是资助赴考旅费。各地考生到京师——南宋时的临安(今杭州市)——赴考所需的路费都是举子自己承担,他们认为这不合适。理由有二,其一是不合大道理,伤害了朝廷的体面,“登籍天府,观上国之光,实众歆艳其荣之时,岂可于道里之费而使家自为备乎,此今日义举所由兴也”;其二,从举子家庭实际考虑,巨额的路费将是不够富裕家庭的沉重负担,“道里远者以数千计,裹粮资费,贫则未免资人介则必至鬻产,因仍积年,无有宽其忧者”。为赴考而借债、卖家产导致长年忧患,违背了科举的美意。前一个理由是务虚,后一个理由是求实。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从化解旅费困难上得来。
3.义举的操作方式是众人自愿集资。“义举之约,以千人为率;每人日出一文,约三岁,得钱一千有奇”,“率乡里同志为义举,计日集钱,积之三岁,以侑其行,士得不困”。壬子科提名者10人,当时“集钱得四十四万八千有奇,析而送之”。每人日出一文,付出轻微,对“乡里同志”不会构成负担。然而集腋成裘,一千人参与义举*我在《南宋科举义约的助考效益与教育功能》一文中,将“以千认为率”理解为“指参加学内考选的生员数”(见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江门市档案局主编《陈乐素先生诞生一百十周年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112页),看来错了。依周有德所说的“每人日出一文,约三岁,得钱一千有奇”,壬子科得钱44.8万余推算,应是指参与义约集资的人数。,经过三年,就能积攒下百万余文。壬子年集得44.8万余,只相当约一年半时间集得的钱,或者参与集资的人仅约500人。按人分送,每人得4.4万余,“士得不困”。“总其事”即负责承办集资的是道州司法严万全、乡先生周英彦、乡贡进士陈忱三人。
4.官府、民众都非常看重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之事。大家认为给这些进京赴考的人以优厚礼遇,是重兴先秦的宾兴、两汉的县次续食传统风尚,故而县官主持饯行典礼,乡里举办盛宴送行。宾兴、县次续食,皆是贯彻朝廷旨意,忠顺于皇权的表现。因为这些人将要“登籍天府,观上国之光”,参加朝廷的考试,载入礼部档案。“县官之劝驾既勤,乡里之饯举甚宠”,都是维护朝廷权威,表示忠顺之举。为求宣扬朝廷旨意,把大事做得更体面,知县赵师奭当众宣布“捐公帑百千以助斯举”,庆元三年(1197年)知县卓洵“复益以公帑之钱”。乡里办宴请,开支是民众负担;赵、卓两位知县襄助,拿的是“公帑”——官钱,何乐而不为。给眼前的赴考者以优待,传递出强化朝廷权威的信息,政治伦理观念由此深入人心。现任官僚形象同时得到提高。
5.“义举”的效益明显。每个举子赴考都有资金保障,原有的后顾之忧将转化为拼搏之力,使“士气大振”,中举的机率势必增大。“越明年,谭一飞实中乙科,调章贡户掾;陈嗣宗次之,调衡州茶陵簿,皆由此其选”,是最近的实例。从长远来衡量,科举义约激发良性循环,书院教育风气持续强劲起来,社会文化自然日益兴旺。这从科举人才数量增加上可以看到一个大概。万历七年《泰和县志》卷七登录的进士、解试人名,北宋时期进士22名,解试53名;南宋时期进士95名,解试439名*1993年版《泰和县志》卷十五《历代进士一览》登录的进士名单人数,唐朝1人,五代9人,北宋42人,南宋109人。南宋部分以谭一飞、陈嗣宗两人分界,之前为20人,之后为89人。反映的增长趋势,与万历县志一致。。进士人数增加4.3倍,解试人数增加超过8.2倍,上升趋势十分显著。推动泰和县科举进步的因素很多,不会只有“义举”一项,但“义举”带来的激励效益是不容置疑的。
6.泰和首创的“义举”,为各地仿效。周有德对首创一事自豪地说:“况义举自吾邑始,今天下闻者类欲效之,夫岂无益。”周氏此话不假。首先是创始,查找已知的科举义约资料,没有发现更早的。洪咨夔《楚泮荣登义约序》,自注为“嘉定三年(1210年)正月望日钱唐洪某序”[6],比周有德晚了17年。徐鹿卿在南安军写《梯云义约》,是他嘉定十六年(1223年)中进士,出任南安军军学教授之后。其次是仿效。这一点周有德说得巧妙,“闻者类欲效之”,知道的人都想仿效,是否兑现,关键要看对方。
周有德说,我们的义举使“古者宾兴之意复见于今日矣。乡举里选三代所尚,县次续食两汉仅见。自科举法行,是意微矣”。在自我表彰之中,说出对科举法的一点批评。他这点见解,在后来人的同类文章中一再重现,成为共识。例如:洪咨夔《楚泮荣登义约序》:“礼宾,周制。续食,汉法。士未尝为舂粮之谋。科举设而待士之意衰。”刘克庄《鄂州贡士田记》:“士贡于乡,古也。使士赍粮重趼而至,非古也……至汉,犹令县次继食……近世宾兴,郡太守备巵酒,饮饯之外,舟车扉屦皆士自任。贫而远者,难是行如登天,有不能行者。”[7]我们要问,朝廷是科举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不继承先秦的“宾兴”、两汉的“续食”政策,从赋税中开支参加科举考试的旅差费?帝王专制追求的只是家天下统治长久,“宾兴”“续食”时代的对象是贵族,而且人数极少。而科举考生的人数众多,若是官费必定数额巨大;而且科举考生是一般百姓,朝中无人,没有话语权;即使有贫寒者来不了也无大碍,帝王不会忧虑。所以,尽管有官绅发议论,始终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关于泰和“南宫义举”的首创地位,本无疑问。可是《永乐大典》录存的《衡州府图经志》写“貢士有义约,自艮斋先生谢谔始行之”,让研究者据以为凭,认为是谢谔最先在临江军创行的。究其实,谢谔没有创行科举义约,他创行的是“义役”,是关于差役的事,与科举风马牛不相干。翻检相关的官私文献史料,都没有谢谔提倡过科举义约的记录*为节省篇幅,这里不拟展开考证叙述。有兴趣者请查阅我的《南宋科举义约的助考效益与教育功能》一文第六节,在那里我进行了详细考辨,《陈乐素先生诞生一百十周年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14年。。
五、科举义约向贡士庄的转变发展
泰和县能够率先出现科举义约,是农耕经济兴旺、百姓生活比较富裕的结果。
严万全、周英彦、陈忱三人发起的“南宫义举”,是富有士绅的集资助考,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受到各方赞扬。但毕竟是个人行为,各因其力,随其自愿,无任何强制约束,资金来源没有保障,出现抚州崇仁县那种得不到赞助的事例,也不足怪*楼钥《攻媿集》卷七十,《跋抚州崇仁县义约》:“媺哉,义约之立也。风俗之媺恶,繋乎士大夫。先正名公有以孤生荐于乡,历求裹粮于亲故,终不满千钱。愤且慙,挂钱于城门,矢之曰:我且显,当徙族以去。已而果然。”。因此,泰和“南宫义举”方式的个人自愿之“约”,属于初期阶段集资模式,在鄱阳、瑞州(今高安)等地也有过,但未见广泛铺开。后来各地解决赴考费用的办法主要是设置“贡士庄”,资金落实于田庄,管理归属州县学校,成为稳定性的经济来源。虽然仍是地方之举,没有朝廷的法令政策,但涉及地域很广,留存的资料例证很多,并且延续长久。例如:
泰和县所在的吉州地区,各县皆有贡士庄。欧阳守道写家乡的情况说:
庐陵县贡士庄者,郡太守豫章李侯某,从邑人刘君某之请所建也。郡三岁贡士六十有八人,而庐陵得人为最……他县贡各有庄,庐陵独无有,至是岁得米三千斛有竒,郡博士偕邑大夫视其入,及期易为泉(钱),视其人分赆之。”这位“刘君某”的儿子刘芮在王氏家塾教其外甥读书,甥病亡,无人读书,王氏遂以稻田赠刘芮。刘氏父子认为不该私有此田,得知郡太守和郡博士正在商议建贡士庄,遂将此田送出。[8]
吉州州学也有贡士庄。文天祥告诉人们说:吉州贡士庄,创始于知州胡槻,有租米二千二百斛有竒,然“庐陵士甲江右,一科数路,资送四五百人”,收入不足支用,于是多次增加庄田,至咸淳六年(1270年),“合今所増,通为米六千一百斛有竒,以学谕提点庄事”[9]。
泰和西北边的近邻袁州(今宜春市)、临江军(今樟树市),曾经有过科举义约,不久也都建立了贡士庄。袁州新昌县(今宜丰县),宝庆间(1225—1227年)知县赵纶“修学宫,置贡士庄”。临江军通判赵师逌,“括在官之田,置贡士庄,以助偕计吏者”。再往北的白鹿洞书院,也在咸淳間(1265—1274年)由南康军知军刘溥汉,“創白鹿洞貢士莊”[10]。
赣东北的饶州(治今鄱阳县)、信州(治今上饶县)在宁宗时期先后建立了贡士庄。开禧元年(1205年)冬,安仁县(今余江县)知县刘强学“置贡士土田五千三百余把,为钱一百六十四万有竒,岁收约官斛四百石……遇大比,士赴礼部、补国学者,捐为续食费。安仁至京都千里,自是赴功名之会者,俱无裹粮之忧”*刘强学《宋安仁县学田记》,见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嘉定九年(1216年)信州通判章良朋以“没官田创贡士庄,而隶于学,命教授董其要,择诸生可任者为司贡以治……积三年租课所入,贮于庠庑,以为六邑宾兴东上之赆……岁管早租二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晚租一百八十二石七斗三升五合,晚园池地四十一贯文”[11]。
赣东的建昌军(治今南城县)的贡士庄称作“青云庄”。南宋理宗时期,建昌知军赵孟藡得知“南丰有寺曰安禅,燬于宼,田若干,无所于属,于是复其租税,为屋四楹,乃积乃仓于寺之废址,命曰青云庄,钱谷有司三岁一会,凡旴之试御前者,赆各有差,所为厚士于方来,盖庶几焉”[12]。
福建、湖北、广东、四川等地的情况,大致和江西相同。福建汀州府长汀县貢士庄,是“郡倅黄大全创,岁收所入,以赡举人之赴试者”。清流县贡士庄,是宝祐六年(1258年),县令林昌泰、林应龙创置[13]。邵武军的军学也有贡士庄,“旧有贡士荘,薄甚”,军学教授方君“节浮费去冗食”,一年多以后“得旧楮三万二千,买田七百余秤,积三岁之入,可得万楮……由学而贡者,岁卒十人,人获千楮,足矣”[14]。
广东雷州府海康县,“郡守薛植夫建,郡人乐助者。买田百余亩为贡士荘,凡遇举子会试,尽所积以送行”[15]。湖北鄂州(治今武汉市)贡士庄,贾似道“董饷鄂渚,时阃帅创南阳书院,公给以官田百三十畆,复斥币如鄱之数以惠鄂士”。此前,贾似道为铸钱使,在饶州鄱阳“斥羡币十万缗,市田为鄱贡士庄”[16]。
四川靖州的贡士庄名为兴贤庄,“靖故有田以给贡士,岁入为钱万七千八百,益以屋僦五万六千,然仅供新士半途之费,而免举者又不及新士十之一”。绍定四年(1231年)知州魏了翁“市近郊田,积三岁所入,以给三邑之新旧进士”[17]。
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御史台文书中指称:“江南地面亡宋时,路县各有贡士庄钱粮,三年一番开选场,赍发中选儒人,作盘纒赴省殿试等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又有尚书省奏“访闻得江淮等处,未附已前,诸学并有贡士庄田産,所出租课,专一养育有学问士人等,津遣赴举秀才用度”[18]。
以上的资料信息中,具体事例部分反映的地区很不全面,元朝的官府文书是整体性的描述,宋代的“路、县各有贡士庄钱粮”、“江淮等处诸县并有贡士庄田产”断语,可以弥补具体事例部分的缺陷。
文献资料证明的一个事实是,南宋晚期进京参加考试的费用,由贡士庄田产的收益支付,考生不论贫富一概享用。设置贡士庄田的资金来源不一,大多数不是州县财政的收入。贾似道给以公田、刘姓父子私人捐田的方式,都只是个别事例。这表明各地官员把贡士庄之事看作政绩在做,借以博取乡绅支持,获取好评。由于民间的自发集资助考改变为官府的一种制度性的政策措施,实质上是自费考试向官费考试的转变,是社会在前进的一种表现。公益性的“贡士庄”出现在南宋各地,无论主其事者出于何种动机,设置“贡士庄”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效益不能抹掉。
六、结 语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推动私家书院兴起,书院按照科举的指挥运作,读书应举、“学而优则仕”成为社会共识,是最热门的人生追求。书院的本质功能在此,祭祀、藏书等其它内容皆是衍生品,不可等同。
泰和县匡山书院为民办书院,是书院发展史初期阶段的珍品;“南宫义举”为拓荒性的创举,未有先例。它们在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两大领域做出了榜样,“启愚发覆”,为后续的发展开辟了前进道路。
“贡士庄”制度是在“义约”基础上发明出来的,克服了助考资金的不稳定性,把自费进京考试改变为官费考试,是这股文教大潮中涌起的精彩浪花。集资助考的民间慈善行为,是这个发展历程初始阶段的产物,其发轫之功是不朽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兴旺、民众生活比较宽松的基础之上。家有余财,能够支撑子弟脱离体力劳动,私家书院才得以滋长起来。即便是进京赴考有资金困难的考生,也不是耕田务工的穷贱小民。经济为文教提供物质基础,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与经济相互推动,兴盛的科举文化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泰和县魏晋以来的粮食重地,南唐时代的匡山书院,北宋的稻种基地,南宋的科举义举,千百年长时段的良性循环,不断进步,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1]许怀林.江西史稿[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70.
[2]曾皋.匡山书院记[M]//泰和县志:卷十六文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734.
[3]王定保.唐摭言: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
[4]文莹.湘山野录: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
[5]姚勉.雪坡文集:卷三十八《古洪三洲义约序》《圆沙桂籍序》[M]//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洪咨夔.平斋文集:巻二十九[M]//四部丛刊:续编·集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7]刘克庄.后村集:卷二十一[M]//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欧阳守道.巽斋集:卷十六:庐陵贡士庄记[M]//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文天祥全集:卷九:吉州州学貢士庄记[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327-328.
[10]雍正.江西通志:卷六十、六十一、六十四[M]//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赵蕃.章泉稿:卷五:重修广信郡学记[M]//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文天祥全集:卷九:建昌军青云庄记[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338.
[13]雍正.福建通志:卷六十三[M]//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4]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十:邵武军军学贡士荘[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5]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三[M]//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6]刘克庄.鄂州贡士田记[M]//后村集:卷二十一.四库全书本:集部四·别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7]魏了翁.靖州兴贤荘记[M]//鹤山集:卷五十.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8]庙学典礼:卷一:省台复石国秀尹应元所献学田[M]//四库全书:史部十三·正书类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卢春艳】
The Origin and Value of Kuang Hill Academy and“Patronage of Southern Palace”
XU Huai-lin
(College of History,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Taihe County is loc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Jitai Basin.Since ancient times,it is a developed area of food and agriculture,and this laid a solid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private academies took advantage of each oth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In Southern Tang Dynasty,Luo Tao founded Kuang Hill Academy in his hometown,which was a model in Jitai Basin.For the first time,people of Taihe county carried out “Patronage of Southern Palace” in the middl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and gave an imitation for others.This meant a great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and education.The originality of “Patronage of Southern Palace” relied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was beyond question.Later,this kind of patronage based on the charitable agreement developed into“Gongshi Farm”;at the same time,the patronage to the poor became the assistance for all the participants to imperial examination,and the examination at their own expense changed to the one at the state expense.This kind of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ystem contributed to the academic educatio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agricultural economy;Kuang Hill Academy;Patronage of Southern Palace;Gongshi Farm
2016-05-20
许怀林(1937—),男,江西宜黄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宋史、江西地方史兼及客家学。
K245
A
1005-6378(2016)06-0001-09
10.3969/j.issn.1005-6378.2016.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