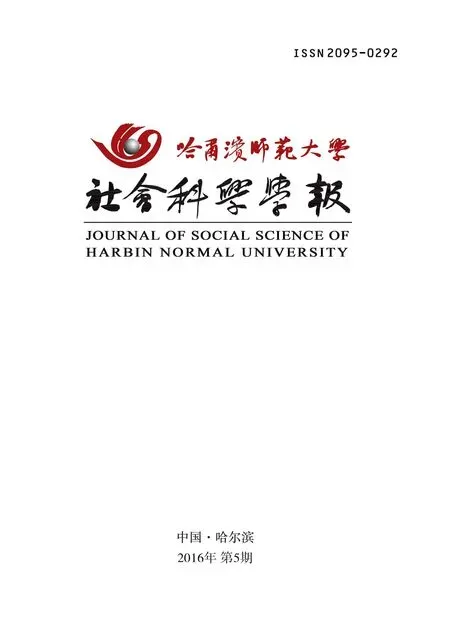归去来——论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
2016-03-07贺与诤
贺与诤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归去来
——论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
贺与诤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在持续性写作三十余年的当代作家当中,阎连科是举足轻重而又备受争议的一位。在经过“军旅”和“乡土”的打磨、历练之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阎连科开始呈现出奇诡、荒诞、寓言化的写作风格。他的作品蕴含强烈的生命意识、深厚的土地情结。在他的许多文本中,呈现出表现苦难和死亡的诉求,和对现实的荒诞、疯狂的超乎寻常的想象。本文以《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为对象,探寻阎连科书写苦难和死亡的真实意图,感悟他对灵魂博弈的生动描摹,把握其从失落、绝望的艰涩回归,以及坚执地从现实中走出困境的悖论图景。
阎连科;《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苦难;死亡;人性;荒寒
一、生死“苦”旅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乡村和土地为题材和依托的写作由来已久。自20世纪初期开始,现代作家们在对故土的记忆与遭际的重组中,发现自己熟悉的创作题材,挖掘出艺术个性之源,寻找到文化之根,从而创作出饱含乡思乡愁和民族命运忧患的文学作品。在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药》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将笔探入乡间土地的深处,去找寻人性与民族悲剧的根源。此外,还有沈从文书写的“湘西世界”中的纤尘不染,老舍小说中讽喻十足的“京味儿”,萧红作品中透露出的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明净与清透……这些,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打着各自迥异而浓郁的地域烙印和乡土情怀。
及至当代,杰出作家对土地的忠诚与守望丝毫没有消退。他们以一种非功利的、超脱的胸怀,在挚爱的土地中跋涉,在作品中呈献对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坦诚思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掀起“文化寻根”的热潮,韩少功、李杭育、阿城等作家将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情风俗融入作品,用现代意识观照历史和传统,探寻文化重建的可能性。当下,在看到贾平凹对商洛丹凤棣花镇的细致诉说,苏童的作品中饱含躁动与温情的“香椿树街”以及狂奔的“枫杨树故乡”的留恋,莫言对充满血性与酒气的山东高密乡的热爱,迟子建对苍老而温热的北方故土的娓娓道来……他们的写作构筑和联结中国大地的血脉,赋予土地生命和情感。
在对土地的书写中,阎连科是一位特立独行者,他以土地为依托,打破传统文体与概念的惯性驱使,去挖掘美和诗意的另一个侧面,回归到对人性的审视,在对自我和他人的磨难历程的呈现中,揭示人性中的某种真相。
阎连科,是以其对土地和乡土独特的情怀,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中艰难跋涉,最终发现、发掘出惨不忍睹的人与人之间复杂纠结、人性的荒谬,完成与鲁迅“吃人”寓言相重叠般的极致书写。在对他作品的探讨中,总是绕不开“苦难”“死亡”这两个关键词。在写作中,阎连科将想象带入我国中原地区湿热而黏重的土壤中,并以此为基点,构建起一个充盈着死亡、灾难的荒寒虚境。他在这片土地上艰难跋涉,笔下流淌出一股股黑红冰冷的血液,凝结成一个个冷硬残酷的故事。在《日光流年》中,生活在耙耧深山中三姓村的村民们始终都在被“喉堵症”导致的四十岁生命大限折磨、摧残着。在《受活》中,在深山的褶皱里,受活庄里的人们无一不是盲、瘸、聋、儒,在自然灾害和贫穷的裹挟中,他们的生死如草样随风飘摇。在《丁庄梦》中,为了挣钱卖血最终患了艾滋病的丁庄人,也都在认命般地等着离世。在作品中,阎连科往往呈现出黑暗、惨不忍睹的逼真画面,给读者带来惊恐、摧残神经的阅读体验。蓝四十死时身下一朵朵绽放的白色“花朵”,绝术团的演员在表演中疯狂的自残,这些扭曲、血腥的描写,呈现出一种极端的美感,让读者无力承受又无法放下。并且,对于阎连科本人而言,这种残忍的创作也丝毫不曾带给他释放、发泄的快感。在刚刚完成《丁庄梦》时,阎连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知道,这种强烈苦痛的绝望,不单单是写作《丁庄梦》的一次结果,而是一种长久写作的崩溃,是对完成的《丁庄梦》死亡式的祭奠,是从1994年开始动笔写作《日光流年》、到2002年写作《受活》、再到2005年写作《丁庄梦》的长达十二年苦痛的积累和爆发。”
“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在这个充满欢乐的世界里,你们读我的小说时,读这部《丁庄梦》我不能给你们带来这些,而只能给你们带来刺心的苦痛。”
在面对自己和读者时,阎连科的内心满是委顿、压抑、痛苦,他的作品也同样给读者带来惊恐、窒息、疼痛,那么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文本意向何在?在他的心中,是什么折磨着他让他惴惴不安,在苦难书写上踽踽前行的他,想要在“苦”旅中看到什么?
从三姓村,到受活庄,再到丁庄,这些村落无一不是被围困在封闭的深山之中,人们同外界的联系微乎其微,当自然的灾害和时代的震荡袭来时,便仿佛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流从四面八方倾泻而下,村落和村民唯有逆来顺受,任由宰割。在凝固不变的环境中,薄如蝉翼的生命体被无限放大,这些生命个体的内心镜像也清晰地得以还原。“我不是要说极终的什么话,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阎连科的自白,让我们明白,他不是要用苦难折磨自己和他人,而是为了回到生命萌动的原点。为了洞见人性的幽微,他甘愿置身苦难的沼泽中,寻求原初的神光。
叔本华曾说:“人的生存就是一场痛苦的斗争,生命的每一秒都在为抵抗死亡而斗争,而这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斗争。”同死亡对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小说中,阎连科选择和死亡站在一起,作为他“苦”旅的起点。他充分地汲取着死亡带给他的养分,去感知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在旅行中,阎连科如愿以偿地目睹天灾人祸之下的“众生相”,他并未如布道者般抒发赞美、悲悯,而是将着力点放在异化和扭曲的人心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苦难的极致书写中,阎连科要向我们展现的是人们内心的疯狂和荒谬。在他笔下的那种极端生活中,悲剧随处可见,在无处遁逃的悲剧之中,有多少是人性的悲剧?
死亡,代表着终结,它不仅意味着寿命的终止,还是精神和灵魂的消亡。因而在死亡面前,人们往往会将自己最坦诚的一面呈现出来,在此时,伦理、日常的法则和规约往往是被打乱、被剥离的。在《日光流年》中,司马蓝和蓝四十的爱情是青梅竹马、一见钟情的。可为了当上村长、修灵渠、救自己的命,司马蓝没有迎娶蓝四十,他让蓝四十向合作社的卢主任献身,去城里做“人肉生意”。而《丁庄梦》中的丁亮和玲玲的爱情,则是垂死前的“偷欢”,是最后的放纵。可玲玲为给丁亮降温,把自己活活发烧烧死了,而后丁亮用刀砍向自己的腿,以致“热病”涌上来猝死。在小说中,司马蓝是一生标榜要造福于三姓村的村长,丁亮是个嘴角总是挂着赖赖的笑的无赖,他们最终都陪着自己的爱人“下世”了,那么究竟是谁的爱更纯粹一些?这是阎连科笔下死亡面前的两种爱情,没有风花雪月,只有切肤之痛:在墓地之前,人们的伪装才会完全卸下,真正地真实起来。
以生者观望生者,或许无论如何还是带着感同身受的意味,于是,许多作家开始从亡灵的视角反观生者、审视世界,用“零度”的心体悟外界的温度,在死亡的溶解下,完成对人性本然的探寻。胡安·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中,用多位亡灵的诉说拼凑出佩德罗巴拉莫这样一个狡诈自私、阴暗滥情的人物形象,揭露人性之恶。奥尔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的第一章“我是一个死人”中道出一个无法安宁的灵魂的控诉和痛苦。方方的《风景》、余华的《第七天》,这些作品都是以亡魂冷静、客观的视角审看生灵,从而更加深刻地还原时代与现实对精神的逼迫。沿着这一思路,在《丁庄梦》中,阎连科以丁辉已经亡故的儿子的全知视角进行叙事。一个因父辈的过错而被毒死的儿童,看着爷爷做关于丁庄的寓言般的噩梦,目睹父亲的发迹史,见证丁庄因卖血而走向毁灭的全过程,没有什么比他的叙述更加有力、客观、真诚。在阎连科笔下,死亡不是一种结局,而是与活着相伴而生、挥之不去的可怕存在。
苦难和死亡是阎连科捕捉生命内在意绪的通行证,他需要用超逻辑、残忍的笔刺穿温情的瞒骗,照亮精神的暗区,厘清遮蔽之下的或许是血淋淋的“灵魂真实”。只要人们还生活在苦难之中,只要人们的内心还在被欲望充塞,阎连科的“苦旅”就永远不会终结。
二、灵魂之役
在阎连科小说的评论文章中,关于土地、苦难、现实、乌托邦的讨论已经比较充分,这些分析与阎连科的文本意向贴近与否,究其根本,是要看其对阎连科关于人心与现实紧张关系的解析是否深入。事实上,对阎连科作品中叙事学和审美层面的评判、论断,阎连科自身对现实的阐释、理论,其实都远没有他作品中呈现出来得那样自然、生动、有冲击力。因此,我们不妨跳出那些惯性观念的窠臼,打开文本形式上的枷锁,从“心”出发,挖掘阎连科在作品中想要呈现的生命意识和灵魂底色。
从《日光流年》到《受活》,再到《丁庄梦》,阎连科作品中悲剧性、宿命般的死亡游戏一刻不停地捉弄着人们,在这场旷久的对峙中,人们闹剧般的反抗方式,使他们付出比自然和现实施加给他们的苦难残酷百倍的代价。当身体被当作出卖灵魂的工具时,他们的内心也被摧残得愈发疯狂和坚硬。在坟茔面前,人们的惊悸、彷徨、自私一览无遗,他们在同命运搏击的同时,也在同自己的灵魂博弈。那是恪守道德和释放原欲之间的纠结,是伪装“善”与袒露“恶”的犹豫挣扎。在周旋之中,目睹一切的阎连科将内心的崩溃诉诸笔下一个个饱满逼真的人物,在静穆肃杀的场域中,打响一场场灵魂之役。
时势造“英雄”,在阎连科书写的一场场征战之中,出现这样一些人:杜桑、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茅枝婆、柳鹰雀、丁水阳、丁辉,他们不是英雄,却在每一场异想天开的运动中,充当“领袖”或始作俑者的角色。这些“领袖”说服他人的逻辑看似不容辩驳,实则一触即破。他们的种种想法使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深信不疑的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都有着强烈的逃离苦难的愿望,以及同样封闭、浮浅的思维。在这里,阎连科为我们展现一种可悲的宿命旋涡。这些“领袖”的思维不仅闭塞,还带有与生俱来的对权力的崇拜。在《日光流年》中,每一任村长都在上一任村长未咽气之前,甚至是孩提时代便开始自己成为村长的幻想。在蓝百岁死后,司马蓝成功地胜任村长,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司马蓝从哭声中威凛凛地走出来,把自己顶天立地地竖在院落里。
“缝孝布的,针脚细一些,这孝帽孝衣村里日后死了人还要用。”
“打灵棚的活粗一些,风刮不倒就行。”
该哭的又哭了,该缝的又缝了,该干活的干活去了。司马蓝的话,在三姓村真正开始落地有声了。
司马蓝的这段独白透露着刚刚就任的狂喜、兴奋、自豪、得意。他从记事起,就幻想着有一天可以成为村长,权力对于他而言,意味着一切。在他的脑海中,领导民众的欲望先于求生的渴望,他习惯把带领大家活过四十岁当作挡箭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三姓村的村民们努力的徒劳,也在书的开头寓言般地宣告一代代村长带领村民们求生的徒劳。
在茅枝婆和丁水阳身上,权力则成为他们酿成一切苦果秘不示人的动机所在。茅枝婆在看完书记、县长一封封盖着手印的亲笔信后,亲手毁掉受活庄的“天堂日子”,使他们卷入“铁灾”“大劫年”“黑灾”“红灾”之中。在《丁庄梦》中,沩县的教育局局长对丁水阳说:“丁老师,你在学校敲钟看大门,不算是老师,可学校报你几次当模范教师我都批准了。每次当模范,又发奖状又发钱,现在我这教育局长给你这一点任务你都不完成,你是瞧不起我这局长吧?”想到透着红光的奖状,丁水阳便将丁庄的人们集合到一起,说着卖血的好处,也就为几年后的热病爆发埋下最初的伏笔。茅枝婆和丁水阳,一位是历经磨难的老革命战士,一位是饱经沧桑的老者,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沦陷在他人蛊惑人心的话语中。
有许多关于阎连科的评论文章,将他对权力的书写归入勾画、讽喻“政治”、意识形态作品的行列,认为阎连科是通过他的一些作品完成他对“乡村政治”的美学书写。然而,从精神劣根性的维度去探讨阎连科笔下的权力或许是更亲近阎连科写作的一种角度。王尧的一段文字契合地切中阎连科的写作中同政治的关联:“阎连科的小说重点不在写权力之争的黑暗,而是侧重于呈现权力是怎样影响生活世界的,从而在更大的背景中揭示劳苦人宿命的原因所在。”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他们的内心,都不突出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强调个人力量完成某一英雄主义行为。群众在他们眼中只是名垂青史的一种工具。正如柳鹰雀以为自己的政治蓝图正在一点点实现时,他在敬仰堂中,把自己的挂像一点点地挪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等人物的最前面。在列宁的水晶棺材下层为自己准备了“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的水晶棺。在他的血管喷薄着权欲的猩红。在内心深处,他们最崇拜的人是自己,在这片孤绝的地域,在狭小的村落中,他们渴望得到所有人的膜拜,即使“宏图”的结果是集体自杀式的毁灭。阎连科想要挖掘的正是这份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私欲给更大的群体造成的灭绝式灾难。
在阎连科笔下,还有一类庞大的人群作为叙述主体出现在作品中,那就是众多的村民,他们是发号施令者的执行者,淳朴、无知、盲目、奴性。他们不同于鲁迅小说中“看客”,鲁迅笔下相近的国民类型是封建迷信和国难之下精神的溃败、良知的丧失的群体。他们的麻木是对国家、民族的存亡懵然不知,是知识分子和文明的悲哀。而阎连科呈现的“看客”,是对生死概念的遗忘,是天生对权力的畏怕、服从,是利益驱使下的尊严丧失和自我放弃,他们的劣根性是人类和人性的悲剧。荒寒,像冰窖中的冷气从脚下丝丝攀爬,如藤蔓般攫住咽喉。在小说中,村民们的举动常常表现出集体式的一往无前和悲壮。三姓村的村民们以各种荒诞的方式执着地试图逃离来自土地的侵袭:夜以继日地生孩子保证人口数,在虫灾和饥荒中放弃粮食去守护油菜地,卖皮卖肉修建灵渠引水;受活庄里的人们,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过富足的“天堂日子”,莫名其妙地入合作社,无意识地卷入到改革的浪潮之中,为了攒下购买列宁遗体的资金组成绝术团,丧失尊严地展示身体残缺的部分;在丁庄上,人们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疯狂地卖血,在胳膊上留下一排排芝麻粒般的针孔……深受苦痛折磨的村民们紧锣密鼓地忙活着,忙着活,没有人深究那些方案是否可行,他们的意志受生命牵引,被死亡推搡。
我们发现,在阎连科的小说中,人们所承受的更深重的苦难,往往不是外界施加的,很多时候是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阎连科笔下的人都很少声嘶力竭,总是在缓缓流淌的日光下过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可一旦实施某一举措的理由足以说服他们,大家便燎原般一触即发。这种一往无前、如梦初醒的气势在“领袖”们荒唐的指令中,显得更加荒诞。在《受活》中,绝术团中的人们都是享受着自己的残缺的,聋子耳上放炮,瞎子盲眼照明,独眼百孔穿针,麻痹症脚穿玻璃瓶子翻筋斗……他们为自己的残缺可以带来的巨大物质收益喜出望外,丝毫不为展示自身的缺陷感到耻辱。在《丁庄梦》中,丁辉给丁庄引来死亡的“鬼火”后,大张旗鼓地做起死人的生意,倒卖棺材、配冥婚、卖墓地。而丁庄的人们仍然配合地让丁辉发了一笔笔大财。每当惨剧如约而至,人们便会爆发式地指责他人,之后则是以新一轮的荒谬来弥补荒谬。阎连科的小说通过对典型群体的描摹,呈现人性中的种种弱点,实现对人格的挑战,也为我们呈现更大的悲哀。
在阎连科的身上,盘踞着开拓的精神气魄,他无视核心文化、先验理念、利益集团的封锁,探索内心现实的玄奥,梳理出独属于自己战线的文学观。他在自己的创作之路中,默默铺展着叙述雄心,在文本中渐渐形成可以辅佐其文学观的人物类型。这种沉稳和宏阔是许多作家无法企及的。凭借这些流淌着阎连科灵魂和血液的人物,阎连科坚执地向现实中存在的虚假冷漠、歌功颂德、黑暗畸形宣战。
三、绝地荒寒
一位自信的、有爆发力的作家,会在他熟悉的地域环境和人文状貌中,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场域,在这片场域中,他能够更加自如地展开想象,更加冷静地审视周遭。荒寒,作为阎连科文本美学特征的概括,散发着孤绝、冷寂的味道。在《丁庄梦》中,在故事开始之前有这样一段话。
庄里的静,浓烈的静,绝了声息。丁庄活着,和死了一样。因为绝静,因为秋深,因为黄昏,村落萎了,人也萎了。萎缩着,日子也跟着枯干,像埋在地里的尸。
日子如尸。
其实这种“绝静”常常弥漫在阎连科的小说之中,它既是对环境氛围的概括,也是一种美学特征和心境的表述,还是与作品中人们隐曲、无常的生存状态密切关联的。阎连科笔下的人们生活得十分艰辛、苦涩,这种苦涩源自苦难,也源自内心的失守。人们得过且过、苟且偷生的生活状态与闭塞的环境、孤绝的氛围结为一体,使多重意义的荒寒之感自然地流淌在文本的每一个角落。
克尔凯郭尔说:“一个作家不能引领一个时代前进,也不能引导他人的人生,但是一个作家真正的贡献是指出他所存在的那个时代的失落。”这段话与阎连科的文本意义不谋而合。在小说中,他所营造出的美学意义上的荒寒与冷硬,以及他对生活当中荒寒的呈现都有了理由。他是要在自己可以主宰的场域中,躲开喧嚣,在“绝静”之中思考现实。
在荒寒的笼罩下,我们渐渐发现,在《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中,有一抹日光始终悬挂在深山上空,静静地散发着暖意,包裹着安宁时的惬意、灾难来临时的躁动和“天在看”的冷冽。阎连科笔下的日光,作为与“荒寒”相对抗的一种意象,执着地存在。在《我为什么写作》中,阎连科谈道:“我希望能通过写作,在我的后半生中,对无处不在的恐惧形成一种抵抗。”在触摸到现实、时代的疼痛和失落之后,在感到孤独、恐惧、绝望之余,阎连科希望通过写作,在充斥着折磨和摧残的绝地之中,实现突围。
阎连科的文本常常饱含隐喻,他总能独到地发现被遮蔽、被遗忘的真实,并冷静地以奇诡、变形的方式展现出来。阎连科作品中的政治、历史、现实常常介于虚与实、梦与醒之间。他挖掘出社会、时代之中给人们带来的无奈和苍凉,同时,也没有止步于剖析和描摹,而是展开想象,抵达超越现实的人性高度。他曲折、掘进的叙述轨迹,构成一幅试图对抗和爆发的乌托邦图景。当一些作家在叙事中过分地注重临摹现实、保存经验,而使文字愈发干枯生硬时,他们的创作习惯也和当下现实中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重叠,这是作家的失责和无力。在被意识形态、消费文化和利益集团等多重因素包围的复杂环境中,人们思维的停滞和自欺亟待转变。阎连科试图冲破秩序和经验束缚,尝试逼近灵魂的写作,无论是从一个作家,或是“生而为人”的角度,这都是一场有意义的爆发。
在当下环境、语境中,审看乡村和土地,往往更多地找到破碎和颓败,回望历史和革命,容易陷入解构和阐释的桎梏,而现代社会又常常受意识形态、利益、世俗影响。加之在长期的压抑之下,作家内心也存在惯性的本能和设防,因而作家想要拨开迷雾、翻越困境是十分艰难的。在围困之中,总有一些作家负隅顽抗,虽然这条路注定无比艰涩的。贾平凹在《秦腔》的写作中,全面呈现中国乡土的溃败,实现对以往乡村书写表现形式的突破;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挖掘历史中的空白并质疑已被定性的史实,打了一场别样的解构之役;对于阎连科来说,他通过耙耧山脉中生活的呈现,穿越空置的真实,实现对内心的深进和唤醒。
在《日光流年》中,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是逆行的,人的生命也是由老到小、从死到生的。时间的逆行给阅读带来障碍,但在打破叙述的常规后,关于生命消失的故事便转化成向死而生的故事,给生命、生存带来更大的力量。然而,在这种力量震撼着人心时,我们并不能从中看到阎连科作品中对未来的希冀和对当下困境的解决方案,他看似神秘的叙述策略中似乎总是潜藏着一份难言之隐。在《受活》中,从触碰“毛须”、深掘“根茎”、细品“苦果”、最终回到幻灭之“种子”。还有《丁庄梦》的梦醒时分,一切又回到“新的蹦蹦跳跳的世界”。在对阎连科文本结构的感知中,我们会发现他在叙述上存在整体性的消解。一次次试图爆发却无法抵达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阎连科写作的艰难和煎熬。
环境和语境的围困造成阎连科在叙述上无法实现内心的期待,从而为他的“荒寒”突围增添逼仄、回旋的悲剧意味。然而,阎连科始终未曾放弃他的抵抗,他在作品中从表达对死亡和苦难的逃离开始,到揭穿人们真实的内心底色,最终在现实世界的失望和守望之中归来。这是一场悖论式的跋涉,在这个过程中,阎连科的内心纵然早已千疮百孔,写作对于他而言也早就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他依然以悲悯、宽容的胸怀,在残酷中,点起一盏诗意之灯。在衰败、失落中,找寻着生命和人生原初的意义。
阎连科曾说:“应该不仅认同世俗的生活,而且要在俗世中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做不到可以抵抗一切,但可以做到不附和一些。反对现实的生活,但爱和理解现实中一切的人。”在人性面前,阎连科的掘进蕴含着宽和、悲悯、力量、不妥协。因为他明白,在多重元素纠结在一起的复杂绝境,想要实现最终的抵达需要的不仅仅是舒展现实扭结的气魄,更要有在叙述中周旋的耐心、抵挡写作内在悖论的坚强定力。
[1]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阎连科.发现小说[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3]王尧.一个人的文学史或从文学史的盲点出发[J].当代作家评论,2007(5).
[4]孙郁.日光下的魔影[J].当代作家评论,2007(5).
[5]阎连科.我为什么写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4(2).
[6]陈晓明.他引来鬼火,他横扫一切[J].当代作家评论,2007(5).
[责任编辑 孙 葳]
2016-06-15
贺与诤,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I207
A
2095-0292(2016)05-01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