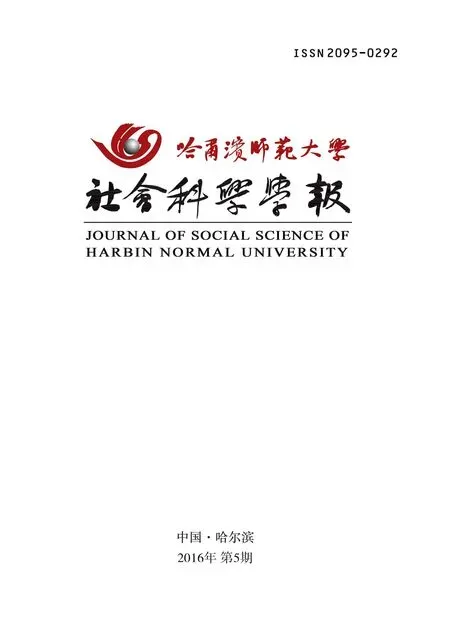明清杂剧对元人杂剧题材的接受
2016-03-07姜丽华
姜丽华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明清杂剧对元人杂剧题材的接受
姜丽华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明清杂剧对元人杂剧题材类型的承袭,主要体现在历史故事题材、男女情爱题材和神仙道化题材等三个类型之中,从中反映了明清曲家的“杂剧宗元”观念。对元代历史故事题材表现的英雄主题,明清杂剧有所延续。由于主题建构的不同诉求,明清历史题材亦呈现出与元人历史题材不一样的美学风貌。在男女情爱题材中,明清杂剧延续元杂剧以“才美”为核心的钟情模式,其才美特征,不是简单固化的郎才女貌,而是男女双方均为才貌双全。明清神仙道化剧对元人杂剧的题材宗尚,主要表现在度脱剧当中。
明清;杂剧;题材;接受;宗元
金埴叙:“今优人登场爨演所谓古戏今戏者,多法元人院本,不能出其范围于十二科之外。”[1](P690)这句话意在说明,古今戏曲包括明清杂剧的题材,不能脱离元人杂剧范畴。明清杂剧对元人杂剧题材类型的承袭,主要表现在历史故事题材、男女情爱题材和神仙道化题材等三个类型之中,从中反映了明清曲家的杂剧宗元观念。
一
明清杂剧对元人杂剧题材类型的承袭,在历史故事题材中表现尤为显著。就杂剧数量而言,历史题材是杂剧创作中的大宗,元代有作者可考者历史剧计162种*刘新文:《〈录鬼簿〉中历史剧探源》,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其中,明初作家贾仲明、谷子敬、汤舜民等三人历史剧各一种,因属《太和正音谱》“国朝一十六人”之列,故未计数。,在钟嗣成《录鬼簿》451种元人杂剧中,占比三分之一强。明清历史故事戏,亦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2](P276-371)。
明清杂剧对元代历史故事题材表现的英雄主题有所延续。如明无名氏《吴起敌秦挂帅印》展现在国家存续的危亡时刻,吴起的文韬武略;清张韬《戴院长神行蓟州道》,写戴宗逗弄李逵,部分承袭元代李逵杂剧书写仗义兼及诨闹的风貌;清唐英《十字坡》,塑造武松胆大心细的英雄形象。但是,歌颂英雄不再是这类故事题材中主要的思想意识,明清人在演绎这类题材时,常爱做翻案文章。比如,明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虽然亦描写了宋江、燕青等人物,但非以歌颂梁山英雄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为旨趣,剧作以李师师为主角,演述文士、帝王之韵事风流。比如荆轲故事,明叶宪祖《易水寒》不但让刺秦成功,而且说荆轲是谪仙下凡;清周乐清《宴金台》叙荆轲骗过秦王,又写秦燕大战,燕国胜出,周朝使臣封太子丹为定亲王。这些显示出作家主体对题材的选择和处理的差异。
才子雅事、文人心理,是明清杂剧的主要题目,清初杂剧中涌现出写心杂剧,盖为文人抒怀心理的一种体现。在历史题材杂剧中,作家们不仅言古事,还观照自身际遇,抒发文人趣尚。明徐渭《渔阳三弄》愤世嫉俗,“意气豪侠,如其为人”[3](P266)。许潮《王羲之兰亭显才艺》,写文人风雅。陈与郊《袁氏义犬》,寄寓讽刺,“作此以愧门墙之负心者”[4](P642)。黄方胤讥刺市井敝俗,结撰《陌花轩杂剧》。叶小纨缅怀姐妹之情,敷演《鸳鸯梦》。清吴伟业《临春阁》,显“遗民人格”;尤侗《西堂乐府》,见“才子情结”;嵇永仁《续离骚》,彰“志士情怀”[5]。吟风弄月、抒情写恨之文人题材为明清杂剧创作带来新气象,郑振铎叙:“以取材言,则由世俗熟闻之《三国》、《水浒》、《西游》故事,《蝴蝶梦》、《滴水浮沤》诸公案传奇,一变而为《邯郸》、《高唐》(车任远有《邯郸》、《高唐》诸剧),《渔阳》、《西台》(徐渭有《渔阳》等剧,陆世廉有《西台记》),《红绡》《碧纱》(梁辰鱼有《红绡》,来集之有《碧纱》剧),以及《灌夫骂座》,对山《救友》(叶宪祖有《灌夫骂座》、王骥德又《救友》剧)诸雅隽故事。因而,人物亦由诸葛孔明、包待制、二郎神、燕青、李逵等民间共仰之英雄,一变而为陶潜、沈约、崔护、苏轼、杨慎、唐寅等文人学士。”[6](P533)郑振铎以文人雅隽故事、人物身份之转换,观照明清题材之改变,洵为知味之言。这一点,实为明清杂剧题材宗元嬗变之主要表现。
在才子故事中,明清杂剧不仅写男性,还勾勒历史上才女的故事,丰富文人事迹的画卷。明陈与郊《文姬入塞》,敷衍文姬事迹;明徐翙《春波影》写明代才女小青的不幸经历;清南山逸史《长公妹》,传写苏小妹文采;清洪昇《四婵娟》,分别从诗、书、词、画层面,书写谢道韫、卫茂漪、李易安、管仲姬的才情。才女题材的涌现,与明清女性生存环境的变化有所关联。从明末开始,社会对闺秀的评价,在德的基础上也有才的要求,涌现了许多的才女,仅清人黄秩模《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即收1949位女诗人的作品。文人对家中出现才女,普遍深以为傲,比如,叶小鸾、叶小纨之于叶绍袁家族,陈同、谈则、钱宜之于吴吴山家族。才子与才女的诗词唱酬,才女事迹的记载、传颂,才女书稿的刊刻,及对现实中才女形象的文学演绎,是文人“文化身份的表达”[7](P103),投射出文人阶层对才女的接受。因而,历史题材中对才女群体的关注,既与明清文人对女性才华的欣赏不可分割,也与明清社会对才女文化的接受密切相关。
总之,与元代杂剧作家居身下僚不同,明清文人多游走于功名仕宦之路,杂剧作家之登进士第者,在在皆有。一方面,社会身份的不同,影响着题材选择的时代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主题建构的不同诉求,明清历史题材展亦呈现出与元人历史题材不一样的美学风貌。
二
男女情爱题材,明清杂剧延续元杂剧以才美为核心的钟情模式,其才美特征,不是简单的郎才女貌,而是男女均为才貌双全。
对于男性角色,剧本强调其俊朗。所谓才子不可无貌,名士焉能无年?正如佳人使才子惊艳,才子的外形俊朗,使得佳人脚步俄延、秋波流转、梦绕魂牵。不过,与女性角色相比,明清杂剧显然着重于描摹男性之才华。萧淑兰形容张世英“那生外貌俊雅,内性温良,更兼才华藻丽,非凡器也”[8](P477)。卢玉香听王文秀吟诗,唱:“多应是公差官长闲来往,莫不是好事的儒流到此方,则他那诗句清新意高尚,料他那才华字样,粲珠玑锦囊,我这里听沉了痴呆多半晌。”[9]以上,均为对男子才华的赞誉。才华被作为男主角的核心特征被着力渲染,剧作家们在反复强调男主角这一特征时,不仅采用人物自述、他人赞誉的方式,还通过人物的种种表现来展示,并且总是与功名联系起来,将所得功名作为男主角才华横溢的注脚。
对男女情爱剧中的女主角,剧本虽然也提到其针黹女工、翰墨诗词或者吹弹歌舞等才识技艺,但是,剧作家不仅塑造以才美为核心质素的女性形象,还突出对女性德行的描摹。杂剧主题也由歌咏男女情爱、终成眷属,嬗变为对节烈贞义的揄扬。明贾仲明《荆楚臣重对玉梳记》写歌妓顾玉香守志不屈,一心想着荆楚臣;贾仲明《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传歌妓李素兰心系李斌,拒绝接客,剪发名志。明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记卓文君在紧急之时,坚持自己驾车、相如乘车,遵循尊卑妇道。清秋绿词人《桂香云影》演刘桂云为歌妓之女,不愿意像母亲一样,沦落勾栏。清沈玉亮《鸳鸯冢》叙吴锡、戴氏是一对恩爱夫妻,吴锡染病而亡,戴氏殉节而死,最后,二人在仙境恩爱。清叶奕苞《燕子楼》讲述张尚书筑燕子楼,将关盼盼安置在此。张殁,关不肯改嫁,独居燕子楼中。白居易从张仲素处得盼盼燕子楼诗,附赠一绝于盼盼“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10],且云“君子爱人以德,予将以此诗,成盼盼名耳”,盼盼得诗,决定自尽。明朱有燉的人物画廊里,云集众多贞妇般的歌妓形象。《春风庆朔堂》中的甄月娥“生的风流可喜,四般乐器皆能,只是他不肯觅行院衣饭,家中三口儿,唱得一两贯钱钞,过其日月”[11],姿容风流、擅长弹奏、行止端正,甄月娥堪称容、德、才兼备。她甘贫守志,所期待的是“立妇名,成家计,情愿待举案齐眉”[11]。男主角范仲淹不信其贞烈,托聪俊才子魏介之前去试探,结果铩羽而返。最后,范仲淹评价甄月娥:“他的真诚恭顺,敬上待下的心,虽是良家妇女,到有不如他的。”[11]虽名为歌妓,实为良人。在取材于石君宝《李亚仙诗酒曲江池》的同名杂剧中,朱有燉亦塑造了“容德兼备,出众超群”[11]的李亚仙,其“始以不正而立身,终当坚持而守志”[11],最终被敕封汧国夫人。尤其,《刘盼春守志香囊怨》以对女主角德行的描摹而影响深远。其主角刘盼春“标致风流,出格之妍,能弹能唱”[11],身为歌妓,卖艺不卖身。遇到周恭之前是黄花女儿,被梳拢之后,虽生活贫窘,也只酒楼唱曲,不肯留客。盐商陆源重金引诱,刘盼春对鸨母言:
【幺】奶奶 休只顾贪图他入马钱,但得个知心的是宿缘。常言道 夫乃是妇之天,若成了欢娱缱绻。尽今世永团圆。[11]
最后,在鸨母的胁迫下,刘盼春自戕守志,焚化之后,周恭送给她的香囊保存完好。周恭前来奔丧,誓不再娶。《香囊怨》对比以“风流子生前言誓愿,贞烈女死后成姻眷。周子敬题情锦字笺,刘盼春守志香囊怨”为题目正名,彰显传事迹、表贞烈的主旨。《香囊怨》影响深远,康海《王兰卿服信贞烈传》对刘盼春故事有所承袭。王季烈言:“其事足以风世,与《香囊怨》相类。”[12](P22)曾永义叙:“对山此剧对于宪王的妓女剧是有所借鉴和规模的。”[13](P209)剧作家对《香囊怨》类题材的追逐,投射出对风世旨趣的推崇,这类主题在元杂剧男女情爱题材中比较鲜见,在明清杂剧中得到强调。明清曲家正是借由对女主角从才美到容德的关注、渲染,实现情爱题材主题的重新建构。
碧玉闺秀才女佳人的贞烈故事,所在皆有,明清杂剧,尤其是明代前中期,却多选择歌妓题材弘扬妇道精神。这种题材选择,既与明代前中期主流对教化的强调有关,也与作家的创作视角密不可分。朱有燉叙:“近来山东卒伍中,有妇人死节于其夫,予喜新闻之事,乃为之作传奇一帙,表其行操。继而思之,彼乃良家之子,闺门之教,或所素闻,犹可以为常理耳。至构肆中女童而能死节于其良人,不尤为难耶……予因为制传奇,名之曰《香囊怨》,以表其节操。惜乎此女子出于风尘之中,不能如良家者,闻诸上司,旌表其节,乃怜其生于难守节操之所,而又难能表白于后世,可为之深叹也矣。”[14](P201)此类作品的涌现,并非现实中良人妇德的缺失,而是从底层低贱处着手,在其别致行文中,体现的是移风易俗、道德教化的强调。
与歌妓贞烈题材配合,在明清男女情爱题材中,有一类以嘲弄讽刺笔触叙述男女之情欲,从中寄寓劝惩。这类题材为元人男女情爱题材之所无,开拓了杂剧情爱题材的表现视域。无名氏《风月南牢记》,叙以弹唱为生的妓女李善真与徐统制相投,却被父亲乱点鸳鸯,嫁给校尉周敏为妻,因而时常思念旧情人徐统制。她让姐妹歌妓刘坠儿送信给徐统制,不料刘坠儿巧言挑唆,使徐相信李变心,乘机与徐统制鬼混。李善真去找徐统制,发现二人之事。另一歌妓臧大姐亦去徐家,与刘坠儿争风吃醋,吵闹不休。因徐统制打骂妻子,徐统制妻兄龚常将其告到朝廷,最后徐妻由龚常带回娘家,徐统制被从轻治罪,刘坠儿交其夫处置。在这部剧中,没有坚贞、守志、真情,有的是权宜、背叛和私欲,在惩戒奸夫淫妇的同时,对淫妇的鞭笞更甚。无名氏《庆丰门苏九淫奔记》亦是一部讽刺之作。剧中主人公苏九姐嫁了一个腌臜的丈夫孟怀仁,心生嫌弃。一日,结识唐国相,以为遇到如意郎君,收拾细软,相约私奔。孰料,唐国相本是强盗,得财之后,怕带着苏九姐惹麻烦,弃之而去。苏九姐邻居发现其私奔之事,喊来苏九姐婆家人,婆婆将之告到官府,判孟怀仁将苏九姐休弃。苏九姐回到家里,思想遇到称意之人。此时,光棍朱邦器、李邦问去苏九姐家,为更加蠢笨的李廷材李四官牵线吊拐。一番哄骗,苏九姐应允。在濮阳城里,承差官高逢先帮李四官准备花红酒礼,入马之期,苏九姐方见到李廷材,失望至极。《风月南牢记》和《庆丰门苏九淫奔记》,是男女情爱剧中的另类,剧中人物,追逐情爱,却最终践踏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受到世人的唾弃和法律的制裁。不过,在情节叙述过程中,作者始终以嬉笑戏谑的态度在行文,尤其是《庆丰门苏九淫奔记》,全剧在嬉笑戏谑之中,裹挟着深深的厌恶和不耻,仿佛冷冷地又痛快地注视着这个淫妇苏九姐,看她的轻信,看她所遇之人的不堪,看她为淫心情欲付出的代价。但是,在男女情爱戏曲中奉行才美与聪俊的典型中,始终没有观照到伶俐美貌之苏九姐与其所遇到的一个又一个腌臜蠢笨的男人之间是否匹配,没有想到这种失衡导致的行为,既是可恨可耻,又有可怜可叹。这种一边倒的指责,当然是风教之需要,也确乎为男性之视角所致。
与元人情爱剧相比,明清情爱题材还有开拓。在人物身份上,情爱剧中的主角,不止是闺秀士子、歌妓书生,还有歌妓与乐工、道姑与书生、僧侣和尼姑等,如陈铎《花月妓双偷纳锦郎》,叙歌妓惜春与教坊司乐人贾中之间的情愫;无名氏《张于湖误宿女贞观》,演道姑陈妙常与潘必正的偷期;冯惟敏《僧尼共犯》,写僧人与尼姑之间的情爱。有研究者解读《僧尼共犯》“借滑稽戏谑来表示他排佛的思想”[13](P220)。诚然,这种思想意识确实存在。不过,从内容上来看,剧作自始至终,在写明进和惠朗之间的偷期私会,写巡捕“情法两尽”[15](P517)的判断,故而,作情爱剧观,亦无不可。在结局上,明清杂剧不都是两情相悦、中举团圆,还有伤心被弃的故事,比如清蓉鸥漫叟《桃叶渡吴姬泛月》《王翘玉阁中掷金钏》《纱帽巷报信伤春》,均写的是女子被弃的伤心故事。
明清男女情爱题材杂剧,还延续了元人杂剧的叙述模式。
一是商人拨乱模式。元杂剧歌妓与书生情爱杂剧中,商人拨乱是常见的模式。在这类杂剧中,歌妓是上厅行首,书生是饱学之士,二人之间有商人作梗,山重水复。然后,或者贵人相助,或者书生考中状元,柳暗花明,爱情圆满。比如,贾仲明《玉壶春》演清明游赏,名妓李素兰与书生李斌一见钟情,鸨母爱财,阻挠李素兰与李斌相见,希望素兰结纳多金的山西商人甚舍。正在二人恋情陷入窘境的时候,李斌朋友陶纲相助,将李斌万言策献于皇帝,李斌被授嘉兴府同知,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明清杂剧的商人拨乱模式时有变异,常常在后半部分,男主角未中科第,爱情亦没有完满的结局。如前所述朱有燉《香囊怨》,既没有中举,也没有贵人相助,剧末虽有香囊的不朽,但在刘盼春的自戕中,回荡着周生的悲啼。
二是诤友相助模式。在这类杂剧中,书生沉溺于与歌妓的恋情,爱美人不爱江山,将功名进身抛诸脑后,当不得不去应试时,又放心不下美人。此时,朋友出现,书生将美人拜托于友人,了却后顾之忧。友人将美人接到府中,保持完璧,却不说明这样做的原因。书生误解其横刀夺爱,中举得官之后,见到旧爱,误会解除,士妓团圆。这类元杂剧的代表是《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在明清杂剧中,叶宪祖《任夭桃巧合鸾皇》堪为继武之作。剧作写书生石中英为刘令公儿子的伴读,在请假拜扫时,被财主赖三舍人邀去见歌妓。初次见面,一个云“那石千之是好一位可人也”[16](P83),一个言“那夭桃好一个美人也”[16](P83)。由此,终日缱绻。嫉妒的赖三舍人将此事告诉石中英的父亲。石中英回家之后,还偷偷见夭桃,不愿奔赴春闱。为敦促石中英,刘令公将夭桃接到自己家中,石中英再去找时,以为夭桃别适他人,终下应试决心。得官之后,石中英与夭桃团聚,了解到令公好心,误会解除。孟称舜《陈教授泣赋眼儿媚》、邹式金《风流冢》、黄兆森《梦扬州》均属此类。
三是《西厢记》推进模式。这类杂剧,在故事演进、情节发展中,模仿《西厢记》,是为《西厢》推进模式。明无名氏《秦月娥误失金环记》叙秦月娥父亲南阳任上谢世,留下夫人与妻子,无法返回故闾。杨儒上京路上投奔父亲老友秦月娥之父,秦母留之后园“翠兰亭”居住攻书。杨儒秦月娥后园相见,杨儒称秦“嫦娥下降”“神仙离洛浦”顾盼留情,秦月娥遗失金环,杨儒捡到。梅香寻金环,杨儒趁机递简,秦月娥酬简。二人偷期,被老夫人发现,梅香代为折辩,老夫人理亏,同意杨儒应举,二人再结为婚姻。杨儒进士及第除授府尹,夫妻团圆。剧中情节与《西厢记》相类,无论父逝羁留、梅香传简、花园约会还是夫人拷红,诸多关目皆能看到《西厢记》的痕迹。王季烈评跋:“其事与《东墙记》绝相类,然关目率直,不如仁甫《东墙》,更不及实甫《西厢》矣”[12](P48),洵为知言。明清剧作家对元曲关目的照搬,有时是有意、自觉的,如傅一臣《错调合璧》自跋:“大段与王瑞兰招商店相似,故不得以淫奔律之。”[6](P885)在对元剧自觉的模拟之中,明清曲家以元剧为参照,寻求题材表达的合理化。
约略言之,明清男女情爱题材,对元人题材既有沿袭又有开拓。其在叙述模式上,对元杂剧有所延续。在人物塑造上,对男性的刻画,以聪俊为核心;对女性的抒写,由才美转向容德。在主题建构上,明清杂剧更关注道德教化,体现出一代风尚。
三
神仙道化题材既是元人杂剧的重要类别,也是明清杂剧创作中又一题材宗元类型。神仙道化剧中可分为度脱剧、庆赏剧两类。元杂剧中度脱剧最多,明清神仙道化剧对元人杂剧的题材宗尚,主要表现在度脱剧当中。以被度者为类分,度脱剧分蘖为三种习见模式:谪仙模式、天赋模式、勤奋模式。
青木正儿云:“度脱剧里面,有一种谪仙投胎式,就是他的前身本是神仙,因为起了思凡之念,被贬谪到尘世中,经验人生的乐事。等到后来省悟其为泡沫梦幻,便又被见许归还仙界了。拿这种的教理,包围剧之外廓者,成了一种定型。此剧即其一例。此类剧的特色,是投胎——即托生于下方人间——者限于金童玉女,而以描写青年男女之爱情或夫妇生活之快乐为主眼,如本剧便是如此。”[17](P156)青木正儿所言正是元人杂剧谪仙模式的基本特征。对明清杂剧来说,谪仙模式有新的变化。其题材走向可以概括为:
触犯天条—贬谪人间—业期满足—神仙接引—重返天庭
即被度者不局限于思凡,而是触犯仙界规矩,因而,必须到人间经历一番,业期完满,才能返回天庭。在元人谪仙模式中,乔梦符《玉箫女两世姻缘》、无名氏《瘸李岳诗酒玩江亭》,堪为代表。《两世姻缘》剧叙梓橦帝君在蟠桃会上,看到金童玉女,各有凡心,被贬到人间。金童投胎为韦皋,玉女投胎为韩玉箫。金童为一世人,玉女为两世人。二人经历酒色财气、人我是非、功名富贵种种人世悲欢,最终结为夫妇。四十年后,梓橦帝君出现,点醒金童玉女,最终证果朝元,重返天界[18]。明清叙及金童玉女的杂剧,刘东生《金童玉女娇红记》,基本承袭了这一模式。剧演金童玉女思凡,瑶池金母将二人降谪人间二十年。金童化身为申纯,玉女化身为娇娘,二人互生爱恋。有权豪杨都统家求亲,申纯、娇娘抑郁成疾。申纯之父听说碧鸡庙前有个师婆下神,就请其为申纯看病。碧鸡神指出二人是金童玉女,有前世宿缘。于是,二人成婚。这时,瑶池金母命董双成接引,董双成点醒二人,金童玉女复归仙道。剧本的开头、结尾都有神仙说明因果,剧本下卷正名“申厚卿难通叔伯婚,王娇娘合升神仙路”[19]。这类杂剧,由于其首尾言说神仙,中间敷衍情爱,常被认为是男女情爱剧,有的选家在刊刻之时,甚至会将首尾去掉,改头换面。明臧晋书《元人百种曲》在遴选《玉箫女两世姻缘》时,就删掉神道部分,使其彻头彻尾成为另一个题材类型,反映出明清人对这类谪仙模式的认知和接受。
在对谪仙模式的宗尚中,明清杂剧有所变化,常常部分地改写模式构成。在《雷泽遇仙记》中,雷泽是天上掌管彩笔的金童,因醉酒失仪,贬谪人间。其与许飞琼有宿缘。一天,雷泽遇到一个绝色美人,正是到凡间游历的瑶池仙子——许飞琼。自此之后,雷泽在人间,许飞琼则往返于人间天上,时常相会。三年期满,许飞琼与雷泽告别,预言雷泽将中状元。雷泽高中之时,许飞琼复又出现,约定雷泽致仕后再相见。雷泽在归田二十年后,重回天界。在这个剧目中,雷泽是谪仙,许飞琼则神仙身份不改,既是雷泽的人间眷属,又充当着雷泽的天界向导。雷泽尽享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归隐林泉的凡人喜事,在风烛残年之时,回归天上,再做神仙,收获长生。王季烈指出雷泽实有其人:“按明天顺八年(1464年)二甲进士雷泽,山西忻州定襄县人。除刑科给事中,抗直不避权势,疏陈戚畹骄恣,被廷杖几死,醒复谏不止,闻者称为铁汉。仕至光禄寺卿。此剧所记姓名爵里,均与之合,当是时人慕其风节,而为此记。”[12]从雷泽故事的走向看,对神仙道化题材中人间部分,多有增饰,确有因人作传的倾向。吴梅评价兼述爱情的度脱题材:“神仙儿女,兼备一身,今古情场,无此美满。”[6](P806)比之雷泽的幸福经历,尚隔一尘。
明人贾仲明《金童玉女》剧则更着眼于度脱。剧叙金童托生的金安寿与玉女托生的童娇兰,在人间业满之后,铁拐李去度脱他们,可是,二人沉溺于人间快乐,乐不思蜀。铁拐李用了种种幻境,才使得二人醒悟过来。而在《两世姻缘》人间生活的部分,金童玉女是在梓橦帝君的预设中,经历悲欢离合、转世轮回。直到剧终,梓橦才出现,二人一点即醒。贾仲明剧的人间部分,没有单纯铺陈人间之爱,杂剧的大段篇幅放在度脱过程上。显然,明清谪仙模式受到其他度脱模式的影响,减弱了卿卿我我,添加了更多度脱的成分。
明无名氏《许真人拔宅飞升》、无名氏《宝光殿天真祝万寿》、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朱有燉《惠禅师三度小桃红》、朱有燉《李妙清花里悟真如》等均属于这一类型。
有一类可归为天赋模式。这一类型,指被度脱者天生异秉,有神仙之分,所谓“你不是个做官的。天生下这等道貌,是个神仙中人”[20](P190)。天赋异秉,故而无须修道,其周身就氤氲一股神仙之气。当神仙看到这股仙气,就会去度脱他。其模式是:
度脱者看到青气—判断有神仙出现—度脱者来到人间—寻找被度脱者—度脱者变化出恶境—度脱实现
明清神仙道化题材中之一部分,就是沿着元杂剧“天赋模式”形成故事框架的。在明无名氏《吕翁三化邯郸店》中,卢志有“仙风道骨”[21],纯阳子吕洞宾降临人间,欲度脱他。由于卢志“久混尘俗,明昧未分”[21],如元代杂剧中那些懵懂无知、贪恋人间的被度者一样,吕洞宾得使出幻化手段,即变幻出“恶境”,才可使其幡然醒悟。于是,吕洞宾先变出一酒肆,自己化身酒家,让卢志于睡梦中经历功名生死,最终促使卢志醒悟,成仙了道。
不过,在恶境的运用上,明清有所不同。在元人神仙道化题材中,度脱过程经历的恶境,虽是幻化出来的,却刻画得逼真而残忍。在马致远《任风子》剧中,任屠休弃发妻,摔死幼子 ;《邯郸梦》中吕洞宾一双儿女,被邦老摔死。明清度脱剧多不取此。在幻境中,只是保留被度者自己穷途末路,大限临头那一刻,以死生对比,强调长生世界的令人向往。在明无名氏《吕翁三化邯郸店》幻境中,卢志得意时,出将入相,失路处,披枷带锁。行将就戮之时,吕洞宾出现,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其余,杨讷《马丹阳度脱刘行首》、清永恩《度蓝关》等剧均属于这一模式。
此外还有勤奋模式。所谓“勤奋模式”,和天赋模式、谪仙模式不同,被度者向往神仙世界,不怕困难,主动习学道法,包括炼丹药、服食仙丹等。勤奋模式的修炼者,在修行到一定境界,就会有仙气生成,直冲仙界。神仙们看到,就会去接引他们。勤奋模式在明清杂剧中占有的比重最大。比如,杨慎《宴清都洞天玄记》,形山道人隐居山中修仙炼道,收服代表心猿意马的六个贼人,降服猛虎,收了婴儿姹女,功行圆满,众仙迎到天上。明无名氏《孙真人南极登仙会》、无名氏《李云卿得道悟仙真》、无名氏《边洞玄墓道升仙》、无名氏《时真人四圣锁白猿》、无名氏《吕纯阳化度黄龙》、朱权《冲漠子独步大罗天》等剧均属于这一模式。这类剧作,因为主人公一心向道、主动修炼不贪恋繁华,所以基本敷衍的就是道教教义,情节比较无趣。
明清神仙道化题材主要沿着这三种模式推进情节,有时,也综合其中的几个模式,比如,朱权《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即为天赋模式和勤奋模式的结合。剧叙皇甫寿(别号冲漠子)夙有仙分,如吕洞宾所描述 “昔为神霄王府上卿,因凡缘未除,复托形华屋,不忘夙本,尝有冲举厌世之心”[21]——这属于天赋模式。而且,冲漠子素慕真风,通过夜观天象,知有真人下凡,翌日寻访,认出了二真人——这属于勤奋模式。二真人决定点化:为其拴缚心猿意马,除去酒色财气,斩了三尸,赐予金丹,教与养婴儿姹女之法,传悟真篇。吕、张二真人扮作渔樵二人,使法术引来冲漠子,若冲漠子能认出二人,便度其过弱水。剧末,冲漠子被度脱,东华帝君领群仙设宴与冲漠子庆贺。
在神仙道化题材中,被度脱者不局限于人类,还包括其他形态的生物,这时,度脱模式与人类有所差异。比如,元马致远《吕洞宾三度岳阳楼》吕洞宾要度的是柳树精、梅花精,吕洞宾指出,若他们想要成仙了道,就要经历一个变身为人的过程。其模式为土木形骸—托生为人—人间经历—实现度脱。明贾仲明《吕洞宾桃柳升仙梦》属于这一类型。与之有变化的是:马剧直接写吕洞宾去度脱,贾剧吕洞宾则为南极真人派去的;度脱前,马剧的柳树、梅花并不相好,贾剧的柳树、桃树已有情愫;境遇上,马剧郭马尔夫妇开个茶馆为生,贾剧中则出身富贵;情节上,马剧较为简单,贾剧一波三折。明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杨讷《马丹阳度脱刘行首》皆属此类。《马丹阳度脱刘行首》被度者是鬼仙,也得先托生为人,才能获得度脱。这种度脱时必先化身为人的规定,投射出剧作家对轮回秩序的认识,反映出宗教的影响。
对元人神仙道化的宗尚和嬗变还包括对度脱者的描述。在道教剧中,元人杂剧度脱者是八仙,明人杂剧中贾仲明《铁拐李度金童玉女》、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杨景贤《马丹阳度脱刘行首》、清叶承宗《狗咬吕洞宾》、郑瑜《黄鹤楼》、永恩《度蓝关》等杂剧度脱者亦属八仙中人。此外,度脱者还有八仙之外的神仙。比如明无名氏《孙真人南极登仙会》度脱者是南极仙翁派去的福禄二仙,明无名氏《许真人拔宅飞升》度脱者是东华帝君派去的崔子文、瑕丘仲,明无名氏《灌口二郎斩健蛟》接引者是玉帝派的天丁,明无名氏《时真人四圣锁白猿》度脱者是时真人,明刘东升《娇红记》接引者是董双成,明王应遴《逍遥游》度脱者为庄子。在佛教剧中,元人杂剧度脱者有忍字和尚、月明尊者和观世音。明清时期佛教度脱者有所变化。明朱有燉《三度小桃红》,为惠明禅师;朱有燉《李妙清花里悟真如》,为毗卢尊者;李开先《打哑禅》,为一个普通的主持;湛然《鱼儿佛》、无名氏《鱼篮记》,叙观世音。清赵进美《立地成佛》,叙名僧丰干。明清神仙道化题材道教剧的度脱者,虽然以八仙为主,但是其他全真教的神仙、道士也有出演;在佛教剧中,观音、罗汉虽然在度脱者中占一定比例,但是其他僧人也有参与,透露出道教、佛教在明清传承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明无名氏《吕纯阳化度黄龙》中,被度者为黄龙寺的黄龙禅师,剧作是以道家去度佛家,这大概出自道教信徒之手,体现明代道教之胜。
总之,从传达的情感来看,元人宣扬道教、向往神仙世界,明清则时有寄托。从度脱者、被度者、度脱模式来看,明清既有沿袭又有嬗变。相对于元人神仙道化题材,在明清时期道教剧中,度脱者不再局限于八仙,佛教剧中度脱者亦更为多元;从被度者来说,明清时期更为多样化,自细民到显贵,皆有可能;从度脱模式来说,明清时期更趋向于勤奋模式,这似乎在敦促众生,只要勤奋修行,就会有所收获,间接反映出对道教的宣扬和道教的盛行。
[1]金埴.不下带编[A].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1集[C].合肥:黄山书社,2008.
[2]张正学.中国杂剧艺术通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3]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A].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2集[C].合肥:黄山书社,2008.
[4]祁彪佳.远山堂剧品[A].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3集[C].合肥:黄山书社,2008.
[5]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6]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
[7]杜桂萍.文献与文心:元明清文学论考[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8]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9]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四[M].上海:上海涵芬楼印行.
[10]叶奕苞.经锄堂乐府[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原刻本.
[11]吴梅.奢摩他室曲丛:第2集[M].上海涵芬楼印行.
[12]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提要[M].上海:上海涵芬楼印行.
[13]曾永义.明杂剧概论[M].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
[14]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1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9.
[15]王绍曾,宫庆山.山左戏曲集成: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6]沈泰.盛明杂剧[A].续修四库全书:第1765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7]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18]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A].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9]刘东生.金童玉女娇红记[M].宣德本.
[20]马致远.邯郸道省悟黄粱梦[A].全元戏曲:第2册[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1]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A].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四集[C].1958.
[责任编辑 孙 葳]
2016-07-20
黑龙江省教育厅面上项目“孟称舜戏曲宗元研究”(2014);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曲家杂剧‘宗元’研究”(2015B016)
姜丽华,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I206
A
2095-0292(2016)05-01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