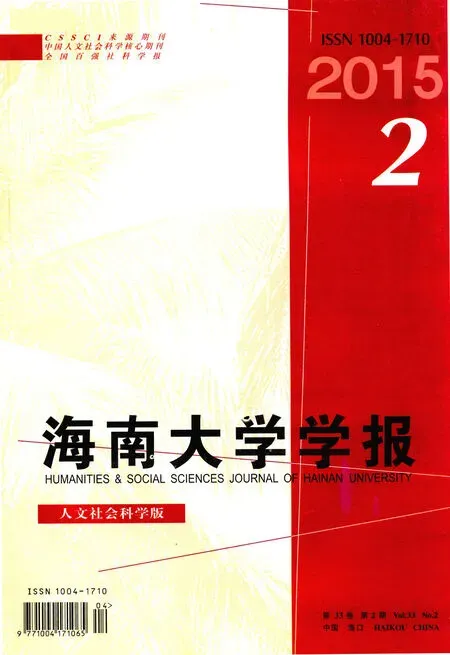胡彬夏与“改良家庭”的女性论述
——兼论“五四”新文学“家”观念的源流
2016-03-06高翔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高翔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胡彬夏与“改良家庭”的女性论述
——兼论“五四”新文学“家”观念的源流
高翔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清末民初留美女性精英胡彬夏,在担任《妇女杂志》主编期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改良家庭论”的女性论述。其中涉及到了改良家庭与改良社会、女子道德、女子教育以及儿童启蒙等方面的内容。“改良家庭论”不仅作为清末民初妇女启蒙思想史中独到的风景线,更为重要的是,同时隐喻了“五四”新文化中家庭与妇女、女性与文学、母亲与儿童等观念的源流。胡彬夏从“妇女启蒙”到“发现儿童”这一思想脉络,恰可为解读“人的发现”的演进轨迹,以及“五四”前后妇女与儿童的教育生态提供典型的范本。
[关键词]胡彬夏;改良家庭论;女性论述;“五四”新文学;“家”观念
胡彬夏( 1888—1931年),江苏无锡人,清末民初女报人、教育家。1902—1903年留学日本,求学于实践女子学校,并组织女性团体“共爱会”。1907—1914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胡桃山女塾、惠尔斯大学,专习文学、哲学,期间担任《留美学生年报》总主笔,1915年12月受聘《妇女杂志》主编。本文拟以胡彬夏在《妇女杂志》任职期间提出的“改良家庭论”为中心,据此探讨该论述与清末民初妇女启蒙、“五四”新文学“家”观念源流之间的内在脉络①学术界对于胡彬夏的生平及基本活动已做出了相关梳理,参见王秀田、梁景和:《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徘徊——以胡彬夏为个案》,《求索》2008年第10期,第224-226页。。
一、“改良家庭论”的提出及其讨论
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张园茶话会发表了一次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说:“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欲建国基,应着手于地方自治……三千县之自治机关,犹三千块之石础……竭五十年之力,为民国筑此三千之石础,必有可成”[1]。
对于孙中山以发达自治机关为巩固共和基础的观点,胡彬夏撰文回应:“以彬夏一女子之目力,瞩建国之妙技,以为基础之下尚有其基础……非地方自治而为家庭。”胡彬夏将家庭场域作为共和大业基础,可谓较孙中山的“地方自治”论更进一步。此中缘由实因家庭为“吾人饮食起居之地,最易造成吾人之习惯”之场所,为“躯壳之所寄存,而灵魂之所依附”。家庭污秽与清洁,与个人习惯养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进而,胡彬夏旗帜鲜明地指出:“改良家庭,即整顿社会也”。对比欧美精致完备的家庭,中国立国四千余年,不惟家庭之中“尚无生活之道”,致污秽垢恶,即便电灯、自来水、排泄渠沟等,皆仰给于西人之供,且社会道德之衰败,甚或袁世凯窃国称帝,政府借款与国脉震荡,“其祸根实深种于家庭”。由此,胡彬夏乃视四千万家庭为民国基础之基础[2]。
事实上,1915年前后的中国,因“二十一条”交涉的受挫、洪宪帝制的复辟,使得诸多有识之士思考改良社会与改良政治之间的关系。梁启超、杨永泰、黄远生等人普遍认为,政治为枝叶,社会为根本,改造社会与改造个人之间互为前提。在“新文化运动”前夕,家庭、女德与国民性的改造之间的关系,亦为时人所重视。论者认为“中国缺少稳练有为之国民者”,由于“家庭之不良”与“女德之不立”[3]。无疑,社会改良思潮的掀起,为孕育胡彬夏“改良家庭”学说之土壤。
胡彬夏主张,“改良家庭为吾妇女今后五十年内之职务”,普及教育、振兴教育、扩充军备,“数千年来相习以为男子之事”[4]。惟改良家庭事业,为女子分内之举。胡彬夏给出了“家庭即主妇,主妇即家庭”的命题,女性当“视其家庭之污秽,如其自身之污秽;视其家庭之整洁,为其自身之整洁;视其家庭之康乐,为其自身之康乐;视其家庭之贫弱,为其自身之贫弱”[5]。并且,胡彬夏以身践行家庭改良,或从改进一场“家常宴会”着手,或择取西餐所长,改良中餐糜费、有妨卫生之弊[6]。胡彬夏以十足信心表示,“用五十年时日,合二万万女子,改良其旧者,建造其新者,举四千万家庭,使皆成良善之家庭,此一极伟大之事业”[2]。
胡彬夏的“改良家庭论”一经抛出,即刻在社会各界引发了激荡和讨论。以积极回应观之,不少读者致信《妇女杂志》,表示对于改良家庭为女子专属责任之肯定。对于家务的整理、家庭陈设之规划、清洁家庭诸方法,亦有论者提出了各自的构想。从消极方面而言,“改良家庭论”一经提出,与之相关的命题是:回家后的“贤母良妻”,与“妾妇教育”、“妇德”之关系,当如何看待?民初妇女参政运动昙花一现,“复古潮流”再度来袭,女子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政府重视褒奖节烈之妇,即便是男女杂座或互相谈笑的行为,亦被警厅严格取缔[7]。教育总长汤化龙在演说中极力批判“男女同权”的新说,转而强调女子教育的方针“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8]。对此,施淑仪致信《妇女杂志》问询:“二年以来,贤母良妻之声,愈唱愈高,激进者至诋之为妾妇教育……而中人以下之女子,以希望贤良之名,不得不求合于妾妇之道”[9]。胡彬夏予以回应,一方面表示万不可将女子之“四德”一网打尽。因“妇容”、“妇德”、“妇工”、“妇言”尚为美国女子奉行为“最高之标准”[10];另一方面宣称,《妇女杂志》所提倡者,并非传统观念的“贤母良妻”,而是一个进化的概念。因“善恶优劣,本为比较的名词,无一定的标准。昔之贤母良妻,今或不复以为贤良”[9]。实际上,就“女德”层面的理解,尽管彰显了胡彬夏徘徊于“新旧地带”的困惑,然而,对传统“女德”观的修正,以及“新思想”的注入,更为胡彬夏青睐与追求者。这体现在胡彬夏对女子教育的目标中:不仅须自执教育之牛耳,养成独立精神与人格,更应以高远情怀,将慈善博爱之精神推己及人,为民族复兴预备[11]。
对于改良家庭与女子教育的关系,胡彬夏可谓是一语道破。即,造就“良善之家庭”的女性,须有“极伟大之能力”,而其源泉则“全恃乎教育”。胡彬夏给出了指南针,即“教育应极其广,极其高。广指教育普及,高指大学教育。若广与高二者不能兼行,则先广后高,先普及教育,后大学教育”[2]。对于“普及教育”,美国各级学校皆采取“先博后专”的教学次序,即以“普通学”——现代学科的基础知识为根本,突破仅专修一门学问的狭隘观念,因“专而不博,拘谨于一隅,难识天下情势……学识必博硕通达,而后其自身能变化运动”。胡彬夏在《妇女杂志》中亦援斯义,于家政等门中,添置天文、地质、铁路、政治、法律、心理、哲学、文学等科,并增设中外大事记[12]。至于“大学教育”,可将日常家事“粗浅简易之事”者,变为深奥奇妙之事,即“能使人见到人所不能见到者,并做到其所见到者……能使人有创作之能力”。以幼稚教育为例,“蒙得梭利教育法”的问世,即是高等教育女性发明产物之明证[2]。
诚然,女子教育不独为提高自身资质,“新贤母良妻”的育儿责任同样为胡彬夏所看重。儿童作为家庭中丈夫、妻子以外的一份子,长期处于被“忽略”与“失语”的状态。胡彬夏指出:“家庭教育之良否,咸视母家之得失……若家庭之自立,则能整理家政,教育子女,斯即自立矣”[13]。胡彬夏结合赴美考察“第三次万国儿童幸福研究会”的经历,一方面指出,儿童教育的承担者,当为家庭与社会的力谋合作,否则“幼稚园中所受教育,回家后抛弃殆尽,殊难收效”[14],并给出了设立幼稚法庭、办理儿童公益事业,建筑儿童游戏场等建议。另一方面,胡彬夏强调,改良家庭是培育优质的新生国民的前提。因男女婚嫁影响胎教及遗传,故禁止近亲结婚、患癫狂等疾或传染病者生育子女,并限制其子女数,实属必要[15]。
胡彬夏摒弃了传统的育儿观,自西方引进“蒙得梭利教育法”、海尔佑氏“训练儿童谈”等理论[16],主张对儿童施以科学的教育,包括脑筋与肌肉训练的配合、寓教育于游戏之方等要素[17]。科学昌明,既能助孩儿发达体育,亦能助孩儿发达智育,甚至可将“脑力薄弱呆獃无知之孩儿,一变而为伶俐敏锐之学童”。倘儿童“习惯于独立自助……乃成真能自由之人”,推而广之,“一家与一国之独立,亦不外乎自助焉,必能自助,而后能独立也”[18]。对于儿童教育,胡彬夏不仅“坐而言”,更有“起而行”。除了撰文立说,胡彬夏亦积极赴身公共领域,如其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演说幼稚园与家庭之关系[14],并于“寰球中国学生会”传播儿童的家庭教育法等[19]。胡彬夏还被推举为“幼稚研究会”主任,曾敦请朱友渔博士演说以改良家庭人种为核心的“生育进化之要旨”等[20]。这种家庭改良与儿童教育问题亦得到了认同者的回应,因家庭为父母、子女的精神交接之域,故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根本,实现家庭与学校的联络,促进二者的合作实为必要。
二、“改良家庭论”与“五四”前夜的女性启蒙
胡彬夏与清末民初知识精英的论述,一并展现了“五四”前夜女性启蒙话语的多元图景。在秋瑾的心中,女性当以“女国民”身份,协同男子革命,共争主权于异族;吕碧城视女学为一国革新之际第一且要之事;张竹君开设女工艺厂、卫生讲习会、女子中西医学院,期此后女子疾病,不假手男医;陈撷芬认为女子惟凭健全的体格,才能脱离脂粉地狱;唐群英则以女子参政为论述核心,力争男女平权。胡彬夏则以“改良家庭”作为女子事业的起点。秋瑾的“革命论”、吕碧城的“兴学论”、张竹君的“实业论”、陈撷芬的“体育论”、唐群英的“参政论”、胡彬夏的“家庭论”,均从不同层面切近了女性启蒙及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问题,从而丰富了近代中国女性的思想谱系[21]。
然而,收复女权的梦想、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的暂时性结合,随着共和曙光的来临迅即幻灭。究其原因,一方面,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间存有先天的隐忧。在女性解放的最初进程中,女性的切身利益,并非是男性首要考虑者,动员女性以“国民之母”/“女国民”的身份,协助完成民族国家独立的任务似显更为紧要。另一方面,因女性在解放进程中激烈“反传统”所造成对于“女德”的偏废,以及女子自身教育能力的缺失,导致了男性同盟者的反感与女界自身的“分化”。事实上,在“革命”、“参政”话语的动员面前,绝大部分女性表现出的是一种裹足不前的姿态[22]92。惟有极为少数被冠以“英雌”名义的女性崭露头角,只是她们的“风头”与“表演”,在男性社会的评价体系中则是一张张“妖魔化”的面孔。唐群英因大闹《长沙日报》的风波,成为了“女德”有缺的代表,沈佩贞则成为了时人眼中“腾笑京内外”的“女流氓”[23]。更为关键的是,共和以后,被动员参与革命的女性普遍面临着“无事可为”的困境。那些多数不为人知的妇女,原先是为逃避封建家庭压迫而“出家革命”的,现在“回家”后,更受家族的奚落,被逼再度出嫁者有之,因流浪而沦为妓女者有之,甚或情形悲惨者,投湖自尽者亦不乏其人[22]103-106。值得深省的是,即便对于“高冷派”的女性知识精英而言,亦难以真正实现其走向社会的广阔成就。失去了英敛之的有力臂膀,吕碧城创办的“天津公立女学堂”终陷孤立无援的停办境地[24]。李平书的离开,使得张竹君主持的“上海医院”无以维系[25]。可见,在男权尚且无法充分保障的时代,侈谈女权的实现,或者徒逞女杰豪气,不修家庭常识,确为一种不循实际的远大空想[26]。
“改良家庭论”既是胡彬夏对于此前激进主义女权观的冷静反思②胡彬夏早年同样以“激烈派”著称,其在拒俄运动中主张女子加入北伐“义勇队”,从事女子军事活动。参见《胡彬夏在“共爱会”集议拒俄会上的演说》,胡杰、陆阳主编:《胡彬夏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版,第3-4页。,同时也是其在民初“贤母良妻”论调回潮之际,为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做出的调和努力。既然男性同盟者以“女德”的缺失,以及女性知识水平不足,为拒绝拥有参政权利的理由,胡彬夏则“对症下药”,一方面从重构“女德”入手,形塑“新贤母良妻”的道德规训,另一方面,着力于女子教育场域,专注“国民常识”的建构。诚然,胡彬夏女学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在“国民常识”的输入外,更以专深的“大学教育”为高瞻远瞩之见。
进一步而言,胡彬夏关于“改良家庭”的论述,巧妙地解决了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内在矛盾,从而实现了二者在目标上的合流。胡彬夏试图在家庭中构建女子的角色,并力争使其将智慧、才能尽情发挥,从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换句话说,胡彬夏的启蒙策略在于将“家事”纳入到国族论述场域,重视女性在家庭中创造财富的社会转化,使女子在家庭中同样成为“生利”之人,与男性在社会中的贡献仅是实现路径的不同而已。这同梁启超等男性关于二万万女子全属“分利者”之说形成了鲜明的比照[27]。如是,改良家庭与振兴民族、国家之间仍存在着一条不可割舍的链条,男“外”女“内”的界限与隔离得以打通,女权启蒙与国族话语之间的内在紧张也渐趋消解。
“改良家庭论”不仅体现了胡彬夏作为女性独特的性别认同,同时其对于女性在营造“家庭融乐”中角色的强调,亦闪烁出智慧的火花。这也为实现男女两性社会的和谐,提供了一种经验与路径。既不同于秋瑾着男装、骑马饮酒、佩剑习武、抛夫弃子等“去性别化”的形象,也不同于张竹君以“女医师”为职业角色而代替二元对立的性别框架,同时区别于吕碧城仅以外部气质为性别角色的扮演,胡彬夏的“改良家庭论”,立足于女性本位,从外在生理及内在道德层面,均注重于对于“女质”的保存,从而捍卫了女性的私性空间,更合乎了两性社会性别角色建构的内在规律。对于女性之于家庭的关系,不同于吕碧城反对女子治理家政,以及柳亚子对“贤母良妻真龌龊”之抨击,胡彬夏则重视女性维持家庭安乐之义务,并视家庭为主翁及子女的安乡乐土,从而避免了“秋瑾式”的悲剧婚姻。胡彬夏这种将女子安置在改良家庭的坐标,并使之自觉承担起社会性别角色的分工的论述,即将“个性”融入到“女性”的角色建构中——既保留了传统“相夫教子”的内涵,又超越了女性困守家庭的限界,既是对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摒弃,也是建立现代家庭文明话语的努力,从而稳定了男女两性在民族国家话语框架下的合作,同时亦有助于女子自身启蒙与解放目标的迂回实现。
三、“改良家庭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及意义
若将研究视域“向后看”,胡彬夏这种将改良家庭与民族国家复兴相联系的认识,像流淌着的河流一样,经过旋转、启迪、消化,作为女性文学的思想艺术资源,在“五四”新文学的书写中也得到了沿袭和继承,进而演绎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文学的写作母本。
不同于“五四”时期将家庭视为罪恶的渊薮,女作家冰心的“家庭本位论”则与以“反传统”为核心的家庭革命思潮形成了鲜明比照。对于那些力谋女子参政、男女开放,否定妇女旧道德,完全仿效欧美女学生的现象,冰心更多表现出的是不屑和批评[28]。而在作品中,其塑造出了一系列家庭淑女形象,诠释了改良家庭与“贤母良妻”的篇章。在处女作《两个家庭》中,前者是妻子亚茜既能与三哥“红袖添香对译书”,又能把家政治理得井井有条,夫妻和睦,子女伶俐;后者是陈太太将家政置身事外而沉溺于交际应酬,结果不但无法相夫教子,而且毁掉了原本幸福的家[29]。继之,冰心在《别后》中同样展现了永明的姐姐澜姑、宜姑两位美丽温柔、人情通达的女性之于家庭改良的意义[30];在《悼沈骊英女士》中,冰心明确了一个“极不平常的女子”理应具备的资质:“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31];《关于女人》则凝聚了冰心对于性别认同的集中表达,其核心即坚守女性以作为“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为本职[32]。故而,在冰心的笔下,家庭与国家之间、家庭的幸福及痛苦与男子建设事业的能力之间,均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惟如此,家庭中的“母爱”也是其孜孜不倦的书写对象。在《第一次宴会》中,作为新式家庭主妇的瑛,其在第一次家宴中用爱心装饰出的“爱巢”,使其顺利完成了从女儿到妻子的身份转变,维系这种延续的正是没有断裂的“母爱”[33]。既然省略了冯沅君、庐隐、苏雪林、石评梅等女性的“反叛”与“性爱”,留在冰心创作世界里的,便满是“母爱”与家庭的温馨。“童真”主题亦与“母爱”互为表里。在《寄小读者》中,冰心所构建的是“姐姐/母亲的女儿”双重身份的叠加。如果说作为“母亲的女儿”,她期望从母亲的怀中寻求情感的慰藉与依托,那么作为“姐姐”,在同“小读者”的通讯中,则建立起了成年同儿童之间平等对话的一种可能性。这种被称作“冰心体”的写作模式,实际上在成年与孩童之间做出了生命的区隔,这不仅消解了中国家庭等级秩序中的人伦关系,而且是对“发现儿童”这一文坛主题的隐喻,并引发了对人类生命平等的想象,为“五四”新文学对于“女性解放”与“儿童的发现”提供了最初的经验。以上“贤母良妻”“母爱”“童真”共同构成了冰心文学中“家”观念的主题,这既是基于她的基督教精神与博爱情怀,同时也是对胡彬夏一整套“改良家庭论”的文学写真与实践。为此,冰心站到了“五四”女性新文学运动的焦点上。
只是,“五四”时期并非每一个作家都复制出冰心笔下的“家”,践行胡彬夏“改良家庭论”。伴随着“五四”时期“娜拉”出走的浪潮,女子“家务劳动社会化”、“儿童公育”等学说的出台与尝试,实未能成功解决女性在“家事”与“职业”中的两难困境。最普遍的情况,仍旧是女性因家庭角色的回归,而牺牲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庐隐的《何处是归程》《胜利之后》,鲁迅的《伤逝》,叶圣陶的《倪焕之》,分别是沙侣、沁芝、子君、金佩璋等女性,将曾经的理想、事业、志趣消磨于家事琐碎中的生动写照[34]。区别于鲁迅关于“娜拉”出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预言,也有少数女性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完成了对社会事功的追求。凌叔华的《绮霞》,即讲述了一位女性为了执著“练琴”的梦想,别夫离家而远赴欧洲求学,然而,学成归来的她,面临的却是丈夫另有新欢的惘然[35];陈衡哲的《洛绮思的故事》则形塑了主人公为学业而割断恋情,在取得成就之后,常为一个幻想有“家”的梦想而困扰的悖论[36]。若是“家事”与“职业”兼顾,则必然使得“娜拉”们疲于奔命。庐隐在《补袜子》中即道出了如是的困惑:“别说我一天到晚都忙着在外面工作,就是有些功夫,与其补那破袜子,我还不如写写文章呢”[37]。
女作家冰心、庐隐、凌叔华、陈衡哲等从多元的场域与视角,不仅从正、反两面阐释了女性、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胡彬夏“改良家庭论”的一种呼应,即女性与家庭之间仍存在着一种无法断裂的纽带,既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力量,也是对社会性别分工的自觉规训。除了文学文本,在现实社会中,一经陷入家事琐碎,女性在事业方面的成就,仍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对冰心而言,“家事”与“职业”的共赢与圆满也仅是一种“想象”的状态,当其与吴文藻结婚,并成为母亲之后,精力的分散,使其无形中与文坛拉开了距离;陈衡哲亦因怀孕之故,一度被迫停课。故而,至20世纪30年代,陈衡哲重新打出了“女子回家”的旗帜,此番论述再度回到了胡彬夏“改良家庭论”的原点。她表示:“一个女子是一个家庭的中心点,而家庭又是国家与民族的中心点”,女性总应把家庭作为终身努力的基础,应当减少、甚至抑制女子在母职、家务以外的事业[38]。
那么,女性在“家事”与“职业”之间,究竟是否为“单选题”?也有论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即“新贤良主义”。“新贤良主义”提倡家庭内男女双方平等,男女两性共同分担家庭责任[39],或谓不仅要提倡“贤母良妻”,“贤夫良父”同为不容忽视之要义[40]。诚然,此论较胡彬夏仍将家庭中的责任偏重于女性一方的论述更进一步,甚至可以视为“改良家庭论”理论的巅峰。然而,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性别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上述观念仍只能停留在假想的空间中,而反观胡彬夏的“改良家庭论”,尝试完成家庭场域与国族场域的对接,则更合乎、切近于时代语境的内在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重视女子教育与启蒙,胡彬夏对于现代“儿童学”知识的引进,从“传统”的蒙学教育跻进“现代”的科学教育,是为儿童教育的里程碑。1910年代初期至“五四”前夜,知识界有关如何认识儿童的特质、认识儿童的方法、发展儿童的天性等零星的讨论,亦浮出“历史地表”。在这些论述中,父母亲与孩童之间不再谨守五伦中的“父子”关系,儿童之于成人的尊卑区隔渐趋被打破。提倡儿童之职务应由儿童自得自择,非成人所当越俎代庖,尊重儿童天性、去“成人化”眼光之声不绝于耳[41]。儿童作为成年世界的“从属者”,开始转向“儿童中心”、“儿童本位”的角色。
如果以周作人对启蒙思想的论述观之,“妇女启蒙”到“发现儿童”——从20世纪之初到“五四”发生,20年的历史相隔,恰好印证了从“人的发现”到“妇女的发现”,再到“儿童的发现”这一人类启蒙史上的演进轨迹。
[参考文献]
[1]美国最新之地方自治机关[N].申报,1916-07-19(3).
[2]朱胡彬夏.基础之基础[J].妇女杂志,1916(8) : 1-12.
[3]湖南公报.女德与家庭[J].东方杂志,1915(6) : 40.
[4]彬夏.何者为吾妇女今后五十年内之职务[J].妇女杂志,1916(6) : 1-5.
[5]彬夏.美国家庭[J].妇女杂志,1916(2) : 1-7.
[6]改良宴会之食品[M]∥徐珂.清稗类钞: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6: 6295.
[7]公布褒扬条例令[M]∥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全集:二十五.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472.
[8]教育总长汤化龙谈女子教育[M]∥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713.
[9]节录施淑仪女士来书,节录复施淑仪女士书[J].妇女杂志,1916(4) : 1-4.
[10]胡彬夏.杂说五章[J].留美学生年报,1911(1) : 1-16.
[11]彬夏.二十世纪之新精神[J].妇女杂志,1916(7) : 1-5.
[12]朱胡彬夏.二十世纪之新女子[J].妇女杂志,1916(1) : 1-13.
[13]无锡胡彬夏女士天足社演说稿[J].女子世界,1907( 4、5合期) : 122-124.
[14]幼稚研究会开会纪事[N].申报,1916-06-26(10).
[15]胡彬夏.赴第三次万国儿童幸福研究会报告书[M]∥陆阳,胡杰.胡彬夏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15: 68-73.
[16]朱胡彬夏女士演说训练儿童法[J].环球,1917(4) : 6-8.
[17]彬夏.脑筋与肌肉的教育[J].妇女杂志,1916(11) : 13-19.
[18]彬夏.蒙得梭利教育法[J].妇女杂志,1916(3) : 1-8.
[19]学生会欢迎新会员纪事[N].申报,1917-11-05(10).
[20]演讲生育进化之要旨[N].申报,1917-11-27(10).
[21]蔡洁.清末民初历史与文学中的“英雌”话语研究述评[M]∥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燕园史学:十.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91-106.
[22]赵连成.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
[23]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续篇[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33.
[24]吕碧城女士辞职案[M]∥张玉法,李又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台北:龙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 1446.
[25]张竹君以南市上海医院推归公办通告[N].申报,1916-04-02(1).
[26]天武.女子参政问题[N].亚细亚日报,1912-08-10(1).
[27]梁启超.变法通议三之四·女学[J].时务报,1897(23) : 2.
[28]冰心.“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M]∥卓如.冰心全集: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5.
[29]冰心.两个家庭[M]∥卓如.冰心全集: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11-19.
[30]冰心.别后[M]∥卓如.冰心全集: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136-139.
[31]冰心.悼沈骊英女士[M]∥卓如.冰心全集: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605.
[32]冰心.关于女人[M]∥卓如.冰心全集: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517.
[33]冰心.第一次宴会[M]∥卓如.冰心全集: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252-260.
[34]郭冰茹.“新家庭”想象与女性的性别认同——关于现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考察[J].文学评论,2009(3) : 48-52.
[35]凌叔华.绮霞[M]∥郑实.凌叔华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 64-78.
[36]陈哲衡.洛绮思的问题[M]∥陈衡哲.小雨点.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64-83.
[37]庐隐.补袜子[M]∥庐隐.庐隐小说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 685.
[38]陈哲衡.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M]∥陈衡哲.衡哲散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74.
[39]蜀龙.新贤良主义的基本概念[J]妇女共鸣,1935(11) : 9-14.
[40]峙山.贤夫贤妻的必要条件[J].妇女共鸣,1935(11) : 15-19.
[41]柯小菁.塑造新母亲:近代中国育儿知识的建构及实践( 1900—1937)[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133-140.
[责任编辑:张文光]
Hu Binxia and the Female Statements of“Family Reform”: Along with the Origin of“Family”Concept in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GAO Xiang-yu
( Department of Histor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Hu Binxia,a female elite studying in US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distinctively put forward her female statements on“family reform”,involving the relation of family reform with social reform,female morality,female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ldren and so on.“Family reform”not only became a unique landscape in the history of female enlightenment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but more importantly implied the origins of such concepts as the family and women,the female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mother and children in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From the ideological thread of“female enlightenment”to“discovery of children”,Hu Binxia properly provided a typical template for interpreting the evolving course of“human discovery”as well as the educational ecology for women and children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Key words:Hu Binxia; family reform; fame statement;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family”concept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6) 02-0126-06
[收稿日期]2015-11-26
[作者简介]高翔宇( 1989-),男,辽宁锦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初政治与近代中国妇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