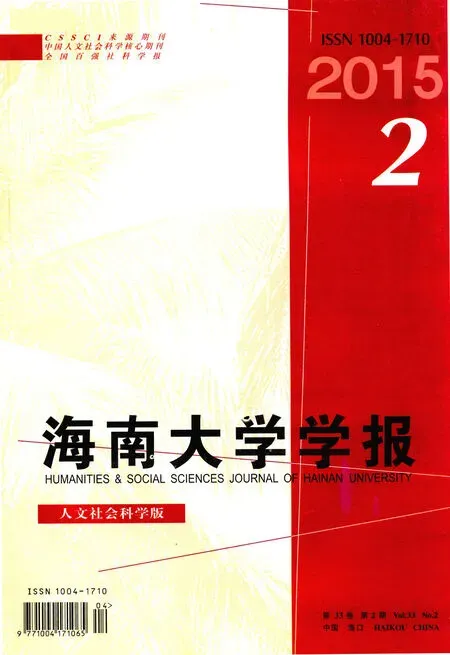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2016-03-06胡良益潘天波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徐州221009
胡良益,潘天波(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徐州221009)
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胡良益,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徐州221009)
[摘要]依托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输出与文化传播,清代漆器文化被广泛地介入欧美世界,并在各国发生阅读、体验与审美想象,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欧美人眼中的他者漆艺想象。但伴随18世纪后期海外漆器文化被中国引进,中外漆器艺术已然开始出现一种不倦的文化环流现象。在此消彼长的中外文化体认、溢出与耦合中,被传播的中国漆器文化显示出全球视野下的他者想象与环流现象,正是通过具有并世功能的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得以实现。认识并把握丝路文化的他者想象与环流特征,对于当代“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战略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清代;海上丝绸之路;漆器文化;想象;环流
一、时代背景要素
中国清代漆器文化发展步入历史的巅峰,就社会语境而言,其发展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及文化消费等背景要素。
在制度层面,清顺治时期国家开始废除世袭匠籍制度,实施“按工给值”的雇工制度。据史载:“凡工匠物料,动支正项,销算公帑,俱按工给值。”[1]这样不但减轻了工匠负担,还解放了户籍对手工业者的束缚,从而释放了手工业者的创造力。因此,清代漆器工匠的创新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各门类漆器的发展均走向真正的自主创造之路。
在经济层面,清初国家重视民生与经济,在全国推行务农养民善政。特别是康熙、雍正与乾隆年间,漆器、瓷器等手工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南方一批中小型城镇在明代商品经济萌芽基础下也真正走向手工业城镇的发展道路。《刘基集》曾载“虞孚卖漆”[2]的故事,这段文献不仅反映吴越间生漆贸易及“吴人尚漆”之时尚,同时“漆膏数百瓮”与“金币取漆”还反映吴越生漆产量之大,且十分贵重。同时,在当时徽州流传“吴茶周漆潘酱园”的俗语中,也可看出安徽周氏漆业在清代首屈一指,“周漆”乃是清代徽商响亮的漆器品牌。
在消费层面,清代帝王及士大夫对漆器格外推崇,极大地刺激了漆器飞速发展。张荫桓在日记中描述:“(光绪二十年)前日慈宁宫筵宴蒙太后恩赏福字、白玉如意、铜手炉、磁花瓶、江绸袍褂、帽纬、荷包、漆盘共八色,向系宴毕分给桌上,所谓‘盘子赏’也。”[3]457可见,清慈宁宫筵宴太后将漆器作为给予臣子“盘子赏”,这反映皇帝对漆器的看重以及漆器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乾隆皇帝对雕漆十分痴迷,还亲拟许多设计方案,帝王的审美情趣对漆器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另外,18世纪法国宫廷“中国风”席卷欧洲世界,西方国家对中国漆器、瓷器的消费需求也大大促进了中国地方包括漆器在内的手工艺发展。
二、清代海上丝路漆器的贸易输出
贸易是清代漆器文化外溢的主要手段。清代港口漆器贸易除传统东亚航线、南洋航线以及南亚、西亚等海上航线之外,还开通了欧美海上航线。东南沿海各大港口均有漆器、漆家具及漆装饰物的对外销售与出口,江苏、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中外海上漆器贸易极其频繁。
传统海上航线除开通“福建—台湾—吕宋”、“广州—万山群岛—吕宋”、“广州—万山群岛—雅加达”的海上贸易航线[4]外,还有“广州—曼谷”、“广州—真腊”的海上贸易航线。据档案载:“1813年,去中国贸易的暹罗船只共26只: 7只到广州,4只到上海,7只到宁波,5只到潮州,3只到天津。”[5]《瀛环志略》也谈及清廷与真腊的海上贸易:“闽广商船,每岁往来贸易”[6]。这些商船运去金、银、丝绸、锡、漆器、瓷器等物大都为日常生活用品。清廷商船在真腊受到优待与这些闽广商船运去的珍宝有关,其中不乏漆器。
清代欧美航线主要以南京、厦门、广州、泉州等港口为依托,与海外进行漆器出口贸易,广州港是当时最为繁忙的国家性大港。美国人赖德烈在《早期中美关系史( 1784—1844)》一书中如是描述:“l784年2 月22日‘中国皇后’号带着国会颁发的一张船证作保护而出发了。该船在威德角群岛停下来,储备了淡水和作了修缮,绕过好望角,然后直向巽他海峡驶去。在巽他海峡,它碰到一只法国船并和这只船一同去中国,于8月28日碇泊于广州的港口黄埔。”[7]可见,早期第一次来华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的航海路线是:纽约—威德角群岛—好望角—广州黄埔。明以来海禁海关政策使得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受到一定限制与影响,但广州港一直以来是欧美人与中国海上贸易的重要贸易中心。瑞典人龙思泰在《中国的货栈》中也提及:“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广州),各省的商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马六甲或马来西亚、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8]可见,广州港是通往欧美的主要贸易基地,清代漆器、瓷器等货物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出。
(一)从“迁海令”到开放广州港
18世纪中后期,东南沿海抗清势力蠢蠢欲动,顺治十八年( 1661年)清廷颁布“迁海令”,强令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居民内迁,以绝海上贸易而瓦解抗清势力,尤其是断绝他们的财源。“迁海令”对于沿海商业、手工业的打击是沉重的,特别是对于海上丝路贸易体系的摧毁引起国内外人的反对与斗争。
法国人布罗斯在《发现中国》中坦述:“当时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之高潮中的英国人,试图打破这一枷锁。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逐渐变得对他们成为一种生死攸关之必要了。他们不再仅仅是为了寻求丝绸、瓷器和漆器了,尽管随着18世纪之豪华风气的发展,使这些商品的需求也大幅度地增加了。……在同一阶段,于广州靠岸的欧洲船舶总数,每年从10多艘增长到40多艘,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英国船。被由中国对其交易制造的障碍激怒的商客们,把经商变成了一种国家事务。”[9]布罗斯的描述隐含18~19世纪英国及英国人对中国海上贸易的立场:首先,18世纪在法国宫廷刮起的“中国风情”使得欧洲宫廷奢华风气迅速蔓延。因此,中国漆器、瓷器等奢华商品需求量激增。18世纪广州“十三行”所经营的广州彩瓷、温州漆器之所以成为欧洲人消费对象,不仅是瓷器、漆器能显示英法贵族的身份与财富,更多的是这些器物的奢华美学迎合了他们的审美趣味。其次,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家经营海上贸易权利是巨大的,“三分之二是英国船”暗示英国人对与黄金等值的瓷器、漆器之贸易权绝对处于垄断地位,当时江南漆器以及景德镇瓷器几乎成为欧洲人的精神符号。再次,对于英法等国来说,“迁海令”已然上升到国家事务,因为他们不仅迫切需要中国提供漆器、瓷器等这些为之迷恋的商品,更迫切需要进入中国内地“盗窃”制瓷与制漆的秘方。最后,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这显然是一种障碍。于是,“他们不再仅仅是为了寻求丝绸、瓷器和漆器了”,这暗示18世纪后期英国人对于中国瓷器与漆器出口不再是主要贸易对象了,因为这个时期英国人已经开始仿制中国漆器与瓷器。1791年英国人对进口中国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于是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它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
据统计,自1655年清廷前后曾5次颁布海禁政策,3次下诏“迁海令”,严重影响商民海上贸易。但实际上,在清廷“迁海令”下,国家并没有取得“坚壁清野”的预期效果,反而使得海外势力更加嚣张,国内社会经济也遭遇极大破坏。
(二) 17世纪东印度公司贸易下的中国漆器
处于扩张和资本积累时期的英国为了在东印度地区掠取大量资源与原料,在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1613年在印度苏特拉设立贸易站。1602年荷兰人征服印尼,驱逐当地葡萄牙人,也成立东印度公司。英国、荷兰等国多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逐步渗透进而达到对当地实行殖民统治,并将触角延伸到清廷的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领域。
17世纪东印度公司的组建与发展暗示荷兰、英国等航海资本主义大国的崛起。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与控制了海上贸易,但到1780年英荷战争之后,英国成为海上霸权国家。贡斯当在《中国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中写到:“法国驻穗的官方代表必须与东印度各部分的公司保持通讯联系,……广州的买家必须了解整个中国:中国的国内贸易、奢侈消费品、生活必需品、丰年与歉年、出口商品与食品、发生了饥荒的省份、灾荒具有普遍性还是仅袭击了该帝国的部分地区。”[10]贡斯当的回忆录不仅再现英国人在广州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还反映当时法国人投资东印度的一些细节,特别是广州买家必须了解清朝国内贸易以及漆器等奢侈消费品。
与荷兰、英国相比,法国在华贸易相对滞后。1664年法国为监管非洲、印度以及印度洋其他岛国的贸易,设立法属东印度公司。1685年路易十四与清廷开始交往,1698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昂菲德里特号”在拉罗舍尔港起碇驶向中国,进行海上漆器、瓷器等贸易活动,1701年“昂菲德里特号”再次来华贸易,1703年该船满载中国漆器、瓷器等大宗货物返航法国,以至于后来法语把精美的中国漆器直接称为“安菲特里忒”。在乾隆八年至二十一年( 1743—1756年)间,法国商船来华贸易极其自由与频繁,中国大量奢华漆器、瓷器被运往法国宫廷以及普通人生活空间。
精美漆器引起西方人的仿制与想象,法国奥古斯都曾让炼金家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和学者瓦尔特·冯·奇思豪思仿制中国瓷器。但西方人在仿制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前后共摸索300多年,到18世纪才学会烧造陶瓷。西方人不仅想仿制中国漆器、瓷器,还对中国漆树移植感兴趣。在18世纪之前,英国人曾想象在殖民地孟加拉种植漆树。I·普理查德在《英东印公司与来华大使马卡特尼通讯录》中记载:“吾所获数种在发育中之植物,倘能小心培养,将必大茂,吾拭目以观,不禁大乐,故吾既得此数种植物之后,立交使团中一科学家丁维提博土( Df.hroes Dinwiddie)看管,此人余特为此项目的而选其随使者也,同时使即送至孟加拉总督索尔爵士( Sir John Shore)处。吾又趁此机会将脂树及漆树等数种植物,方在发育状态者,一并送往,每种种植在孟加拉必有利焉。”[11]217可见,东南亚国家的大漆资源丰富或许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相关。
除了东印度公司漆器海上贸易之外,清廷还通过“赏赉”或“恩赐”方式赠予漆器给海外使臣。据《清朝柔远记》载:“(清雍正五年夏四月,葡国)遣使臣麦德乐表贡方物抵粤。巡抚杨文乾遣员伴送至京,召见赐宴。于赏赉外,特赐人参、缎匹、瓷漆器、纸墨、字画、绢、灯、扇、香囊诸珍,加赏使臣,旋命御史常保住伴送至澳,遣归国。”[12]张荫桓在日记中曾写到:“(光绪二十四年)十七日己卯( 7月15日)晴。晨起,为日本使矢野送行,承以紫漆砚、银为别,意良殷也。”[3]544张荫桓在日记中还写到:“(光绪十五年)十一日丁亥( 3月12日)晴。……承赠漆盒、棉纱袜,皆其土产,又映相一帧,纳交之诚甚切。”[3]370这说明,欧洲、东亚以及中东人对这些“异域之花”的瓷器、漆器迷恋之极,并把得到清廷赏赐漆器视为珍宝。
(三) 18世纪“昂菲德里特”商船与中法漆器贸易
路易十四以来,中国漆器被源源不断地输入法国宫廷。中国漆器之美成为法国宫廷、富人以及官僚们各自炫耀的对象,弥漫法国宫廷的中国情调很快被他们接受与迷恋,中国式高贵与典雅也很快影响到法国贵族们的生活理想与审美情趣。
随着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时代的到来以及工业革命的兴起,法国社会城市与农村发展进入快车道,资本主义工商业势力迅速抬头,终于在17世纪殖民扩张的基础上迎来了路易十五时代——法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潮。“1698年第一艘法国船‘昂菲德里特’号来华,1701年它第二次东行。两次远航从中国运去大量包括漆器在内的工艺品,中国精美的漆器受到欧洲人的普遍喜爱,法语因之把漆器称为‘昂菲德里特’( Amphrityite)。一时间穿丝绸衣服、摆设中国瓷器和漆器成为法国流行的风尚。”[13]298-29918世纪30年代,罗伯特·马尔丹曾受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的邀请,专门为她的城堡制作漆器,漆器也成为蓬巴杜夫人显示财富与地位的物品。
令法国宫廷神魂颠倒的中国漆器、瓷器等物品,使得中法海上贸易异常活跃。法国在1660年成立中法贸易的“中国公司”,到1700年又组建第二个“中国公司”,后改组为“皇家中国贸易公司”。1712年又新成立“皇家中国贸易公司”,该公司先后派出3艘商船来华进行海上贸易[14]。大量的中国漆器、瓷器运往法国,在法国家庭设立装饰有中国异域情调的“中国室”成为当时的生活时尚。为满足法国宫廷贵族消费,法国也开始规模化仿制漆器。“法国的漆业,居于欧洲的首位,马丁( Martin)一家不久就成为漆业的中心。马丁一家共有兄弟四人,其中最重要的为罗拔·马丁( Robert Martin),他在制漆技艺方面有卓越的成功,得到滂巴沱夫人( La Pompadour)的青眼。”[15]法国对中国漆器从迷恋到仿制已然昭示中国漆器艺术对法国人的影响是深刻的。
(四) 18~19世纪“中国皇后号”商船与中美漆器贸易
大约在17世纪初,中国漆文化被英国人带到美洲,美国工艺家在继承英国漆艺文化基础上开始本土漆艺制造。1784年,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派出“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中国,开启中美最早海上商业贸易。从此,中国漆器及其文化被大量输入美国。
1784年底返回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带回的布匹、丝绸、茶叶、漆器、瓷器等物品令美国人争相购买。美国人卡尔·L·克罗斯曼在《中国贸易:出口绘画、家具、银器及其他产品》一书中写到:“虽然Jr·杜德利·皮克曼极大部分投资于丝绸,但是他似乎更关心他的小订单,在他信里,首先最重要的是两套漆器托盘或碟子,这些漆碟尺寸固定,每套六个。一套给他自己,另一套给他朋友。”[16]185可见,美国人对中国漆器的爱好与需求。“中国皇后号”商船不仅为美国民众带去了中国艺术品,更带去了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他们对中国漆艺需求从一开始的漆器,到后来的漆家具、漆扇子、漆橱柜、漆桌椅等各种中国漆艺产品。譬如1800年,在Minerva商船上运有5箱漆器。1815年来广州的“新冒险号”,漆器商提供了两对果篮,与之相匹配的6打果盘,5个茶盘。1816年“波斯顿鞑靼号”发货清单上有51美元的60个茶盒、25美元的10个茶盒、每套10美元的decanter stands35套、1个女士高级梳妆镜等[16]195-196.这些中国漆器无疑给美国人的消费及其生活方式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因为它已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漆器,它的身上烙有中国的文化与美学思想。
三、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的他者想象
康乾盛世时期漆器艺术被广泛输入欧美,并在各国发生阅读、欣赏与审美,来自异国的“他者想象”是一种吻合东方中国文化的想象。欧美的“中国想象”在漆器领域中呈现出来的古典中国以及异国情调具体而微地再现了中国大漆之美。
(一)诗人普赖尔的中国漆艺想象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法等国商舶从印度孟加拉湾的科罗曼德海岸将中国漆器运至欧洲各国,因而在欧洲中国漆器又被称为“科罗曼德漆器”。中国漆器文化嵌入欧洲社会的发展,不仅起到了传播与弘扬中国优良文化之目的,还为世界漆器发展提供了契机与范例。18世纪英国漆艺产业进入发展鼎盛时期,英国人托马斯·阿尔古德和其子爱德华,伯明翰人约翰·泰勒、约翰·巴斯泰克维勒和丹尼尔·米尔斯等均是英国著名制漆高手。1680年英国的家具商开始仿照中国的漆艺,大量生产漆艺家具。
1700年诗人普赖尔对中国漆橱柜之美十分神往,他写下诗句:“英国只有一些少量的艺术品,上面画着鸟禽和走兽。而现在,从东方来了珍宝:一个漆器的橱柜,一些中国的瓷器。假如您拥有这些中国的手工艺品,您就仿佛花了极少的价钱,去北京参观展览会,作了一次廉价旅行。”[17]普赖尔对中国“漆器的橱柜”的赞美道出一个事实:第一,18世纪英国人仿制中国漆艺家具之前,“英国只有一些少量的艺术品,上面画着鸟禽和走兽”,但1680年之后的英国家具商开始仿造中国的漆艺家具,采用中国生漆涂髹家具,并精于雕刻各种图案,包括中国式的龙凤、宝塔、花卉等。一股中国风情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成为时尚,并反映中国审美情趣在英国生根发芽。第二,18世纪的中国漆艺精于装饰,并具有绘画性,特别具有“故事性”情节。以至于你欣赏“一个漆器的橱柜,一些中国的瓷器”之后,“您就仿佛花了极少的价钱,去北京参观展览会,作了一次廉价旅行”,这充分说明这个时期漆器图案能反映中国社会风情和社会状况。换言之,18世纪中国漆艺具有绘画叙事功能。第三,“东方来了珍宝”与“您拥有这些中国的手工艺品”等描述体现出诗人普赖尔对中国漆器艺术的惊叹与欣赏,特别能感受到普赖尔对中国漆艺的钦佩与陶醉。实际上,通过文学诗歌的方式描述对中国漆艺的感受,不仅体现出西方人不自觉地接受并认同了中国艺术及其美学思想,更反映出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
诗人普赖尔对中国漆器艺术的审美体验不是孤立的,中国漆器与瓷器一样,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品性与艺术风范。英国人米歇尔·康佩·奥利雷在《非西方艺术》中这样评价中国的工艺品:“与书画艺术一样,中国瓷器的美与中国人高雅的品味有关,并且他们还经常在瓷器上创作精美的绘画,这无疑又提升了瓷器的价值。”[18]这就是中国工艺文化的魅力,也是欧洲人为之迷恋的关键。
(二)伏尔泰、歌德与雨果对中国漆艺的想象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与“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伏尔泰对中国漆器艺术十分神往,对包括中国漆器在内的工艺品给予很高的评价。
一向赞扬东方文化和文明的伏尔泰,在《尔汝集奢》中,对法国工业的新成就表示出他的喜悦:“马丁的漆橱,胜于中华器。”[19]28同样,“18世纪中叶以后,爱好漆器的风尚也传入德国。德国艺术家施托帕瓦塞尔( Jahann Heirich Stobwasser)开始出售漆器,上面绘制中国的人物和风景。他在不伦瑞克成立了一家漆器厂,生产上漆的鼻烟壶。”[13]298-299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叶,中德文化交流处于高峰期。“他(歌德)生活的时代,欧洲仍然处于中国强大的文化影响之下。在法兰克福的诗人故居二楼被命名为‘北京厅’的主厅里,至今仍能看见古色古香的中国式描金红漆家具和瓷器,墙上挂的是印有中国图案的蜡染壁画。”[20]可见,歌德对中国漆器艺术的欣赏与爱好。
1791年歌德撰写《Gross-Kophta》一剧,因欲收光怪陆离之效,布景时用中国物品。1790年左右,歌德有一首威尼斯短诗,诗中把浪漫情味和中国人扯在一起:“纵使中国人,以其工致笔,绘维特及绿蒂于玻璃镜上,于我有何益?”1796年,他又作短诗《罗马城的中国人》曰:“我昔在罗马,见一中国人。一切建筑物,无论古与今,在彼心目中,粗俗且沉沉。喟然长叹息,‘汝等可怜人,奈何不三思。文木可作柱,屋顶赖支持。纸皮兼木板,亦可漆银朱。触发文明威,令人喜可知。’惟我觉其人,审美徒支离,遐想入非非,谓可侔造化。”[19]199从这里也可见出歌德对中国漆艺的印象,也能见出他对东方人的浪漫与优雅持有一种肯定态度。
1681年11月25日,雨果在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这样评价:“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的一切都荟集于圆明园。……艺术大师、诗人、哲学家,他们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也曾谈到它。”[21]圆明园是中国集建筑、园林、漆艺、绘画等于一体的皇家园林,雨果以及伏尔泰对圆明园的想象或许能反映出他对中国艺术的美学想象与赞美。
漆艺最能表达中华民族的艺术创造魅力与文化想象力,它引起西方的哲学家与美学家的赞誉与欣赏体现中华艺术的世界性传播力及文化力,西方人接受中国漆器艺术的“洗礼”意义是深远的,他们对中国漆器艺术的审美体验也是独特的。
(三)杜赫德对中国漆艺的想象
18世纪30年代,神甫杜赫德对中国漆艺之美多有溢美之词,他在《中华帝国通史》中指出:“从这个国家进口的漆器、漂亮的瓷器以及各种工艺优良的丝织品足以证明中国手工艺人的聪明才智。……如果我们相信了自己亲眼看到的漆器和瓷器上的画,就会对中国人的容貌和气度作出错误的判断。……不过有一点倒没错,美在于情趣,更多在于想象而非现实。”[22]杜赫德道出了中国漆艺之美的艺术特征:“美在于情趣”。
杜赫德的审美体验与美学判断至少体现出以下几点中国漆艺之美的要义:第一,“美在于情趣”——生活的情趣。中国漆艺是生活的漆艺,与生活息息相关。漆器上的绘画通过中国画的方式展现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其社会场景,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艺术的“神似”,这与西方绘画的“现实之情趣”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漆器图案取材于自然、山水以及动植物,旨在提升生活的审美情趣,漆器也因此成为中国人优雅气质的载体,并浓缩于生活之中。第二,“美在于情趣”——工艺的情趣。中国漆艺之精雕细刻,足以“证明中国手工艺人的聪明才智”,漆器将工艺与绘画、雕刻、镶嵌、书法、诗歌等诸多艺术融于一体,在不同背景中,漆器图案有人物活动、神话故事、亭台楼阁、山水流云等,其层次分明、结构完美、凹凸有意,无不体现出工艺人的审美情趣与高超水平。第三,“美在于情趣”——手与心的情趣。对于漆艺而言,手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手就没有漆艺。漆艺的情趣就在手与心的完美结合。中国漆艺人通过他的双手与朴素的中国思想建立联系,漆艺之手开采着中华思想的矿石,并赋予这些矿石以独特的形式或风格。第四,“美在于情趣”——想象的情趣。神甫杜赫德所言“美在于情趣,更多在于想象而非现实”,指出了中国漆艺想象创作的基本规则。艺术想象对于漆艺意象表现具有决定作用,如何将山水、楼阁、故事等表现于一个很小的空间,很明显,联想、形象以及情感是艺术想象所必须的,它能将叙事性画面藏于漆器画面之中。第五,“美在于情趣”——休闲的情趣。“美在于情趣”不仅指向内在的审美体验,还更多地指向漆艺手工创作的特有情趣——“休闲”。神甫杜赫德指出:“一件上好的漆器应该在悠闲中完成,整个夏天都不足以使它尽善尽美。”中国漆器多为贵族漆器,皇家是不计成本的,更不计时间。漆器在漆工“休闲”中实现它的尽善尽美。
从神甫杜赫德“美在于情趣”的审美判断,可以窥见他对中国艺术的理解与钦佩,并被中国漆器艺术所陶醉与迷恋,更反映中国漆器艺术的美学特征。
(四)清代漆艺在拉美家庭中的想象
中国“丝船”,拉丁美洲称“中国之船”,经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将中国漆器等工艺品行销拉丁美洲各地,并深刻影响拉美人的工艺发展及其家庭生活。
沙丁等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中援引清代张荫桓杂在《三洲日记》卷5中的描述:“查墨国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瓷漆等物。”[23]在19世纪初,中国漆器文化沾溉由美国远及墨西哥,特别是墨西哥虽然受当时“表现理想社会艺术”的影响,但“民众仍然非常喜欢组画、漆器、宗教仪式用的面具和龙舌兰酒店的壁画等这些乡土作品。”[24]296墨西哥著名画家西凯罗斯颇受中国漆画艺术影响,“在运用源于哥伦布到达以前时期雕刻的人体形态方面,西凯罗斯显示出娴熟的技巧。他喜欢使用新型材料作画,如加漆的颜料。洛杉矾艺术中心广场的几幅优秀壁画就出自西凯罗斯之手。”[24]29919世纪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北安第斯国家厄瓜多尔的基多人特别喜欢仿制中国漆艺雕像,“中国在雕刻方面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雕像使用玫瑰红的颜色上,而且也表现在使用描金技术上,……基多人特别想模仿东方的上漆方法并按照中国风格的配色使用红色、蓝色和绿色”[24]293。厄瓜多尔的基多人的工艺在刻刀、用色及其髹法上明显受到中国漆器技法的影响。
四、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的世界环流
清代漆器以特有的“中国风格”在欧美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追慕与迷恋,被传播到欧美的漆器符号所体现出来的“他者想象”也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海外漆文化也在清代流向中国,特别是以“倭漆”与《垸髹致美》为代表的海外漆文化被输入中国,一股不倦的漆器文化环流现象产生了。
(一)清代漆器文化流向欧美世界
在英国,为得到异域的漆器与瓷器,他们的商船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而专门贩卖异国趣味。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结束语”之“异国趣味的贩卖者”条这样描述:“马戛尔尼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专贩异国趣味的商人,他除了供给英国人茶叶、丝绸、漆器、瓷器外,还满足他们到远处冒险的梦想,从中得到某种乐趣。”[25]除此以外,17~18世纪的海上丝路漆器贸易作为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对话,对英国宫廷装饰及其文化发生很大影响,中国漆艺及其表现的中国风情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特别是在家具陈设、建筑等层面的影响十分明显。L·W·哈克尼在《西洋美术所受中国之影响》中指出:“英国威廉( William)及马利( Mary)朝家具,已早受其影响,甚至今日吾人所用家具,犹未能脱尽华风,契彭得尔( Chippendale)及虾披威( Heppelwh-ite)家具之直接受中国之影响,又何待言。”[11]136可见,中国漆饰家具作为英国皇家的开奖之物,尤能显示华风家具在异域的礼遇与珍视。另外,在英国,奇彭代尔根据中国的样品制作家具,也极大地推动一种中国式家具在英国的流行。18世纪英国建筑风格受清代建筑风格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屋宇、宫殿、亭台、花园等设计领域均能见出中国建筑的影子。
在法国,17~18世纪中国漆器被大量输入法国,当时漆器仅次于瓷器被法国宫廷所喜用,特别是被宫廷贵族所迷恋,漆器成为他们炫耀财富的象征。为了大规模地使用中国式的漆器,很快仿制漆器的工业在法国社会兴起。“到1730年,漆柜、漆盒和其他油漆家具先后问世,甚至可与中国生产的漆器相媲美。如同欧洲的瓷器一样,这种漆器几乎也是模仿中国的图案。”[26]为装饰有人物与花卉图案而着迷的法国贵族视中国漆器为“特殊而罕有的物品”。18世纪流行于法国宫廷的“洛可可艺术”与中国的漆器风格十分类似:中国漆器重视自然景物的图案装饰,“洛可可艺术”也特别能将螺钿、山石、金银作为装饰题材,特别是吸收明清时代漆器图案重视卷草舒花的装饰偏向,以至于西方人认为:“提起罗柯柯,在我们心目中,构成为一个幽美动人的可爱的世界;恍如听见诗歌剧中的旋律,……华贵客厅中的壁镜及漆橱,互相辉映,令人目眩。”[19]66可见,令法国宫廷贵族神往的漆器艺术风格与他们的“洛可可风格”近乎一致,或“洛可可风格”是一种中国式的漆器风格。应该说,明清时期漆器的纤巧与奢华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法国路易十四以来的法国趣味,当法国人厌倦了严肃、古板的巴洛克艺术的时刻,中国艺术那种既亲近自然,而又不失奢华的美学趣味走进了法国宫廷。
与欧洲相比,美国与中国的海上丝路贸易要迟得多。自从18世纪以后,美国与中国建立正常的海上丝路贸易,并大规模从中国的广州港以及南京等地区进口中国漆器。美国的普通家庭也因此拥有了来自中国的漆屏风、漆家具、漆器皿以及瓷器和丝绸等,一些中美贸易商的家庭更是大量藏有中国漆器等。美国人乔纳森·戈尔茨坦指出:“假如说旁观者已被早年美国家庭里中国海景的现实所迷惑,那么,拉蒂默书房里展示的东西更会使他大吃一惊,中国的瓷茶杯、茶杯碟、奶壶、茶壶、糖盘、茶几,以及茶叶罐,每件东西都绘有彩色的‘广州’或‘南京’边纹。……洗脸架上还放着一些耀眼的紫色和金黄色的中国漆制盥洗用具。”[27]美国人所拥有的漆器意味一种财富,更意味一种自豪。与其说,他们在消费中国漆器,不如说他们在体验中国美学。在美国的许多博物馆、收藏家那里,至今还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漆器家具,包括清式座椅、橱柜、梳妆台、屏风等。在18~19世纪拥有“中国式房间”成为美国人的一种情趣与时尚。根据《中国贸易》记载:“威廉莫斯堡的那些沙发明显就是中国的木材和中国的制作工艺。它的设计优美……另外还有两个类似的沙发,一个在温特苏尔,另一个在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总部,它们在结构和设计上纯然一致,但它们分别用黑漆,应用像漆器家具的金色葡萄叶装饰。”[16]188-189即便是19世纪后期,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的房间也充塞中国风格的家具[16]188,并以此为财富与荣耀的象征。明清时期,中国皇帝对屏风的酷爱以及大量生产,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与喜爱,尤其是具有中国绘画叙事特征的漆屏风激发了美国人的想象与美学情趣。
在德国,柏林的蒙彼朱宫街存有一本旧指南书,记载当时所藏关于中国文物饰物珍品,目录中提到下面的藏品:“……十一、中国式黑漆的房子一间。……二十四,瓷器陈列室,有精雕的紫漆木器。”[19]66这说明中国风味的漆器艺术占据德国人的建筑空间。G.F.赫得森在《罗柯柯作风——西洋美术华化考》中指出:“漆器初亦受华漆之影响,其家具多用漆器,亦采中国之作风及模仿。十八世纪欧人之漆器,实难办何者为袭自中国者也。”[11]154德国人对中国漆器艺术的欣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风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以及美学理想。
在罗马尼亚,人们对中国髹漆游船与建筑大加赞赏。1677年前后,罗马尼亚学者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来到中国,他在《中国漫记》中这样描述:“由国库开支建造了许多海船、内河航船和官吏乘坐的楼船,其精巧与豪华,若非亲眼见到,……门窗精雕细刻,漆得金碧辉煌。”[28]63米列斯库对中国漆船的审美体验是独特的,特别是对“漆得金碧辉煌”的描述反映出中国漆器艺术的装饰性、情趣性与绘画性的美学特征。米列斯库来到中国的“红城”(紫禁城),他这样描述道:“宫中所有的建筑均用黄色——皇帝的标志——琉璃瓦盖成。木制品都是镏金的,或髹以别的色彩,表面再涂一层中国漆。”[28]88中国“红城”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近乎是一座漆彩的宫殿。
(二)清代海外漆艺文化环流中国
一直以来,中国漆器输出是一种常态,但17~19世纪“洋漆”开始输入中国,并被中国皇帝所喜爱。从漆器文化的输出国向输入国的转变,反映中国漆器文化被海外国家所接受,更反映海外漆器技术已然超越中国漆器技术。张岱在《陶庵梦忆》记载:“朱氏家藏,……余如秦铜汉玉、周鼎商彝、哥窑倭漆、厂盒宣炉、法书名画、晋帖唐琴,所畜之多,与分宜埒富,时人讥之。”[29]可见,一开始人们对于拥有“倭漆”时人讥之,但是随着日本漆器的大量输出,中国对倭漆的态度也发生新的变化。清代皇家御用品均由宫廷造办处督造,雍正初期,雍正皇帝主要是委托怡亲王负责办理漆器制作的有关事项,如给造办处一件洋漆双梅花香几,怡亲王又交给造办处一件洋漆小圆盘,造办处于四月二十九日做得洋漆小圆盘八件等[30]。明代时由东洋日本传入,即用金粉和大漆调合后涂绘于漆器上的一种装饰技艺,故得名“洋漆”。清雍正、乾隆年间是洋漆生产的鼎盛期,清宫廷内“造办处”就设有“洋漆作”专门生产洋漆器。从对“哥窑倭漆”的讥讽,到清廷造办处的“洋漆作”,可以看出,中外漆器文化的交流是互动的。
在国家层面上,晚清社会引进美国髹漆文本《垸髹致美》,它的背后隐喻一部全域式的知识社会学。它既是晚清洋务思潮、发展工商业与奢华消费的征候,又是社会发展实业、学习新知识与注重科学的产物。从社会背景上看,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廷讲求时务、提倡西学蔚成风气。在洋务大臣的眼里,“美以富为强”。富有省思的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均认为:“(美国技术)最新,距华最远,尚无利我土地之心。”[31]清光绪25年( 1899年)小仓山房石印本《富强斋丛书正全集》汇辑有关西学之译著八十种成此编,以备求强救国者采撷。该丛书涉及漆学的有1884年刊行的美国髹漆文本《垸髹致美》[32],内容涵盖东洋漆的种类、配方及上漆工艺。可见,《垸髹致美》是西“漆”东进的时代产物,其知识语境与中国“洋务”思潮有密切关系。从技术语境上分析,引进《垸髹致美》实则反映晚清社会对西方新技术知识的需求。在晚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选译书的原则有三条,它们是:第一,选最近出版的新书和名著,即‘更大更新者始可翻译’。第二,西人与华人合选当前急用之书,没有按大英百科全书分门别类进行译书,故所译之书不配套。第三,主要选择科技方面的书籍,但由于清政府军事上的需要,选择了许多‘水陆兵勇武备’之书。根据以上原则,徐建寅他们选择的大多是英美最新出版的书,有些是著名科学家的名著。”[33]据此,《垸髹致美》应当符合当时“更大更新者”、“当前急用之书”与“科技方面的书籍”的三条选译标准。《垸髹致美》中“所述各种工艺,有的在西方尚属先进,有的虽已过时,但在当时中国,仍不失为有用的技艺。”可见,晚清引进技术文本《垸髹致美》是当时社会之需。从晚清发展实业看,学习西方技术与技术引进成为当务之急,引进《垸髹致美》反映晚清社会注重科学与发展实业“自强救国”的立场。洋务重臣盛宣怀、张之洞等人无不强调“制器”之重要性,并主张“工商立国”论。在洋务运动期间,在轮船、铁路、造炮、开矿、冶炼等部门都要大量使用油漆及其技法,而中国的《髹饰录》侧重髹漆技法,其技术“配方”只在家族内传承,很难适应晚清实业的发展需要。于是侧重髹漆技术“配方”的《垸髹致美》无疑有补于《髹饰录》之广漆配方的缺陷。
《垸髹致美》既表征晚清社会洋务思潮、发展工商业的状况,也见证家族传承式的《髹饰录》知识在遭遇晚清实业时的尴尬与不足,更昭示晚清社会发展实业、学习新知识与注重科学的社会征候。
五、结论
一言以蔽之,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的外溢具有中外文化交流的特别意义与丰富内涵,它还至少能显示以下几点全球化文化共享的发展要义:第一,在国际贸易下,借助海上丝路及其贸易,清代漆器文化被广泛地介入欧美世界,并在各国发生广泛的阅读与深刻的审美体验,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欧美人眼中的他者艺术想象;第二,在文化互动中,被传播至欧美世界的清代漆器所体现出来的他者想象恰恰吻合了东方文化之美,尤其以审美体验的方式再现或体认了清代中国漆器特有的美学形象;第三,在此消彼长的中外漆文化的体认、溢出与耦合中,伴随18世纪后期“倭漆”与美国《垸髹致美》文本被中国的引入,中外漆艺文化已然出现一种不倦的环流现象,清代海上丝路漆器也显示出全球视野下的他者地位与身份。同时,漆器文化不倦的环流现象不仅表明近代以前处于东方中心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所秉承的“文化输出主义”理念开始裂变,还标志着中国清代后期漆器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呈现文化的“贸易逆差”。
在“一路一带”的当代发展战略下,自觉对待与理解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的海外输出、他者想象与世界环流,对于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水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蓝浦.景德镇陶录校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27.
[2]刘伯温.刘伯温寓言选[M].戴山青,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81.
[3]张荫桓.张荫桓日记[M].任青,马忠文,整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4]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东南亚历史学刊: 3[M].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86.
[5]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文献辑要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78.
[6]宋大川.瀛寰志略校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
[7]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 1784—1844)[M].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0.
[8]龙思泰.早期澳门史[M].吴义雄,译.上海: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
[9]布罗斯.发现中国[M].耿升,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92-93.
[10]纪宗安,汤开建.暨南史学:第二辑[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372.
[11]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12]王之春.清朝柔远记[M].赵春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64.
[13]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66.
[15]徐肖南.东方的发现:外国学者谈海上丝路与中国[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 171.
[16]陈伟.中国漆器艺术对西方的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7]陈伟,周文姬.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陶瓷艺术[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40.
[18]米歇尔·康佩·奥利雷.非西方艺术彭海姣[M].宋婷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11.
[19]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0]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88.
[21]何兆武.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6-77.
[22]周宁.世纪中国潮[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302-313.
[23]沙丁,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56-57.
[24]陈-罗德里格斯.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M].白凤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5]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王国卿,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 623.
[26]德克·卜德.中国物品传入西方考[G]∥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229-230.
[27]乔纳森·戈尔茨坦.费城与中国贸易( 1682—1846年)——商业、文化及态度的作用[G]∥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四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85.
[28]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中国漫记[M].蒋本良,柳凤运,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29]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151.
[30]张荣.漆器型制与装饰鉴赏[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94: 204-205.
[31]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25.
[32]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J].中国科技史料,1995(02) : 3-18.
[33]凌瑞良.物理学史话与知识专题选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2.
[责任编辑:张文光]
Spillover of Lacquer Culture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Qing Dynasty: On Trade,Imagination and Circulation
HU Liang-yi,PAN Tian-bo
( School of Media,Film and Television,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009,China)
Abstract:Relying on trade output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lacquer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widely introduced into Europe and America,causing reading,experiencing and aesthetic imagination in many countries while vividly displaying the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for lacquer in the eyes of Europeans and Americans.However,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lacquer culture into China since the later 1700s,lacquer art home and abroad has obviously exhibited a phenomenon of tirelessly cultural circulation.During the dynamic and unbalanced cognition,overflow and coupling of Chinese and overseas cultures,the Chinese lacquer culture that was spread displayed the phenomena of the other’s imagination and circulation in a global perspective,which are realized through lacquer culture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ith the function of linking the world.Knowing and grasping the features of the other’s imagination and circulation in the culture of Silk Road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a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rategy under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One Belt One Road”.
Key words:Qing Dynasty; Maritime Silk Road; lacquer culture; imagination; circulation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6) 02-0029-09
[收稿日期]2015-09-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4BG067) ;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 14JHQ039) ;江苏省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项目( SJZZ15-0196)
[作者简介]胡良益( 1992-),男,江苏邳州人,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与传媒文化。
[通讯作者]潘天波( 1969-),男,安徽无为人,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工艺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