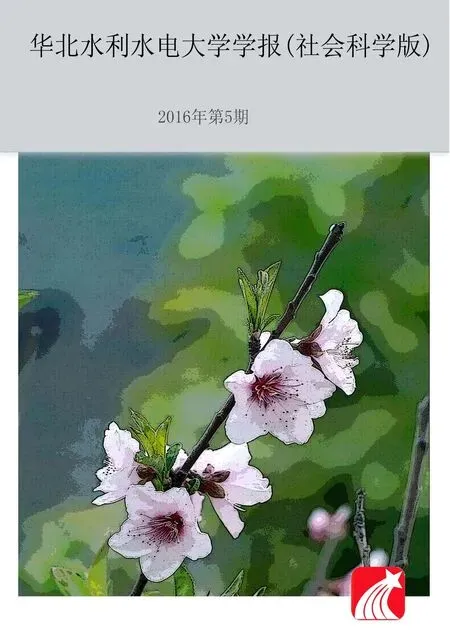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起诉之构建
2016-03-06王长水齐鑫卉
王长水,齐鑫卉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起诉之构建
王长水,齐鑫卉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强制起诉作为刑事不起诉决定的一种制约机制,目的在于限制检察机关过大的不起诉裁量权,保障被害人人权,德国、日本和韩国均有独立的程序加以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强制起诉制度,但有着与之相似的公诉转自诉制度,只是目前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国家完善的强制起诉制度,结合中国国情对现有的公诉转自诉加以改造,构建我国特有的强制起诉制度。
强制起诉;公诉转自诉;困境;出路
一、强制起诉的内涵
基于人权保障,节约司法资源,贯彻刑罚个别化理念等多重价值因素的考量,现代法治国家均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公诉案件的不起诉裁量权,将案件终结于法庭审判之前,具体在刑事诉讼中,就表现为不起诉制度。强制起诉作为应对不起诉处分结果的一种补救措施,对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意义重大。所谓强制起诉,是指在刑事非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对检察机关不起诉的决定不服,在一定期限内将案件提交至法院请求审判,法院经审查被害人的申请理由,认为理由确实充分,进而开启审判程序的一种制度。若法院认为被害人的申请理由不成立,则驳回申请,案件终结。由于这种起诉异于检察机关主动提起的一般公诉方式,是由法院直接将案件推进至审判程序的,产生了强制检察机关起诉的法律效果,所以称之为“强制起诉”。德国、日本和韩国都结合本国实际制定了此种制度,只是名称有所不同,但不论各国具体程序设计有何差异,其本质都是相同的:将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限定在被害人能够自我救济的合理限度内。
二、强制起诉与我国刑事诉讼
在古代中国“德主刑辅”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下,不起诉制度伴随着检察机关的产生一并发展起来,我国在1954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就已有规定。通常在控审分离原则之下,检察机关垄断公诉案件的起诉权,法院专司审判,互不干涉。但是如果不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任其膨胀势必会造成被害人权益受损,犯罪分子被放纵的严重后果,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1]342。再加之当时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办案能力参差不齐,“有罪不纠”现象大量发生,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填补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空白,创设了公诉转自诉制度作为不起诉的制约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5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5条的规定,被害人如果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对于维持不起诉决定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不经申诉直接起诉,这就赋予了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和起诉权。1996年此制度的创立确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立法者旨在“防止公安、检察机关会随意地将公民要求立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推之不顾”[2]291-292。发挥公诉转自诉在被害人权益保护和检察公权力监督方面的双重功效。也正是因为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存在,我国未再建立诸如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强制起诉制度,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的背景下仍然保持原貌,未作修改。但实践中,公诉转自诉已运行了将近20年,实践效果却不容乐观,比如樊崇义教授就认为公诉转自诉“已经名存实亡”[3]。究其原因,是这一制度本身缺陷所致:理论依据不充足造成公诉、自诉的混淆,制度设计不合理不仅无法保护被害人权益反而加重其负担,法条简略使这一制度不成体系。既然公诉转自诉同强制起诉的实质均为对不起诉的规制,在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已暴露出诸多缺陷的情况下,分析并总结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作为强制起诉蓝本的德国之先进经验,改革原有的公诉转自诉为我国本土化的强制起诉不失为一条捷径。
三、强制起诉的合理性分析
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强制起诉制度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日本与之类似的准起诉制度和韩国的裁定申请制度都根源于此。尽管不同国家有关强制起诉的具体规定不尽一致,但都体现出了强制起诉作为刑事诉讼一项重要制度的合理性。
(一)强制起诉之于检察机关:符合检察一体化原则
德国、日本及韩国都将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抗告作为前置程序,告诉人在向法院申请裁决之前,必须要经过检察机关的两次不起诉决定,穷尽检察系统内部救济后,方可向法院提出申请。在“检察一体化”的组织方式下,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以整体名义决定检察实务,德、日、韩均属大陆法系国家,其检察一体化较之英美法系松散型的一体化模式更为强有力。强制起诉使检察机关能够在部门内部进行复查及自我监督,为案件的起诉与否设置了第一道审查程序,上级检察机关有义务监督纠正下级检察机关错误的决定。德国学者布赫曾提出检察一体化体制可以有效防范错误裁判,在不告不理原则下,检察官错误不起诉的决定非常危险,一旦被害人的告诉权被剥夺,案件就止步于法庭审判,法院也就失去了审查的机会,强制起诉制度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4]。同时检察机关的自纠也能相对减轻案件在不同机关移送过程中产生的司法资源浪费,在当前我国推行立案登记制以及司法员额制改革的背景下,不乏有大量新型复杂案件进入审判程序,这一制度可以有效缓解法院因“案多人少”“诉讼爆炸”等现象引发的资源紧张,贯彻了诉讼经济的价值理念。
(二)强制起诉之于法院:符合权力制衡体系
如果说强制起诉体现的检察一体化是对案件的第一道救济程序,那么法院的权力制衡就是对不起诉决定的第二道救济手段。德国的强制起诉、日本的准起诉亦或是韩国的裁定申请都规定:一旦法院准予起诉并交付审判,就视为案件已提起公诉。只要不服上级检察机关的拒绝起诉通知,告诉人都有权寻求法院的司法救济。其法理依据来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三权分立”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赋予三种不同的国家机关,三机关呈现出平面线型结构,各自拥有各自的权限并互不干扰,但同时他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5]114。在世界人权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也随之扩大,为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用法院中立的审判权去制约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因为在检察机关的两次不起诉决定之后,公民权利制约检察公诉权力未能发挥作用,只能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形式将案件交付审判。根据近年来我国平反的一些冤假错案,司法人员为及早结案不惜违反诉讼程序规定,说明实践中公权滥用的现象仍要引起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行的司法责任制改革,对于法官、检察官的权力约束和错案终身追责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也与强制起诉权力制衡的理念相一致。
(三)强制起诉之于被害人:符合司法终局性要求
在刑事犯罪中,被害人作为法益直接遭受侵害的个体,要求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愿望最为强烈。强制起诉在检察机关公诉不能的情况下,赋予被害人进入司法审判的机会,使他们更能从心理上接受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因为在民众的心中,法官是正义的化身,终局性的司法判决具有公定力。美国联邦大法官杰克逊有句名言:“我们是终审并非因为我们不犯错误,我们不犯错误仅仅因为我们是终审”[6]161。法院的裁判理所当然就被推定为是公正的,减少了现实中不必要的申诉和缠讼数量。此外,司法终局性也体现在其执行力上,被害人期待终局裁判得以约束被告人,强制其服从并履行生效裁判内容,如果被告人逃避履行其义务,就会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制裁,强制起诉衍生出强制履行的义务,能够从起诉阶段到执行阶段给予被害人全方位的保护。在我国增强被害人的主体地位,能减少错案发生的几率和因裁判结论不满意引发的无止境的信访不信法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扰乱了我国社会稳定,对司法的独立性和公信力也是巨大的损害,强制起诉能增加被害人依靠诉讼进行自我救济的途径。
四、我国强制起诉之构建困境
虽然我国的公诉转自诉制度的本质同强制起诉制度类似,都是对被害人起诉权的救济,但从发展历程上看,德国早在1877年的《德意志帝国刑事诉讼法典》就建立了强制起诉的雏形,并在日后司法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日本也于1948年确立了准起诉程序。而我国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才规定了公诉转自诉制度,且只有寥寥数语,过于简略,2012年《刑事诉讼法》也未涉及到此制度的修改,急待改善。从国情出发,纵观中国近现代法律的渊源,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制度和理念都源自德国,司法传统中留下了不少大陆法系的法律烙印。检察一体化原则下,我国与德国、日本和韩国具有相似的制度根基,强制起诉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制度,不可避免存在有不足,但总体来说优大于劣,尤其是对于弥补公诉转自诉制度缺陷来说,若想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就必须正视我国现行法律与强制起诉制度设计相冲突所带来的种种困境。
(一)强制起诉实践效果的质疑
经过上文分析,强制起诉制度对于检察机关、法院和被害人来说都富含重要的理论价值,可我国的实务界对移植强制起诉的效果提出了深深质疑。因为根据资料,1992年德国成功提起强制起诉的案件只有10起左右,成功率不足1%[7];日本自现行法实施以来通过准起诉程序交付审判的案件只有17件[8]135。但就此得出强制起诉无用的结论太过武断,抛开具体数字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澄清移植无用的误解。德国的相关法律文献中就适用率低的现象作出了分析,认为并非由于这一制度自身不起作用,而是其在刑事案件中适用余地太小。由于德国的侦查模式较为特别,刑事诉讼的侦查权由检察官和警察共同行使,各州对警察在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侦查仔细且全面,检察官同时也是主导者,享有监督指挥权,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正确率很高,案件在强制起诉程序发动前就能得以解决。此外,德国、日本和韩国将抗告程序前置,经过检察机关两次不起诉决定后尚未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本来就寥寥无几,案件基数小也是导致低适用率的一个原因。我国现有的公诉转自诉的施行效果,可参看赵永红博士在2001年对北京市检察机关不起诉工作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数据。据统计,2001年北京各级检察机关共决定不起诉刑事案件287件,涉及人数337人。在侦查机关和当事人对不起诉决定起复议和申诉的案件中,本级法院或上级法院审查后均维持了原决定;不起诉案件中,无被害人自行向法院起诉的案件[9]。北京市的数据突出表明了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似乎仅停留于法律的字面表述上,被害人并没有开启这一程序的意愿。不同于域外国家强制起诉适用空间的狭小,我国构建强制起诉制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唤醒被害人的主观维权意识,更重要的是在我国目前侦查程序尚不完善的前提下真正为被害人提供客观的法律保障。
(二)我国现行公诉转自诉与强制起诉构建之冲突
1.公诉权和自诉权冲突
公诉权是国家主动对犯罪进行追诉的一种刑罚请求权[10]。它伴随着封建主义色彩浓厚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后于自诉权而产生并旨在弥补自诉权救济范围小、力度弱的缺陷。一般来说,公诉权适用于情节严重的犯罪案件,自诉案件只涉及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两者有明确的界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公诉转自诉制度无法解决公诉权和自诉权的界限问题。虽然立法赋予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选择权,既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上一级检察院经复查作出起诉决定的,交由下级检察院提起公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此时,检察权退出诉讼程序,仅由被害人扮演控诉角色,实质上是自诉。这样对于同一案件,被害人拥有公诉和自诉两种程序启动权,公诉和自诉的界限消失,势必会造成程序适用的冲突和混乱;同样,在有多个被告的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同一被告触犯多个罪名的案件中,就会出现只对部分被告或部分罪名提起强制起诉的情况,被害人就会拥有公诉和自诉的双重身份,也涉及到基层和中级不同级别法院都有管辖权的问题,这造成了司法实践的一大困境。反观德国,强制起诉程序启动后案件性质仍是公诉,由检察机关承担控诉职责,按照公诉案件的审理程序进行诉讼,被害人无需承担证明责任,符合强制起诉的立法初衷。日本和韩国也只是在公诉人选的设置上有所不同,以律师代替了检察人员,未曾改变案件的公诉性质。公诉自诉界限明晰,规避了公诉转自诉产生的不良影响。
2.被害人权益和被告人权益冲突
18世纪贝卡利亚对犯罪本质作出了系统的论述,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契约”的违反[11]11,由此便产生了“犯罪人—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被害人的地位不被重视,所受的伤害被抽象和虚化。直到20世纪人本主义法律观兴起,1941年德国汉堡大学教授汉斯·冯亨梯的《论犯罪人和被害人的相互作用》一书引发了世人对被害人角色的关注,实现了被害人地位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设置初衷就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实现被害人和被告人权利均衡化,可现实情况中立法者期望是很难达到的,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现行法律条文的简略导致制度缺乏执行力。立法规定被害人向上一级检察院提起申诉,但公诉转自诉制度中对申诉的复查期限、复查流程未作规定;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后关于法院的办案程序及案件材料的移送也不够详细,制度的操作性不强,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有被虚化之嫌。第二,证明标准过高,缺少事后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是有关自诉案件范围的表述,第三款中“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将公诉转自诉案件的证明责任加诸于被害人,却忽视了原本就是公诉性质的案件所固有的复杂严重性,既然依托国家公权力力量的检察机关尚不能收集足够的证据提起公诉,有何理由苛责缺乏举证能力的普通被害人完成?况且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之后,其生理及心理受到重大打击,往往处在经济困难的状态。一旦被害人提供的证据达不到第205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就会被法院说服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案件就此终结,这种进退不能的尴尬状态会阻碍司法终局性目标的实现;况且拥有公诉和监督权双重属性的检察机关在公诉转自诉程序启动之时就会退出诉讼,监督权的缺失会使被害人更显孤立无援,从这点看来,立法者显然没有考虑到被害人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而德国、日本及韩国对强制起诉不仅有法典的规定,还存在着大量的法条注释,将起诉的期限、方式和流程都明文确定下来,比如将对上级检察机关的申诉限定在2周之内,向法院申请强制起诉的期限规定为1个月内,整个强制起诉也自成体系,案件的公诉性质决定了被害人不用承担苛刻的证明责任,减轻被害人负担,操作性强。
3.被害人人权保障正当性和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有效性冲突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将立案审查制改革为立案登记制的决定,一时间大量案件涌入审判庭,法院出现了“案件井喷”的景象,法官办案负担沉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对于案件的分流、减轻法院案件负担以及提高诉讼效率有着重要意义,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被害人的起诉权利;反之,若对被害人的强制起诉权不加以限制,在检察机关作出有效的不起诉决定后仍赋予被害人申请法院审判的机会,同样会使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权不具有效性,处于架空状态。在两种利益孰重孰轻不能简单定论时,公诉转自诉并不能设定一个合理的标准权衡两者的关系,但德国的强制起诉巧妙处理了这个问题,其在《刑事诉讼法典》第172条第三款为被害人设置了义务,要求强制起诉书必须有一名律师签名,律师要对申请文书的内容负责,律师迫于职业危机感也会尽量消除“每一个公民都能提起公共诉讼”的潜在危险;同时德国和日本还规定,法院可以裁定要求告诉人对程序给国库和被指控人预计产生的费用提供担保。由于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具有对向性,《刑事诉讼法》在保障被害人人权的同时,也要保证被害人提起强制起诉的合法、合理性,通过增加被害人的保证义务的方式,去交换法院最大程度上裁定强制起诉的可能性。
五、我国强制起诉之构建设想
(一)限定强制起诉的案件范围
我国以往的《刑事诉讼法》将不起诉类型分为三种: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一章特别程序中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不起诉方式:附条件不起诉,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体系。根据以上各种不起诉适用的条件和特点,把强制起诉的案件范围限定于酌定不起诉更为合适。原因如下:强制起诉制度的适用前提是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存在,只有在检察机关不能适用普通公诉程序提起诉讼之时,强制起诉才有启动的余地。以此为标准,法定不起诉是指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不起诉,这种绝对不起诉有明确的标准,不会引起被害人的争议,并无不起诉裁量权适用的空间,因此排除在范围之外。证据不足不起诉是在检察机关经过两次补充侦查仍无法证据不足,达不到起诉条件时,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如果公权力机关经过多次补充侦查后仍无充足证据提起公诉,被害人恐怕更无把握收集到充足的证据使案件进入审判,此时赋予被害人强制起诉权无实质意义,只能看不能用。此外,《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并得到被害人谅解,但我国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较小,只适用于未成年人,而且不起诉决定的作出本来就含有被害人的自身意愿,被害人继续向法院申请起诉的现象一般不会发生,就算犯罪嫌疑人违背了不起诉所附条件,检察机关有主动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提起公诉的义务,被害人完全不需要强制起诉的救济。排除了三种不起诉类型,酌定不起诉恰恰是检察机关根据犯罪情节轻重酌定使用裁量权的表现,在被害人看来这种不起诉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情感上最不容易接受,把范围限定在酌定不起诉案件中,可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法院也可将精力集中于对不起诉案件的审查上,防止被害人强制起诉权的泛滥造成被害人权益受侵害。
但同时要注意,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类案件不受上述不起诉类型的限制。日本和韩国均将职务类犯罪进行特别规定,将强制起诉只适用于公务员犯罪案件,这是由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缺乏外部监督,自己起诉、裁判的做法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原理;职务犯罪案件也较一般案件危害性更大,所以必须作出特殊的规定。
(二)界定强制起诉的主体范围
强制起诉程序的启动主体是不起诉案件的被害人,具有行为能力的被害人可以直接提起强制起诉。通常,刑法学上的被害人是指因犯罪人违反刑法的规定,实施犯罪行为致使合法权益遭受直接侵害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上并没有明确定义被害人的概念,但学术界达成共识认为被害人不包括遭受犯罪间接侵害的人,这种界定不无道理,因为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具有多方面性,间接侵害的程度往往难以把握,司法操作困难。但对于已死亡被害人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来说,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权利得不到救济,如果忽视了这些人的权利保障,会引起近亲属和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引发同态复仇等私力救济,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将更多的社会权益纳入保护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日本和韩国由于强制起诉的案件适用范围小,被害人的范畴也相对较小。而德国理论界倾向于被害人概念扩大解释的“法益不法侵害说”,认为被害人应为其权利、法益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之人。因此,首先应借鉴德国被害人概念的扩大解释,在观念上正确看待被害人这一定义的外延,将自然人、单位、国家和社会都包括其中;同时不能忽视被害人程序权利的保障,使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程序权利与被害人实体权利齐头并进,完善被害人权利体系。其次,在被害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由其及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提起诉讼,这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60条特殊情况下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为提起自诉的精神相一致。另外,由于刑事公益诉讼的兴起,在没有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时,对案件有管辖权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与本案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利害关系人提起强制起诉,彻底解决空有权利却无人行使的问题。
(三)明确强制起诉的案件性质为公诉
首先,明确规定被害人依强制起诉制度提起的诉讼不应改变案件性质,法院仍应将其作为公诉案件判决,适用公诉审理程序;依然由检察机关行使公诉职责,在审判过程中也要负证明责任,但必须在德国强制起诉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要另行指派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而不得指派原审查起诉的检察官[15]。因为原检察官在刑事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案件未达到起诉标准的内心确信,规定其出庭履行公诉职责会导致认知的前后矛盾,势必会影响公诉效果,这样设置也能有效避免日本和韩国指定律师担当公诉可能出现的律师为迎合法官而丧失辩护独立性的隐患。其次,取消被害人既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又可不经申诉直接向法院起诉的程序选择权,这是造成现实中公诉、自诉界限混乱的最大根源,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76条为:“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该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在7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15日内作出裁定。”穷尽检察系统的内部救济,同时将刑事诉讼法与相关的司法解释作统一归纳,细化强制起诉制度的诉讼流程,提高这一制度的可行性。
(四)增设相应的保障救济措施
就被害人义务履行方面,借鉴德国和日本的被害人担保程序,在被害人提起强制起诉申请时应责令其提供适量的担保,担保费用的金额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但不能超过可能给国家和被告人所产生的费用限额,担保期限则依案件严重程度确定。此外,对于不起诉决定错误并且被指控人被采取逮捕措施的情形,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赋予被指控人申请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机关赔偿的权利,从而实现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总体平衡。就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最重要的是辩护权利的保障,赋予被害人在启动强制起诉程序时的法律援助权,对于没有能力委托律师的被害人,国家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职责的律师为其提供帮助。因为在强制起诉成功率尚且不高的司法环境下,一般律师出于执业业绩和辩护压力的考虑是不愿意代理强制起诉案件,但是法律援助律师所产生的费用由国家财政支出,法援律师就可以将精力完全集中在案件中而不受外界因素影响,增大了被害人成功提起强制起诉的几率。
[1] 阿克顿勋爵.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周道鸾,张泗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3] 樊崇义,叶肖华.论我国不起诉制度的构建[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6(1):10-19.
[4] 孙谦.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是检察官的基本追求:《检察官论》评介(三)[J].人民检察,2004(4):5-11.
[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6] 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 宗玉琨.论德国强制起诉制度[J].刑事司法论坛,2009(2):194—195.
[8] 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9] 赵永红.不起诉的实践运作、加强与改进:关于北京市不起诉工作的调查[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6):88—89.
[10] 赵永红.公诉权制约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4):5-8.
[11]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12] 叶瑞.我国构建强制起诉制度之理论探析[J].三峡大学学报,2014(5):80-87.
(责任编辑:袁宏山)
Establishment of Compulsory Prosecution in Criminal Lawsuit in China
WANG Changshui, QI Xinhui
(School of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Compulsory prosecution for criminal decided not to prosecute a restriction mechanism aimed at restriction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is too large prosecution discretion, protect the victim rights,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independent regulated procedure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our country has not established compulsory prosecution system, but has the similar to a set of public prosecution, only there are many defects at pres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countries outside perfect compulsory prosecu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of existing private prosecution indictment are modified, build unique compulsory prosecution system in China.
compulsory prosecution; public prosecution; the mire; way out
2016-04-08
王长水(1960—),男,河南开封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及司法制度;齐鑫卉(1992—),女,黑龙江肇东人,郑州大学2015级诉讼法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
D915.3
A
1008—4444(2016)05—00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