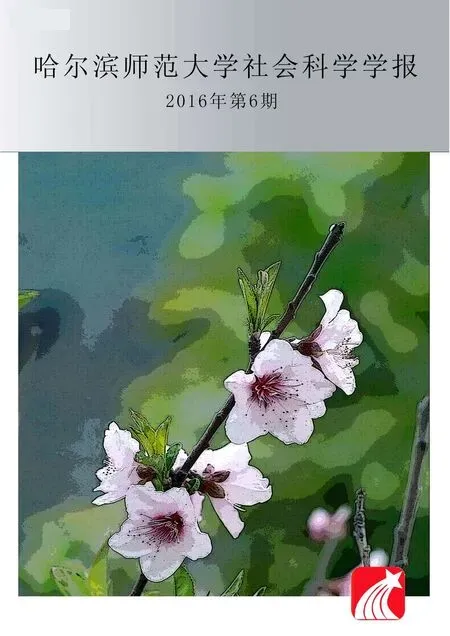痛彻心扉的悲凉
——谈鲁迅小说死亡意识的独特意蕴
2016-03-06魏静
魏 静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如皋校区,江苏 如皋 226500)
痛彻心扉的悲凉
——谈鲁迅小说死亡意识的独特意蕴
魏 静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如皋校区,江苏 如皋 226500)
鲁迅小说秉承一贯的文学改良人生的创作主旨,借此对社会进行无情的揭露、抗争。其小说大量描写到人物的“死”,甚至以悲剧性的死之作为人物的结局,这种自觉的对人物死亡结局的观照显现了鲁迅强烈的死亡意识。对于生命而言,死亡是最大的悲剧。为此,鲁迅一面不留情面地揭示、批判,一面真诚地怀抱愿望,企图解救,然而终不得救。于是鲁迅呐喊、反抗,几经彷徨、绝望,但又由绝望中再次树立希望,即便是知道幻灭的结局,依然义无反顾。这就构成彻底的悲凉,鲁迅的死之意识是他强烈悲剧意识更深层次的展现。
鲁迅小说;死亡意识;悲剧意识
鲁迅的小说习惯以悲剧性的死之作为人物的普遍结局,孔乙己在穷困潦倒中死去;阿Q以莫须有的罪名被 “枪毙”;祥林嫂在“祝福”之日倒毙街头;夏瑜死于刽子手的屠刀之下;魏连殳在自戕中最终结束了性命;子君走投无路郁郁而终;眉间尺最后身首异处……鲁迅小说中的这个现象曾被许多的研究者关注,并且达成一定共识。吴永江在论文《论鲁迅死亡形象的创作动机及艺术特征》中指出:“鲁迅似乎对死亡有深刻的感触和洞见,从创作于1918年至1925年间的25篇短篇小说中,读者明显地感觉到一个艺术特征,那就是作品中往往用死亡来注解人物的结局。”[1](P75-76)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中也指出:“鲁迅是一个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各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 “很少有作家能以这样大的热忱来讨论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2](P373)为什么鲁迅的小说规避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而有意制造出种种的死之恐怖呢?笔者试以此疑问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一探鲁迅小说中死亡意识的独特意蕴。
一
毕绪龙在《死亡光环中的严峻思考——鲁迅死亡意识浅探》文中,对于鲁迅作品中的“死亡意识”这一概念做出了界定:“基于深刻的死亡体验,对死亡进行痛苦观照的死亡意识的实质是一种现代哲学意识。”[3](P10)可以看出在阐释鲁迅作品的死亡意识的同时,论者把鲁迅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和鲁迅个体的死亡体验联系在一起来考查。皇甫积庆在《“死”之解读──鲁迅死亡意识及选择与传统文化》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鲁迅对‘死’有着超乎常人的‘自觉’。他是在‘死’之意识中写着‘死’的作家。”[4](P23-25)也就是说,鲁迅对于死的描写是出自他的对于“死”的“体验”意识。纵观鲁迅一生的经历,从家中父亲的病逝到社会上无数无辜生命的被残害,可以说现实种种的死亡一直围绕着鲁迅。无奈、悲痛,但却必须承受、直面,这无疑成为影响鲁迅小说中死亡写作的直接原因。到了后来描写死亡便成为他作品的一大主题。鲁迅对于死的描写和关注,并不代表他对生命“生”的不重视,“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5],这是鲁迅曾表达过的坚定立场,由此可见,生命在鲁迅看来,是“第一义”,是最宝贵的。而鲁迅“对于‘死’的描写、议论,正是对生命奥秘的窥探”[4](P23-25), 死亡意识,是其生命意识的核心部分,正是因为鲁迅意识到生命的宝贵,才让他对“死”有了更强的敏感,其“死亡意识”的背后,是对已逝生命的无奈、悲哀,甚至是叹惋。“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6],人的死无疑是人生最大的毁灭 ,因此,鲁迅作品中的“死亡意识”,源自其思想深处的悲剧意识。
“‘死’意味着存在的痛苦,无奈,荒谬,寂寞,意味着无可避免的灭亡的悲剧。‘死’是悲凉的”[4](P23-25)。祥林嫂的一生毋庸置疑是痛苦的。即使她有着所有传统女性历来的无言的坚韧和逆来顺受,但当所有的苦难都向她涌来的时候,即使是出自生命的本能,她内心的痛苦定是难免的。这样看来,“死”成为她必然的结果,因为她可以承受成为寡妇,甚至可以暂时抵御改嫁后来自内心和外界的“精神恶魔”,但是还有更悲惨的在等待着要去吞噬她。祥林嫂的“死”因此证明了她活着的“苦”。与祥林嫂相比,阿Q好像活得更为“豁达一些”,他可以随时忘记苦痛,不然就在精神上“转败为胜”“转忧为乐”。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忘却”、他的容易被“麻醉”,让他具备成为“代罪羔羊”的充分条件,那被“枪毙”也就顺理成章了。鲁迅的小说中也有一些头脑颇为清醒者,像夏瑜、魏连殳、子君等。他们称得上清醒者,是因为在他们的人生之初,他们都是“豁达无畏”的,据此他们承受着他们的“高处不胜寒”,精神抖擞,在“反抗斗争”中激情满满。可是没过多久,现实就将他们美丽的梦境打破,经历他们各自不同的“寂寞”“无奈”“幻灭”之后,等待他们的也必然是“无可避免的灭亡的悲剧”。
二
人的死亡,有时是源自生命的无常、意外,是“宿命”,但鲁迅作品中人物的死亡却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必然结果,有一双无形的大手,终将把他们推到悬崖的边缘,并将他们推下去,让他们坠落、死亡,没有任何的侥幸。生命如此渺小,不禁令人悲叹。鲁迅通过作品告知人们,这一切不是因为命,尽管有人事先屈从于命运,导致人死亡的多是那因杀戮而到处充满血腥气味的罪恶的现实社会。“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关于国民性的问题”[7]。鲁迅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他的艺术力求真实。因此,他极力揶揄“欺骗者”:“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是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需我们焦躁;放心喝茶、万事大吉。”[8]这就是鲁迅要揭示“有问题”“有缺陷”“不团圆”的“死亡”结局的真实原因,鲁迅无法“忘怀于人们的死”,也无法“忘却”死去的人们,因此,他选择了通过小说来揭示,这正是其小说创作的根本意旨。正如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中所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扔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9]。这种启蒙思想,也体现出鲁迅文学功利性的追求。他认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爱国”的“立志于献身于时代的人”,“就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说出一些温吞水似的话。因为对于这种批判时代来说唯一重要的武器,就是批判”[10](P27)。因此,鲁迅的死亡意识的出发点就是揭示与批判。
鲁迅意在通过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类“铁屋子沉睡”者的死亡过程及死亡结局的揭示,以惊醒众人从而避免更多人的“死”。因为“里面有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就要死的悲哀”[11]。为此,他在小说的创作之初坚守这样的信念:“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12]通过小说,鲁迅一面不留情面地揭示、批判“黑暗时代中国农民、中国妇女、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的生活”[1](P75-76),悲剧性的死亡;一面真诚地怀抱愿望,企图解救更多还未走向死亡的中国农民、中国妇女、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种启蒙的意义及影响,鲁迅也是较早就有敏锐而复杂的感知的,在经历一系列惨烈的社会事件之后,鲁迅由“呐喊”而“彷徨”,由“坚信”转而开始“怀疑”, “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3],“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14]。
三
但纵观鲁迅整个创作,其文学观念始终未变,他依然坚守着通过文学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使命。前面说过,鲁迅如此执着于对“死”的描写,还源于他的对于死的自觉的“体验”意识,这就进一步表明,鲁迅对人生命运结局的关注、对他们死亡结局的设置,依照的不是旁观者的看客态度(这也是他极力批判的),他是始终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甚至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来“改革”和“反抗”,也因此,鲁迅所描写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更不是他一己的悲剧,他用他博爱的胸怀在为整个社会和人类受苦,他的悲剧意识观照的是普遍的社会和人生。这样的能够不惜自我牺牲,甚至适时准备赴死的鲁迅,他的内心注定是强大而无畏的,而他的目光也注定是深邃犀利的。他对于人物关注的终结不是到“死”为止,而是直至其死之后。既然鲁迅是站在批判社会和人生的立场上来关注“死”的,那么,他对于“死”后的社会和人生价值肯定是极力期待的。在众多“无可避免的死亡”之后,他立即将目光转移向还在世的周围人的身上。在满怀希望与失望之后,鲁迅再一次勇敢地选择相信。于是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有关“死”之后的许多描绘。
祥林嫂死后,受到的不再是生时那般责骂,而是变本加厉成为咒骂。且不说人之间的冷漠、残忍如何,可是那信鬼神、懂“祝福”的鲁四之流,应该知道“死者为大”的道理吧,他可以不懂对于生命的“敬畏”,但至少应该遵循对“鬼神”一贯的忠诚吧,可见,他们的愚昧至极。这种人何以“疗救”?阿Q死后,人们的普遍反应就是“不满足”,“多不满足”,因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边好看”。“看戏的人”没看到好看的“戏”,所以“不满足”。人们的关注点根本不在于他“死不死”而在他死得“不可笑”。 “揭出病苦”的意义都没实现,何以“疗救”?他们一面相信“枪毙”的“坏”,一面又怀疑“枪毙”的“不好看”。一个“阿Q”已死,千万个“阿Q”却在麻木地等待着“死”,这时的鲁迅,没能从周围的人看到一丝的微光,只能是无尽的悲凉了。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15],通过对死后现象的揭示,再一次显现出鲁迅死亡意识深处的悲剧意识。
不得不承认,在“拯救”的道路上,鲁迅的真诚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选择直接与周围人对话,另一方面,他又在寻找着“先觉”的人来向他呼应。这些“先觉”的人,比如魏连殳、子君、夏瑜等,他们曾反抗的激烈,但是结局也是惨败。能够以“牺牲”生命作为反抗甚至拯救的代价,他们的死应该足够激起涟漪的。然而,魏连殳生前的反抗与死后依然“孤独”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死不过更添别人的“古怪”之感,直至其死后,依然无人能真正理解他。子君,这个大胆为自己呼喊的女性,在她死后,受到的是恶毒之人再一次的“讥笑”,除此之外,她的死与祥林嫂无异,在别人看来也只是“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这个大胆以“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来标示自己独立与觉醒的女性,最终不仅不为人识,更可悲的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夏瑜死后,她被人期待的是热气腾腾的“人血馒头”,还有就是“该杀”的名头。“革命者为了愚昧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16],批判、反抗依然没有让愚昧者觉醒,“庸众”已中毒太深,在这里鲁迅已不仅仅是失望,革命者、启蒙者的被杀害,已经让鲁迅对民众和社会近乎绝望。人民的永无觉醒,社会的一如既往的黑暗,甚至让鲁迅深感恐惧。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表达了这种恐惧:“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17]这进一步证明了鲁迅在关注、描写死亡的同时,他正在深刻体验着“死”。鲁迅拼力寻找光明,带着希望和信念,然而终是“虚无”乃至绝望。
四
可是鲁迅终不能“闭眼看世界”,他再一次秉承一贯的反抗精神,于绝望之中再一次激起强烈的反抗。《铸剑》中的眉间尺形象的塑造,即是其再一次反抗的体现。如他所愿,这一次的复仇痛快淋漓,手刃仇人,玉石俱焚,极为悲壮。可是眉间尺的复仇愿望完成的还是不够完美,而且鲁迅在结局上有意为之,不是所谓的善恶终有报,看结局善与恶已分不清,因为他们的结局一样,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复仇者眉间尺和他的仇人最后葬在一起。作为由历史故事演绎的现代小说,鲁迅在死亡结局上的有意渲染,甚至“油滑”笔法的运用,都表明鲁迅的特殊用意。鲁迅后来结集的《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是有其独特的审美特色的,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喜剧的表现。对于喜剧,鲁迅也有界定:“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6],《铸剑》中鲁迅通过对眉间尺复仇过程和死后的处置的对照,复仇的意义最终被消解,一切的努力其实又归于“虚无”。但是尽管是这样,通过这个作品,鲁迅依然完成其反抗的使命,这也便展现出鲁迅思想的深刻与复杂。《起死》让已故之人复活,其荒唐不言而喻,然而这不啻为鲁迅对“死亡”结局的一种另类描写和关注。尽管是喜剧的形式,仍然有可怖的氛围,从人物的对话中,我们同样可以体会到深刻的悲哀。
纵观所述,鲁迅小说对于死亡的关注,以及由此构成的自觉的死亡意识,依然构成他的悲剧观,形成一种痛彻心扉的悲凉,这种悲凉甚至成为他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他真诚地对待,加以解救,然而终不得救。于是愤慨,于是呐喊、反抗,几经彷徨、绝望,但又由绝望中再次树立希望,即便是知道幻灭的结局,依然义无反顾。这就构成他的彻底的悲凉,这便是他小说中的痛彻心扉的悲剧。
[1]吴永江.论鲁迅死亡形象的创作动机及艺术特征[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
[2]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国外鲁迅研究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3]毕绪龙. 死亡光环中的严竣思考——鲁迅死亡意识浅探[J].鲁迅研究月刊,1994(7).
[4]皇甫积庆. “死”之解读——鲁迅死亡意识及选择与传统文化[J].鲁迅研究月刊,2000(2).
[5]鲁迅.译文序跋集·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C]//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C]//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C]//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坟·论睁了眼看[C]//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C]//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朱晓进.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 [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11]鲁迅.呐喊·自序[C]//.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鲁迅.阿Q正传序[C]//.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鲁迅.两地书·四[C]//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4]鲁迅.两地书·二四[C]//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5]鲁迅.华盖集续编·空谈[C]//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孙伏园.谈《药》[J]. 宇宙风,1936(30).
[17]鲁迅.坟·写在《坟》后面[C]//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孙 葳]
2016-09-28
魏静,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如皋校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
A
2095-0292(2016)06-014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