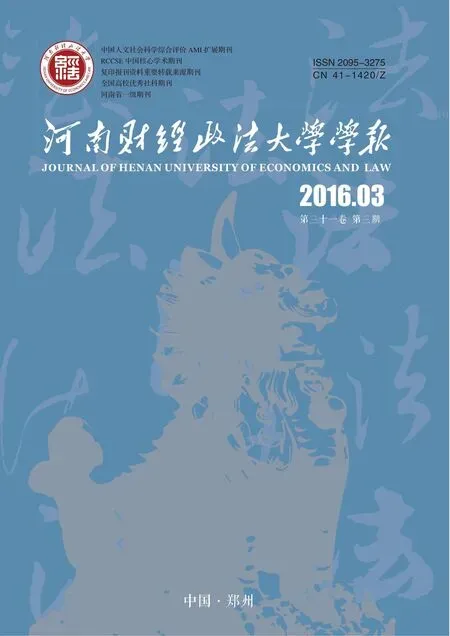法教义学视域中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再诠释
2016-03-06童伟华
李 至 童伟华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法教义学视域中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再诠释
李至童伟华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促进了我国强制医疗制度的司法化。但是现行法律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缺乏明确规定,有弱化人权保障机能之虞。在法教义学的视域中,重新界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不具有行为能力或无受刑能力的行为人因欠缺刑事责任能力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明确“有病无罪”和“有病有罪”的行为人都应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加强程序中各主体之间的协作,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阶段重构参与主体的范围,保障律师、被害人及鉴定人的参与权。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价值,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平衡和化解社会防卫和无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之间的矛盾。
刑事强制医疗;刑事责任能力;行为能力;受刑能力
一、程序的确立与瑕疵:强制医疗程序的模糊性
根据现代国家宪法的精神和要义,任何公民未经法定程序,其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自近代刑事社会学派提出旨在防卫社会,消除人身危险性的保安处分制度以来,以隔离和治疗为手段的强制医疗制度就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过,对此制度可能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质疑从未中止。时至今日,即使刑事古典法学派批判刑事社会学派所提出的保安处分制度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刑法色彩,但随着两派观点的融合,两派观点的对立已不如之前尖锐。折衷的观点提出了报应与预防相结合的理念——“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的刑法格言就揭示了刑罚适用目的既是报应又是预防。Carl Stoos将保安处分制度作为对报应主义刑罚进行的有益补充,其起草的《瑞士刑法预备草案》对众多国家的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1]。
大多数国家采用此种并合主义理念进行立法,由此,经过修正后旨在防卫社会的保安处分制度在当代刑法体系中也有了“容身之处”。在刑事制裁的二元化体系中,日益对特殊预防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出以社会防卫为目的之保安处分制度在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我国1997年《刑法》确立了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1997年《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是我国实施刑事强制医疗的实体法律依据。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刑事诉讼法的程序保障,也导致这一制度的真正价值始终停留在纸面。甚或在实践中,权力机关以“强制医疗”之名,行“权力滥用”之实,出现“被精神病”的情况。而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最终确立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实现了此制度的司法化,完成了实体法和程序法间的衔接,有利于完善我国刑事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但是,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却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其适用主体范围的规定模糊,突发精神病而不具有受审能力或欠缺受刑能力的行为人是否适用此程序存在疑问;律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等参与主体的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也需要重新定位。既然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主体范围及判断标准都显得模糊,而这一程序的效用又十分依赖于程序的可操作性,那么缺乏明确规定将弱化其人权保障机能。因此,在现行制定法秩序的框架中解释、明确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主体范围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适用主体的再诠释
正如丹宁法官在Bratty案中所言,“对于行为人表现为暴力并且容易复发的精神疾病,限制其在医院进行强制医疗要比给予不切实际的无罪释放要好”*See Bratty v.AG for Northern Ireland(1963).。职权主义为主导的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德国、俄罗斯)和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导的英美法系代表性国家(英国、美国)都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并严格依照程序对具有重大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虽然不同法系的司法程序具有不同的操作模式,各有特色的规定,但各国对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和实践经验也具有共性。比如,强制医疗适用主体的多元性*德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强制医疗适用的条件之一就是行为人无责任能力或不具有受审能力,即具有适用主体的包括了无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和不具有受审能力的行为人。俄罗斯的《刑法》规定法院可以对下列人员适用医疗性强制措施:(1)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本法典分则规定的行为的;(2)在实施犯罪之后发生精神病,因而不可能对之处刑或执行刑罚的;(3)实施犯罪并患有不排除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失常的。美国将施以刑事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分为两类:其一,“有病有罪”模式,即对虽患有精神病仍具有刑事责任的行为人执行强制医疗措施;其二,“有病无罪”模式,即患有精神病但不具有刑事责任的行为人执行强制医疗措施。“有病有罪”模式的精神病患者,监狱需给予其必要的精神治疗。在经过一定的服刑期后还可以假释,但是要接受假释审查委员会的精神医疗命令。“有病无罪”模式的精神病患者虽免除了刑事处罚,但患者需要接受强制医疗。英国的刑事法庭根据《精神健康法》的规定,被告人因精神病而无罪却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在充分、全面的法庭调查之后,法庭确信入院治疗是合适的,并且是为保护公共利益所必须,就会判决精神病患者接受强制医疗且附上出院限制令。对于不具有受审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法庭一般是裁定其入院进行治疗,直至恢复受审能力之后则继续接受法庭审判。和执行理念的人性化——不仅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对于不具有受审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及在服刑期间患精神病或间歇性精神病发作的,一般也可适用强制医疗程序,且程序主体各方都有充分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措施。由于精神疾病如今已并非不可治愈的疾病,在确定需要进行强制医疗之后,各国都不仅限于消极的监督保护为已足,除此之外,亦注重积极治疗其疾病[2]。其他国家对于强制医疗程序规定积累的一系列成熟经验,我国也可予以借鉴。
根据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仅限于精神病人,但是对于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则会影响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申言之,此规定适用于“有病无罪”的精神病患者自无疑问,但我国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把握并不统一,如何界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内涵,将直接影响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因此,有必要区分“有病无罪”的精神病患者和“有罪有病”的精神病患者,从而明确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
(一)“有病无罪”的精神病患者之刑事强制医疗
在“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模式中,刑事责任只是充当犯罪与刑罚的中介,即行为人实施了刑事法所禁止的行为而由此承担的后果[3]。在司法实践中也基本是限于在此种模式中,对“有病无罪”的精神病人,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参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刑医字第2号决定书;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5)郴苏刑医字第1号决定书;河北省隆化县人民法院(2015)隆刑医字第1号决定书。。只不过“有病无罪”模式中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条件规定过于抽象,皆具有进一步细化的余地,其明确的适用条件也能为“有罪有病”模式提供参考。
1.暴力行为危害性之限缩。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精神病患者,其行为必须具有客观的危害性,实施暴力行为*暴力行为一般分为四种类型:(1)最广义的暴力行为包含非法行使有形力的全部情况;(2)广义的暴力行为是指非法行使在物理上具有强烈影响的有形力;(3)狭义的暴力行为是非法对人的身体或物施加有形力;(4)最狭义的暴力行为是危及不特定或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有形力。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中的暴力行为应该是指最狭义的暴力行为,已经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或者虽未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但造成可能引起危及不特定或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等严重后果的危险状态。对公共安全或公民人身安全造成现实、紧迫的威胁或损害。因此,其中:(1)行为方式是当事人施加的有形力,通常以殴杀、毁损等为其表现方式;(2)行为结果是行为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既可以是已经造成实际损害,也可以是造成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危险状态。
之所以把刑事强制医疗的范围限定于具有最狭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原因在于:其一,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对社会的危险性大,才有必要触发刑事特别程序对其进行社会防卫。如果是轻微的暴力或者尚未达到危害公共安全或公民人身安全的程度,就不属于刑事强制医疗规制的暴力行为。其二,基于节省医疗资源和司法资源的考虑*过去,美国隔离危险性精神病人采取的措施就是将其长期安置在精神病院。但后来政府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也不得不对法律和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分流。参见张羽:《“武疯子”的法律难题》,载《方圆》2014年第8期。。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4],考虑到重性精神病患者数量庞大,政府只能集中司法和医疗资源强制治疗具有重大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以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刑事责任为核心。与我国颁布的《精神卫生法》相对比会发现,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具有二元化的性质。《精神卫生法》只规定了民事“保护性”措施,而《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是具有刑事违法性的,不过是阻却有责性。关于精神病患者的非自愿医疗出现这种“并驾齐驱”的局面,区别二者的核心就在于刑事责任。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基本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对象限于“有病无罪”的精神病人,刑事法的通说也一直以辨认、控制能力(行为能力)作为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条件之一,从而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承担[5]。其中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是其控制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控制能力反映人的辨认能力。行为人需同时具备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就不承担刑法非难的后果。易言之,刑事责任因实施犯罪而产生,行为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就不会构成犯罪,即意味着不承担刑事责任。比如,在实施危害公共安全或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时,行为人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就不负刑事责任,如果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则对其可以实施刑事强制医疗。
3.人身危险性的检验。根据社会预防的理念而衍生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目的在于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以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防止继续危害社会,而不是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替代性刑罚手段。因此,基于“无危险不强制”原则,强制医疗措施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考察精神病患者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其中的难点和重点就在于“有无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基于“推定危险性”标准的随意性,我们既不能通过法官的主观推断,也不能以异化的社会舆论及被害人等情绪化的反应作为判断标准。而应当根据一定的标准做出客观判断:首先,对比行为人的本次危害行为和之前的行为,判断本次行为的危险性是否有明显增强;其次,根据行为人是否具有攻击性人格,判断“再犯可能性”;再次,如果精神病人和被害人的关系是导致暴力行为的唯一原因,判断在隔断唯一原因后是否可以降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6]。
然而,在实践中,还经常出现精神病患者无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无能力、不愿意进行监管的情况。无人监管,任由精神病患者随意行事,也可能致其继续危害社会。因此,案件除考虑精神病患者的暴力行为本身外,还需以精神病患者是否有监护人或近亲属,且有能力并愿意监管患者,为其提供应有的医疗条件等风险要素作为测算参考[7]。
(二)“有罪有病”的精神病患者之刑事强制医疗
施行刑事强制医疗的“有罪有病”精神病违法者是指:(1)行为人于犯罪之后,有罪判决之前发生精神紊乱而不具有受审能力和受刑能力;(2)在看守所或监狱服刑期间,行为人发生精神紊乱而不具有受刑能力。因此,此处所主张的“有罪有病”的模式不同于前述美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有病有罪”模式。
虽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人提倡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从立法论角度将不具有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的精神病犯罪人纳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8],但法律不是嘲弄的对象,司法要实现社会安定的机能,不可能指望频繁地修改法律,修法经历的时间漫长、过程复杂,不止是修法成本造成的资源消耗,而且还不能及时发挥法律应有的作用,限制其效益的发挥。法律研究方向与目标不在于批判,重心在于合理地解释现有法律。笔者以法教义学为进路,根据现实的发展不断修正刑事诉讼法体系内个别“教义”的理解与解释方案,力求在现行法秩序的框架内主张自己的观点[9]。将“有罪有病”的精神病患者纳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范围内,其行为条件和人身危险性条件与“有病无罪”的精神病患者差别不大。即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或服刑人员之前所犯之罪,是由于暴力行为对公共安全或公民人身安全造成现实、紧迫的威胁或损害。如果不对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或服刑人员进行治疗,其还有继续实施类似行为的可能性。此种模式的重点就在于“刑事责任”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解释得以重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使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有罪有病”的精神病患者。
1.“有罪有病”的精神病患者处理之现实困境。《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97条规定“在实施犯罪之后发生精神病,因而不可能对之处刑的行为人”可以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13条针对无受审能力的行为人,也有类似规定。俄罗斯和德国如此规定,这是因为在犯罪之后,有罪判决之前发生精神紊乱而不具有受审能力和受刑能力的行为人,已经无法理解《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他们更不可能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会导致不利于自身的结果。在此情况下进行涉及人身权的刑事诉讼,并不能保障程序和结果的公正。英国的审判实践也表明因被告人突患精神病,重要刑事诉讼主体的缺位将使法庭审判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因此,就要对其先进行强制医疗直至完全恢复,再交付法庭审判*See R v.Smith (1845).。对比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对无受审能力的人是否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则表现得语焉不详,实践中基本不将无受审能力的人纳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考虑范围,如何通过明确规定具体的操作程序保障其正当的权利值得考虑。
对于在看守所或监狱服刑期间因发生精神紊乱而不具有受刑能力的行为人,《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和英国《1983年精神健康法》规定也可以进行强制医疗[10]。一方面,行为人在被判处实刑后,由于不能理解刑罚的意义,不能感知承受刑罚的痛苦,当然也就无法实现刑罚的特别预防机能。相反,如果对其适用强制医疗,可以做到在剥夺其自由的同时又对其进行矫正和治疗,达到社会防卫和保护行为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需要专业医师进行诊断、治疗的精神疾病不同于一般的疾病,一般的监狱医院以现有的条件和设备不能胜任如此专业的工作。但是我国不仅对此种情况无明文规定,而且《看守所条例》和《监狱管教工作细则》的规定*《看守所条例》第十条规定:“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1)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2)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但是罪大恶极不羁押对社会有危险性的除外;(3)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的婴儿的妇女。”《监狱管教工作细则》第九条规定:“收押犯人,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拒绝收押:(1)有精神病或者患有急性、恶性传染病的;(2)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3)妇女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由此可知,精神病患者是不能被羁押在看守所或监狱的。与《监狱法》及《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监狱法》第十七条规定:“罪犯收监后,监狱应当对其进行身体检查。经检查,对于具有暂予监外执行情形的,监狱可以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批准。”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所附“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第二项中明确规定属于适用保外就医的疾病是,“反复发作的,无服刑能力的各种精神病,如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等,但有严重暴力行为或倾向,对社会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除外”。由此可知,收监之后具有严重暴力行为或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不具有保外就医的可能。相冲突,行为人在服刑期间因精神紊乱丧失受刑能力是否要就医治疗还存在法律法规相抵牾的尴尬,导致执行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服刑人员发病期间是否还应执行刑罚、以什么形式执行刑罚、看守所或者监狱机关如何处理都颇有争议。
如此,面对相关法律法规中某些规定的疏漏与矛盾及“有罪有病”精神病患者处理的现实困境:其一,不具有受审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缺位,使法庭审判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我们可能会对“有罪有病”精神病患者的权利保障和审理程序的公正产生诸多质疑;其二,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目的在于为防卫于未然,通过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减少其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如果对“有罪有病”的精神病患者不予以医治,只是将刑罚执行完毕,对于此种复发率非常高的疾病[11],在其服刑出狱之后也将对社会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2.“有罪有病”的精神病患者处理之实现路径。要将“有罪有病”的精神病患者纳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成为解释的重点,也直接影响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是否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判断,一般是指行为人的犯罪能力[12]。作为行为人犯罪能力的刑事责任能力就是刑法上的行为能力。但是,也有观点指出,“刑事责任能力应是指行为人适应刑罚的能力,即受刑能力,是执行刑罚时司法机关应当查明的内容”[13]。由于刑事责任的主要表现是领受刑罚,预防犯罪是通过施以刑罚的方式对行为人进行教育和改造。为使教育和改造的目的得以实现,行为人即被改造人必须能够理解刑罚的意义,并能承受刑罚的痛苦。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这种理解和承受能力。在审判和刑罚执行阶段,行为人不管是对刑罚的理解能力丧失,还是承受刑罚的能力丧失,都属于丧失了刑事责任能力。
以上两者在阐述刑事责任能力时体现的角度并不一致,前者是以行为人犯罪为视角进行分析,对无行为能力之人不追究道义责任;后者则以刑罚目的角度进行阐释,考虑改造目的,对无受刑能力之人暂不追究其社会责任。矫枉往往容易过正,当长期被蒙蔽的观点被揭示和提出,便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刑事责任能力的内涵界定问题上,我们断然不可采取一种片面而简单化的观点。尽管两者的角度不同,但也不是完全排斥的关系,其界限并不截然分开,行为能力与受刑能力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基于刑罚的报应目的,刑罚是对具有行为能力的人犯罪进行报应;而刑罚又追求功利的目的——预防目的(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行为人能够理解刑罚教育改造的意义,才有可能达到预防其重新犯罪的效果。刑罚的适用对象只能是具有行为能力且能承受并理解刑罚的行为人。因此,有观点指出,“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能力与受刑能力的统一”[14]。即行为人兼有行为能力和受刑能力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因实施犯罪且能承受刑罚而产生。
职是之故,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扩张解释,重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主体,不具有行为能力和受刑能力的行为人都不具有刑事责任。只不过不具有行为能力的行为人,在此状态期间所实施的行为,是永久性的不负有刑事责任;不具有受刑能力的行为人,在此状态期间不能理解刑事审判和刑罚的意义,只是暂时性的不承担刑事责任。如此,“有罪有病”的精神病患者就能纳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中,在通过强制医疗将其治愈,恢复受刑能力之后,则依然需要对其继续进行刑事审判或执行刑罚。这也为司法实践中处理因精神病而无受审能力和受刑能力的行为人提供了法律根据,既能保证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又能通过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减少其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还能兼顾刑事程序中多方适用主体的利益,彰显强制医疗制度独特的属性与解决纠纷机能,从而提高刑事法的自身价值,表明其人道性和公正性。
三、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参与主体的再诠释
国家于维护公共福利与保障个人基本人权的平衡实为难事。尽管如此,也不能以维护“公共福利”的名义限制基本人权。对公共福利的追求应建立在与之相应的公正程序之上[15]。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虽有一定行政化的倾向[16],但对“有病无罪”的精神病患者和“有罪有病”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医疗并不会脱离刑事程序的制约。
基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独特属性和解决纠纷的功能,其程序的启动和结果都牵动多方主体利益。因此,程序的公正、透明就显得尤为重要,备受社会的关注。通过重构强制医疗程序参与主体的范围,保障参与主体的权利,也能制衡和监督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有效运行。毕竟以程序构建为重点,建立司法审查程序为核心的强制医疗制度彰显其制度价值就在于需贯彻程序法定原则和司法审查的原则[17]。首先,通过对刑事强制医疗适用主体范围的重构,将“有病无罪”和“有罪有病”的两类精神病患者纳入规范性的治疗轨道。其次,通过司法审查对重构后参与主体的权利进行保障,确保各方利益特别是被害人一方的利益得到平衡。
(一)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一般启动主体
明确刑事强制医疗的启动主体,对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可分为两类,即附属性的启动主体和独立性的启动主体。
1.附属性的启动主体。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机关又是司法机关,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所受制约和监督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因此,《精神卫生法》中规定其协助精神病患者治疗的行政性职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公安机关的行政职能则是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行为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其强制精神病患者治疗的司法性职能应有所区分。此种二元体制决定了只有属于刑事违法行为才能适用刑事强制医疗[18]。同时也划定了,公安机关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践行司法职能的范围。
对于“有病无罪”的精神病患者,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依附于刑事普通程序,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拥有事实探知和信息收集的能力,较容易确定行为人的精神状况。经过依法鉴定之后,如果医疗机构鉴定行为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对其作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检察机关。由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单向性,公安机关出具的强制医疗意见书须受检察机关的审查和监督,而不能直接向法院启动此程序。因此,公安机关并不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独立的启动主体,而具有附属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后30日以内作出是否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因此,相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控制了启动权。。
2.独立性的启动主体。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贯穿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所有环节,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审查和监督机关。针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监督公安机关递交强制医疗意见书;针对法院,人民检察院又可以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根据医疗机构的鉴定意见,依职权决定中止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而自行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因此,人民检察院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独立性。
3.独立性的启动和决定主体。强制医疗程序是依据法官的决定权而确立的程序,人民法院的决定在此程序中具有最终性。对于检察院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以及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行为人是疑似精神病患者,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则可以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当然,经过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两道审查程序仍有遗漏,法院偶然发现被告人不具有行为能力而自行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是作为补救的备用手段。如果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因突发精神病而不具有受审能力,法院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则是为了刑事审判公正性的保障手段。
法院不能将医疗鉴定机构的医疗意见作为决定的唯一依据,而意见只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参考医疗鉴定机构给出的医疗判断后,法院还要进行是否予以适用的司法判断。
(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特别附属性启动主体
上文通过重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主体,将无受刑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纳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但是针对此类适用主体如何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也是应解决的问题。基于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独立启动主体的限制,对于在看守所或监狱服刑期间,因发生精神紊乱而不具有受刑能力的行为人,看守所或监狱也面临如何处置行为人的难题。
由于监狱的侦查权都是在《刑事诉讼法》的附则中予以规定的,看守所或监狱是否有资格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则更无明文的规定。虽有人指出可以通过《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应当采用强制性住院治疗[19],然而,以此种行政化的思路,即无程序制衡,自行启动、自己决定,虽较为便利,不过却有违程序公正。之所以把强制医疗司法化而非行政化,就在于行政性强制医疗不能受到司法审查,而刑事诉讼程序更有利于保障行为人所应有的权利。
而且我们需要看到,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看守所或监狱与公安机关一样都具有侦查职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又附则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由此,在一定条件下,公安机关和监狱都可履行刑事侦查职能,都是刑事侦查机关,应当可做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然后应移送人民检察院。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独立启动主体则只能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因而亦如公安机关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所具有的附属性,看守所或监狱也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对发生精神紊乱的服刑人员进行刑事强制医疗的意见,由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按照强制医疗的程序进行审理,最终决定服刑人员是否适用强制医疗。如此,看守所或监狱通过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处置无受刑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从而化解此类主体无法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及监狱或看守所也无法对其进行处置的难题。
(三)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其他参与主体
从表面观察,似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只规定了上述司法机关的职责,对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保障有所欠缺甚至无任何规定。但究其实质,其权利保障精神已经蕴涵于程序的其他规定之中。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则无需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至第二百八十九条中再次规定。
1.律师的程序参与。律师在刑事程序中能够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补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足,且有助于法庭查明事实。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即使《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则、解释均未明确规定审判前律师是否有资格对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但也无规定限制律师为其提供帮助。那么,律师应当可以成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参与主体。
从域外经验看,《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第438条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7款都规定律师必须参加适用强制医疗措施诉讼。在美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庭审中,律师基于精神病患者的利益,可以质疑强制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0];从法理角度看,既然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都有获得法律帮助权*《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那么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就更应当有资格获得法律帮助权;从现实依据看,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解释》)也明确“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有关规定”。精神病患者由此可以参照刑事案件的普通程序执行相关规定。
因此,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律师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帮助权不是没有规定,而是隐藏于法条背后,需要我们通过法教义学的进路,参照域外经验,根据体系解释得出。
2.被害人及近亲属的庭审参与。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权的同时也在于实现公正,我们不能忽略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和损失的弥补。如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被严重边缘化,成为“旁观者”,将违背司法正义的内在价值。这不仅不利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而且不利于法院形成正确的判断。即使法院作出决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也可能因为不服而申诉,容易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甚至会出现反复申诉、上访或其他过激行为,从而造成新的社会矛盾[21]。在庭审中,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参与权,使之成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参与主体,能够成为其感情宣泄的渠道之一,对于减轻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内心的痛苦,弥补其心理创伤,修复被破坏的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庭审参与权类似于精神病患者的法律保障权之规定。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虽无明确规定,但依然可从刑事法及其解释的总体精神层面得以把握,参照适用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有关规定赋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庭审参与权。被害人可以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并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而无需再通过修改立法实现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庭审参与权的保障。以此,可以充分发挥公权力主体之外的其他参与人的监督作用,通过保障其权利的行使得以制衡权力的恣意。
3.鉴定人的诉讼参与。鉴定人的活动贯穿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在刑事侦查阶段,专业医疗机构就可以提出鉴定意见,从而引导公安机关做出刑事强制医疗的意见书;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根据鉴定意见做出是否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申请;在审理阶段,鉴定意见将对法院是否做出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具有资质的鉴定人作出的专业判断一般应推定为正确,除非治疗决定会实质性地偏离鉴定人的医疗专业判断*See Youngberg v.Romeo,457 U.S.307 (1982).。鉴定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挥其自身作用,能够帮助法庭查清事实。
当然,对于一份强制医疗的鉴定意见,也必须经过法庭的质证、辩论的程序,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辩论不仅仅是程序正当及形式理性的要求,也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重要方式。在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持有不同观点之时,应有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做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不出庭的后果影响的不只是具体个案的正当性,而且会影响到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是关系着司法公正与程序正当不可忽视的环节。在美国Alabama州的法院就有精神健康专业的医生,专司在法庭审理中对被指控供人的精神状况进行阐述,以确保法庭基于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决定[22]。德国的《刑事诉讼法》第415条第(5)项也规定在庭审中要对鉴定人就被指控人的状况予以问询。既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可以帮助法庭作出适当的决定,能够有效防止因采信有偏差的鉴定意见造成不利后果,因此,基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解释》的精神,这一规定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也应适用。
四、破局与重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价值优化
在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仅仅依靠完备的立法,更依靠精细的司法。不能以立法简单化、行政化倾向为由就否定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价值,改变“决定”的行政色彩,将其司法化坚持到底。刑事强制治疗具有合法利益的基础,体现在通过合法、合理的司法程序的确立对精神病患者采取强制医疗*See O.Connor v.Donaldson,422 U.S.563 (1975).。
第一,强制医疗措施在于其是改善当事人的健康状态以及恢复其精神正常的治疗性质的措施,目的不仅是监督和保护,而且是改善和治疗。如此,就更应当排除一切损害人的人格与尊严的方法[23]。离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保护,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价值将会在根本上失去其意义。
第二,为了防止维稳思维中出现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异化为刑罚执行的替代性措施,必须严格贯彻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程序法定原则和司法审查的原则,从而平衡各方利益。在程序中不管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司法机关,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精神病患者,其利益都不具有排他的正当性。权力应以仁慈的面目出现,在程序的运作中,各主体相互作用,在国家与个人利益之间、精神病患者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之间维持其最基本的平衡。确保司法过程的公正性、人道性和合理性,强制医疗的效果将更加深入人心。
第三,在日益提倡规则治理和公正的社会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保护公民自由和实现公正的机能。防止滥用权力的方式之一,就是以透明、公正的程序约束权力。虽然公民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自由受到限制,但也是基于公共利益,囿于最低和必要的限度,并在程序中仍然为其配置了一系列的救济途径和制约方法。司法程序对公民自由保护的精髓,就在于实现社会公正的同时,制约权力恣意。
由此,对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主体范围进行重构,消解其模糊性,坚守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独特的价值属性——非惩罚性。解构传统观点中强制医疗程序的主体范围,突破其中所具有的思维定势,以刑事法的基本精神和人权保障机能为视角,从而得以重构程序主体范围。首先,将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有病无罪”模式和“有罪有病”模式的精神病患者的强制医疗统一纳入刑事特别程序。其次,强化程序中参与主体的权利,得以优化程序的合理性。一方面,保障真正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患者得到隔离和治疗,避免悲剧重复上演;另一方面,以相对公正、合理的保障参与主体权利的程序堵截权力的专横,防止个别人滥用权力而达到不正当目的,将精神正常人或者根本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医疗。通过法教义学进路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予以分析,其最终目的在于此制度能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并通过不断的解释得以优化。依靠程序公正的运作机制,通过司法机关与医疗机构之间相互支持、配合,构建规范的司法体系、创造完善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24],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平衡和化解社会防卫和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之间的矛盾。
[1] [日]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91.
[2][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M].王秀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25;[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1.
[3]R.A.Duff,Punishment,Communication,and Commun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84.
[4]李妍.我们的病人: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J].中国经济周刊,2011,(28).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1.
[6]倪润.强制医疗程序中“社会危险性”评价机制之细化[J].法学,2012,(11).
[7]张品泽.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4).
[8]李娜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适用对象之研究[J].法学杂志,2012,(10);奚玮,宁金强.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界定与程序完善[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3,(5).
[9]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J].环球法律评论,2010,(3).
[10][英]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M].李贵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46.
[11]温薷.北京精神科病床缺口达6000张[N].新京报,2013-07-15.
[1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80.
[13]侯国云,么惠君.必须将行为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区别开来[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5).
[14]赵秉志.犯罪主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6;马克昌.责任能力比较研究[J].现代法学,2001,(3).
[15][日]高田卓尔.刑事訴訟法[M].东京:青林書院,1959.28-29;[日]田宫裕.刑事訴訟法[M].东京:有斐閣,1996.12.
[16]张晓凤.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J].求是学刊,2014,(6).
[17]陈卫东.构建中国特色刑事特别程序[J].中国法学,2011,(6).
[18]王志坤.强制医疗程序及其检察监督[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6).
[19]张品泽.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与反思[J].中国司法鉴定,2014,(1).
[20]胡肖华,董丽君.美国精神病人强制住院治疗法律制度及其借鉴[J].法律科学,2014,(3).
[21]邓思清.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及法律监督制度[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6).
[22]Reese Mckinney.JR.Involuntary Commitment,a Delicate Balance.20 The Quinnipiac Probate Law Journal.38( 2007).
[23][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M].卢建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28-130.
[24][日]森久智江.障害のある犯罪行為者に対する刑事司法手続についての一考察[J].立命館法学,2009,(5·6 ).
责任编辑:王瑞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Procedure with Dogmatics of Law
Li ZhiTong Weihua
(LawSchool,HainanUniversity,HaikouHainan570228)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stablished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and promoted the judicialization of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system in China.But the law on the scope of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being lack of clear rules,has weakened the fun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define the offender’s “criminal capacity” by Rechtsdogmatik.People,who are not capable of active ability or penal ability,do not need to bear responsibility in criminal law.So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applies to both of the above.By collaboration between judicial organ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we should guarantee the value of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system in the investigation,prosecution,trial and execution.This will strengthen the value of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realize the unity of practical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and elimin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 defense and criminal liability which no one is responsible for.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criminal capacity;active ability;ability of torture
2015-11-16
李至(1991—),男,湖南益阳人,海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刑事法学、犯罪学;童伟华(1971—),男,湖南岳阳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博士后,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 刑事法学。
D925.2
A
2095-3275(2016)03-0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