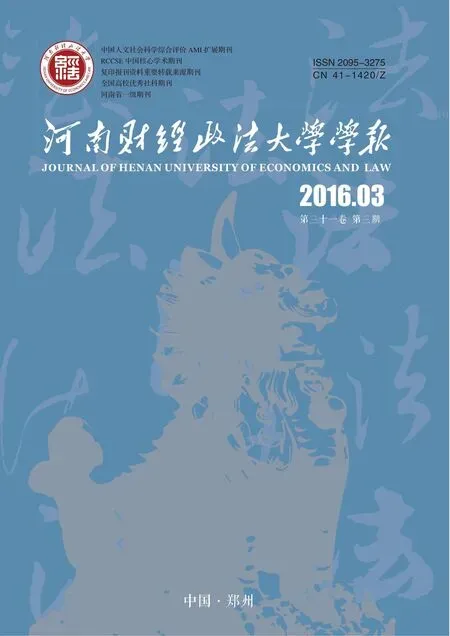宪法解释的诡谲
——管窥日本宪法第9条的解释
2016-03-06高慧铭高丹丽
高慧铭 高丹丽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宪法解释的诡谲
——管窥日本宪法第9条的解释
高慧铭高丹丽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日本宪法第9条的原意是放弃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严格的修宪程序致使修宪未果,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释宪,一步步地释宪最终造成了“第9条与自卫队存在”这一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所谓的宪法变迁,但违背宪法精神的宪法变迁是否具备正当性值得我们深思。
日本宪法第9条;原旨主义;宪法解释;宪法变迁
日本宪法第9条*日本国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了达到前款目的,永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是最具日本特色的条款之一。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切反思,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的《日本国宪法》采用“和平主义”作为其基本原理之一*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基本原理,即麦克阿瑟三原则,可概括为尊重基本人权、和平主义以及国民主权三大原则。,其内涵体现为:第一,放弃包括侵略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武力的行使以及武力的威胁;第二,为贯彻前项内容,宣示不保持战斗力;第三,否认国家的交战权[1]。故该宪法也被形象地称为“和平宪法”。值得注意的是,第9条是该宪法前言规定的“和平主义”原理*和平主义原理最早源于麦克阿瑟草案,是著名的麦克阿瑟三原则之一,即:“放弃作为国家主权性之权利的战争。日本放弃作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手段的战争,以及作为保持本国安全之手段的战争。日本的防卫与保护,应委之于当今世界正开始推动的崇高理想。绝不允许设立任何的日本陆海空军,也决不赋予日本军队任何交战权。”以及宪法第二章“放弃战争”之唯一条款。此条款足以彰显二战过后的日本国民彻底否定战争之态度坚决。
一、日本宪法第9条的形成
为了更好把握第9条的原意,首先需要了解该部宪法制定时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于1945年8月14日接受了反法西斯盟国签署的休战条约——《波茨坦宣言》,并于次日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该休战条约在内容上规定了日本方面应于战后修改明治宪法,具体体现在该条约第10款*第10款规定:“……日本政府应去除日本国民之间复活强化民主主义倾向之一切障碍,应确立言论、宗教与思想之自由以及基本人权之尊重。”与第12款*第12款规定:“于前述诸项目已达成,且依日本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思,具和平倾向且负责任的政府建立之时,盟国占领军应立即撤出日本国。”的表述中。依据该条约,日本被置于盟国的管理之下,天皇及其国家机关被置于为实施《波茨坦宣言》的条款而采取必要措施的盟国最高统帅的权力之下,并受其发布的所有指令的约束,盟军总司令部*盟军总司令部的权力依据来自日本国对《波茨坦宣言》的接受以及盟军对战败国日本的实际占领。即是推动日本宪法制定的重要因素[2]。
1945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国务大臣松本蒸治为首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松本委员会),着手对明治宪法进行修改*1945年10月8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日本政府体系改革的初步政策,并将其发给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要求“给日本当局改革政府体制的机会”。10月11日,币原首相造访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就向其发布了“五项改革指令”,并暗示其“明治宪法必须自由主义化”。于是,在同月的25日成立了松本委员会。。松本委员会于1946年2月8日将其起草的宪法草案提交给盟军总司令部。盟军总司令部认为该宪法草案的内容过于保守,不符合《波茨坦宣言》的基本精神,于是,盟军总司令部于同年2月13日召开的草案提示会谈中将其自行草拟的宪法草案(即麦克阿瑟宪法草案)交给日本政府。在盟军的操控下,日本政府决定依据盟军总司令部自拟的麦克阿瑟草案重新制定宪法草案,最终于1947年重新制定了新宪法。
此外,根据题为《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中“鼓励个人自由的愿望和民主进程”(编号为SWNCC150/4)的文件,盟军总部在1945年10月4日发布了“公民自由指令”*United States Initial Post-Surrender Policy for Japan(SWNCC150/4)[Z].U.S.State Department Recorrds Decimal File 1945-1949,“740.00119P.W./9-645”,Roll No.3,U.S.National Archives.P48、52.。根据该指令,币原内阁废除了限制人民思想、宗教、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法律;释放了3000多名政治犯;解散了秘密警察组织。这些措施使得日本国内进步力量的发展成为了可能*例如上文提到的《每日新闻》,该报刊在报道松本宪法草案时,对该草案作出“过于保守和维持现状”的评价,可见日本媒体便从战时的军国主义宣传工具变为一支推动宪法修改的进步力量。。
日本政府再三斟酌下最终依据麦克阿瑟宪法草案制定了日本宪法草案,自然,麦克阿瑟的和平原则便被写入日本宪法草案,成为最受瞩目的第9条。
在该草案进行批准的过程中,日本众议院对其进行了一些修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宪法第9条进行的修改。时任日本众议院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长的芦田在第9条第一句前面加了“(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Aspring sincerely to an international peace based on justice and order;日本国民は、正義と秩序を基調とする国際平和を誠実に希求し)”;在第二段前加了“为了上述目的(For the above purpose;上記の目的のために)”,之后,贵族院在审议时又将该句改为:“为了达成前款目的(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aim of the proceeding paragraph;前項の目的を達するため)。”[3]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芦田修正”,日本宪法第9条最终形成。
二、日本宪法第9条的原意
1951年,盟军结束了对日占领,日本国内对第9条的讨论也随之增多。针对第9条的原意,存在着两种迥异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基于日本国和平宪法制定的背景,该条制定时的原意应是放弃一切战争,包括了自卫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因为但凡战争无不是用以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以及远东委员会最后都默许了宪法草案批准过程中芦田的修正,那么表示他们也默许了日本将来发展自卫力量,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因此,宪法第9条的原意仅仅是放弃侵略战争,而不包括放弃用于自卫的战争力量。
原旨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宪法应当按照起草和批准时公认的理解予以解释[4]。因而,要把握第9条的原意,应当全面分析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对第9条的理解、宪法制定时日本政府对第9条的理解以及芦田修正对第9条的影响。
如前所述,盟军总司令部尤其是麦克阿瑟草案对日本宪法第9条的制定有重大影响。因此,对第9条进行原意解读的关键就在于麦克阿瑟方面对第9条的理解。一方面,“麦克阿瑟备忘录”中认为,日本应“放弃作为国家主权性之权利的战争。放弃作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手段的战争,已经作为保持本国安全之手段的战争”,至于日本的防卫与安全则应“委之于当今世界正开始推动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麦克阿瑟个人在不同场合中也多次强调过这一意图。可见,麦克阿瑟在制定宪法草案时是坚决主张日本放弃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的。
其次,对我们了解第9条原意有重要帮助的还有宪法制定时的日本政府。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国会讨论宪法草案时的答辩中曾这样谈及自卫权和自卫战争:虽然第9条没有直接否定自卫权,但将作为自卫权的战争与交战权都放弃了。二战时期的战争各国均是以自卫权为名而战的,所以在日本不论以何种名义,首先就从自己开始放弃了交战权[5]。他还明确指出:以国家正当防卫权为名义而承认战争的行为是有害的;将交战权区分为自卫性质的交战权与侵略性质的交战权也是有害无益的。由此可见,制宪时的日本政府对第9条的官方理解也应是放弃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
再次,至于芦田修正,单从上文所述的英文文本看,很显然无法涵盖其修改的目的能使日本拥有自卫权。尽管后来芦田在《第9条修改的经过与理由》中明确指出修正的目的在于“即便根据现行宪法的原文,保持自卫军事力量的行为也是理所当然,不违反宪法的”。这后一解释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很难令人信服。
此外,当时的日本宪法学者对第9条的解读也有助于我们对其原意的探析。如当时著名的宪法学者美浓布达吉(东京大学教授)在其著作《日本新宪法精义》一书中对第9条进行的解释:有权进行自卫战争乃一国生存之所必须,所以在日本之前未曾有一国曾放弃过进行自卫战争的权利,唯独日本因为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缘故,作了世界上没有前例的绝对抛弃战争的宣言[6]。此后,美浓布达吉的学生宫泽俊义又在1955年出版的《日本国宪法精解》中明确将第9条解读为“放弃一切战争和完全废除军备”[7]。
综上所述,由于第9条是在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等情况下制定的,而《波茨坦宣言》中明文规定要完全解除日本的一切武装力量,加之麦克阿瑟草案以及后来的芦田修正英文原本,可以揭示出宪法第9条的原意应为放弃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并禁止保持任何战争力量。
三、第9条的修改浪潮
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治风向右倾,日本国内的修宪浪潮不断高涨,作为和平主义条款的第9条无疑成为日本国迈向政治军事大国的严重束缚。因此,对如鲠在喉的第9条,日本政府颇费心思。日本国内护宪派与修宪派的纷争跌宕起伏、暗潮汹涌。
(一) 修宪态势
二战后的日本虽然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了和平宪法,但是由于冷战的开始,美国无暇对日进行彻底改造,致使岸信介、崇光葵等一大批原先被整肃的政治家有机会重新踏入政坛并出任要职,开始主张修宪。1954年鸠山一郎当选首相后大肆鼓吹修宪极具紧迫性、必要性,并将茅头直指第9条。1955年自由民主党诞生,并将“自主修宪”写入党纲,作为该党出身的首任首相,鸠山一郎在国会强行通过《宪法调查会法令》。1957年岸信介当选日本首相,继续推行鸠山内阁的修宪主张,并根据《宪法调查会法令》,成立了由国会议员和资深学者组成的宪法调查委员会[8]。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口号,修宪势力再度活跃,以日本外务省提出所谓的“讨论防卫问题”为契机掀起了新一轮修宪浪潮。1982年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相的内阁执掌政权,大力推行修宪主张,加快修宪进程。中曾根内阁时期的法务大臣也标榜“宪法应当反映本国民众的真实愿望,而该部宪法是被强加的、非自主性的宪法”,试图挑起国民修宪的热情,各党派也纷纷卷入修宪浪潮之中[9]。
冷战结束后,国内的修宪讨论愈演愈烈。1994年社会党与自民党联盟,主张维护和平宪法、认为自卫队违宪的社会党,抛弃以往的原则,加入到修宪派阵营中[10]。战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和平主义”思潮趋弱,“新国家主义”思潮不断上升,而此时披着“维护民族自主权”外衣的修宪主张深得人心[11]。这一时期的修宪派又将茅头指向第9条,集中体现为2000年自民党桥本派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要求直接修改宪法第9条,以增强日本军事力量。
21世纪的修宪风波更是气势汹涌,从小泉纯一郎到野田佳彦,再到安倍晋三,这几位首相都肆无忌惮地提出修改和平宪法。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上台后便提出重新审视集体自卫权问题,在其执政后期着手推动修宪。2005年参众两院宪法调查会公布了修宪《最终报告书》,结束了“论宪”阶段。11月自民党正式提出“新宪法草案”。2007年日本众议院通过《国民投票法》,允许就修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并制定相关法律程序,进而解决了修宪的程序问题[12]*参见新浪新闻:《日本众议院通过〈国民投票法〉 公决法案为修宪铺路》,2007年4月14日,http://news.sina.com.cn/w/2007-04-14/023711635512s.shtml,访问时期:2015年9月20日。。2012年野田佳彦首相公开表示修改宪法以重新定义“集体自卫权”。同年,安倍晋三二次当选首相,更是露骨地宣传修宪思想。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示有意对规定修宪提案条件的宪法第96条进行修改。之后,安倍就修宪解释事宜召开专家会议,进一步加紧鼓吹修宪,并且明确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13]。2014年6月13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企图将修宪议案提交全民公投表决[14]。2015年2月26日,自民党召开修宪推进总部会议,提出将把“在第9条中写明创设国防军”和“放宽第96条的修宪提议条件”等作为特别重要项目[15]。
(二)修宪未果的原因
日本宪法自颁行以来,国内的修宪浪潮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但至今尚未实现对宪法文本的修改,这是因为和平宪法作为一部刚性宪法,规定了极为严格的修宪程序。宪法第96条规定:本宪法的修正,必须通过国会经各议院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而提议,并向国民提案,且经其承认。此项承认,必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举行的投票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各议院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方可提议以及“国民投票中的过半数的赞成”方可通过这两个要件,使得日本宪法的刚性程度更强。具体说,在国会层面,虽然从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以来,自民党掌握了政权,成为所谓的“万年执政党”,但是,社会党统一后在国会中所占的议席增加到156席,外加共产党和劳农党也占据6个席位,此外还有反对修宪的在野党所占的席位也多达三分之一,因此,修宪在国会内部已不可能[16];其次,在日本国民层面,由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尤其是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大多数民众极为认可第9条绝对和平主义条款,宪法第9条所确立的和平主义原理早已深深扎根于包括许多自民党成员在内的多数日本民众心中,故通过国民公决修改第9条的做法也难以实现。
因此,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修改宪法第9条来解决发展自卫队、重整军备的合宪性问题便不具有可行性。
四、日本宪法第9条含义的蜕变
修宪虽未果,但是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却不断地通过宪法解释,事实上改变着第9条的内涵与外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与修宪相同的目的。
日本宪法并未直接规定解释宪法的主体,依据宪法第81条*日本国宪法第81条规定:“最高法院,是拥有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或处分是否符合宪法之权限的终审法院。”之规定,实际上将违宪审查这一被动解释宪法的权限赋予了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在涉及第9条问题上始终采取回避态度。在司法实践中,有关自卫队的合宪性问题,诉讼上也曾发生过多次纷争,最受关注的有“惠庭案件”和“长沼案件”。在“惠庭案件”中,最高法院通过对《自卫队法》进行严格解释作出了判决,未涉入宪法判断,从而回避了对自卫队问题的合宪性审查问题;在“长沼案件”中,最高法院也在完全没有论及自卫队之合宪性问题的情形下终结了诉讼。直至今日,最高法院仅有9个案件被判决违宪,且均未涉及第9条[17]。与之相反,自吉田茂首相在国会就新宪法作出答辩、对第9条进行阐述之日起,针对第9条的宪法解释均是由内阁法制局作出的,其权限渊源来自宪法第65条*日本国宪法第65条规定:“行政权属于内阁。”规定的行政权归属内阁,日本政府认为自卫队属于行政编制,日本内阁因而具有解释宪法上的自卫队的权限[18]。因此,事实上由内阁法制局掌控释宪权,内阁法制局的合宪审查结果成为政府正式观点,并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的宪法解释。
(一)最初的原旨主义
日本宪法颁布前后,一直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一方面,美国将对日占领的政策确定为“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在日本国内积极推行非军国主义化,并进行民主化改革;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由于经受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惨痛打击,以吉田茂为首相的日本政府也将工作重点放在战后恢复上。1946年吉田茂首相在国会发言中明确表示:关于宪法中放弃战争的规定,虽未直接否定自卫权,但在第9条第2款中不承认一切军备及国家交战权,其结果是放弃了依自卫权发动的战争或交战权[19]。可见,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府对于第9条的解释是基本符合该条款的原意,即倾向于否定国家自卫权。
(二)原旨主义的背反
随着战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最初的惩罚性改革转变为战略性利用。以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契机,盟军总司令部层要求日方组建一支75000人组成的警察预备队。在这一情势下,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对第9条的态度上发生转变——开始认可自卫权,在1950年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吉田茂首相明确指出:彻底贯彻放弃战争的旨趣,绝不意味着放弃自卫权。在这之后的国会答辩中又表示其所指称的“自卫权”不包括以武力方式行使的国家自卫权[20]。1952年日美两国缔结《日美安保条约》,形成了“美日同盟”,日本开始重新考虑国家的武装问题。1954年,日本政府进一步释宪,宣称自卫权乃是一个独立国家当然具有之权利,宪法并未否定此项权利;宪法规定放弃战争,但并未规定放弃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拥有自卫队并不违宪。并提出了行使自卫权的三项条件[21]。同年6、7月份,吉田内阁依据该项解释促成国会通过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即“防卫二法”),并据此将保安队和警备队改组成为一支拥有165000人的陆海空三军自卫队。至此,日本政府完全颠覆了由其作出的先前的解释。
从1955年开始,鸠山内阁对自卫权采取了更为扩大性的解释:自卫权作为国家所固有的权利,即使在宪法第9条上也未被否认。因此,拥有为了行使自卫权的实力,也为宪法所允许,即为了自卫而所拥有的必要最小限度之实力,并非是宪法所禁止保持的“战争力量”[22]。经过鸠山内阁的这一解释,日本政府不仅认可了国家的自卫权,使自卫权具有了合宪性,而且使“必要最小限度”这一自由裁量极为宽泛的模糊界定成为战后日本发展自卫队力量的限定标准。这样,日本政府便通过对第9条的扩大解释,在明确认可自卫权的基础上,将有悖于和平宪法旨趣的重整军备行为演变成可由政府自主裁量的政府行为。
1957年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自卫权”的范围,宣称在敌方导弹未发射时,为防止受到攻击,打击对方导弹基地的行为,法理上属于自卫权。此次释宪实际上赋予了日本政府在战争问题上先发制人的权利。1960年日美双方缔结了新《安保条约》,约定当事国一方受到武力攻击时,双方必须共同应对,不过这里所谓的相互防卫仅限于对日本统辖领土施加的武力攻击。1962年,日本政府宣称“在公海上排除对日本船只的武力攻击,也在宪法允许的范围之内”[23]。自此,自卫队保卫的对象由本土扩大到公海上的日本船只。1969年与1978年的政府宣称,宪法禁止日本拥有能够毁灭其他国家的武器,如洲际导弹、远程轰炸机等,但F-15战斗机、P-3C预警机等属于并非对其他国家产生威胁之武器,因此在宪法允许的范围之内,日本可根据国际形势与科技发展等条件,在自卫范围内增强武力。
冷战期间,日本政府通过释宪实现了自卫队的“合宪化”,并不断扩大自卫权的范围。但是,这一时期的释宪却禁止实施集体自卫权与海外派兵行为。日本政府认为,在冷战格局下,应当对自卫队的使用范围加以限制,避免卷入美苏争霸战中,以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参议院出于对政府向海外派兵的担心,于1954年6月2日通过了“关于不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决议”;次日,吉田内阁外务省条约局长下田武三又在众议院会议上针对《相互援助防卫协定》中所涉及的集体自卫权做出解释:“本国被攻击时的自卫权”可视为“不能与别国缔结规定行使集体自卫权并相互防御的共同防御条约”,其根据即为宪法第9条第2款*日本第19回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录第57号。。
1972年10月,日本政府释宪称:日本既然是主权国家,当然拥有国际法上的集体自卫权。但是在宪法第9条之下,可被容许的自卫权的行使已被解释成为“仅限于防卫我国所需的‘必要最小限度’”,而行使集体自卫权将超出这一范围,宪法上不被允许。根据该宪法解释,日美双方虽有同盟关系,美国可以在日本遭受攻击时助战,但日本却不能派兵协防美国。
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对应,1954年在创立自卫队时,日本参议院作出决议:根据现行宪法与国民炙热的爱好和平的精神,日本不派兵海外。并于1973年进一步明确释宪:根据宪法第9条第1款放弃战争之规定,海外派兵之行为超越了自卫权的界限,应予以禁止。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认为,向海外派兵参加国际合作可以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故于1991年释宪称:即便由各国组成的维和部队行使武力,若日本派出的维和部队确保与此武力的行使“不一体化”,则并不违反宪法第9条[24]。1992年日本国会便通过了《联合国维和行动法》,从法律上为为自卫队首次走出国门扫除了障碍。1997年日美双方制定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日方应当在亚太地区对美军进行后方支援。1999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周边事态法》等国内相关法,通过扩大对周边“事态”的解释,将个别自卫权与集体自卫权之间的灰色地带作为个别自卫权加以定性,实质上突破了“集体自卫权”的禁区[25]。
2014年7月1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召开安全保障法制建设磋商会,就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定案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内阁决议以对日本宪法第9条做出“重新解释”的方式,修改了1972年的宪法解释,宣称随着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即便是对其他国家的武力攻击,也可能威胁到日本的生存,因此行使集体自卫权被包含在“必要最小限度”的范围内,日本享有集体自卫权[26]。2015年7月16日,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幅转变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安保相关法案。同年9月19日,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自此日本在法律上便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27]。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二战后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日本已经彻底告别二战结束以来由日本宪法所规定与实施的、以“非战”为核心的防卫体制,未来的日本将因此而重新拥有“战争权”,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拥有动用武力和军事手段的权力,致使宪法第9条否定战争与交战权的条文已近同虚设。
(三)第9条变迁的反思
从各国的宪政实践看,日本国政府对和平宪法第9条的扩大解释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其独特之处表现为:一方面,日本国宪法自1947年实施以来,已愈半个世纪,宪法文本从未有过变动,这使得该部宪法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之一;另一方面,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却通过宪法解释、制定法律等方式不断背离着第9条和平条款的原意,造成所谓的“宪法变迁”*“宪法变迁”概念由德国公法学者拉班德(Paul Laband)于1895年在《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变迁》一书中首次提出,后由耶林内克(Georg Jellinek)最先建构宪法变迁的理论体系。宪法变迁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除宪法修改之外的一切变化,包括宪法的废弃、废止、破毁及停止;狭义上是指宪法条文未修改,而现实上发生宪法内涵变化的现象,这也是自拉班德、耶林内克以来学者们普遍认同的概念。。
这样问题就来了,当产生与宪法规范的原意相背离之社会现实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是否能够认为发生了与修改宪法规范相同的法律效果?
关于宪法变迁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1)事实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宪法状态中不应允许新的宪法规范的产生。宪政实践中存在的违反宪法规范的社会现实实质是对宪法权威的侵犯,构成事实上的违宪,而宪法变迁实际上对这种违宪事实的认可,不应提倡。(2)习惯法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宪法状态中所产生的宪法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宪法上的习惯法。随着社会发展,规范与现实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成文宪法规范实效性的发挥遇到障碍时新的宪法规范便以习惯法的形式出现,起到充实宪法规范内容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矛盾,避免宪政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规范空白。(3)习律说是根据英国宪政理论中的习律概念来说明宪法变迁的法律性质。该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实效规范不仅是一种违宪行为,而且不宜以习惯法的形式完全承认其法的性质。宪法变迁作为一种习律,其法律性属于“低层次法”的范畴,有的学者把它表述为“未完成的变迁”[28]。
芦部信喜教授认为宪法变迁应当同时具备两个特征:(1)宪法文本虽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改变,但宪法规范的现实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2)这种变化是不违反宪法精神的。目前的日本宪法明显出现了规范与现实之间的背离,如果承认这种现象是宪法变迁,就会导致宪法规范的原意失去实效性,这种违宪的状态又该如何定性?对此,芦部信喜教授认为,有限的违宪状态达到一定的程度便具备一种法的性质,但这种违宪状态并不具有完整的作为宪法规范的性质。也就是说,仅可赋予此种违宪状态以宪法判例的效力,不能认可其具有与宪法规范相同的效力。这一观点是目前日本国内关于宪法变迁理论的通说。
宪法作为“活法”,应当不断适应变迁中社会的需求。一般而言,当规范与现实产生不一致时,可以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消除这种不一致现象。相反,若轻易认可宪法变迁的效果,则严格规定宪法修改程序的宪法本身的制度便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这本身就是违背宪法精神的。回顾日本宪法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主要是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有目的地推进,并不能代表民主意见,与国民主权原则相违背,其合法性始终是有争议的。而且对和平主义原则的改变也威胁到了日本宪法的精神,动摇了日本宪法的根基,如果承认宪法变迁的规范效力,只能继续加重规范与现实之间的背离。
[1][日]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M].高桥和之增订,林来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8.
[2][日]宫泽俊义.日本国宪法精解[M].芦部信喜修订,董璠舆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5.
[3]Koseki Shoichi,Japanizing the Constitution,Japan Quarterly[J].Vol.35,No.3(Jul. 1988),P237.
[4][美]基思·E.惠廷顿.宪法解释——文本含义,原初意图与司法审查[M].杜强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2.
[5][日]三浦隆.实践宪法学[M].李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57.
[6][日]美浓布达吉.日本新宪法精义[M].陈固亭译.南京:正中书局,1951.31.
[7][日]樋口阳一,大须贺明.日本国宪法资料集[M],三省堂出版社,1989.28.
[8][日]宫泽俊义.日本国宪法精解[M].芦部信喜修订,董璠舆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132.
[9]刘杰.战后日本“修宪”思潮论[J].外国问题研究,1995,(1).
[10]包霞琴.90年代后日本修宪论及其特点分析[J].日本研究,2004,(2).
[11]宋长军.对日本改宪问题的回顾与前瞻[J].比较法研究,2001,(3).
[12]参见新浪新闻:日本众议院通过《国民投票法》 公决法案为修宪铺路[EB/OL].2007-04-14,http://news.sina.com.cn/w/2007-04-14/023711635512s.shtml.
[13]管颖,吴琪.日本修宪与宪法第九条问题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3).
[14]参见凤凰财经.日本国会通过《国民投票法》[EB/OL].2014-06-14,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14/ 12540890-0.shtml.
[15]参见中国新闻网:《日本自民党探讨修宪议程,称难早日修改宪法第9条》,2015-02-26,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2-26/7082632.shtml.
[16]李寒梅,等. 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4.
[17]霍建岗.日本“修宪”、“释宪”的历史与现状[J].国际研究参考,2015,(3).
[18]管建强.论日本政府架空、废弃和平宪法的法理缺陷[J].法学评论,2014,(6).
[19][日]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戦後50年の模索[M].东京:东京読売新聞社,1997.28.
[20]陈道英.“解禁集体自卫权”与“超越”宪法解释[J].法学评论,2014,(6).
[21][日]浦田一郎.政府の憲法九条解釈[M].信山社,2013. 4.
[22][日]正村公宏.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01.
[23][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2005.59.
[24]金熙.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J].日本学刊,2002,(2).
[25]吴怀中.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的演变和影响[J].日本学刊,2007,(5).
[26]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容認、憲法解釈変更を閣議決定、戦後 の安保政策転換、首相“必要最小限で”》,[N].日本经济新闻,2014-07-02.
[27]参见新华网:《日本参议院强行表决通过安保法案》,2015年9月19日,http://japan.xinhuanet.com/ 2015-09/19/c-134639309-2.htm.
[28][日]川添利辛.宪法变迁的意义与性质[J].法学家,1985 年增刊。转引自韩大元.宪法变迁理论评析[J].法学评论,1994,(4).
责任编辑:邵东华
transformation
The Treacherous Vari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9 of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Gao HuimingGao Danli
(LawSchoolof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0001)
The Article 9 of Japanese Constitution is the Pacifism clause, which is to admit that Japan renounces all forms of warfare,including Self-Defense War.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uld not amend it although they tried their best, because of the strict procedure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S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focusing on interpreting it. These co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eventually led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riterion and reality—the existence of Article 9 and the Self-Defense Forces, and formed the so-called Co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this transformation violates the spirit and original intent of the Constitution. We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it has legitimacy.
Article 9 of Japanese Constitution; Fundamentalism;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2015-12-1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新兴基本权的形成与保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CFX006)。
高慧铭(1977—),女,河南濮阳人,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高丹丽(1990—),女,河南周口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D93/97;313;1
A
2095-3275(2016)03-015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