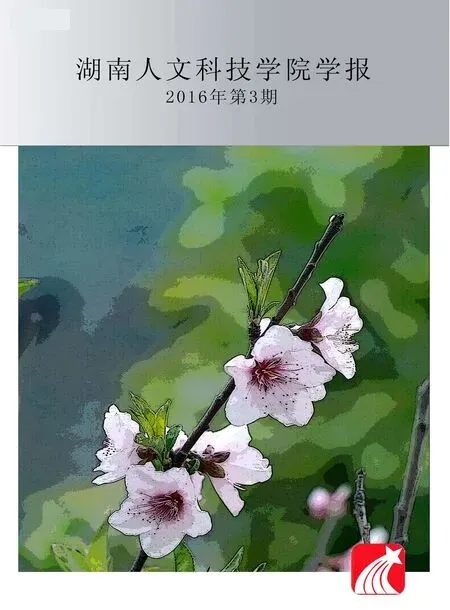“转型”语境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2016-03-06周兰桂
周兰桂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教育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转型”语境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周兰桂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教育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摘要]在“转型”作为时代语境与共名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必然成为高等教育调整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优化发展结构与路径、提高发展质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结构性系统风险的国家战略与正向优变的理性发展之路。“转型”语境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坚持以下几个“变”与“不变”:第一,高等教育追求效益与竞争的“市场化”程度可以变,而坚守独立、真理与大爱的大学精神不可变;第二,高等教育追求更科学合理的布局分层与结构系统可以变,而应坚守的高教规律与高校平等发展的权力不可变;第三,高等教育所设置的学科、专业与课程及教学方法可以变,而提高并坚守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主体终身发展的意识不可变;第四,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中的制度设置、办学主体及治理模式可以变,而追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及创新应用的本体存在不可变。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机遇与风险并行,应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以顺利地避免风险,走出转型发展中的误区与困境。
[关键词]“转型”语境;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正向优变;可变;不可变
“经济转型”“文化转型”“教育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转型发展,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济放缓的当下时代的语境与共名①。
虽然,发展、变化、改革、创新,是个体、行业、国家以及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但我们却并不太清楚如何去“转型”,转什么样的“型”,也甚至不太理解“转型”的辞源与语用涵义。从转动到转变到转轨再到转型,它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升级与系统优化”的过程,但要谨防将“转型”理解为“转向”。转型发展,即寻求新的发展出路,调整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优化发展路径,提高发展质量,破解发展难题,走出发展陷阱,是化解结构性系统风险的理性发展之路。
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战略,是在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常态”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我国高等教育在恢复高考与“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随着我国社会形态的全面升级与发展,从温饱到小康,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与发达国家逐步迈进,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人才需求链中的供求矛盾日益凸显,“用工荒”与“就业难”作为一对矛盾的社会问题被凸现出来,教育作为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极,虽然不可能承担矛盾与问题的全部,但是,也到了一个必须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是否必要?不言而喻。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是否可能?不证自明。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如何展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与此相关的,还有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基本诉求、现实路径与规避禁忌等一系列问题被连带着提了出来。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核心内容如果说是“创新与应用”,那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基本诉求则应该是“提质与优化”,因此,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提升质量,优化结构,突出特色,稳步发展。至于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中的规避与禁忌,特别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中的“变”与“不变”,需要我们理性、冷静与缜密地去思考和解决。
一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是教育正向优变的必由之路
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从内容到形式,从路径到方法,还是从诉求到现实,不外乎高等教育的体制活化、结构优化以及质量强化,归结起来,就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然而,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中的“变”与“不变”,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既是一个宏观的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微观层面的战术问题。从哲学层面看,“变”与“不变”,变则通,通则强,强则存,存则久;变者,可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不变者,不可变,以不变应万变。变分二相,一为正变,一为异变。正变向好,异变向坏。佛道之所谓“生、住、异、灭”②,生、住为正变,异、灭为反变。转型即正变,转型发展,则是正向优变,教育转型应该是一种正向优变的发展过程。
恢复高考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走过了近40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业绩,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支持中国社会快速前行的三大动力源(政治解冻、经济开放、恢复高考)之一。政治解冻的直接成果是思想解放,为社会发展提供昂扬的心理动能;经济开放的直接成果是技术进步,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劲的生产动能;恢复高考的直接成果是人才培养,为社会发展提供配套且优质的人力资源。可以这么说,“三大动力源”的启动与确立,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态势与内在结构;三者的相互依存与有机关联,则成就了“新时期”崭新的社会形态。高等教育的成败,取决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它将长期而显性地支撑并隐性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与根本质量。
然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仍然援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制,换一种说法,它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经济背景下教育新体制的全面转轨与转型,并没有实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真正而完美的接轨与融合。所以,高等教育借鉴市场思维、建立市场机制、引入市场竞争,可以说是高等教育改革转型的显性维度与首要任务。我们不能否定传统教育体制的可取之处,也不能否定计划经济教育体制的优越面,但是当市场经济发展已经远远地走在教育发展的前头的时候,我们的教育问题,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教育体制问题与局限就彻底暴露出来。更加让人焦虑的是,怎样才能避免教育体制与教育现象呈现出一种反向异变的颓势——传统教育的优势未能保持而其劣势却暴露无遗,市场体制的教育优势未能建立而市场体制下的教育问题与矛盾却十分尖锐且不容乐观,这成了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既然转型属于一种正向优变,教育转型也应该是一种正向优变,也就是说,教育转型应在尽可能保持传统教育好的一面的同时又尽可能快而好地确立市场教育体制。
所以,转型发展,的确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窗口期”。同时,它不仅仅是新建“二本高校”发展最好最新的窗口期,同样也是“一本高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不外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的转型:
从宏观层面说,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思想、体制与布局的转型。高等教育的思想不变,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就不会变;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不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就不会变。比如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通过严格的行政手段布点设校与分层定级(一本、二本、三本),学生录取也严格通过计算机匹配招录分流,所谓“名校(上品)无寒门,二本(下品)无世族”,以分取人、以分定校、技术性分流,看似公平公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失为正确的选择),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意或无意地阻止了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与优化,人才培养不但缺乏令人信服的比较优势,而且人才培养机制中的个体自我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严重缺节。正因为“以分取人”的教育思想与做法,其绝对局限性不难被理解;正因为爱因斯坦、爱迪生等不胜枚举的科学家与政治伟人,并不都是传统教育中高分的“好学生”,也并不都是出自所谓的名校,此类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也未能给人才成长发展提供必要的“柔性时空”,所以国内曾有“取消‘211’‘985’”的强烈呼声。我们又可曾想过,一所2万左右师生的二本普通高校的年收入为近3亿元,却只相当于甚至还不到国家政府投给一所重点高校一年的精品课程建设费。这种通过严格的政府控制与财政扶持发展起来的重点高校,是否符合高等教育市场化发展与竞争的比较优势呢?然而发达国家的名校,无一不是市场与竞争的自然结果与历史产物。
从中观层面说,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则是各个高等院校专业学科设置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中国的高等教育,同质化、趋同化,甚至“标准化”发展,从一本到三本,大而全,小而全,不是高水平复制,就是低水平重复。每所学校,没有自己的办学理念,没有自己的特色专业,也没有自己的优势学科。传统教育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流弊与特征,在今日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表现得如此充分,让人吃惊。社会转型了,经济转型了,教育在喊“转型”、在写“转型”,却未能真正地、及时地、积极自主地转型发展,为什么?大学校长们,不敢转型,不想转型,也不太会转型。教育行政官员们,则不敢让大学校长们转型,不想让大学校长与教授们自作主张地转型,关键是他们不太懂得如何让大学校长与教授们去转型。因循与同质,“企业化”加“衙门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等级森严又缺乏比较优势,就成了今日中国大学的时代特征。
从微观层面说,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则是高等教育内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的优化与调整。说起来,这才是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落脚点。人才规格与人才质量的实现,理想的“概念人才”是合格的现实人才的逻辑起点。依托学科设置专业,依托专业发展学科;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优质高效的课程设置;归结起来,是以教学名师为奠基石。人才培养、人才规格、人才质量,到底应取何种“人才观”呢?以市场发展为取向、以国家发展目标为取向、以社会发展目标为取向还是以受教育者个体发展为取向呢?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培养模式与以人格技术养成为主导的培养模式,应该如何选择与平衡呢?专业化发展的学理倾向与职业化发展的市场倾向,应该如何侧重并中和呢?
二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时代在变,但人性的良知不可变;科技在变,但科学的精神不可变;市场在变,但市场竞争的规则不可变;文化在变,但追求人类幸福的文化本质不能变……教育在变,高等教育在变,然而,什么是它的“变”与“不变”呢?教育体制可变,教育规模与布局可变,人才规格可变,培养方案可变,课程教材可变,教学方式可变……但是,必须遵循的教育规律与高等教育的规律不可变,追求教育质量提高的理念不可变,着眼学生终身发展与服务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才意识不可变,突出教育双主体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观念不可变。
(一)高等教育追求效益与竞争的“市场化”程度可以变,而坚守独立、真理与大爱的大学精神不可变
“市场化”维度,可以说是现代大学得以建立的重要力量,也是衡量现代大学“现代化”程度的重要特征与标尺。我国传统的大学教育,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教育在内,显然没有市场意识,也没有市场思维,更没有市场竞争。高等教育市场化,自然是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市场转型,高等教育的市场转型,却也是一种必然而艰难的选择——完全依赖市场的力量,以市场力量为主导,还是引入市场的思维、机制与竞争,这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3种不同选择。推行完全市场化的高等教育,行得通吗?显然是冒险的和行不通的。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发展高等教育,使得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高等教育在思路与政策方面必然会有诸多担心。适当引入市场思维、机制与竞争,自然成为了新时期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稳妥”选择。然而,“双轨制”的制度冲突与由此而带来的问题与矛盾,始终像雾霾、梦魇一样笼罩着,所以,有学者认为,当下的高等教育是“仿市场化的”,甚至是“伪市场化的”。我国高等教育以大学生自主择业和大学教师脱离公务员系列作为两大突破口,展开了其市场化的转型发展之路。以美国为例,美国虽然是以市场力量主导高等教育发展,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也最高,而且也是市场化最为成功的范例,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断言完全市场化的高等教育在我国就行得通。就是在美国,市场化与市场力量,也只是主导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其中,国家力量、学术力量与文化力量,同样不可或缺。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高等教育市场化转型,如果只停留在“大学生自主择业”与“大学教师非公务员化”两个层面,那么这种市场化转型则是表层的、功利的、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强而有力的制度支持,高等教育不仅要面向市场,而且要深层次地对接市场,关键是要引进市场的规则、机制与灵魂于其所有层面。
大学凭借独特的精神气质走到了今天,而且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走下去。我们经常将大学比作科学技术的孵化器、社会进步的加速器与精神文化的象牙塔,然而,什么才是大学存在的精神气质呢?也就是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之道呢?有人认为大学是传播和创生高深学问的地方,所以大学乃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梅贻绮语);我们的古人,则用“在明明德,在新民,止于至善”来概括大学之道;德国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费希特在《论学术自由唯一可能遇到的干扰》一文中指出:大学存在和办学的主旨不外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自由探索真理”3个方面[1]。尽管人们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存在出入与差异,但是,大学精神的存在却是客观和恒久的。尽管世俗权利与意识形态目的会有意或无意地控制大学,甚至想干扰、改变和取消大学精神,但这显然是浅薄和短视的,因为大学被支配和控制以及大学精神被扭曲的结果,就是大学的死亡或消失,所以在市场化转型发展的当下,我们必须强调大学精神的确立,我们必须强调大学相对于市场与权力的独立性、相对于效益与功利的真理性、相对于意识形态与文化偏执的普世性。因此,我们所理解的大学精神不外乎“独立、真理与大爱”。如果更通俗地说,大学之道包括:1个理想(塑造完善的人格),2个目标(弘扬科学理性、培育人文精神),3个任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4个构成(大师、大爱、大材、大楼),5个特征(独立性、创造性、批判性、包容性、开放性)。大学借鉴市场思维、引入市场规则,并不等于将大学推向市场。只要大学的精神不变,高等教育就只能是“精英教育”,所以,即使是市场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或“普及化教育”的提法也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特别是良莠不齐的扩招与推卸责任的自主择业,那是有重大负面影响的。
(二)高等教育追求更科学合理的布局分层与系统结构可以变,而应坚守的高教规律与高校平等发展的权力不可变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创立至今,师欧仿美,可谓起点颇高,众美兼容。120年不到的年轻历程,大致可以分为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清末民初,以救亡图存、师夷长技为目的的“创立期”,此期的高教以国家与王权为主要创办者,服从国家目标,满足战争与技术需要,重点布局,结构分散,不成体系。二是从新文化运动至民国失陆的“发展期”,此期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布局,以英美模式为圭臬,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在服从救亡兴国等民族大义的同时,更注重个体精神人格的确立与完满。此期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布局,初成体系,稳步发展。三是从1950年代至“文革”年代的“探索期”,此期的高等教育依托民国高教基础,以苏德模式为师范,突出高等教育的行业特征与专业特性,以理工和技术人才培养为主旨,重新布局分层,调整院系,改变结构。当然,文革时代,由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从而出现反向“畸变”。四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回归期”,政治上拨乱反正,恢复高考,虽然按苏德模式布局不变,按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控制和主导办学不变,大学依托行业办学,对专业人才的规格严格分层,以师范教育为例,分为本科、专科和中专3个层次,但是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健康发展。五是1990年代以来的“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计划经济制度下的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自然就因时而生,也就是由国家政府为唯一办学主体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满足不了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此期的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结构调整期。于是,重新师法“英美模式”,大学走全学科、多专业综合相融的发展之路,人才培养面向市场,在满足国家目标的同时又关注个体的人格精神健全及终身发展。但是,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也是无须讳言的。
大学有大学教育的规律,高等教育不论如何发展、如何转型,大学教育的规律是必须尊重并坚守的。所谓规律,就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这种内在联系所规定的可重复性。大学教育的健康发展是由大学教育的规律所决定的,一切违背高教规律的制度设置、行政指令和长官意志都会使高等教育蒙受与之相称的巨大损失。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简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坚守了高等教育的规律,尊重了高等院校平等发展的权利,高等教育就能获得健康的成长与发展,不论是学习英国模式、德国模式、苏俄模式还是美国模式;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政府主导办学,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政府、个人、企业以及教育机构共同办学。主导高校办学的物质力量无非是两种:一是国家力量,一是市场力量。主导高校办学的目的,也无非是国家目的与市场目的。那么,高等教育也无非是两种形态:一是单一化发展的高等教育,一是多元化发展的高等教育。办学目的决定办学的力量、办学的形态与模式。高等教育无论是遵循何种办学目的、形态与模式,尊重所有高等院校平等发展的权力,是高等教育事业获得全面而健康发展的前提。尊重高等院校平等发展的权利,才谈得上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竞争,才谈得上效率、效能与效益。尽管服从于国家目的的办学与服从于市场目的的办学,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可能完全同一起来,尽管向办学“出资人”负责的理念[2]一度成为转型发展时期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服务理念,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高等教育的“市场目的”与“国家目的”是一定会统一起来的。惟其如此,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方至理想境域。
(三)高等教育所设置的学科、专业与课程及教学方法可以变,而提高并坚守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主体终身发展的意识不可变
大学教育的所有规律都只能指向和保证大学教育的质量,而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途径却是“因材施教”。材,即是人。所以大学教育的质量自然只能取决于人——学生与教师的质量。大学教育的全部核心价值也只能是人——由一批批知情意行潜能可塑的青年学子和一支支卓越精干学高德隆的教师队伍所构成。
严格来说,一所好大学,是容不得劣质师资的,同样也容不得劣质的生源;恰恰相反,一所差大学,则容不得优秀师资,也同样招不到优质的生源,前提是充分竞争。然而,名校有名师,算不得正常的高等教育;校校有名师,才是健康的高等教育。名校出名生,算不得成功的高等教育;校校出名生,才是成功的高等教育。一所好大学,成功的高等教育,不在于它的学生整齐划一的高分,也不在于它整齐划一的人才规格,而在于它能因材成型,有教无类。通俗地说,不论鸭蛋鸡蛋鹅蛋,只要是“蛋”,我们均能把它孵化出来,让它成材。假如,我们真正引进市场竞争的精神与规则于高等教育,少一点人为的分流与歧视,少一点教育万能的错觉,少一点追求绝对公平的幻想,我们的高等教育又该是怎样一种成就与面貌呢?可是,世界一流大学从来就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突击创建出来的,也不仅仅是用钱就可以堆垒出来的。
正因为高等教育的质量与价值集中表现为教育主体与被教育主体的良性互动与相互塑造,所以高等教育(大学)形象地说,就是高端人才的孵化器。而作为“孵化器”的高校,它的本体追求主要表现为孵化人才、创新知识和引领文化。而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孵化器的主要部件——就只能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等,还有最后落实到高教名师。孵化器的质量,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
所谓人才规格,只能是一种预设的“概念人才”,“概念人才”的实现基础就是培养方案、专业课程与教学名师的相互依托与支撑。而高等教育的质量光有“方案、课程与名师”,即使是三位一体还是不够的,还得有与“培养潜力”相符合的学生来共同实现。所以说,预设的人才规格并不能等同于教学质量,更不能等同于人才质量。人才培养的质量取决于“概念人才”与“培养潜力”的匹配度。因此, 在“概念人才”不变的情况下,那就必须保证与人才的“培养潜力”相匹配;当人才的“培养潜力”发生了变化,自然就必须适时地改变“概念人才”。当今高等教育的趋同化与同质化现象,因为预设的“概念人才”的高大上或先天不足、学生“培养潜力”的不匹配,而使得教育质量滑坡的现象更加尖锐和突出,“扩招”自然不能说是唯一的元凶。
什么是人才质量?如何评估人才培养质量?衡量人才质量的基本指标不外乎:“精神质量”(灵魂与价值观)、“基础质量”(知识、思维、能力)、“职业质量”(行业特点、岗位技能、就业与生存)、“时代质量”(时尚、风气、规范)、“学校质量”(个性、特色、优势)等5个方面。高等教育相关院系学科专业实现人才培养质量诉求主要表现为6个方面:第一,构建并优化人才培养的学科群与专业群;第二,确立并柔化人才培养的目标、理念与规格;第三,制订并落实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第四,精建并融合相关学科专业师资队伍;第五,打造并丰富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与教材;第六,强化并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办学成效。
但不论怎么说,“概念人才”是可变的,而人才质量是不可以变的。坚守质量意识、强化质量标准、建构质量体系、破解质量难题、规范质量评估,是转型语境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时代主题。
(四)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中的制度设置、办学主体及治理模式可以变,而追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及创新应用的本体存在不可变
纵览古今中外的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从制度设置、办学主体、治理模式无不取决于4股力量的博弈与平衡。哪4股力量呢?一是国家力量,二是学术力量,三是文化力量,四是市场力量。于是,就出现了4种主要类型的高等院校——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大学,如古代皇家的太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可以欧洲大学为代表;以学术力量为主导的大学,如古代的学园、书院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院,可以英国大学为代表;以文化力量为主导的大学,如古代西方的经院与东方的道院,还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党派学校,可以用我国的大学为代表;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大学,如古代的孔丘办学、现代意义上的民办民营高校及西方的私立大学,尤其以美国大学为代表。于是出现了4种代表性的大学治理模式:一是政权主导的治理模式;二是权威的治理模式;三是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治理模式;四是市场的治理模式。实际上,不论是由何种力量为主导办起来的大学与高校,其他3股力量也是必然地存在着并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事实也告诉我们,不论是何种制度设置、何种治理模式、何种办学主体,都可以办出好的、成功的和一流的大学。所以,高等教育史雄辩地告诉我们: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制度设置、办学主体以及治理模式,肯定是可变的。只是我们如何将作用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这4种力量有效地配置起来,而不让其畸变成为危害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异化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不论制度设置及办学主体与治理模式怎么变、怎么转型,只要它不改变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创新应用的本体存在,它就不会畸变成为一种异化力量而危害大学的健康发展。大学的治理,是一种学术生态的治理,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的行政管理可以解决的,更不是单一的、偏执的意识形态可以控制的。大学的治理,应该是自主的和内在的、学理的和权威的,首先满足学术目标与国家目标,再来满足文化目标与市场目标。最理想的大学治理,就是同时满足这4种目标,而不相互损害。也只有当学术自由的时候,学术才会健康地发展;只有健康发展的学术才会更接近于科学与真理;只有科学与真理,才会符合国家的目标、市场的目标与文化的目标,才会符合自我的福祉乃至全人类的福祉。只有这样,“学术自由乃现代大学存在的奠基石”的命题才会成立。
从市场化发展战略看,“创新”与“应用”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两大时代主题。如果说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核心也是“创新与应用”,那么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在转型发展前,主要是学习与追赶层面的“应用”,而在当下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则应是“创新与应用”并重。如果说重点高校在“创新与应用”上应侧重于“创新”,那么,普通高校在“创新与应用”上则可侧重于“应用”。而过去那种“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的提法与分流,显然也是有局限性的。“研究型大学”离不开教学,“教学型大学”也同样离不开研究。教学与科研并举,这是大学永不可变的通则。自然,“创新与应用”也是大学永不可变的通则。
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创新与发展的正向优变之路,然而如何实现“创新与应用”的正向优变呢?概括说来,无外于5个大的方面:“创新与应用”并重,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与办学层次;“创新与应用”并重,调整、优化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与专业结构,走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之路,有所为有所不为;“创新与应用”并重,确保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于个人、社会与国家共同发展的目标与需要;“创新与应用”并重,破解就业难题,打通就业出路;“创新与应用”并重,切实提高高校教师与学生的质量、待遇与职业幸福感。
三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中的误区、风险与困境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教育不是万能的,没有教育是万万不能的;市场不是万能的,没有市场是万万不能的;同样,转型不是万能的,不转型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凡事务必讲究辨证,多存中庸,有所为,有所不为;该转的转,可变的变,不该转的坚决不转;该回归的要勇于回归,回归常识,回归本位,回归本体,回归本质。于有意与无意之间,转于无形。所谓机不可失,但又必须相机以成事。然而,如果发生“不可变者变,可变者不变”的现象,事业就会朝着与人们预想相反的方向前进,转型发展作为正向优变,就会出现反向异变,甚至发生颓败衰变。
所以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是机遇与风险并行,务必加强几种意识:“教与学”双主体的发展意识;理论与实践、创新与应用相结合的能力意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对接意识;尊重高教规律与“因时、因地、因材”施教的平衡意识;专业化人才培养与职业化社会发展的关系意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
因此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也应谨防几种困境及负面认识倾向的发生:一是错误地认为转型发展是一把无所不能的“万能钥匙”;二是错误地认为转型发展是将传统高等教育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三是错误地认为高教发展重在“应用转型”,所以是二本高校的事,与重点高校无关;四是错误地认为转型发展只重视技能,不重视理论,只要应用,不要基础,只管眼前就业,不管长远发展;五是错误地认为转型发展以效率优先、市场优先和功利优先,而忽视了质量优先、主体优先与全面发展优先;六是错误地认为转型发展只是教育官僚们摸脑壳发热、心血来潮、换汤不换药的花架、花肠、花枪,不必当真,只要应付应付就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当下,如何才能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呢?教育发展从来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牵涉社会与教育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还必须处理好几大基础性关系:个体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党派的关系;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关系……同时,我们也要充分看到并有效解决转型发展中的深层困境与对立。诸如,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深层矛盾;普世情怀与意识形态的深层对立;质量意识与效益追求的现实困境;人才发展理想与现实职业生存的深层矛盾;人才规格的刚性与可塑性之间的失衡与平衡等。
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实际上就是转变我国高校的治理模式与发展方式。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无不取决于4种力量的博弈与平衡,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学术力量与文化力量构成了大学的独特品质,然而,真正处理好4种力量在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与过程中的关系,自然就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如果是这样,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就很好把握了。
注释:
①所谓语境,即言说与对话的环境与条件,包括上下文、历时语境、共时语境与文化语境等;共名,原为一个文学史论概念,由复旦大学陈思和等教授提出,即时代思潮、主题概念等。
②生、住、异、灭,即佛教的哲学教义,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四个阶段,构成生命与历史的循环,见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
参考文献:
[1]陈列.关于西方学术自由的历史演进[J].世界历史,1994(6):57-64.
[2]宋佳.市场失灵?西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路径、困境与反思[J].高教探索,2016(3):5-11.
(责任编校:彭芬辉)
[收稿日期]2016-05-13.
[作者简介]周兰桂(1963—),男,湖南双峰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建设、高等教育教学论、人文与哲学。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6)03-0087-07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Things That Can and Cannot Be Changed
ZHOULan-gui
(School of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bstract:In the age of transformation, it is a part of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to transform higher education by adjusting the thinking on its development, innovating the mode of its development, optimizing its structure, improving its quality, and alleviating the systematic and structural risks facing it. Measures like these will make possible a reasonable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things open to change, and things not subject to change. Firstly, we can make changes to the market forc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competition it brings, but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 of university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truth and universal love. Secondly, we can make changes to the distribution and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a better one, but we should always stick to 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afeguard the right of every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o equal opportunity of development. Thirdly, we can make changes to the disciplines, specialty,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 but we should always be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keep in mi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both educators and students. Fourthly, we can make changes to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subject that runs schools, and the mode of management, but we should always be the champion of university self-government, academic freedom, innov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In the course of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re accompanied by risks. To have a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we must deal well with the things that can and cannot be changed so that we can reduce risks and avoid being misled into a plight.
Key words:the context of transformati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positive development; changeable; unchange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