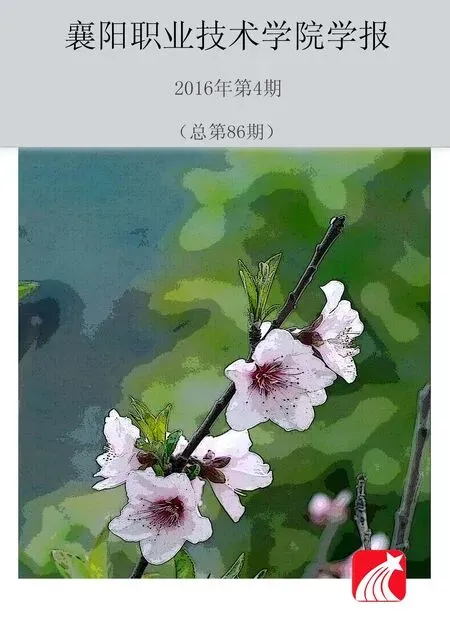从《生死疲劳》看莫言小说中的视角与常用结构
2016-03-01杨明巍
杨明巍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70)
一、视角的自由与转换
叙事视角是小说给读者呈现的观察窗口,是对故事内容进行讲述的特定角度,处理的是故事的叙述者和故事本身之间的关系,视角不同,效果也不同。对于叙事角度问题,西方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体,莫衷一是,国内理论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大致认为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谁在讲,也就是叙事人是谁;一个是谁在看,也就是通过故事中的哪些人物来看世界。”[1]西方理论界大致把叙事角度的类型划分为三种,分别是“零聚焦叙事即全知全能、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2]美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创立者布鲁克斯和新批评派代表沃伦把叙事角度分为四种,分别是第一人称自传性叙事角度、第一人称观察者角度、作者——观察者角度、全知作者的角度。国内的理论批评家又借鉴了西方理论家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如儿童视角、成人视角、民间视角、都市视角、女性视角、男性视角等新概念。本文主要采用布鲁克斯和沃伦归纳的叙事角度和国内的儿童视角等来剖析。
(一)第一人称叙事
《生死疲劳》在叙事角度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具变化性,尽管主要是以第一人称行文,但小说仍具有多层次变化。从最外层看,小说以蓝千岁、蓝解放、“莫言”三人的对话来讲述,都是以“我”为主的第一人称自传性叙事角度,以主人公的身份跳出来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所以文中的叙事者“我”不一定是动物,也可能是蓝解放或者“莫言”,这是第一层变化。而在各自的具体讲述中,又往往转为第一人称观察者角度,以故事中的次要人物出现,尽管参与到故事中来,但只作为观察者,讲述所发现的事情,这是第二层变化。例如西门猪对蓝解放的爱情纠葛的观察。西门闹在各个年代投胎为驴、牛、猪、狗、猴,以动物视角来观察历史给人民带来的摧残和伤害。作者塑造的这些动物英雄,驴的潇洒,牛的倔强,猪的暴烈,狗的忠诚反衬出政治奴役下人的精神普遍孱弱。这种以动物们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土地和农民的方式大大强化了小说反讽的效果。
莫言笔下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特点就是“我”的个性化很强,这与莫言极富野性的语言是分不开的。作者往往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把“我”的某些特点突出,比如“莫言连说带比划,其状滑稽,像个手舞足蹈的小丑”、“偷看胡滨的妻子白莲和人乱搞,结果被电得尿湿裤子”等把“莫言”多嘴多舌爱闹腾的特点表现出来。
这种以第一人称行文的叙事角度,最早出现在莫言1982年在《莲池》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丑兵》中,但是富有变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当时还不突出。在《丑兵》中,“我”作为一个老兵,尽管当了快八年的兵,但以貌取人,厌恶“丑得扎眼框子”的老兵王三社,多次刁难,最终被这个朴实热诚的丑兵感动了。在传统的全知全能叙事里,作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这样的叙事被长期使用以致泛滥,也缺乏现实感,不是生活的真实镜头。而第一人称观察者叙事,则打破了真实性不足的缺陷,正是“我”对丑兵的观察和接触是有限的,才向读者吹来一股新鲜的风。
(二)第三人称叙事
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即全知视角,是常用的叙事视角,与第一人称的真实、第二人称的亲切相比,它以灵活、客观见长。在《生死疲劳》中,蓝千岁、蓝解放两人对话,“莫言”补充的外围叙事结构和五种动物与人之间的视角转换完全可以使小说能够灵活多样地叙事了,实质上已经有了和第三人称叙事同样的效果。同时,这种叙事人称提供的细节客观真实和本质客观真实,也不是莫言所完全需要的,莫言意在强调的只有后者。
第三人称视角最早出现在他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放鸭》、《为了孩子》和《透明的红萝卜》中。在《透明的红萝卜》中,作家全知全能,不仅告诉了读者与黑孩有关的一切,还含蓄地告诉了读者黑孩所看不到的事:小石匠和菊子姑娘恋爱,小铁匠和老铁匠的勾心斗角,小铁匠的嫉妒阴暗。在这部中篇小说中,不仅充分表现了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灵活,更重要的表现在他对军旅题材的摒弃,开始拾起熟悉的故乡记忆,而且一出手就很成熟。
(三)视角的自由转换
《生死疲劳》中叙事非常自由,上述的几种叙事视角之间都可以相互转换,作为第一人称叙事的“我”,虽然是叙事者,但是并不贯穿始终,在小说里“我”可以是西门闹、蓝解放、蓝千岁、“莫言”,也可以是西门闹的几世轮回而生的驴、牛、猪、狗、猴。也就是说不仅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转换,也打通了人与动物的界限。《生死疲劳》里西门闹轮回后变成的五种动物,除了最后的猴以外都是以他们的动物视角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的。这种对动物们的“另眼相看”最早在《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牛》中就有过展现。
视角自由转换在他字数较多的长篇小说中得以体现,如《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基本上每一章的“我”的所指都不一样,同时不少地方人物之间的对话都不加引号,也不独立成段,也加大了阅读难度,这在他早期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生死疲劳》中“我”的频繁转换早在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就有同样的展现,但最早出现在1995年发表的《丰乳肥臀》中。《丰乳肥臀》前十章视角为第三人称叙事,从第十一章至三十六章为第一人称叙事,“我”是那个具有恋母情结的上官金童,之后到第六十三章和六篇补叙都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交互讲述。第一人称的安排使得故事真实可信,有较强的抒情性,拉近读者的距离,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事使得故事全面客观,离得较远。这两个镜头的相互使用,既相互补充,又给读者新鲜感。
二、结构的包容与开放
(一)常用模式:书信体与二元对话
莫言小说结构繁多,不单纯,变化较大,往往和叙事角度,特别是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紧密联系,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极具包容性的开放的特质。近几年,莫言在长篇小说里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从中或可见出些常用模式。笔者概括出两种:一是书信体,例如1986年出版的《酒国》、2009年发表的《蛙》。二是人物对话式,如《生死疲劳》、《檀香刑》、《四十一炮》。对话是人们日常交流的最常用的方式,也是最包容而开放的形式,模拟这种日常交际方式,小说就能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最直接的桥梁。作家可以像日常说话一样,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对话,极具直观性、亲切性、包容性、开放性。书信在日常使用时,与面对面交流最大的不同就是时效性不够,不是实时对话,但用在小说里就轻易达到同样的效果。
对话式在莫言的小说中表现为一对一的叙谈,一般只有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倾听者,形成二元对话结构,两者都是作家虚构的,读者在两人的对话中充当在场的旁听者,语流是双向的,往往互有对话和问答。《生死疲劳》中蓝千岁即西门闹和蓝解放的对话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生死疲劳》共五部五十八章,除了第五部开头和小说结尾由莫言讲述外,其他章节都有蓝解放和蓝千岁的对话。“这三人的对话结构中,三者的话语量并不是均匀,而以‘大头儿’为主,并延伸出驴、牛、猪、狗、猴这些动物的经历……建构了与‘蓝解放’相互叙述的关系,而第三者‘莫言’的出现在叙述中则是个插科打诨、拾遗补缺的角色。”[3]实际上整部小说是以他们两人的对话构成的二元叙事。而这种以“动物的视角”来叙述被两人一问一答有层次地剪辑成片,使得读者不断地被提示叙事人的存在,与记忆中的历史保持冷静观察的距离,造成了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
而莫言的《四十一炮》中,虽然也有“我”和大和尚的对话,但大和尚基本上只有行动没有说话,语流是单向的,结构上有些失衡。有时倾听者会直接由读者充当,在场的人只有小说主人公和读者,这种形式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由于第一人称叙事本身就是偏独白式的叙事角度,如果加上这些信号一样的互动语言,那么这里的独语者就得以向叙事者靠近,读者也得以向倾听者转化,形成二元对话。例如《檀香刑》是第一人称叙事,“我”可以是眉娘,可以是钱丁,也可以是赵小甲,三者在各个章节中交替叙事,但“我”在某一章中却只有一个所指,“我”的倾诉者由读者扮演。所以这部小说最外层是三元叙事,但在各章中都是二元对话的。
从1986年《酒国》书信体的答复对话,到2001年的《檀香刑》只依靠叙事视角制造对话,到2003年的《四十一炮》的单向语流的对话,再到2005年的《生死疲劳》双向互动的对话的运用,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莫言对话模式的不断完善。莫言最新的小说《蛙》前几章也采用了书信体形式织就对话模式,之后用第一人称自传性叙事不变。正如莫言自己所说:“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五十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4]
(二)元小说叙事:“莫言”的参与
有意思的是在众多小说人物中常常会有一个“莫言”的存在,使得小说呈现元小说的色彩。元小说即自觉暴露叙事行为的小说,当一部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关于小说本身的叙事时,这种叙事就是“元叙事”,而具有元叙事因素的小说则被称为元小说。在这里讲元小说,主要是把它看做是使莫言小说结构更加开放的一种技巧,它让作者堂而皇之地介入小说,打开了小说世界和叙事者现实世界的沟通大门。
在莫言小说中元小说的技巧一般有三种,一是暴露小说来源。比如《幽默与趣味》中作者以主人公朋友的身份揭露故事的来源,“作者曾问过王三变成猴子的感觉”。二是用典型的语言使得作家自我暴露,这种最简单。上面交代的构成对话模式中诸如“好吧,让我们回来,回到吃肉的赛场上看看对手们的吃相吧”、“这是铁笼中古怪口味叙述者的错误结论”[5]等用语,也都是元小说最常见的用法。三是莫言以现实中的自己为原型在小说中塑造一个“莫言”,这里主要讲第三种。
小说中莫言塑造的这一类人物有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换,就叫“莫言”,给予读者更多元小说的感觉,这在他的作品《酒国》中都存在。有时会将人物名字换了,或者只交代了他的当兵、作家等职业,或者交代与作家莫言类似的经历,使得读者们一读就会联想到作者。例如《牛》中的罗汉、《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中的“我”、《司令的女人》中的二皮、《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蛙》中的蝌蚪。小说具有虚构性,特别是在这么会讲故事的莫言笔下,“莫言”告诉读者的信息并不单纯,有真有假。但都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嘴馋、相丑、话多,令人讨厌,当过兵或做过作家,这些《生死疲劳》中的“莫言”身上得到全面的体现。
莫言在《小说的气味》中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塑造几百个人物……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6]这些“莫言”的性格特征很多都来自于莫言的童年生活,特别是饥饿的记忆对他影响非常大。但小说具有虚构性,这个由于叙事者声音的凸现而从幕后被推到前台的叙事者,既有真的部分又有虚假的部分。例如,莫言的确和一位日本作家聊过姑姑的故事,的确当过兵,让正怀孕的妻子打掉胎,莫言的姑姑的确是一个乡村妇科医生等等,这在《蛙》中的蝌蚪身上有如实的反映。但那位日本作家不叫杉谷义人,而是大江健三郎,也不是日军司令的后代,他们更是从来没有书信往来。
归根到底,“莫言”形象的塑造和其他元小说手法的运用,就是为了打破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从而达到向现实逼近的效果。表面上元小说叙事是作家主动戳穿故事的虚构,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真实。
三、总结
当先锋小说作家们陆续落马时,莫言找到了将西方现代技巧与中国民族相结合的道路,创造出许多新颖、自由、立足民族语言又吸引读者眼球的叙事技巧。他对小说叙事艺术,特别是叙事视角和结构的探索,踩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过渡的关键点上。如他在创作《檀香刑》时所说:“尽管这样会使作品的丰富性减弱,但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牺牲。”从这段陈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莫言力图摆脱外国文学的影响,创造出有本民族特色的小说。
[1]张相宽.莫言小说的叙事艺术[D].济南:山东大学,2011:15.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05.
[3]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73.
[4]夏兆林.论《生死疲劳》的三元叙事话语[J].语文学刊,2011(7):33.
[5]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844.
[6]莫言.超越故乡[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