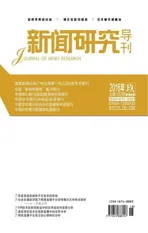文化传播视域中的“网生代”电影
2016-03-01汪楠
汪 楠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文化传播视域中的“网生代”电影
汪 楠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机械复制时代对于艺术、艺术作品的影响力在如今互联网的助力下演变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互联网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亦不可能与互联网隔离开。“网生代”电影以一种更彻底、更清晰、更普遍的方式诠释了光晕的消失。20世纪30年代,关于如何评价技术作为某种媒介或工具对艺术领域的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争论,在当今电影“互联网化”的发展趋势下具有跨时代的参考价值。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网生代”电影
一、光晕的消失与文化工业
(一)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文中,本雅明对于光晕(Aura)的概念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说明,而是用一种浪漫的比喻来解释:“如果您在夏日的下午闲憩,放眼望到天边的群山,或者见到树枝把阴影洒到您的身上时,您就体验到了群山和树枝的光晕。”从比喻中,我们可以窥见艺术作品光晕的距离感,人们无法触及天边的群山,就连树枝也是通过洒下的阴影来感受。然而机械复制的技术将这种模糊的、朦胧的距离感打破,本雅明通过三个角度来论述了光晕的消失。首先是艺术品的原真性,由时间性和空间性构成,“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每一个艺术品都是艺术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特殊的情绪和思想状态下创作出来的,这样的过程赋予了作品原真性。因此,即使是最先进的机械复制品也不能够重塑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诞生时空和艺术家的内心。原真性的存在良好地保存了艺术作品的原创价值的同时,制约了艺术作品的传播和分享。当光晕(Aura)被破坏,追求作品的原真性就失去了意义。譬如,随着摄影技术的诞生,胶片可以被无数次洗印,也就不存在所谓照片的原真性。其次,由于原真性的丧失,艺术作品的价值侧重点也发生了改变。“原真性艺术作品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仪式当中,即体现在原作使用价值的地方。”拥有光晕的艺术作品的侧重点偏向其崇拜价值。譬如,石器时代人们在他们居住的洞穴中描绘的壁画、牧师房间里被遮盖着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以及中世纪教堂的雕塑等。但是,机械复制的技术将艺术作品从被膜拜的仪式框架中解放了出来,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被提升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最后,由于艺术作品价值侧重的转移,大众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艺术作品因为光晕的存在变得神秘,但此刻,大众需要的是尽可能地拉近与艺术作品的距离。得益于机械复制艺术,大众可以轻松地以低价购买到艺术品的复制品。光晕消亡的同时,大众文化随之崛起,欣赏艺术作品不再是少数人所拥有的特权,“世间万物皆平等的意识”在艺术领域得到了加强。
本雅明对于艺术作品光晕的消失持乐观正面的态度,他通过对电影的褒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机械复制的艺术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最落后的关系——如对毕加索,激变成了最进步的关系——如对卓别林。”以“群体性的共时接受对象”——电影为代表的大众艺术使艺术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由凝视的崇拜转化为娱乐的“消遣”。然而这种消遣性接受,对于艺术作品以及欣赏者而言并非有百益而无一害。伴随着光晕的消亡,消费文化逐渐成形,艺术作品从神坛上走下,成为大众消费的商品之一。艺术作品从崇拜价值走向展示价值,再发展延伸至商品价值,不可忽略的是造成了为展示而创作艺术或是为售卖而创作艺术的可能。为了使艺术作品更广泛地被传播,或是谋取更大的利润,艺术家创作的动机可能变得不纯粹,而对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也会随着消费文化的侵袭而变得功利。西奥多·阿多诺就由此与本雅明展开了一场备受瞩目的争论,他持有与本雅明相反的消极观点。
(二)被消遣的艺术与文化工业
阿多诺在书中撰写了“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他指出:当今标榜多元化竞争的文化发展,其实早已被悄悄地贴上了一致的标签。“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而这样的一致性则来源于大众对于艺术作品的娱乐消遣的诉求。这样的评价标准使艺术作品丧失了批判现实的特质,大众无法通过欣赏艺术作品产生对现实的思考。正如面对一幅画作,人们会凝神思考,但面对飞速移动的电影画面,人们很难冷静地沉浸其中。与此同时,当艺术品变成可出售的商品,文化工业为了占有尽可能大的消费市场而提供通俗易懂的艺术作品,以迎合在生产劳动中身心疲惫的人们通过艺术作品消遣娱乐的需要。这看似使双方获利的改变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文化工业所生产出的雷同的、肤浅的作品,让人们逐渐养成将艺术作品作为消遣的习惯,并且丧失了对艺术作品批判性欣赏的能力。而为了娱乐大众而诞生的艺术作品则会消解对现实社会的不合理进行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其次,阿多诺尖锐地控诉了光晕消失令大众文化具有欺骗性、操控性的特点。“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教的,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够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可以使数十年转变为一瞬间,使逆境迅速转变为顺境,所有改变的过程都可以简化,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解决,电影为人们塑造了无数的美梦。电影业的工作者们正在不遗余力地使电影作品无限度地贴近“真实”,引导观众走近梦幻的世界。可是,当人们沉浸于电影中的美梦,就会把电影里所发生的奇迹带入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知中,从而影响了观众进行理智分析和冷静判断的能力。
艺术作品由多元变单一,由复杂变肤浅,由追求真实变成追求大众眼中的真实,这样巨大的转变引发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强烈地震。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培养、塑造出符合工业社会所要求的人的摇篮。创作者和得利者利用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操控性,美化现实生活,使大众逐渐被美好的表象所蒙蔽,失去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抗争的意识。
二、“网生代”电影的出现
互联网在电影营销上的强大助推力在2011年伴随着《失恋33天》的走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4年,互联网对电影的影响达到了一个巅峰。百度、阿里和腾讯作为互联网行业三巨头皆进入了电影行业。互联网公司的大举进入对电影行业的整条产业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内地电影的发展因为互联网的介入来到一个转折点。
学术界对于电影和互联网的产业融合的看法诸多,既有支持也有忧虑。王广振认为,广义来看,电影与互联网的产业融合,是“文化”与“技术”的融合,旨在利用技术手段推动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发展;狭义来看,电影与互联网的融合,将增加电影产业的复杂性,加剧跨行业竞争,但同时也将推动各类电影企业转型升级,从而带动整个电影产业链良性运转。熊澄宇支持产业融合,认为电影不是实验室文化,电影也不是精英文化。批量生产是电影的基本属性之一。电影需要观众,需要市场,需要与时代同步。曹书乐认为,互联网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电影多元化的发展,“在电影创作获得解放,有更广阔表达空间的时候,是否还要警惕别让消费主义成为流行电影的主流,而让更多元化形式、主题和追求的电影都有生存的土壤和机制?”
2014年是互联网进入电影行业的里程碑,由此电影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名词,“网生代”的概念被提出。中国电影评论协会学术活动部主任王旭东认为,“网生代”具有鲜明的标签,“他们反映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拥有碎片化表达和渐进式的文化消费”。他指出,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第五代、第六代之后,中国电影的互联网时代已经正式到来。因此,“网生代”不是时间概念,而是空间上的划代。因而“网生代”电影指的是依互联网而生,由互联网造就,用网络模式来运营的电影。优酷土豆集团高级副总裁朱辉龙认为“网生代导演”有几个特点:第一,这部影片里面诉求的,是目标受众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第二,“网生代”导演会把完整的故事片段化、碎片化去考虑它;第三,营销更多元化,更碎片和矩阵化;第四,参与创作的人更多了,他们创作的过程,往往和目标观众实时互动,实现某种意义的共同创作;第五,创作来源更多元化,因为他们对互联网有深入的了解。
三、“网生代”电影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一)网生代电影与光晕的消失
原真性的丧失是光晕消逝的关键,原真性强调了艺术家独一无二的创作理念,甚至是创作时的情绪和心境。“网生代”电影对原真性的破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首先,“网生代”导演不再专注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是将目标受众的诉求转化为影像。“网生代”导演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原创力的艺术家,“网生代”电影的构思成型亦不是传统观念上的独立创作。导演的个性和独特性被弱化,导演的职能被强化。其次,原真性代表了不可复制、不可再现,然而“网生代”电影依托互联网科技,超越了电影数字技术的拷贝功能,在内容生产上也可以做到复制。大数据是新兴被用于电影产业的互联网技术,数据库叙事代替了导演和编剧。此类电影脱胎于用户大数据反馈出的观众喜好,市场与观众的重要性被提升到第一位,可谓是专为特定的观众市场所打造的电影。在数据库叙事的模式下,导演和编剧被替代,艺术家被技术代替,其成果可以任意复制、合并、修改,毫无原真性可言。乐视影业创新事业副总裁陈肃认为,未来电影业真正要使用的是基于互联网的用户数据,它们是前端数据,它们是消费,是动机。在“网生代”电影的生产过程中,导演担当的是产品经理的角色,好的导演就是能够将产品以高销量卖出,而非表达导演个人的观点或是追求艺术造诣上的突破。
如果说电影技术的发明使艺术的光晕黯淡,那么互联网的介入则使电影全然失去了作为艺术品的光晕。当人们沉浸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等带给电影业的新鲜空气中时,不可忽略它们带来的弊端。利用大数据制造的电影真的能够代表观众的诉求么?互联网思维影响下的电影真的能够促进多元化的发展么?本雅明赞同光晕消失的原因在于其拉近了人们与艺术品的距离,“世间万物皆平等”的意识在艺术领域得到了加强,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互联网上众声喧哗,个人的、商业的因素炒作出大量热门话题,僵尸粉丝、刷点击量、刷评分等不良竞争手段不足为奇。这种来源的数据缺乏理性的思考,亦无法代表大众群体的诉求与喜好。另外,大数据的来源是逐年递增的网民群体,他们来自大都市并且年龄层次较低。依托大数据制造出的电影恰好符合了这些既是网民又喜爱去电影院的人群的喜好,在票房上回报颇丰不足为奇。然而,那些处于偏远地区,或是年龄较高的庞大人群是缺乏使用互联网的资源和能力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诉求在“网生代”电影中极易被忽略。如今,本应该是第六代导演在影坛展现才华的时刻,但他们的作品却受到了“网生代”电影的冲击。喜爱以山西汾阳小县城为创作题材的贾樟柯在法国深受好评却在本国沦为小众,娄烨斩获大奖的影片《推拿》在国内院线的排片被挤压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非学院派,“网生代”导演郭敬明、韩寒等人电影的票房一路飙升,《小时代》甚至一度完全占据了院线的排片表。第六代导演票房的惨败原因在于他们关注的都是边缘化人群,如三四线城市的人、农民、盲人等,与“网生代”用户的关注点重合度很小,远不如大都市的青春忧伤和阵痛来得引人注目。这些成功的“网生代”电影关注的对象集中于年轻群体、叙事碎片化、内容相似度高、视听语言追求华丽炫目。若这样的电影成为主流,那么电影创作将不再是导演个体的深度思考,而是用技术将不同人群的需求简化为统一的需求;将电影发散性的创作禁锢于几个所谓的热门关键词上,电影行业将陷入同质化的竞争危机中,失去作为一门艺术所与生俱来的多元和创新的特质。其次,“网生代电影”将电影从文化变成商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思想、情感的表达,迫使电影创作者从艺术家变为产品经理,卑微地迎合所谓的观众的需求。中国电影历经百年风云,一代代电影人为了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当互联网思维介入新一代电影人的创作中,是否还能够立足本土,走向世界?互联网究竟是带来了突破还是增添了创作的桎梏,值得进一步的思考。
(二)被弱化的文化启蒙
本雅明笔下的光晕消逝带来的是大众文化的兴盛,人人皆可以欣赏艺术,参与创作艺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超越前辈的优势在于此,然而“网生代”电影却从根本上违背了这种宝贵的文化启蒙的意义:光晕的消失使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被强化,而崇拜价值被弱化。许多人指责美国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故事内容雷同,叙事模式单一,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反观中国新兴的“网生代”电影,崇拜的不是普通人通过努力创造奇迹,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而是羡慕拥有与生俱来的财富和权力的富二代,普通人依附于他们才能过上优越的生活。这样的观点倾向否定了个人努力的价值,比起个人英雄主义,更会带来价值观的混乱。尤其是在这些电影的目标受众是年轻群体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心态和认知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尹鸿指出,无论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播,造“梦”的机制其实是永远不变的。“互联网时代的电影,并不只是被互联网的某种下坠的力量所诱惑,而更多的是要为互联网提供真善美的正能力。”笔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启蒙的工具,表现的是社会现实,启蒙的是对于反思历史和当下、创造更好未来的决心。现阶段的中国“网生代”电影显然缺乏这一功能,制作方盲目地鼓吹技术的先进,力图将电影做成商品赚取利润,忽略了电影的艺术价值和人文精神。
中国的“网生代”电影有着特殊的背景:美国的媒介是市场化的,互联网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内容尺度上的差异不明显。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媒体管制相对严格,而互联网就起到了对传统媒体的补充和反差的作用。依托互联网而产生的“网生代”电影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喜好,会追求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宣泄带来的娱乐体验。在互联网基因的影响下,“网生代”电影在内容上有时就会显得有些低俗,暴力、色情、恶搞等元素的运用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而这与互联网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很大的相似性。并且,“网生代”电影由于创作者缺乏专业的电影教育,塑造人物时往往带有标签化的色彩,比如“高富帅”“穷矮搓”等,这又与互联网中的“标题党”相似。2015年暑假上映的《刺客聂隐娘》由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他擅长叙述中国故事,从本国历史和文化中挖掘素材。十分讽刺的是,《刺客聂隐娘》在法国戛纳电影节斩获大奖,却在中国市场遭遇票房惨淡。相反,同为暑期档,由互联网公司出品的《煎饼侠》将好莱坞式的美国梦和英雄主义本土化,收获了票房大捷。以古典、含蓄的美为艺术基调的《刺客聂隐娘》不敌“屌丝文化”的《煎饼侠》,可见互联网对人们审美观和艺术偏好的影响。“网生代”的年轻观众尚未充分了解传统文化及其传承价值,而电影作为具有现代化特质的文化启蒙工具在互联网负面效应的介入下逐渐失去了这个作用。中国故事在本土的传承和在国际上的传播依然前路漫漫。
四、互联网时代的电影工业与新光晕
当艺术作品的光晕消逝之后,当复制——展示——售卖的模型被熟练地运用在艺术作品上,文化工业的雏形开始形成。阿多诺所担心的就是文化领域以工业领域的方式来发展:“垄断资本和权力机构操纵着文化工业,并以最有效的机械复制方式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提供的文化商品。”如今,互联网为各行各业带来改变,互联网公司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介入电影行业,以“网生代”电影来替代传统电影,以产品来代替艺术。“公众的态度,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支持着文化工业体系,因此它也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并没有被排除在外。”“网生代”电影的一大特征就是符合目标受众的诉求与喜好,阿多诺所提出的“公众的态度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在互联网模式的作用下契合度达到了巅峰。本雅明所推崇的大众与艺术作品的近距离在阿多诺的批判下成为了文化工业的利益获得者的一种阴谋。在互联网公司进入电影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的当下,阿多诺的担忧显出了跨时代的价值。以消费商品的方式来对待电影作品强调了娱乐性,压制了批判性,更关键的是造成了对电影作品价值判断的失衡。电影作品在思想上的高度、表现形式上的创新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通俗和娱乐特征受到了从创作者、电影的推广发行方到普罗大众的重视。电影虽然有着飞速转变的画面,无法以画作的凝视的方式来欣赏,但仍然需要冷静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在互联网文化工业的背景下,从题材内容、制作方、创作过程乃至营销渠道皆与互联网有着紧密关联。若导演在年轻网民群体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一部电影就有可能沸腾成现象级的文化事件,相反,致力于表现个性化、小众化思想与情感的导演反而面临着遭遇忽视的风险。
当技术决定论进入电影行业,当电影行业内行业外的人都在谈论大数据,谈论电影的商品属性,谈论如何生产出更明确地针对目标受众的电影,谈论如何利用高新技术将票房收益最大化,笔者认为有必要呼唤一种新的光晕的产生,帮助电影行业走上良性发展而非趋同竞争的道路。当代电影作品的新光晕与古典艺术作品的光晕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原真性上,虽然这些电影作品是可机械复制的,但它们的原真性的回归源于电影创作者在互联网工业时代对个性、原创的重拾,避免了对技术的依赖和对受众的迎合,这就赋予了电影作品在时间空间和创作者心境上的研究价值。在价值侧重上,当代电影作品源于机械技术与生俱来的展示价值并不是为了谋取商业利益,而是为了呼唤更多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以及完成文化传承的使命。光晕的回归并没有带来崇拜价值的提升,接受了科学洗礼的人们将视盲目的崇拜为一种后退。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电影创作者或公司试图谋求崇拜价值的重塑,其目的是打着推崇高端艺术的幌子谋取商业利益,这样虚伪的行为显然不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被独立创作的艺术家所赋予新的光晕的电影作品可能成为一种驱使人们共同追寻幸福的力量。这一类型的现代艺术作品与阿多诺激烈批判的欺骗性、操控性的艺术作品有着在形式上的相近,却有着在本质上的区别。文化并非制造业,电影亦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诚然,互联网技术实现了许多新的功能,却并不能代替艺术家的自主创作。互联网的各种产品为电影的发行放映带来了便捷,但电影作为艺术的审美价值却始终在于内容创作的优劣,而非互联网的营销手段能够达成。不仅是“网生代”电影,遵循传统创作方式的电影都应该被赋予一种新的光晕,在喧嚣繁杂的互联网影响下的世界,以独特的光芒彰显艺术的原创性、独立性和批判性。
五、结语
互联网对电影行业的影响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互联网公司来势汹汹的介入,电影行业需要对自身有着更清晰的认知。电影是一门艺术,而非某一工业产品,互联网对其他产业的革新不可在电影业生搬硬套。“网生代”电影不具备艺术的光晕,原真性全然丧失,电影的原创性和批判性被受众诉求所替代。而与本雅明的理论相矛盾的是一种全新的崇拜感的人为塑造,而这种崇拜感正是为了掩盖其思想情感的虚无缥缈,更是一种文化工业模式下对观众价值观的蓄意操纵和负面影响的手段。互联网时代,公众对电影的参与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文化交流空间的塑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电影行业对于利益的谋求胜过对艺术造诣的追求。呼吁新光晕的回归是希望电影行业在互联网的浪潮中坚守艺术的创造、批判和审美的价值,而不是下降为一种消遣性质的快速消费品。新光晕也将推动电影行业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发展,让小众题材以及边缘人群也能出现在荧幕上,得到人们的关注,激发思维火花的碰撞。不能忘记的是,互联网的初衷是推动个体平等、独立、个性地表达,而不是个人和机构操纵下的趋同。虽然互联网时代重视高科技,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漠视思想和情感的冰冷时代。而电影作为一门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艺术,在纷繁复杂,有着许多对立与矛盾的当下,是承载着丰富人文情怀的宝贵力量,这种力量从未消逝。
[1] 瓦尔特·本雅明(德).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7-26.
[2] 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07-152.
[3] 温恕.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看本雅明的艺术生产思想[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2-4.
[4] 范萍萍.机械复制与艺术的命运——阿多诺本雅明之争及其现实意义[J].浙江学刊,2001(06):2-5.
[5] 王慧青.技术的礼赞——本雅明机械复制艺术理论探析[J].电影评介,2007(04):1-2.
[6] R·沃林,李瑞华.艺术与机械复制:阿多尔诺和本雅明的论争[J].国外社会科学,1998(02):2-4.
[7] 尹鸿,朱辉龙,王旭东,朱晓敏.“网生代”电影与互联网[J].当代电影,2014(11):1-4.
[8] 王广振,王新娟.互联网电影企业:产业[9] 熊澄宇,雷建军.作为传媒的电影和作为产业的电影[J].当代电影,2006(01):1-3.
融合与电影产业链优化[J].东岳论丛,2015(02):5-7.
[10] 曹书乐.新媒体环境中的“现象电影”[J].当代电影,2014(05):5-6.
[11] 裴菁宇.“网生代”电影发展现状及运作模式分析[J].中国电影市场,2015(02):3-5.
[12] 陈坤.变革还是颠覆:论互联网对电影制作的影响[J].电影文学,2014(22):1-2.
[13] 胡黎红.热概念的冷反思——从关键词看互联网对电影制片的影响[J].当代电影,2015(01):1-3.
[14] 陈旭光.猜想与辨析——网络媒介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新力量”[J].当代电影,2014(11):5-6.
[15] 安晓芬,赵海城,尹鸿,丁涵,陈晨.互联网时代的电影生产与传播[J].当代电影,2014(05):4-5.
G206
A
1674-8883(2016)18-0199-03
汪楠,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