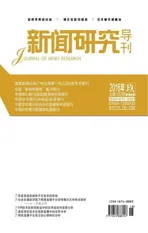浅析严歌苓小说《扶桑》符号学
2016-03-01向梦
向 梦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浅析严歌苓小说《扶桑》符号学
向 梦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以其对“女人”“东方人”“妓女”,这些边缘角色的关注而进入了文学殿堂的中心。作者对文学符号的独特运用赋予了其作品独特的魅力。本文探讨严歌苓是如何使用隐含的叙事符号、意蕴深刻的东方文化符号以及色彩艳丽的视觉符号,来表达其作为女性、作为“第五代移民”对人性和文化的独特思考。
符号学;象征符号;色彩符号
一、引言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如同刻画在历史画卷中的美丽女人,让人不断地去翻阅回味,历久弥新。无论是从女性文学角度,还是从新移民文学角度来看,都是作者对人性和东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
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严歌苓的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很多研究者从新移民的角度对严歌苓的作品进行分析,认为“当代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严歌苓在其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了很强的对于作家自身文化身份的探寻意识。多年的国外生活、异质文化的冲击、中西文化的冲突等人生体验,使严歌苓在文学创作中一度表现出了诸多华裔作家共有的创作焦虑感和自我怀疑意识”。[1]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也是很多研究者探讨的对象,指出:“‘母性’表征着严歌苓对人性开掘的深度。”[2]还有很多研究者从叙事的角度对严歌苓的作品进行分析。
直至目前,很少有人从符号研究的角度对严歌苓的小说进行探究。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严歌苓的小说《扶桑》,考察其作品中的符号运用。探究严歌苓是如何使用隐含的叙事符号、意蕴深刻的东方文化符号以及色彩艳丽的视觉符号,来表达其作为女性、作为“第五代移民”对人性和文化的独特思考。
二、隐含的叙事符号
在小说开篇的描写中,作者以“你”“我”的第二人称和第一人称的形式引出小说的主人公扶桑与作者自己,“这时你看着二十世纪末的我……”[3]在相互审视中,让两个看似命运不尽相同的女人历史地碰撞在一起,不禁让读者将曾经都踏上过金山码头的两位中国第五代移民的女性命运联系在一起观察,同样充满东方神韵的女性色彩更能引起读者的窥私欲望。
我们从严歌苓的成长环境与命运选择不难发现,女性角色对她的价值观与人物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性别理论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操演论”(perfomativity)提到:“男女性别不是生理上与生俱来的,而是操演出来的,我们对某个性别化的本质期待,生产了它假定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因此,严歌苓本身作为一个女性符号在小说的开篇就给了小说文本隐性的符号暗示。
小说本身的故事冲突所形成的双轴关系也在推动小说的发展。小说中女主人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男主人公则代表了优越的西方现代文化,呈现出你强我弱,我弱你强的矛盾发展,让小说在内容上近乎疯狂而令人抓狂。
在文化上,无疑是女主人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强烈的优势地位,扶桑的三寸金莲让一个西方男子为之疯狂,她所执着的红色外套,扶桑自己也深深地明白,只有这件衣服才能标识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与独特魅力。正是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神秘国度的女子,让男主人公无比着迷并深陷其中。
在人物性格上,女主人公隐忍、宽容甚至有着母性才有的包容;而男主人公一味地索取与伤害,将小说的悲剧发展推向高潮。在命运面前,扶桑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与妥协,甚至从来没有过明显的反抗,男主人公既惊异于她的包容,也是她痛苦的来源,与其说是一个施惠者,倒更像是一个刽子手。
双轴观念首先是索绪尔提出来的,任何符号的表意活动,小至一个梦,大至整个文化,都必然在这个双轴关系中展开。雅柯布森提出:“选择轴”,即比较与选择;“结合轴”,即邻接与黏合。简言之,聚合构成了文本的单向内容,组合选择构成了文本的表现形式,聚合与组合共同构成了双轴的关系推动了文本的内容情节发展。不难看出,双轴关系更像是一个横轴与纵轴的螺旋式推进的过程,我们在横轴上选择我们的文化特征,再通过纵轴将两条不同的横轴交互推进,通过融合与碰撞形成独特的结构形式推动事物的发展。
三、东方文化符号
扶桑和大勇这样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人,虽植根于美国社会却依然梳着长辫子、穿着繁重刺绣的大红衣裳,与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美国文明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的脸庞和来自东方的痕迹过于显眼甚至让人气愤,这种气愤来源于对东方文化的渴求,它包容、坚毅、仪式感的庄重让拥有现代文明的美国在沉甸甸的历史面前不禁自惭形秽。
“一扇红漆斑驳的门,上面挂着四个绫罗宫灯。几乎是每个中国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门脸,高档的,细致而烦琐。”就是这样一扇门带着克里斯再次走进扶桑、走进她的世界。简单的描写让一座灯火通明的中国窑子浮现眼前,红漆门、绫罗宫灯、蜡莲花、古怪假山,简单的事物却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同时蕴藏了诸多的中国文化,如佛教信仰、山水美学、视觉美感等,让独树一帜的中国建筑更显活力与独特。
在很多的场景中都描写了扶桑嗑瓜子、嘬田螺的样子,认真而谨慎,无疑瓜子和田螺这种在外国人眼中低廉而粗俗的食物却是扶桑的最爱。这一简单的动作却让心存爱慕的克里斯无比沉醉,让两种不同的欣赏矛盾凸显,同时这种饮食文化也带着浓厚的中国色彩。
四、色彩艳丽的视觉符号
在初次阅读小说《扶桑》后,给人以最大的感官体验就是作者对色彩的描写,无论是场景描写还是人物描绘,红色这一主题色彩充斥着整篇小说,给人以影视化呈现的想象空间。红色不仅仅局限于衣服的鲜艳、嘴唇的红润、大红的灯笼与建筑,而是将读者引申到扶桑所代表的中国女性与中国文化,表达了这一时代中国女性的鲜活生命与隐忍宽容强烈对比的悲情特征。全球化时代是图像时代,影视成为通用艺术门类,部分原因在此。文化提供了各种深入读文本的可能性。
严歌苓小说《扶桑》是一部对比中西方文化强烈冲突的符号化解读蓝本,无论是文本小说还是影视作品,都能够在不同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中通过各自的符号特征给读者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
[1] 吴玉苗.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3):407-408.
[2] 付立峰.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J].华文文学,2007(03):84-89.
[3] 严歌苓.扶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08):1-18.
I106.4
A
1674-8883(2016)18-0138-01
向梦(1991—),女,湖北人,北京印刷学院国际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