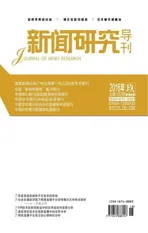弥尔顿与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之比较
2016-03-01贺元双
贺元双
(云南大学 新闻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弥尔顿与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之比较
贺元双
(云南大学 新闻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本文通过对弥尔顿和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进行比较,阐述弥尔顿要求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个体自由,并且携带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而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是由权力中心赋予的自由,是“文人论政”的保障,具有厚重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色彩。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王韬;言论出版自由
弥尔顿吹响了人类历史上争取言论自由的号角。两个多世纪后,王韬率先在中国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呼吁朝廷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纸,允许报纸“指陈旧事,无所忌讳”,“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1]然而,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展程度不同,两人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观点也有诸多差异。弥尔顿和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分别对后来的西方国家和中国的言论出版自由的话语建构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要对西方国家和中国在言论出版自由观差异方面进行研究,就不能避开对弥尔顿和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进行比较分析。
一、人物及时代背景介绍
约翰·弥尔顿是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他出生在伦敦的一个清教徒家庭,家境殷实,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曾求学剑桥,游历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深受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新教义中的宗教自由和宽容精神。自1641年起,弥尔顿开始投身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撰写文章著作反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国教。1643年,英国实行书刊预先检查制度,制定了《出版管制法》,该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1644年,弥尔顿由于发行了论述离婚的小册子触犯《出版管制法》禁令,受到国会质询,于是,弥尔顿在英国议会审议庁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论出版自由》,慷慨陈词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弥尔顿的言论出版自由观点也主要集中在《论出版自由》这本小册子中。
王韬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报刊政论家。他自幼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代文史经典,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八九岁时,已“通说部”“毕读群经”,18岁考取秀才。王韬曾在外国传教士麦都思主办的墨海书馆兼任《六合丛谈》编辑,在流亡香港期间受理雅各赏识,协助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并主编《近事编录》。在1867~1870年间,王韬随理雅各到英国“佐译经籍”,又两度游历法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直接的考察,深受触动。回到国内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社会思潮中,王韬发出“穷则变,变则通”的呼声,主张国家学习西方之“器”,走变法图强的道路。看到“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2]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并担任主笔,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要求清政府放开言禁,提出言论出版自由的要求,鼓励民间办报纸。
二、弥尔顿与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比较
(一)弥尔顿的言论出版自由观
弥尔顿认为言论出版自由是人权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真理的发现和知识的形成都依赖于它。他在《论出版自由》中讲到“哪儿有学习的要求,哪儿就必然有争论、笔战和分歧的意见。因为善良人们的意见就是正在形成的知识”,[3]“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3]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它像天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它解放了、扩大了并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见识”。[3]从这些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弥尔顿对言论出版自由具有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弥尔顿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捍卫是从反对书籍出版许可制出发的。弥尔顿痛切陈词批判《出版管制法》,他认为这条法规不但不能禁止诽谤性和煽动性书籍,反而只会破坏学术和窒息真理,是星殿的出版法令的翻版。首先,弥尔顿通过对历史上著名国家关于制止出版界紊乱情况的办法的旁征博引,得出书籍出版许可制从最反基督的宗教会议和最专横的宗教法庭发出。弥尔顿指出,“雅典的长官只注意两种文字,一种是渎神和无神论的文字,另一种是诽谤中伤的文字”。[3]虽然禁止旧喜剧派作家的作品上演,却没有说禁止他们写剧。“直到那个牛鬼蛇神似的罪恶机构(罗马教廷)由于宗教改革而感到心慌意乱,才找出一个新的灵薄狱和地狱,以便把我们的书籍归入应遭天罚之列。”[3]这些都充分表明,弥尔顿对古代历史上言论出版自由的赞赏和向往,对当局实行书籍出版许可制的强烈反感。然后,弥尔顿对书籍出版许可制检查员的品质提出质疑,“他们不是骄傲而又疏忽怠慢,就是卑鄙地贪图钱财”。[3]弥尔顿认为出版许可制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让检查员去决定一本书的命运,是对学术、书籍、作者的莫大侮辱。
在《论出版自由》中,弥尔顿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依据建立在他对书籍、人的理性、真理的论述的基础上,在论述的过程中,他多次以上帝的名义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因此,自然而然地弥尔顿的言论出版自由观沾染了宗教神学的色彩。弥尔顿认为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保存了创作者智慧中的精华,是充满活力和繁殖力的,实行出版许可制,有可能会对整个出版界造成大屠杀。因此,弥尔顿说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3]弥尔顿认为,上帝赋予亚当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因此,“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情”。[3]弥尔顿还认为真理是最有价值的商品,而书籍出版许可令阻挠了真理的输出,真理会在人们自由讨论、自由抒发过程中取得胜利,“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的进行交易”。[3]这么做意味着在人类发现真理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二)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
王韬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要求建立在他对报刊认识的基础上。王韬结合自己的报刊实践经验和在游历欧洲时对西方报刊的发展观察后,认识到报刊可“广见闻,通上下”,又可“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可使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4]极度重视报刊在社会中的影响。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一文中,王韬建议内地各省仿上海、香港设立新报馆,“其所益者有三:一曰知地方机宜也。……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4]紧接着,王韬继续在文中呼吁清政府放开言禁,给予言论自由。“今新报指陈时事,无所忌讳,不亦类于讪谤乎?非也”,“若指陈时事,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之而已”。[4]从这里可以看出,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与报刊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同于弥尔顿的言论出版自由服务于学术和真理,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主要是侧重于给“文人论政”和“办报立言”提供保障,他要求清政府开放言禁,让人们能在报刊上自由地讨论时政。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王韬创办《循环日报》的目的之一就是“办报立言”,宣传自己的改良资产阶级思想。在王韬的主持下,《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建议国家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强军惠民,反对因循守旧的保守势力,《循环日报》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外,王韬擅长写政论文,他认为文章所贵之处,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开创了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政论文风,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时务体”。总而言之,王韬的报刊实践活动为“文人论政”奠定了基础。
王韬除了要求言论出版自由,而且还建议朝廷求言,博采舆论。王韬列举了圣人求言的例子,“尧有直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问老衢室,途议巷说,靡不收采,岂直以市好谏之名哉,诚以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非博采舆论,何以措置咸宜”。[2]王韬认为“唯恐民之不议,未闻以议为罪也”。[2]而周朝的衰落就在于“上不求谏于下,而下亦不敢以谏其上”。[2]因此,王韬鼓励民间办报纸,通上下之情。除此之外,朝廷应专设直言极谏一科,许其指陈朝政,必洞中利害,毋得虚应故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韬已经有了舆论的意识,而开放言论自由是博采舆论的重要之举。
(三)弥尔顿与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之异同
弥尔顿和王韬要求言论出版自由,都希望人们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意见,这是言论出版自由最重要的内涵,弥尔顿和王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弥尔顿说,“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王韬说,“唯恐民之不议,未闻以议为罪也”。这是弥尔顿和王韬言论出版自由观的共同点。另外,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道,身居草野的人,没有直接进言的机会,如果看到有什么可以促进公益的事情,便只能笔之于书,这和王韬希望当局鼓励民间办报,允许人们指陈时事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
弥尔顿强调言论出版自由是人权自由中最重要的,认为言论出版自由是促进学术和真理发展的保障,有利于人们辨别是非、善恶。而王韬虽然接触了西学,但并没这么深刻的认识,在王韬眼中,他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不是从人权出发,而是从政治出发,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只是王韬变法主张中的一部分。在王韬看来,开放言禁是统治者理政的一种方式,它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正如前文所讲,王韬建议在内省设报馆时,他只是单一地强调报刊对当局者管理国家的作用,“其所益者有三:一曰知地方机宜也。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
在笔者看来,造成弥尔顿和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的差异,在于弥尔顿受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言论出版自由观带有宗教神学的色彩,不完全是自然转态下的人权,这是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这个阶段,资本并没有完全战胜宗教。而19世纪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人们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下,王韬等有学之士虽然接触了西学,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彻底,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是处于萌芽阶段,王韬只是希望借助西学来进行变法图强,改良中国社会现状。
(四)弥尔顿与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之局限性
弥尔顿和王韬的言论出版自由观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弥尔顿的言论出版观包含太多的宗教神学的东西,他用了很多宗教故事,借用上帝的名义去呼吁当局取消出版许可制,他只是提出了反对书籍出版许可制的理由,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措施去保障个人的言论出版自由。所以,弥尔顿要求的言论出版自由是一种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言论出版自由。而王韬直接把实现言论出版自由的途径寄希望于清政府,本身没有强调言论出版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它有赖于统治者的施与,这也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
三、结语
尽管弥尔顿和王韬在言论出版自由观方面有诸多差异,但弥尔顿和王韬在相隔两个多世纪的时空中先后发出了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呼声,为当时的社会发展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冠以“传播学之父”的韦伯·施拉姆在《传媒的四种理论》中指出,正是从弥尔顿的思想出发,发展出了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两个概念。弥尔顿为西方新闻自由的最终胜利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王韬也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对于梁启超等人的报刊活动具有不可缺少的指引作用。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0.
[2]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71,310.
[3]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51-53,47,30-31,14,7,16-17,6.
[4] 黄旦.王韬新闻思想试论[J].新闻大学,1998(3):69-72.
指导老师:郭建斌,李凤萍
G230
A
1674-8883(2016)18-0088-02
贺元双(1992—),女,湖南株洲人,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