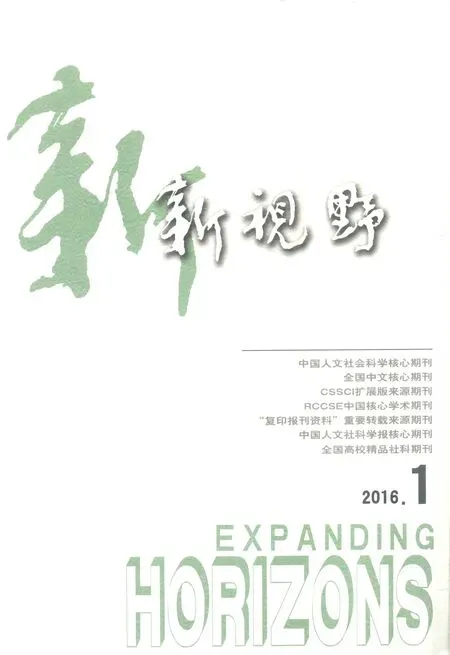家文化对社区安全治理的启示与实践
2016-02-28周延东郭星华
文/周延东 郭星华
家文化对社区安全治理的启示与实践
文/周延东 郭星华
近代以来我国传统家文化变迁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转型特征,阻碍了家文化治理资源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应用与创新,导致社区“共同体”情感和道德联结意涵逐渐瓦解,社区安全治理面临严峻困境。对此,应该立足本土观的价值理念,系统地梳理和挖掘传统家治理的具体影响因子,包括家认同、经济利益和情感文化联结机制以及家的“类”“推”精神等等。建议动员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培育社区认同感;赋予社区更多治理资源与权力,畅通经济利益和情感文化联结机制;发扬家的“类”“推”特性,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为社区安全构建具有本土文化气质的治理模式。
家文化;社区安全;本土化;治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在“传统人向现代人”“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型变迁中,社区所承载的功能日益丰富和强大,成为推进社会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平台和主要载体。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的居住空间与其它主要活动领域相互分离,推动了社区的“去家族化”“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社区“共同体”的情感和道德联结意涵逐渐瓦解,导致社区犯罪、社区治安侵害和社区矛盾纠纷等问题直接威胁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本研究针对以往较多借鉴西方治理模式,而较少涉及本土治理资源挖掘应用的现实状况,尝试从家文化维度作为切入点,构建具有本土文化气质的社区安全治理模式。
一 传统家文化的弱化变迁
清末民初时期,以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所倡导的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和人权天赋等理念原则被康有为、严复等先进知识分子引入我国,与当时正开始形成的私有制和契约经济直接呼应。康有为在《实里公法全书》中论述父母子女关系时,径直将个人本位宣布为“实理”和“公法”,指出“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 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1]谭嗣同认为传统的三纲五常是“害人的地狱”,“五伦”之中,只有“朋友”关系是符合现代自由、平等观念的,其它四伦都应以“朋友”之伦作为参照、予以改造。[2]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在中西文化“重三纲”与“明平等”、“亲亲”与“尚贤”以及“尊主”与“隆民”的对比中,旗帜鲜明地倡导个人主义,其矛头也直指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原理特性。[3]这都直接动摇了以伦理秩序为特征的家传统基础,也从本质上否定和撬动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合理性。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时代精英高高举起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激烈而彻底地检讨和批判中国传统。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深刻地体会到“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弥足珍贵,但这对于传统的杀伤力也是极强的,使得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它一方面引导人们通过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走向现代,另一方面却使我们逐渐割断历史、抛弃传统,逐渐丧失了对于本土文化的温情与依赖。在新文化运动中,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传统伦理是其主要攻击对象,而以家文化系统为载体的礼教和习俗更是其攻击的核心。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消灭了封建政权和地方族权,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人民公社体制”“单位组织体制”以及“破四旧”“移风易俗”等系列政策全方位地撼动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传统的“家族人”向“单位人”转变,进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时期,进一步加速了传统家文化的瓦解。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传统家文化的冲击和破坏是最具颠覆性的,“五四”时期的反传统虽然是激烈的、彻底的,但它基本上是思想与思想的冲突,“五四”精英大都是受过传统文化训练、带有浓厚中华文化味道的知识分子,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理性的运动,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非理性的反传统,是情感的宣泄,是政治权力的冲击,家庭道德也在“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街坊揭发邻里”等行为中荡然无存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从以血缘、姻缘和地缘为联结机制的传统“伦理型”社会向以货币、权力和地位为联结机制的现代“法理型”社会转变,[4]传统家文化的深刻内涵也在理性逻辑和功利主义思维中继续弱化,尤其是传统家文化的权威体系和伦理秩序进一步“失灵”,在现代社区居民看来,他们的居住地是一个“私人空间”,不愿参与到那里的公共事务和社会交往中去,这就难以发生相对稳定且高频率的交往互动,社区安全治理的基础呈现弱化的趋势,对于社会安全稳定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通过梳理分析可知,我国传统家文化呈现不断弱化的转型特征,社会成员也可以从“单位之外”和“市场之中”获取资源,从而降低了个体对于家族和单位的依赖性,使社区成员互不相识、缺乏信任,依“理性”和“市场规则”行事,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追求导致人际关系和情感的消逝。传统家文化的弱化变迁,导致了“共同体”意涵的瓦解,也使现代社区安全治理陷入严峻困境,如社区安全保障不足、社区环境污染、服务设施不到位、医疗卫生缺失以及社区矫正功能虚化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社区矛盾冲突不断升级。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家文化的治理资源,为现代社区安全治理提供新思路。
二 家文化的三大治理资源
叶启政认为,在现代社会,家文化知识体系依然能够引起社会成员的感知认同和共鸣,拓展和激发人们的理解空间,让人们感觉到“家”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依然“贴切而有用”。[5]社会成员从“家庭人”到“单位人”,再到“社会人”,其伦理道德观念、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家国情怀的价值观念一直是国家治理中的内生型动力,具有重要价值。[6]传统家文化内涵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发生着深刻变迁,诸多落后的封建礼教弊病都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逐步退出现实生活实践。但其维系社会秩序和安全的治理资源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家认同
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家,家的宗教性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源泉,自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自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自“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我国的封建传统家文化受到强大的冲击。尽管如此,“传统”是在多维时空范围内积累和沉淀形成的,具有超稳定的“惰性力”,所以中国人的家庭和家族观念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家文化内核仍然是维系家庭血缘纽带的基本规范,也是社会成员最为重要的生活场域。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在对传统家文化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在新时期呈现出新的活力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逐步确认家庭联产承包、城乡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合理性,并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支持保障,很多家庭又重新作为经济单元主体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成员回归家场域。
在家观念的认同体系中,“孝”是其核心内涵,“知恩必报”成为社会正义的基础,感恩文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涵,是社会成员实现社会认同的连接点。家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演进发展中,不单指家、家族和宗族范围内的概念,还包括在相对封闭场域内不同个体、家庭相互之间在广义或狭义范围中产生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或情感方面的联系,以礼制道德为纽带延伸至社会国家,因此,从传统的“家认同”转向现代的“社区认同”具有极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这就需要从多维立体的思维方式弥合构建传统家族文化和现代社区安全治理的联结因子,提高社区成员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经济利益和情感文化联结机制
在传统家庭中,家庭的延续和再生产包含诸多内容,其中,“分家”的作用至为关键,分家是指父母将财产传递给已婚兄弟,是年轻一代享有了父亲部分财产的专有权,并从原有大家庭中分离出去的状态和过程。[7]麻国庆指出,分家“有继也有合”, 他认为,中国的家并不像细胞分裂,不是整体的破裂和分离,而是在“分”的过程中,更体现了一种“合”的精神,本家与诸家虽然在经济上分开了,但是作为整体的家庭责任义务和情感文化仍然将家庭成员紧紧联系在一起,生产生活实践的相互合作、礼俗节庆的欢度共享以及红白喜事的协调互助都存在着密切互动。即中国的家在其生命周期一段时间内是存在分离倾向的,主要是经济的分离,但是在情感和文化中又表现出极强的向心力。[8]这就形成了维系家族秩序的两种机制:一种是传统家文化通过分家使家庭子嗣获取“成家”的主要经济基础,构成了传统家族的经济联结机制;另一种是分家之后家族相互之间依然保持紧密的协调、互助与合作,构成了传统家族的情感文化联结机制,正如费孝通所说,“他们经济上变独立了,但是这种社会义务仍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9]
当前,家的经济和情感文化联结机制失去了自给自足小农封闭经济机制的基础,社会成员都被“市场化”地进入社区之中。在现代社区中,社区居委会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作为“国家基层治理的最基本单位”依然是其主要职能定位。杨敏曾直接指出,现代社区治理是为了解决转型期的社区整合和社区控制问题,是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10]王汉生和吴莹也认为,当前社区治理过程一直是在政府的“参与” 和“在场” 下实现的,浸透着国家的身影和力量。[11]然而,现代社区治理资源和治理权威的弱化,严重影响了社区安全治理的效果。由此可见,社区安全治理需要借鉴传统家文化的两种联结机制,并将这种联结机制转移到代表国家治理最基层的社区之中,赋予社区更加完善有效的治理资源和权力,尝试构建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成员、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沟通机制,推进社区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三)“类”“推”精神
中国传统家文化具有“类”和“推”的特征,对于这一特征,将其与日本家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明确。日本学者对于日本社会的家和亲属制度的研究认为,家不仅仅是亲属集团,而且还作为生活共同体以及经营共同体。滋贺秀三指出,中国的家既注重有形的经济联结要素,又注重无形的生命传承文化要素,是将有形和无形融合在一起的组合形态。而日本的家则偏重于居住和经济要素,家庭居住成员并非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收养养子以及亲族以外的人(如佣人)都可以作为家庭成员而形成一个生活共同体。[12]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家是“合伙的”,强调血缘体及其外延关系,那么日本的家则是“财团的”,强调经营体的功能组合。对此,诸多中国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家并不是不注重经营概念的,除了文化意识形态之外,中国的家同样注重经济功能。费孝通指出,家的概念是伸缩自如的,一个家的规模和构成常常随政治、宗教和经济需求等因素而定,在发现核心家庭无法完成各种任务时,那就会扩展血缘关系范围,甚至是非血缘关系,并加强相互之间的情感认同,并纳入家的范围,也可称之为“自家人”。[13]麻国庆指出,社会和国家只不过是家庭组织的一种扩大,家庭与社会并不是两个对峙的东西,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存在“推广”和“扩充”的关系。[14]
家文化中“推”是以血缘的家为基础,向外扩展进行社会结合的联结方式。这种特性在我国社会组织结构中十分普遍,如现代家族企业、行会等等。由此可见,现代社区可以充分发挥传统家文化中的“类”“推”特性,构建社区安全治理的“共同体”,推动社区安全建设。此外,相对于前两种治理资源,“类”“推”具有动态性和系统性的特点,是联接传统家文化与社区安全治理的重要支点,将家文化所包涵的“家认同”、“经济利益和情感文化联结机制”等治理资源通过这一特性应用于具体实践,使社区安全治理成为一个动态、整体和有机的系统体系。
三 构建社区安全治理体系
在现代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资本投资和管理机制是实现社区安全建设的重要手段,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社区安全治理实践,建立社区成员之间的道德和情感基础才是社区安全的基本目标。对此,只有在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信仰中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才是最具亲切感、最被认同的。现代“家”的组成形式大不同于传统社会,这就需要将其对象从“家”转向“社区”,正如潘光旦在论述家的孝道时所说,“由家族主义之孝扩充而为民族主义之孝;或者说,孝道不可废,而对象不能不改,而最适宜的是以民族的对象替代家族”。[15]社区作为家的承载体,成为现代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主要支撑体,也是其最为关心的场域。因此,挖掘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整合资源,搭建传统家文化与现代社区安全治理的连接系统,补充国家、社会以及“碎片化”实践在社区安全治理中的“缺位”,希翼对我国社区安全治理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动员社区各主体参与,培育社区认同感。在传统家文化体系中,对于家庭角色都做了精确的角色定位,这就需要家庭成员尽力满足角色期待,保证家庭功能的有效运行。在现代社区中,就需要基层政府、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第三方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成员多主体共同参与。此外,还要建立社区精英参与的机制策略,赋予其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身份,提升参与社区安全治理的荣誉感。肯尼斯和罗纳德曾说,社区是对付暴力和骚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其核心是建立并维持相互信任关系。[16]这就需要明确各个主体在社区安全治理层面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教育宣传和参与实践等多种方式动员社区成员参与到社区安全建设中来,通过实体活动和虚拟网络两个平台建构以互惠、信任和情感为基础的社区互动网络,大力培育社区认同感,提高社区安全治理水平。
第二,赋予社区治理资源与权力,畅通经济利益和情感文化联结机制。社区居委会要充分发挥社区安全治理的主体地位,在经济利益联结机制方面,要严格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能,积极协调处理涉及到社区成员利益的相关事项,整合资源、共驻共建,增强管理和维护社区集体资产的能力,组织筹措社区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的发展基金,为社区安全治理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利益权威;在情感文化联结机制方面,要围绕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特别是广泛宣传家文化中所倡导的“父慈子孝”“伉俪和美”“兄友弟恭”等和谐家庭关系理念。此外,还要促进社会成员在社区场域内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了解和热爱,在增强传统情感的基础上构建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结机制。
第三,发扬家的“类”“推”特性,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杜维明在讨论现代中国时指出,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很难转换成公民社会。[17]麻国庆对杜维明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存在“家族化的公民社会”,其基础正是家族伦理与延续的纵式社会,它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必然存在着诸多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需要从家的“类”“推”特性出发,从局部到整体,逐步实现社区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对此,英国社区的邻里守望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巧妙地体现了“类”“推”的特征,邻里守望作为一种自愿行为,参加邻里守望的社区居民在自己家的窗户上贴上“邻里守望”的标志,参加此活动的街坊四邻就可以相互注意、相互关照,以免遭受犯罪的侵害。据英国内务部调查结果显示,在样板社区,邻里守望活动使犯罪减少了四分之三,英国罗秀迪尔的卡克霍尔特实施邻里守望计划三年后,几乎所有的社区居民都参加了这一计划,社区安全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此,现代社区可以以地缘、业缘或兴趣爱好等为共同体基础,逐步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为社区安全治理体制所用,维护社区安全稳定。
综上所述,在我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社会成员逐渐从“传统家族”中脱离出来,家文化的丰富内涵在理性逻辑和功利主义思维中渐渐消逝。不过,我国毕竟具备漫长的、丰富的家文化传统,基于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应当系统梳理维系传统家族秩序的影响因子,大力发扬家的“类”“推”特性,积极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构建具有本土气质的社区安全治理体系。
注释:
[1]康有为:《康有为大同论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9页。
[2]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卷,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第350页。
[3]严复:《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8页。
[4]宫志刚、周延东:《行走在自由与秩序之间——构建治安实践运作中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5]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6]杨善华:《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7]麻国庆:《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8]麻国庆:《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第112页。
[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10]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11]王汉生、吴莹:《基层社会中“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国家——发生在一个商品房小区中的几个“故事”》,《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12]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の原理》,东京:创文社,1967年,第58-68页。
[1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44-349页。
[14]麻国庆:《类别中的关系: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文史哲》2008年第4期。
[15]潘光旦:《优生与抗战》,《潘光旦文集》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16]Kenneth J.Peak,Larry K.Gaines and Ronald W.Glensor, Polic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n an Era of Commuity Policing. 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 Hall, 2003, p.145.
[17]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38页。
责任编辑 刘秀秀
C911
A
1006-0138(2016)01-0113-05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村改居社区安全多元共治机制研究”(15SHC038);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传统家文化与社区警务机制建设”(2015JKF01405)
周延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讲师,北京市,100038;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