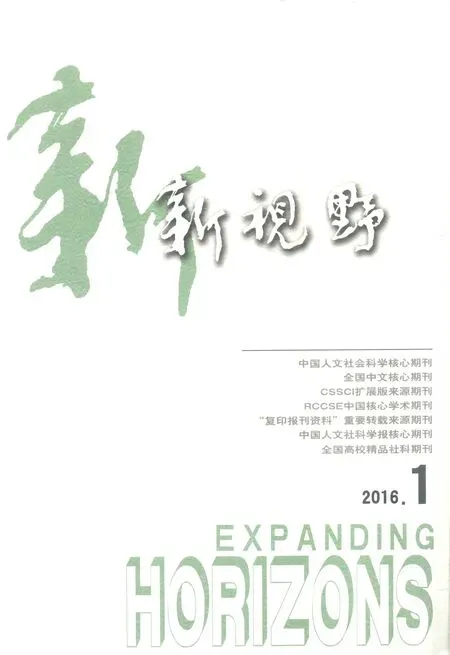城际高铁背景下区域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2016-02-28文/殷平何赢袁园
文/殷 平 何 赢 袁 园
城际高铁背景下区域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文/殷 平 何 赢 袁 园
城际高速铁路的发展,对沿线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在高速铁路“时空压缩”机制影响下,旅游市场边界不断延伸,旅游产品消费空间上发生转移,旅游产品面临转型或发生替代,旅游目的地加剧空间竞争,区域旅游空间格局重构,从而带来区域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契机。城际高铁发展,促进了旅游业与铁路交通业的深度融合,形成铁路旅游业的新产品与新品牌;促进了旅游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形成新的旅游业态;促进了旅游业内部各行业的融合,形成消费空间的创新与行业创新;促进了交通行业内部与各地区交通企业的融合,形成交通集团或交通联盟;促进了区域旅游空间的深度融合,形成区域旅游经济复合体。
城际高速铁路;产业融合;区域旅游业
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圈或者城市带,短距离、公交化的城际高铁以高频次、大运量的交通运输优势,改变了区域的交通格局,促进了地区产业的资源整合、产品创新和市场共享。可以预见,我国的高速铁路将真正实现网络化,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将更加便捷。旅游业是受交通影响最大的产业之一,每一次交通技术变革都带来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在闲暇时间越来越成为旅游约束条件的背景下,城际高铁对旅行时间的大幅度节约使得高铁沿线城市之间的大规模、高频次互访成为旅游“新常态”。很多城市都针对“高铁时代”的到来采取了新的宣传口号,推出了“高铁旅游产品”,但成效并不显著。基于此,本文从城际高铁对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入手,重点分析区域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为城际高铁沿线区域响应高速铁路发展、获取持续空间竞争力提供理论支持。
一 产业融合的理论阐释
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最终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1]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引起产业融合的最重要因素。[2]尽管产业融合的质变建立在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兴产业革命之后,但产业融合的思想却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相关论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曾提到“当分工的精细不断增大时,名义上不同的各种行业之间的分界线,有许多正在缩小而且不难越过”。[3]“技术革新或政府放宽管制”后,行业间、产业间的壁垒降低,竞争加速,促使产业界限不断模糊直至缩小并被超过,从而出现产业融合。在推动产业融合的动力中,程锦等又在技术革新、放松管制之外,提出了管理创新。[4]
技术边界、业务边界、运作边界与市场边界共同作用,界定了一个产业或产业内部的一个行业。当技术创新或进入壁垒消失后,提供接近性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提供上下游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出现新的竞争或合作环境,边界会逐渐模糊。不同产业之间或不同企业之间发生交叉,出现融合性产品、融合性市场、融合性制度等。产业融合发生在边界模糊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斯蒂格里兹根据技术、供需和产品三类标准,将产业融合划分为技术替代性融合、技术互补性融合、产品替代性融合和产品互补性融合四种类型。[5]随着融合发生的越来越广泛,融合类型判断出技术还是产品得替代已失去意义。在斯蒂格里兹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又将产业融合划分为技术渗透融合、产业间延伸融合、产业内部重组融合、全新产业取代传统旧产业融合等四种形式,[6]或者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等三种形式。[7]
二 城际高铁带来区域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变革
厘清城际高铁对旅游产业带来的影响,是探讨区域旅游产业融合的前提。城际高铁对于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是相对复杂的概念。对于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而言,城际高铁所提供的交通条件,既是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要素,同时也是与旅游业并列的产业。因此,从产业融合产生的动因来分析,把城际高铁作为区域旅游业发展要素之一,则产业融合的动因更多来自于技术变革;把城际高铁作为区域旅游业的并行产业,则产业融合的动因更多来自于管理创新。
(一)城际高铁提高了交通可达性,引发旅游市场边界延伸
城际高铁通过影响交通网络的向心度和连接度而改变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与景点可达性。向心度和连接度作为衡量可达性的重要指标,其大小取决于交通网络中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数量与节点数量的关系。最短路径越小,交通网络的可达性越高。一般来说,交通网络中节点数量是稳定的,但由于交通技术的变革带来交通设施的变化会影响到节点之间最短路径数量的变化。城际高铁作为快速交通的出现,使得节点之间出现新的最短路径,从而提高了网络的交通可达性,也提高了城际铁路节点城市的向心度和连接度。
交通系统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就在于旅游市场的边界大小受交通网络可达性影响很大。交通网络可达性高,旅游市场边界较大;交通网络可达性低,旅游市场边界较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高铁运营前,区域旅游交通网络中不同交通节点上的旅游企业市场边界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高铁运营后,旅游交通网络的向心度与连接度都将提高,区域旅游的可达性提高,整个旅游交通网络的通达性提高。同样的交通节点城市的旅游企业,其市场边界将得到延伸。市场边界延伸首先将改变市场定位,使原先的中程市场成为近程市场,远程市场成为中程市场;其次将会引发市场性质,即原有的观光旅游市场由于旅游交通时间的缩短而成为休闲市场,原有的度假市场成为观光市场。
(二)城际高铁压缩旅行时间,引发旅游需求的空间转移和动机转移
人均自由支配收入逐渐提高给旅游出行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支付能力不再成为出行限制因素,而闲暇时间上升为第一制约因素;二是旅游动机类型更加多样,且休闲类动机将多频次出现。这两种影响所引发的新的旅游需求,在传统交通工具时代其实现有一定难度,但高铁缩短旅行时间的背景下则可以得到充分地满足。
传统交通工具帮助下5天的旅游行程,在高速铁路帮助下可能会缩短至2天。如果有5天的闲暇时间,旅游者可以在高速铁路帮助下到达更远的旅游目的地。这样旅行时间的节约,一方面使得短时间、长距离的旅游出行成为可能,同时也使短时间、短距离的旅游出行成为常态。在现行的假期制度下,周末闲暇时间借力高铁由旅游的非热点出行时间转变为热点时间;公共假期时间的旅游需求实现空间可以被扩展至更远的距离。城际高速铁路紧密地联系了两个或多个城市,休闲类旅游资源可以实现共享,从而满足城市居民常态化、多频次的休闲类旅游动机。天津的居民在京津城际高铁的帮助下,下午5点钟出发到北京全聚德与朋友吃一顿烤鸭晚餐,晚上9点钟再回程;北京的居民周末郊游活动在城际高铁的帮助下,可延伸到河北的农村体验农家生活。由此可见,对于城际高铁连接的城市来说,游客的旅游需求、休闲需求不再局限于城市或城郊,而是另外一个城市的城市和城郊都在公交化的城际高铁帮助下成为可选范围。
(三)城际高铁带来城市边界的模糊,引发旅游产品的替代与转型
城际高铁的开通与运营,拉近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城际高铁连接的两个或若干个城市之间的地域边界逐渐模糊。城市的旅游景区、旅游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等在城际高铁带来的“同城化”效应下能够极大程度地实现共享。城市的旅游者在短途出行时不再受到时间和旅途的束缚,局限在城市地域内选择旅游产品,而将选择范围扩大到同城化的旅游经济圈中。因此,同城化旅游经济圈中的旅游产品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危险。
在旅游者追求最大效益原则的作用下,知名度低、等级品位低、旅游体验弱、服务质量不高的旅游产品将被其他旅游产品边缘化和替代,从而失去生存空间,最终在旅游经济圈的产品体系中消失。在特色相似的旅游资源基础上开发的不同旅游产品,急需在旅游形象清晰化、旅游市场目标化、旅游营销精准化等方面提升水平,从而实现旅游产品的升级或转型,进而获得发展的可能。
(四)城际高铁降低旅游时间成本,引发旅游目的地空间竞争
随着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影响力越来越小,闲暇时间逐渐成为影响旅游决策的首要因素。在给定的旅游时间约束前提下,追求最小的旅游时间比(最多的游玩时间、最少的旅行时间)成为旅游者效用最大化的最佳途径。在给定的时间约束下,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空间位移上花费的时间越少,则留给目的地游览的时间将随之增加。在这一原理的驱动下,旅游者会通过寻找更便捷的交通方式来获得节约旅行时间的途径。如果旅游目的地的交通便捷程度达不到强化旅游吸引力时,旅游者的兴趣将会转移到其他交通便捷的旅游目的地。[8]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游客在旅游消费预算的约束下,将会根据旅游交通成本选择不同的消费组合,从而选择不同的旅游目的地。因此,在住宿费用、自由支配费用相似的情况下,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交通成本的大小。同时,目的地空间竞争不仅数量发生变化、程度发生变化、对手发生变化,同时原有的合作对象也会变成竞争对手。
(五)城际高铁加速旅游要素区域流动,引发旅游空间格局演变
杨维凤提出,高铁带来核心节点与其它节点城市之间发展的势能差,从而引发生产要素尤其是核心生产要素集聚度的空间分异,形成经济发展隆起带。[9]对于旅游业而言,高铁发展带来了较低的交通成本,旅游产业要素将向成本较低的城市集聚。在同一个区域内若干旅游城市(目的地)在要素集聚效应的作用下,空间结构将呈现出核心—边缘模式。[10]
高速铁路对产业要素配置的影响在于通过旅游交通条件的改善改变了区位的优劣价值判断,从而引发旅游产业要素向更优的区位配置。在旅游产业的生产要素中,旅游从业人员、投融资、产业技术等一般性要素的流动成本将比旅游资源等要素低,因此这些要素将随着高速铁路向区位更优、存在规模递增收益的区位集聚。高速铁路开通后,沿线城市由于区位的改善而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原有的一般品类的旅游资源或非传统旅游资源将获得开发机会,形成若干旅游景区。以景区为核心,其它旅游服务如住宿、旅行服务、餐饮、购物等相关要素集聚到高铁沿线城市,形成沿高铁分布的旅游城市带;在城市微观层面,高铁站附近地块成为优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地块,因此商务型酒店、购物街区等将大量布局在站点附近,形成城市内部的旅游产业的集聚区,同时也成为城市旅游的集散中心。这一表现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中“鼓励依托城市综合客运枢纽和道路客运站点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游客集散中心”[11]的精神。由此可见,高速铁路加速了旅游产业的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引发了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变。
三 城际高铁背景下区域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表现形式
产业融合的外在表现为产业边界模糊化。旅游业发展到今天,游客的旅游需求趋向多样化和综合化,高速铁路引发动机的变化和交通条件的变化,使不同产业与旅游业或旅游业内的不同行业进行业务、组织、管理和市场的资源整合,并在更大范围的产业价值链上重新分工,最终形成新产业或出现新的增长点。
(一)城际高铁与旅游业深度融合,表现为业务融合与铁路旅游产品创新
铁路旅游产品在我国已经并不新鲜。从传统的旅游专列到特色的旅游专列,都已有较长的开发历史和开发经验,也形成了我国特色的铁路旅游产品和旅游行业。铁路旅游产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以铁路交通功能为主,开通从客源地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冠以旅游景区或知名旅游产品的列车。例如每年旅游旺季时焦作推出的云台山号普通列车(从北京晚上出发,早上到达焦作)即属于这一层次的铁路旅游产品。第二层次为旅游专题列车,即铁路列车转为旅游目的地开设,所经地区为同一旅游主题,车厢设计、列车广播、沿途活动安排等都以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为目的。“长沙—韶山红色旅游专列”、兰州铁路局开通的“丝绸之路”主题专列为这一层次铁路旅游产品的代表。第三层次为铁路交通本身就是一种旅游产品。邮轮旅游即是这种理念的水上交通工具开发而成的交通旅游产品。铁路列车作为陆地交通工具,其空间容纳力、旅行时间长度等,最适合开发成为专项旅游产品。国际上已有成功开发的先例,如辛普朗东方快车、南非“非洲之傲”列车、瑞士“冰河列车”等。在我国,前两类铁路旅游产品已经相对成熟,但“铁路本身就是旅游的品牌”尚未实现。
乘坐铁路成为一项旅游产品的价值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列车设施豪华,服务种类齐全,国外的豪华列车等属于这一类。第二,列车有独特个性,可以提供特殊体验。如名人乘坐过,或发生或特殊事件,国外的东方快车为这一类。又如铁路运行速度极快,代表科技发展方向。我国的高速铁路即可围绕这一价值开发产品,“乘坐高铁本身就是旅游”可以成为高铁旅游产品创新理念。
(二)旅游业与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表现为市场融合与旅游业态创新
通过城际高速铁路的交通技术创新,旅游企业的市场边界得以沿高铁线路延伸,旅游者的需求沿高铁线路转移,旅游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是第三产业(如餐饮业、房地产业、零售业等)的市场绩效将得到显著提高。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出现旅游业与传统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扩展第三产业的市场结构。商贸业、餐饮业、房地产业等,与旅游业融合之后,形成购物旅游、特色餐饮旅游、旅游地产、商务旅游等。这些新的产业均可在城际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机制下,在城际高铁沿线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同样,沿线城市的第三产业,则由于高铁带来的市场延伸机制从而引来消费人群的空间延伸,实现消费市场结构的升级。
(三)旅游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深度融合,表现为消费空间融合与旅游行业创新
旅游产业本身的边界模糊性强,迄今为止尚无法完全明确旅游产业的边界。一般来说,凡为游客服务的交通行业、住宿行业、餐饮行业等,都可划分到旅游产业中。从产业融合的角度来看,这些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最容易产生融合。这种产业融合在城际高铁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跨边界服务的现象更易出现。在城际高速铁路的服务过程中,消费主体旅客、游客身份实现互换,从而对应着交通空间与旅游空间的互换,带来交通产品与旅游产品的深度融合与创新。高铁列车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空间,高铁广播节目、阅读杂志等转换为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平台。同时,铁路运营公司在多元化经营战略拉动下也在积极探索旅游服务的创新切入点。北京铁路局在2014年国庆节期间推出的“自驾游汽车运输班列”即是行业创新之举。随后呼和浩特铁路局、兰州铁路局等也都推出相应的服务,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四)交通行业内部与地区间的深度融合,表现为跨界融合的交通集团和交通联盟
城际高速铁路可以实现城市间快速、便捷的空间移动,但从车站站点到景区、酒店或其他旅游消费空间的距离,则需要公路交通的强大支持。这种交通服务的无缝对接,在城际高铁发展的初期,可能由城市的公共交通、汽车租赁公司自发实现服务。但从长远看,随着高速铁路带来越来越多的商务游客、小团体游客等,旅游交通的无缝对接需求将逐步深入,将推动交通行业内部、不同地区的交通集团的深度融合,造就优势旅游交通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打造跨界融合的交通集团和交通联盟。随着铁路部门多元经营理念的深入、市场化改革脚步的推进,高铁运营公司可能将会为应对城际高铁的强大旅游客流而整合汽车租赁公司、城市轨道运营公司等,打造为巨无霸性的交通集团或交通联盟。
(五)区域旅游空间的深度融合,表现为跨区域旅游复合经济体
城际高铁将两个或多个城市通过高速铁路交通连接为一个区域整体,城市间实现半小时或一小时交通,通过公交化的高速交通方式实现了区域城市间的同城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目的地城市的空间竞争主要体现在区域内同质化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层面。对于区域外的旅游市场,城际高铁沿线城市最应当通过分工与合作,推动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线路等旅游供给层面的空间深入融合,形成面向远程旅游市场的一体化的跨区域旅游复合经济体。
四 城际高铁背景下区域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未来趋势
产业融合有不同侧面,包括产业间融合和产业内行业的融和。城际高速铁路促进了旅游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促进了旅游业内部各行业的融合,促进了交通行业内部与各地区交通企业的深度融合,也促进了区域旅游空间的深度融合。城际高速铁路除了带来区域旅游产业融合和产业内行业融合外,还将带来更重要的融合层次,即跨地域的产业融合。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出现了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市场,也推动交通集团或交通联盟的出现,并促进跨地域旅游复合经济体的形成。
高速铁路引发旅游产业不同层面的融合,要求沿线旅游目的地做出战略调整。沿线旅游目的地在这一浪潮下应迅速捕捉商机,构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融合模式,以应对高铁带来的新需求、新市场、新竞争格局,以促进我国旅游产业融合的整体水平;同时应注意到旅游产业融合不仅局限于产业内部,更多的发生在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这就要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敏锐地觉察到政策需求,加大部门间、地区间的政策协调力度,在旅游跨界融合、跨区融合、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出台引导性政策,优化旅游产业融合的环境。
产业融合不仅要求加强现有高铁沿线城市的区域合作,更要求加强待建高铁沿线的区域合作,以推进区域融合发展水平。铁路建设今后的一个重点任务是中西部地区的高铁建设。而中西部高铁开发,对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战略中,由于文化脉络的相近特征,旅游业将成为相关区域产业体系中重要的发展突破口。《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巩固旅游等产业的规模优势,培育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产品,推进承载中华文化的特色服务贸易发展。[12]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鼓励错位竞争、协同发展。结合“一带一路”的高铁规划与建设,“丝绸之路”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产品的开发势必要在产业深度融合的理念下建设,才能创新出旅游精品、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产业发展水平。
注释:
[1]厉无畏、王振:《中国产业发展前沿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
[2]陶长琪:《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自主创新与产业成长的协同机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页。
[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2-275页。
[4]程锦、陆林、朱付彪:《旅游产业融合研究进展及启示》,《旅游学刊》2011年第4期。
[5]N.Stieglitz, “Industry Dynamics and Types of Market Convergence”, DRUID Summet Conference on“Industry Dynamics of the New and Old Economy-Who is Embracing Whom?”, Copenhagen, June6-8, 2002.
[6]聂子龙、李浩:《产业融合中的企业战略思考》,《软科学》2003年第2期。
[7]胡汉辉、邢华:《产业融合理论及其队我国发展信息产业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2期。
[8]B.Prideaux, “The Role of the Transport System in Destination Development”,Tourism Management,2000(1),pp.53-63.
[9]杨维凤:《京沪高速铁路对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0]殷平:《高速铁路与区域旅游新格局构建——以郑西高铁为例》,《旅游学刊》2012年第12期。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2015年8月11日,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5-08/11/content_10075.htm,2015年10月16日。
[1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2015年2月14日,http://www.gov. cn/zhengce/content/2015-02/14/content_9482. htm,2015年10月17日。
责任编辑 马相东
F592
A
1006-0138(2016)01-0081-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高速铁路影响下京津冀地区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研究”(13YJC790184);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高速铁路发展的京津冀旅游一体化战略研究”(13JGC103)
殷平,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京市,100044;何赢,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管理系研究生,北京市,100044;袁园,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管理系研究生,北京市,1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