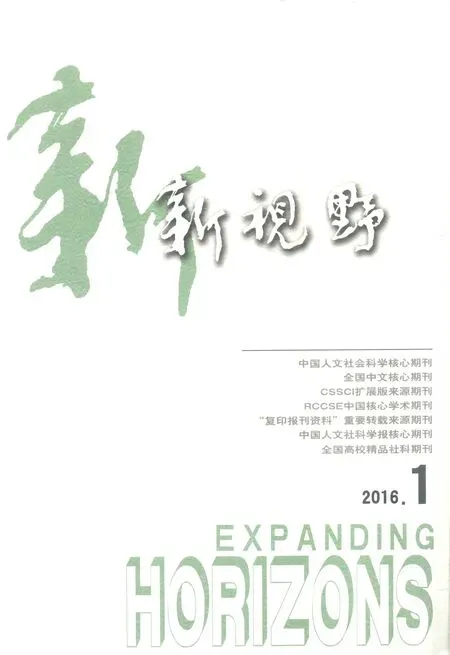马克思论虚无主义的双重维度及其破解路径
2016-02-28王海滨
文/王海滨
马克思论虚无主义的双重维度及其破解路径
文/王海滨
虚无主义侵袭的问题,是现代性的问题域中关涉根本又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虚无主义所涵摄的双重维度:资本逻辑塑造的外在人化世界的虚无,其内在逻辑是以历史性摒弃神圣性与超越性;物化生存导致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虚无,其内在逻辑是人的内在本质的空虚化。马克思超越抵制虚无主义侵袭的思辨路向,把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求放置在客观的历史性维度之上,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冲出双重维度的虚无主义的路径。马克思的这些探索,对于破解在一定意义上存在于当代中国的“物欲横流”“价值真空”“精神虚无”等文化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资本逻辑;物化生存;虚无主义;双重维度
虚无主义侵袭的问题,是现代性的问题域中关涉根本又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在当代中国,虚无主义及其在民族、历史和文化等领域的诸种表现形式,成为侵袭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消解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进而阻碍中国现代化征程的一种深层文化阻滞力。在直面时代问题、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虚无主义思想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虚无主义的双重维度,并开辟了破解的路径。马克思的这些探索,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虚无主义以及自觉抵制虚无主义的侵袭,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 资本逻辑塑造的外在人化世界的虚无及其内在逻辑
与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不同,现代化进程是世俗取代神圣、神性让位理性的过程。尼采用“上帝死了”这个惊人的论断形象地表达了现代化进程的这种特征。随“上帝死了”而来的是支撑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传统信仰、价值和道德体系崩溃了,虚无主义不可避免地开始侵袭人间了。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现代人试验性地一会儿相信这种价值,一会儿相信那种价值,然后又把它取消了:过时的和被取消的价值的范围变得越来越丰富;价值的空虚和贫困越来越明显可感”,因此,“虚无主义的来临”,“这场运动是不可遏制的”。[1]在价值虚无主义笼罩生活世界的时候,尼采反对通过重设理想以抵制虚无:“直到现在,理想都是真正地诽谤世界和人类的力量,是笼罩在实在性上面的瘴气,是使人走向虚无的大诱惑。”[2]尼采主张坚强地面对现实生活,呼唤“超人”的出现,并寄希望于“超人”能够以“权力意志”为标准,“重估一切价值”,进而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实现人的使命与价值。
从逻辑上看,面对虚无主义的侵袭,尼采反对理想世界、信仰世界而肯定权力意志支撑下的现实生活世界。与尼采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通过对经济问题的深入探讨以把握时代特征,并以哲学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显然不会苟同尼采的理论洞察和方案设计。实际上,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深入揭示了现实生活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的虚无特征。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时代的虚无主义涵摄双重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就是资本逻辑塑造的外在人化世界的虚无,其内在逻辑是以历史性摒弃神圣性与超越性。[3]
面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代,马克思曾这样鲜明地揭示这个时代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既“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又“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还“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4]因此,“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5]这里的四个“一切”,形象地描绘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动荡不安与虚无缥缈式的诸种文化景观,深入揭示了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与交往过程中辩证法的否定性作用。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资本具有构造社会组织、支配社会关系、塑造思想观念的动力和功能,成为笼罩一切的光。因此,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也成为资本逻辑的支配物,成为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对此,马克思曾深入地揭示了社会关系及其观念表现的暂时性:“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6]
在马克思多次运用“历史性思维方式”表征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资本逻辑不仅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而且新生的诸种社会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也不再容易凝成固化的状态。这种变动不已的文化景观就是基于“历史性的取代传统的现代也必将为未来所取代”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暂时的地位上升到永恒的、规律的地位的时候,曾用如此清晰明确语言揭示“历史性的取代传统的现代也必将为未来所取代”的内在逻辑:“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7]简言之,取代封建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并不能成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也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暂时的和走向灭亡的。推而言之,建立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上的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景观,也都是不是永恒的不可变更的,而是暂时的历史的。
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不断地基于以历史性摒弃神圣性与超越性的内在逻辑,形象地描述资本逻辑塑造的外在人化世界的虚无:“自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甚至旧法规中按农民的习惯规定的关于昼夜的简单概念,也变得如此模糊不清。”[8]这种外在人化世界的虚无,以及对神圣性与超越性的摒弃,所造成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传统所重视的事物与观念统统让位于琳琅满目的商品,诸种商品尤其是奢侈性商品逐渐取代传统事物成为人的身份的标识与地位的象征。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9]这里“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当然就是指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下,对商品的崇拜与主体性的伸张成反比,资本和商品的力量模糊、淡化直至虚无化了其它的活动和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为片面的极端的发展所代替。
二 物化生存导致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虚无及其内在逻辑
在世俗取代神圣、神性让位理性的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的伸张成为突出的特征。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是人类精神之梦, 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实际上是在通过虚化宗教进而彰显现实的人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并“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0]马克思基于现实实践和社会关系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在现实资本主义生活世界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虚无化。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虚无主义所涵摄的第二个维度,即物化生存导致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虚无,其内在逻辑是人的内在本质的空虚化。
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11]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空虚化”体现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分离甚至对抗,进而促使本来能够证明劳动者本质价值的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带来的却是劳动者的贬值。作为资本家眼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的劳动者,能够体现他们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精神生活,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关注或所要发展的对象。马克思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悖谬现象的本质,并具体阐释了劳动者存在与价值的虚无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2]这种分离与异化使人的内在本质的对象化退变为空虚化,与这种退变相对应的景象就是资本逻辑催生的物化生存导致内在精神世界的虚无。
马克思曾通过对人的活动与商品的分析,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化生存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于人的活动,马克思曾指出:“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关系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3]对于商品,马克思则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4]这里,不论是人的活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活动、物的社会关系、物的能力,还是商品通过遮掩劳动的社会性质进而把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时代物化生存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景观。
在物化生存达到极致的资本主义时代,内在精神世界坠入了虚无的深渊。这一过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逻辑中曾反复出现,其表现形式就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与交换过程中,对物的依赖不断渗入并腐蚀人的心灵,有个性的人退化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提供者,而能够体现人之地位与尊严的其它特质均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阿诺德·盖伦曾这样指认马克思的这个理论逻辑:“一切专门化都必然产生出的片面性和固定化,发展出两种后果:一方面,在被规定了的范围内,操作变得越来越无限的精细(只有专家才能成为表演者)。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固定化使得人格的那些品性因素相对地成为不相干的了,而剩下来的那些相关方面的片面性又使得他身上真正个人的‘不可分离’的因素变得无关紧要。于是我们就可以像马克思那样,指出个人的生命(就其对它乃是个人而言)与他的存在(就他附属于劳动的某个分支,并处于与那种劳动习惯的条件之下而言)这两者之间所出现的差别。阿尔弗雷德·韦伯也指出了这一差别。”[15]当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陷入“物的依赖”,一个社会过度追求物的占有,并且人们开始以拥有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的时候,外在世界的膨胀必然开始挤压内在世界的伸张,物欲横流必然导致精神萎缩,而其深层逻辑就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的内在本质的空虚化”。
三 虚无主义之双重维度的逻辑关联及马克思开辟的破解路径
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虚无主义的双重维度,尽管一个存在于外在世界,一个存在于内在世界,它们之间却存有密切的逻辑关联:首先,资本逻辑既塑造了外在人化世界的虚无,又通过制导物化生存进而催发着内在精神世界的虚无。也就是说,塑造了外在人化世界之虚无的资本逻辑,由于它主导的异化致使人的内在本质与人的对象化过程及其产品严重分离,也成为导致人的内在本质的空虚化的“始作俑者”。其次,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化世界的虚无,尤其是“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的烟消云散”,以及“一切神圣的东西的被亵渎”,必然成为导致内在精神世界虚无的客观力量。最后,内在精神世界一旦堕入虚无的深渊,一切意义支撑、价值依据、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就会荡然无存,这自然严重侵蚀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并急剧加深人们对外在人化世界的虚无化判断。
资本主义时代的双重虚无,一定意义上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虚无的深渊。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时代和世界必须改变,并开出了治本的药方——依靠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消灭私有制,消解资本逻辑,建立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社会何以克服资本主义时代所无法抵御的虚无主义的侵袭呢?
首先,从主导资本主义时代双重虚无的资本逻辑来看,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终结资本的历史使命:“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16]这样就从根本上消解了导致资本主义时代双重虚无的“罪魁祸首”。
其次,从个人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个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17]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人的内在世界能够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且内在世界的价值通过“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在外在人化世界中得到证明与体现;同时,作为人的对象化本质与能力的体现,人的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劳动产品等现实的“社会财富”,也成为证伪外在人化世界的虚无化的有力证据。这就使人的内在本质与对象化力量及其产品达致统一,从而避免了人的内在本质的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
最后,从社会性质来看,“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之中,塑造外在人化世界虚无的资本逻辑消解了,冲击内在精神生活的物化生存消逝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人化世界实现了和谐统一,既抵制了外在人化世界的虚无,也克服了内在精神世界的空虚。
在当代中国,从物质贫穷时代走出来的人们,又盲目地陷入了过度满足物欲的时代潮流。占有物和消费物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是为了使用的需要而是为了攀比或炫耀的需要,不注重物的使用价值而注重物的交换价值,甚至把对物的需要扭变为受广告操纵的对符号的需要,就成了需要深刻反思的文化现象了。与“物欲横流”相辅相成的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双重危机:一方面,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文明荡涤了一切陈旧价值体系,传统价值陷入严重的认同危机,而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尚未真正落实,转型期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分化趋势,所以遭遇着历史性的“价值真空”;另一方面,在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冲击下,重占有的物化生存方式取得压倒性优势,标志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的精神生活处于严重的压抑与忽视之中,所以遭遇着主导性的“精神虚无”。
对于当代中国虚无问题的解释,只有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结构框架内进行宏观把握与系统分析,才能找到虚无的内因及其本质,这就无法绕过马克思对于虚无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对此,伯曼有深刻的认识:“晚近的一代人会用‘虚无主义’予以命名的那些无法无天、无法衡量、爆炸性的冲动——尼采和他的追随者会将那种冲动归因于如上帝之死的那种宇宙性创伤——被马克思放到了市场经济的表面上看来平常乏味的日常运作之中。他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是一些技艺高超的虚无主义者,其程度远远超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想象能力。这些资产阶级已经是自己的创造性异化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去考察他们的创造性所开辟的道德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深渊”,因此,“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虚无主义力量,马克思的理解要比尼采深刻得多”。[19]显然,也要比海德格尔深刻得多。马克思正是从社会存在出发,超越了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其他理论家的思辨路向,把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求放置在客观的历史性维度之上,找到了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的社会形态作为抵制资本主义时代虚无侵袭的良方。马克思为彻底破解虚无主义开辟的这条路径,散发着永恒的理论魅力,对于破解在一定意义上存在于当代中国的“物欲横流”“价值真空”“精神虚无”等文化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1]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0、732页。
[2]尼采:《权力意志》,第731页。
[3]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资本逻辑塑造的外在人化世界的虚无”,并不是说整个外在人化世界陷入虚无的境地,而主要是指在资本及其强大力量的耀眼光辉下,其它诸种事物及其关系黯淡无光,相对弱化甚至被虚无化。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40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0-321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8-89页。
[15]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何兆武、何冰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2003年,第140-14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19]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9、144页。
[20]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70页。
责任编辑 顾伟伟
B516
A
1006-0138(2016)01-0020-05
王海滨,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北京市,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