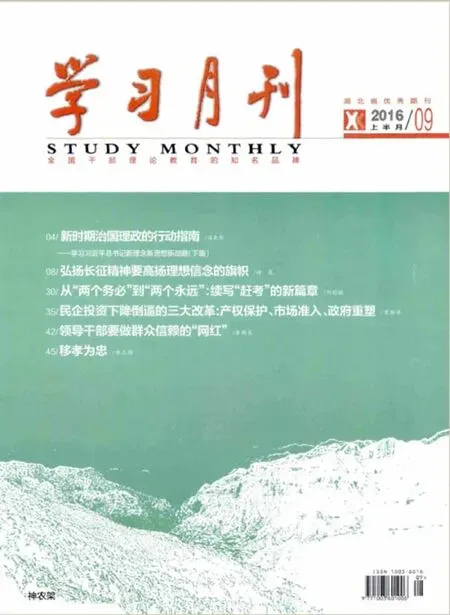移孝为忠
2016-02-28
忠是重要的政治伦理和社会规范。忠与孝相结合,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文化的基石,成为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忠,表达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挚情感,其行为指向是舍己,即要求人们为忠诚对象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那么,忠的内涵和本质究竟是什么?这需要先弄清楚忠德是怎么产生的,亦即它与另一极为重要的德目——孝的关系。“忠”先是寓于孝,然后又独立于孝,或叫移孝作忠。
忠与孝,是中国古代两个最普遍的行为概念,亦是中国人两种最基本的道德义务。程颢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五)朱熹也强调:“君臣父子之大伦,天之经,地之义,而所谓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则教养之,没则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诚者,无所不用其极而非虚加之也。”(《朱熹集·戊午傥议序》卷七十五)简单点说,儒家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来探究忠和孝的。人是父母所生,必须“善事父母”,其自然属性决定人必须守孝,人又是相持相待,相互支撑的,必须“尽己利人”,其社会属性决定人必须尽忠。正如《孝经》开篇所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可以说,人区别于动物既是因为其有“恻隐之心”,更是因为人具有忠孝的行为。而且忠孝行为不可分割,也就是通常说的“忠孝一体”。
忠孝一体是我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社会结构的集中体现。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行孝尽忠往往具有同一性,因为两者都是指行为主体“尽心尽力”地做人做事。尽心尽力地善事父母是孝,而尽己利人的行为本身也就是忠,是忠德的体现。《礼记》说:“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论语·为政》)这种推己及人的孝,离开家庭走向社会就会变成忠。《战国策·赵策》说:“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吕氏春秋》也说:“人臣孝,则事君忠”,“事君不忠,非孝也”(《礼记·祭义》)。正因为尽孝与尽忠在实践上具有一致性,所以古代在选拔官吏的时候,往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所以东汉韦彪说:“夫国以贤为务,贤以孝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忠孝之人,持心近厚”。(《后汉书》卷二十六)这是典型的忠孝同一观点。传统社会法律体系中有“十恶不赦”之罪,包括谋反、恶逆、不道等,其中“不孝”、“不忠”都在其列。”“十恶不赦”罪的伦理基础就是忠与孝。
同时,由于忠孝一体,不孝就暗含不忠,反之亦然。所以《孝经》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荀子曾经把孝分为三个层次:小行、中行和大行。“人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这样的行孝才是合理的德性,而这种孝的德性本身就是一种忠的行为。
上述我们说忠孝一体是从其基本精神和实践行为的同一性而说的,并不是说忠的道德概念与孝的道德概念是同时产生的。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孝的道德观念,而忠的道德观念起初是寓于孝德之中。忠德是在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产生的,准确的说是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形势下被“移孝为忠”的。认识这一点对于认识忠的本质和内涵很重要。
西周时期,孝与德并称是西周国家宗教与伦理政治的基础。孝不仅是维系家庭伦理关系的主要道德规范,而且也是调节政治伦理秩序的道德纲领。这是宗法分封制的社会结构决定的。
与古希腊那些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城邦国家不同,中国进人阶级社会时,建立的是以氏族(宗族)为基本单位的部落联合体国家。著名历史学家张光年先生就认为,在这样的宗法制国家里,“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中国青铜时代》)嫡长制和分封制促成了这种结合。
据《史记》的夏、殷、周本纪载,三代都是“用国为姓”进行分封的宗法社会。而宗法制的基础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分封制,而且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西周一开始就确定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嫡长子继承制,天子按嫡长子继承制世代相传,是天子“大宗”。其他不能继承王位的庶子、次子也是按照分封制,被分封为诸侯,是从属“大宗”的“小宗”,分封的地域就成了诸侯国。这些诸侯也是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对于这些卿大夫来说又是“大宗”,依此类推。大夫以下又有“士”,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不再分封。在这样的情形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全国形成了以天子为根基的系统而完整的宗法制度。
在这种封建宗法制度下,政治与伦理、血缘与政权紧密结合,天子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兼具孝子、宗子、天子三重身份,小宗对大宗的孝,就是诸侯对天子、臣民对诸侯、下级对上级的忠。由于亲缘与政权的结合,这时还没有出现超越伦理范畴的单纯的政治行为,下对上的忠诚情感就通过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忠观念包含在孝之中,孝观念将宗教意义、伦理意义与政治意义集中到了一起。比如周人的追孝祖先活动,既是一种慎终追远的孝行,更是一种维系宗法统治的手段,通过借助祖先来凝聚家族、巩固王权,即以孝来维系宗族的团结,保证诸侯、公卿、大夫以及庶民对周王及其上级的忠诚,维护政权的稳定。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说:“‘庶人’之孝固以孝事父母为主,然贵族之‘孝’则最重要者为‘尊祖敬宗’、‘保族宜家’,仅孝事父母,则不以为大孝。”(《春秋左传研究》)君臣上下关系体现为宗族上下关系,宗族关系统帅着君臣关系,诸侯对祖先的尊敬,既是对逝者的缅怀,也是对天子的服膺。孝既是宗法伦理,也是政治伦理,孝在维护宗法政权稳定的同时,也维护了统治阶级内部秩序。这就是“寓忠于孝”,忠被包含在孝之中,并通过孝表达出来。
孝的观念已在三代时占据宗法和政治伦理的支配地位,而忠的观念是在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凸现出来的。因为这时,宗法制度渐趋瓦解,社会阶级阶层上下易位,旧的道德规范已无法调节新的社会,特别是政治生活。家国分离呼唤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的政治伦理关系,“忠”这个道德范畴就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出现了,并逐渐成为人们普遍遵从的社会和政治道德。
春秋时期,以平王东迁为标志,中国逐渐进人了封建社会。随后100多年,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革。其中,经济上以土地私有制代替井田制,政治上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由于“两制”的出现,导致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颠覆性变化,经济上,私田出现,地主阶级产生了,随之井田制跟着瓦解,奴隶也从“井田”中解放出来,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形成。同时,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秦、楚、晋等国相继设置郡县,郡县由国君直接控制,这就等于取消了分封采邑的世卿世禄制,血缘关系已不再是唯一的政治控制手段。政治上,因天子大权旁落,其政治共主地位已名存实亡,诸侯逐鹿,五霸迭兴,王纲解纽,人心紊乱。各国霸主均以共主自称,挟天子以令诸侯,昔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霸主取代了共主,霸权取代了王权。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景象:“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背叛,莫修贡聘,奉献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杀其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不能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总之,这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社会。
由于“礼崩乐坏”、社会大乱,宗法分封制度瓦解,政治共主名存实亡,使得孝观念随之失去了昔日控制诸侯和小宗的效能;以孝为基础的宗法道德的式微,使君权观念与君臣意识也随之大大削弱,诸侯对天子的效忠之心日益淡漠,宗子之亲、君臣之义的宗法政治秩序荡然无存。随着孝这一宗法政治伦理基础的摧毁,社会道德、政治道德也陷人混乱,道德重建成为社会和政治秩序重建的当务之急和重要内容。忠君利人的忠德呼之欲出,忠德从孝德中剥离出来,“移孝为忠”成为历史的必然。
我们说忠德剥离,移孝为忠成为必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阶级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宗法分封制的瓦解,诸侯国经济、政治势力日渐强大,天子与诸侯、卿大夫血缘关系愈发松弛和疏远,新型地主、手工业者、商人等社会阶层也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从奴隶转变而来的农民也有了自己的独立利益,形成了“上下交争利”之势,这种变化引起了公共政治领域与家庭私域的分离,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道德来加以平衡。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下,家国一体、世卿世禄是其典型特点,这种制度使公共政治领域与家庭私域之间的利益紧密连结,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在宗法分封制解体、家国分离的过程中,基于血缘的世卿世禄官僚制度,被非血缘的官僚雇佣制度所代替。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使家国分离,形成君国的公共政治领域与新兴阶级的家庭私域并存的社会结构。当公共领域与家庭私域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在道德生活领域就表现出了忠与孝的冲突。因为忠德与孝德所针对的是不同的伦理主体,调节的是不同领域的伦理关系,忠对君、国,孝对父、家,当二者利益发生冲突,就需要在发挥孝德作用的同时,突出忠德的作用。这样一个充满着痛苦与希望,蕴含着极大创造力的历史场景,催生了体现新的政治规则的崭新观念——忠。事实也正是如此,金文最早的忠字,就是见之于战国中期中山国的青铜器上,上面明确记载“竭智尽忠”等铭文,表现了臣忠于君的政治品德。
忠德就这样从“寓忠于孝”被历史地“移孝为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