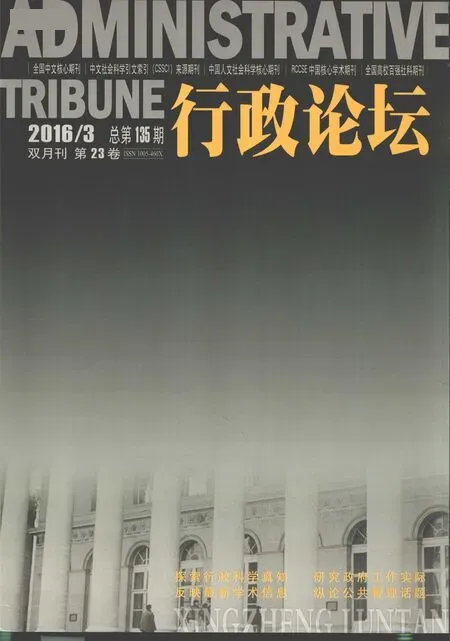风险社会、治理有效性与整体治理观
2016-02-27杨雪冬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北京100032
◎杨雪冬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北京100032)
风险社会、治理有效性与整体治理观
◎杨雪冬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北京100032)
制度既是对风险的系统性回应,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制度面临着普遍性治理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治理问题的凸显,在知识界和实践界中出现了从关注制度现代性到重视治理有效性的转向,治理结果有效性优先于制度形式的合法性。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应该树立整体治理观,并重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改革。
风险社会;制度现代性;治理有效性;整体治理观;国家治理改革
近年来,制度的重要性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达伦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著)和《政治秩序的起源》(福山著)为代表的学术畅销书的流行,就说明了这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讨论是在治理这个新的范式进入多个社会科学领域背景下发生的。治理作为描绘制度运行的过程形态和体现制度绩效的整体形式,为认识制度的重要性提供了系统化的视角。进一步说,这次讨论也是在全球风险社会成为社会认知前提的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何种制度,哪种治理模式,都需要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风险,这是对它们综合能力的检验。全球交往的深入,还为不同类型制度和治理模式提供了相互比较、交流学习的更多机会和渠道。
本文将从风险社会角度讨论全球性的治理危机发生的原因,分析制度现代性虽然解决了制度形式的合法性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制度有效性这个更根本性问题,而在风险社会中,制度有效性是一种系统性综合能力,也是制度合法性的更有力支撑。最后提出要从国家治理改革出发,建构整体治理观,来提升制度的综合效力。
一、风险社会与治理危机
风险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人类干预外部环境能力和行为自主性的提高,各种形式的人为风险大量出现,不但与自然风险交织在一起,而且产生的后果更难以预料。因此,以乌利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社会理论家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用以描述和分析人为风险的社会政治后果。
在他们看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和强度的提高,风险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风险,还出现了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生态风险、生活风险等多种类型风险。这些风险按照其影响对象又可以划分为个体风险、组织风险、国家风险、社会风险、跨国风险以及全球风险等。诸多人为风险的出现,使得风险社会成为可能。
就风险社会概念而言,它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处于风险社会时代,但不能讲某个国家是风险社会,尽管那个国家的国内情况比其他国家更不安全。进一步说,风险社会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概念,还是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1]。
从风险的角度而言,制度和治理是人类辨别风险、分担风险、应对风险的稳定化行为模式。在不同的环境下,针对不同的风险,会形成不同的制度形态和治理模式。罗斯与米勒认为治理有多种形式,从个人的“自助”到人寿保险再到国家政策都属于治理的方式[2]。在风险社会中,现有的各类制度和治理模式都遇到了挑战。
首先,风险社会凸显了现代制度的内在限度。贝克等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尽管人类物质生存条件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面临着新出现的技术性风险,比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这些风险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与方法:风险计算或计算理性。这体现在四个方面:(1)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此,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2)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3)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3]。
其次,风险社会提醒制度也是风险来源。任何一种制度或者治理模式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深受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的限制,并且针对的是当时的具体问题。尽管它们在运行过程中,得到社会成员的承认、遵循、信奉,由此形成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增强关系,得以延续并保持生命力。但是,制度不是万能的、永存的,也会成为风险的来源。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即现代性制度与其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们对安全和威胁的认识和理解的变化;团体和社会的意义之源的弱化,由此造成了制度与外部条件和环境的脱节[4]。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诱发核大战的爆发[5]。
最后,全球性风险挑战着现有制度应对的能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全球性风险出现了,一些地域性风险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吉登斯认为,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5]4。“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6]。贝克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出了“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7]。他认为,有三类危机是可以确认的,即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所带来的危险。这些全球风险有两个特征:一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在原则上都可能受到它们的影响或冲击;二是应对和解决它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全球性风险是在政治层面爆发的,它们不一定取决于事故和灾难发生的地点,而是取决于政治决策、官僚机构以及大众传媒等。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各类风险冲击着各国治理体系以及国际治理体制,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步积累为全球范围的治理危机。治理危机首先是在西方国家,从环境治理领域开始的。工业化造成的环境问题,大国之间核武器的竞争,加之社会成员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保护运动在西方许多国家兴起,不但对现代生产制度,国家政策进行了激烈批判,而且产生出以绿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改变了多个国家的政党格局。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资本的跨国流动加快,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面临财政资源难以为继的困境。福利制度本来是作为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协调国家—资本—劳工三者关系设计,现在必须打破原有的均衡,重新分配风险的承担比例与方式,国家遭遇了合法性危机[8]。而同时期的前苏东国家也开始感受到制度风险的冲击。官僚体制的僵化,经济运行的低效率,无法有效回应社会公众的需求,体制的合法性也受到巨大冲击。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看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国家都在热衷于改革。双方的区别在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国家侧重的是“公开化”的政治改革,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国家选择的是“自由化”的经济改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市场改革处方变成了“万能良药”,各国都在积极推行解除管制、缩减政府开支、控制国家规模等方面的结构性调整。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社会差距的拉大。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大大加强,全球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全球金融风险开始酝酿,最终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呈现出来。市场风险与国家防范风险能力之间的差距,得到了各界重视,提高国家能力比缩减国家职能更为重要[9]。
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有人将其称为“第三波全球化”[10]。一方面,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进程;另一方面,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复杂,为风险的转移扩散传播提供了更为多样便利的渠道。有三类风险尤其突出:第一类是以全球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全球风险,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个体国家或单一国际组织的应对能力。第二类是“国家缺失”产生的制度性风险,造成了权力真空,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在美国占领后的阿富汗、伊拉克、“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国家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凸显了国家作为风险应对基本单位的重要性。第三类是互联网导致的衍生风险。互联网的发展,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生活,也为风险的衍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提高了风险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降低了风险转变为现实威胁的成本。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通过互联网宣传自己,招募成员,组织资源,协调行动,就说明了这点。
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显示了西方治理模式陷入危机。这场危机首先在被认为制度完善成熟的美国爆发,然后蔓延到欧洲,最后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卷入其中,并且影响至今。库普钱认为,目前西方世界出现了治理危机,原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已经使这些国家的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失灵;二是西方国家民众要求政策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三是国内社会公众情绪低落并且分裂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竞争以及制度制衡[11]。福山进一步批评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政治衰颓趋势。受国内利益集团的干扰、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许多关系到未来以及更多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无法做出,形成了一种“否决体制”(Vetocracy)。①福山认为,美国政治中的三个主要结构性特征现在都出现了问题:司法和立法部门影响力过大,导致行政成本增加,效率低下;利益集团影响力在增强,扭曲了民主进程,侵蚀了政府有效运行的能力;联邦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两党之间缺乏共识,导致重大决策无法做出(Francis Fukuyam.“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American Interest,December 11,2013)。
二、制度现代性与治理有效性
制度是对风险的自觉应对,现代制度尤其体现了这种自觉性。现代制度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建起来的。一方面,国家作为暴力工具的合法垄断者,是诸多制度的创制者、确认者、维护者甚至否决者;另一方面,国家又为许多制度的实施划定了地理边界或者对象界限。正是由于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最突出的“权力集装器”的存在[12]145,才能推动各项现代制度从现代化的先行国家向后发国家扩散,从而实现了制度现代性的普遍化。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综合性现代制度形式,首先经历了从西欧向世界范围的扩散。列宁曾经说过:“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13]在吉登斯看来,从19世纪初以来至今,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世界范围不可抗拒的政治形式[12]305。除了在西欧出现的第一批民族国家,其他民族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方式实现。在独立的过程中,民族和领土重新结合,新的认同和情感被塑造出来,既划分了许多民族活动和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也为现代制度设定了运行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而这也是各国制度运行绩效产生差别的基本原因。
从20世纪初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族运动成为欧洲、亚洲和非洲许多社会变革的核心主题,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普遍趋势和共同目标。亚洲的民族运动从20世纪初开始,非洲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亚洲比欧洲晚了100年,非洲比亚洲晚了50年[1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了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等三个老帝国的快速瓦解,使30多个国家依次获得了独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和亚洲新建了10个民族国家,二战结束后到1959年,新建了19个民族国家,20世纪60年代新建了38个国家,1970—1990年新建了15个[15]。就世界范围来看,到1993年,共有183个国家[16]。而目前,世界上共有193个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
对于这些独立后的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国家成为整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尽管对于“现代化”的特征有不同理解,但是“现代国家的所有这些特征都源自于西方,无一例外”[17]。西方模式自然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芬纳归纳说,西方国家有六个基本特征:作为疆域组织基础的民族性原则;作为所有政治权威合法化基础的人民主权原则;世俗原则;社会的目的性;经济独立原则;公民权的概念。这些现代特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以不同形式的制度呈现。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模仿或者移植这些现代制度上,以为这些制度是西方国家取得发展成功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出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制度性竞争的局面,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采取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或者根据本国国情建立了自己的制度。尽管这些国家采取了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形式,尤其是信奉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模式有着本质差别,但是并没有放弃基本的现代性制度原则,比如人民主权、世俗原则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探索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制度现代性。尽管如此,大部分后发国家追随的还是西方制度模式。
就具体制度而言,并非每一项现代制度都是由英美国家创制的,也非同步在西方国家出现的,而是逐步扩散的。张夏准分析了现在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的多项制度,指出任何一项制度的普遍实施,都是一个历史过程。例如,成年男子普选1848年首先在法国实行,美国1870年实行,英国1918年实行。全面普选1907年首先在新西兰实行,英国1928年实行,美国1965年实行。中央银行制度1688年首先在瑞典建立,美国在1913年建立。工伤医疗制度1871年在德国首次实行,英国1897年实行,美国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于1930年,没有医疗制度[18]130-131。而这些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组合形式,产生了多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也出现了不同的制度绩效[19]。这说明,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制度现代性也不是单一形式的,而是多样的。
对于许多后发国家来说,这些现代制度都是外来的,如何适应本土环境,发挥制度效力,成为普遍性问题。虽然能够在短时期内建立现代式样的制度,但取得充分的制度绩效并不容易。这尤其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因为政治制度的持续有效运行不是由某种现代观念或者政治人物的个人意志决定的,更多地取决于其对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和对社会政治力量关系的调节。以非洲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为例,虽然殖民统治时期,为非洲国家划定了国家边界,确定了国内主体民族,建立了正式的官僚体系架构,实现了更高程度的权力集中,使这些国家有了“现代国家”的制度模样,但是这些现代性制度与非洲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之间并不兼容,因此,政治现代化很难利用非洲本土的制度与文化资源。①参见阎健撰写的《本土社会与外来国家:非洲国家构建的社会逻辑》一文,属未刊稿。
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围绕选举进行的民主化又摆在突出位置。按照西方的理论或者经验,这是赋予政权合法性的现代方式。由此,推进民主化成为许多后发国家现代制度建设的主题,也是国际组织援助的重点。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第三波民主化,席卷全球,并将社会主义国家卷入其中,实现了更重大的制度转轨[20]。
事实表明,将制度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将政治制度现代化等同于民主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片面和误导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第三波民主化的回潮,“阿拉伯之春”后产生的地区性动荡,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问题的凸显,政治运行的停滞,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对西方模式的盲目追捧[21],在福山看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难以实现西方自由民主的现代性”[22]。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制度现代性的认识更为深刻:各国制度不仅要具有现代的形式、要素和结构,更要能解决多样的问题,应对复合的风险的能力;不仅要能回应和满足民众的当下要求,更要能做出长远规划,生产政治信任,达成共同应对风险的集体行动。治理的有效性比制度现代性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
世界银行1989年发表的《南撒哈拉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的报告首次提出治理概念,用于分析和解释这一地区经济成功国家的核心概念和原因。此后,治理理念陆续被主要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政府接受,用来理解和分析在解决具体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变说明,对于发展的认识正在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市场机制转到政治行政领域,更重视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所需要的国内制度环境。而治理作为一种知识和行动框架,也能将正在兴起的非政府组织纳入其中[23]。
目前,对治理有效性的研究散布在多个学科中,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改革实践之中。这表明,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新变化、各类新风险,研究者和决策者的问题意识正在淡化抽象的价值关怀,对治理结果有效性的关注也在超越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在理论研究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治理有效性实现有多种途径。一方面,西方国家固然已经建立起一套由多种制度要素构成的治理体系,并且取得了明显的发展成就,但是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也没有普遍的证据证明,某一套制度比其他制度更有效率[24]232。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都陷入了治理困境,不再是各国学习的楷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发现“治理失效”(Bad Governance)不仅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之中[25]。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发展成就。中国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外交政策方面的,更是发展模式意义上[26]。“中国的崛起”说明,全球化为后发国家动员本土制度上的比较优势提供了新的机会,那就是要提高以国家为单位的整体效率。中国与美国相比,决策效率更高,动员社会能力更强。对治理有效性的关注也推动着西方学者重新反思“转型范式”[27]“第三波民主”“威权主义”等用来划分、评价不同制度类型的理论范式或者流行概念。
第二,民主选举只是实现良好治理的要素之一。选举民主往往被视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因素,民主化被等同于举行自由选举。据统计,世界上的采取选举民主制度的国家从1970年的35个增加到2014年的110个,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举行民主选举比其他制度建设更容易做到[28]。但是民主选举与治理之间并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民主选举并不能自动带来良好的治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还会造成治理混乱,导致民主化倒退。一些热衷于民主化的西方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意识到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的差别[29],林茨和斯替潘指出,光有选举制度不一定就有高质量的民主,也不一定就能造就一个高质量的社会[30]。随着第三波民主化的回潮,越来越多的批评集中在选举之后出现的破坏法治、政府腐败、缺乏问责等治理问题上。有学者指出,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是一种反方向的民主化,因为这些国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现代国家制度,就开始实行自由选举,结果就陷入了既要实现制度化,又要确保自由选举公正的双重困境[31]。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组织开发了多种测量治理质量的指标体系,而民主选举只是其中的指标之一。①有关评论可参见:Christian Arndt and Charles Oman,Uses and Abuses of Governance Indicators,国内中译本书名《政府治理指标》,杨永恒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第三,国家制度建设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础。从理念上说,治理是多主体参与的,国家只是主体之一。但是,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国家又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方面,绝大部分治理活动都是在国家边界内发生的;另一方面,国家是基本政治秩序的提供者和维护者。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既不是“守夜人”,也不是“全能者”,而是在多种要求和约束条件进行理性选择,甚至主动变革的能动者。有学者就归纳了国家多个新角色,比如,“管制国家”(RegulatoryState)“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裁决型国家”(Adjudicatory State)“道德倡导型国家”(Moral Advocacy State)[32]。因此,在福山提出的政治秩序的三要素中,国家位列首位[33]。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府质量”“善治”“国家能力”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国家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25]。
国家制度建设不仅包括军队警察体制、文官体制、司法体制、税收体制等一系列现代国家运行必需的制度性因素,还包括提高国家的能力。国家制度建设要重视时序性和配套性。不可能把所有制度一天内建成,应该分出主次,有所侧重,实现暴力垄断的制度应该优先建立。国家制度的配套性不仅体现在制度的完备性,还要重视制度与政治领导人的关系,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重视国家制度建设,就必须打破自由主义“最小国家”的思维定式,将国家制度与社会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结合在一起,更要增强国家能力,发挥国家的适当作用。越来越多的案例说明,国家软弱无能,甚至政府虚置,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发展的根源之一,也是许多民主化国家政治失序的原因。
第四,现代制度也存在失效的可能。尽管制度化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条件,但是制度也存在失效的可能性。一种可能通常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它们主动或者被动地移植了一些西方国家创制的现代制度,但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制度有效运行所需要的条件。张夏准认为,发展中国家正承受来自发达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发展政策机构的巨大压力,要求采取一系列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来促进经济发展。“好政策”往往是被“华盛顿共识”一致认可的政策,“好制度”指的是被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采取的制度。但是,“很多现在认为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其实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经济发展的原因”[18]11。因此,发展中国家要么必须为这些制度运行创造条件,破坏既有的社会环境,造成社会矛盾和动荡,要么必须依靠外部资源来分担制度运行的成本,导致对外部的过度依赖。另一种可能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即制度功能衰退。福山在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衰败”概念。他认为这种“反制度化”的产生,是因为制度成立的原始条件发生了变化,制度却不能随机应变[33]443。在他看来,导致制度功能衰退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观念的僵化,二是既得利益格局。美国目前就面临着制度衰退的危险。第三种可能是面对跨国界的风险,以国家为单位的制度存在内在缺陷。面对跨国风险,许多国家常常缺乏足够的资源、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及应有的合作文化习惯。依托属地管辖、部门负责的科层制治理方式就会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问题[34],虽然在形式上每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都有明确的责任范围,但是一旦出现难以明确责任的问题,就容易相互推诿。
从制度现代性到治理有效性,既是一次知识性转变,也是一场实践变革。这双重转变是在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发生的。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新变化和各类新的风险,意识形态偏见、理想模式期待以及各种“中心主义”的傲慢,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风险的应对。应该客观分析时代发生的新变化,认真反思现代性制度的缺陷,挖掘和发扬各国内在的治理优势,这样才能在有效治理过程中追求共识性价值。
三、简要结论:走向整体治理
我们正处于深刻变革的时代,治理的有效性更为凸显。一方面,不同的制度体系都面临着如何应对和化解分布在各个领域的各类风险,为民众提供安全感更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全球化为不同制度体系展示各自的治理绩效提供了平台,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格局。因此,治理的有效性在塑造各个制度体系合法性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亨廷顿早就断言:“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35]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是否增进人们的团结,改善人们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36]。
尽管我们面临的问题复杂多样,但是已经形成了复合治理的格局。一方面,出现了多元的治理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等在内的各类行为体参与到应对风险的治理过程中。实现良好治理成为基本共识,现代性制度和理念成为全球主流。另一方面,治理又是在多层次和多领域进行的。从纵向看,从村庄、部落到地方、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层次,都出现了不同的治理机制;从横向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在发生着治理活动。多层次多领域治理的发生,说明了治理问题的严峻,也显示出治理主体的回应性和责任感。
在复合治理格局下,有效治理的实现不仅要发挥各个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更要追求治理的整体性,实现整体绩效[37]。因为多样的治理主体更需要达成合作,复杂的治理关系更需要协调。
整体治理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共生共存原则。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共同的风险,不同群体之间,以及他们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共生共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成员,也是许多边界重叠、规模不等共同体的成员。不同规模的治理必须追求共生共存的理念。二是统一与自主原则。在解决影响范围跨层次的治理问题时,层级更高的治理主体拥有日程设置权,层级越低的治理主体拥有问题处置权。换句话说,当一个治理问题涉及多个治理主体的时候,层级更高的主体应该发挥规划协调的作用,层级越低的主体要有解决问题的自主性。三是现代性治理原则。民主、法治、透明、廉洁、效率等现代性价值已经被普遍接受。相关主体、相关行为要按照这些价值的要求调整行为,自我改革,形成治理合力,才能在整个治理体系框架内协同运行,确保实现整个治理体系的治理效果。
在民族国家依然是治理主权单位的前提下,追求整体治理首先要从改革国内治理结构、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开始。国内治理的改进是实现整体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大部分的治理活动都是在国家内部展开的,各类国际合作也是以国家为首要主体实施的。实现有效的国内治理,既提高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也会控制许多问题的跨国蔓延,促进了更高层次的整体治理。尽管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各自的问题,但是有两个基本任务是共同的:实现国家制度现代化,提高国家职能部门和官员能力,以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打破国内地区性、行业性、部门性以及阶层性既得利益格局,增强全社会的活力和参与能力,以有效制约和协同国家权力行使。
其次,要重视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全球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38],而不能与国际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就无法真正实现国内的良好治理,更不能推动更大范围的良好治理。由于各国的全球化水平和全球性影响存在差别,所以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全球治理互动在领域、方式、机制、程度等方面也不相同。尤其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内治理能力不足,很容易受到国际变动的冲击,引发国内问题,甚至动荡,因此,这些国家要平衡好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国家主权原则应该成为平衡这些关系的重要保障。
再次,要注重将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化是整体治理无法回避的前提。多元化意味着差异化也会导致矛盾和冲突。全球化带来的悖论性现实就是,一方面,人们的交往在扩展和深化,共同性在增多;另一方面,经济收入的差距在拉大,认同在分化。这种情况既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国家内部。整体治理并不回避这个现实,而是要从问题解决入手,通过提高治理效果增加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结合点,扩大共同利益的覆盖范围,提升共同价值的接受程度,以利益引导行动,用价值维护合作。
最后,要发挥国家的预防和引领功能。大量事实说明,国家既没有“终结”,也没有被“掏空”,而是在职能上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国家的职能早已经突破了“守夜人”的最小范围,渗透到各个领域的治理过程之中。同时国家也不可能是全能的,有着活动的边界和能力的限度。许多研究发现,全球化并没有弱化国家,而是要求国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一个社会的政治和制度的稳定对于该社会经济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24]58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国家应该重点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种是预防风险的功能。国家虽然不是风险应对的唯一主体,但是拥有公共权威的地位,可以发挥提供制度,加强培训,推动合作的作用,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另一种是创新引领的功能。应对各类风险必须进行创新。尽管市场、社会具有各自的创新优势,但存在短期性、无序化问题。国家可以通过长期规划、集中资源等方式,克服外部不经济,推动关键领域、关键问题上的创新以及创新成果的普及,提高创新的社会效应。
[1]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9.
[2]ROSE N,MILLER P.Political Power beyond the State:Problematics of Government[J].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92,43(2):171-205.
[3]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J].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26-45.
[4]BECK U.Risk Society[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M].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J].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2):70-83.
[8]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4.
[9]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0.
[10]STRAW W,GLENNIE A.The Third Wave of Globalisation[R].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Report,2012.
[11]KUPCHAN C A.The Democratic Malaise,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J].Foreign Affairs,2012,(January/February):62-67.
[12]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1.
[1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M].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151.
[15]宁骚.民族与国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02.
[16]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文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6.
[17]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三[M].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51.
[18]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肖炼,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9]HALL P A,SOSKICE D W.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M].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0]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1]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EB/OL].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
[22]FUKUYAMA F.The Imperative of State-building[J].Journal of Democracy,2004,15(2):17-31.
[23]WEISS T G.Governance,Good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Conceptual and Actual Challenges[J].Third World Quarterly,2000,21(5):795-814.
[24]弗雷格斯坦.市场的结构: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M].甄志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5]SMITH B C.Good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26]FUKUYAMA F.The Patterns of History[J].Journal of Democracy,2012,23(1):14-26.
[27]DIAMOND L,FUKUYAMA F,HOROWITZ D L,PLATTNER M F.Reconsidering Transition Paradigm[J].Journal of Democracy,2014,25(1):86-100.
[28]FUKUYAMA F.Why is Democracy Performing so Poorly[J].Journal of Democracy,2015,26(1):11-20.
[29]DIAMOND L.Developing Democracy:Toward Consolidation[M].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10.
[30]LINZ J J,STEPAN A C.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Communist Europe[M].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30.
[31]ROSE R,SHIN D C.反向的民主化:第三波民主的问题[J].王正绪,译.开放时代,2007,(3):95-114.
[32]HARDIMAN N,SCOTT.Governance as Polity: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the Evolution of State Functions[EB/ OL].Public Administration,Online publication December,2009.
[33]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4]BECK U.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Rethinking Modernity in the Global Social Order[M].Translated by Mark Ritter.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7.
[35]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3.
[37]PERRI 6 D L.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M].New York:Palgrave,2002:13.
[38]CEMY P G.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5,49(4):595-625.
(责任编辑:于健慧)
D0
A
1005-460X(2016)03-0001-07
2016-02-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机理研究”(12B22039)
杨雪冬(1970—),男,河北涞源人,主任,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当代中国政治与地方治理等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