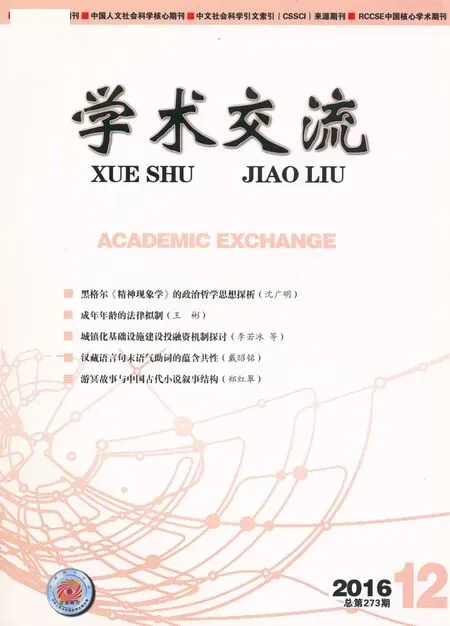游冥故事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结构
2016-02-27郑红翠
郑红翠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报社科版,哈尔滨 150001)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小说研究专题·
游冥故事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结构
郑红翠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报社科版,哈尔滨 150001)
游冥故事是中国叙事文学中一个独立的故事类型,故事的基本结构相同,体现为因果相属的以环形结构为基础的连环套式结构。这种结构形态为中国小说家们所承继和借鉴,对中国小说叙事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游冥故事的“冥判”环节是冥界游历的重要环节。“冥判”被嫁接入小说的结构设置中,使人物的“生命”延长,以完成对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报应式的解说,并融进作者的善恶忠奸观念。为实现小说的创作宗旨、完成小说的功能起了结构小说框架、统驭全篇的作用。
游冥故事;地狱;冥判;小说结构
“叙事”就是讲故事。叙事过程关涉到三点:记述活动者即叙事人;记述活动即叙述行为;故事或事件本身的特点即所叙之事。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是构成小说叙事模式的三大要素。[1]叙事视角、叙事结构本身就是叙事的主体,如何编织故事就是叙事的主要任务。游冥故事要达到劝教劝善目的,在叙述策略上,就必须考虑如何才能使虚构的故事变得真实可信。游冥故事无论在叙事时间、叙事视角还是叙事结构方面,都是为使叙事达到“真实可信”目的。本文主要分析游冥故事的叙事结构,并试图勾勒游冥故事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一、因果相属的连环套式结构形态
关于游冥故事的结构形态,有学者提出了游冥故事“暂死入冥——接受冥判——游历地狱——复生”这一结构框架,这是游冥故事的基本框架,还可以更为深入地研究。在这一框架基础上,本文力图对游冥故事的结构形态作全面立体透视,以还原游冥故事的结构形态。结构是一种功能框架,是组成作品的脉络和纹理,是作者对小说情节在发展过程中所实施的一种艺术处理。通过结构,原本处于自在状态的故事被编织整理成一系列情节。在情节运动变化的链条中,作品结构内部常常呈现出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相互交融的状态。
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有很多共同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中国古代小说一般结构完整,开头结尾,前因后果,构架结构清楚严密,并且多数都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观念及佛教因果业报观念对中国小说这种大团圆结局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也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思维习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小说里,从整体来看,善恶交织、正邪两赋的复杂型人物性格并不多,多数人物性格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的矛盾,总会有某种偶然或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化解矛盾。结构完整、结局圆满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突出代表性特征。[2]
游冥故事在结构上的共同点非常明显,故事结构基本相同,情节模式相似。其结构特征表现为因果相属的连环套式结构形态,这种连环套式结构形态包含有两方面特点:一是以因果相属的环形结构为基础框架,二是环形结构基础之上的故事套故事的层级连环。
1.以因果相属的环形结构为基础框架
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小说在结构上因果完整。成熟的游冥故事发端于佛教地狱观念,其受佛经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多数学者认为,佛经文学在佛教因果观念支配下具有因果完整的叙事特点。佛经因果叙事的思维方式“给中国输入了叙事文学的结构和模式”[3]。
因果叙事的思维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小说的叙述特点。中国早期的小说主要记录街谈巷议的奇闻异事,缺乏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基本属“残丛小语”式的简单记录,严格说还不能算小说,只能算是“故事”。而“故事”与“情节”是有很大差别的。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而情节则“特别强调因果关系”[4]。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六朝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小说受佛教因果思维影响,人物的命运遭际作为组织情节、谋篇布局的发展线索,前因后果、兴衰际遇形成一个个因果链,实现了小说依从情节与人物行为的内在因果性叙述结构。
游冥故事受到佛教地狱观和因果观影响,因果叙事的思维模式贯穿于整个游冥故事的叙事之中。无论是相对复杂的游冥故事还是小说的游冥情节,因果叙事的思维模式始终潜藏于其中。游冥故事因果叙事的思维模式体现为因果相属的环形结构,依凭佛教因果观,来建构故事内在的逻辑秩序,叙事时空呈现“现实世界——幽冥世界——现实世界”的环形叙事结构,叙事上实现了由生入死、死而复生的循环,即“暂死”——“游冥”——“复生”这样一个简单的环形结构。
“暂死”——“游冥”——“复生”, 这是故事大的结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在“游冥”这一环节,可能会增加一些情节,穿插一些小故事,表现为“冥判”、“观狱”等。几乎每个游冥故事都是在这样的结构框架下展开情节的,如《报应录》“李质”(《太平广记》卷一一七)故事:
唐咸通中,吉州牙将李质,得疾将死忽梦入冥。见主吏曰:“尝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执簿书,以取上命。久之,出谓质曰:“事毕矣。”遂命使者领送还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质潜志其事,自是疾渐平愈,后果十四年而终。
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游冥故事,冥中经历部分并没有展开复杂的情节,没有游观地狱的内容,只有受审的简单情节,故事要传达的观念是善有善报。李质因疾而死,又因曾活人命而生,从现实世界到幽冥世界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后果,故事环形结构清晰,因果完整。
2.环形结构基础之上的层级连环套式结构
在很多游冥故事中,尤其是唐以后游冥故事,随着故事篇幅的加长、情节的曲折、冥界经历的丰富,故事的结构在环形结构基础上已开始分层叙述,出现了故事套故事的连环套式层级结构叙事。在多数游冥故事中,“暂死”——“游冥”——“复苏”是故事总的环形框架,是故事结构的第一层。在这个环形框架之下,“游冥”环节是游冥故事的主体,是故事结构的第二层。在这一层面,叙述死而复生之人的游冥经历,以主人公的冥界活动为线索,会串联起一系列看似不相干的小故事。在故事结构的第二层,主人公的冥界游历过程可能会经历多个“站点”,每一个“站点”还可能串联起新的小故事,新小故事的叙述就成为故事的第三层。这样以主人公为线索就形成了故事套故事、小故事套更小故事的连环套层级叙事结构。一般的游冥故事有两层叙述,部分篇幅较长的游冥故事达到了三层叙述。
在“游冥”这一层面包含冥界游历的多个环节,游冥之人可能会经历“入冥”——“冥判”——“阅簿”——“遇旧”——“观狱”——“索贿”多个环节。在这一层面上,除“入冥”外,顺序没有先后。有的冥界经历的环节可能多一些,有的则经过较少环节。多数游冥故事的冥界经历是“冥判”和“观狱”。
“入冥”是冥界之旅的第一程,《幽明录》“石长和”故事、《广异记》“程道惠”故事的入冥旅途就插入佛弟子与普通人的不同待遇。而多数冥界之旅的第一程非常简单,有的甚至直接进入冥界“中央机构”接受审判。“冥判”是冥界旅游的“重点站”,这是绝大多数游冥故事的主体部分。“冥判”这一环节,常常会串联起新的小故事。有时入冥之人会作为证人去见证审判,也会耳闻目睹一些新故事。《法苑珠林》“陈安居”(《太平广记》卷一一三)故事中,陈安居的冥界审判经历就非常复杂,陈在等待审判时,旁听了冥王主审的两宗案件,一件是一男子与女弟子成奸并弃妻娶女弟子之案,一件是一女因眠婴儿于灶上、婴儿粪污爨器被舅姑责骂事。这两个小故事与陈安居毫不相干,但通过陈安居的“旁听”被有机地串联起来,增加了故事的容量,强化了善恶报应观念。“观狱”也是游冥故事的主体部分,佛教地狱观念与因果报应观念通过对地狱的描写巧妙地传达出来。游冥之人在游历地狱时可能会遇见死去的亲人或故友正在地狱受苦,也会穿插这些亲朋故旧的小故事。有时“遇故”的地点并不在地狱中,“故人”还有可能担任冥府某职,因着这种“便利”便有了“请托”情节,也有可能串联起新的故事。有的游冥故事有“阅簿”环节,指查看簿书——富贵簿、善恶簿或寿算簿,在“阅簿”过程中可能会查看到自己或别人的某些不可泄露的“天机”,这就为串联起新故事增加了机会。“索贿”多发生在游冥之人返回阳间的途中,会有冥吏向其索贿,而游冥之人都会承诺满足冥吏的要求后被送回阳间。
以上是冥界游历的常见环节,这些环节串连搭建起游冥故事的层级连环套式结构。有的故事篇幅长,冥中经历复杂,环环相套,游历的“站点”多一些。有的则非常简单,但在简单的环节中有时也会出现故事套故事的情况,如《广异记》“阿六”(《太平广记》卷三八四):
饶州龙兴寺奴名阿六,宝应中死,随例见王。地下所由云:“汝命未尽,放还。”出门,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卖饼为业,亦于地下卖饼。见阿六欣喜,因问家人,并求寄书。久之,持一书谓阿六曰:“无可相赠,幸而达之。”言毕,堆落坑中,乃活。家人于手中得胡书,读云:“在地下常受诸罪,不得托生,可为造经相救。”词甚凄切。其家见书,造诸功德。奴梦胡云:“劳为送书得免诸苦。今已托生人间,故来奉谢,亦可为谢妻子。”言讫而去。
这是个最为简单的连环套结构。这个故事的第一个环形层面是阿六入冥因“命未尽”被放还死而复生的故事,阿六在冥界遇到了卖饼为业的“素相善胡”,引出了第二个故事,胡的故事是叙事结构的第二个环形层面。其实这个游冥故事中,胡的故事是作者叙述的重点,阿六只是一个“线人”。“线人”的作用在游冥故事中非常重要,很多重要的情节、若干不相关的故事都是通过“线人”连缀成统一整体的。
游冥故事“这种大故事中套有小故事、小故事又套有更小故事的连环套式结构”形态与佛经文学叙事非常相似。有学者曾称佛经文学的叙事结构为“葡萄藤式”结构。[5]“此种叙事结构在唐前的子书、史传中所见甚少,而在印度古典文学和佛经中则是一种常见结构。”“这种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又套更小故事的结构形式,是印度文学及中东文学所惯用的,如印度《五卷书》《故事海》及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等等的结构都是如此。”[6]游冥故事作为佛教地狱观与因果观念的载体,受佛经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吴海勇在谈到佛经文体特征时说:“多级层面的讲述始可谓是佛经讲述文体最具特色的内涵。经首语中的 ‘我’是第一讲述者, ‘如是我闻’ 以下尽为其所述,此构成佛经的第一叙事层。第一叙事层一般首先交待一时佛在某地,随即引出说法缘起,此后详记佛陀说法。……佛陀所述就成为第二级叙事层,其中故事似可称之为元故事,一般具有解释说明佛经缘起事件的功能。作为元故事的讲述者,佛陀显然也就是第二讲述者。”[7]游冥故事的复生后“自云”与佛经文学的“如是我闻”在结构上确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以环形结构为基础的连环套式结构为中国小说家们所承继和借鉴,对中国小说叙事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游记》《老残游记》等小说似乎能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
二、“冥判”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结构的影响
游冥故事所体现的佛教地狱观念、因果报应观念、三世轮回观念是融为一体的。佛教观念认为,人的前生、今生和来世都是互为因果的。在生命轮回过程中,前世为因,今世为果;今世为因,来世为果,“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8]。最能体现报应观念与轮回观念的就是“冥判”环节。
游冥故事的“冥判”环节是冥界游历的重要环节。明清以前游冥故事中的冥判多是对入冥之人进行冥判,入冥之人因为某种善因或奉经等宗教行为得以重生,故事多以人物的重生、“寿终”为结束。明清时期,随着小说的繁荣、小说想象力的丰富、小说技巧的纯熟、小说完成创作主旨的需要,小说利用冥判模式使人物的“生命”延长,人物不止于今生,前世、今生和来世通过“冥判”连接起来,以完成对历史事件、人物命运的解释,并融进作者的善恶忠奸观念。“冥判”进入明清小说中,常常勾连起人物的前因后果、前世今生,并同时进行人物今生与来世的转接,按照因果报应规律,人物的未来或者说是下一世的命运得到重新安排。而这种沟通阴阳、连接今生来世的自由转换功能为小说家拓展情节、传达创作理念提供了极大方便。随着小说技巧的成熟,一些小说把“冥判”嫁接入小说的结构设置中,为实现小说的创作宗旨、完成小说的功能起了结构小说框架、统驭全篇的作用。孙逊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转世”与“谪世”》一文中谈到佛教转世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它为中国古代小说提供了一种最为广泛而普遍的主题,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小说找到了一种常见的结构形式。”[9]实际上,这种转世与冥判的设计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对人物命运进行因果报应式的解说。
1.以“冥判”引领全书格局
明清时期,一些小说利用“冥判”模式进行结构布局、实现创作理念。在有些历史演义小说中,“冥判”成为一种结构范式,以实现小说家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游冥故事较早采用冥判模式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前因后果式的重新安排,是赵弼《效颦集》中的《酆都报应录》。该文叙渝州士人李文胜因母病向北阴酆都大帝祈母病痊,入冥见北阴酆都大帝审勘汉代七国之乱、外戚专权、王莽篡汉等积案。北阴大帝对于汉武戾太子被江充诬以巫蛊自经、晁错被袁盎以私怨谮杀案,判太子生于某公卿家为冢嫡,江充生其家为奴,受鞭笞四十年后仍以罪诛之。晁错与袁盎偕生于某处为子,仍同游官,后以计谋杀之,以报昔年之怨。对于汉外戚吕史窦梁四家专权国事,判生生世世为夷狄。对于史高与弘恭、石显陷死萧望之案,判萧生于某官家,史、弘生于其家为妾,二人后被其杀,石显则生为羊豕者十次以偿其冤。对于“王商王章冯野王郑崇王嘉翟义”等汉之良臣被王凤、王莽等陷案,北阴大帝判王凤受七世畜生之报,王莽生为水族类,三百年后生夷狄为女人身。这种忠节者托生贵室、佞恶者为奴为畜的冥判方式,既是宣扬因果报应,也表达了作者的善恶忠奸观念。
利用“冥判”模式对历史进行重新演绎并以此来结构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是司马貌断狱故事。司马貌断狱故事在《新编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卷上,已有一个模糊的影像,以天帝判韩信、彭越、陈豨分别托生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分刘邦天下,作为三国的起因。这个故事到了元代《三国志平话》,基本骨架已经定型。《三国志平话》叙司马仲相被请至阴间为阎君,韩信、彭越、英布三人状告刘邦。司马仲相断汉高祖刘邦有负功臣,让三人共分天下。韩信转生为曹操,彭越为刘备,英布为孙权,刘邦为汉献帝,蒯通为诸葛亮,仲相为司马仲达,从此展开了三国分合的情节。在结构上,司马仲相断狱成为历史小说的引子,以此来引出一段纷繁复杂的三国历史。
冯梦龙《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卷三一《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对三国历史进行安排的是司马貌,在三国局面的安排上,与《三国志平话》司马仲相的安排大致相同,只是增加了几个人物扶助刘备,蒯通为诸葛亮,许复为庞统,樊哙为张飞,项羽为关羽,纪信为赵云,而丁公则投胎为周瑜等。[10]
司马貌故事对后世的历史小说影响深远。清代有通俗小说《半日阎王传》,正文另题“司马貌断狱”,另有《三国因》一回,清醉月山人编,清又有醉月山人编《新刻三国因》,此书仍是冯梦龙“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的单行本。依据现存的文献资料,除了平话小说《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三国因》以外,清初徐石麟撰《大转轮》、嵇永仁撰《续离骚·愤司马梦里骂阎罗》杂剧,也都演司马貌断狱故事。[11]
从司马仲相断狱到司马貌断狱,二者都是对历史进行一种超越现实的解释。这种冥判式的对历史的重新安排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将历史事件纳入因果报应的思想体系,站在道德评判的立场上,通过游冥模式的框架表现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道德感受,虽然消解了复杂历史的严肃性,但却是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历史所能作的最“合理”解说。这种解说进入历史演义小说,很自然地成为结构小说的框架,作为小说统驭全篇进行结构安排的一种手段,它与小说的整体构思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常见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叙述模式。
历史演义小说《混唐后传》,同样以“冥判”模式来构架小说,小说的第一回以“长孙后遣放宫女,唐太宗魂游地府”作为小说的引子,其中唐太宗魂游地府的情节引出了书中唐明皇与杨玉环的故事,以佛教三世因果报应思想来解释李杨故事。署名为“竟陵钟惺伯敬题”的《混唐后传序》云:“昔有友人曾示余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为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12]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作为故事情节插入李杨故事中,作为小说的创作手段来构架小说的整体结构。
清代艳情小说《姑妄言》第一回,也是一个典型的游冥故事,主人公闲汉到听(名字就很有意味,到听,即取道听途说)一日醉卧城隍庙,梦中入冥,亲眼目睹冥王对汉朝至嘉靖年间的一些疑案予以审判,对某些历史人物依据情节轻重,判令转世受各种报应,从而对主要人物作出交待。以冥判模式来构架小说结构,对历史进行具有宿命意味的解释和演绎,从而使故事具有了历史感和信服感。[12]
小说以冥判模式作为全书结构的引子,既对人物的渊源因果作以解释,又巧妙地与全书的构思结合,把纷繁错综的历史事件融进组织严密的巨大因果网络构架中。以“冥判”作小说结构的引子,在小说结构上起到引领全篇的作用,并在总体上为小说定下一个基调,使读者先入为主,能够以一种平静的态度面对小说情节的发展,接受历史既定的格局,使全书浑然一体,结构完整严谨。
2.以“冥判”为结收束全文
以“冥判”来结构小说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以“冥判”作为小说结尾,对小说人物和事件作以因果报应式的总结和解释,“冥判”处于情节的收束部分即作为人物事件的结果。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七十四、七十五回,以明代赵弼《效颦集·续东窗事犯传》故事为小说的结尾。《效颦集·续东窗事犯传》主要写书生胡迪读《秦桧东窗传》,对奸臣秦桧谋害岳飞之事深为不平,愤而吟诗骂冥。后胡迪于梦中应阎王之召魂游冥府,亲睹冥王审判,秦桧在“普掠之狱”所受惩罚,“妒害忠良,欺枉人生”、“贪污虐民、不孝于亲、不友兄弟、悖负师友、奸淫背夫、为盗为贼、不仁不义者”,遭受酷刑,“万劫而无已”,忠良义士则生活于“云气缤纷、天花飞舞”的“忠贤天爵之府”。[13]这种冥判式的结尾,严峻的历史感得到了强化,使历史最终得到一种超越现实的解释。
明末世情小说《轮回醒世》十八卷183则故事,每一则故事的结尾都是阎罗王审案,阎罗王点出两世因果缘报,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家庭现象用“冥判”的形式作结收束全篇,使得小说结构非常严谨整齐。这一开头一结尾的“冥判”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同类描写的不同艺术功能。
“冥判”对小说结构上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它使小说结构框架清晰谨严,形成组织严密的因果网络构架,试图对历史、对社会现象作以解说,但这种构架和解说以佛教因果报应作为思维逻辑的依据。事实上,对于复杂严肃的社会历史来说,这种解释太过于轻巧,不是简单的因果报应就能解释得了的。同时也使作品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浓浓的宿命色彩,弱化了本该严峻的历史感,这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
[2]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15.
[3]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2:221.
[4] [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75.
[5] 糜文开.印度文学欣赏[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0:10-17.
[6] 李宗为.唐人传奇[M].北京:中华书局,2003:50-51.
[7] 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418-419.
[8] 孙逊.中国古代小说的“转世”与“谪世”[G]//黄子平.中国小说与宗教.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98:179.
[9] 刘勇强.千年怨气一朝伸——谈《闹阴司司马貌断狱》[J].文史知识,2006,(1).
[10] 张桂琴.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
[11]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291.
[12] [明]钟惺,罗贯中.混唐后传·五代残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卷首.
[13] [明]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第74回.
〔责任编辑:曹金钟〕
2016-09-28
黑龙江省社科研究规划年度项目“游冥故事——中国古代小说的建构空间”(13B015)
郑红翠(1970-),女,黑龙江林口人,副主编,副编审,博士,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编辑学研究。
I206.2
A
1000-8284(2016)12-01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