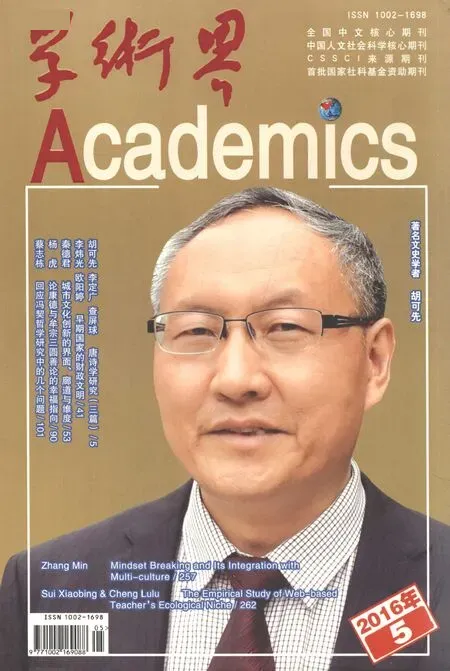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及其意义
2016-02-27杨晓琼
○ 杨晓琼
(1.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2.湖北民族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及其意义
○ 杨晓琼1,2
(1.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武汉430079;2.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恩施445000)
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涵义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所指的理论。弗雷格认为,与一个符号相关联的,不仅有符号的所指对象,还有符号的涵义,在其涵义中包含了符号呈现的方式和语境。符号只能经由涵义这个“媒介物”才能与所指建立联系,涵义决定所指;而句子的涵义是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句子的所指则是句子的真值。以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层层剖析为基础,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不仅促进了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为意义理论奠定了第一块思想基石,而且对翻译学等其它学科也具有多维启发。
弗雷格;意义理论;意义
一、引 言
探讨语言符号意义的理论,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起就有了名实之辩。荀子认为,万物之名,都是人强加给它们的,但一旦一个名称为大众所接受,那它的名实之间的关系便固定下来,所谓“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1〕不过,这种约定俗成的前提是稽实定数,即根据客观事物的实际来确定事物的名称。而确立名称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分辨客观事物,进行思想交流,贯彻政治原则,所谓“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2〕同时,为了与客观事物相符,还需“制名以指实”,〔3〕使名称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期的另一位名家辩士,是大名鼎鼎的公孙龙。他认为“名”就是对“实”的称呼,而“实”的意思则是“物”,就是在客观世界中占据某种空间的东西。他不承认摹状词所修饰的“实”(白马)与无摹状词修饰的“实”(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不承认“白马”只是“马”在意义上的附加,无异于本质的马,从而得出了“白马非马”的结论。针对公孙龙的“物莫非指”〔4〕和庄周的“得意而忘言”〔5〕,墨家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6〕的观点,应该说,墨家的这种观点也是比较中肯的。
在西方,指称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把世界中的有形物质看成是流动变化的,他认为不会变化的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理念”,比如说,当我们说到“老虎”时,我们实际上并不是指任何一只老虎,而是称任何一只老虎。而“老虎”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有形的“老虎”,也不存在于时空之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存在于感官世界、生活在丛林之中的某只“有形”老虎,却是“流动变化”的,它会老去、会死亡、会腐烂。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概念是由事物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他提出的十范畴实际上就是十种类型的概念,具体对象则从属于这些概念,或者说概念(谓词)对应于对象。
尽管哲人们对意义的探讨源远流长,但真正将意义问题凸显为思考的核心,并形成一系列自成体系的意义理论,则始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而促成这一转向的关键人物就是弗雷格。他发表于1892年的那篇著名论文《论涵义和所指》,从思想上为语言哲学意义理论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二、弗雷格对符号涵义和所指的区分
弗雷格对符号涵义和所指的区分,最早出现在《函数和概念》一文中,是应用于数学表达式的。他说:“我们必须区分涵义和所指。尽管‘24’与‘42’有着相同的所指,即它们是同一个数的专名,但它们的涵义不同。因此,尽管‘24=42’与‘4×4=42’有着相同的所指,但其涵义却不相同,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包含的思想不同。”〔7〕后来在《论涵义和所指》这篇语言哲学的扛鼎之作里,这个区分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解释。在该文中,弗雷格对符号所指涉的对象和蕴含的涵义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并对二者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发。
弗雷格从分析等同问题入手,开篇就提出这样的问题:“等同(sameness)是一种关系吗?一种对象(object)之间的关系?还是对象的名称(names)或符号(signs)之间的关系呢?”〔8〕如果A=B仅表示符号之间的等同关系,那么,这两个符号之所以能联系起来且具有等同关系,是因为它们不仅命名或指称了某个东西,而且是指向同一个所指。若此,等同关系就不单属于符号方面。如果A=B仅表示符号所标志的对象与对象之间的等同关系,那么,在A=B为真的情况下,指称同一个对象的A=B与表示对象与自身有着等同关系的A=A在认知意义上就会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差异仅在于:符号的呈现方式。若此,等同关系就不单属于对象方面。这就说明,等同关系是既属于符号也属于对象的关系。因此,弗雷格说:“与一个符号(名称、词组、表达式)相关联的,不仅有被命名的对象,亦即符号的所指(nominatum),而且还有符号的涵义(sense)、内涵(connotation)或意义(meaning),在其涵义里蕴含着符号呈现的方式和语境。”〔9〕
当我们用不同的符号来描述同一个对象时,并不是多余的无谓之举,因为符号的呈现方式(manner of presentation)本身就承载着意义。尽管“晨星”和“暮星”指称的是同一对象——金星(Venus),但显然它们的涵义是不同的:黎明见于东方的是“晨星”(morning star),黄昏见于西方的是“暮星”(evening star)。“晨星是/等于晨星”这样的命题是先验有效的,除了表明自身与自身等同之外并没增加任何新的内容;而“晨星是/等于暮星”是天文学上的发现,它包含着新的天文学知识,而且这类命题并不总是能先验地加以验证。同时,符号呈现的语境也与其涵义密不可分。比如说,“我们约好一起去看先生”,这里的先生到底是指风水先生、说书先生、某个老师还是医生呢?显然,“先生”的“涵义”还取决于该词出现的语境。举例说,若两人因身体不适而相约去看“先生”,那么,此时的“先生”就是指“医生”。这一思想与弗雷格提出的语境论原则是一致的,即“只能在命题的语境下而不能孤立地询问语词的意义”。〔10〕
对于符号、符号涵义和符号所指之间的关系,弗雷格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与某一符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涵义,与特定的涵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所指。而与一个所指(对象)相对应的,并非只有一个符号。在不同的语言里,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之中,相同的涵义也是由不同的表达式所表述的。”〔11〕在这段话中,弗雷格不仅明确区分了符号、符号的涵义和符号的所指,而且还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涵义决定所指”的原则——语言符号只有表达了确切的涵义,才能指称对象;语言符号究竟指称什么样的对象,取决于该对象是否具有符号的涵义所描述的那些特征。同时,他还提到,有的符号有意义,但没有与其涵义相对应的所指。例如,“离地球最远的天体”这种说法有意义,但是否也有一个所指,则并非不容置疑。“最小发散级数”和“最大收敛级数”这种说法有意义,但却没有所指,因为理论上而言,对于任何一个发散级数,我们都能找到一个参照级数发散;对于任何一个收敛级数,我们也都能找到一个参照级数收敛。因此,可以作为永恒参照级数的“最小发散级数”和“最大收敛级数”并不存在。
在明确区分“涵义和所指”的基础上,弗雷格进一步指出,不能把符号的涵义/所指和与之相联系的“意象”(image)混为一谈。
如果一个符号的所指是感觉的对象,那么我对此对象的意象是一种内心图像,这种内心图像源于我的感官印象和活动所留下的记忆。……即便是对于同一个人,同样的涵义也并不总是伴随着同样的意象。意象是主观的,一个人的意象不是另一个人的意象。因此,与同一种涵义相联系的意象之间就产生了差异。“亚历山大大帝的战马”(Bucephalus)这一名称,在画家、骑手、动物学家心里所唤起的意象可能大不相同。因此,意象在本质上不同于符号的内涵。符号的内涵可能是许多意象的共同特征,因而并不是个别人心灵中的一部分或个别人的心智模式;因为我们不能否认,人类拥有代代相传的、共同的思想宝库。〔12〕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弗雷格所说的“意象”,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象”,是针对个人对符号涵义或所指的“理解”而言的,或者说是个人对符号的理解而形成的“主观涵义”;但符号还有反映客观世界、不随认知主体变化而变化的“客观涵义”,符号涵义的客观性使得不同的认识主体能够把握并分享同一个“涵义”,人类思想传播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符号的“客观涵义”具有共享性和普适性。也就是说,尽管对一个涵义的理解过程属于个人的内在心理行为,但被理解的涵义却并不是私人的或心灵内部的东西,因为不同的心灵可以通达同一个涵义,不同时代的人也能通达同一个涵义。弗雷格的这一思想也符合他探讨数学基础时所遵循的客观性原则——“始终严格区分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13〕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符号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涉及三个层次:第一、意象;第二、涵义但并不涉及所指;第三、所指。对于意象、涵义和所指之间的差别,弗雷格以“月亮”为例作了精妙的说明。“涵义”类似于用望远镜观察月亮时,望远镜内物镜上所显示的真实图像,这种图像是客观的,能被许多不同的观察者所利用;而观察者眼中的月亮,亦即观察者视网膜上的图像,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意象。千人眼中或许就有千种月亮的意象。但是,不管是物镜上的客观图像,还是个人眼中带有主观色彩的图像,都有一个共同的所指:天体月亮。需要注意的是,弗雷格所说的符号是宽泛意义的符号,他的形式语言是符号,语词、表达式和句子也是符号。
三、句子的涵义和所指:思想与真值
弗雷格把符号具有涵义和所指这一思想延伸到句子,他认为,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就是句子的涵义,而句子的真值就是句子的所指。弗雷格这里所考虑的句子,是判断句,即逻辑中所考虑的命题。至于思想,弗雷格说他并不想给出一个定义,他把思想称为探讨真理问题时所涉及的东西。他认为,就像一个判断有正误之分一样,思想也有真、假之分。当我们说思想是语句的涵义的时候,也并不是说每个语句的涵义都是一个思想,因为并非所有语句都涉及真假问题,比如说,表达愿望、请求、命令的祈使句和感叹句也有其特定的涵义,但这类句子的涵义与真假问题无关,也就不是思想。同时,思想又是无形的,凡是有形的、可感知的东西都与思想无关,但是这无形的思想需借助有形的语句(基于对世界的感知而形成的语句)的外衣,才能成为我们所理解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个语句表达一个思想。当我们说“太阳升起来了”这样一个句子表达了一个思想的时候,并不是说它表达的思想是一个目之所见、散发光芒的客体对象(object),而是基于感官印象的一种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格所说的语句本身的“思想”并不是指思维的主观活动,而是指思维的客观内容,是能为许多人所共同拥有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在勾股定理中所表达的思想,它的真就是无时间性的,它的真也不会受到是否有人把它视为真的影响。”〔14〕至于如何通达思想这一思维的客观内容,弗雷格是这样说的:“我们既不能像拥有一种感官印象那样拥有一个思想,也不能像看见一颗星辰那样看见一个思想。因此,明智的做法是选取一种特殊的表达,而‘领会’这个词则正好合适。”〔15〕
语句的涵义是思想,而思想是可以领会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弗雷格对“思想”的一种界定吧。不过,在这种可以领会的东西里,弗雷格排除了措辞、语气以及语态等因素所造成的差异对句子所表述的思想的影响。他说:“不管我选择‘马’‘骏马’‘拉货车的马’还是‘母马’,都对思想没多大影响。论断力度(assertive force)不会波及到这些词语的差异之处。诗歌中所谓的语气、馨香和启迪以及节奏韵律所传递的东西,并不属于思想。”〔16〕因此,一个句子的内容往往会“大于”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反过来,“语词”不能充分表达思想的情况也同样存在。比如说,“我是音乐爱好者”这样一句包含人称代词“我”的话语,出自不同人之口,表达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些思想可能是真的,另一些可能是假的。
在领会了语句的思想或涵义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满足了呢?弗雷格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对真的追求要求我们从涵义推进到所指。”〔17〕如果我们止步于句子的涵义或思想,那么许多错误的认识就无法得以修正。哥白尼把对“地球是宇宙中心”这一命题的理解推进到对其是否为真的科学探索,最终推翻了统治西方思想千余年的“地心说”。弗雷格把句子的真值(即句子为真或为假的情况)理解为句子的所指,他强调说:“对于任何一个陈述句,若语词的所指至关重要,则可以把它看作专名,并且如果它的所指确实存在,则这个所指要么为真,要么为假。”〔18〕比如说,句子A“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真的,句子A的真值为“真”;而句子B“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是错的,所以其真值为“假”。当然,对于文学作品里的句子,比如说欣赏一首史诗,语句的所指和真值对我们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得到艺术享受,能被语言的优美、语句的涵义及其所唤起的意象和情感所吸引。把真值表示为对象并非纯粹的文字游戏,因为“任何判断——且无论是多么自明的判断——都是从思想层次到所指层次(客观事实)的进一步推进。”〔19〕
弗雷格指出:“如果我们的猜想(即句子的所指就是它的真值)是正确的,那么,当句子成分被所指相同但涵义不同的表达式替换时,句子的真值必定保持不变。”〔20〕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英国的首都是伦敦”改为“英国最大的城市是伦敦”,那么,这两个句子的所指仍然是相同的,真值也保持不变,因为“英国的首都”和“英国最大的城市”指的是同一个城市,即伦敦,但这两个句子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知道“英国的首都”也是“英国最大的城市”的人,可能会认为一个句子是真的,而另一个是假的。
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就是句子的涵义,而句子的真值就是句子的所指,弗雷格的这一论断与他在《算术基础》中提出的概念和对象相区分的原则——“绝不要忘记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区别”〔21〕——密切相关。弗雷格所说的概念和对象有着特殊的含义,是他把数学中的函数表达式与命题加以类比后引入的术语。根据这一类比,命题也可以用主目(argument)和函项(function)来分析。函项类似于命题中的概念或谓词,主目则类似于对象或主词。在数学中,每一个函项都是不完整的,有一个由主目来填充的空位。比如,36、46、56、66、76、86……这组表达式就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1.函数表达式“()6”;2.主目3、4、5、6、7、8等。只有当函数表达式与主目结合时,即上述3、4、5、6、7、8等主目与函数表达式“()6”结合在一起时,才是一个完整的表达式。同样,在命题中,概念也是“不饱和的”,要由主词所挑出的各种不同对象来使其变得完整。比如,“()是英国首相”,如果在括号中填入“卡梅伦”,就组成一个真值为真的的句子;反之,若填入1、2、3、4、5等阿拉伯数字或大树、山川等与概念毫无关系的词语,就是一个真值为假的句子。概念和对象的如此区分,说明谓词对应于概念而不是对象,由概念表示的抽象对象寄生在具体对象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格说:“概念是其值总是为真值的函项”。〔22〕
在弗雷格看来,把谓词和主词如此结合以引入概念、并选出对象使概念完整,正是语言表达思想、发挥作用的途径。由于概念词(谓词)的所指是概念,专名(主词)的所指是对象,所以,这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专名和概念词的结合就形成了断定句所表达的思想,思想是借以考察真的东西,因此,一个断定句的思想实际上表现为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当对象处于概念之下时,思想为真;反之,思想为假。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弗雷格对符号的涵义和所指的区分以及对涵义的界说,与他探索数学基础时提出的“语境论原则、客观性原则和概念/对象相区分原则”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对日常语言的思考也同样遵循了这三条原则。
四、弗雷格意义理论的意义
弗雷格在其意义理论中,对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对涵义和所指的区分和探讨,对思想的探讨,对真值问题的探讨,以及他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所坚持的三个原则,对后人有着如下启迪:
(一)促进了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
弗雷格在阐述其意义理论中用到的三原则,尤其是语境论原则,经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引用和诠释,发展成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原则。“只能在命题的语境下而不能孤立地询问语词的意义”,这条原则主要是强调句子的作用,强调句子的作用也就是对语言分析的强调,正是这一点使得语境论原则超出了它被运用于数学的意义,最终成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原则。而弗雷格对句子或思想真值的逻辑分析,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句子来研究真,这与语言哲学中通过语义上行来探讨哲学问题相契合,或者说,通过语言分析探索哲学问题的路径是弗雷格开辟出来的。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的本体论阶段,研究对象主要是客体,即对知识对象的探求;第二阶段是近代的认识论阶段,着重探讨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和限度的探究来解决知识的基础和来源的问题;第三阶段是以现代语言哲学为标志的“语言转向”,重点探讨主体认识活动的内在机制,以及认识及其语言表达之间的具体关系,也即是从对知识基础的研究转向对知识的表达、知识的本质的探讨。简单说来,这三个阶段的哲学研究是围绕着知识的对象、知识的来源和知识的表述展开的,而语言哲学通过“语义上行”的方法就可以探讨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内的诸多问题。比如,我们可以把命题“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变为命题“‘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是真的”,这样就把哲学问题变成了语言问题,从而可以撇开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将注意力贯注到语言上,通过语言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和解释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即从句法通达本体和认识。
(二)为意义理论奠定了第一块思想基石
弗雷格对涵义和所指的区分始于对同一性问题的追问,但其区分的后果却是澄清了有关意义的许多问题。“这种区分……虽并未直接产生导致或否定某一种意义理论的后果,但却为人们后来研究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构思精密的概念框架和一种注意细微差别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在当代意义理论的发展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23〕戴维森说:“……我们一直遵循着弗雷格的足迹。由于有了弗雷格,人们才清楚地知道这条探寻的途径,人们循着这条途径进行探寻的劲头甚至经久不衰。”〔24〕
循着这条路径,蒯因成为意义的怀疑论者,他说:“意义与指称的混淆助长了把意义概念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倾向。好像‘男人’这个词的意义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可以触摸,好像‘暮星’这个词的意义就像空中的星星一样清晰可见。而质疑、否定意义概念就是假想一个只有语言却没有所指的世界。实际上,我们可以承认那一世界的对象,我们可以尽情地让我们的单称词和通称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指称那些对象,而根本不必提及意义这个话题。”〔25〕蒯因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区分的批判,就是以他对分析性这个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的论证为基础的:由于“分析性”无法界定清楚,因此,依赖于这个概念所做出的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截然二分的传统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蒯因的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结果在几十年间,形成了对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激烈、精辟的辩论,使得分析性这个概念得到了较之以往更加明确的刻画。循着这条路径,普特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论怎么说,意义都不在头脑之中”〔26〕的口号,批判了内涵决定外延(从“内涵相同,则外延相同”的意义上而言)的观点。循着这条路径,戴维森用他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对语句意义如何依赖于语词意义进行了全新的解释。
在弗雷格开辟的这条探索意义的道路上,镌刻着诸多伟大哲学家的名字。不过,不论是探究名称、摹状词及指示词的语义性质,还是考察真理与意义的关系;不论是对涵义决定所指提出质疑的语义外在论,还是对语义内在论的坚持;不论是行为主义意义论,还是意向性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莫不以弗雷格对涵义/所指的区分以及对涵义的界说为其背景理论。如果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在为柏拉图作注(怀海特语)的话,那么,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整个西方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史也不过是在为弗雷格作注而已。弗雷格,无愧于“语言哲学之父”的称谓。
(三)为翻译学等其它学科研究提供思想源泉
弗雷格对意义问题的哲学思考,不仅理所当然地成为哲学家们的思想源泉,也为关注意义的译学研究者提供了思想源泉。以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作为背景理论,我们可以对可译性问题、翻译标准等问题进行全新的解释。由于句子的所指就是它的真值,而用所指相同涵义不同的表达式替换该句子的构成成分,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所以,只要译文与原文的所指保持一致,就是对等的翻译。同时,尽管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符号载体,尽管描述相同对象的符号在不同人心中唤起的意象不完全一样,但涵义是客观的,思想是思维的客观内容,能为多个不同的心灵所理解,能为许多人所共享,这是使一切翻译成为可能的基础。翻译是可能的,但意象与语词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意象间的差异性又决定了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弗雷格所说:“如果人们的意象之间没有某种相似性,艺术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诗人的意图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却永远也不可能确切得知。”〔27〕
注释:
〔1〕〔2〕〔3〕安小兰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7、242、244页。
〔4〕庞朴:《公孙龙子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页。
〔5〕郭庆潘:《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44页。
〔6〕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42页。
〔7〕〔22〕Frege,G.,Function and Concept,P.Geach and M.Black(eds.),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 of Gottlob Frege,Oxford:Basil Blackwell,1960,pp.29,30.
〔8〕〔9〕〔11〕〔12〕〔17〕〔18〕〔19〕〔20〕〔27〕Frege,G.,On Sense and Nominatum,A.P.Martinich(ed.),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86,187,187,188,190,190,190,190,189.
〔10〕〔13〕〔21〕Frege,G.,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A Logico-Mathematical Enquiry into the Concept of Number,Trans.J.L.Austin,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53,p.xxii.
〔14〕〔15〕〔16〕Frege,G.,Thought,Beaney,M.(ed.),The Frege Reader,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7,pp.337,341,331.
〔23〕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61页。
〔24〕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页。
〔25〕Quine,W.V.,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Logico-Philosophical Essay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3,p.47.
〔26〕Putnam,H.,Mind,Language and Reality(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2),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p.227.
〔责任编辑:钟和〕
杨晓琼,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哲学及翻译学研究。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融资政策与学术支持〔*〕
- 我国宪法文本中“文化”表述的剖析〔*〕
- 占有保护理论与实践问题之反思〔*〕
- Discussion on Great Ruins Presentation Method
—— A Case Study of Wuhan Panlong City Archaeological Park - Research on the Variability and Impac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Era〔*〕
-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ief Activities from the Municipal Office in Wartime
——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Municipal Health Arch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