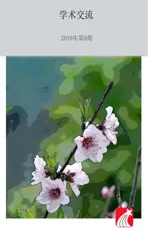中西戏曲戏剧语言与文体比较
2016-02-27俞航
俞 航
(南京大学 中文系,南京 210046)
外国文学研究
中西戏曲戏剧语言与文体比较
俞航
(南京大学 中文系,南京 210046)
中西戏剧在起点处均为歌、舞、乐一体,语言形式也是韵体的,在发展进程中二者却分道扬镳,西方戏剧以散文为主要语言,散文体为主要文体;中国戏曲以韵文为主要语言,诗歌为主要文体。西方戏剧注重反映现实生活,形成相对独立的文类;而中国戏曲更强调对形式美的提炼,文类互渗的现象甚多。在戏剧理论方面,西方戏剧理论从“摹仿说”到新古典主义的“逼真”再到现实主义的“真实”脉络清晰;而中国戏曲在礼乐传统及诗歌正宗的影响下,最终确立了以“曲”和“歌”为重的戏曲理论。尽管发展道路不同,但诗性的内质却是中西戏曲戏剧共同的本质特征。
西方戏剧; 中国戏曲; 语言; 文体
在西方戏剧的源头古希腊时期,戏剧是一种综合性艺术,歌队不可或缺,这既是戏剧仪式的残留,也是悲剧表现抒情特性的必需。因此,古希腊戏剧与中国戏曲的相似性不言而喻:歌舞俱全,文体以诗体为主。戏剧的散文化,是在19世纪现实主义戏剧占主导地位时发生的。西方戏剧的历史进程最终选择了散文体作为戏剧的主要文体。而西方戏剧理论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始就奠定了“摹仿现实世界”的主旨,从“摹仿说”到新古典主义的“逼真”,直到现实主义的“真实”,西方戏剧理论的脉络是比较清晰的。然而中国戏曲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将诗、乐、舞综合一体的艺术形式保持至今,形成独特的戏曲艺术,其唱词、宾白直到今日依然保留浓浓的诗性韵味。西方戏剧的“散文化”实际上并未使之抛弃戏剧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应具备的诗性特征。然而,西方戏剧语言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散文化倾向,而中国戏曲在礼乐传统下更强调辞藻、唱腔等形式上的技巧,中西戏曲戏剧的分野是历史与逻辑的共同选择。
一、反映百态与提炼形式
(一) 西方戏剧反映社会人生百态
艾布拉姆斯指出:“摹仿倾向——将艺术解释为基本上是对世间万物的模仿——很可能是最原始的美学理论”[1]。在亚里士多德以“摹仿”为本质的戏剧理论体系中,情节是最为重要的。“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由此可见,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2]64注重情节也就是注重戏剧所表达的内容,通过情节承载的内容,古希腊戏剧能够引发观众的恐惧和怜悯,使这些情绪得到宣泄(即卡塔西斯katharsis)。在新古典主义时期,戏剧通过情节所反映的内容起到道德训诫作用,推崇理性支配下对君王的服从及对国家的忠诚。到了现实主义戏剧时期,戏剧家们渴望通过情节反映现实真相,匡正时弊。从这一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西方戏剧最看重的是对现实生活、人生百态的描摹和反映。西方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试图真实地反映现实。因此自然主义戏剧理论认为真实即道德,他们要求剧作家做一名观察者,把观察到的所有事物写入戏剧,将真实生活搬上舞台。然而许多西方戏剧理论家早已认识到,这绝不是一面“沉默”的镜子,戏剧表演也绝不是一部留声机。虽然人们对西方戏剧的总结往往是“再现”生活,但这种“再现”并不是死板的反映,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提炼,甚至可以有所夸张。剧作家试图真实地反映所见所闻,但这其中必然包含他的看法,必然蕴藏着他的价值判断。有理论家认为,倘若不经选择将现实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话,反而会让观众觉得不真实。只有经过编排,经过提炼,才能为观众创造“真实的幻觉”。
西方戏剧的语言与文体特征是基于以上戏剧摹仿现实、反映生活的原则。从古希腊悲剧到新古典主义悲剧,剧中人物均用诗体来对话,直到19世纪的现实主义戏剧,散文体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体。但戏剧理论家认识到戏剧语言中的散文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并不同,“日常生活的谈话,如果放到戏里,就会使人感到无法容忍的乏味,而且,从没有一个伟大的剧本是用这种语言写出来的,不论它看起来可能多么‘现实主义’”[3]。戏剧语言是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具备抒情性、形象性特征的精炼式语言,是艺术性的语言。在西方近代戏剧中,诗剧衰落,无韵体诗句几乎被散文所取代,这并非现实主义戏剧抛弃了对语言艺术性的追求,而是因为诗剧已经变得书本气,甚至矫揉造作。当现实主义奠定了西方戏剧以“真实”为标准的戏剧理论的主导地位之后,为显“真实”,戏剧家在写剧本时必须为人物选择合乎其身份的言辞。如果一个乡村女孩在倾述自己的爱恋时说道:“请告诉我对这选择我该抱什么希望,这么娓娓动听的谈话真叫人感到余音绕梁,我和他的情意终于有了公开表白的自由,对这自由你可千万别说过了头。”文雅的语词并不符合她的身份,但如果这话出自高乃依笔下的施梅娜之口,却正是她的习惯语言方式。可见,西方戏剧的语言是经过提炼的,但绝不是矫揉造作的。例如,哈姆莱特的语言是对真实生活的反映。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语言所具备的不仅仅是诗的外壳,更重要的是诗意的内涵——这才是西方戏剧语言最重要的内核。然而,中国在引进西方戏剧时存在着误读:人们分不清戏剧中的对话与日常对话、政治演讲之间的差别,将戏剧中的对话等同于现实生活的谈话。因此,中国对西方戏剧的最初引进和译介往往省略了对话,传统戏曲则认为新剧(话剧)只说不唱,“无功可言”。
(二) 中国戏曲注重提炼形式美
中国戏曲以曲辞为主,宾白为辅。西方对中国戏曲的误读集中在曲辞:西方人认为戏曲中的歌唱每每出现在人物感情激动之时,是人物情感抒发的媒介手段。西方译介戏曲时在很多情况下删去了曲辞。既定的传统构成接受的背景与前提,使得人们只能在自身的知识结构框架中理解外来事物,因此误读不可避免。事实上,戏曲的曲辞承担着提炼程式美的功用。不同于西方戏剧注重情节所反映的内容,中国戏曲从古至今都很重视对形式美的提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往往有一套固定的程式来表现不同的情境。程式是指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思想、情感进行分类,以规范的成套的语言、动作或旋律来表现这些分类。中国戏曲绝大多数剧种人物都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几大类,其下又可分若干小类。不同角色各有各的表演程式,唱、念、做、打各有各的规定。例如:“起霸”表现古时候将军出征前整理盔甲,“走边”是江湖好汉夜间在崎岖艰险的路上潜行,“打哇呀”表现鲁莽英雄的暴怒,“软卧鱼”表现女性俯身摘花、扑蝶时柔美的姿态。戏曲表演的程式化,并不意味着简单化、类型化,而是指其非常讲究舞台和表演的形式美——姿态美、服饰美、旋律美、唱腔美等。这种规定性不是想逼真地描绘什么,而是要让演员运用程式化的手段使观众有一种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中国戏曲的程式化本质上而言是由中国戏曲美学决定的。戏曲美学淡化了摹仿功能,强化了表演中的形式因素。不把理性认识的“真实”作为评价标准,而是依托于感性判断的“美”,因而中国戏曲艺术形成了具有超逸特征的形式美。观众在戏曲审美过程中因程式化的表演而与舞台角色保持了恰到好处的审美距离。
受中国戏曲注重形式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押韵具有声韵美的韵文成为戏曲语言的理想媒介,对仗工整、清词丽句的诗歌则成为戏曲文体的最佳选择。戏曲对形式美的追求决定了语言要守音律、别阴阳、合平仄四声,这其实正是填词作曲的规范。属于曲牌体的元剧、南戏的唱词都由所属的曲牌规定了长短、字数、平仄、韵脚。正因如此,古人论戏曲语言,如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的“乐府”“乐章”、明代王骥德《曲律》“曲禁四十条”,等等,几乎都是对词式音律的诠释。除了唱词之外,宾白也十分注重韵律,正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宾白之学,首务铿锵。一句聱牙,俾听者耳中生棘;数言清亮,使观者倦处生神。世人但以‘音韵’二字用之曲中,不知宾白之文,更宜调声协律”[4]。可见,无论是唱词还是宾白,中国戏曲都讲求节奏鲜明、抑扬顿挫、声调铿锵、音色清亮之美。戏曲语言形式美主要体现在音节对称、韵辙整齐、平仄抑扬。音节的对称主要指上下两句的言词音节对称,可以营造一种匀称、和谐之美。例如《西厢记》:“空撇下碧澄澄苍苔露,明皎皎花筛月影。白日凄凉枉耽病,今夜把相思再整。”“青山隔送行,疏林不作美,淡烟暮霭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宁。有一日柳遮花映,雾帐云屏,夜阑人静,海誓山盟。”一系列宾白唱词语言节奏相同,观众在音节的均衡、和谐之中体会到形式上的对称之美。韵辙的整齐主要指的是唱词宾白中的韵脚,以同韵字母按一定规律反复出现,造成韵律的回环反复形成美感,这其实就是中国诗歌创作方面的押韵规则。中国戏曲中许多名段大多是押韵的唱词,旋律优美,回味无穷。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第十出“惊梦”的著名唱段: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贴〕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
唱段中“遍”“垣”“天”“院”均押韵,声律协调,朗朗上口。唱段既能很好地表达杜丽娘的内心情思,又韵律优美,意境如画,可与诗歌媲美。而平仄的抑扬是指四声平仄相间而形成的抑扬顿挫之美。戏曲语言的平仄并不像律诗、绝句那样严格,但符合平仄的语句演唱起来必然更加朗朗上口,适于应和曲调,因此元杂剧、明清传奇都有一定的平仄规律。如果合了平仄规律,则优美清亮,否则便诘屈聱牙。
二、文类独立与文类互渗
(一)西方戏剧的文类独立
西方文学在发展的原初状态时就十分注重对各种文学体裁(genre)的区分与界定。体裁纯粹的观点在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条戒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通过摹仿所采用的不同媒介,针对不同对象,对不同体裁进行了界定。戏剧一开始就是一种较为强势,发展得较为完善的文类。在古希腊,其地位与史诗几乎平起平坐。《诗学》就将戏剧(主要是悲剧)与史诗相比较论述,因为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和史诗(荷马史诗)是亚氏生前希腊发展得最好的两种文类。正是通过与不同文类体裁的对比,亚里士多德才能给予悲剧一个完整的定义。因此,早在古希腊时期,戏剧就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文类意识,其核心概念——“展示”也已经初具雏形:戏剧不是像史诗那样由吟游歌手讲唱故事给观众听,而是由一组演员在观众面前表演故事。随着西方戏剧的发展,“冲突”则逐渐成为推动情节的重要手段,而展现“冲突”的方式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之间由于意志、价值、视界的差异而有了对话的动力——矛盾,西方戏剧在开始文本“对话化”运动之后,语言的主要功用就是推动剧情、表现和发展矛盾冲突、设置和组构悬念以及刻画人物性格。中西戏曲戏剧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两种不同的话语模式。西方戏剧注重内交流系统,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将剧情展示出来,这种话语形式就是“展示”。中国戏曲注重外交流系统,文本中的剧作家、舞台上的演员直接与观众接触,近乎史诗或讲唱文学的话语形式,即“叙述”。 叙述性的文本以指称功能与诗歌功能为主,审美化的诗体语言形式成为必然的选择。展示性的对话文本以意动功能与表现功能为主,散文是理想的媒介。而西方戏剧从“叙述”占主导到之后的彻底“展示”化,最深层的动因便是戏剧文类意识的自觉。在“展示”这一核心概念统型之下,西方戏剧的语言有了不同于其他文类的功用。
首先,戏剧对话中的语言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语言六要素*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提出了语言六要素的理论,分别为:说话者、受话者、信息、 语境、接触、代码,分别对应六种功能:表现功能,意动功能,诗歌功能,指称功能,交际功能和元语言功能。参见罗曼·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滕守尧译,《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中的意动功能在戏剧对话中运用得最多,因为意动功能强调的是信息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其关注点在接受者的反应,双方的不同反应能够有效地推动情节进展。当戏剧语言的主导功能是意动功能时,话语的行动性就被突出出来:其一是这种语言能够引起角色自身的外部形体动作,而不是单纯的叙述事件;其二是语言能够影响剧中人物之间的交流,作为催化剂刺激双方产生相应的意念及动作。双方对话相互作用、促进,推动剧情不断发展。如高乃依《熙德》第一幕第三场,罗德里格与施梅娜的父亲因争夺太傅一职而发生冲突。双方对话从冗长到简短直到升级为行动,语言的意动功能不断加强,也不断推动剧情发展。伯爵不断强调自己才配得到荣誉,并暗示唐·狄埃格是靠耍手段获得太傅的职位,而唐·狄埃格由最初的忍耐到后来语露讥讽,最终激怒伯爵,外部行动(打耳光与按剑)的激发是通过双方对话意动功能的不断强化来完成的。
其次,戏剧对话中的语言是塑造人物,展现人物性格的基本手段。“展示”为主要话语模式的西方戏剧主要依靠人物自身的台词来表现人物性格。因此,西方戏剧经典理论认为,如果把台词当作叙事的工具,即使运用的语言再文采飞扬,所叙述的故事再引人入胜,也只能算是演员在台上说故事,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物在台上演戏,观众也只是听故事,而不是看戏。只有人物说话的方式最能体现人物的性格,而语言六要素中的表现功能展示了说话者的态度,最能体现话语主体的特性,在描述人物性格时运用得最多。如莫里哀的《伪君子》在达尔杜弗出场前,通过“间接描写”的方式来塑造其形象:家庭争吵中不同人物对他的看法。观众虽然已经大体上了解了这个人物,勾起了好奇心,但百闻不如一见,“伪君子”达尔杜弗在第三幕第二场出现,一开口就暴露了他的伪善,他唯恐别人不知道他的苦修行为和“善心”,矫揉造作、欲盖弥彰的言辞使观众明白了他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伪善,让观众对人物的性格没有一分一秒的疑惑。这里的表现功能突出了主体的话语形式,也就是“怎么说”。
(二) 中国戏曲的文类互渗
不同于西方戏剧的文类意识相对独立,中国戏曲一直处于文类互相渗透的状态。自古以来强大的礼乐传统使中国文学带有韵律。而强大的诗歌传统对中国戏剧文类模糊并最终的“曲化”影响很大。节奏感极强的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正宗,甚至散文也带着韵文色彩,戏曲形制也偏向于歌唱的表演性、音乐化、舞蹈化。另外,由于中国戏曲定型较迟,因而在发展过程中综合了其他一些表演艺术。中国戏曲艺术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祭祀歌舞、巫觋等表演。周代宫廷的仪式性歌舞,已有一些戏剧因素。由于中国戏剧在萌芽之初,内容较复杂,包含了杂技、歌唱、演戏等诸多成分,因而文类界限不十分清晰,没有专门的理论对戏剧单独进行研究和总结。后来戏曲在发展过程中,陆续将武打、滑稽表演、说唱艺术等囊括其中,直到唐宋时期,大量的歌舞戏、参军戏、胡人戏等表演艺术也综合进去,戏曲作为一种体裁才相对成熟。
中国戏曲从形成起,就受到说唱艺术很深的影响,说唱艺术是戏曲源头之一。“叙述”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戏曲的核心概念,正是说唱艺术渗入戏曲后表现出的典型特征。元杂剧完成了说唱艺术到戏曲艺术文类转化的第一步,即代言化,但说唱的痕迹依然很重。元杂剧以唱为主,而唱就是从说唱艺术即诸宫调中继承而来的。“董解元《西厢》,为‘诸宫调’体……要知道元剧所用各牌名,都本于董词。如[点绛唇][端正好][斗鹌鹑]等等,哪一个不是董词里的?……可见董词,才是元剧的嫡亲祖父母。”[5]据王国维对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所列三百三十五个曲牌进行的研究,元杂剧的曲调不少是直接来自诸宫调、大曲等说唱艺术。而许多说唱作品就直接被创作为戏曲,最著名的就是王实甫改编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而创作的《西厢记》。说唱成为戏曲唱、念、做、打的一个有机部分之后被戏剧化,由剧中人物各自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对他人和事件的看法。受说唱艺术的影响,“叙述”为主导的元杂剧在进行人物代言时文体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犹如作者叙述故事,强调的话语功能是指称功能。
中国戏曲是一种融合了唱、念、做、打的歌舞剧形式,因此,以何种音乐为载体,用何种与此相应的歌词形式作为戏曲文学的表现基本,是戏曲形式的决定因素。戏曲家接受了曲的音乐体系,将之作为元杂剧的音乐载体,而其文体形式散曲,由于功能的多样化,也成为戏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元初散曲和戏曲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所用曲牌已成规模。由于散曲相比诗词有不同的文体风格,更为平易通俗,直率自然,多用口语俗语,这种活泼生动的文体风格更能为戏曲所用。散曲节奏富有变化,如对仗的多样化,多用排句,可加衬字,为戏曲人物的塑造、戏曲场景的烘托、故事情节的阐述提供多种选择。同时散曲的文体功能多样,既可以抒情,如关汉卿的《不伏老》,又可以叙事,如马致远的《借马》;可以描写景物,如张可久的《湖上晚归》,又可以议论,如刘时中的《上高监司》。
在说唱文学影响下,戏曲文学以“叙述”作为主导话语模式,那么指称功能即最为常用的话语功能。指称功能主要指向对象,观众被叙述描写对象的语言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符号不再是传播工具,而成为传播的对象,增加符号本身的吸引力或美感力量,清辞丽句,韵律节奏,语言的音乐化就成为必要的手段,言语的诗歌功能突出了”[6]。这是中国戏曲以诗歌为主要文体,语言多为韵文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国以诗歌为正宗的文学传统,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双重影响。戏曲语言不但体现了抒情性、形象化和精炼性,而且还具备了音乐上的节奏和旋律。对于西方戏剧来说,所谓诗化语言实际指的是具有诗意的语言,因此在文体上,用不用诗体关系并不大,诗剧在戏剧发展过程中反而因矫揉造作而被淘汰。但中国的戏曲,无论是曲牌体的杂剧、传奇、昆曲,还是板腔体的京剧,其语言形式在很多情况下是歌唱式的,唱词自不必说,宾白也具有吟诵韵味。因此中国戏曲语言特别强调声律。正因如此,中国戏曲理论大多是对“声”“腔”、格调和节奏的总结规范,而很少提到情节等要素。中国戏曲语言的诗化、音化是对生活中自然语言的高度艺术加工,用外在的诗形(格律、节奏、声调、韵律)来框定内在的诗意,用外在的“美听”来反映内在的意蕴,最富诗意的地方往往是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三、戏剧理论与戏曲理论
(一)西方戏剧:“摹仿说”—“逼真”—“真实”
无庸置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代表了希腊戏剧理论的最高成就,其中的戏剧理论被人们奉为圭臬,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一盏明灯。“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诗学》逐渐成为西方戏剧理论的第一经典;现实主义戏剧理论和实践在剧作与演剧两方面全面实现了《诗学》的理论并发挥到极致。”[6]254那么,《诗学》的戏剧理论体系是如何开创西方戏剧以散文体为主的文体观呢?
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建立在“摹仿”的概念上。亚氏认为,诗人的“摹仿”是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比历史更加真实。“摹仿”的概念总括了亚氏对各种艺术的看法,“诗”(包括史诗和悲剧)是对现实的摹仿,而节奏、语言、音调、歌曲等是摹仿的媒介。对于悲剧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摹仿”所体现的现实内容,也就是情节。为使情节显得真实可信,摹仿的媒介就极为重要。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亚氏认为悲剧中短长格代替四音部长短格是不可避免的。“在所有格律中,短长格是最适合于讲话的,可资证明的是,我们在相互交谈中用的最多的是短长格的节奏,却很少用六音部格——即使偶有使用,也是因为用了不寻常的话调之故。”[2]49可见,西方戏剧理论从《诗学》就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实生活的语言——散文是戏剧摹仿现实的最好媒介。“摹仿”的核心概念使《诗学》中戏剧创作理论以“真”作为根本的美学原则。在论述悲剧的情节时,亚里士多德提到了“美”的诸种构成要素:各部分的排列要适当,体积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戏剧的情节长度也有规定,戏剧完美的布局要有一个单一的结局等,这些要求都是为“真”服务。另外,亚氏把戏剧与史诗严格分开,认为戏剧是人物行动的“展示”而不是用“叙述”。在“以真为美”原则指导下,人物的行动是现实生活中的行动,人物的对话是现实生活中的对话,散文作为文体选择和“展示”作为话语模式在西方戏剧中相得益彰。
文艺复兴时期,卡斯特尔维特洛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诠释》从观众在观看时的心理状态这一角度出发,用“逼真”这一概念重新诠释了“摹仿说”。“戏剧摹仿的意义不在真实,而在‘逼真’,戏剧要对人们从命运得来的遭遇做出逼真的描绘,只有表现得‘逼真’,才能让观众信服并从中获得娱乐与教益。”[7]在戏剧文体方面,卡氏认为戏剧体是用事物和语言来代替原来的事物和语言,而叙述体只是用语言来代替事物。戏剧体也就是“展示”侧重的是再现真实的生活,那么语言形式也要尽可能真实。为了“逼真”地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与人物,散文就成为理想的文体。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布瓦洛的《诗艺》同样以“逼真”为戏剧形制的核心,而戏剧内涵的核心则是“理性”。他认为艺术应该追求“一般的真”,也就是“逼真”,这是道德价值统摄下的社会伦理秩序的真实。《诗艺》开篇布瓦洛就对辞藻的文从字顺,表情达意进行了严格要求。布瓦洛等新古典主义文论家反对剧作者用光怪陆离的诗句来炫耀文才,认为内容所包含的情理,如高贵、荣誉、尊严等要远远重要于文章的文采。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戏剧名作十分注重用人物之间的对话冲突来推动剧情的发展,引领剧情高潮的到来。逼真的散文式语言能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也能够更好地实现新古典主义戏剧道德教化的功能。
西方戏剧散文化倾向在古希腊戏剧发展过程中已经初露端倪,但散文彻底代替韵文则是19世纪现实主义戏剧发展的结果。“真实”是19世纪现实主义戏剧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又可以分为客观真实和艺术真实。19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实证主义哲学流行,使西方剧作家相信人类具备认识世界的理性能力,并能够通过戏剧创作反映现实。当时出现了社会问题剧,剖析社会问题,关注现实生活。如易卜生《玩偶之家》、萧伯纳的《鳏夫的房产》。而戏剧中“艺术真实”则缩小世界与舞台的距离,将舞台变作世界,这就是幻觉剧场。在这里,古典主义的“理性之真”已经让位于“自然之真”,这为舞台艺术的拟真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语言作为戏剧表演的重要媒介自然要为“客观真实”服务,需与现实中的语言相仿,这样才能成功地在舞台上制造“真实的幻觉”。
(二)中国戏曲:礼乐传统—诗性因素—曲学
中国戏曲形式之所以偏于歌唱表演,是因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强大的礼乐传统的影响。中国文艺实践从一开始就是诗、乐、舞紧密结合的。上古时期艺术尚未从祭祀仪式的母体中脱离,诗、乐、舞三者中,乐占最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国古代所讲的“乐”常常不是单指音乐,而是包括了诗、乐、舞三者。这种以“乐”为核心的三位一体观,使中国的诗歌一直与乐难以分离。孔子的美学思想主要特征是美与善的结合,而所谓“善”的具体内容,是他的仁政德治和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礼记·乐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美学著作,由于诗乐关系极为密切,实际上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乐记》中的“乐”是亦是指诗、乐、舞三者一体,对于三者对政治的作用也提出了要求:“治世之音安亦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可以说,礼乐传统是统治阶层试图通过教化这一人为手段使日益分离的个体统一在一起以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而产生的。诚然,宋元戏剧发展与繁盛离不开城市商业文明的繁荣,诞生于勾栏瓦舍的杂剧、南戏并非一味遵循来自儒家道德的礼乐传统。但作戏曲理论总结的文人却是有意无意地受礼乐传统的影响。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观念无疑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特性,戏曲艺术也不例外。中国戏曲的表演形式,如舞台语言、剧本结构、唱腔处理都沉浸在诗、乐、舞的精神状态中,带有浓郁的诗性、音乐性和舞蹈性。
中国古典戏曲美学具有写意性特点。戏曲美学的写意性和抒情诗抒情言志方式是相通的。所以,当剧本中的文字符号变为舞台语言时,便具有了诗的因素,在注重形象性、抒情性的基础上,表现出音乐性和节奏感。中国戏曲如《长生殿》《孔雀东南飞》原本就是根据古代著名的诗篇改编的,它们自然具有从母体脱胎遗传的诗意。而《西厢记》《牡丹亭》等又都是作者以诗人的目光观察生活,字斟句酌,写出了诗意盎然的剧本。剧本中诗化的语言还体现在充分的抒情和精炼含蓄二者的统一。诗的语言要求简洁、浓缩,但必要时却不惜笔墨,目的都是恰到好处地表现人物的情感。中国戏曲许多抒情唱段都是以诗化的语言表达的。宋元阶段,随着戏曲的繁荣出现了相应的理论,这些戏曲理论就是《唱论》《中原音韵》《青楼集》《录鬼簿》等。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并未提出“戏曲”这一概念,而是强调“歌”的概念。这里的“歌”实际上指的是宋元戏曲中的“唱”,还提到了戏曲一直极为看重的“声”和“腔”。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确提到了“戏文”与“传奇”的概念,不强调戏剧的整体情节结构,而是强调戏曲的唱念呼吸等演唱技巧。《青楼集》与《录鬼簿》则突出戏剧艺术的表演与创作。从这些戏曲理论可以看出,中国戏曲理论从源头开始就较为强调以唱为主的戏曲表演。《唱论》强调“歌”“曲”“声”“腔”,《中原音韵》强调“乐”,《青楼集》核心概念为“乐”与“色”,《录鬼簿》则是“乐府”“乐章”。虽然这些理论有不同的核心概念,但可见这些理论最看重的乃是以“乐”为中心的综合性表演形式。继元代戏曲理论后,明代的戏曲理论更加强调戏剧中“乐”的因素——曲。明确标明“曲”的戏剧理论就有《曲论》《曲藻》《曲律》等,戏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词曲理论。正本清源,中国戏曲一开始就具备“乐”与“诗”结合的重要特色,二者相携相生,中国戏曲最终确立了具有形式美学特征的曲学理论。直到清代的李渔才在《闲情偶寄》中独辟蹊径,提出“结构第一”的创作理念,但他同时也没有忽视词与曲的创作。
四、结语:戏剧中的诗意
中西戏剧曾经站在同一个起点,最终却在历史与逻辑的进程中分道扬镳。语言上西方戏剧选择了散文,文体是更接近生活的散文体;而中国戏曲却一直追随诗、舞、乐三位一体的传统,诗体成为表情达意、展现作者文采的最佳选择。对于西方戏剧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情节之真来反映现实,匡正时弊;而中国戏曲却更看重通过表演之美,辞藻之华来吸引观众,给予观众美的享受。
但二者将再无交集吗?哈贝马斯指出体系一旦完备就会封闭,封闭即老化的开始,解决的途径是与另一参照系相互比照,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他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以此突破原体系限制,容纳其他因素而得到更新。这正是中西戏曲戏剧建立跨越差异的共同诗学的必经之路。事实上,即使再强调“真实”,艺术怎可能是现实的复制品呢?戏剧并非映照现实的一面普通镜子,而是焦点集中的透镜,透过这面镜子,剧作家将现实生活的场景凝聚提炼,并寄予自己的思想。西方戏剧语言文体散文化的背后,诗意的核心依然存在。西方戏剧最终选择的并不是生活中的散文,而是富有诗意的散文。中国戏曲注重语言的诗性特征,但由于诗化语言过分精雅,过分注重辞藻,常使戏曲艺术难以被普通或当代观众所接受。清代李渔就对《牡丹亭》的语言提出过批评,认为只可作文字观不可作传奇观。因此,中国戏曲的剧情,大多选择人们较为熟悉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内容家喻户晓而不会因诗化语言的隔阂而降低戏曲艺术的审美效果。一味的诗化只会物极必反,中国戏曲也应与时俱进,选择一种诗化但不拘泥于格律的语言来实现戏曲诗意的传承。戏剧中诗意或许正是中西戏剧戏曲殊途同归的交集点。
[1][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4.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英]阿·尼科尔.西欧戏剧理论[M].徐士瑚,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95.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9.
[5]吴梅.吴梅戏曲论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194.
[6]吕薇芬.杂剧的成熟以及与散曲的关系[J].文学遗产,2006,(1):295.
[7]伍蠡甫.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61-262.
〔责任编辑:曹金钟孙琦〕
2014-12-17
俞航(1987-),女,浙江绍兴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J804;I053
A
1000-8284(2016)09-01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