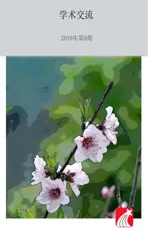欣欣子序是《金瓶梅》的宣言书
2016-02-27孙志刚
孙志刚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 哈尔滨 150025)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明清文学专题·
欣欣子序是《金瓶梅》的宣言书
孙志刚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 哈尔滨 150025)
在《金瓶梅词话》的序跋中,第一篇就是欣欣子所写的《金瓶梅序》。虽然这篇著名的序言被后世学者一再提及和引用,但多数学者仅仅是把它当成研究《金瓶梅》的重要史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欣欣子这篇序言是极为重要的,它很可能就是作者笑笑生的自序,而且在这篇序言中表现出写作者很多新的文学理念和对人生深刻的思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序言就是《金瓶梅》的宣言书。
欣欣子;《金瓶梅序》;宣言书
在《金瓶梅词话》卷首的序跋中,第一篇序言就是欣欣子所写的《金瓶梅序》。虽然这个欣欣子同《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一样是一位无可考证的人物,但从文字风格上看,欣欣子很可能就是作者笑笑生本人,因而这篇序言很可能就是作者的自序,故它对《金瓶梅》的研究来说应该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然而,尽管欣欣子这篇序言在“金学”研究中颇为著名,学者们在有关《金瓶梅》的论文中对这篇序言也不断加以引用,但至今为止尚未见到一篇专门对欣欣子这篇序言进行解读的文章。为此,本文将尝试对这篇序言作一个较为详尽的阐释。欣欣子这篇序言不仅说出了此书在叙事内容和创作方法上的变革,同时指出了作者的叙事目的和潜在读者,并赞美了此书叙事技巧和语言风格的高超之处,此外它还为作者写丑进行了辩护。尤为重要的是,欣欣子在这篇序言中写出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而这些很可能就是笑笑生本人的思想。在这些人生的感悟和思考中蕴含着儒释道三种思想,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阐释《金瓶梅》的思想主旨会有所帮助。值得一说的是,《金瓶梅》的序和跋有多篇,相比之下,其中唯有欣欣子的《金瓶梅序》对《金瓶梅》的分析和阐释较为深刻和透彻,其他只是泛泛之谈而已。因此,本文认为欣欣子的这篇序言可以说是《金瓶梅》的宣言书。
一、“寄意于世俗”的深远意味
欣欣子在《金瓶梅序》中所写的第一句话是:“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世俗,盖有谓也。”[1]1在此句话中,欣欣子首先交代了此书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这是目前我们对《金瓶梅》一书作者所能知道的唯一信息,因而学者们对这句话中的这一点是极为关注的。然而,本文认为欣欣子在这句话中除介绍作者的姓名之外,其更为重要的信息是指出了笑笑生具有创新性的写作方式——“寄意于世俗”,而对这一点学者们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欣欣子所说的“寄意于世俗”,指明《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是以书写现实生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寓意的,这一点实际上关涉整部《金瓶梅》在写作内容和写作方式上的总体特征。欣欣子把这句话放在整篇序言的第一句中,可见他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对此我们将从几个角度来加以分析。
首先,欣欣子的这句话揭示出了《金瓶梅》在写作内容上的重大变革,同时也说出了《金瓶梅》与其他小说的区别所在。这是因为《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其所书写的都不是真正世俗性的现实生活。如《三国演义》所写的主要是东汉末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水浒传》所写的主要是绿林豪杰聚义江湖。这些小说中所写的内容,要么是历史故事,要么就是英雄传奇。而且这些故事是现实生活中很难见到的事情,与世俗生活、与正在进行着的现实生活无直接关系,而《金瓶梅》所写的恰恰是世俗生活本身,其故事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并且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姑且不论《金瓶梅》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单就此书能还原现实生活,写出一个非常有质感的原生态生活状态,这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新,在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欣欣子在这篇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金瓶梅》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寄意于世俗”,这说明他抓住了《金瓶梅》的实质。其用意在于指导读者在读这部长篇小说时,既不能像读《三国演义》那样追求故事性,也不能像读《水浒传》那样注重传奇性,而是要在此书所写的平淡的世俗生活中咀嚼出意义。我们不能忽视《金瓶梅》书写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这是中国长篇小说在书写内容上的一次革命,也是中国长篇小说由古代转向现代的一个标志。在此,我们要借用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观点来阐释这一变革的意义所在。巴赫金是研究西方长篇的专家。他在研究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时指出,西方的文学体裁可划分为史诗、传奇、小说三种。其中,史诗和传奇都属于古老的体裁,因为它们所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或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它们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巴赫金认为西方的小说是一种新兴的文学表现形式,它诞生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与史诗和传奇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小说所书写的是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巴赫金认为,由于小说所写的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拉近了人们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从而使现实生活本身变成人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和思考的对象。而小说在叙事内容上的这种变革无疑是文学中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2]
如果我们以巴赫金的小说理论来看《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区别,就会发现它们的区别恰恰就在于书写内容。《三国演义》所写的是历史故事,类似于西方的史诗;《水浒传》所写的是英雄传说,类似于西方的传奇故事;而《金瓶梅》所写的是现实生活和世俗人生,因而它才是巴赫金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正是从《金瓶梅》起,中国的长篇小说才开始告别了史诗和传奇式的叙事方式,从而走向对日常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关注。而《金瓶梅》这一成就的取得就在于它是“寄意于世俗”的。
其次,欣欣子说《金瓶梅》“寄意于世俗”,实际上也指出了《金瓶梅》在写作方式上的创新。因为《金瓶梅》之前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世俗的东西。在这些作家眼里,世俗生活是平庸的、乏味的、混乱不堪的、缺少戏剧性的、缺少崇高和美感的,因而这些作家在创作中尽量避免世俗,而去追求人物的传奇性和故事情节的戏剧性。由于《金瓶梅》“寄意于世俗”,因此它在创作方式上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第一,由于作家在创作时其着眼点就是世俗生活本身,为了让平庸的世俗生活变得鲜活起来,从而对读者产生吸引力 ,作家必须善于捕捉世俗生活中的戏剧性。第二,由于书写内容本身的乏味,作家必须靠精细的描写,才能使世俗生活变得有趣味。第三,作家必须要挖掘出世俗生活本身的意味,必须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否则他所写出的内容只能是流于世俗。因此,“寄意于世俗”对作家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欣欣子在“寄意于世俗”这句话之后,提醒读者注意此书是“盖有所谓也”,其意思是让读者注意到笑笑生这部世俗小说背后的意义,即关注这部小说自身的思想价值。
其三,欣欣子说《金瓶梅》“寄意于世俗”,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这句话把《金瓶梅》与晚明时期的心学运动联系起来了,突显出《金瓶梅》所处时代的特征。《金瓶梅》诞生于晚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中,而这个时代在思想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心学运动,而心学运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走向世俗。欣欣子说《金瓶梅》“寄意于世俗”显然是暗示此书与心学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晚明时期的心学运动发起于王阳明,壮大于王隆溪和王艮,在何心隐和李贽时期达到顶峰。心学运动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儒家僵化而死板的道德伦理宣教方式,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人的良知和道德。晚明时期一些激进的思想家认为穿衣吃饭就是道,偏离日常生活的所有道德宣教都是虚假的、骗人的,因此在晚明时期世俗的日常生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晚明时期的思想家们正是以日常生活为标准,来对中国以往所有的道德规范进行新的审视和批判。这些思想家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人性才是正常的人性,他们以此为根基,对人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义。比如泰山学派的王艮就提出人的身体是第一位的,要明哲保身。李贽更是大胆地提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没有自私就没有人的存在。可以说,晚明时期的心学家们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具有哲学本体论的作用。这正如李泽厚所说,晚明时期的人们发现了生活。[3]而欣欣子说《金瓶梅》“寄意于世俗”,其潜在的含义是指出了《金瓶梅》对世俗生活的书写是与晚明时期心学运动遥相呼应的。
二、写作动机与潜在的读者
欣欣子在《金瓶梅序》中谈及此书的写作动机和潜在的读者时说:“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1]1*本文以下有关欣欣子序言的引文皆出自梅节校订,陈昭、黄霖注释的《金瓶梅词话》(香港,1993),不再另注。
在这段文字中,欣欣子指出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因此人最容易被情感和欲望所困扰。在人群中,“上智者”对七情六欲有着与生俱来的化解能力,“中智者”有着可以排解七情六欲之苦的理性精神,而唯有“下智者”既没有化解七情六欲的心胸,也没有诗书情趣可以消遣,所以这些人最容易困于七情六欲之中,以至很少有不生病在身的,而笑笑生写《金瓶梅》就是为这些人服务的。如果我们说不受七情六欲困惑的“上智者”是圣人,能控制七情六欲的“中智者”是贤人,而“下智者”实际上就是生活中最平凡的人,即芸芸众生,而笑笑生作《金瓶梅》就是为解决这些人的精神痛苦。
为“下智者”而写作可以看成是《金瓶梅》的一个突出亮点。任何文学作品都有潜在的读者,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实际上是与他心目中潜在的读者进行对话和交流。《三国演义》的潜在对话对象是帝王将相,因此它所说的是如何做一个贤良的仁爱之君;《水浒传》的潜在对话对象是江湖义士,它所说的是如何才能身在江湖而情在朝廷;而《金瓶梅》的潜在对话对象是平凡的庸人,所说的是庸人们如何才能解除七情六欲的困扰,因此《金瓶梅》的潜在读者更具有普遍性。在《金瓶梅》中,我们发现笑笑生所写的这些庸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穷人,而是中产阶级,即诸如西门庆这样的有产者。或许有人会以此为借口说这部作品没有人民性。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晚明时期最显著的时代特色恰恰是商人阶层的兴起,能与帝王将相、江湖侠士分庭抗礼的也是这个阶层。他们在本质上属于市民阶层,在财产上属于中产阶级。这个新兴的阶层是晚明时代商业文化的产物。由于这个阶层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他们才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提出自己的要求,才能有权力去追求一种与传统文化不同的生活。而作为下等的贫困人民还没有成为一个显性的阶级,还不具有作为阶级的独立性。因此,笑笑生关注于中产的市民阶级是时代的必然,而作家书写这个阶层并为这个阶层解决精神上的疾病,恰恰说明作者对社会的洞察力是极为深刻的。
凭借财富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中产阶级,与生于官宦之家的贵族甲胄,与靠科举走向仕途而成为国家官员的书生学子截然不同,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相信财富的力量,相信自身的能力,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财富从而去过如意的生活。对他们这些人来说,求得财富就是其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享乐人生就是其生活的最高理想。因此,这个阶层也是最容易被“物化”的阶层,也是最容易沉迷于酒色财气而不能自拔的阶层。笑笑生笔下的西门庆就是这个阶层最为典型的代表。笑笑生对这个阶层人的思考是极为深刻的。笑笑生认为他们对财富的追求是有合理性的,因而他对西门庆这个人物是有赞赏之处的,称其为大丈夫。但是,人靠什么来换取财富,这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伦理问题,而人应该如何利用财富更是一个思想境界问题。因此,笑笑生对西门庆发家致富的方式和纵欲无度的生活方式又是批判的。笑笑生认为这些人陷入情欲与物欲之中实际上是一种苦,而他写《金瓶梅》的目的是让这些人从情欲和物欲的痛苦中摆脱出来。笑笑生所涉及的这些问题实际上至今仍在困扰着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仍有些人疯狂地赚取财富,纵情地挥霍财富,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而这就是财富对人的“异化”,就是财富给人带来的病态。这种对财富的崇拜就是人的异化,由于崇拜物而失去人性,这难道不是人最大的病态吗?马克思在19世纪指出现代社会的弊病就是人的异化,而笑笑生把这种异化称为“病”,与马克思的说法是一致的。因此,笑笑生写《金瓶梅》这部书来救治世人之病,这其中实际上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怀。
下智者的病在“心”。欣欣子指出《金瓶梅》是治病之作,而其所治之病恰恰就是人心之病,这与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不谋而和。王阳明认为人的病就在于其心里的“良知”被遮蔽了,而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去启发人的良知,修正人心。因此王阳明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欣欣子在序言中指出《金瓶梅》是医治心病之作,等于说《金瓶梅》暗合了王阳明的心学主张。
三、对叙事艺术的高度赞美
欣欣子序言中高度赞美了《金瓶梅》的叙事艺术:“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叙事最为复杂的小说,其线索繁多,不胜枚举。然而,笑笑生最为高明之处就是能让众多的情节线索环环相扣,一丝不乱,从而使全书成为一个浑然整体。举例来说,由于《金瓶梅》缺少五十三回到五十八回共五个回目,后人千方百计地补写,但所写的内容漏洞百出,难以与全书保持一致,正如沈德符所说,是鄙儒所作。这正从反面证明了《金瓶梅》内部情节的完整性。
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中结构完整如一者只有《金瓶梅》。这说明此书作者叙事水平的高超,也完全可以说此书的作者是一位巨儒和才子。有学者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书会才人,更有人说《金瓶梅》是集体创作,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从文本来看,《金瓶梅》的作者控制故事情节、书写人物的能力超人,如果不是一个才子所作,我们找不出任何其他解释的理由。
《金瓶梅》在叙事上的成熟和高超正如欣欣子所说,“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如果我们把诞生于中国16世纪的《金瓶梅》与西方同时期的名著《堂吉诃德》做一个比较,就会惊讶地发现,《金瓶梅》在叙事艺术上的成就是多么了不起。《金瓶梅》写了800多个人物,主要人物就有十几个,而《堂吉诃德》的主要人物只有两个。《金瓶梅》的故事情节复杂多变,但整齐划一,而《堂吉诃德》的故事情节简单而松散。可以说,《堂吉诃德》在艺术上与《金瓶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西方,能与《金瓶梅》相比的作品直到19世纪之后才出现,其代表性作家是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单从艺术角度来说,《金瓶梅》是一部在世界文坛上都堪称一流的小说,而这绝不是溢美之辞。我们一向说诗歌是中国文化中的精美之作,在世界文坛上没有能与之媲美的,其实《金瓶梅》作为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在同时期世界文坛上也是没有能与之媲美的。
在此,我们要注意到欣欣子说《金瓶梅》“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实际上是最准确地概括出《金瓶梅》这部长篇小说整体的艺术特征。如果这个欣欣子就是笑笑生本人,那么这句话就是笑笑生对自己这部长篇小说艺术技巧的高度肯定,这显示出作家对自己艺术才华的自信。而“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则表现出对小说娱乐性的肯定。小说从来就不是道德的简单说教,它担负着道德的使命,但它必须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出现。小说的教育功能是潜移默化的,是在一笑之后的欣然接受。从这简单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笑笑生是深谙小说美学之道的。值得一提的是,《金瓶梅》充满了讽刺和幽默,甚至被后人称为“笑书”,而在实质上《金瓶梅》所写的是人生悲剧。笑笑生能在人生悲剧里增加喜剧因素,这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是可以相媲美的,因为莎士比亚也是经常在其悲剧中加入喜剧因素的。此外,在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想到《金瓶梅》最了不起的艺术手法——反讽。这是西方现代小说才有的写作手法,而笑笑生早在16世纪时已经驾轻就熟地采用这种艺术手法了。这代表着中国长篇小说在叙事方法上的早熟。
四、为写丑辩护
众所周知,《金瓶梅》写出了生活中的丑,涉及俚俗和胭脂之气。所谓“俚俗”指的就是低俗之事,所谓“胭脂气”指的就是色情描写。这也是人们常常对《金瓶梅》诟病的两个方面。而欣欣子在序言中为作者写这些内容进行了辩护,他是如此说的:“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曰 :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在这段话中,欣欣子首先用“不然”二字否定了人们对作家的攻击。然后,欣欣子以《诗经》中的《关雎》为例,说明笑笑生为什么要写俚俗和胭脂气。欣欣子首先认为《关雎》也写了“低俗”之事,如它写男女之间的爱慕,但它能做到嘻乐于其中而不放纵,有一点小小的哀伤,但不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但是,欣欣子认为《关雎》所写的都是简单的情感,所以它才能保持这种“中和”之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荣华富贵生活的羡慕和追求是一种激情,因而人们很难不沉溺于情欲的放纵中,而人的欲望又是难以满足的,人们虽然厌恶哀怨,但哀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很少有人不为此而生病的。所以,作为一位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家,是难以保持《关雎》中那种“中和”态度的,作家写俚俗之事和胭脂气是必须的,非此不能反映现实生活本身。
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欣欣子看出笑笑生在对生活素材的选择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家在选择生活素材时,所寻找的是崇高和美,而笑笑生所寻找的却是生活中的丑。这句话也标志着笑笑生审美观念的转变,即由审美转向审丑,这使他更接近于现代小说家。笑笑生这种审美观念的变化有着重要意义。19世纪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美是单一的,而丑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在文学创作中要表现丑,要美丑互相对照,丑就在美的旁边。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更是重视丑在文学中的作用,他说:“我纵情于淫荡和放纵之中,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可写的东西。”[4]
至今,我们还不能明确地指出从何时起中国文学开始关注到生活中的丑,并大胆地主张表现丑,但从欣欣子的这句话中,可以确认欣欣子在为文学作品中写俚俗和胭脂之类的事进行强有力的辩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学中有关“丑学”的理论,因而有划时代意义。从根本上说,笑笑生的《金瓶梅》在创作之时所遵循的就是“审丑”原则。对笑笑生来讲美是虚幻的,而丑才是最真实的;写美是理想主义的,而写丑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文学在19世纪之后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作家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19世纪之前西方作家的创作是为了审美,而在19世纪之后西方作家发现了“丑”这个无比丰富的天地,于是写作的内容就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因此,处于16世纪的欣欣子能在《金瓶梅》的序言中为笑笑生写丑进行辩护,这说明其创作理念具有现代性。
五、对语言之美的赞美
欣欣子不仅说出了《金瓶梅》在审美观念上的变化,而且把此书与同时代作家做了比较,指出《金瓶梅》在文笔上的优美之处:“吾尝观前代骚人,《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
在这段话中,欣欣子论述的是笑笑生创作中的语言问题。欣欣子认为以往的作家在文笔上的缺点是“语句文确”,即呆板、呆滞,缺少变化之美。而《金瓶梅》所用的是“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能“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在这里,欣欣子对《金瓶梅》语言的赞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称其语言可以与“天浆”和“鲸牙”相提并论。
用“市井之常谈”和“闺房之碎语”来写现实生活,这是《金瓶梅》在写作艺术上的创举。而这一点也与王阳明在心学运动中所提倡的知识分子语言通俗化密不可分。王阳明告诉他的学生说,你向小商小贩讲心学,就不能用文绉绉的语言,必须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否则没有人会理你们。在王阳明的倡导之下,晚明知识分子的语言开始了一个“由雅变俗”的转变,甚至有很多大知识分子以俗为美,大俗即大雅。
《金瓶梅》的语言是日常生活中最为鲜活的语言,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是这部小说最为优美之处,很多学者最喜欢的就是《金瓶梅》中的“老婆舌头”,闲言碎语。然而,有学者却认为《金瓶梅》这种俗语式的表达方式说明其作者的学问不高,是位俗人,这是对此书的严重误读。要知道,正是因为《金瓶梅》用语的这种大俗,我们才有理由确定此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位文化修养极高的大儒。因为在这个时代,越是大儒,越显示其大俗之气,这是一个人率真之气的表现,而在晚明这个时代里人们是以率真为美的。相反,只有那些“馊儒”才满嘴的书卷气,咬文嚼字,被人耻笑,就像《金瓶梅》中西门庆所聘的文书温辟谷一样,是被人嘲笑的对象。
在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找出更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欣欣子就是笑笑生。因为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这句话带有自谦之意,说的是此书的文笔虽比不上古人,但是有理趣,还是很可以观赏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此序的作者真的是笑笑生之友,他没有必要在高度赞美笑笑生之后,又把话拉回来,说此书的文笔与古人比还有一定差距。因为这样说,与上句的赞美之辞是矛盾与不合逻辑的。显然,只有笑笑生自己才会在高度赞美自己的文字之后,谦逊地说,自己与古人比还有不足之处。所以,这句话反而证明这篇序言是笑笑生自己所作。
六、对人生的感悟
欣欣子在赞美《金瓶梅》的语言后,再次强调了《金瓶梅》对人生的教育作用。他相信《金瓶梅》这部书一定会对世道起到教化作用:“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而之所以能起到这个作用,就是因为这部书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在这句话之后,欣欣子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这种思考和感悟很可能就是笑笑生本人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因而它更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欣欣子说了对性的看法:“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有不为所耽。”在这里,欣欣子指出人们对性既好又恶的双重态度:“好之”是因为它是人的本能,“恶之”是因为它是本能,人难以控制它,它有着巨大的破坏力。正因为这种矛盾态度,作为常人没有不受性困扰的。这句话实际上也表现出欣欣子对性的困惑,因为他认为人非圣贤,没有人可以不受性的困扰,他自己也包括在其中。我们注意到在《金瓶梅》中作者对性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如作家对李瓶儿的性意识是有同情之处的,但作家对性的破坏力更是深有顾忌。
我们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在对人生进行思考时,欣欣子要把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才说富贵对人的诱惑。我们认为,《金瓶梅》所写的主要对象是晚明时期兴起的中产阶级,而作为当时发家致富的中产阶级来讲,享乐人生的第一快事就是放纵自己的肉欲,因此性的放纵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欣欣子把性放在第一位来思考,主要是针对当时的这种社会现象有感而发。
欣欣子思考人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富贵善良”问题,认为它“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在这里,富贵可摇动人心,使人失去最朴素的情怀,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为什么“善良”也会动摇人心,激荡人心呢?本文认为这里的富贵所指的是人们在物质方面的追求,而“善良”所指的并不是人的善心,而是泛指人的情感方面,即人的温情,而这种温情同样会使人心浮动,失去最朴素的情怀。对性的追求使人“耽于情欲”,对“富贵和善良”的追求使人失去本心,虽然这二者都属于人间的乐事,但一旦这种追求走向极端,必将给人带来悲剧。而欣欣子认为这就是人生的定数:“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軃,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
在这里要注意,欣欣子并不是反对人对快乐的追求,而是反对把这种追求推向极端。在这句话中“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与“金屏绣褥,何美丽也”及“锦衣玉食,何侈费也”都代表着极为富贵的生活,而“鬓云斜軃,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所代表的是极端放纵的情欲。欣欣子认为一旦在这两个方面达到极端,乐极必生悲:“如离别之机将兴,憔悴之容必见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所不能无也。患难迫切之中,颠沛流离之顷,所不能脱也。陷命于刀剑,所不能逃也;阳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
从这段文字看,欣欣子认为人生总体上是悲剧性的,他认为人生的转换只在瞬息之间,要避免人生悲剧就是避免对极乐的追求。在此,欣欣子实际上是提出一个应该如何去把握人生尺度的问题,即不能过分追求人的情欲和物欲,而是要持盈慎满。这种观念可以看成是《金瓶梅》重要的主题之一。
由于人对富贵和情欲的极端追求,人就会走向作恶的境地,而作恶者就更难逃因果报应:“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如果说,在上一句作者所说的是人生无常,而这一句中他所要说的是在无常的世界中,一切皆是因果相报,而人是脱不出循环之机的。在此,欣欣子把对人生的思考提升到道德伦理这一高度上,认为这是天道循环。所以,作恶的人得到恶果,就像“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欣欣子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与佛家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是一致的。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因为《金瓶梅》中就有着浓厚的佛家思想,假如欣欣子就是笑笑生,那么在他的思想中佛家思想应该是占主导地位的。
人生既无常,而因果相报又是丝毫不爽,那么,如何既能逃避人生的无常之苦,又能不陷入因果循环之天机呢?对此,欣欣子提出一个合理化建议,即符合“天时”:“和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何谓“天时”?天时本是道家的概念,指的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出自《易经》中《易·乾》:“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这里“天时”是一个抽象概念,指的是先天存在的“道”,它类似柏拉图所说的绝对理念,也类似希伯来宗教中的上帝,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而面对它,人只有敬畏和顺应。“天时”是一个形而上的本体,它是宇宙之道,也是人生之道,而人对这个道的接近,只能采取顺其自然的方式。从天时观念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出欣欣子是具有道家观念的,而欣欣子如果是笑笑生的话,这位作家也是应该有道家世界观的。
在这句话中同样也包含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因为符合“天时”者最终所得到的利益是:“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而这一切都是对现实世界中人的关怀,并不是道教所讲的出世和逍遥,因而,合天时的最终意义是落在现实生活层面上,而儒家思想就是关注现实的人生。
从欣欣子这一长段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来看,其思想是包含儒释道三个方面的,其中:佛家说人生无常,因果报应,而道家说的是顺天时而不违。最终,儒家说的是子孙悠远,安享终身。
在欣欣子序言的结尾处,作者感慨道:“人之处世,虽不出乎时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其意思是说:人生在世,虽然是在时运中起伏,人自身是难以控制的。然而,不要说你一直会吉星高照,只要你不经受凶祸,不蒙受耻辱,你就是幸运者了,或者说你就是幸福了。在这句话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欣欣子对人生所持的是悲观主义看法,他认为人生叵测,极易陷入灾祸和羞耻之中。
在序言的终结处,欣欣子说道:“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谓也。”其意是说,我说了这么多,这就是笑笑生作《金瓶梅》想说的意义吧。
总之,欣欣子所写的《金瓶梅序》是目前我们研究《金瓶梅》最为重要的资料,这一方面是因为此序极有可能就是作者的自序,不可不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序言中包含着极多有关《金瓶梅》的信息,可以说它是我们研究《金瓶梅》的第一手资料。它包含作者的写作动机、理想的读者、写作的手法、审美观念的变革、语言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和三教合一的世界观。此外,它还在蛛丝马迹之间透露出《金瓶梅》与心学运动的关系,为我们探讨《金瓶梅》所具有的时代精神打下了基础。自《金瓶梅》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忽视《金瓶梅》与心学运动之间的关系,而《金瓶梅》虽诞生于晚明之际,但它与晚明浩浩荡荡的心学运动却毫无半点关系,成了悬浮于时代精神之外的小说,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是我们对《金瓶梅》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肤浅之处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1][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梅节,校订.陈昭,黄霖,注释.香港:梦梅馆,1993.
[2][原苏]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169.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1.
[4][法]福楼拜.福楼拜全集(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43.
〔责任编辑:曹金钟〕
2016-07-30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金瓶梅》中的儒释道精神及其在文本中的叙事作用”(11B048)
孙志刚(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206.2
A
1000-8284(2016)09-015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