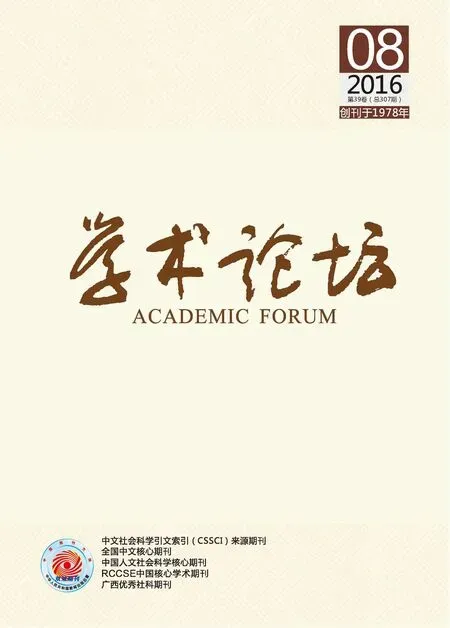刑事审判话语中的预设现象研究
2016-02-26向波阳李桂芳
向波阳,李桂芳
刑事审判话语中的预设现象研究
向波阳,李桂芳
已有文献对机构话语尤其是法庭审判话语中的预设现象鲜有讨论。真实的法庭审判现场录音转写语料显示刑事法庭审判话语中的预设现象普遍,预设主体为法官、公诉人、诉讼代理人、辩护律师、被告人。预设主体在庭审中的预设性话语呈程序阶段性分布,具有个体频度差异性特征。研究表明,刑事审判话语在庭审五个阶段中的法庭调查阶段预设出现最频繁,其次是法庭辩论阶段,审前序列、被告最后陈述和法庭判决阶段没有出现预设。个体差异性方面公诉人话语预设频度最高,法官、诉讼代理人、辩护律师、被告预设频度依次递减。庭审参与各方话语行为的目的性和策略性是预设出现的主要原因。
刑事审判话语;预设;特征;原因;策略;目的
一、引言
“预设”概念首先由Frege于1892年提出[1]。预设从命题的逻辑-语义定义[2]到话语的语用解释[3],其学科归属一直以来在学界颇有争议。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热烈讨论,“语用预设”概念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
Stalnaker首先使用语用预设这个概念,他认为:说话人在一定语境中陈述了一个命题,其本人假设或者相信这个命题,并且假设或者相信听话人(或者观众)也假设或者相信这个命题,说话人同时假设或者相信听话人(或者观众)知道他的这些假设或者信仰[4](P447)。由此可以看出,“语用预设要求言者和听者具备共享信息或者共享知识”[4](P451)。
以Stalnaker为主要代表的国外“语用预设”学者关注的是日常会话中的预设现象,没有涉及机构话语①尽管文献中有很多类似“你什么时候停止打你妻子的”这样含有强烈预设的法庭问话的例子,但研究都不是基于真实庭审语料。。以汉语语料为研究对象的国内文献同样很少涉及机构话语。
机构话语不同于日常会话,它侧重体现话语与文化、权力、身份等之间的关系。法庭审判话语是典型的机构话语,在法庭这个特定的语境里,参与法庭审判各方的话语策略性、目的性都十分明显。语料显示法庭审判话语中的预设现象十分普遍。本研究拟讨论中国刑事法庭审判话语中预设现象的特征和预设现象出现的原因,以期给司法语言实践提供启示。
本研究将预设定义为:说话人在一定语境中(本研究中的刑事审判法庭)通过话语假定听话者理解并相信他的意图。我们认可Stalnaker[4]的观点,即预设是说话人通过话语所传递的预设,而非话语本身的预设。语用预设纯粹是说话人行为,语境依赖性很强②区别于徐盛桓[5](P1)的语义-逻辑定义“预设是在句义中体现出或暗含着的某些客观事态、情况,作为句子所表述的整个事态、情况的事实基础”,这种研究视角认为“语言本身是自足的,不依赖于语境;而且,预设具有唯一性,不可能因语境的不同而暗示着不同的预设”。。
二、刑事庭审话语中的预设特点
(一)刑事庭审程序概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国刑事法庭审判通常包括以下五个阶段:
审前序列。审判长确认当事人到庭情况,对案由及参与诉讼各方情况和相关权利进行说明。
法庭调查。首先是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然后是举证和质证环节。
法庭辩论。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互相辩论。
被告人最后陈述。法庭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权做最后陈述。
法庭判决。
(二)语料介绍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是根据一例真实刑事案件庭审视频转写而成的,约十万字①视频网址http://fayuan.xinmin.cn/spzbhf/2013/11/26/22794996.html。笔者转写完该视频庭审记录后偶然发现网名为“高大全沙”发表于2014年1月11日的博文也有同案庭审的记录,参见http://blog.sina.com.cn/u/3541382241。同一个案件庭审的记录内容大致相同,这可以理解,但是笔者转写该语料的目的是做法庭话语分析,因此对该语料做了详细具体的标注,特此说明。。该案件的基本案情是:国内某大学寝室投毒案,被告人涉嫌以往饮水机投毒方式故意杀害舍友被提起公诉。案件审理在审判长主持下主要以问答形式进行。
(三)刑事庭审话语预设特点之一:预设现象呈程序阶段性出现
语料显示,庭审话语中的预设现象频繁出现,且呈现一些规律性的特点,首先是庭审预设性话语具有明显的程序阶段性。总体来看,庭审五阶段中法庭调查阶段预设出现频率最高,其次是法庭辩论阶段,其他三个阶段都没有出现预设。
分阶段略举数例:
法庭调查阶段:
(1)被告人xxx原系②下划线为预设触发语。xxx大学医学院xxx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公诉人用“原系”预设被告人现在不是xxx大学医学院xxx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2)因涉嫌故意伤害罪,由xxx公安局执行拘留。(“涉嫌”预设符合拘留条件)
(3)被告人xxx因琐事与被害人xxx不和,竟逐渐对被害人xxx怀恨在心。(“因”和“竟”预设被告人xxx的作案动机)
(4)被告人xxx决意采取投毒的方法杀害被害人xxx。(“决意”预设被告人故意杀人心理意图明显)
(5)公诉人举证暂时到此。(预设后面还有其他证据)
(6)被告人可以坐下。(“坐下”预设被告人之前是站着的)
(7)你当时把这个原液和注射器内的这个原液一起倒入了这个饮水机是吗?(预设被告人投毒的量之大,故意杀人的决心之大)
法庭辩论阶段:
(8)xxx自此以后才逐步地供述了投毒犯罪事实。(预设被告人xxx之前不合作,不交代犯罪事实)
(9)但被告人xxx一再辩称,他投毒的目的只是为了整一整xxx。(预设被告人不坦白,认罪态度不好)
(10)被告人xxx所投的化合物是有色暨伴特异性刺激嗅觉的液体,从xxx饮水时存在可能喝可能不喝。(辩护律师用“化合物”预设投进饮水机内的并非剧毒品)
(四)刑事庭审话语预设特点之二:预设频度具有个体差异性
语料显示,刑事庭审话语预设主体包括:法官(审判长和审判员)、公诉人、诉讼代理人、辩护律师、被告人。预设频率最高的是公诉人(157次),占了预设总数(238次)的近三分之二,其次是法官(44次),诉讼代理人、律师和被告人预设频度递减(依次为16次,14次和7次)。
各预设主体预设性话语举例如下:
公诉人:
(11)公安人员找过你几次啊?(公安人员找过你)
(12)而作为被害人xxx舍友的被告人xxx,在同年的3月底,却又一次因为一些事情受到了实习单位博士生导师的当众批评,被告人xxx向他人表达了抱怨的心情。(被告人之前被导师当众批评过)
法官:
(13)被告人,法庭再次提醒你一下: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大一点。(法庭之前提醒过被告)
(14)公诉人继续举证。(举证环节前面中断了,公诉人接着举证)
诉讼代理人:
(15)所以他这个罪轻我们认为怎么样考虑也不能成立,那我们还是坚持(2s)以故意杀人而且直接故意啊从重处罚。(我们的立场一直不变)
辩护律师:
(16)辩:那么根据你刚才的叙述等于是xxx先开了一个玩笑是不是?
被:是的
辩:(2s)那么请问你xxx当时的那个上述语言触发你什么想法?
被:就触发我想整他的一个想法
(辩护人预设“你——被告人”——当时是有想法的,这个想法是被害人的整人玩笑触发的)
被告人:
(17)审:你从204实验室取的注射器里面是原液吗?
被:应该是原液
审:这个原液是你们当时实验的时候(0.5s)直接从【用】注射器从那个瓶里面吸的是吧?
被:应该是的
(被告用“应该是”预设不太确定)
三、刑事审判话语中预设出现的原因
庭审话语是具有非常严格程序的机构话语,是策略性很强的目的性言语行为。庭审参与各方为了实现各自目的都策略性地使用语言手段。预设就是一种集策略性和目的性于一体的非常有效的语言手段。
前面的统计数据表明,庭审参与者中预设频率最高的是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或者准确地说是公诉团队——在庭审各阶段的话语机会最多,在起诉书中有不少预设(比如例(1)-(4),篇幅考虑,不再一一列举),起诉书宣读完后公诉人对被告人的讯问中也含有大量的预设(比如例(7)),举证环节也有不少预设(如例(5));两轮法庭辩论中公诉人除了以充分的事实和证据来证明被告有罪外,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现场进行道德教育,其话语量明显大于辩护律师。
公诉人讯问被告人的话语有个总预设:被告人的所作所为都已被掌握,都有证据证明,法庭上的讯问是希望其端正态度,老实交代(犯罪事实);所以所有的问话都指向一个目的:被告人有罪,而且罪行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应当依法受到严惩。比如:
(3)被告人xxx因琐事与被害人xxx不和,竟逐渐对被害人xxx怀恨在心。
(4)被告人xxx决意采取投毒的方法杀害被害人xxx。
(18)被告人xxx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必然造成xxx死亡的结果,而决意实施并希望这一结果发生,被告人xxx的这种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审判全过程中公诉人话语同时还有一个总预设:这是发生在高校校园内一起罕见的而又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恶性刑事犯罪案件,现场旁听的和各种媒体前的观众/读者/听众一定会同情并支持被害人。所以,公诉人利用这个机会感染现场旁听的和各种媒体前的观众/读者/听众,同时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6],这也是中国刑事法庭审判的一个特点。比如:
(19)被告人xxx的犯罪行为不仅摧毁了xxx及其家庭,而且也重创了我们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交往间的信任和互助依赖关系。
(20)要学会包容,真诚欣赏别人的成长与成功是我们可以从本案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
法官话语中的预设数量虽然仅次于公诉人,但审判长预设的频度远大于其他的法官,因为审判长是法庭程序的组织者,是话轮的分配者,其话语中的预设基本都是程序性的。这符合法庭组织者的身份。比如:
(6)被告人可以坐下。
(14)公诉人继续举证。
(21)审长:法庭希望你声音大一点,对着话筒声音大一点
原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虽然不同于公诉人,他们一方代表被害人/被害人家庭这个个体,另一方代表国家,但共同证明被告人有罪并让被告人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是双方的共同目的。所以,诉讼代理人话语预设的目的与公诉人是一致的。比如:
(7)你当时把这个原液和注射器内的这个原液一起倒入了这个饮水机是吗?
(15)所以他这个罪轻我们认为怎么样考虑也不能成立,那我们还是坚持(2s)以故意杀人而且直接故意啊从重处罚。
辩护律师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的话语也有两个总预设:一是被告无罪或者罪轻;二是因为是全国瞩目的案件,大家非常关心,现场旁听的和各种媒体前的观众/读者/听众一定会同情并支持被告。所以,辩护人利用这个机会感染他们[7],争取他们的支持①据悉一审前后确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同学及校友分别联名写信给法院院长意图影响判决,当然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比如:
(22)以上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官的行使权》,而起诉书的指控却叙述为“竟逐渐对xxx怀恨在心,被告人xxx决意采取投毒的方法杀害xxx。”
(23)上述被告人xxx的供述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不仅有助于公安机关搜集定罪证据,对于定案证据的搜集亦有重要作用,上述供述构成坦白,依法应当从轻处理。
相对而言,被告人话语中的预设较少,这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被告人在法庭上的地位:他是被审、被讯问、被调查的对象;第二,法庭问答多是有目的的问,有备而问,带着答案的问,所以被告回答问题的空间并不大。但是,在本案中被告也能用预设策略地实现自己的目的,为自己辩护。当然这与被告人受教育的程度有关。本案中的被告原是某大学成绩非常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其话语的目的性和策略性都非常强。这主要集中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公诉人、诉讼代理人、辩护律师以及法官都要对其进行发问。如下例中:
(24)我就(2s)有那么一个小时不知道做了什么,但是平静下来之后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药物。
当被问及上网查什么,被告人策略地回避了查询“剧毒化学品”这个词。又如在法官问到他看见被害人喝下被投毒的纯净水难受以后为什么不告诉被害人实情,被告人回答:
(25)我当时不认为这是难受。
回答明确地预设案发当时自己对结果的无知,意为“如果当时知道的话,我肯定会告诉他实情的”,以此来策略地辩解自己并无投毒杀人的故意。
四、结论
通过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刑事审判话语中的预设现象普遍。第二,刑事审判话语中的预设现象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庭审程序阶段性。集中出现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其中以法庭调查阶段最为集中,次数是法庭辩论阶段的两倍还多。二是预设主体个体差异性。预设出现的频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公诉人、法官、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被告人,其中公诉人话语中的预设最多,占了总数的近三分之二。第三,刑事庭审中预设现象的出现是有原因的:预设主体的预设性话语是具有目的性的策略行为,公诉人和诉讼代理人通常对被告人进行有罪预设,以客观的事实和充分的证据说服合议庭相信被告有罪或者罪重;相反,辩护人往往对被告人进行无罪或者罪轻预设,以对自己当事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说服合议庭相信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
本研究能够对司法语言实践提供一定的启示:庭审活动是通过话语来展开的,法律的严肃性要求庭审活动参与者必须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所谓言之有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话语中适当的预设可以策略性地帮助预设主体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不恰当的预设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会令自己落入尴尬的境地,比如:
(26)诉代:呃就是在你的学习生涯里面关于刑法的知识你了解多少?
被:(2s)基本上不了解
诉代:(2s)就在你看来话就是哪些罪名哈可能是判处死刑?
被:我这个罪名应该有可能判处死刑
诉代:(6s)
诉讼代理人对被告人的两次问话都包含有预设:“你对刑法知识应该有所了解,你的罪行是可以判处死刑的”,但实际上他的第一次问话中的预设已经被被告的答话否定了,“基本上不了解(刑法方面的知识),所以后果我不太清楚”,所以他的第二轮问话就被被告呛了回去。因为审判没有结束,合议庭还没有宣判,现在谈刑期是不合适的。
[1] Frege, G. On Sense and Reference [ A ]. In P. T. Geach and M. Black(ed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eb Frege [ C ]. Oxford: Blackwell,1952.
[2] Strawson, P. F. Referring [ J ]. Mind,1950,(59).
[3] Levinson, C. S. Pragmatics [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4] Stalnaker, Robert C. Presuppositions[ J ].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1973,2(4).
[5] 徐盛桓.“预设”新论[ J ].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93,(1).
[6] 牟宏玮,王萍.对“90后”大学生实施抗挫折教育的思考[ J ].求实,2014,(S1).
[7] 王立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主体性文化教化[ J ].求实,2015,(3).
[责任编辑:索原]
向波阳,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北黄石435002;李桂芳,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北黄石435002
DF6
A
1004-4434(2016)08-01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