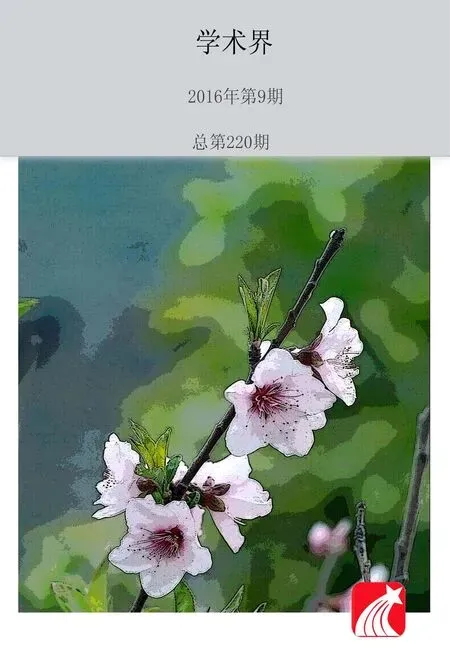“意见”视角下的戴震哲学〔*〕
2016-02-26阚红艳
○ 阚红艳, 孙 超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意见”视角下的戴震哲学〔*〕
○ 阚红艳, 孙超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安徽合肥230036)
戴震视程朱离情之“理”为“意见”,并斥之为“以意见杀人”,但同时,戴震之“理”亦面临困境,有转变为“意见”的可能。故而他提出“以情絜情”作为消解“意见”之道,“以情絜情”所体现的意义在于,戴震把方法论作为其理论的重要部分,把思想理论与方法论进行紧密关联,从而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圆融,更具张力。
意见;理;以情絜情;方法论
“意见”是戴震思想中一个重要却又模糊的概念,戴震晚年著《孟子字义疏证》,他在给段玉裁的信中自述其意曰:“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1〕可见,解世人“意见”之弊而明人心之“理”是戴氏作《疏证》之意图与根本。对于戴震之“意见”,现时学者多从认识论的视角来审视之,比如,沈玉龙认为:“‘意见’实际上是指个人的主观看法,这些看法不是依据‘理’而来,而只是个人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所作出的关于对象的主观判断。”〔2〕刘锦贤认为:“意见者,一己之私见,非客观义理之真也。”〔3〕表面看来,这与戴震所述的“凭在己之意见”涵义相侔,但实际上却未必完全切中肯綮,其只是表述了“意见”的一个面向。依戴震的思想理路,其所批驳者,主要针对程朱形上之理及由此而生之种种弊端,故其所谓“意见”,当是指程朱之理而言。戴震提出“以情絜情”作为消解“意见”之道,戴震把方法论作为其理论的重要部分,把思想理论与方法论进行紧密关联,从而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圆融,更具张力。
一、何为“意见”
戴震的“意见”究竟所指为何,他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定义,而是通过理欲之辨、“理义”与“意见”的对举来勾勒其内涵的。在戴震看来,“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4〕所谓“理”,就是“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之谓。而宋儒“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5〕其结果就是对人之生道穷促,漠然而视之。宋儒舍情欲以求理,故其所谓“理”实为“意见”,“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6〕由此我们可以对戴震之“意见”作如下的推论:程朱之误不在其“理”之谬——就内在价值理念而言,仁政爱民当是程朱之宗旨,此一点戴震亦应有所同感。但理念之善意并非就能得到善之结果,程朱之弊在于以“理”行“理”,只强调了价值、理念的正当不易,而忽视了现实之“情”。故而,戴震所言宋明之“理”为“意见”,其实并非指其价值理念导向的偏差,而是针对其由抽象的价值理念向具体现实的转化过程中,其“理”只是“空有理之名”而无理之实。因此,戴震以“意见”名程朱之理。以此观之,就价值理念内容而言,我们并不能简单的直接说戴震所言之“意见”,就是“一己之私见”,是现代认识论所谓之“意见”。我们不能以西方认识论的“意见”来比附戴震之“意见”,虽然戴震之“意见”亦含蕴有西方认识论之“意见”的某些内涵因素。
戴震之所以视程朱之理为“意见”,因“其言足以贼道”。正如戴震所言,“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意见也。离人情而求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见当之。”〔7〕从理论上说,程朱之理“如有物焉”,是一个超越之形上存在。在与理所对举而生的范畴组合中,不论是宇宙论的理与气,还是人性论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者之间主次分明,由对分而至对立,“并最终归结于非此即彼,且是此非彼的思想方法和价值理念”〔8〕这种此是彼非的理念在道德论上便表现为天理与人欲的严峻价值对立,而此一对立延续到现实之中便是严苛的道德“律法主义”,生活化之道德原则变为律法性质的道德规范,从而使得生活之生养之道被打压与排挤。程朱之“理”重在突出存在价值之超越性,而忽视了“存在”本身所具的应然内涵。尽管这种超越性体现了存在的本质特征,但对本质超越性的过分强调易于使得本质独立于存在,从而导致本质与存在割裂为二,存在反而屈抑于本质,进而本质亦失去了其价值所应有的意义。反映在现实之中,就是理欲二分。尤其是当程朱理学被意识形态化、庸俗化之后,这种对立更显突出。有此“法弊”而致“人弊”丛生。由此而来,本是以仁义为本的程朱之“理”便异化为“祸斯民”之“意见”。
依戴震,大致而言,由理论之弊而生践行之祸之“意见”有三种情态。其一,“其人廉洁自持,心无私慝,而至于处断一事,责诘一人,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严气正性,嫉恶如仇,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祸,己且终身不寤,或事后乃明,悔已无及。”〔9〕此类之人,大概是戴震所言之“俗儒”,其心无私慝而行正,往往过于自信自己持理有据而非理莫行,但却于事情之原委隐曲未能得,只是惟理而为,然事情的结果却并不能尽如人意。唐君毅先生对此有所评述,“宋儒之学者,……当其应事接物之时,若因思及其心之性理之自足,……而自视其心与其人,若高居所接之其他一切人物之上者。缘是而或不免自对于其当前已知之理,执一废百,而成意见。或者乃更坚执其意见,鼓荡其血气,以成意气,乃以理责人,以理杀人。”〔10〕所谓“高居”,是说理的至高无上亦使“得理者”产生心理优势,而这种优势往往使行为者更加以理为则,而忽视了事情之隐曲。故周国良先生有言,“东原的批评……足以提醒吾人在待人处事上不可形成傲慢的态度,此乃东原批评宋儒之积极意义。”〔11〕其二,“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雎,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 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12〕此处戴震所述者,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如其所言只为“自宋以来”,阶层分立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社会角色的分配决定了在他们的利益冲突中,弱势者基本都处于绝对劣势一方,而强势者所使用的手段就是普遍被社会认同的,看似公平、正义的公理,这就产生了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客观而言,在社会之中,这种“以理杀人”很难避免,它的产生并非由于程朱之“理”,而是社会本身的必然现象。其三,“在位者多凉德而善欺背,……在位者行暴虐而竟强用力,……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13〕统治者之所以敢于这样奸诈、残暴、贪婪,就在于他们以执“理”者自居,理之所在当是权之所在,对理的反对就是非圣枉法,就是异端邪说。章太炎先生认为,“戴震理学批判思想的产生缘于其对统治者以‘理’责人,不恤民生的失政不满。”〔14〕此语或许言之不谬。胡适先生亦言,“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15〕以“天理”为核心的程朱理论在世俗化、制度化、意识形态化之后的负面作用日渐凸显,而其所造成的现实结果与其理论之初所设想构建者亦歧道而行,并最终被批判与抛弃。
综上而言,戴震所以谓程朱之“理”为“意见”,与其说是由理论辩证而致,毋宁说是由社会批判所生。在理论上,戴震认为程朱以“理”为形上之实体,舍情欲而言理,是不明“理”之真义,因此而使人心“疑似而生惑”,导致社会种种弊端。但问题是,戴震的理论批判是否合当?依刘锦贤先生所言,“理欲对举不相容,系道德的决断语,意在勉人去人欲之私,充本然之善。程朱严分理欲,所以使人孳孳进德也。若对于生民之涂炭,无动于衷,只企慕一如有物焉之理,此正是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也。……东原将程朱以理导欲之说,看作绝情欲之感,空想的天理,实不善会。……东原之为此言,盖对当时横施意见以害人祸天下者,深恶痛绝,又对程朱所言之理不能把握,视之为意见之私遂将害人祸天下之罪归诸程朱矣。”〔16〕此语可谓颇有见地,在前所举三例之中,只有首例稍涉程朱理论之弊,而后二例皆非完全关乎义理。称程朱之理为“意见”,戴震非能从理论上得出,而是因现实之困以将其归罪于程朱,然现实之困所由者多,岂能仅以一因概之。陶清先生言,“‘以理杀人’ 对于戴震来说,绝不只是概念术语的逻辑推演、思想体系的形上建构,……而是目睹耳闻乃至鲜血淅沥而感同身受的经验事实。”〔17〕同理,戴震以程朱之“理”为“意见”也是以现实为论。故而,若以“私见”等来定义戴震之“意见”实为不妥。按戴震之意,将所有现实之流弊归咎于程朱之“理”,而这远不是程朱所应承受者。
但如若以现实为论而臧否理论之得失的话,其实戴震自己的“理”论恐怕亦难以逃脱“意见”之命运。方东树曾在《汉学商兑》一书中批驳戴震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而天下方同然和之,以蔑理为宗,而欲以之易程朱之统也。”〔18〕如观此言而细思之,我们就会发现,当戴震大谈特谈作为“情之不爽失”之理时,他很少论及作为“不易之则”之理,或者说,他一直是在试图刻意地回避什么吗?
二、戴震之“理”的困境
戴震对程朱之“理”的批判,主要针对其庸俗化与意识形态化之后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但假若戴震之“不易之则”之理成为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它亦很难避免被庸俗化、工具化的命运。 戴震极力反对程朱基于形上之“理”而形成的“理欲”关系,进而,他依据自己的理路建构了新的理欲模式。在戴震看来,“理者,存乎欲者也。”〔19〕此一理欲模式亦即戴震一贯所执之逻辑进路——应然之本质源自实然之存在。所谓“理”并不是一种先验之实有,而是存在于实然之中的道德本质、规律,具体而言,就是“欲,其物;理,其则也”〔20〕。自然之物之则,戴震称之为“分理”,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正确反应。然当此特性应用于社会伦理领域时,以“物”“则”来定义“理”“欲”关系时,伦理之“理”就成为“不易之则”,作为其具化之社会之“礼”亦是“千古不易者”,虽然戴震解其“不易”为“乃语其至,非原其本。”〔21〕试图区分其与程朱超越实体之理之异,但就实质内容而言,依戴震逻辑进路而出的伦理之“理”,不仅没有体现出其与程朱之“理”的迥异,反而又有落入程朱“理”之窠臼的可能。作为“不易之则”的礼具有不可移易之永恒性。只是戴震从礼的普遍性本质得出其超越性,而宋儒之礼则由其超越性而推衍出普遍性。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就会显得有些吊诡——虽然戴震与程朱之学说“只是争辩一个‘理’字”〔22〕。但其实,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如戴震所言的那样泾渭分明。正如村濑裕也所言,“将客观的善——仁义礼作为‘不易之则’来把握这一点,……它本来就明显地显示了戴震认识的限度。”〔23〕另者,严格上说,如金观涛先生所言,戴震“并不反对儒家伦理”〔24〕,戴震与程朱在“理”之上推演出的社会法则(礼),二者于内容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其范围不出仁义礼智及当时社会所具之规范。就内在价值而言,二者所体现出的儒家伦理思想几无分别,君臣、夫妇等等的社会规范伦理价值观是它们的共同内涵,亦即,戴震在“理”(礼)的内涵上并没有充实异于程朱传统的新内容,二者的差异只是伦理道德的合法性根据及理论论说理路的不同。虽然从二者理所自出的依据及推论方式看,宋明之理蕴含着的是一种森严的等级伦理,个人成为被压抑的道德对象,而戴氏之理则更多的包含了平等的意蕴,它来自于人情,是人“心之所同然”。但问题是,如何在内容高度相似的情况下,凸显二者气质及价值的迥别呢?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假若戴震之“不易之则”之理成为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它很难避免被庸俗化、工具化的命运。道德价值原则之善最终还是要被落实于具体的道德规范——礼,然其一旦变为“规范”,其所蕴含的价值便不能自主呈现,而是要借助于行为主体来践行,这一过程的转换既可以实现价值的现实化,也可能是价值的异化。究其原因,其一,虽然社会行为体现在个体对个体的活动之中,但其蕴含了更多的社会因素,强者对弱者的俯视并不能简单地适用于个体对个体的假设,所以,出现价值异化不能归咎于代表价值的规范;其二,个体对规范的理解不一定完全契合其价值精神,这种偏差造成价值的失落。再者,最初所体现价值的规范,很容易被固化、制度化,这似乎是道德价值的宿命,而其一旦如此,规范所能表现出的价值必定是异化的。若如此,戴震之“不易之则”的命运很难逃脱程朱的理论轨迹。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中对戴震的评价更能表现出戴震之理的问题所在,“戴君之误,误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25〕毕竟价值理论的构建与实践存有隔阂,程朱之“以理杀人”非是其理论的出发点,理论并不能保证实践的全部效果。在戴震亦然,其理论如放在实践之中,恐怕难以避免如他对程朱的指责那样的命运。
对于戴震之“理”论,从积极层面来看,他完成了对程朱“理欲之辨”的“反动”。但客观而言,戴震的这些思想在程朱的理论中也并非未见。朱熹亦曾言:“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26〕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不论是天道,还是人道,求“生生之道”是他们的一贯主线。程颢言:“天只是以生为道”〔27〕朱熹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28〕所谓“生生之道”,即博施于众而济民、安天下,这是每一个儒者之志业。何以数百年之后,程朱之思想竟然成了“以理杀人”?——这绝非他们的初衷。如果就思想点而言,戴氏所主张者在程朱那里亦不缺乏,甚而,程朱之理论更系统、更精致。然结果如是,戴震亦不会不意识到此一点,并作一考量,进而对之进行合理的理论应对。
三、“意见”消解之道
当然,以物则关系解“理”,只是戴震“理”论的一个面向,相对于程朱之理欲二分,戴震主张循情而致理,“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29〕所谓“不爽失”,就是要“通情”“遂欲”。戴震认为,作为自然之人“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之为人之根本特性,既是人之生理的需要,也是人之价值本质的体现。至于“通情”的方式,戴震以“恕”为道,“以己推之” “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絜之人,则理明。……诚以弱、寡、愚、怯与夫疾病、老幼、孤独,反躬而思其情。人岂异于我!”〔30〕此亦即“以情絜情”。依戴震,情之所通就是理之所达,程朱“舍情求理”,故其“理”是为“意见”而“祸斯民”,戴震絜情使其顺达则使“理”“無不得其平”。
对于戴震之“以情絜情”说,学界评议者多,容肇祖先生认为,“‘以情絜情’ 的学说,是一种消极的道德。……戴震以情絜情的学说,就是由于他的大前提,‘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的谬误。欲不是很简单的东西,从细细的分析上看,人的欲望,也有由于习惯的养成,不能完全同一的。概言之,‘人是同有欲的’这可以说是对的。如果说‘人是同所欲的’,可就不对了。‘遂己之好恶,忘人之好恶,往往贼人以逞欲’,即所谓侵犯他人的自由,这固然是不好;而施与人是以己所能受者,亦不免有时流于困苦他人的毛病。则所谓‘以情絜情而无爽失于行事’,当不易做到。”〔31〕容氏之论可谓平实,但他没有看到“以情絜情”所具有的另一面向之内涵——“以情絜情”是一种行道之方法,即,其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
安乐哲先生言,恕(以情絜情)是“‘人’‘己’建构的关系域中彼此的譬比。”〔32〕以“彼此”言人与己之关系,表明个体在进行道德行为之时,其所遵循者不仅是理则,而且还须考量到行为对象之情实,如此而来,戴震之“不易之则”之理在现实行为之中所面临的困境将会被极大的消解。所谓“惟以情絜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33〕对“意见”的消解,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在“理”与“欲”之间达成了某种动态之平衡,既不会重理以窒欲,又不会纵欲而失理。
丘为君先生认为,“在方法论上的开展上,戴震与理学家的做法则是南辕北辙。”〔34〕程朱等理学家之方法路径是通过涵养察识、惩忿制欲之个体修养来为践行仁义作工夫,而戴震之方法则是通过人与己的关照与考量来实现性理之真。而这一方法之最大意义在于,它不仅是理论性的,亦是实践性的,平等个体之间的情实相絜,有效地消解了理则固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进而,此方法可能带来更进一步的价值意义延伸,蔡元培先生言,“至东原而始以人之欲为己之欲之界,以人之情为己之情之界,与西洋功利派之伦理学所谓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者同。”〔35〕由此可见,“以情絜情”之方法所包蕴者具有巨大的扩展空间。
任何一种思想,不论它的结构多么完美,理论多么深刻,如果没有合适方法论的指导,最终会陷入僵化,以致失去其生命力,而变为“意见”之流。提出“以情絜情”说,其真正用意在于,在方法论上建立一个原则,以使自己的理论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戴震理论的最大贡献或许就在于思想理论与方法论原则的紧密结合,从而使其体系更加圆融,更具张力。或者说,思想体系本身是否完善,很大程度上要关涉于其方法理论的建设,只有有合适的方法论,思想本身才具有活力。戴震之“以情絜情”论,也表明其开拓了与宋明理学传统不尽相同的新理路,即重视方法论的建构。正如黑格尔所言,“方法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以情絜情”之意义或许就体现于此。
张立文先生曾言:“哲学批判有助于对象性理论在根本前提上实现突破,一般来说,哲学批判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和功能,它能突破旧哲学的旧思想、旧思维、旧方法、旧视角,而转变为新思路、新思维、新方法、新视角,由理论前提而推及理论自身的各层面、各环节。”〔36〕或许戴震所作之方法与理论的结合就属于此种情况吧。
注释:
〔1〕〔4〕〔5〕〔6〕〔7〕〔9〕〔12〕〔13〕〔19〕〔20〕〔21〕〔29〕〔30〕〔33〕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81、329、328、269、175、268、268、350、273、273、278、265、278、269页。
〔2〕沈玉龙:《“己之意见”与“心之同然”——论戴震的“意见”、“理义”说及其意义》,《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28页。
〔3〕〔16〕刘锦贤:《戴东原思想析论》,花木兰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17、217页。
〔8〕〔17〕陶清:《戴震与理学思辨模式批判》,《哲学动态》2010年第3期,第36、36页。
〔10〕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新亚研究所,1968年,第503页。
〔11〕周国良:《形构之理与存在之理》,花木兰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1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23 页。
〔15〕〔18〕转引自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7卷),黄山书社,1994年,第400、303页。
〔22〕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页。
〔23〕村濑裕也:《戴震的哲学——唯物主义和道德价值》,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24〕金观涛:《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自我意识》,载于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序》,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5〕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3页。
〔26〕〔28〕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224、224页。
〔27〕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
〔31〕容肇祖:《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第688页。
〔32〕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2页。
〔34〕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35〕蔡元培:《中国理论学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05页。
〔36〕张立文:《戴震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
阚红艳,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安徽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孙超,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学。
〔*〕本文系2014年度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2014A241)的成果之一;2016年安徽省弘扬核心价值观名师工作室项目(Szzgjh1-1-2016-4)“《原理》课校本资源利用与教学方法综合创新”的工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