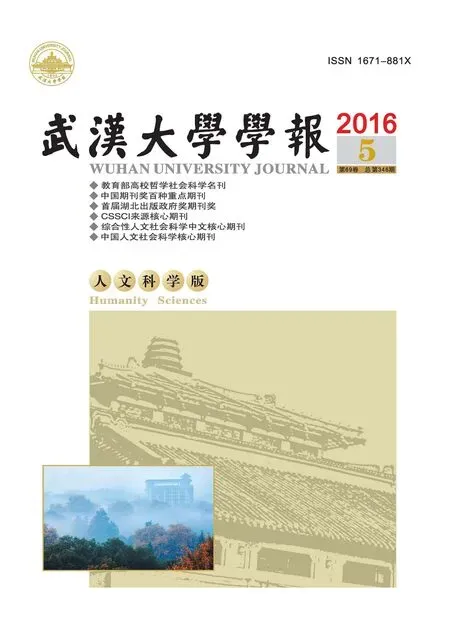晚期法兰克福学派视域中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2016-02-21杨礼银
杨礼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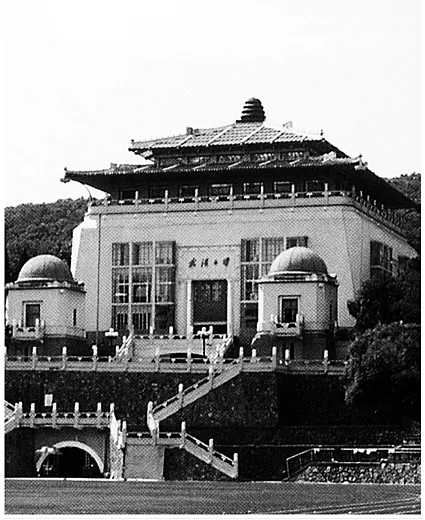
晚期法兰克福学派视域中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杨礼银
针对民主与正义能否协同增效等问题,以哈贝马斯、霍耐特和弗雷泽为代表的晚期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探索。哈贝马斯提出了后形而上学正义观,凸显出了多元主体之间的程序民主在正义规范的选择、制度的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霍耐特在分析黑格尔正义理论的基础上,试图重建一种基于民主伦理要求的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理论。弗雷泽对参与平等的强调深化了哈贝马斯所凸显出来的正义的民主合法性问题,同时引入了霍耐特的承认机制,在后社会主义的视域中充分揭示了民主与正义的循环关系。这三种关于民主与正义间关系理论的出发点都是预设的理想价值而不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因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民主与正义间的循环问题。
哈贝马斯; 霍耐特; 弗雷泽; 民主;正义;法兰克福学派
在西方思想史上,“民主”与“正义”作为两个关键概念一直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从苏格拉底以民主的方式被判处和执行死刑这一事件引起的民主与正义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到今天大多数国家以民主方式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一基本制度来促成民主与正义的联姻为止,民主与正义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民主与正义间是否协同增效将直接影响政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的剖析,以哈贝马斯、霍耐特与弗雷泽为主要代表的晚期法兰克福学派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民主政治伪装下的合法化危机、承认危机与非正义的制度结构,在他们看来,要化解这些危机,理顺民主与正义间的关系尤为关键。
一、 哈贝马斯论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民主与正义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关键概念,虽然哈贝马斯并未直接言明民主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问题却内蕴于其思想始终。早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对民主与正义间的关系问题就有所涉及。他在论及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向社会福利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转变时说道:“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超越自由主义基本权利的消极规定,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而对此哈贝马斯表现出悲观失望的情绪。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福利国家的“正义”是由国家自身给予的而非公民争取的,缺少合法性基础。而且,这种被给予的“正义”正在丧失其真实性。他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治国家的法律概念有两个组成因素,即保障平等的普遍性和保障正确或正义的真实性。它们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以至于其形式范畴不足以使新的材料充分规范化。”*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57页。而要实现正义,在哈贝马斯看来,首先需要确保公共领域中公众自主自律话语交往的公共性与批判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了转型,其中的公共性和批判性丧失了,公共领域沦为了利益斗争、操控与妥协的场所,从而无法确保制度是否正义。在这里,哈贝马斯虽然是从17和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出发来描述的,但是其中他先验地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只有经过公众(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自主自律的话语交往,所制定的制度才可能是正义的。相反,如果未经公共领域中公众的反思和批判,该制度就丧失了正义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从而丧失其合法性。这种预设逐渐远离其历史的视角而走向理想化,并贯穿其理论始终。
哈贝马斯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集中阐释民主与正义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在开篇前言中,哈贝马斯就直言不讳:“在完全世俗化的政治中,法治国若没有激进民主的话是难以形成、难以维持的”,因而他亮明观点:“作为私人的法权主体,若他们自己不通过对其政治自主的共同运用而澄清正当的利益和标准,并且就在哪些相关方面平等者应该受平等对待、不同者应该受不同对待达成一致,是无法充分享受平等的主观自由的。”*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11年,《前言》第6页。这样,基于个人政治自主的自由主义观点,哈贝马斯将民主作为正义制度构建的基础置于自己政治哲学的奠基石中,从而确定了个人政治哲学的基调。在与罗尔斯的对话中,哈贝马斯提出了后形而上学的正义论,这种正义论在建构论的视野中主张民主与正义的协同增效。哈贝马斯认为,后形而上学的正义观并不指向任何好的生活或价值,而是指向话语民主程序的合法性。他指出:“在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中,正义理论要指望人们接受,它就必须仅仅局限于一个严格地来说是后形而上学的观念,也就是说,它要避免介入彼此竞争的诸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之间的冲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74页。正义理论需要经过从主体—客体单向设定的形而上学思维转向主体间话语实践的后形而上学思维,即从一种实质的普遍的关于好的或正当的生活观念向一种形式的基于程序民主的程序正义观念转换。
哈贝马斯把程序正义的合法性诉诸公共领域的话语民主机制。他认为,在市民社会中,具有交往理性的人们在生活世界的话语交往中对引起共鸣的社会问题自主地加以感受、选择、反思和主题化而引入公共领域,由社会公众在其中就这些问题基于已有的规范共识进行理性的提议、质疑、争辩而达成共识,并通过公共媒介促使这种共识与其它公共领域中所形成的共识相互渗透最终形成非正式的公共意见,进而汇成一股作为集体意志的交往之流即公众舆论,并在正式的建制化的公共领域(如议会)中凝成为一种具有潜在行动力的交往权力,这种交往权力又通过立法、司法等法律中介被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与公众舆论转变为政治权力相应,政治权力通过法律中介得到有力执行,从而保障公众的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而这种执行还会受到公共领域中交往权力的持续影响。也就是说,公众在公共领域中会对公共权力进行话语监督和公共批判,这种批判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发展成“公民不服从”的政治运动。这种基于公众间自主交往的话语民主程序构成了话语正义的基本建制,基于这种建制,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张力依靠公共领域中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可以得到有效调节。这种调节主要表现为:为了维护正义的根本价值,话语民主通过程序而不是原则来确保事实层面的制度的制定、实施和维持的合法性。然而,正如哈贝马斯在评价科恩的“协商民主”时所说的那样,“支配民主过程的是对于每个公民团体都同等地具有构成性意义的普遍的正义原则”*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379页。,维持其话语民主得以可能和持续的也是公众心中的正义原则和现行制度的正义有效性。公众基于三个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交往行为越是遵循普遍的正义原则,其话语民主程序就越具有有效性,与此相应,制定和反思制度的话语交往越民主,这种制度对于制定者而言就越正义。这样,民主与正义就相互支撑,协同增效。就这种话语程序是否正义的问题,南茜·弗雷泽对哈贝马斯这种基于国家公共权力的正义建制进行了严厉批判。她认为这种正义建制是在民族国家公共权力的基本框架下实现的,只能保障作为国家公民的特定人群的利益或价值,而忽视了全球化过程中已成为现实的更多元正义主体的利益或价值*参见杨礼银:《从罗尔斯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的发展逻辑》,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8期。。
哈贝马斯关于民主与正义协同增效的理论力图实现正义论从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变,在罗尔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正义的主体间性,凸显出多元主体之间的程序民主在正义规范的选择、正义制度的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了正义制度对于话语民主的保障作用,从而设定了民主与正义之间的良性循环。为了解决这种循环论证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应该更加凸显民主在其中的基础作用。他以欧盟为试验田,试图实现民主正义协同增效的良好愿景。然而,由上可知,哈贝马斯对话语民主程序过多的限制而将主体间的社会冲突排除在外,同时对正义制度的过度理想化而忽略了制度本身对一部分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从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话语交往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和掣肘。而恰恰是这一点为霍耐特从主体间的蔑视问题出发探索承认的正义和弗雷泽从全球化的多元视角出发探索以参与平等为核心的三维正义观留下了理论空间。正是他们沿袭哈贝马斯关于民主与正义相互作用的路径重构了民主与正义的循环关系。
二、 霍耐特论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霍耐特在哈贝马斯所引领的交往范式的社会批判理论框架下来重新思考民主与正义的关系,他补充了被哈贝马斯忽略了的社会冲突维度。在《为承认而斗争》中,他试图以更加社会学的方式抓住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轮廓,把交往理性作为相互承认的原则直接植入社会再生产中,并将“承认”作为规范基础来捍卫社会批判的理论旨趣,以此种下了民主与正义间互动关系的种子,即基于承认规范的民主合作机制与正义价值目标之间的社会理论重构。不过,他直接关注民主与正义间关系的文本却是《作为反身性合作机制的民主》。在此文中,受哈贝马斯影响,霍耐特也将公共领域中的意愿形成视为理解现代民主的重要窗口,但是与哈贝马斯将民主的意愿形成诉诸言语的有效性不同,他吸取杜威将民主理解为社会合作机制的观点,认为不应该仅仅将民主看作一种政治理想,而应该首先且首要地将它看作一种社会理想。
这样,在他看来,民主从政治合法性的功能性工具变成了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在这篇文章中,霍耐特初步提出了杜威民主理论中民主与正义间的循环问题。
在《作为反身性合作机制的民主》中,霍耐特考察了杜威民主思想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其关于民主与正义互动关系的理论。他认为,与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对话成为当今民主理论的主流,其中阿伦特等所主张的共和主义民主模式和哈贝马斯等所主张的程序主义民主模式主导了近年政治哲学关于民主的讨论,然而在这替代政治自由主义的两种激进民主模式之外还有第三种模式,即杜威提出的作为社会合作机制的民主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具有共和主义和程序主义不可比拟的优点。在杜威早期著作《民主的伦理学》中,他将民主与自由以及二者的合作关联起来,认为民主是联结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三个指导原则的社会理想:“一种民主的宪政预设了无限制的个性发展的个人自由,这种个性发展以制度化的机会平等为条件允许所有社会成员发挥他们的才能,这些才能使得他们在与他人的联合中友爱地,或者更好地说,团结地追求共享的目标。”*Axel Honneth.“Democracy as Reflexive Cooperation: John Dewey and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Today”,Political Theory,1998,26,p.770.霍耐特吸收了这里所蕴含的民主宪政与平等正义间相互作用的理念,并在后来的《自由的权利》里进一步加以阐释。
不过,霍耐特认为,杜威早期的这种作为自由合作理想的民主模式具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缺乏关于交往自由的政治维度:“杜威如此直接地从合作的自我实现转向集体的自我管理,以至于没有为个人在形成联合意志过程中留下任何话语的程序实施空间。”*Axel Honneth.“Democracy as Reflexive Cooperation: John Dewey and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Today”,pp.773~774.在后期著作《公众及其问题》中,杜威将公众的政治参与问题作为民主理论的出发点,这个问题就是:作为工业化、复杂性增长和个人主义化的后果,现代社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整合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使得所有公民在民主公共领域中的参与都变成了一种幻觉。霍耐特认为,针对这一问题,杜威引入了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和以公共领域为机制的民主参与方式,使得民主的意愿形成程序与正义的劳动分工组织相互指涉,而这种相互指涉既克服了其自身的问题,又克服了共和主义和程序主义民主模式的问题。相较于共和主义过于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的美德而忽视社会分工的不公正,杜威将民主看作是特定分工合作的社会机制从而使之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功能;相较于程序主义过于强调政治参与的程序性而忽视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价值,杜威将民主的伦理生活理解为所有相关的社会成员通过一种正义的社会分工组织而相互关联的共享经历的结果。霍耐特对杜威民主模式的推崇展露了他关于正义与民主间关系的观点,即民主与正义相互构成。
在《自由的权利:民主伦理大纲》一书中,运用社会病理学与批判性重构的方法,霍耐特在分析黑格尔正义理论的基础上试图重建一种基于民主伦理要求的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理论。他将个人的自由作为民主与正义的最大公约数来阐释民主且正义之社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这里,不管是法律自由还是道德自由,抑或是社会自由,都要建基于“我们”视角的承认原则。
那么,霍耐特如何构建民主与正义的互动关系呢?在《自由的权利》中,霍耐特认为,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理论需要满足四个前提:(1)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与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普遍价值相关联;(2)作为正义,就意味着以恰当的机制或实践在一个社会内部实现那些普遍价值;(3)从社会现实的多样性中梳理出那些机制或实践,以重构一种能够真正确保和实现普遍价值的规范;(4)不能在重构过程中只是展示已经现存的伦理机制,应当同时也能够对它所体现的价值作公开的批判*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24页。。社会成员共享的普遍价值贯穿这四个前提,成为正义的价值旨归,而如何形成和实现普遍价值就变成了正义的实质内容。在霍耐特看来,对于普遍价值,不应该像康德及其后继者(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那样先验地将之假定为自由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设定保障个人自由的机制或实践,而应该遵循黑格尔及其后继者马克思的路径,以辩证的方法在社会的现实中考察自由的可能性和真实性。他认为,从古至今,个人的自由有法定自由(消极自由)、道德自由(反思自由)和社会自由。法律和道德只是为个人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只有社会再生产的现实条件才为个人自由提供了真实性。霍耐特指出:“为了能够对我们时代社会关系中自由的‘现实’有所影响,现在需要一种行动领域的重构,在这种行动领域中,相互补充的角色义务的作用是,使个人能够在他们合作伙伴的自由活动中,看到实现自己目标的条件。”*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第201页。他所重构的行动领域就是体现友谊、爱情、家庭等的私人关系,体现交换、消费等的市场经济活动以及体现民主决策的公众政治活动这三种领域。在这三个行动领域中,基于社会成员(朋友、爱人、亲人、生产者、消费者、雇佣者、劳动者、公民、公众等)之间相互承认、团结互助、话语协商的民主伦理所要求的“我们”视角处于正义机制的核心。“我们”意味着个人作为主体的参与、参与中与他人的互动以及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这种民主伦理不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更是存在于正义所及的一切生活领域。这样,民主被视为正义的伦理基础,而正义则被当作民主的最终目标和根本保障。可见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中,民主与正义被植入了相互建构的循环机制之中。
由上可知,霍耐特的理论中心经过了从承认到民主再到自由的逐步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民主与正义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步凸显,最终成为霍耐特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然而,尽管霍耐特批判哈贝马斯等人的基于平等话语交往的后形而上学建构论,试图凸显出社会再生产对于民主正义的构成作用,但是其预设的承认原则同样脱离了民主与正义的历史性,不但没有逃脱民主与正义的循环论证,而且最终还落入了其刻意逃避的形而上学窠臼之中。
三、 弗雷泽论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弗雷泽是在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对话中逐渐明晰关于民主与正义间的关系的。在《对公共领域的再思考》一文中,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这不但使得公共领域丧失了部分民主功能,而且对于广大女性来说也是非正义的。由此出发,公共领域中的参与平等逐渐变成弗雷泽民主与正义的最大公约数。在接下来的《再分配还是承认》、《正义的中断》以及《正义的尺度》等著作中,受马克思剥削理论、哈贝马斯话语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在批判霍耐特基于文化承认的一元正义论过程中,弗雷泽提出了具有“后社会主义”特征的以参与平等为核心的三维正义,即基于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正义、基于文化认同的承认正义、基于代表权的政治重构正义。在这种正义理论中,民主与正义作为其中的关键词,具有两方面的关系。
第一,民主是正义社会的根本要求,正义制度是实现民主价值的根本保障。一方面,弗雷泽认为,当代社会非正义的三个维度(经济上的分配不公、文化上的错误承认和政治上的错误建构)都源于基于民主价值的参与平等的丧失,若要矫正这三个维度的非正义,所有相关者作为正义的主体都应该在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与政治诉求中平等地参与,这样,作为参与平等的民主价值从而成为制导经济文化与政治制度是否正义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与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对正义制度的强烈期望一样,弗雷泽致力于探讨正义的实现路径——制度建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构。在非常规正义时代,一种正义理论需要诉诸对话来民主地解决框架性争议,这种方法被她称为“对于‘如何’的批判—民主路径”(the critical-democratic approach to the “how”)*Fraser.Scales of Justice: Reimaging Political Spa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p.37~47.。她认为,至今有两条路径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建构,一是公民社会路径,二是正义的制度路径。前者保障了制度建构的民主对话要求,但是仅靠公民社会的对话自身,无法形成有约束力的解决方案,而后者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正义制度的建构需要公平的程序和合理的结构来确保民主协商的合法性,而相对于公民社会的路径而言,制度路径还需要确保公众有能力针对制度结构做出正确的判断。正如她自己所说,反规范的正义需要创建新的全球化民主制度,在其中各方争论得以公开和解决*Fraser.Scales of Justice: Reimaging Political Spa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p.69.。弗雷泽主张这两条路径相互作用,在与跨国公民社会的持久对话中建构民主解决各方争论的新制度。
第二,正义是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民主是实现正义社会的根本路径。弗雷泽认为,通过经济的再分配制度、文化承认的制度化以及政治代表权的重构,每位受到制约的主体都能平等地参与其中,从而使得正义的价值将得到实现和保障。也就是说,相关者的民主参与是为了实现正义的价值,民主参与的结果也必定是正义的。同时,也只有通过民主的平等参与,正义才能够实现。根据弗雷泽对参与平等原则所作的激进民主的解释,正义要求允许所有人具有成员资格并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制度安排,与此相应,若要消除不正义,就要消除那些阻止某些人作为平等、完整主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制度障碍。受哈贝马斯话语民主理论和正义理论的启发,在回答如何消除这些制度安排又如何来重构正义制度的问题时,弗雷泽诉诸公共领域中民主的话语交往。她认为,对于一种批判理论而言,公共领域要真正成为正义制度的有效装置,就要充分体现公众舆论的规范合法性(normative legitimacy)与政治有效性(political efficacy),没有它们,公共领域概念就失去了其批判力量和政治立场。这种规范合法性和政治有效性应该在全球的跨国视域中来考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民主功能只有充分地突破民族国家及其权力对参与者话语交往的局限,才能构建出没有歧视、伤害和侮辱的全民参与平等的正义制度,从而实现多元化的正义诉求。
由上可知,民主与正义在弗雷泽那里是相互构建的,二者作为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价值而相辅相成。另一方面,二者不可避免地深深陷入了循环论证之中。对此循环,弗雷泽并不否认,她坦言道:“关于承认诉求价值的公平的民主协商,需要对于所有现实的和可能的商谈者的参与平等。参与平等反过来需要公正的分配和相互的承认。因此,这一说明中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承认诉求只能在参与平等的条件下得以证明,这一条件包括相互的承认。”*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事实上,民主与正义间的循环对于其批判理论来说不仅不是缺点,而且表明了一种优势,因为它“忠实地表达从民主的观点所理解的正义的反思特点”*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第35页。。
理论界对这种循环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凯文·奥尔森(Kevin Olson)认为,民主与正义的这种循环是必要的,但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参与平等的规范基础,而政治参与平等是这一基础的核心。这意味着民主比正义具有更加基础的地位。他说:“政治参与平等并不仅是一种正义的民主范式,而且还是暗含于民主正义实践中的规范。”*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高静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而与此相反,西蒙·汤普森(Simmon Thompson)则针对弗雷泽关于民主与正义的循环指出:弗雷泽关于参与平等的两个预设前提(参与者的反思能力和公共领域)由于要求过高而会陷入不民主与非正义的恶性循环。在他看来,民主与正义间的确存在循环,但是正义比民主具有更优先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得协商更加充分的正义的最低要求能够比促使参与平等得以进行的最高要求获得更多保障*Simmon Thompson.“On the Circularity of Democratic Justice”,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2009,35,pp.1079~1098.。
在我们看来,弗雷泽的民主正义理论对参与平等的强调承接并深化了哈贝马斯所凸显出来的正义的民主合法性问题,同时引入了霍耐特的承认机制,在后社会主义的视域中将民主与正义的循环关系充分地揭示了出来。然而,她对参与平等的过高要求也使得其理论很难适应后社会主义的复杂状况,从而不能解决汤普森所提出的不民主与非正义的恶性循环问题。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霍耐特与弗雷泽都在批判理论的视野中逐渐深入地踏进了民主与正义的循环关系问题之中。作为当代政治的主导价值取向,民主与正义的这种循环关系在宪政民主的政治框架里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然而循环的另一端可能就是恶性的,即不民主的程序导致非正义的结构,或者非正义的结构促使专制的后果,关键是如何避免让它们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尽管霍耐特强调植根于现实社会生产中的社会分析方法,然而与哈贝马斯和弗雷泽一样,其理论的出发点也是理想价值的预设(话语的有效性、自我的实现以及参与的平等)而不是现实的社会关系,从而背离了批判理论的理论根基,即历史唯物主义,很难解决不民主与非正义间的恶性循环。要真正地解决民主与正义的恶性循环问题,更好地促进其协同增效,只有立足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将民主与正义看作依据不同的社会和时代条件而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价值,具体地分析可能促使它们进入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的特定社会条件。
●作者地址:杨礼银,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liyinyang77@163.com。
●责任编辑:桂莉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Justice in the Horizon of the Later Frankfurt School
YangLiyin
(Wuhan University)
The later Frankfurt School has creatively explored the problems such as whether democracy and justice can make synergies.Habermas comes up with a post-metaphysical theory of justice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cedural democracy among the plural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just norms and constructing the systems.Honneth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a theory of justice as an analysis of society on the base of the democratic ethical requirements.Fraser deepens 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of justice which Habermas highlights, adapts Honneth’s mechanism of recognition and brings to light the circular rela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justice in the horizon of post-Socialism.The three theorie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justice all start off the ideal prediction rather than the real social relation,so that they can’t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circular relation.
Habermas; Honneth; Fraser;democracy; justice; Frankfurt School
10.14086/j.cnki.wujhs.2016.05.0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ZX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