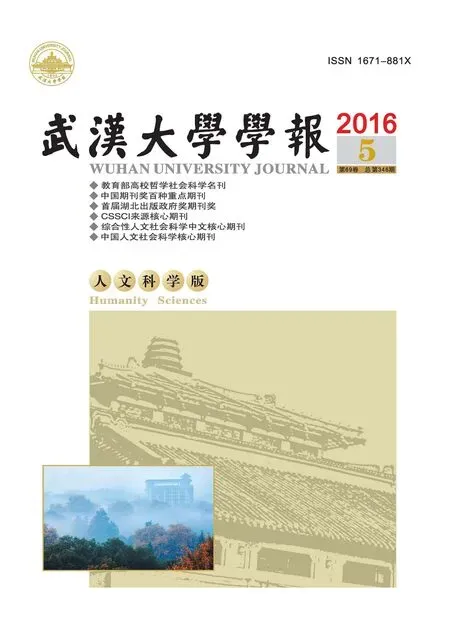政治领域的“游击战”与红色民主的建构
——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政权选举研究
2016-02-21王建华
王建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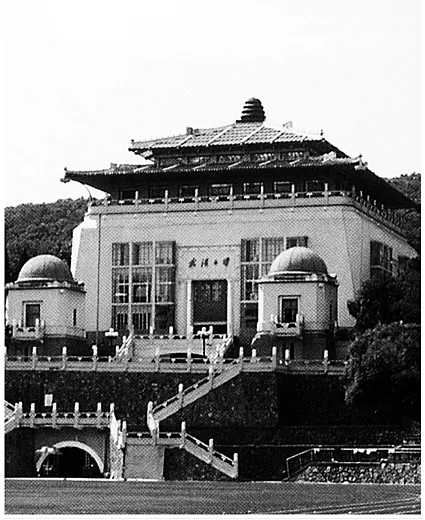
政治领域的“游击战”与红色民主的建构
——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政权选举研究
王建华
共产革命在颠覆乡村传统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建构根据地的红色民主。从中央苏区到陕北,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力推动下,根据地选举得以运转起来;但选民的被动参与决定了以选举为中心的基层政权改造,更多的是发挥了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打上了战争动员的烙印。为赢得生存空间,中共倡导的“三三制”选举,也充分展示了制度的灵活性。可以看出,当选举内化为战斗的“武器”时,不同时期的选举必然呈现差异性特点,表现为制度成长的非连续性、突变与碎片化,成为施米特“游击队理论”的政治诠释。
民主选举; 中央苏区; 红色民主; 苏维埃
西方世界对中共局部执政时期政权选举的了解,主要来自各国记者与军事观察员在延安的采访与调查报告。根据地群众普遍享有的选举权与“划圈法”“投豆法”等原始投票方式所折射出的现代民主的进步意义,使得亲历者惊叹于落后国家的民主奇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刘维宁译,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87~96页;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19页。,但意识形态的隐形偏见,使得西方学界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后,虽偶有学者论及选举,但多是佐证中共民主政治或动员能力的材料,少有以选举为中心的研究成果*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9~167页;Philip C.C.Huang,Lynda Schaefer Bell,Kathy Lemons Walker.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1927-193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8,pp.21~25。。可以说,这一领域尚未真正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
1980年,台湾学者陈永发在《现代中国》发表《战时中国中部农村地区选举研究:亚官僚制的民主化》一文,成为境外研究根据地选举的代表性成果。该文通过考察选举过程,即选前动员、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选举投票等诸环节中,组织与个体的表现,思考乡村选举的多重功能。该文作者认为,中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选举建立人民大众对于封建力量的霸权*Chen Yung-Fa.“Rural Elections in Wartime Central China:Democratization of Subbureaucracy”,in Modern China,1980,6(3),pp.263~310.。可以看出,基于选举要素的个案研究,对于了解根据地选举的动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但仅通过中部乡村的选举试验,显然无法认清中共选举的成长历程与制度性特征。
大陆学界有关根据地选举研究,更多地还处在议题设立与建构的初级阶段,表现为史料梳理多,理论阐释少;线性叙事多,动态观察少*张国茹:《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4期,第182~184页;颜杰峰、邵云瑞:《论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的政治诉求及其启示》,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168~172页。。近年来,部分学者试图超越选举动员的简单逻辑,关注选举权、罢免权与选举委员会等选举要素的建构,为深化根据地选举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相关研究还处在制度文本的分析阶段,缺少对制度实践的深度考察
*王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王建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选举委员会》,载《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54~63页。。同时,受知识储备与学科背景影响,少有学者对根据地选举进行政治社会学的分析,对其历史局限或可能存在的问题,更有刻意回避之嫌。
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选举是为了改造基层政权,更是为了提高社会动员能力。深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需要厘清根据地选举的实践逻辑,更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普鲁士军官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战争即政治的延续。事实上,战争的延续也在塑造着政治生态,进而影响政治制度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战场上的游击战无疑也在塑造着根据地的政治生态,使得制度成长呈现出非连续性、突变等特点,也就是德国政治思想家施米特总结的游击队理论的典型特征。有鉴于此,如何借鉴这一理论,在史料梳理的基础上,思考根据地选举制度的中国特色,就成为笔者努力的方向。以主力红军长征为分水岭,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中,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中央苏区与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政策的发源地,也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
一、 如何让选举运转起来
1933年8月25日,中央苏区的《选举运动周报》发刊词写道:“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兴奋着拿自己的血浇灌自己的政权——苏维埃的花。本刊的任务,就是要使这战斗的选举运动,生成更强大的阶级力量,以更加坚固的苏维埃政权,扫荡反动阶级的政权,争取全中国的胜利。”*《写在前面》,载《选举运动周报》1933年8月2日。可以想象,用鲜血浇灌的“战斗的选举运动”,绝不会是一场和平选举,而斗争的对象就是任职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其他候选人,目的是挖出不称职的干部与阶级异己分子。在中央苏区,大规模的选举运动总共有三次,该报的创办是在第三次选举运动即将大规模推进之时,也就是说,至少到此时,强调选举的斗争性仍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努力的方向。梳理三次选举运动,改变乡村社会传统秩序,让选举成为群众战斗的舞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31年12月15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苏维埃建设的训令”,各级苏维埃的组织还很不完善,选举手续不完备——不是用简单的群众大会,就是不按选举程序选举各级政府,特别是乡与城市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各级政府须依照宪法及中央颁布的各种条例细则,重新划分行政区域(选区),并依照选举细则,选举乡和城市苏维埃的组织。训令规定从1931年12月20日起,到1932年3月31日止,江西、福建两省和瑞金直属县,须依照新法令做出适当的工作计划,使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各级苏维埃的选举能于百日内,有步骤地完成*《毛泽东苏维埃建设重要的训令》(1931-12-15),载《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8日。。
检讨中央苏区第一次选举运动,中共闽粤赣(福建)省委坦言,两个月来,由省委到各级党部,都忽视了选举工作。工农群众团体没有动员起来,不能依期进行选举斗争,选举“战斗”变成了和平的群众运动,以至“冷冷清清”,毫无生气*《省委通告第4号:加强全省选举运动》(1932-2-16),福建省档案馆藏,91-2-386。。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江西省苏维埃发出指示,江西的选举运动已开展近两个月,可是,各地情形非常不能令人满意,没有在运动中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没有深入开展阶级斗争,造成最热烈的群众运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选举运动与合作社——中央政府指示江西省苏的一封信(1932-2-17)》,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4~185页。。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中央苏区第二次选举运动中,据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运动检查,各级选举运动都是和平的,没有以斗争来发动群众参加选举,许多地方在实际工作中不仅割裂了选举运动与土地革命战争的关系,而且没有经过选民选举代表,多以上级指派代表敷衍了事*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关于各级选举运动的检查(1932-12-1)》,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6卷,第533页。。
如何使选举运转起来?在中央苏区第三次选举中,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地方苏维埃负责人必须向群众汇报工作,而能否形成群众性批评意见,成为评价选举成败的主要标准。及至1933年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选举运动发出指示,乡(市)苏在选举前一星期,以屋子(集中居住的几家人)或村子为单位召集选民大会,总结乡(市)苏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情况,并发动选民进行批评与讨论,欢迎他们提出具体意见,作为指导政府此后工作的方针*韩延龙、常兆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关于此次选举运动的指示(1933-8-9)》,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77页。。在共产党人看来,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现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才能选出积极肯干、为党与群众利益而奋斗的苏维埃代表*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苏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决议(1933-8-4)》,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5页。。
相较前两次选举,中央苏区第三次选举准备得更为充分,重新颁布了选举法与选举工作细则,召开了南部、北部两个18县的选举动员大会。但考察选举过程,仍存在选举动员迟缓、组织不健全等诸多问题*梁柏台:《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1934-1-1)》,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62~1266页。。据江西省苏维埃选举运动检阅,各级苏维埃没能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即便省苏对选举运动的领导,也没能真正注意这一问题*《江西省选举运动检阅》,载《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3日。。此时,正在兴国县长冈乡调研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现,该乡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对于候选名单,群众没有展开批评。在乡政府工作报告会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进行批评*毛泽东:《长岗乡调查(1933-11)》,载《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11~212页。。兴国是中央苏区的先进县,长冈乡的选举情况在各地方选举中理应是好的,由此可以管窥根据地选举的真实情形。
从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培养选民斗争热情绝非一日之功。家族本位的乡村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形成的差序格局固化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及思考问题的方式。共产革命要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秩序必然会受到传统力量与习惯的抵制,因此,即便在红都瑞金,土地法的执行也不彻底,土地没有彻底分配,“太平观念,不但在群众中就是在政府工作人员中也极其浓厚”。由于部分干部对基本纲领的执行不正确和怠工,削弱了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甚至有的乡政府来保土豪*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1932-7-29)》,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6~217页。。乡土观念浓厚,在中共早期革命动员中具有普遍意义。总结秋收暴动失败的原因,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发现,干部及党员对于中央暴动的政策没有深切的了解,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畏惧心理,希望不经过激烈的暴动就可以解决土地问题,夺取政权。他批评长沙县委书记怕暴动得太厉害扰乱了乡村秩序、得罪了自己乡里的人。在彭看来,暴动是一门艺术,每个暴动的制造者对于暴动必须如艺术家对于艺术一样,要很细心地去赏鉴,去组织,去发挥,然后才能做出一幅很好的艺术作品。秋收暴动,在艺术上还没有开始*《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8)》,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40~41页。。暴动的艺术是什么?如毛泽东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3)》,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显然,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动中还存在寻求妥协的心理,不懂暴动艺术也就有了文中应有之义。理解了革命的艺术,也就理解了革命情境下选举的特性,根据地选举不仅是一个选拔人才的过程,更是一个甄别阶级成分、改造基层政权的过程。乡村中温情脉脉的邻里关系是不可能识别敌我矛盾的,如此,就可以理解苏维埃中央政府反复强调选举斗争性的意义所在。
及至陕甘宁边区,批评政府工作依然是选举动员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力推动下,选举的革命艺术得到了全面操演,并重塑着根据地的乡村秩序。根据1941年各县选举工作报告,选民对干部和政府是有意见的,但是,他们不敢在会议上直接提,有的说“事情过了,说也不顶事”;有的怕惹人,只在背后偷偷议论。如何让选民把意见表达出来?延安县选举委员会利用选举宣传与选民登记,以个别谈话的方式深入到群众中去,从家常话一直聊到工作上去,“使他觉得你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什么话都愿意和你说”。问题是,群众能力有限,心里有意见但提不出来,干部必须去启发他们。如问他乡长怎样?乡上动员工作做得好不好?优待工作怎样?有时,他会敷衍说:“什么都好”。那么,你可以拿别人的意见去问他:“有人说乡长把草钱压了不发,你看对不对?有人说乡长派差使按家户不按劳动力计算,你以为如何?”个别谈话后,要鼓励群众到会议上发表意见,为此,干部要预先做些准备工作,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否则,收集群众意见是很困难的事情*《1941年延安、延长、安塞、固临、鄜县县乡选举工作计划总结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2-1-830。。
毋庸置疑,干部的启发与诱导可以唤起部分选民的政治热情,但以个人付出为代价的政治参与,民众感受到的更多是义务而非权利,因而这种热情是间歇性的,或者说是选择性的,趋利避害是其参与政治生活的原始动机。1941年6月11日上午,延安市东区第一行政村直选乡参议员,300名选民到会的只有一半,“大家对开会总不感兴趣,有人总是托故不到,有人将到会作为应付”。会场上,还有人因闷热的天气而打起了瞌睡*郁文:《选举浪潮中的一角:记延市东区一行政村选民大会》,载《解放日报》1941年6月14日。。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延安县。作为革命老区,延安县的征粮征兵工作一直走在其他各县的前面,但农民对选举没有太高的积极性,部分群众怕当选为议员或乡长。东一区有个妇女被选为乡参议员,大发脾气,连会也不参加了,她说:“你们随便给人放了一个差事”,并说众人把她“咬着”( 连累)了。随后,她和区妇女主任大吵一场,结果开参议会也没来。东二区区妇女主任是乡长候选人,可是,她在妇女中大量活动,让群众不要选她*《1941年延安、延长、安塞、固临、鄜县县乡选举工作计划总结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2-1-830。。
可以看出,较之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选民的参与热情与政治觉悟同样有待提高。好在根据边区各县选举工作报告,不愿当选的只是少数人,选举动员更因“三三制”原则而赢得了边区地主、富农与民主人士的支持*《1941年延安、延长、安塞、固临、鄜县县乡选举工作计划总结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2-1-830。。在选举委员会与群众团体的组织下,根据地选举以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方式全面展开,据边区政府民政厅总结,在一个县的乡选中,115个宣传队和881个工农小组把党的声音直接带给群众,以确保80%以上的选民参加选举。由于选举的目的与意义不仅表现为选民对政府的批评与监督,对基层政权的改造,还承载着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展示中共民主执政能力等多重任务,因而抗日根据地选举动员的技术手段还带有部分竞争性民主的色彩,在延安机关学校的参议员选举中,候选人的竞选报道时而见诸报端*《选举边区参议员,延安市南区竞选热烈》,载《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日。,成为展示根据地民主的名片。
二、 聚焦基层政权的选举方向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工作情况如何?根据1932年5月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工作报告,“一个乡政府经常可有三四桌人吃饭,区政府可有七八桌人吃饭,每月的客饭一个乡政府可开一二百元,因此,党内党外对苏维埃工作的雇佣观念特别浓厚,一般的是不吃苏维埃的饭就不作苏维埃事的观念,一切群众团体均依赖政府吃饭,建立一个群众组织就要津贴伙食办公费等”*《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一、二、三、四月总报告)(摘录)(1932-5)》,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2~83页。。江西省委的工作总结表明这种情况绝非个案,一定带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以打土豪、吃大户为目的的政治参与者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与这一群体的社会出身与经济地位是分不开的。如彭真所言,早期革命队伍中,流氓无产者最积极,但又有着“有奶便是娘”的性格弱点*彭真:《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1941-6-4-8-21)》,载《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页。。
如何做好基层政权的改造?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的选举细则规定:“城市苏维埃和乡苏维埃的主席,不得为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韩延龙、常兆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1931-11)》,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第137页。就制度建构而言,基层政权负责人的回避制度无疑有利于保证选举结果的客观公正。问题是,经过第一次全面选举,地方苏维埃在工作上虽有进步,但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距离甚远。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号训令,有的地方苏维埃领导在完成革命任务的过程中阶级观念薄弱,不积极动员群众到前线参加战争,不领导群众对敌人作坚决斗争,反而畏缩逃跑;有的地方苏维埃还有阶级异己分子隐藏在内,官僚腐化与贪污现象严重。为了加强苏维埃对革命战争的领导,消除苏维埃工作中的一切缺点与错误,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建立坚强而有力的地方苏维埃,担负领导革命战争的任务*《中央委员会第十五号训令——关于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政府问题(1932-9-20)》,载《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增刊,第31页。。
改造基层政权有多种形式。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乡苏维埃须每两个月召集选民开会,做工作报告一次。选民对于乡苏维埃的报告,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代表如有违背选民公意者,或无故连续两个月不出席代表会议者,或违抗代表会议决议经警告不改正者,或犯其他重大错误者,可由选民十人以上提议,经选民半数以上同意撤回不称职的代表,或由代表会议通过,经选民半数以上同意开除之。撤回或开除的代表,以候补代表补充其职务*韩延龙、常兆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3-12-12)》,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4~45页。。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韩延龙、常兆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11-7)》,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第9页。。
问题是,乡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使得根据地政治生活更多地表现为政党对社会的嵌入式动员,作为被动主体的工农群众没有行使撤回权的习惯。1933年8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对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改选运动作出指示,“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也是如此)的斗争中,苏维埃的领导者必须使苏维埃的公民学习使用他们的召回权与改选权。关于苏维埃公民的这一召回权在苏维埃宪法上是分明写着,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告诉群众如何使用这一权力”*洛浦:《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莫克拉西》,载《斗争》1933年8月12日。。张闻天的指示是在中央苏区第三次选举前夕,而此次选举刚一结束即迎来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也就是说,根据地群众几无行使代表撤回权的实践,因而,选举是改造基层政权的主要形式。
193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的选举大会上强调,凡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同地主、富农、资本家妥协的分子都不能当选,要把工作积极、观念正确的工农群众吸纳进来。同时,要注意候选人的工作能力,能力过于薄弱的同志亦不宜到政府工作*毛泽东:《今年的选举》(1933-9),载《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据苏维埃地方政府选举工作报告,经过选举,各地均清除了一批不称职的干部与阶级异己分子。在兴国县长冈乡55个代表中,老代表连选连任占6/10,新当选的4/10*毛泽东:《长岗乡调查(1933-11)》,载《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集》,第212页。;在宁化县城市区,查出了一批偷窃选举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选举运动中查田斗争》,载《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6日。。总结苏区选举,如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所言,依靠工农群众积极参与,吸引了许多新的工农干部参加苏维埃工作,一些隐藏在苏维埃中的不良分子被洗刷出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1933-10-24)》,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7卷,第1144页。。
为使基层政权充满活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规定,市区苏维埃、区属市苏维埃以及乡苏维埃的代表,每半年改选一次;市苏维埃的代表,在居民五万人以下的市,每半年改选一次;居民五万人以上的市,每年改选一次*韩延龙、常兆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3-12-12)》,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37页。。及至1942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乡(市)参议会一年改选一次,乡(市)长及政府委员同时改选,行政村主任、自然村村长每半年改选一次*韩延龙、常兆儒:《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1942-1)》,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235~236页。。革命情境下,改选的方向就是使它能够完全适合发展革命战争的要求,“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1934-4-10)》,载《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3页。,也是乡村政权改造应该实现的目标。
抗战爆发后,根据地选举仍以改造基层政权为中心。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发出指示信,“政府做了些什么工作?老百姓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没有?有优点,优在哪里?有缺点,缺在哪里?要很具体明白地报告出来,请求老百姓检阅”。指示信特别强调乡级工作报告的写法:一要明白具体,容易看懂;二要忠实无欺,好的不夸,坏的不瞒,“把货色摆在老百姓面前,请老百姓来评价”*韩延龙、常兆儒:《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造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1941-1-30)》,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第215~216页。。1941年5月22日,边区政府为改选各级参议会发出第二封指示信,再次强调在各级参议会改选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乡级政府报告工作。政府替老百姓究竟作了些什么?作得如何?按本处的情形,以后应该怎样作才更好些。“凡此种种主人有权利过问,政府有义务向老百姓诚恳的报告”,无论是质问及批评,要诚恳地接受,耐心地解释,发动他们分小组讨论,作成提案,在选举会讨论,并交给新的参议会去办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造各级参议会第二次指示信(1941-5-22)》,载《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279页。。
在“民主政治,选举第一”的口号下,1941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无疑具有彻底改造基层政权的意义。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此次自下而上的改选是成功的。边区80%的选民参加了选举,绥德、清涧、延川则在95%左右。延安县乡政府委员中,新当选者为185人,连任者仅有133人, 61个乡长中有41个是新当选的;绥德旧乡政府人员落选者达1001人;安定70%乡市政府人员是新任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力推动下,仅乡市参议员就选出了4万多*林伯渠:《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11-8-9)》,载《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另据各县选举工作报告,在群众的支持下,淘汰了一批腐败干部,充分证明了民主选举是惩治腐败的良方*《1941年延安、延长、安塞、固临、鄜县县乡选举工作计划总结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2-1-830。。
由此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陕甘宁边区,选民与候选人的选举热情并未完全动员起来,但基层政权中工作人员的淘汰率却很高。看似矛盾的背后是政党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或者说,以民主选举为中心的基层政权改造,更多的是发挥了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想象,在二元对立的革命理念下,落选者失去的不仅是职务,还有工农阶级的身份,如此,在连任与落选的动态过程中,个体必然会体验到身份与角色危机。中国共产党基于选举的身份认证,为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活力,同时,也使得选举成为改造基层政权的有效手段。
以政党为中心考察根据地选举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并不否认选举对根据地民主成长的社会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底层民众真正享受到了民主选举的权利,而共产党鼓励选民对干部提出批评意见,也使得红色民主有了全新的内涵,可以说,彻底翻转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同时,群众参与选举的热情不高,是基于一己私利的利弊权衡,并非不认同选举,因为根据地选举强调的是公共利益,或者说党的利益而非私人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以及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品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动员中虽有偏差,仍能得到选民认同的精神力量。
三、 “三三制”选举的工具效用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当着革命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像过去那样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像过去那样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必须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12-27)》,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153页。。
走出“狭小的圈子”,需要适时进行政策的调整。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原则,根据地各级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做到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3-6)》,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对革命性政党而言,能否赢得最大多数中间力量的支持,无疑关涉组织的生死存亡,因而,“三三制”原则的关键是中间分子的确定。林伯渠指出,中间分子主要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其次是中产阶级,“他们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不能进步到土地革命”。在确定谁是中间分子的时候,要经过党的“物色”,如何“物色”?在林看来,应该“看看他的阶级关系,也看看他的政治态度,看看他的历史,也看看他的现在”,既要掌握原则,又要具体分析*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1944-3-25)》,载《林伯渠文集》,第380~381页。。
针对“三三制”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政治力量不均衡问题,毛泽东指出,“三三制”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3-6)》,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3页。。如何“酌量变通”?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对“三三制”人员的分配要看实际情况,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地主绅士没有了,共产党、非党进步分子数量多一些,中间分子少一些,是合理的*边区政府研究室:《推广三三制(节录)(1945-2-23)》,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1~592页。。通过对未进行土地改革地区(简称:新区)的调查研究,中共西北局办公厅指出,在新区,按照上述精神落实“三三制”原则,同样也是合理的,不如此不足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乡村政权;尤其对于那些刚刚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农民还没有翻过身来(未经减租斗争),倘若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员占了1/3的议席,农民难保不被压倒,所谓“10个小参议员斗不过1个大参议员”*《西北局办公厅关于边区“三三制”经验的初步研究(初稿)(1944-3-23)》,载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4年)》甲5,1994年,第221页。。
中间分子的“物色”与酌量变通的背后是“三三制”原则不能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1942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提出,统一战线首先要代表基本群众,即工农阶级的利益。他们与地主资产阶级在抗日的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不可能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忽视这二者之间的斗争是错误的。“三三制”不是无原则的各阶级各党派的大联合,建设民主政权,不能容许反共分子在内,那种把“三三制”笼统地理解为党外人士占2/3的观点是不对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文献(1942-10-19-1943-1-14)》,陕西省档案馆藏,17-317。。
稳固革命政权的关键是基层政权建设,因而,在抗战初期的陕甘宁边区,中共基层支部直接提名乡参议员候选人几成惯例,问题是乡村中又无其他党派,如此就成了一个政党的选举,有碍选举的程序民主。如何既巩固基层政权,又不失民主的形式?1945年10月5日,中共西北局就乡村选举问题发出指示:支部不预先提出乡参议员或人民代表候选人名单,让群众自由提名;但群众提出候选人后,支部须加以研究,如发现“有坏人或不适当的人”,可经过党员在群众中活动,“设法去掉”。在选举过程中,既要避免发生“代替包办”现象,更要反对“放任自流”的错误倾向*《西北局关于选举问题的指示(1945-10-5)》,载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甲6,1994年,第110~111页。。对共产党人而言,如何把握“宽松适度”的原则确非易事,宁“左”勿右的阶级观念使得政策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
在林伯渠看来,“三三制”原则主要在县级以上政权中表现出来,中间分子在县级政权机关中占取1/3乃至更多一点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要作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1944-3-25)》,载《林伯渠文集》,第376~377页。。为展示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的诚意,边区政府通过的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参议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同级政府认为必要时,可聘请边区内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者为参议员*在陕甘宁边区,1941年11月通过的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政府聘请名额不得超过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参见《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1939年2月)》,载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181页。在晋察冀边区,1943年2月通过的边区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以下简称参议会)由边区公民选举之参议员,及边区行政委员会聘请之参议员组织之。聘请之参议员不得超过参议员总额五分之一”。参见《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组织条例(1943年2月4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7页。。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选举中,中共所提非党候选人中多人未能当选。在中共西北局看来,各县党委领导不力是此次选举运动的最大缺点,妨碍了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进步人士参加边区民意与政权机关的活动。10月15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为了补救这一缺点,边区政府已决定聘请落选的非党候选人为边区参议会正式议员*《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聘请非党民主人士为边区参议会正式议员的通知(1941-10-15)》,载《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79页。。
强调“三三制”选举的统战意义也是中共建构民主政权的内生逻辑。据时任陕甘宁边区建设厅长的刘景范回忆,早在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之时,到会的146名参议员中,就有10人为边区政府聘请的民主人士*刘景范:《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52页。。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51名常驻议员候选人中,因共产党员人数较多,徐特立、肖劲光等6名党员主动要求退出。39名政府委员候选人中,共产党员超过1/3,谢觉哉、马锡五等12名党员主动申请退出*《林伯渠、李鼎铭当选边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按“三三制”选出》,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1日。。为落实“三三制”原则,边区政府发出指示,各县参议会中,共产党员超过1/3的,应该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同时,政府可酌量聘请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各县参议员与政府委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调动离职者,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1942-3-6)》,载《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8页。
受益于“三三制”原则,开明士绅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安文钦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霍子乐为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贺连城为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的民主人士柳湜在《解放日报》上刊文《从这里看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前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根据地政权的赞叹:在边陲的高山深沟里,第一次演出民主竞选的喜剧,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在最落后的边区,如何实行普选的问题,对于许多人是一个谜。国内反民主的政客们,最有力的论据就是人民文化程度太低,不能实行民主。现在,这里给了他们事实的答复*柳湜:《从这里看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前途》,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3日。。
通过“三三制”选举,中国共产党展示了民主执政的能力,也赢得了根据地外社会舆论的认同。1944年,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即西奥多·怀特)在考察延安后坦言,相比国民党,共产党是“光耀四射的”,访问延安的人士,仿佛“是逃脱了国民党的压迫,进入到光明的地区”*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56~357页。。显然,共产党的光芒,离不开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在赛尔登看来,“三三制”还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与无党派人士分享权力并共同有效地工作,使“共产党声称代表全国”有了法律依据*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67页。。
四、 “游击队理论”视域下的根据地选举
“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贺绿汀:《游击队之歌》,载李晓:《群众歌会红歌经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70页。当共产革命在中国以游击战的形式全面展开的时候,必然影响政治领域的制度建构。梳理根据地的选举动员与制度成长,它高度契合于施米特总结的游击队理论——依托大地的品格、高度灵活的积极战斗、非正规性与高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等特点*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以“游击队理论”考察根据地选举,可以发现根据地制度成长的另一面相。
通过选举这一“武器”,根据地工农群众被组织起来,而选举的民主形式则赋予了政党底层动员行动的正当性,成为依托大地的有效形式。在中央苏区,中共建立了苏维埃代表与居民的联系制度,根据1933年12月12日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在市、区、乡苏维埃与区属苏维埃管辖的全境内,为着代表与居民的密切联系,便于吸收居民意见及领导工作起见,应本着代表接近居民住所的原则,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通常以居民30人至70人置于1个代表的领导之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下的居民发生固定关系*韩延龙、常兆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3-12-12)》,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28,38页。。根据毛泽东长冈乡调查,乡苏维埃每个代表管理居民二十几人至五十几人不等,每个代表手中有一个居民册,册上分为男成年、女成年,男少队(可当长夫)、女少队(可当短夫),男儿童、女儿童;成年人又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长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新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等。在毛泽东看来,值日代表10天一换太频繁了,应选择最好的代表任职1到2个月*毛泽东:《长岗乡调查(1933-11)》,载《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集》,第208~209页。。选民的组织化管理对于提高组织的动员能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如毛泽东所言,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乡苏维埃怎样工作(1935-12-26)》,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博古、陕甘省委宣传部1933 至1935 年关于土地斗争、阶级分析,对富农政策问题的决定、命令及有关材料》,陕西省档案馆藏,4-1-2。。
游击队理论强调“灵活、迅捷、突变”的机动作战*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278页。。根据地选举制度的成长同样呈现出非连续性与突变的特点。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选举强调阶级民主的至上性,通过考察个体在查田、征粮与征兵运动中的表现,深挖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地主、富农与阶级异己分子。及至抗战爆发后,根据地政权建设转而强调“三三制”的组织原则,强调给予开明地主、绅士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由此可见,较之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是制度突变,或者说断裂。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间力量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三三制”原则就成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符号,失去了制度成长的意义。
回到选举委员会的建构,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都强调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回避制度。1941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法院、驻军长官,不得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规定*韩延龙、常兆儒:《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1941-1-1)》,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第207页。,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但及至1945年,根据修改后的边区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各级选举委员会受同级政府的领导,选举委员会委员人选由政府聘任政府、群众团体、抗日党派代表及当地公正人士组成,也就是说,取消了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回避制度*《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改意见(1945-8-28)》,载《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制度成长的非连续性还体现在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以及新中国政权建设中各级代表或议员产生的方式上*中央苏区实行间接选举,即由选民选出乡代表,乡代表选出区代表,区代表选出县代表,形成宝塔式选举;抗日根据地则实行直接选举,即由选民直接选出乡议员、区议员、县议员直至边区议员;新中国成立后,又转而实行间接选举制度。。可以说,根据地选举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的多是碎片化的制度遗产。
总结游击战特点,施米特指出,队员们在隐蔽处作战,“不仅使用敌军的制服,也佩带或固定或临时的标识,更经常穿任何一种便服作掩护”*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291~292页。。回到中国战场,毛泽东强调,革命者要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8-6)》,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1页。。以独立自主为例,毛泽东提出了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十六字诀*毛泽东说:“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在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参见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页。。军事上的游击战必然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那就是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正规—非正规、合法—非法”的相互交错*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278页。。
在陕北,新开辟的中共控制区域,事实上存在着国共双重政权。以米脂县为例,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米脂划入八路军绥米佳吴清警备区,同时,保留国民党县级政府的组织机构。1938年夏,中共成立米脂县抗敌后援会,通过发动与组织群众,逐渐替代了国民党县政府,也就是说,米脂事实上存在着双重政权。1941年8月31日,绥德专署专员曹力如致信边区政府,米脂县选可否将县长选出,让高仲谦(国民政府任命的县长)“滚蛋”?边区政府函复绥德专署:米脂系榆林专员区的建制,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副司令高双成曾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变更县长,以免国民党省府责备他们。米脂不选县长,可以与邓、高维持友谊关系,不使他们左右两难。事实上,只要中共地方党组织将参议会及下层政权机关整理好,即可实际掌握县级政权。如逼走高仲谦,实际上等于选县长,将使邓、高的处境更为困难,而影响中国共产党与邓、高的友好关系。同时,高仲谦系中统系统,在陕西省党政系统中正受到(新)政学系及朱家骅系的打击,米脂党组织应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对高采取灵活策略。米脂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佳县*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给绥德专署专员的函——复米佳县选及该区公粮意见(1941-9-15)》,载《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69~171页。。如此,根据地选举的“游击”策略得到了充分体现。
制度表象的背后是中共基于生存政治的动员逻辑。如毛泽东所言,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城市和农村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能滋生冒险主义的急性病,必须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去进行*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12)》,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页。。毛泽东的主张是军事上,也是政治上的,那就是要善于根据生存需要修正行动路线,而理论的本土化就成为化解冲突的最好理由。基于此,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根据地政权选举,可谓政治领域的“游击战”。
五、 结 语
宪政情境下,民主选举是推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工具,强调社会正义、程序公正。同时,选举以竞争议会议席与国家领导人为目标,而选举的高潮与热点也聚焦于此。共产革命在颠覆旧世界的同时,它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新世界。按照革命蓝图建构乡村秩序,必然是反传统的,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它需要坚固的基层政权去推动社会变革,去占有革命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在此意义上说,根据地选举确实具有“战斗”的意味。
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力推动下,根据地乡村社会的选举得以运转起来,但选民的被动参与决定了以选举为手段的基层政权改造,更多的是共产党人的自主性行为,并打上了战争动员的烙印。从赢得生存空间出发,中共倡导的“三三制”选举也充分展示了制度的灵活性,从中间分子的“物色”到“三三制”原则的酌量变通,从基层政权的坚守到“三三制”原则主要在县以上政权中体现出来。可见,当选举内化为战斗的“武器”时,不同时期的选举必然呈现差异性特点,表现为制度成长的非连续性、突变与碎片化。
●作者地址:王建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Email:wjh7@sina.com。
●责任编辑:何坤翁
◆
The Guerrilla in Political Fiel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Democracy:Elections in the Local Ruling Period of CPC
WangJianhua
(Nanjing University)
Whil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subverte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order in village,it was construc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red democracy in the base area.Under the enforcement of CPC,elections were made to work in the base areas from Central Soviet toShanbei(陕北).However,the fact that voters were involved passively has determined that the elections were only the autonomous behavior from CPC and were aimed at war mobilization.To survive,CPC advocated a “tripartite election”,fully displaying the flexibility of the system.Exploited as the “weapon” for war,elections would certainly diversify in different periods,being discontinuous,mutational and fragmented in institutional growth,conform to the “The Theory of the Partisan” proposed by Schmitt.
democratic election; Central Soviet; red democracy; Soviet
10.14086/j.cnki.wujhs.2016.05.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3BDJ00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5ZDAXM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