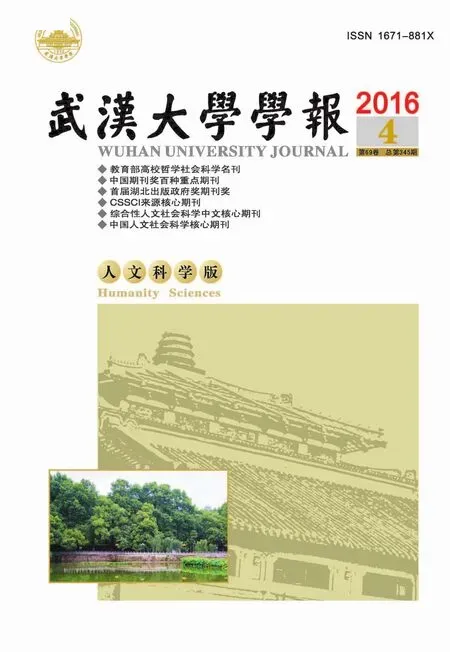讽寓·语境化·规范性
——综论欧美汉学界《诗经》阐释学研究
2016-02-21李会玲
李会玲
讽寓·语境化·规范性
——综论欧美汉学界《诗经》阐释学研究
李会玲
摘要:欧美汉学家将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定义为西方阐释学话语中的“讽寓”、“语境化”和“规范性”。他们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理性化的分析态度摆脱了前期学者对中国《诗经》道德化阐释的反感情绪,开创了《诗经》阐释学研究的新领域,带来《诗经》研究的新变革。但对中国《诗经》研究中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特别是《毛诗序》研究中的盲点问题,导致他们在用西方阐释学术语来定义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的时候存在着诸多的片面性。关键词: 《诗经》阐释学; 《毛诗序》; 欧美汉学界
自比利时来华传教士金尼阁将中国的“五经”翻译成拉丁文本,1626年在杭州镌板印行以来,《诗经》在欧洲的传播与研究已经有近4个世纪的历史。二战后,随着世界汉学中心由法国转移到美国,《诗经》西传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北美。柯马丁总结北美《诗经》研究现状时说:“新近的研究成果常常着力于诠释学的专门问题、文本的早期接受以及由出土文献中出现的《诗经》片断而带来的特定问题。”*柯马丁:《学术领域的界定——北美中国早期文学(先秦两汉)研究概况》,载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年,第576页。北美《诗经》研究重点之一的阐释学研究以三本著作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分别是余宝琳(Pauline Yu)的《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读法》(TheReadingofImageryintheChinesePoeticTradition,1987)、范佐伦(Steven Van Zoeren)的《诗歌与人格:中国传统的读解、注疏和阐释学》(PoetryandPersonality:Reading,Exegesis,andHermeneuticsinTraditionalChina,1991 )和苏源熙(Haun Saussy)的《中国美学问题》(TheProblemofAChineseAesthetic,1993)。这些著作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怎样认识《毛诗序》及其影响下的儒家注释,其核心观点流行于欧美汉学界并影响中国学界。本文着力梳理欧美汉学家在阐释学视域中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的认识与定义的过程;并分析这些认识对《诗经》学带来的新变革,以及在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 欧美汉学界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的认识与再认识
最先遭遇中国《诗经》阐释问题的是翻译家。欧美世界最具盛名的《诗经》英译本有三:理雅各(James Legge)1871年译本、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937年译本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942至1946年发表于《远东古博物馆学报》上的《诗经》语词汇注*柯马丁:《学术领域的界定——北美中国早期文学(先秦两汉)研究概况》,第572~573页。。理雅各广泛参考中国传统《诗经》学成果,但倾向于遵循朱熹的注解。他认为,如果遵信序说,将使许多诗篇降为荒唐的谜语。高本汉批评中国卷帙浩繁的《诗经》文献时说:“那些著作,大半都是没有价值的,可以置之不顾,因为总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些传道说教的浮词。”*高本汉:《高本汉诗经注释》,董同龢译,中西书局2012年,《作者原序》第1页。
如果说理雅各、高本汉等译者对《毛诗序》及中国传统《诗经》注解的看法停留在宋代“废序者”的认知上,翟理斯(Herbert Gilles)189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则已经开始引导人们朝“讽寓”的方向来定义《诗经》的汉唐注疏。只是翟理斯还没有使用“讽寓”一词。他说:“上古的注释者看不到这些诗歌朴素自然的美感 ……又不能无视圣人深思熟虑的评判,便努力从这些民间歌谣中解读出深刻的道德与政治意义。《三百篇》中每一篇不朽的诗歌就这样不得不衍生出许多隐含的意义,并导出一种特有的道德寓意。”*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卞东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页。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他的《古代中国的节庆和歌谣》(1919年)中开始把以《毛诗序》为中心的《诗经》汉唐注释定义为“讽喻式阐释”和象征主义*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和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导论》第5页。。于是,“讽寓”一词就成为欧美汉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内最流行的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的定义。韦利在他的《诗经》译本的附录中声称《诗经》三分之一以上的诗都被“寓言化注释”*Arthur Waley.Thebookofsongs.New York:Grove Press,1960,pp.335~336.了,并指出这种寓言化类似于西方学者对《圣经》的诠释。王靖献在《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中干脆直接将秦代以后的《诗经》学称为“寓意阐释学”*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页。。他借用套语理论来研究《诗经》的创作方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从源头上解构中国传统《诗经》学中的道德象征主义和“讽寓”性阐释。
如此,“讽寓”一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俨然成为欧美汉学界对中国《诗经》汉唐注疏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及命名,直到余宝琳提出异议。1983年,余宝琳发表《寓言、寓言化和〈诗经〉》(Allegory,Allegoresis,andtheClassicofPoetry)一文,专谈《诗经》及其“传统评注家理解《诗经》的方法在怎样的程度上能称之为讽喻化的批评”*余宝琳:《讽喻与〈诗经〉》,曹虹译,载莫砺锋编:《神女之探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页。的问题。1987年,其专著《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读法》出版时,她将前文稍事修改作为此书第二章的主要部分。与绝大部分的汉学家将中国传统的《诗经》注解定义为“讽寓”的做法不同,余宝琳认为西方学者把三百篇统统看作是讽寓之作(allegory)是不准确的,把中国传统的《诗经》笺、注看作是“讽寓解说”(allegoresis)也不确切。她主张用另一术语“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来代替“讽寓”。
余宝琳并不否认《诗经》汉唐注疏中“言此及彼”的明显的荒谬性;她力图论证的是“讽寓”这一西方阐释学术语对中国传统《诗经》学的不适用性。她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中西文化相异之源的本体论的高度来论证。她说:“西方诗人在模仿上帝造物主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虚无的世界”;“西方讽寓作家力图证明希腊神话包含一种更深邃的哲学或宗教的意蕴——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维度”,而“(中国)尽管某些设想与西方的相似……但它们所依赖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认同一种本质性的一元宇宙观……真正的现实不是超凡的,而是此时此在的,而且在这个世界中”*Pauline Yu .TheReadingofImageryintheChinesePoeticTradi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32~33.。既然没有“彼岸世界”可资参照,她就认为《诗经》中的诗歌不符合“讽寓”创作的西方模式。不仅《诗经》中无“讽寓”性创作,她还认为中国传统《诗经》注解也无“讽寓”性。她说《诗经》的儒家注释者“通过证明它植根于历史来让这部诗集合理化”,展示的“不是形而上的真实,而是此岸世界的真实,一种历史的语境”;所以,“建立在另一套与西方的隐喻或讽寓从根本上就不同的设想上”*Pauline Yu.TheReadingofImageryintheChinesePoeticTradition,p.82.的中国传统《诗经》注释只能说是一种置本文于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的“语境化”的解读方式,而非“讽寓化”的阐释。余氏此论引发强烈回响,欧美汉学界、比较文学界的学者纷纷著文回应。大家在中西文化、比较文学、文艺美学和《诗经》阐释学的交汇点一起来讨论“讽寓”这一西方文论概念的中国适用性问题*参见张隆溪系列文章。张隆溪:《讽寓》,载《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第53~58页。张隆溪:《文为何物,且如此怪异》,载王晓路主编:《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第35~62页。。苏源熙的《中国美学问题》也是对余宝琳的回应之作。针对余宝琳的重新定义,苏源熙从“讽寓”术语的多面性出发,指出《诗经》与其汉唐注疏之间的关系符合西方文学范畴中“讽寓”的定义。他认为:“讽寓”并不拒绝历史的“语境化”,西方的“讽寓”也“决不依赖超验的主题”;“从古代修辞学专业与无教义的意义上说,‘讽寓’即说一个事物而意味着另一个,而不管这个事物说了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余宝琳等以为中国无“讽寓”是把“神学家的讽寓”而不是“语法家的讽寓”当作了“讽寓”的典型,所以得出错误结论*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31~33页。。
然而,重新肯定中国传统《诗经》注解的“讽寓”性特征,并不是苏源熙的主要目的。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诗经》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言此及彼”的“讽寓”性的解读方式?这样解读《诗经》的目的以及它们的社会作用分别是什么?他认为:如同大人告诉孩子们的仙境“成为一个关乎理解的领域,一个完美的参照中心,以及可为规范的基地”*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87页。一样,“经常进行道德化及历史化的批评,同时有着描述性及规范的一面......为‘王道’——政府的教化使命——提供一种范式”*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103页。。注释者为着完成教化使命有意识地通过《诗经》注释、解读使诗歌成为社会伦理的规范;就像《伐柯》一诗中的“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使自然成为重塑自然的一柄斧子”*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145页。一样,注释者把《诗经》“当作规范来读”*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129页。是为了形塑和规范未来社会。这样,苏源熙又给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起了一个新名字——规范性阅读。
从“讽寓”到“语境化”,再到“规范性”,可以看到欧美汉学界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定性、命名到争论,到重新定义的步步深入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诗经》连同它的传统注解经历了一场异质文化、文学视角的审视与再审视。这场审视给《诗经》研究带来什么呢?
二、 西学话语中《诗经》阐释学研究的新视野
欧美汉学界关于《诗经》及其中国传统注解的定性讨论,看似是一个新问题,其实是中国《诗经》学史中的一个老问题——《毛诗序》及其影响下的历代注解——在新的语境和学术视域中如何定性与定义的问题。《毛诗序》在中国从汉至唐的《诗经》学史中曾占据核心位置。经过宋代的“尊序与废序之争”和民国“古史辨派”的猛烈抨击,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多数读者来说,它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不需要再讨论的问题,朱熹的一句“穿凿附会”早就给它定了性。可是,对于欧美汉学家来说,如何在他们本土的学术体系中来认识和定义以《毛诗序》为中心的那些看起来明显不符合《诗经》本文的儒家注释呢?西方源远流长的“两希”经典的阐释学研究给他们提供了现成的借鉴。
“讽寓”、“语境化”、“规范性”都是西方阐释学中的常见术语。从“讽寓”、“语境化”到“规范性”,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欧美汉学界《诗经》阐释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力求在西学话语体系中认识、把握中国传统《诗经》注解的性质及其背后的文化及社会意义。这一做法给中国传统的《诗经》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打开了新的视界,并产生了许多具有变革意义的《诗经》学研究成果。
首先,汉学家通过“讽寓”等概念,把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纳入到世界学术之林,使中国《诗经》及其释经学借助西学话语参与到世界文学、学术的对话与比较研究中去。 “讽寓”的基本含义是指在表面意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寓意的文艺形式。在阐释学中,它最早与荷马史诗的解释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以为荷马史诗在神话故事的字面意义之外,还深藏着关于宇宙和人生的重要意义,讽寓( allegory)和讽寓解释(allegoresis)的观念便由此产生。后来又有学者将荷马史诗的讽寓解释法引入《圣经》的解释,于是“讽寓”一词就成为两希经典——希腊荷马史诗与希伯来《圣经》——的阐释学的常用术语*张隆溪:《讽寓》,载《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第53~58页。。当《诗经》及其丰富的阐释材料进入欧洲汉学家的视野时,《诗经》本文与以《毛诗序》为中心的历代注解之间明显的不一致性,极易让人联想到西方阐释学中“言此及彼”的“讽寓”阐释法。于是,中国的传统《诗经》阐释学就有了一个西方阐释学的新名字——“讽寓”。
“语境化”也是西方普通阐释学中一个概念。阐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为了克服早期诠释学中单一的语义学分析的局限性,曾提出过历史情境的“心理重建”方法。他认为读者要把握作者在所创作的文本中表达的原意,就必须通过一种“心理移情”的方法,在心理上进入作者创作文本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重建文本与它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余宝琳等汉学家看到《诗经》汉唐注解,特别是《毛诗序》与《左传》之间的密切联系,就借用过来,将之定义为历史“语境化”。同样,“规范性”也是西方普通阐释学中用来概括经典的权威性所带来的社会作用的一个常用语,范佐伦、苏源熙移植过来用于他们对中国《诗经》传统释经学的研究。
其次,通过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史的反思,欧美汉学家开拓了《诗经》阐释学研究的新领域。《诗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研究史中,作为经典不断地被重新阅读与理解。人们一方面进行着语文学的考据工作,力求恢复《诗经》原意,以便将从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忠实地传给后代;另一方面进行着阐发义理的解经工作,力图发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神秘意义,如汉代经学家在其间发现“美刺”之旨,宋代理学家深挖字里行间的“修、齐、治、平”之术。在整个过程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阐释经验和一大堆有关《诗经》学史的批评性反思意见。可是,同样是经典,中国两千多年的《诗经》释经史中并没有发展出如西方学术中《圣经》阐释学那样的《诗经》阐释学,即没有产生出对阐释现象和此现象所涉及之各种因素——作者、文本、读者以及它们三方之间关系所延伸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的学问。如果硬要找的话,在孟子和欧阳修那里曾经有那么一点点的《诗经》阐释学的萌芽。可是,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读诗方法并没有发展出如施莱尔马赫那样的“心理移情”和“历史语境”等系统的阐释学理论。欧阳修将宋以前人们对诗义的解说归纳为“诗人之意、圣人之志、太师之职、经师之业”*欧阳修:《诗本义》卷十四,《四部丛刊三编》,上海涵芬楼影印吴县潘氏滂憙斋藏宋刊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四大类;但是,他的这种对《诗经》文本与解说者之间关系的理性化分析,很快就被宋代的“疑序者”们对《毛诗序》的强烈反感情绪所淹没。这种反感从宋代的“尊序与废序”之争起,经元、明、清,再经民国“古史辨”派,一直持续到中国的现代学术中。正如张隆溪所言:“我们厌恶传统的《诗经》注解……因为它们解读诗歌的方法,把诗歌糟蹋为欺骗性意识形态的宣传,而我们早已抛弃这种宣传。”*Zhang Longxi.“The Letter or the Spirit:The Song of Songs,Allegoresis and the Book of Poetry”,inComparativeLiterature,1987(39),pp.213~215.直到近代,欧美汉学家用西方阐释学中的“讽寓”概念来定义《诗经》的汉唐注疏,人们才开始重新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注解“言此及彼”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原因。于是,中国《诗经》阐释学就在西学话语体系中建构起来。
欧美汉学家借用西方阐释学术语来定义中国传统的《诗经》阐释学,其准确性如何,是下一个话题。这里要说的是这种引入和借用,继《诗经》因翻译而进入世界文学之林以后,又创造了一个让中国《诗经》阐释学可以与西方学术对话的平台。否定性的定性认识也好,适用性的争论也罢,《诗经》的阐释学研究在一片质疑之声中粉墨登场了。
再次,欧美汉学家的《诗经》阐释学研究中理性化的分析态度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解决了许多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被搁置的问题。无论是葛兰言最初借用“讽寓”一词,还是余宝琳否认其“讽寓”性,并用“语境化”来代替,以及范佐伦、苏源熙在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称之为“规范性”,这些都建立在对中国历代《诗经》注解“言此及彼”的阐释现象的理性化分析之上。他们的分析并非都符合历史实际,但他们都摆脱了大多数中国本土学者以及欧洲早期翻译家所持有的那种对《毛诗序》等传统解说的反感性情绪,并且在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引导下进行理性分析。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带来了《诗经》研究的新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的《诗经》注解,卜松山说:“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诗篇,我们仍必须首先弄清以下几个问题:1.这些道德说教的解读实践从何而来;2.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解释;3.有哪些依据;4.以及它们对中国文学、艺术和阐释实践产生了什么影响?”*卜松山:《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页。纵观欧美汉学界《诗经》阐释学研究,大家基本上都围绕着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理性分析。
率先思索并回答以上问题的葛兰言并不是不反感中国传统《诗经》学中的道德说教,但是他并不被这种反感情绪所左右,而是认真分析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读实践以及这种解读产生的后果。由此,他在当时法国年鉴学派兴起的学术潮流中用社会学、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在季节性仪式和庆典中产生的“风诗”,从而开创了《诗经》的人类文化学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诗经》传统阐释中政教、伦理批评的产生根源也是余宝琳、范佐伦、苏源熙一再追问的问题。苏源熙的《中国美学问题》就是一部问题解答集。除了回答“《诗经》的文本以及自《诗经》被立为经学以来就和它共存并生的《诗序》、传疏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不是西方文学范畴中所谓的‘讽寓’”*邓建华:《苏源熙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载王晓路主编:《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第473页。这一问题外,他着力解答中国《诗经》“讽寓”化阐释的哲学、文化根源、目的及社会作用等问题。其中,《毛诗序》是他研究的重中之重。他说:“如果《毛诗序》是一种古代误读的起始,那么试图解释它们的历史批评必须(像史诗中的缪斯一样)说明最初的误解发生在何处。”*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66页。通过对“《诗大序》的观点是什么,它的逻辑何在,怎么解释它压倒性的影响力”*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97页。等问题的思索和追问,他发现“《诗序》所谓‘穿凿的解释’并非开始于一个局部的错误,然后通过传播与重新解释的链条而扩散;而是产生于一套明确打算要系统实施的先见。”*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66页。
宋代以来,中国学者就一直在《毛诗序》是否真实地传达了《诗经》的原意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却很少在伽达默尔阐释学所谓的的三大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中去分析作者意图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而范佐伦、苏源熙等在西方阐释学视角中,从阐释者自身在历史文化中的性格出发,创造性地把理解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理解,将《毛诗序》从它与《诗经》原意的纠结关系中剥离开来,渐渐接近对《毛诗序》本质的认识了。
最后,欧美汉学家对中国《诗经》传统释经学中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但解决了中国《诗经》学史中长期让人困惑和争论的问题;而且由此生发出来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结论已经成为当今中西学术的共享性成果。例如:葛兰言因着对“讽寓”问题的探究,开始用社会学、民俗学视角和理论研究《诗经》的起源和原始意义。这一方法经过日本学者白川静和中国学者叶舒宪等发扬光大,如今已经发展成蔚为大观的《诗经》研究的分支——《诗经》人类文化学研究。《诗经》不同诗歌中相同的习语所产生的时间上的混乱性,一直是困扰《诗经》注疏者的一个大问题;王靖献运用套语理论来研究《诗经》的创作方式就非常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说:“类似于镶嵌图案的习语创作所产生的时间的非一致性,应被看作是口述套语诗歌的特征标志之一”*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第8页。。
如果说,在以训诂、注疏及义理阐释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诗经》学中,人们主要解决的是《诗经》“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从西学话语体系中兴起的中国《诗经》阐释学在反思中国传统《诗经》学的过程中,更多解决的是中国传统注疏“为什么”如此阐释、呈现出怎样的阐释特色,以及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力等问题。这些在阐释学视野中的系列研究内容的出现转变了过去中国本土《诗经》学研究的方向。如今,中国本土学界各种《诗经》阐释学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都有赖于欧美汉学家的开创之功。
三、 缺陷:简单化处理复杂的中国《诗经》学史
欧美汉学界《诗经》阐释学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毋庸讳言的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将复杂的中国《诗经》学史进行简单化处理。
将中国《诗经》学史简而化之是整个欧美汉学界《诗经》研究者的共同做法,其中苏源熙表达得最为直接。他说:“事实上,最古老的评注和19世纪的评注间的区别是微小的。”在注释中他更具体地申述了这个观点。他说:“《诗经》最早的注释已经对大量矛盾持折衷态度。它们固定了几世纪的研究成果,同时为一个阶层的士人所阅读,这些士人遵循这些注释并对其加以补充。既然下文的讨论指向的是读者及解读方法的类型而不是历史学,所以摒弃了大部分影响、时代与学派的细节。”*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127页。的确,整个中国传统《诗经》学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毋庸置疑的一致性。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思潮与学术风气的变革,《诗经》的读者群及解读指向在漫长的中国《诗经》学史中,即使是在经学体系内部也曾发生过多次转向。而对这一问题的忽略导致了欧美汉学家《诗经》研究的盲点,及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进行类型化分析时存在着定型不准的问题。
在漫长的经学发展史中,《诗经》的读者群发生了数次大的转向,而读者群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说诗目的及解读方向的改变。这些变化使中国《诗经》学史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周代,诗歌的收集、整理是周王朝政治体制中“巡狩”制度的一部分。《说苑·修文》:“天子曰巡狩,诸侯曰述职。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职者,述其所职也……天子五年一巡狩……见诸侯,问百年者,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刘向:《新序、说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64页。目的是了解地方风土人情并作为考察各诸侯国治政之绩的依据。收集起来后最早的读者群主要是“王者”、“天子”。那时,并不存在诗歌解说的问题。春秋时期,《诗三百》编辑成集,成为太师、师氏、保氏教授“国子”及“贵游子弟”的教科书。《诗三百》的读者群变成了国家未来的执政者和他们的老师。“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国语·楚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28页。,目的是培养未来国君的品德和执政能力。汉代,著名的“以三百五篇谏”*《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01页。的王式之辩告诉我们,《诗经》的读者群依旧是执政者及其老师。也就是说,至少在西汉前期以前,《诗经》的读者群一直是统治者而不是下层民众。汉中期以后《诗》分多家,各家争立官学地位的局面,导致《诗经》的教授者即解说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经师们争相迎合统治者的旨趣,从而引起说《诗》方向的改变,由针对上层统治者的修德解说转向了针对下层被统治者的教化解说。魏晋南北朝,纷乱动荡的政局中,《诗经》学术曾一度沉寂。唐初,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命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并将之作为各级官学教育中的指定教材和科举“明经”科的考试用书*蒋方:《诗经与唐代教育》,载《北方论坛》2008年第4期,第115~119页。;《诗经》学术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者和统一思想的工具。至此,经典阐释所要说服、教育的对象由周、汉时期的统治者下移为所有的争取功名的读书士子,其注疏、解说的目的沿着汉中期以后经师们的教化解说进一步加强。宋代,“尊序与废序”之争此起彼伏,《诗经》学术分为两途,汉学与宋学分庭抗礼。朱熹反对《毛诗序》及其汉唐注疏,固然有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原因,最初起因却与他的初识者身份有关。他说:“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朱鉴:《诗传遗说》卷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第17页。。20岁的读书士子和视野不广的乡先生自然读不懂《毛诗序》厚厚的历史积淀。他后来“废序”、还原“诗三百”的“里巷歌谣”性质、“集传”《诗经》,是他以诗人与理学家的双重身份研究《诗经》的结果;目的是在文学家读懂《诗经》原义、体味个中情感的基础上,进行理学家的说教。这一说诗路径与周代针对统治者修德治国的说诗路径迥然有别,与汉、唐时期针对读书士子、下层民众的统一思想的教化说诗又有新变。元、明为朱学羽翼,清代汉、宋争锋,左右袒。民国“古史辨派”是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文史研究者,他们面对的读者群是新学术体系下大学校园内的文学青年。周、汉之际帝王之师的修德解说和汉、唐时期御用经师的教化解说都是他们所急于推翻和打破的枷锁,在民歌整理运动的时风影响下自然要强调“风”诗的文学趣味与民歌特色;所以他们选择继承朱熹以来的文学说诗,而唾弃汉唐注疏中的政治、道德化解说。
从以上简单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漫长的中国《诗经》研究历史中,即使是在经学的体系内部,《诗经》的解说者与读者群的身份地位也都是一再变化的,注解的目的也随之数变。并不像苏源熙所说的那样“最古老的评注和19世纪的评注间的区别是微小的”,中国几千年的《诗经》学研究成果也并不只是简单地对古老注释的“遵循”和“补充”。至于历代评注之间的相似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是文字、音韵、训诂等语文学方面的确定性与固定性;二是经典阐释的传承性。传统的生成过程是不断阅读的积累过程,任何一次对经典文献的阅读的精髓都会积淀到传统的本文中,从而成为后世阅读的起点;后世的阐释即使发生新变也需要袭用前代正统话语,借助其权威性来增强说服力。
以苏源熙为代表的欧美汉学家只看到几千年来中国传统《诗经》学的相似性,却对其沿袭传统中的数次新变缺乏认识,其中的盲点问题是《毛诗序》。
四、 盲点:无视《毛诗序》文献与解读上的复杂性
《毛诗序》是《诗经》研究中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它始终是中国《诗经》学史中讨论的第一对象,同时,又是其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部文献。中国学术大转型后,《毛诗序》明显被分为两半:一半是《诗大序》作为中国文论的开山鼻祖进入文艺学讨论的领域,另一半是“小序”被讥为是对《诗经》主题“穿凿附会”的解释而束之高阁。目前,中外学术界对《毛诗序》的研究都分为两途:一方面在文学艺范畴中讨论《诗大序》的诗学命题及其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并将其与西方诗学、美学理论相比较;另一方面在《诗经》阐释学领域中重新认识《毛诗序》。
欧美汉学界《诗经》阐释学研究中所谓的“讽寓”、“语境化”、“规范性”都是主要针对《毛诗序》的小序而言的。欧美汉学家特别是范佐佐、苏源熙对中国长期的道德化、政治化《诗经》解读已经进行了非常深入细致的分析,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了。但是,他们的问题是全盘接受朱熹以来的对《毛诗序》的否定性论断,完全无视漫长的《诗经》学史中与“废序”派相左的另一“尊序”派的研究成果,也无视《毛诗序》文献形成的复杂性,以及后世对《毛诗序》的误读与误用,将《毛诗序》与其后的儒家注疏视为铁板一块,从而导致了他们对中国《诗经》阐释学进行定性研究时存在诸多的片面性。
《毛诗序》有许多难解之谜,成书何时、作者为谁等文献学上的疑问首当其冲。在漫长的研究史中,有些谜已经解开,如宋代学者将“小序”分为首句和“续申之词”的观点经清代四库馆臣的肯定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定序首二句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四库全书总目·诗序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19页。,不仅仅是作者、时代不同的问题,更在于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说诗方向与路径。中国传统的《诗经》学者虽然没有将《诗经》研究上升到阐释学的高度,但是凭借深厚学养与学术直觉,将二者分开,就是敏感于它们的说诗路径不同。这种文献学上的清楚认识为清中期的四库馆臣所继承。对于《毛诗序》说诗路径的正确理解也一直反映在“尊序”派的研究中,如宋代的吕祖谦、严粲、陈傅良以及清代的部分学者。但是,当“废序”派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后,再无人去细究被重重瓦砾所掩盖的真相。欧美汉学家在这些问题上也缺乏细察,将《毛诗序》未解和已解的谜都付之阙如,全面接受宋代“废序”派以来直到民国“古史辨”派们的观点。
《毛诗序》处于周、汉诗说分途的转捩点。其中既有周代“国史”、太师们针对“天子”、“国子”的修德说诗遗存,又有像王式之类的人物身为帝王之师在尴尬境地中借说诗以“谲谏”的曲说之词,还有“毛苌以后经师”误读“首序”而作的“续申之词”。三者之间的纠葛因古代学者著作权意识的缺乏以及历代文献的叠加让人很难辨识,以至于误解迭起。
从朱熹起,“小序”中的“刺××”、“美××”之语就被讥笑为是对“风诗”主题的“穿凿附会”性解释。可是“小序”的“刺××”、“美××”并不是对诗歌主题的解说,而是把一国之“风”所反映之事,如民心所感、风俗好坏等,全都归根到该国统治者的德行上,认为这个国家内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品德及行为影响下的产物*李会玲:《〈孔子诗论〉与〈毛诗序〉说诗方式之比较》,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597~602页。,统治者即是《诗大序》中一再提到的“上”和“小序”中的某位君王。“小序”是在这个意义说一首反映美好风俗的婚嫁诗是“美诗”,一首反映不良风气的幽期密约的恋爱诗是“刺诗”的。这跟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孙钦善:《论语本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4页。的为政思想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毛诗序》中的“美、刺”与诗歌创作中的“美、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小序”的“美、刺”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说诗之外的统治者的德行问题,而不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谈诗歌内部的人物形象问题。
误读、误用从《毛传》及“续申之词”开始。他们将《毛诗序》“言诗之外”的修德“美、刺”论误读为诗歌创作上的“美、刺”。同时,争立官学地位的经师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旨趣,还把《毛诗序》中针对“上”之修德的教化论的矛头调转,指向了“下”。这样,《诗经》和《毛诗序》都变成了教化下民的统治工具。而实行这种转向的策略便是欧美汉学家所说的“讽寓”解读,通过赋予《诗经》名物以它们并不具备的某种特质来实现。范佐伦曾说过,如果说整个西方哲学是柏拉图的一个注脚,那么,“中国阐释学思想绝大部分都是对《诗大序》的一种评注。”*Steven Van Zoeren.PoetryandPersonality:Reading,ExegesisandHermeneuticsinTraditionalChina.Redwoo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81.确实如此,但是正如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并不都是对柏拉图的正确解读与精髓继承一样,中国《诗经》的儒家注释也在沿袭传统的过程中偷梁换柱地转变了说诗的方向。以为《毛诗序》教化论的主要内容与后来儒家注释一样是统治者以诗歌为教化下民的策略的观点是对《毛诗序》的误读和对《诗经》学史缺乏细察。
误解《毛诗序》的教化论之所指,将“小序”误会为是对诗歌主题的解说,必将会在许多事情上感到困惑。到底是该把“小序”中的“美”、“刺”对象放进诗内还是放在诗外,一直是中国《诗经》释经史上的疑难问题。苏源熙在论《桃夭》时说:“对一首足以自我解释的诗,后妃似乎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忽略后妃的存在就是证明后妃的出现是不必要的。12世纪时的大儒朱熹对后妃在这里牵强附会的出现也很不满,甚至《毛诗》派的注释者也对后妃的出现感到难办:学者们对把后妃放入诗中(作为祝福的新娘),还是放在诗之上(作为国家无数婚礼的鼓励者)颇有分歧。”苏源熙对此的理解是儒家注释者让“后妃”进入诗中是为了实现诗歌的“规范性”阅读,因为“后妃是唯一一条‘周王’可以进入《桃夭》的管道”;从而“把诗歌化约成‘风吹草偃’的寓言”*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125~127页。。苏源熙的解释适合于《毛诗序》以后的儒家注释,却未必符合《毛诗序》。
误解”小序“也造成苏源熙眼中的另一不解之谜,即“风”诗与“颂”诗的“小序”之间的不一致性。他说:“《商颂》、《周颂》部分的诗序……摆脱了《毛诗》编者名声不太好的‘讽寓’模式:它们不是告诉读者这首诗写成去美或刺什么人或者什么现象,而是指明吟唱该诗的典礼……说一首诗是‘为’某种仪式而作与说它‘关于’某个特定的事件而作似乎是不同类型的判断。”*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78页。苏源熙的疑问是有道理的,但是他的解释却是牵强和猜测的。他说:“也许《诗经》最早的版本只对礼诗及关系到周朝形成的组诗进行了注释。《国风》注释分歧之大的原因可能是它们的作者没有较早的(汉代之前)传统可资参照。并试图延伸既有的《豳风》与颂诗注释模式,扩展到整个《诗经》注释之上。”*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164页。其实,正确理解《毛诗序》的教化观之所指,再结合周代《诗三百》用作教育贵族子弟即未来国君的教科书的社会用途来回答这个问题,就会有完美答案。“风”诗的“小序”建立在针对“上”之修德的教化观的基础上:民风是统治者德行教化的结果,可以通过其统治区域内出现的诗歌所反映的民情民俗来反观他的德行。如此,不管是“颂”诗还是“风”诗和“雅”诗的“小序”,都是在培养、训练未来的国君做一个优秀的统治者:通过“风”诗,教育他们借鉴历史上的好、坏榜样以修德行,通过“雅”诗让他们了解政治以懂权术,通过“颂”诗让他们经过礼乐文化的训练以知礼仪。从培养未来国君的角度看《毛诗序》,就会发现“风、雅、颂”诗的“小序”体现出完美的一致性。
五、 欧美汉学家认识的片面性
简单化处理复杂的中国《诗经》学史,特别是无视《毛诗序》文献形成与解读史上的复杂性,必然导致欧美汉学家在用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术语来研究以《毛诗序》为首的中国《诗经》阐释学时存在着认识的片面性和定性不准的问题。
先谈“讽寓”。欧美汉学界用“讽寓”来定义《诗经》的儒家注释,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毛诗序》及后来《诗经》注解中的“言此及彼”。可是,如前如言,《毛诗序》的“小序”并不是对诗歌主题的解说,而是追溯促使诗歌所反映社会风俗出现的统治者的原因。“小序”的“言此及彼”,与希腊荷马史诗、《圣经》阐释学中的“讽寓”除了在“言此及彼”这一点上相似之外,其路径是完全不同的。西方释经中的“言此及彼”是通过文本中的意象来实现的;无论是象征还是预表,总有“比喻”或“类比”的成份在里面。例如,《圣经》阐释中,以《旧约》中献祭的羔羊来预表《新约》中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雅歌》中的书拉密女与所罗门王之间的爱情被“讽寓”性地解释为人、神之爱,都是建立在某种质的相同的基础之上。可是,《毛诗序》“序首二句”与诗中情、事之间的“言此及彼”却是政治伦理学中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完全没有“类同”或“比喻”的成份在里面。如此不同的路径,怎么可以说《毛诗序》也是《圣经》阐释学中的“讽寓”呢?
虽然不可以将《毛诗序》定性为西方阐释学中的“讽寓”;但是如此认识“小序”的某此“续申之词”及以后的汉唐注疏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毛苌及以后经师误读《毛诗序》,已经将《毛诗序》中独立于诗歌之外的“美、刺”对象读进了诗内;而实现这个跨越的办法就是对诗中的人物、意象进行牵强附会的象征性解读,赋予《诗经》中的名物以它们并不具备的意义。例如:《毛传》从“雎鸠”身上发掘出“挚而有别”、“慎固幽深”等许多可以媲美后妃的美德。这一手段就是西方阐释学话语体系中的“讽寓”。
余宝琳将中国《诗经》传统阐释学定义为“语境化”,缘于“小序”与《左传》历史事件之间的密切联系。她说评注者“将这些解释植根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的目的是借“历史实证法,来论证这部专集的价值”*余宝琳:《讽喻与〈诗经〉》,第19~25页。。苏源熙赞同余说。他说:“大部分《诗序》提到诗的意义时总要回到它(假想的)成诗时的情境中”、“在每首诗上都发生过一次的历史事件。这样的事件提供了惟一足以决定诗意的践言性(performative)语境。每首诗不得不被补足有关怎样、由谁及为谁而作的缘由。”*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77页。他们都以为“小序”是对诗歌的主题解说和历史场景的再现。如前所论,这是对《毛诗序》的误解,《毛诗序》将某首诗歌与某位君王相联,不是要“回到成诗时的情境”也不是为了“建立历史的脉络”,而是追溯民风、民俗出现的道德根源,以此来婉讽和“谲谏”统治者德行。只是在汉代,经师无意与有意之间误读、误解《毛诗序》,把“小序”中本来独立于诗歌之外的国君放进了诗歌之内以后,这种强行在《诗经》与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才成为中国《诗经》阐释学的传统。
范佐伦和苏源熙在其著作中,曾花大量篇幅来论证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通过注释使《诗经》成为教化下民的工具,发挥其规范社会的作用。苏源熙说:“教化不仅是《诗序》论述的一段枝节,也是解读的目的……教化理论把《诗经》中的诗变为道德规范……《诗大序》(以及整个《毛诗》传统)的意义一直是清晰的……把传统对《诗经》的解读看作对某个可能的伦理世界的描绘……以历史的形式作为对种种模范行为的叙述。”*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第115~117页。“教化”确实是《毛诗序》说诗的指导性思想,但是《毛诗序》的目的却是针对“教化”中另一端的“上”,促使统治者修德并改变治政策略;而不是把诗“变为道德规范”来教化“下民”。
欧美汉学家用阐释学术语“讽寓”、“语境化”、“规范性”等,准确地概括了复杂中国《诗经》阐释学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一历史时期的特点。但是,这些并不属于《毛诗序》这部特殊的《诗经》研究著作,所以说他们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的定性认识存在着诸多的片面性。
●作者地址:李会玲,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00006726@whu.edu.cn。
Allegoresis,Contexrualization & Standardization:Review on Studies ofTheBookofSongsHermeneutics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Sinology
LiHuili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Sinologists in Europe and America definedTheBookofSongsexegesis in traditional China as terms of allegoresis、contextu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in Western hermeneutic theory.They had strong sense of problem awareness and rational analysis attitudes to get rid of the mood of aversion that those precious scholars showed on the moral interpretation ofTheBookofSongs.They opened up the new field ofTheBookofSongshermeneutics,and brought new changes in the studies ofTheBookofSongs.However,simplifying those complex problems in the studies ofTheBookofSongs,especially the blind spot in the studies ofTheMaoPrefacetotheBookofSongs,resulted in many one-side problems.
Key words:TheBookofSongshermeneutics;TheMaoPrefacetotheBookofSongs; European and American sinology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4.013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项目(2013)
●责任编辑:桂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