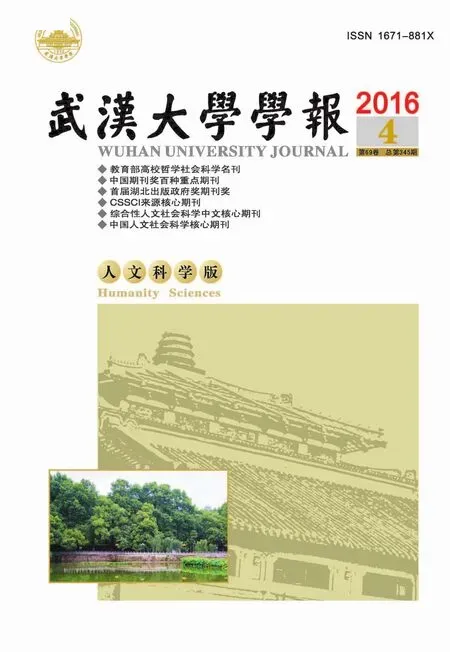从百年变革看中国新权威主义改革模式
2016-02-21萧功秦
萧功秦
从百年变革看中国新权威主义改革模式
萧功秦
摘要:中国自洋务运动以后,走上了寻找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变法图强的百年之旅。从清政府的开明专制化过程失败,到陷入政治脱序的早期议会民主政治,再到北洋军政时代的碎片化状态与山头林立的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中国的现代化陷入困境。直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体制形成,才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凝聚成一个坚实的政治实体。经过文革的重大挫折后,经由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元老改革派主导的改革开放,最终形成了具有新权威主义特点的中国发展模式。这种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坚持执政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在强势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进行倒逼式改革。它坚持常识理性的经验主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开放性的制度创新,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走向未来的新文明。
关键词:国家治理; 中国模式; 新权威主义; 社会资本; 薄壳效应
中国经历的巨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何看待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它是从何演变来的?用什么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这种体制与结构?它的优势与弱势何在?它在未来将面临什么挑战?什么样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才是具有可持续性并能成功地向新文明推进的良制?本文从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及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尝试提出一种宏观的解释框架。本文试图从百年史的长视角,对百年中国的变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简要的考察。中国模式,即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可以解释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新权威主义模式。本文还提出一些与新权威主义相关的理论问题,如新权威主义与“薄壳效应”、新权威主义对传统“社会资本”的运用、新权威主义强调的中道理性及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以及判断良性新权威主义体制生命力的四个标准,等等。
一、 中国百年变革述略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运急转直下,震荡起伏了一百多年,到邓小平主政的1978年,中国的命运才真正向好。从1840年到1978年,共计139年,中国人在漫漫路途中,终于求索出了自己的发展之道。为了文辞的简便,本文把这139年约称为百年。从1978年至今,几乎过了40年,中国这一时期的变革仍是小平路线的赓续,所以,我们把这40年与前面的139年合在一块儿讨论。我们把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以每十年为单位,作一个概览。
从1840年到1850年的第一个十年里,发生了鸦片战争。对于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农业专制帝国来说,中国内部很难产生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推动力,无法完全靠自身的力量演化出先进的新文明。鸦片战争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化起步的外推力,然而这个开局不好。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被迫割地赔款的中国人深怀受欺侮的悲情与屈辱感,群体性的排外心态变本加厉,阻碍了因势利导的变革起步,中国人在此后20年其实并没有醒过来。
从1850年到1860年的十年里,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破坏。根据清朝户部战后人口统计,中国人口比战前减少数千万。在这十年里,中西文明进入更激烈的冲突碰撞时期。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国难进一步加深。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中国士绅官僚与百姓对西方文明的逆反心理变本加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对洋务运动与外来文明的基本态度。
从1860年到1890年的30年,或许可以说是近代史上相对平静的时期。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进入同治光绪中兴时代,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三大条约的签订,让西方人觉得中国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的国际秩序,于是美英法等国开始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支持中国对外开放,这本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契机。中国也试图小心翼翼地推行洋务自强运动。中国国运似乎有了新的转机。然而,在对外关系上,士绅官僚中大言高论的清流保守派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天津教案表明,清流党保守势力进一步构成了对步履维艰的洋务运动的压抑态势。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使中国失去南方屏障的中法战争,在1986年到1979年的光绪二年到五年之间,中国国内又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旱灾,按照外国传教士李提摩泰的统计,灾荒面积遍及清朝一半以上的省,死亡人口近两千万人,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李提摩泰:《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这种社会生态的脆弱,也预兆着即将到来的民族大灾难,传统体制生命力的脆弱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进入近代历史上最为屈辱的、国运最坏的时期。甲午海战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滑铁卢。从1894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战争短短六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其对外战争赔款合计接近7亿两白银。19世纪末的西方列强在《马关条约》的刺激下,也改变了对中国原先的“合作政策”,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人们不得不感叹中国的国运陷入“墨非效应”*“墨菲效应”是一种心理学效应,是由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的深渊:如同人们穿衣服时上错了第一颗纽扣,第二颗、第三颗都会上错,从此中国祸不单行。
从1900年到1910年,庚子劫难之后的清王朝统治者终于大彻大悟,开始一场颇为认真的“辛丑变法”。这场晚清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各个方面,但为时已晚。随着慈禧与光绪于1908年逝世,新的满清统治者平庸无能,青黄不接,他们在亿万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已经丧失统治的自信。
概括地说,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70年,变法与中外战争关系紧密,国家只有在外战失败后才被迫改革。战争失败引起的士绅官僚的屈辱感与悲情,又产生了强大的群体性的抵制学习西方的逆反心理,从而使新的改革注定备受挫折与困难重重。改革的挫折,又导致新的战争再次失败,战败后的统治者推出新一轮改革,新的变革又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再次失败。如此周而复始,胶葛纷纶,恶性循环,直至统治王朝的权威合法性在连续不断的危机中消耗殆尽,使中国失去了在既存秩序下改革的可能性。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此时的清王朝如同朽木粪墙,一推就倒,这场世界史上或许可以说牺牲人数最少、最为轻易取得成功的民族主义革命,虽然结束了二千年帝制,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极端缺乏组织力与执行力的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的弱势政权,民国中央政府连地方的税款都收不上来,弱到这个国家的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的地步,更无法开展现代化运动。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南方国民党针对北方政敌袁世凯而因人设法的“临时约法”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内阁制无法合理运行,又引发各派之间严重的分歧与纷争,内阁危机与党争、政潮不断,从此,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陷入了弱国家的陷阱难以自拔。
袁世凯在1914年作为军事强人来收拾残局。这位军事强人在平定局势以后,致力于发展实业,引入外国教育,公布商法,开始几年似乎风调雨顺,经济发展也甚为可观,中国似乎进入了一种威权体制下的现代化路径。然而,作为北洋系军人结合成的朋党型政权,袁世凯威权政治素质低下,无法实现全国统一。且好景不长,日本咄咄逼人地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此后不久,袁世凯居然异想天开地搞帝制运动,迅速失去了统治合法性,被迫退位之后因病逝世,不久内战爆发,中国从此就陷入了兵荒马乱的北洋军阀时期。各派军政势力从1917年打到1928年,南北军阀势力多次尝试走袁世凯式的强人政治之路,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南北分裂,南方与北方各省内部也分裂,全国陷入了碎片化状态。
到了1928年以后,国民党终于统一了中国,开始了十年的建设,从1928年到1937年,历史上称之为国民党的“黄金十年”*黄金十年又称南京十年、十年建设,是指1927-1937年间建都于南京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执政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为近代中国较高水平。。然而1931年出现“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几年以后,1937年又是“卢沟桥事变”,中国不得不在国力不足、没有做好最低限度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匆匆进入八年抗战,与强大的敌人展开力量悬殊的战争。1944年,日本人的军队已经打到离重庆不远的地方,退处云贵穷乡僻壤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弱到难以动员兵力投入持续战争的地步。国民政府动员能力之滑坡,与这个政权现代化程度不足有关,到了战争后期,国民党这个脆弱政权几乎被中日战争拖垮了。
抗战刚取得胜利,和平建国的可能性由于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而消逝,中国进入国共内战时期。到了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然而,接下来是一打就是三年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冷战时代又开始了。虽然建国后我们在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受到“穷过渡”与“超阶段论”思想的影响,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得不放弃,1956年发展高级社,1957年搞“反右斗争”,1958年搞“人民公社”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接下来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灾荒,导致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1966经济形势刚有所恢复,就发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大灾难是众所周知的,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在贵州有些地区,两个强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值,还不如老母鸡生的一个蛋值钱。最困难的地区,有些农村的成人衣不蔽体。泱泱文明古国在鸦片战争140年后,中国国民生活水平只相当于非洲最落后的国家的水平。这是中国国运艰难曲折的明证。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按照邓小平的提议,会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中国历史从此迎来了新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要求激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两种声音都出现了。有人要求全盘西化,有人则声称“多一分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特别强调“十三大报告一字不改”,提出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通过拨乱反正,超越左右两极势力,奠定了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基础。此后,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就是中国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大展宏图的20年。
江朱体制的十年,沿着小平路线继续前进,中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十多年里,执政党做成了三件大事情:分税制、国营企业转制、加入WTO,让中国经济焕发出空前活力。胡温治国的十年,即2002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中国经济真正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看,中国国运的真正转变是1978年。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的国民人均年收入已经从350美元上升为7000美元,中国经济发展以9.8%的年增长率持续了30年。全国有6.4亿人脱贫,从最贫穷的国家一变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持续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等收入阶层大为增加,那些在假日中像蚂蚁一样在泰山、华山与国外旅游的人们,就是中国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虽然30多年改革中也存在着贫富不均的社会分层化、腐败与社会不公等改革综合征,农村也为城市现代化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无可怀疑的是,这30多年是有史以来中国国运最好的时期。
二、 中国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的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体制是“共产党领导”加“市场经济”两个因素相结合,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两点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的体制,只要坚持这个“两点论”,在逻辑上与实践中就自然而然地展示为一种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的现代化路径。共产党领导加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就起到后发展国家中的新权威主义的作用。它区别于西方式的多元民主体制,也区别于改革开放以前追求平均主义理想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全能主义体制。
这种新权威主义体制,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有着特殊的现代化功能。这是因为,对于后发展民族来说,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在数百年的漫长时间内,由社会内部微观的多元力量,通过无数“看不见的手”的多元彼此互动,自发地实现社会发展的驱动与整合。非西方后发展国家与民族,要发展本国经济,首先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需要强势政府保持安定的政治环境,需要政治精英具有现代化目标的导向性,以利于整合各种资源,致力于民族统一与现代化的富强目标。这就在逻辑上需要建立起一个具有强大执行能力的政府,来发挥“开明的大家长”的作用。一方面,这个强势政府要运用铁腕来维持既存秩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尊重国际经济秩序,鼓励实业,促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发挥地方、企业与社会成员自身的竞争主动性。凡是能起到这种双重作用的威权政治,就是新权威主义。
从历史上看,后发展国家在反殖民斗争取得独立以后,在激进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几乎总是直接建立起仿效西方的多党议会政治,其统治精英虽然具有现代化导向性,但其政府实际上都是权力分散的弱势政府,难以实现国内的政治稳定,也无法有效发挥市场经济的引导功能。而新权威主义体制是后发展国家长期试错的产物,历史上一些推行新权威主义的后发国家的政治精英,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他们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经验尝试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有现代化导向的威权体制的。从历史上看,新权威主义体制并不是统治精英们的理性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在历史各种因素的碰撞中“无心插柳”的结果。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就是百年现代化试错的经验结晶。它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40多年中,数代中国人集体经验的结晶,前后共经过了六次政治选择*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52~92页。。
因保守与挫折的恶性循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失败。中国作为后发展民族,在鸦片战争经历西方挑战之后,最适宜的历史选择就是利用现成的专制官僚机器进行制度创新,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逐渐将传统专制转变为开明专制,并逐步实现本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无疑是最为便捷的路径。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走的都是这条开明专制路径。然而,在长期封闭的帝制环境中,朝贡体制与儒家的教条形成中国顽强的文化保守惰性,皇帝、官僚、士绅与民众固有的观念阻碍了统治者常识理性的正常发展。清朝统治者在保守、战争失败、再改革、再失败的恶性循环中,消耗了自己残存不多的合法性,被排满民族主义的辛亥革命所推翻,失去了通过开明专制的威权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的可能*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8~240页。。
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议会制是一种分权化的反向运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精英比清王朝统治精英有着更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世界眼光,有更强烈的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意愿。但他们摧毁旧制度后,直接仿效西方而建立起的多元民主体制,无法形成足够的权威来实现稳定秩序。多元体制造成的权力分散化、党争频繁化,与现代化初期所要求的权力集中南辕北辙。这个内部充满不同政治派系党争的体制,注定是一盘散沙状的成事不足的弱政府体制*萧功秦:《反思的年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页。。从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来看,现代化需要建立有发展导向的中央集权,这是非西方后发展国家以政府为主导的现代化的逻辑所决定的,辛亥革命恰恰是一个与这种发展逻辑相反的逆向过程,即权力分散化、分权化的过程,中国将不得不在这种虚弱散乱的多元民主体制解体之后,将分权式的弱国家再度整合于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之下,才能开始现代化的起步,而这是长达数十年的漫长曲折而充满痛苦、成本高昂的历史过程。
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政治缺乏现代政治所必要的素质。袁世凯在镇压反对派以后建立起个人独裁,同时本人又具有朴素的现代化导向性。在袁世凯统治下,国家权力得到初步的集中,这种强人政治下的初步集权,对于20世纪初以宗法传统作为社会聚合力基础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似乎也差强人意。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政治,本来在客观上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后发展国家的新权威主义路径,但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把重心移到欧洲战场,原来的平衡点打破了,中国处于东亚一霸独强的日本的虎视眈眈之下。袁世凯本人的权力欲与低素质注定这一政权终将陷入权力私人化、朋党政治与“苏丹化”。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朋党式人际关系、军人集团内部组织力的脆弱显露出来。所有这些都使袁世凯与北洋的强人政治难以担当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重任。
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民党的威权体制被战争拖垮。1928年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建立起党国一体的权威政治,可以说这又是一次新权威主义的历史选择,国民党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威权体制,从组织聚合力、意识形态聚合力、政党动员力与政府执行能力上,比袁世凯松弛的军事强人体制要强一些。国民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行全面国防建设、交通建设与社会改良运动,逐渐走上新权威主义道路。然而,这个政权有两个重大的缺陷与弱点:一是北伐迅速成功使北洋军阀大量投诚国民政府,这就使军阀这些外部山头变为国民党的内部山头,这是一种内部派系林立的结构。第二点是,国民党是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聚合人心的基础的,但国民党于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步步紧逼;另一方面,国民党推行高调的民族主义的“革命外交”,要求短时期内把不平等条约全部收回。中国国力增长的速度,跟不上国内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速度,这就给日本民族沙文主义者借机加紧对华侵略提供了借口。于是,在日本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与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的权威体制终因现代化力量不足,最终在力量悬殊的战争中被拖垮了*萧功秦:《从两次中日战争汲取历史警示》,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事实上,抗日战争胜利时,这个政权已经气息奄奄,在抗战后期已经无法控制其自身的腐败,最终失去人心,在全国内战中失去政权。
中共革命体制建立了有效动员的基础,但被左的思潮干扰。中国革命为中国现代化作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中日战争中形成一种具有强大战争动员能力的革命民族主义。在一盘散沙的中国,中共革命组织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起到国家与民族黏合剂的作用。学者们也已注意到,具有民族主义动员力的东亚国家相比较拉美国家在现代化动员能力上有很大的优势。
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磨炼,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与内部聚合力达到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地步。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共列宁主义型政党的严密纪律与组织系统、革命意识形态的精神凝聚力、毛泽东在战争中形成的领袖威望与号召力、中共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的动员能力、党领导军队形成的战斗意志、统一战线对社会精英的广泛吸引力以及延安整风运动后党内山头主义的克服与消除,所有这些在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中磨砺出来的政治特质与制度,彼此相互结合,使中共革命政府的权威所发挥的效率达到以前四次政治选择(即清王朝、民初议会政治、袁世凯强人政治,国民政府)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在指出这种政治优势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后发展国家政体的高度集权,有利于革命夺取政权,并发挥现代化动员的有效功能,但也留下了个人权力过于中而形成的隐患。。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进入国共战争的新时期,新兴的中共力量与被战争拖垮的国民党相比,在对社会的整合力、组织力与动员力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强调尊重市场经济、五种生产方式并存,克服了以往的“超阶段论”,表明中共思想上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如果1949年建国以后,中共革命政权以其高度组织力、凝聚力的政治权威与务实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相配合,尊重文化与社会经济多元,拒绝政治浪漫主义的诱惑,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经济,无疑就会形成一种令世界各国羡慕的高效的、具有新权威主义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国就有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传统文化精神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美结合,也就不会有此后左的激进主义灾难了。
然而,建国以后,由于冷战时代来临,战争动员与过于理想主义的“超阶段论”发展观念,使左的思潮逐渐浮出水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左的思想干扰与左的信仰力的膨胀,使中国失去了通过新权威主义迈向现代化的大好时机。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种尊重多元又具有强大社会整合能力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才得以在中国逐渐形成。
中国大转型的契机,首先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极左灾难之后,常识理性在中国人心中普遍觉醒。历史的钟摆效应使新的价值趋势出现了——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为此而务实地反思文革的灾难,寻找新的道路——凝成了一种新的以务实的常识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共识。
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这样的饱经风霜的元老派重新回到了政治中心,并成了改革家。他从长期束缚人们的教条信仰中超越了出来*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第125~140页。,并深深感到,中国再也不能置身于整个世界潮流之外。他在新加坡观察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非西式的多元竞争性政党,而是一个新权威主义型的执政党,它居然能够领导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家的人民,在20年内建设成人均生活水平超过美国的东亚发达国家。新加坡体制给了邓小平很大启示,他决定改革*萧功秦:《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习什么》,载《同舟共进》2014年第4期。。邓小平的常识理性让他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他认为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拿来用。对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深刻记忆,又令他十分警惕重蹈街头民粹政治的覆辙,意识到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仿效实行西式民主,必将影响政治稳定,并最终因街头广场运动的无序化而导致改革失败。这就是他必然选择“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大方向相结合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总是会受到左与右的两种极端思潮对改革的挑战。这里,左的极端,是指文革左派与体制内坚持教条理念的保守派;右的极端,是指西化自由派。能否成功地应对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政治挑战,是新权威主义成败的关键。
西化自由派相信,存在着某种依据普世性价值建构起来的良好秩序,这就是西方多元民主体制,他们认为只需通过大幅度地移入好秩序或通过“斗争”来清扫原有秩序,一个按“自然权利”与“人性”设计的美好社会就会应运而生*《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9~139页。。但是,对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实行多党民主制后所造成的灾难,西化自由派却视而不见。
而左的教条主义是作为西化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西化自由主义对现存秩序的挑战往往使左的教条主义有了“用武之地”,左的“阶级斗争为纲论”往往被认为可以对右的自由主义起到政治上的制衡与威慑作用,这样,左的原教旨式的保守思潮就在政治生活中有了合法活动的舞台与空间。极左思潮的危险就在于,它分享着“红色文化”符号,占有话语上的居高临下的制高点。一旦发生政治上的冲突与经济发展出现困境,他们就会煽动起左翼的民粹主义思潮。
与左右激进主义所凭依的建构主义不同,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是经验主义。它承认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方案。人类认识事物只能逐步推进。任何进步都是利弊相兼,所以,它主张改良,走渐进之路,利用现存的社会资源,发展出民主政治。它把本国的传统秩序作为发展的杠杆,以保持秩序的历史连续性与变化的可控制性,以旧育新,力求降低变革成本,实现政治转型的软着陆。
邓小平改革始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来防止左或右的教条信仰来干扰改革的大方向。他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是用经验与试错的方式来应对复杂环境以及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政治挑战,激进的自由派和保守的左派整体上被边缘化,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就此确立。
三、 中国模式的内涵
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又被学者们称为中国模式。与其他类型的新权威主义相比,中国模式的特点很清晰:由于历史路径的选择,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不同于东亚模式中的韩国与台湾地区。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一党政治的社会资本,更具体地说,东亚模式是属于后发展国家中作为对议会民主制失败后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是以军事强人为特点的权威政治。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权威主义,则是全能主义体制通过维新路径形成的产物。历史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垂直结构在总体结构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如果说,横向的组织结构是西方文明生活中的社会资本,那么,中国自郡县制以来,垂直的、纵向的集权结构与组织文化,对于长期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来说,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当这一社会资本在转型时期得到灵活变通运用时,就足以维系转型与变革时代的秩序稳定。
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充分运用了纵向垂直结构这一社会资本,如“举国体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资源动员与整合作用。中央集权的执政党系统、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号召系统、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执政党对强力部门的控制及其对金融系统与大型国企的有效控制以及国人对革命文化传统的尊重等等,所有这些全能主义体制中原有的制度、文化与组织要件,构成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时的“整体的号召机制”、动员机制与资源整合机制。治国者可以利用这种全能主义时代的“历史惯性”形成对转型过程的有效控制,这也是中国改革顺利与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也可以解释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恰恰是在改革过程中放弃了苏俄体制中执政党领导这一原有的社会资本,从而失去了改革的主心骨与主导力量;同时,前苏联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不断地弱化执政党的统筹与执行功能,直至戈尔巴乔夫从根本上失去苏共这一社会资本。因此,他在与叶利钦进行政治斗争时,就变得无所凭依;而后者却掌握了激进的民粹主义,在广场与街头政治中如鱼得水,最终在民粹主义话语霸权的支持下所向披靡。
什么样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是良性的体制?新权威主义体制如何应对来自保守与激进的政治势力的挑战?如何才能将一个民族引向民主富强、自由平等与繁荣的新文明时代?从人类历史上大量的经验事实比较来看,一种良性新权威主义要取得这样的成功,就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强势政府能力;具有排除左与右的教条意识形态干扰的常识理性;对社会与文化的健康多元性的尊重;开放性的制度创新能力。
强势国家能力。这是判断良性新权威主义的第一个标准。强大的国家能力,表现在能有效地排除国内保守势力与激进极端势力对现代化既定方针与目标的干扰,保持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连续性。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政府,就是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强势政府,它具有上令下达的高效率以及对转变中社会秩序的掌控能力。良性新权威主义的强势国家能力,体现在它能发挥以下五种重要功能:一是维持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二是现代化的动员功能,即制定与实施发展战略,有效地整合、动员一个国家的人才物力财力资源,以致力于现代化重大战略的实施;三是转型杠杆功能,即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培育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转型软着陆;四是应对自然灾害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功能;五是再分配功能。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利益分化的过程,因此,完全靠市场分配资源,在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之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城市内部的富人和穷人之间,都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因此,一个良好的新权威主义强政府,应在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常识理性。单有强势政府,并不足以引导一个国家成功地走向现代化;如果一个铁腕治国者头脑中充满宗教迷信,其行动与选择受过时的教条观念、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理念、民族主义的狂热、浪漫的政治幻觉等种种干扰,这样的政治家他的威权越高,他领导的国家能力越强,他造成的社会灾难就会越大,施政效果就越是南辕北辙。正因为如此,新权威主义成功的关键,是当政者必须具有常识理性。常识理性之所以特别值得提出,这是因为,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统治者,在整合社会人心时,往往要藉助于政治神话、动员型意识形态的理念、宗教的符号来鼓动民众,聚合人心,他本人也可能受某种浪漫激情的支配,这种浪漫激情在历史上也曾起过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作用。然而,这些非理性因素会干扰人们对决策思维的冷静判断。相反,所谓的常识理性,就是世俗理性,就是与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式的天国信仰相反的东西,更具体地说,就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健全的常识判断能力,就是摆脱了教条观念、乌托邦理念、民族主义的狂热、政治幻觉、宗教执迷等非理性因素对人们行动选择的干扰,运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人的理性来判断问题的能力*文革后期,湖北麻城地区出现多例农村女青年集体自杀事件,当时上面派了一个大干部来调查此事,当地人告知女青年自杀的一些具体原因,如妇女劳动强度太大,某位女青年分红后所得的钱,还买不起一件红色外套,觉得活着没有意思,等等,然而,调查团却指责说,你们全错了,关键问题是你们没有“狠抓阶段斗争与路线斗争”。这就是典型地用教条代替常识理性来考虑问题的实例。文化大革命中,此类用意识形态代替常识理性进行判断的例子不胜枚举。。用邓小平的话说,一个政治家就是要“做明白人”,其实指的就是要做用常识理性进行思考的人。
尊重多元。这是判断良性新权威主义的第三个标准。从客观上看,社会多元化与新权威主义集权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张力。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社会组织的多元性,既是文化创新的微观细胞体,又是自主性的集体行动的组织平台,多元性的存在、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潮有可能利用文化多元、社会多元这样的自主平台,形成对现存秩序的挑战与冲击,这就往往会引发政治参与膨胀、影响社会稳定的可能,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以强制方式来抑制多元性这种文明常态的发育成长。成功的新权威主义必须充分尊重多元性,用严复的话来说,“培其根本,卫其生长,使其效不期而至”*来自严复早期论著《原强》。,如同园丁一样发展社会的多元新文明。应该意识到,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文化思想多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持续进步的前提。思想和文化多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这句话最早来自韩正2011年1月16日于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经济与文化多元,能激发个体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文化创造方面的竞争活力。多元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更多的试错机会与方案,而这种方案与机会越多,一个社会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就越强。多元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各种新思维,还提供了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形成竞争活力。正因为如此,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第77页。
开放性的制度创新。这是良性新权威主义的第四个标准。所谓开放性集权,就是一种制度文化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做出适应性的调适。体制是集权的,是威权性质的,但在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上,这个体系可以不断通过自我更新来适应环境与时代的变化。这种体制承认倒逼的作用,可以通过吸纳社会诉求,在解决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和应对挑战时,会由于新因素的吸纳而发生结构与价值的更新与演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对环境的反应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开放性的。这是一种可以通过制度变迁与调适来适应挑战的活的生命体。一方面,它具有自我反思能力,有多元性的容受力,对自我优越感抱一种谦虚警惕的态度;另一方面,多元性的存在,会源源不断地为体制提供各种备选的文化、制度新智慧。
一般而言,威权体制与开放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这是因为,威权体制要运用传统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来作为强化自身刚性威势的工具,对于来自极端势力与激进势力的挑战,治国者也会通过强化这种习惯性的文化符号与意识形态来稳定现存秩序,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会形成路径依赖。许多曾经有过开明的现代化导向的威权统治者,在外部压力下回归到旧专制传统,就是这种路径依赖的结果。能否在开放性与守成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判断新权威主义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改革就具有常识性思维、尊重多元、开放性集权这些特点。邓小平总是说,一个政治家要“做明白人”,要“不讲空话大话”。邓小平及其后继者所执行的中国体制,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破除了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为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开辟了意识形态的通行证,“三个代表论”提供了去教条化的合法性基础,“和谐社会论”则提供了用非阶级斗争方式解决社会阶层矛盾的新思维。
中国模式强调“倒逼论”。它意味着,只要有环境挑战与问题倒逼,就必须改革,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产生,改革将在问题挑战中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这就是制度的开放性。所谓开放性的集权,就是尊重倒逼机制对行为的引导作用,只要保持制度的开放性,尊重社会的首创精神,善于从社会上汲取新智慧来丰富体制的生命力,它就会与时俱进地保持生命力与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四、 中国模式的利弊及前途
比较政治学发现,传统集权型的国家一旦对外开放与维新变革,往往会陷入革命动荡的高发期。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种“改革—动荡”的高相关性,称之为“薄壳效应”。众所周知,地球的地壳最薄处是最容易出现火山爆发的。传统集权体制在积重难返的情况下进入改革期,就是进入“政治地壳”最薄的区域。中国模式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它能有效地守护变革秩序的稳定性,克服传统集权国家转型时期往往会陷入的“薄壳效应”。
传统集权体制进入改革阶段后之所以会陷入持续的政治动荡乃至发生革命危机,可以这样来解释:一般而言,传统集权体制结构的封闭性、对社会多元的排斥性,造成其本身缺乏矛盾化解的机制,一旦统治精英意识到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严重到会引发危机,因而非变革不可的时候,统治精英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压抑政治参与的各种政策。于是就会出现政策宽松期。在这种情况下,受治者也会因“政策解冻”而相应产生政治宽松预期,各种政治诉求在短时期内集中地喷发,街头与广场式的各种政治参与活动也会空前活跃,甚至产生连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偶发事件,就会成为朝野之间政治冲突的爆发点,实行改革新政的统治精英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矛盾*萧功秦:《新权威主义能否主导新一轮改革》,载共识网“中国研究”栏目,2012-05-06。这是作者在共识传媒举办的“新一轮改革进程观测”研讨会上的发言。。如果统治精英对井喷式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让步或妥协,会进一步刺激抗争者提出新的更多的要求。尽管从长远来说,大众提出的要求都有其合理性;但由于社会经济落后,矛盾与问题堆积如山,大众的要求在短时期内是很难满足的。雪上加霜的是,传统集权的危机时期,往往又是反体制的自由激进主义思潮崛起的时期。激进主义思潮会把这种要求受挫在政治上解释为政府的无能。激进主义与大众亢奋的政治诉求的交相影响,会使当政者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地运用刚性手段镇压这些诉求者,就会在政治参与者群体中形成强烈的激愤与道德悲情,引发抗争者更剧烈的反弹。政治学上把这种冲突称为“参与爆炸”(The explosion of participation)。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镇压行动导致的诉求方的悲情、挫折感与焦虑心态就会纠结在一起,形成以政治参与爆炸为特征的改革危机。
但事实是,面对改革危机时,统治精英出于对本身权力地位的担心,往往会本能地做出强硬的甚至过度的反应。政府的强硬反应,会形成更为剧烈的抗争反弹。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双方的温和派也在“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中失去话语权,同时也失去道德制高点,他们或者转向强硬派,或者由于失去话语权而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政治参与者的焦虑感与激进心态也将随之日益强化。广场与街头各种反体制的激进主义甚至极端主义的“革命”思潮也会趁势而起,社会将陷入全面危机状态,直至发生暴力革命。
从18世纪以来的传统集权国家的改革历史来看,由改革维新而引发的社会政治参与爆炸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世界改革史上薄壳效应的第一个例子。路易十六是一个开明的君王,任上首推改革,召集了一百多年来没有召开的三级会议,让第三等级参与了政治;他任用具有改革思想的杜尔阁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取消各种奴役与特权;他还计划免除农民的徭役,取消省界壁垒,废除贸易关卡,振兴工业发展,让贵族和僧侣与第三等级承担同样的税率。此外,他还计划利用现存的省议会来扩大政治开放,让人民能够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然而,在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基础上,被压抑的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诉求,如同潘多拉盒子一样,在短期内井喷而出。路易十六在镇压与妥协之间动摇不定,结果被法国革命者以“里通外国”与“阴谋复辟罪”处死。
俄国尼古拉二世的改革也是如此。由于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三世相继推行反动政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原先保守的尼古拉二世任用改革家斯托雷平推出了大改革方案,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让俄国变成立宪民主国家;与此同时,薄壳效应开始出现,农民提出更多的诉求,旧贵族也群起反对,战争又使局势雪上加霜,物价飞涨,经济崩溃,请愿运动层出不穷,俄国统治者同样在镇压与妥协之间进退维谷,于是引发了二月革命。雅可夫列夫在他的《雾霭》一书中说,“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没有找到既能抵制专制复辟,又能抵制革命的政治力量。”*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章。二月革命后,红色十月革命应运而生。
中国的清末新政,是集权帝国改革引发薄壳效应的另一个典型事例。自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战争的60年里,保守的清王朝统治者从来没有认真地进行过改革。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对自己以往近40年的保守顽固所造成的庚子国难深感内疚。她在还没有进入北京以前,就主动宣布实行“辛丑变法”。该变法力度之大,超越前期的所有变法*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第241~247页。。1905年清廷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又进一步宣布实行扩大政治参与的筹备立宪。1908年慈禧与光绪死后,筹备立宪运动日益激进,东北奉天总督府前出现“万人伏地悲泣声嘶力竭不能自已”的场面。清廷被迫将九年筹备立宪期改为五年。此后激进派并不满足,要求立即实行立宪。摄政王拒绝妥协,民间的不满情绪受此刺激进一步扩大,排满主义思潮日益强盛,清王朝的新政改革很快就陷入“薄壳效应”。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从慈禧逝世到辛亥革命,只有三年时间。
用“薄壳效应”来解释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远比简单的“西方阴谋论”更有说服力。戈尔巴乔夫改革后,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长期积累的矛盾,尤其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问题,成为“薄壳效应”集中爆发的焦点,东欧各国的独立要求,引发苏联波罗的海三国宣布退出苏联,并引发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连锁反应。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进一步加大了苏联国内的激进主义抗争运动的浪潮,苏联的崩溃从而难以避免。主张新权威主义的当代俄国学者米格拉尼扬指出:“如果没有长期民主的传统,转轨时期就可能出现失去控制的危险,在那时,暴民政治的激情就开始猖獗。被唤醒的和不受控制的激情需要缓和下来,这时就需要强力政权。”*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集权国家改革必须迈过的第一道坎就是“薄壳效应”。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新权威主义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守护变革秩序的稳定性,防止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初期政治参与急度膨胀所形成的“薄壳效应”。新权威主义用改革的权威,抑制民粹主义政治参与,防止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对改革的干扰,避免政治参与膨胀与爆炸。另一方面,新权威主义运用政府权威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失时机地进行渐进改革,通过改革来化解矛盾,缓解政治参与的压力,通过经济发展赢得人心,争取到新的合法性资源。
中国模式是“后革命型的新权威主义”,由列宁主义革命体制通过维新与制度创新,以改良方式转变过来的。它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组织资源,其国家能力更强于东亚“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府功能之强大,远远超过一般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个人家长式的强人政治*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第113~127页。。在整合资源、提高效率、控制社会、应对突发事件方面,中国模式有明显的优点。但是,这种“后全能型”的威权政治,也有其结构性的缺陷。
首先,转型时期的人们与改革以前的旧思维、旧观念的剥离度较低,思想上不容易与旧思维告别。他们对多元文化的容受度有限,传统的左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运动式的动员习惯,往往无形中支配人们的选择,会形成思维上的路径依赖,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极左的观念有可能从假死状态中被激活,被保守派利用,构成干扰改革大方向的习惯势力。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前的保守派活跃就是一个鲜明的实例。
其次,在这种新权威主义体制里,社会自主力量发育相对较为薄弱,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来看,这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型的结构。市民社会不发达,无从监督权力阶层的腐败活动。经济利益被权势人群掌控,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税制漏洞明显,由此而产生的贫富两极化的程度也会更高。正因为如此,权威体制下的低度参与虽然有利于政治稳定,但又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上的贫富两极分化趋势。事实上,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最不平等国家的行列,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不同群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速度在加快,那些依靠行业垄断获取的不合理的高收入群体与非垄断企业劳动者收入群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越来越感到不满。
中国模式的纵向结构,承袭了传统社会和革命社会的组织资源。它有管理高效的一面,但是也有思想钝化的一面。这是因为,自中国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单纯的传统的纵向命令贯彻结构,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往往与一种“上尊下卑”的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荀子对此有过很深刻的分析,他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国》);王国维则把这种垂直体制概括为“以分防乱,以分治国,求定息争”*萧功秦:《从千年史看百年史——从中西文明路径比较看当代中国转型的意义》,载《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1期,第17页。。
这种结构中,“分,官,禁,一”是纵向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使得社会内在活力难以如西方“横向—个人中心”结构那样,具有微观活力与竞争所激活的整体社会生命力。更具体地说,“分”(即“各守其分”)在维持秩序的同时,也造成形格势禁,压抑了个人的活力;“官”形成命令系统,而官僚病则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常态;“禁”形成的法禁文化,抑制了社会的创新能力;“一”,就是大一统,一刀切,压抑了社会的多元性,包括观念与文化的一统性。所有这些都是造成近代中国在应对西方挑战时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
纵向结构虽然可以作为转型的社会资本而起积极作用,但它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以纵向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的命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素质、智慧、个性与品德。这就带有很大的历史或然性。这是纵向结构本身无法解决的两难问题。开明的强人是民族的福音,而固执保守的或充满浪漫幻觉的强人则是民族的灾难。“好皇帝”可以利用纵向结构这一社会资本,高效率地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而“坏皇帝”则适得其反,他可以任意运用这一社会资本,为所欲为,给社会带来灾难。在每个国家具体的历史情景中,从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倒退到封闭的权力个人化、独裁性的人治、腐败与朋党化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然而,这一切负面后果的发生,又是生活于这一垂直组织结构中的人们难以选择的。
新权威主义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必要选择,但并非所有威权体制都能有效地推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包括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这些军事强人,他们对国内也是采取铁腕治国,他们也并不拒绝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然而,这些强人政治并不成功,有的蜕变为朋党式的苏丹式政权,有的被激进革命所推翻,有的则在经济衰败与腐败中停滞不前。从世界历史上看,新权威主义政治存在着不同的前景。
中国改革要在未来取得成功,关键就是如何把传统的纵向结构的优势与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横向结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改革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在横向结构与纵向结构之间形成协调与平衡。
邓小平改革所走的路,正是把一党制下的执政党的领导(纵向结构)与市场经济(横向结构)结合了起来,并力求在两者之间达到平衡。这种新权威主义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利用垂直控制这一传统的社会资本,稳定秩序,形成整体号召机制,通过垂直方式宏观地整合各种资源,致力于发展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市场经济,发展自由竞争,形成地方、企业、社会个性这些社会细胞体的自主性,激发社会活力。从未来发展方向上看,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让社会焕发出活力,公民文化与自由将在这种公民组织中得到培育,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条件也就相应成熟。纵向的国家权威与横向的公民组织的均衡发展,将是中国新文明的基础。
这样的探索还在进行,也可能会有挫折。这是因为,纵向结构中许多糟粕性的东西,会不自觉地支配并影响人们的选择。能否在利用传统社会资本提供的积极功能的同时,排除这种纵向组织结构的消极性,如家长式的专制文化、民众中的个人崇拜心理、命令一律而缺乏权力制约、人治式的权力任意性、意识形态对多元文化的排异性以及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民粹主义,等等,这就成为中国新权威主义能否引领这个民族走向健康新文明的关键。
只要新权威主义体制保持制度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与开放性,随着社会利益分殊化达到一定程度,单纯的一元性的整合将不再适应社会日益多元化的需要,这就有了向本国特色的更高阶段的民主发展的巨大空间。从新权威主义转向未来民主新文明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绝不是对他国民主体制的简单仿效与移植,它是开放性体制在不断自我更新过程中的符合逻辑的历史演进的结果。
未来中国将如何?中国特殊的历史路径,决定了革命政治文化对于中国模式的新权威主义具有持续的影响力,这种政治文化与组织文化,使中国不是走向西方式的多元民主,而是形成一种全新的国家—社会模式。国家的强势力量如果运用得当,就能使中国有条件避免百年专制解体后出现的乱局。在中国式的新权威主义体制中,革命传统、市场经济、民族主义、儒家文化以及对民主、平等、自由、法制这样一些人类共同价值的肯定与尊重,所有这些要素,都有可能糅合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多地观察到中国现在的新权威主义所具有的独特性。中国全能主义通过改良与维新方式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反过来也制约着中国未来的走向。这肯定是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模式。中国未来的新文明的方向,很可能是一种把横向结构与纵向结构予以平衡的有机系统。
我们可以简单地描述这一过程:新权威主义如果具备常识理性,又能尊重多元,它就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具有支持体制自我更新的文化品格以及制度发展的弹性空间。在这种环境中,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法制这样一些人类共同价值,将在和谐的多元化的文化气氛中得到哺育与生长。国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也将得到不断提升与更新,法制文化将成为人们游戏规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具有本国特色的更高程度的民主制度创新成为解决问题所必需,成为全社会共同要求,这将倒逼社会通过民主制度的创新与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倒退的办法来解决矛盾与问题,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社会不但无法实现现代性治理,而且会导致制度缺位而产生的脱序,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民主制度创新的条件将会日益成熟。
从历史上看,强势政府只有同时表现出开明,表现出对多元性的尊重,让社会多元焕发出创新活力,在多元社会与集权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制衡,这样的体制,才不会陷入权力任意、腐败化、“乌托邦理想国”化、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陷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势政府、常识理性、尊重多元、开放性集权,以上这四个条件相结合,就能够形成高质量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它将推动一个民族逐渐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走向未来新文明时代。
●作者地址: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Email:xiao9981@126.com。
●责任编辑:何坤翁◆
On China’s Reform Model of New Authoritarian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Reform History
XiaoGongqi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Since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China had embarked on a road searching for modernization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From the failure of enlightened despotism of Qing Dynasty to early disorderly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lso the fragmented state of the Northern Warlords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era, China’s modernization fell in troubles. China didn’t condense into a solid political entity until the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system was built by CPC. After a big frustration in the Big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subsequent Reform and Opening-up led by Deng Xiaoping, China had been culminating a development model characterized by a new authoritarianism. Its basic features are adhering to the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ruling party, beyond the left and right radicalism, under a strong government maintain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gradual reform. It insists on rational empiricism, respecting for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and the openness of system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China towards a new civilization by tim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governance; Chinese model; new authoritarianism; social capital; shell effect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