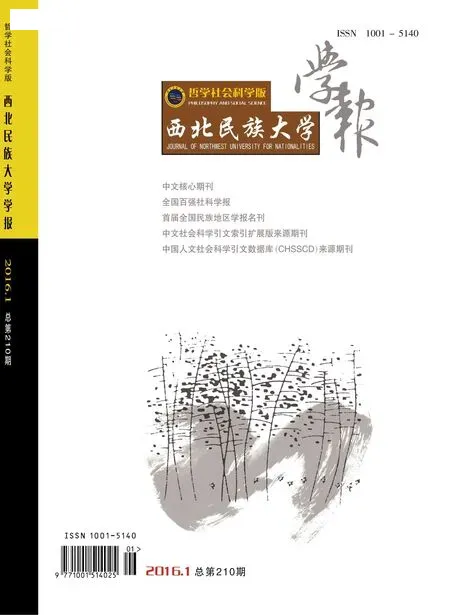霫族考
2016-02-19李荣辉
李荣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历史学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霫族考
李荣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历史学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出现于隋唐史料中的霫,最早见于《隋书》《通典》等唐代编纂的文献中;霫之族源为《魏书》中的地豆于,隋唐时期它活动于蒙古草原东部与大兴安岭两侧。霫之兴衰与突厥、回鹘等草原民族及契丹、奚的消长有密切关系。唐代中后期以后,由于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诸族与唐王朝的交往受到限制,霫的记载晦暗不明,史料中常出现霫与铁勒之白霫混淆的情况。唐末辽初霫在室韦的压迫下逐渐南移,经过契丹的征伐后最终融合于奚族中。
[关键词]地豆于;霫;白霫;地理
霫是见于隋唐时期文献,活跃于东部草原与大兴安岭两侧的游牧民族。在隋唐之前的史料中霫无载,隋唐之时,史料中提及契丹、库莫奚时多涉及到霫,这些族群相邻而居,关系密切。安史之乱后,北方道路不通,文献失载,而晚出史料中多把霫与铁勒之白霫混淆,本文试图通过对隋唐及辽代初年霫之基本史料进行辨析,勾勒出这一民族的发展及消亡的过程。
一、霫之基本史料概述
霫之名最早见于《隋书》,开皇元年(581年)突厥摄图可汗趁改朝换代之时政局不稳欲入侵中原,长孙晟给隋文帝上书应对突厥入侵时说:“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1]。这是现存文献中第一次出现霫,从奚、霫并称来看,它们应为相邻民族。《隋书》中霫出现次数颇多,但没有为霫立传,直到杜佑编纂《通典》时才有霫传。《通典》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801年),是杜佑在唐玄宗、肃宗年间史官刘秩所作《政典》的基础上修成。唐初非常重视四夷之事,“贞观时,远国皆来,中枢侍郎颜师古请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为王会篇”[2],《唐会要》蕃国朝贡条记载,“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3],故《通典》霫传之史源当来自唐初官方的记录。《通典》曰:“霫,匈奴之别种,隋时通焉。与靺鞨为邻,理潢水北,亦鲜卑故地。胜兵万余人。习俗与突厥略同。亦臣于颉利,其渠帅号为俟斤。大唐贞观中,遣渠帅内附”[4]。据杜佑所记,霫臣于颉利并受其封号俟斤,这应为唐初突厥称霸草原之时;“贞观年间内附”是指突厥颉利可汗任命突利可汗掌管东部地区时“突利敛取无法,……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内属”[5]一事;从以上史料可知杜佑所撰霫传记事的时代下限应为贞观年间。
继《通典》后《旧唐书》有霫传。《旧唐书》曰:“霫,匈奴之别种也,居于潢水北,亦鲜卑之故地,……东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与乌罗浑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环绕其境。人多善射猎,好以赤皮为衣缘,妇人贵铜钏,衣襟上下悬小铜铃,风俗略与契丹同。有都伦纥斤部落四万户,胜兵万余人。贞观三年,其君长遣使贡方物。”[6]与《通典》相比,《旧唐书》霫传更加详细,对霫之四至及其周围民族、人口、部落名称、风俗习惯都有记述,其史料来源应于杜佑时代之后。
二、霫之前身地豆于史料辨析
《旧唐书》与《通典》都记载霫是匈奴的别种,居住地在潢水以北原鲜卑故地,有兵力万余人。据《通典》霫隋时始通中原,《隋书·李询传》《隋书·高祖纪下》《隋书·韦世康传》等都有关于霫的记载,霫之名在隋前文献无考,《旧唐书》与《通典》皆记其为匈奴别种,不知所据。《全唐文》有“北殄匈奴种落”之语[7],可知唐初有称北方草原民族为匈奴的习惯。鲜卑故地指匈奴打败东胡之后,东胡余众保鲜卑山,*张穆考证鲜卑山在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蒙格罕山,见张穆著《蒙古游牧记》卷1,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17页。这一鲜卑活动地域被称为鲜卑故地。从《魏书》太祖本纪及库莫奚传可知,北魏时期鲜卑故地为库莫奚所居,后受地豆于抄略向南迁徙,而《魏书·契丹传》记载高句丽与蠕蠕谋取地豆于之地,那么地豆于应该位于高句丽与蠕蠕之间,其活动范围应包括库莫奚南迁之前的鲜卑故地,而霫早期的居地大体与地豆于相同,故白鸟氏从霫出现的时间及所在地域推断霫即地豆于[8]。地豆于最后出现在文献的时间是《北史》上的记载地豆于“及齐受禅,亦来朝贡”[9],这一事件发生在550年5月。《隋书》中记载581年长孙晟上书中曾提及霫,因此霫在581年前就应存在,隋代霫活动地域正是地豆于的领地,而两者出现的时间也非常接近,霫应为北魏、北齐时期的地豆于。《通典》记载霫之习俗与突厥略同,不同于周边的室韦、靺鞨等族。《魏书》记载的地豆于“多牛羊,出名马,……无五谷,唯食肉酪”[10],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生活状态,霫之习俗与突厥略同,可知霫之生活方式与地豆于习俗相近。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编号1283的藏文卷子中记载Tatabï有以祖先头颅镶嵌金银用作酒杯的习俗,*芮传明先生认为突厥人所称Tatabï可能为地豆于,也可能泛指霫、奚等民族,见其《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第248页。这种习俗广泛流行于欧亚草原地区,冒顿以月氏王头颅为饮器,柔然可汗醜奴以高车王颅骨为饮器,文献中未见库莫奚、契丹等东胡诸族以头颅为饮器的记载,鲜卑和契丹墓葬中也未发现过这种杯子,这种风俗应为霫继承自北方草原民族之传统。霫“妇人贵铜钏,衣襟上下悬小铜铃”,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葬中发现有铜铃和铜钏,发掘者根据墓内出土的五铢钱认为此批墓葬上限为公元一世纪,下限为七世纪[11],此断代显然过于宽泛,而且五铢钱也有可能为前代流传下来,墓葬中遗体位置保持原样的有六个,其头部都面向西北,这或许暗示他们来自西北方;葬式有单人葬和多人葬两种,而早期鲜卑墓葬多为单人葬,这批墓葬的主人从时间与地域看很可能为霫之前身地豆于。
三、霫之方位考证
《通典》称霫“理潢水北”,《旧唐书》则记载南与契丹相接,北邻乌罗浑(《魏书》中称乌洛候,《旧唐书》中称乌罗护)。《通典》记载乌罗浑的方位为“东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为邻”[12],《旧唐书》记载室韦最西端与回鹘相邻的乌素固部在俱轮泊(今呼伦湖)的西南,移塞没部在乌素固部东,塞曷支部在乌素固部的东面,此部落出良马,其位置在啜河的南面,与塞曷支部相邻的是和解部,乌罗护部在和解部的东面,乌罗护东北二百余里的地方有乌丸国[13]。塞曷支部居啜河以南,出良马,啜河即今哈拉哈河,其地应在哈拉哈河中游以南草原地区。和解室韦即黑车子,其居地在呼伦湖东南,兴安岭一带[14],乌罗浑在其东,《唐会要》说乌罗浑“居磨盖独山北,啜河之侧”,其位置应西至哈拉哈河上游以北,东至嫩江以西,南至洮儿河上中游以北,东北距离乌丸国二百余里。《旧唐书》记载唐代契丹活动范围“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15],契丹北与室韦相接,乌罗浑在《旧唐书》中被作为室韦一部,此室韦应为乌罗浑;而《隋书》中记载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此时契丹在“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16]。纥臣水即老哈河。《通典·室韦传》载契丹与室韦的距离为三千里,居靺鞨之北,《通典》这条记载的史源应与《隋书》相同,室韦在隋代及唐代早期并不与契丹相接。大贺氏兴起后“蚕食扶余、室韦、奚、靺鞨之区,地方两千余里”[17],《通典》《旧唐书》中契丹北与乌罗浑相接的记载应与唐代大贺氏兴起后向北扩张有关。
《旧唐书》记载奚“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国”[18],《新唐书》载奚西界为大洛泊(今克什克腾达里诺尔)[19],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设置的饶乐都督府在今林西西拉木伦河北岸西樱桃沟古城,霫在其北。《通典》曰霫“东接靺鞨”,因唐代早期契丹活动范围在土拉河一带,而洮儿河以南大兴安岭东侧为霫之牧地缘故,此地即《通典》《旧唐书》所载的鲜卑故地。《旧唐书》记载霫“四面有山,环绕其境”,孙进己先生认为“今东西乌珠穆沁旗之间地,正符合此地形”[20],但这与《通典》《旧唐书》所记霫于潢河之北矛盾,霫之领土继承自地豆于,其领地应包含兴安岭以西东西乌珠穆沁牧地与兴安岭以东洮儿河以南之地,南与奚相接。《新唐书》记载白霫“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陉山”,《新唐书》白霫传把霫与铁勒之白霫史料混淆,白霫南下应在716年拔曳固攻杀突厥默啜可汗之后,故避薛延陀应为霫向大兴安岭以东洮儿河以南牧地移动之事。太宗二十一年(647年)有诏曰:“其室韦、乌罗护、靺羯(应为鞨之误)等三部被延陀抄失家口者,亦令为其赎取”[21],其时薛延陀兵锋已到靺鞨之地,霫在这时保冷陉山以避之。
冷陉山的位置,《辽史·地理志》曰:“临潢西北二百余里,号凉淀,在漫头山南,避暑之处多丰草,掘地丈余即有坚冰。”[22]据《辽史·地理志》庆州条记载庆州有馒头山,《武经总要》载“曼头山,……南距潢水,本契丹之地,虏主避暑之处,今更名大安山。”[23]《新唐书》云奚“盛夏必徙保冷陉山,山直妫州西北”[24],胡三省认为冷岍山即冷径(径即为陉)山,其地在潢水之南,黄龙之北[25],冷陉山应为兴安岭南部一带山区。
唐代早期霫的北界大概为乌拉盖盆地北部山区和洮儿河中上游以南,与乌罗浑相接,南界至达里诺尔以北、乌尔吉木伦河以北与契丹、奚相接。游牧民族有冬营地和夏营地之分,霫在这一带游牧,其位置也是游移不定,因而史料中记载的具体方位也不尽相同。薛延陀兴起后,遂由大兴安岭以西向东移动,此即《新唐书》记载避薛延陀之事。契丹大贺氏强盛后,逐渐蚕食兴安岭以东地区,阿保机五世祖勃突即生于庆州勃突山(今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新唐书》记载契丹“与奚不平,每斗不利,辄遁保鲜卑山”[26],鲜卑山在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蒙格罕山,由此可知霍林河南岸已为其领地。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汗国灭亡,草原没有出现较强的政治势力,而契丹在大贺氏的领导下兴起,霫在契丹的压力下向大兴安岭以西原牧地移动,退到《旧唐书》所记“四面有山,环绕其境”的东西乌珠穆沁旗之间,故《旧唐书》说契丹与室韦相接。在此后不久契丹中出现霫人,《资治通鉴》载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使守牢霫绐之曰:“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27],这些霫人或为游牧于潢水之北被契丹兼并的部分,或为契丹掳掠的人口。《旧唐书》记载霫有四万户,胜兵万余人,按游牧民族的兵民比例,四万户有兵万余人显然过少,《通典》亦记霫胜兵万余人,但没记户数,四万户约二十万人,从当时的政治态势看,霫似乎没有那么多的人口,颇疑《旧唐书》记载四万户为四万口之误。
四、霫、白霫、黑霫、奚之关系辨析
霫之地曾设立居延州,《新唐书》贞观年间载“以白霫它部为居延州”,此白霫它部应为霫。《资治通鉴》显庆五年(660年)条下这样记载“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侯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28],《唐会要》记载“显庆五年,以其首领李含珠为居延都督,含珠死,以其弟厥都为居延都督,自后无闻焉”[29]。从以上史料看,霫之地应离奚与冷岍山不远,故因其便利,任命李合珠冷岍道行军总管讨叛奚。但《唐会要·霫》中所记霫之事已混入白霫史料,如“贞观三年(629年)朝贡,二十一年(647年),列其地为寘颜州”[30],而《通典》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才通使中原[31];杜佑大历元年(766年)以前就开始收集编纂《通典》的材料,又有刘秩的《政典》为基础,《唐会要》乃宋人王溥所编,从这两书的史源看,显然《通典》比晚出的《唐会要》更为可靠。贞观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唐太宗下诏讨伐突厥,突利因与颉利不和于十二月投向唐朝,霫本为突利属部,《通典》记载霫贞观年间内附,《旧唐书》记载贞观三年遣使贡献方物,此二者所记应为同一件事,即突利归附唐朝以后,其属部霫也随之内附。贞观四年(630年)二月突厥始亡,漠北薛延陀兴起,白霫等诸铁勒皆为所用,白霫此时在拔野古东;贞观二十一年薛延陀灭亡之后,铁勒诸族相继归附,寘颜州正是在此时为白霫设置。《通典》《旧唐书》中霫都有专传,其传与契丹、库莫奚等在一起,白霫在两书中都归为铁勒类,而《唐会要》始把贞观三年霫内附与贞观二十一年白霫地设寘颜州之事混为一谈。霫与白霫的名称应同为译音,霫在文献中出现的较早应为隋代之译音,而白霫耿世民先生认为可与回鹘汗国早期的《铁儿痕碑》中的bädi bärsil勘同[32];据《广韵》白旁陌切,霫为先立切,白霫可以拟音为bek sǐp,接近于bärsil。
岑仲勉先生认为唐初突厥、铁勒诸族降唐者颇多,除阿史那思摩之外没有赐姓李者,而东北奚、契丹多赐姓李,因而怀疑李含珠并非铁勒之白霫[33]。《全唐文》中《征突厥制》、《移蔚州横野军于代郡制》有霫都督比言,比言乃716年随拔野古从漠北降唐的铁勒白霫之族,其原居地并不在与奚相邻东部地区,其姓氏也非姓李,冷岍山附近的居延都督李含珠应为霫人,贞观年间居延州亦为霫所设立。《毗伽可汗碑》中屡次提到出征Tatabï,白鸟氏、岑仲勉先生等认为是地豆于,芮传明先生则提出Tatabï可能是地豆于,或者泛指霫、奚等部族[34]。从词源上来说Tatabï可能来自Tatar,在古突厥文中有省略现象如barïr省略为bar,突厥文中biriki有联合之意,bir意为南方,Tatabï很可能是Tatar biriki 或者Tatar bir的省略,意为与Tatar联合在一起的民族或者Tatar南方的人。Tatabï这个名称也可能如芮传明先生指出的或许是借用了前代的族名,用来泛指契丹附近的霫、奚等部族,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716-734年在位)时期多次与Tatabï作战[35],东面一直征战到西拉木伦河[36],而突厥碑文中并没有出现霫。作为一个胜兵一万、有四万户的大部落,其游牧地位于大兴安岭西侧草原突厥讨伐契丹的战略要地,自然不可能逃脱突厥的征伐,因此合理的解释是霫或被突厥认为是三十姓鞑靼(otuz tatar)之一或被当做Tatabï,从其所在位置看,后者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745年突厥汗国灭亡,回鹘成为草原霸主,《铁兹碑》中有“一直到居住在日出之方的人民(都归属了)”[40],《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记载回鹘五部落分为五州,北接乌罗浑即反映了这时的态势,东部草原在回鹘的控制之下。《辽史》记载“仪坤州,……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41],仪坤州在今克什克腾旗,糯思正是生活在回鹘占据草原的时代,716年降唐活动于张家口以北的白霫与乌拉盖盆地、东西乌珠穆沁一带的霫并入回鹘也应在这个时期。中原人为了区分这两部,分别冠以黑霫、白霫的名称,因早先南下的白霫部靠近幽州,幽有黑之意,故称之为黑霫,而霫则称之为白霫。此时的霫已被作为回鹘部落看待,居延州之霫应为高宗时居延都督李合珠部众的后代;黑霫应为原铁勒寘颜州之白霫,而这两部后来亦逐渐融合,黑霫之名不见于史料。
840年回鹘被黠戛斯打败,会昌三年(843年)回鹘残部乌介初在幽州八十里以外驻扎,后又依附和解室韦至幽州东北约四百里外下营,从和解室韦到幽州的距离计算此地大约在今达里诺尔以北,其地原为霫活动之范围,而和解室韦占据于此,霫应在回鹘汗国崩溃时南下。关于霫的流向,《新唐书》中记载,霫“其部有三:曰居延,曰无若没,曰潢水”,《新唐书》为晚出材料,而霫传中抄录前代史书时把霫与白霫混淆,但这条材料不见前代史书;霫部中有一部为潢水部,此部应因水得名,这一部应靠近契丹和奚。《新唐书》记载大中元年(847年),诸奚叛乱,张仲武烧帐落二十万,此时的奚族势力很大,霫在回鹘崩溃时应依附于奚。
906年阿保机派偏师征讨奚、霫诸部,霫应该在这次讨伐中离散,这是现存史料中霫作为部族最后存在的记载。912年“上亲征西部奚……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霫之地。”[42]阿保机讨伐奚而尽有奚、霫之地,此时霫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应已不存在。辽寿昌三年(1097年)的贾师训墓志载,“自松亭已北,距黄河,其间泽、利、榆、松山、北安数州千里之地,皆霫壤也”[43],松亭在今河北宽城县西南,松山今赤峰松山区,榆州今朝阳凌源县,此所载诸州都在库莫奚之活动范围。河北平泉出土的咸雍六年(1070年)萧福延墓志载,“以霫诸部地方千里,……,册共为奚王。”[44]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记,“馆宅川间,中有大水,曰霫水,乃故霫之区也。”[45]霫水即今滦平兴州河。辽代之时,霫有时也称白霫。《辽史·地理志》载,“大定县,白霫故地。”[46]辽代墓志中也经常出现称中京为白霫[47]。辽代所称霫壤的地域多在奚活动范围之内,霫与白霫在文献和碑铭中多以地名出现,由此可知霫在辽的征伐之后部落离散,逐渐融入奚中。霫作为部族虽然消失,但霫人在辽早期并没有被迅速同化,其聚居地仍以霫为名,这也是辽代文献中许多地方被称为霫地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长孙览传[A].隋书(卷51)[C].北京:中华书局,1974.1327.
[2]回鹘上[A].新唐书(卷271)[C].北京:中华书局,1975.6150.
[3]使馆上[A].[北宋]王溥.唐会要(卷63)[C].北京:中华书局,1955.1089.
[4][12][31]边防十六[A].杜佑.通典(卷200)[C].[唐]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5490,5489,5490.
[5]突厥上[A].新唐书(卷215)[C].北京:中华书局,1975.6038.
[6][13][15]北狄[A].旧唐书(卷199下)[C].北京:中华书局,1975.5362,5349,5349.
[7]太宗皇帝[A].[清]董诰等.全唐文(卷7)[C].北京:中华书局,1983.
[8]东胡民族考下篇[M].[日本]白鸟库吉方壮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4.
[9]地豆于[A].北史(卷94)[C].北京:中华书局,1974.2131.
[10]地豆于[A].魏书(卷100)[C].北京:中华书局,1974.2222.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J].考古,1964,(1).
[1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64)[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94.
[16]北狄[A].隋书(卷84)[C].北京:中华书局,1974.1882.
[17][22][41][元]脱脱.辽史(卷37)[M].北京:中华书局,1974.438,442,446.
[18]北狄[A].旧唐书(卷149)[C].北京:中华书局,1975.5354.
[19]北狄[A].新唐书(卷219)[C].北京:中华书局,1975.6173.
[20]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册)[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178.
[21]仁慈[A].[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2)[C].周勋初等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454.
[23]蕃界有名山川[A].[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22)中国兵书集成本[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1120.
[24][26]北狄[A].旧唐书(卷219)[C].北京:中华书局,1975.6173,6167.
[25][27][28]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五年[A].[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0)[C].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6320,6506,6320.
[29][30]霫[A].唐会要(卷98)[C].北京:中华书局,1955.1755,1755.
[32][40]耿世民.突厥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223,223.
[33][35]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卷14)[M].北京:中华书局,1958.757.165.
[34]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1,43.
[37][38]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语史料中に现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J[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1977.14.
[39]关塞四夷篇第三十四[A].[唐]李筌.太白阴经杂仪(卷3)[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88.
[42][元]脱脱.辽史(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74.2.
[43][4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479,131.
[45]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144.
[46][元]脱脱.辽史(卷39)[M].北京:中华书局,1974.482.
[47]李义,胡廷荣.辽中京大定府别称白霫考略[J].中国历史文物,2004,(5).
(责任编辑贺卫光责任校对马倩)
[作者简介]李荣辉(1978—),男,山东青岛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及北方民族考古。
[收稿日期]2015-11-23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1-012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