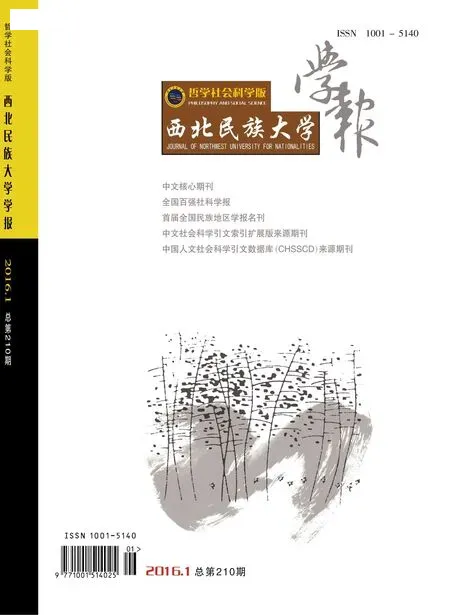近代史上藏族康区政治秩序建构的重要意义——晚清康区改土归流为中心的考察
2016-02-19曹海霞
曹海霞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近代史上藏族康区政治秩序建构的重要意义——晚清康区改土归流为中心的考察
曹海霞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鸦片战争,开启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晚清政府抛弃传统的因地制宜的“羁縻怀柔”的治边政策,开始走上化边疆为腹地,国家建设政治一体化之路。改土归流成为国家重构康区政治秩序的制度性选择,改土归流剔除了地方土司的割据势力,使得中央政府的力量延伸到了基层民族地区,开启中央王朝在康区大规模行政建制的滥觞,逐步将西南边疆地区纳入到国家的统一行政建制中来,近代康区政治秩序的建构在政府力量的主导下得以实施。
[关键词]康区;政治秩序;改土归流;赵尔丰
在藏族传统的地理历史概念中,习惯上将其居住地域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部分,“康”的藏文名字(Khams)亦译作“喀木”。在清代文献中常常被称为“川边”或者“边地”。西康作为一个地域名称在近代史上多有变更,以致为一般人所不知,“西康”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清末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于宣统三年(1911年)6月上奏清廷的奏折:“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省’,建设方镇,以为川滇屏蔽,藏卫根基”。[1]傅氏所谓的古康地就是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的“康”区。历史上的西康在地缘上正处于川、藏、滇、青、甘五省结合之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挟制三边,大为国防之重镇,小为滇蜀之屏藩”[2]。因为康与藏在地缘上唇齿相依,所以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战略中,该地区都充当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有清一代,康区扮演着清政府治藏的“依托”,控驭藏地“锁钥”的重大角色,康区社会秩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清政府对藏地的治理。
一、改土归流:内忧外患的时代选择
清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制定因俗而治的政策,如蒙古地区的蒙旗制,新疆回部的伯克制、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以及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始自元代,明、清两朝继承了这一政策。由于土司世代盘踞之地,掌管地方的军政民事,土司在自己的辖地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许多土司称霸一方,鱼肉百姓,为所欲为,兴兵作乱,鉴于此,清在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即废除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改为与内地相一致的地方官职。但是由于康区地形挟有峡谷高原,大部分地区是荒芜的砂地和岩石,冬季气候严寒,大雪封山,行路艰难,往往一二日的路程荒芜人烟。康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清末全国范围改土归流之际,清政府对其仍然实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羁縻政策,封授不同等级的土司职衔,允其世袭罔替,只是设立流官进行试探性的改革。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在打箭炉设立打箭炉厅,是属于散厅性质的行政单位,雅州府同知分治其地“兼辖番汉”,“自理塘、巴塘以西,直抵西藏”皆归其管辖,隶属四川省建昌道,朝廷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土流兼治的政治构架。此后,清政府对康区的统治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偶有土司叛乱,但规模都不足以对清王朝的统治造成直接的威胁。
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加紧了对我国边疆地区的蚕食,边疆危机日益加剧,整个中国从东北、蒙古、新疆直到西藏都处于肢解危机中;台湾、广西等海疆省份,也岌岌可危。西藏更是面临着危机,英国于1888年和1904年发动了侵掠西藏的战争,强迫清政府签《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拉萨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侵略范围触及到了川边和西藏,并笼络达赖、培植亲英分子、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西方殖民国家以“游历”“探险”“传教”等名义,不断地派驻间谍分子渗人西藏,插手西藏事务。而西藏内部达赖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和驻藏大臣的无能两次出走,从而对武力强大的英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对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来讲,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它说明清政府对西藏的影响力和控制能力已大大减弱,西藏地方的离心力在逐渐增大,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正在尖锐化、公开化。
面对藏区岌岌可危的局势,清政府接受了边疆大臣“固川图藏”“内固滇蜀”“外杜英俄”的战略,决心在川边康区派官设置,改土归流。光绪三十年(1904年)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加强对康区的管理,但是因为收复瞻对问题,被当地土司杀害于巴塘,这就是“巴塘事变”,巴塘事件的发生,使清政府感到了川边事态的严重性。凤全是清政府钦定的帮办大臣,乃朝廷命官,却被地方土司戕害,其中固然有因凤全改革急功近利,违背康区民众利益的一面,但朝廷命官被随意杀害,可见清政府在川边地区的权威何其薄弱。面对地方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统治者必不能容忍,清政府痛下决心,遂派赵尔丰平息事变,经营川边,揭开了康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序幕。
二、改土归流:康区设治的基本形态
1905年,赵尔丰率军进入川边,开始了赵尔丰对川边的经营时期,赵氏经营西康的理念主要体现在“经边六事”*经边六事”即“练兵”“兴学”“通商”“招垦”“开矿”和“交通”。和“平康三策”上。其中平康三策之首策就是将四川腹地三边的馃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使“一道同风”;第二策就是,“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山为界,扩充疆域,以保西陲”;第三策是开发西康、联川、康、藏为一体,建西三省,“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西藏,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即奉天、吉林、黑龙江)之例,设置西三省(川、藏、康)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3]。赵氏的平康三策把康区、川边和西藏的经营放置于一体考虑的治边理念,切合了时代的需求,从而得到了当时四川总督锡良的赞赏:“嘉其议,据以入奏,廷旨报可”[4]。晚清政府也认识到对康区地方建设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藏地安危,于是痛下决心,开始在康区设官建制,逐渐放弃传统中央政府“羁縻怀柔”的统治政策,从而寻求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之路。
1906年,清政府正式在川边设立边务大臣,并委任赵尔丰为边务大臣之职,政府为了支持赵尔丰,使他办事不掣肘,又特将其兄赵尔巽由东三省将军调任四川总督,“以免扦格,而便联络”,“无分畛域,随时接济”,[5]利用四川的人力、物力等地方的优势经营边、藏。赵尔丰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开始了在康区大规模行政建制的滥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处理德格土司兄弟纷争,消灭了昂翁降白仁青势力,设立边北道、邓科府、德化州、白玉州、冈普县、石渠县,并将察木多(今昌都)、乍丫(今察雅)、江卡划入康区范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奏请将巴塘改为巴安府,三坝改为三坝厅,盐井改为盐井县,乡城改为定乡县,稻坝改为稻城县,贡噶岭设县垂,均隶巴安府,将打箭炉改为康定府,里塘改为理化厅,中渡改为河口县,均隶康定府,设康安盐茶道,统辖新设各府、厅、县。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高日、春科两土司均情愿将印信、地土、百姓交还朝廷,赵尔丰奏请改土归流,并在郎吉岭设官管理。1911年3月,赵尔丰协同傅嵩炢平定了明正土司叛乱,将明正土司领地改为泸定、九龙、道孚、丹巴四县。赵尔丰从1905到1911年,经营康区历时七年,“所收边地(指改土归流),东西计3 000余里,南北计4 000余里,设置州县30余”“俨有行省之规模焉”[6]。于是傅松炑向清政府提出在康区建省的建议:“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藏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四方皆有建瓴之势,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省,建省之后‘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一举而三善备’”[7]。西康建省建议出于“以建康省,俾定名义而站领土”的战略考虑,一方面打击康区土司只知道有西藏不知道有朝廷的地方割据局面,另一方面使得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深入到康区,这一措施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
赵尔丰的改流措施,是清末中央政府在康区开展的有关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等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经济上鼓励屯垦,兴办开矿;交通上修筑道路,办理邮政,改革度量衡;文教卫生上创办学堂;风俗上,改革旧的风俗习惯等等。这些措施实行使得康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赵氏的改革,注重制度的建设,改革过程中制定和颁布了《巴塘改革章程》[8],内容宏范,主要涉及“永远废除土司之职,改土归流,土司从前所设马本、协廒、更占、百色、古噪等名目,一概裁撤不用”“无论汉人、蛮人,皆为大皇帝的百姓”,将世袭土司的职权在康区民众中剔除,表达了要把中央权威深入到康区的治理观念。还有大量站在康区民众角度制定的措施“废除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将无偿支派乌拉改为价雇,禁止放高利贷”等等,这些措施减轻了民众的杂役摊派,同时也是对当地土司、头人利益的一种重创。为了确保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力切实的深入到民族地区,确立牢固的边疆统治系统,在打破康区原有土司统治的基础上,设置了相当于县一级的政权组织形式,凡属管理地方百姓的钱粮诉讼等一切事宜,直接隶属于边务大臣。赵氏本着“官足以养民,民足以养官”的原则,每县设立委员一人,负责全县事物。每县分为东、西、南、北、中五路,每路设立保正一人,协助地方委员办理日常事务。设立了与内地相一致的行政建制,这样保证了土司被废除后康区地方行政事务的正常运转,避免地方政治权利出现真空状态,使得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逐步的向基层地方延伸。
三、改土归流:近代康区政治秩序的建构
清末的改土归流,打破了传统的康区地方行政建制,在川边设置了道二,府四,州一,厅二以及河口、定乡、稻城、盐井、白玉、同普、瞻化、科麦、宁静等十几个县,建立了与内地相一致的政治制度,康区各项政治机构初具规模,这一措施成为国家在民族危机时刻重构康区政治秩序的制度性选择,因而近代康区政治秩序的建构是清政府面临西方殖民国家鲸吞蚕食的危机时刻,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治秩序的建设,国家的政策导向成为政治秩序建构的主导力量。
改土归流打破了康区土司的世袭特权,使得中央政府的力量逐步深入康区基层社会之中,川边康区一步步从封建王朝的土司辖地转变为现代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一个行政单元。加强了清政府对川边的直接管理,增强了川边与内地联系,有利于促进藏汉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加藏汉兄弟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民族团结。中国的土司制度始于元代,中央政府对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因地制宜的羁糜政策,在当地封受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长官等各级封号。土司名义上直接隶属于清王朝,有向清政府定期朝贡、献纳贡粮和接受征调的义务。但因其职务可以世袭罔替,对辖区内的居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因而土司对朝廷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在各地的辖区内为所欲为,逐渐形成与中央统一领导向背离的割据势力。赵氏的改流措施剥夺土司特权,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各地建立与内地相一致的行政建制,使得中央的力量延伸到了民族地区的基层。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改土归流的推行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做出了卓越贡献,进而也为民国时期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巩固西南国防,维护国家的统一,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我们知道,边地是国家的屏藩,屏藩的存毁,关系国家的存亡。改土归流是在外来侵略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边疆民族危机的时刻,中央政府作出的时代选择,改土归流中的众多举措很多是关于规划西藏、经营西藏的的内容,沟通了川、藏联系,根本改变了过去川边阻绝,“西藏孤悬”“英兵入藏,川不问战”的局面,使川省和内地成为西藏边防前线的后盾。这样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图谋,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在中国传统的治边思想认为:“中国即定,四夷自服”。中心领导边缘,有着严格的华夷等级秩序,认为治理边疆就应该采用符合民族地区特殊民族政策,因俗而治成为了最好的选择,实行了以“土官治土民”和内地郡县制迥异的地方政策。但清末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打乱了中国传统的治边政策,中央政府不得不寻求边疆治理新的良方,政治体制一体化成为了时代必要的选择。康区改流在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改革着眼点是强边,从而确立了边疆与内地利益一致性。而且,巩固了西南边防,使得地方政治秩序处于平稳状态。
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头人、寺庙的政治经济特权,免除了各种沉重的乌拉差役、高利贷盘剥,减轻了广大农牧民的负担,废除了旧的经济生产结构,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川边藏区社会稳定。构建康区民众对于政治秩序建构的认同。康区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和强制力这种“硬件基础”,也依赖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公民)民族主义这样的非常感性的“运行软件”。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合法性,即决定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只有获得人民支持和社会合作的国家政权,才是稳定与有效的。改土归流废除了康区剥削百姓的经济制度,使得广大百姓欢欣鼓舞,加深了民众对这一措施的认同。
四、结语
政治秩序是社会的基本需求之一,它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更迭嬗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探求理想政治秩序的过程。清末的改土归流,设置流官管理,构建了康区现代基层政府的基本框架,这是康区政权建设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这一措施沟通了汉藏关系,维护了国家统一,构筑了西南国防,促使现代国家的构建与发展,从而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改土归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说到底就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势力逐步介入到康区,并渐成主导之势,尽管随着辛亥革命这种主导力量轰然倒塌,但是我们看到这是地方政治秩序建构不可或缺的力量。正如亨廷顿所说:“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9]”。的确,许多国家恰恰在传统权威削弱的同时,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公共权威,因而不能够有效控制社会势力左右政治发展局势,从而导致政治秩序混乱。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秩序很快就被破坏,土司复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但是这也恰恰说明权威与制度化是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建构是保障。中国辛亥革命后,传统的政府不复存在,而新的权威政府没有出现。西康秩序的失控主要是和当时中央政府缺乏权威,中央政权没有把势力深入到民族地区去,地方各个实力派军阀为己私利,不顾民族国家大义而出现。因此,能不能提供一个合法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的政治权威,对于国家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7]傅松炑.西康建省记[M],民国元年铅印。
[2][6]杨仲华.西康纪要(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361.
[3][4]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1-2,2.
[5]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M].5857.
[8]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M].成都:巴蜀书社,2004.149-150.
[9]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 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6-7.
(责任编辑杨士宏责任校对包宝泉)
[作者简介]曹海霞(1977—),女,河北邯郸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2015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西康建省过程中政治秩序的多元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0301-01500202)
[收稿日期]2015-05-19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1-007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