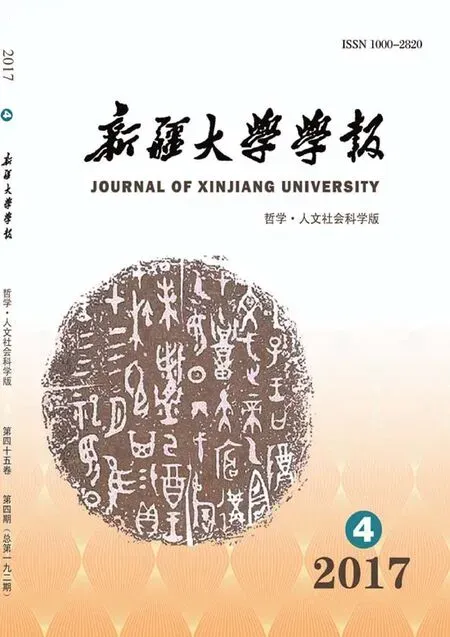论唐传奇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改写*
2016-02-18何亮
何 亮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1],鲁迅先生此番话,精辟概括了志怪小说与唐传奇的渊源关系。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受时势影响,内容虽吸收新的文化因子,文体体制却没有跳出志怪的藩篱,仍然是“残丛小语”、“粗陈梗概”;另一方面,在承袭中有意识地加以重构,形成新的小说类型——唐传奇。唐传奇的成熟、繁荣,很大程度因其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进行了改写。这种改写,体现了唐人“有意为小说”,表现在故事情节、叙事思维、文体体制等诸多方面,是对志怪小说文体的一种再创造,是促使小说文体独立的重要原因。
一、增衍、改编故事情节
唐传奇中的许多作品,有些是口耳相传的奇闻异说,有些是文人士子于驿馆官舍的“昼晏夜话”,有些是科场士子逞才炫学的怪谈漫说……“说”“话”“谈”,透露出小说消遣、娱乐的性质。神奇怪异、看似荒诞不经的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符合接受者求新、求异、求奇的审美心理,成为唐传奇创作的重要素材库。唐传奇沿袭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题材,继续演绎花妖狐魅、神仙道士、精灵鬼怪等类型故事。但为吸引接受者视线,唐传奇小说家对此类故事的情节进行了增衍或改编。增衍、改编的重要方式是移植、组合不同题材的故事入小说,形成内容细致详实,情节委婉曲折,意蕴深广、绵长的故事,彻底脱离了六朝志怪“残丛小语”、“粗陈梗概”的樊笼,演进之迹甚明。
“扣树传书”是志怪小说的重要题材,源自曹丕《列异传》“胡母班”:“胡母班为泰山府君赍书诣河伯,贻其青丝履,甚精巧也。”[2]19《列异传》全文仅一句话,简述胡母为泰山府君给河伯送信,河伯回赠“青丝履”。胡母班、泰山府君、河伯的人物形象,胡母送信的经过,及送信后的情况,都没有具体叙述,留下了叙事的“空白”。这些空白,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能激发创作者的灵感,为创作者的再创作提供故事的原型。唐传奇“扣树传书”系列故事,就是针对此文本留下的“空白”,通过移植、组合不同的志怪题材进行敷衍、填充。故事情节得到丰富的同时,情节发展脉络与最初的故事也大相径庭,从而产生了新的故事文本。
如《柳毅传》,小说以“人神遇合”开篇,柳毅与受丈夫摧残的龙女相遇,接着,借用扣树传书,描述柳毅在正义感的驱使下,替龙女送信,引出钱塘君杀小龙,解救龙女,龙女与家人团聚。最后,因袭人神婚恋的故事模式,写柳毅与化身为寻常女子的龙女缔结连理,后亦仙去。柳毅的行侠仗义、龙女的柔婉娇媚、钱塘君的暴戾、龙宫的富贵奢华等,在作品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无不跃然纸上。故事情节柳毅与龙女相遇—柳毅替龙女送信—钱塘君为侄女复仇—钱塘君逼婚—柳毅与龙女成婚—柳毅成仙等,腾挪跌宕,扣人心弦。整个故事,融合“扣树传书”、龙的传说、人神遇合、人神婚恋等题材,演绎出旖旎的爱情故事。又如李復言《续玄怪录·刘贯词》,以“扣树传书”为故事核心,叙述刘贯词替龙神幻化的蔡霞秀才送信,引出故事人物龙母、龙妹。送信使命完成后,故事并没有结束,龙妹对龙母异于常态的牵强解释,都为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埋下伏笔。最后,移用善识宝物的胡商题材,借胡客之口,揭示蔡霞秀才一家的真实面目。这则故事最大的成功,一是情节曲折离奇,一波三折。刘贯词替蔡霞秀才送信,遇难以抑制食人本性的龙母;脱离险境回到人世,因宝物而遭致灾祸;得道士相助转危为安。二是人物形象的刻画鲜活生动。蔡秀霞一家的狡猾、阴险、奸诈,栩栩如生。尤其是龙母,潜藏在人形下的兽性描写形象逼真。《刘贯词》融合“扣树传书”、“胡商”、“龙的传说”等故事,上演了在人性、兽性、道义之间,人与神的一场交锋。
同为“扣树传书”故事,相比《列异传》“胡母班”,《柳毅传》、《刘贯词》等唐传奇通过对不同题材故事的移植、组合,故事情节得到了加工创作,虚构出截然不同的故事。不仅故事主题迥异,情节波澜迭起,故事人物形象也千姿百态,绝不相似。
根据现存文献资料,“幽冥类”故事的肇始者为刘义庆《幽冥录》“法祖与王浮”:“蒲城李通死来云:见沙门法祖为阎罗王讲《首楞严经》。又见道士王浮身被锁械,求祖忏悔,祖不肯赴。”[3]全文不到40字,故事情节、人物都颇为简单,通过描述李通入冥间所见,反映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徒与道教徒相互争斗的史实。同写人在冥间的经历,唐传奇“幽冥”类系列故事,因与其它故事题材相融合,补充了故事人物入冥间的前因后果,还敷衍故事人物在冥间的具体情形,内容比《幽冥录》“李通”更详实,情节更丰富,蕴义更深刻。
如《法苑珠林·萧氏女》,沿袭“入冥”题材,以萧氏女死后坠入冥间开篇。因植入妒妇题材,补充了萧氏女入冥间的原因,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合情理,更令人信服。接着,小说借用“梦幻”题材,以萧氏鬼魂幻化进入遭她毒打的婢女闰玉梦中,讲述其在冥间的痛苦遭遇,并约定相见之期。然后,再次以“入冥”故事的叙事模式,嵌入婢女闰玉被萧氏女召入冥间,亲眼见证其在冥间所受之苦。这种故事中套故事的叙述方式,丰富了故事情节。在叙事视点上,改变了《幽冥录》“李通”以第一人称全知视角自述冥间经历的方式,由第三人称限知视角通过婢女转述萧氏女在冥间的始末。佛法的威严、冥界的实存,都非常真切。最后,叙述者文末发表议论,宣扬因果报应的主题。相较于《幽冥录》“李通”,《萧氏女》中故事人物颇多;叙事结构以“入冥”故事嵌套“入冥”故事,萧氏女与闰玉先后进入冥间的情节分头进行而互有交接,头绪更纷繁复杂,但作者将故事叙述得有条不紊。《萧氏女》以“入冥”题材为内核,融合“妒妇”“果报”“梦幻”等题材,寄托信奉佛法的寓意,也警醒世人不论尊卑贵贱,须友善相待。
又如《韦讽女奴》,借用“死而复生”故事,以女奴复生开端:“小童薙草锄地,见人发,锄渐深渐多而不乱,若新梳理之状。讽异之,即掘深尺余,见妇人头。其肌肤容色,俨然如生。更加锹锸,连身皆全。唯衣服随手如粉。其形气渐盛,顷能起……”[4]949女奴复生的神异,暗示其经历、身份不同寻常,为情节发展埋下伏笔。女奴复生后,融合“妒妇”和“幽冥”类题材故事,由女奴亲自交代入冥间是因女主人好妒,并描述冥间见闻。最后,用“修炼成仙”题材揭示复生在于修德成仙:“修身累德,天报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4]50多种题材的融合,尤其是佛教入冥题材与道教成仙题材的相融,将佛教的轮回转世与道教的成仙融为一体,彻底颠覆“幽冥”类故事弘扬佛法的套数,强调修德可成仙的神仙道教思想,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影响下的产物。
《萧氏女》《韦讽女奴》都是以“幽冥”类故事为题材衍生的小说故事。因融合“妒妇”“修炼成仙”“复生”等故事题材,人物入冥后活动与生前经历得以勾连,作品对人物的介绍不再是片段式的截取,而是完整的呈现。故事场景、人物活动的范围、故事发生的时间与空间都得以扩大。同时,“入冥”故事嵌套“入冥”故事的叙事结构,使小说情节由单一直线向双向复线演进。更重要的是,此系列故事主旨不仅仅宣扬宗教观念,更有警示世人的现实意义。“中国古小说具有强烈的沿袭性,这一特征使得许多辅教之书中的作品,在其承传、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宗教色彩而蜕变成文学性更‘纯’的作品。”[5]唐传奇逐渐从宣扬宗教的“释世辅教”之作,向表达有一定现实主题的文学作品发展,其重要手段和方式是对多种题材加以移植和重组。
通过对“入冥”“扣树传书”系列故事的比较分析,对于单篇小说而言,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容纳的题材单一,故事情节较为平实、简单,缺少波澜:“扣树传书”即简单交代信使通过敲击树木连接神异世界,将信件送给主人;“入冥”类故事讲述人死后入冥间一遭,后复生返回人世。作品平铺直叙地描述整个事件,情节并不生动。唐传奇虽袭用汉魏六朝志怪小说题材,却不简单照搬,往往结合时代特征对多种题材的故事加以移植、重组:多种题材故事的融入,丰富了故事情节。《萧氏女》等唐传奇小说,在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人物进入冥界返回世间”的情节主干上节外生枝,移植“妒妇”“复生”等题材作为情节的补充,叙述了婢女丧命进入冥间的前因后果、婢女得以重生的前后始末、婢女的人生经历及最后结局。多种题材故事的移植,故事篇幅明显变长,情节更加曲折有致;题材重新组合后,唐传奇情节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同类故事相比大相径庭,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柳毅传》等小说作品,扣树送信部分只是整个故事情节链的重要一环。由于作品将“扣树传书”题材与“人神婚恋”“龙的传说”等进行组合,情节的主体及主题不再是传书,而是人与异类的婚恋。多种题材的移植、重组,使唐传奇小说作品的意境、主题、故事结构、叙事模式等都与同类志怪作品不同。唐传奇从志怪小说中以一个题材为文本核心,与其它题材故事交融而衍生为一个“超文本”。核心文本,是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依据和动因,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组合其它与之相关文本。如“扣树传书”系列故事与龙神、胡商、人神相遇等重组,“入冥”系列故事与死而复生、修炼成仙、妒妇等重组。重组是对“前文本”的隐括和延宕,核心文本则从故事原型中剥离,嵌入新的叙事,按照新的需要,成为“超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文本产生明显或潜在的关系,使各文本形成内在联系衔接在一起,产生新的叙事文本①热奈特在《热奈特论文集·隐迹稿本(节译)》中指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出现,表示其间存有互现关系。主要有几种表现形式:一,即传统的“引语”实践(带引号,注明或不注明出处);二,不太明显,不太经典的形式,即秘而不宣的借鉴,还算忠实原文本;三,以寓意的形式潜藏于另一文本。对唐传奇而言,主要是第二种形式。唐传奇以某一题材为核心文本,移植其它故事题材,并加以重新组合,使各题材间形成内在联系,从而产生新的故事,即超文本。参见热拉尔·热奈特著,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集·隐迹稿本(节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页。。
二、转换叙事思维
不论事件真实与否,人类叙事思维的存在,可跨越时空的限制,将不同时空的事件加以呈现,“改变了人的生存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叙事思维的主观性,使事件的叙述不可避免地带有叙述者的情感色彩,潜在表达叙述者自身的思想、看法及欲望,“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生命的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无常抹去的自我”[6]。汉魏六朝小说与唐传奇的叙事思维有根本区别。汉魏六朝的小说编撰者②形成于汉魏六朝时期的小说,是小说家将流传于民间里巷的小家之言编撰而成。编采者只是对其进行整理、结集及润色,还不是有意的小说创作。,搜集、整理、结集小说时力求客观,一如史学家记载历史事件。而唐传奇小说家将叙事思维的主观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有意敷衍故事,提高了写人、叙事的技巧。
汉魏六朝时期,迷信思想盛行,方术大行其道,佛道也逐渐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加之当时社会动荡、朝代更替频繁,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极为有限。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此时期的叙事思维,大多将神怪看成真实。东晋史学家干宝在《搜神记》序中也说,他撰写《搜神记》是为了“明神道之不诬”。不仅如此,人们还将人的力量向神灵鬼怪延伸,趋利避害,获得庇护。因而,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超自然法术的故事,如《列异传》“营陵道人”:
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使人与死人相见。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死人,不恨。”遂教其见之。于是与妇人相见,言语、悲喜、恩情如平生。良久,乃闻鼓声,悢悢不能出户,掩门乃走,其裾为户所闭,掣绝而去[2]7。
这是一则招魂故事。关于招魂,可追溯到淫祀之风大畅的楚国。屈原《招魂》③《招魂》作者的归属尚有争议。司马迁说是屈原作,王逸说是宋玉作。经一些学者研究,一般都把它归于屈原名下。载有具体仪式:“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归来归来!不可以托些。”[7]道家认为,魂、魄相依,生命长存。魂、魄分离,则生命消逝。逝去之魂,利用法术可将其召回。故事旨在说明神异的法术可帮助生人与死人相见,营陵道人、妇人、同郡人的形象模糊不清,招魂的具体仪式、妇人魂魄与同郡人见面时的具体情形,作品用粗线条勾勒出简单的轮廓,没有细致地渲染、铺展。
又如《博物志》卷五“方术”,记超脱生死、自然的法术故事:
近魏明帝时,河东有焦生者,裸而不衣,处火不燋,入水不冻。杜恕为太守,亲所呼见,皆有实事[8]63。
据典籍记载,传说中有一种入火不燃的火浣布。《海内十洲记》曰:“取其兽毛,以缉为布,时人号为火浣布,此是也。国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终无洁净。唯火烧此衣服,两盘饭间,振摆,其垢自落,洁白如雪。”[9]《博物志》也提到了火浣布:“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汙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臈。”[8]26《搜神记》“何参军女”也提到了火浣布:“其母取巾烧之,乃是火浣布。”[10]焦生不惧水火的法术,具有火浣布般神异的特性。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表达了人们确信通过修炼,可超脱、驾驭自然。文末特意将杜太守作为事件的见证人,强调事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焦生的年龄、样貌、衣着、性格,从作品中无法得知。修得此法术的过程,作品也没有交代。
汉魏六朝时期,受诸多因素影响,即使是神怪之事,时人也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小说编撰者秉着还原真实的叙事宗旨,当成实有其事来记录,绝少加工、创作。这样的叙事思维方式,限制了小说家写人、叙事技巧的运用。唐传奇亦讲述这类神秘故事,不同之处在于唐人的叙事思维发生了变化。他们强调主观性思维对叙事的意义,用一定的艺术技巧组织所描述的人、事件,从而虚构故事、表达情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言:“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对于唐传奇的虚构性,虞集《写韵轩记》也说是唐之才人想象之作,“非必真有是事”。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的神异故事,激发了才情满腹的唐小说家的创作灵感。他们对“幽怪遇合”之事精雕细刻,表达内心的诉求及欲望,故事也因此而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气息。
如裴约言《灵异志·许志雍》,叙述男巫为裴约言亡妻招魂的动人故事。作品开篇即以诗情画意之笔,描述裴约言亡妻的仪容淡雅、秀美,铺叙裴约言对亡妻的思念至深。每当清风月明、笙歌散尽之时,裴约言就叹泣悲嗟妻子的早逝。裴约言的痴情,引出亡妻现身及请道士作法。亡妻于八月十五月圆夜出现意味深长,表明他们两人心心相惜,伉俪情深。但人鬼殊途,裴约言只能听到亡妻的声音,无法见其真容。因此,他不惜重金请男巫协助。事前,男巫跟裴约言商议所需资费:“乃计其所费之直,果三贯六百耳。”[4]905显然,男巫掌握招魂术是为了谋生。然后,作品详细描述了招魂的具体经过,及夫妻相见时的感人场面:“遂择良日,于其内洒扫焚香,施床几于西壁下。于檐外结坛场,致酒脯,呼啸舞拜,弹胡琴。”[4]906晚,亡妻靓装华服与之相会于堂内东隅,细叙款曲,一如平生。美丽柔媚、温情款款的亡妻,对爱情痴心不忘的丈夫,为蝇头小利以法术谋生的男巫,形象都饱满、充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亡妻悄然现身的神秘场景,裴约言与男巫为法术费用商讨的过程,亡妻与丈夫相见时的情境,敷衍得细致、详实、真切,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些在志怪小说中都是语焉不详的。当然现实中不可能真有招魂术,唐传奇小说家通过此故事意在赞美裴约言夫妇彼此恩爱的真挚情感,而不是志怪小说所宣扬的法术实存。
又如陈绍《通幽记·东岩寺僧》,讲述寺庙僧人与道士崔简斗法,故事在两人法术的对阵中逐步走向高潮:
博陵崔简,少敏惠,好异术……初,僧拒诈,吕生忽于户间跃出,执而尤之。不隐,即曰:“伏矣!贫道行大力法,盖圣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归之,无苦相逼。向非仙宫之命,君岂望乎?愿令圣者取来。”俄顷,见猪头负女至,冥然如睡[4]922-923
道士崔简一出场,作者用先扬后抑之笔刻画其人物形象:年少聪慧,身怀异术,能役使神灵、凭空变化。但救人之困时,他却收受钱财,沾染了世俗的气息。紧接着巧设悬念,将斗法场面写得惊心动魄:狂风中,数以万计、手执剑戟等兵器的神兵,与几十丈高、横眉立目的金刚对阵,腥风血雨的战斗一触即发。神兵是崔简召唤来的,而金刚则是掳走吕谊女儿的胡僧所派出。区区一个金刚镇住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神兵,故事的发展扣人心弦。崔简亲自作法上阵,最终打败胡僧,找回吕谊的女儿。至此故事本可圆满结束,作品陡然插入她对被掳事件的回忆,由此获得胡僧藏身之所的线索。这一事件,推动故事的进一步展开。按理胡僧作案地点在掌握之中,完全可以将他绳之以法。等官兵赶到的时候,他早已逃之夭夭。出乎意料的结局,让人回味、叹惋。整个故事以寻找吕谊之女、抓捕胡僧为核心事件,经由作者精心设计,穿插了斗法、掳人等场景的描写,人物形象性格鲜明,情节波澜迭生。小说通过寺庙僧人与道士的斗法,折射出佛教与道教在思想文化、政治领域的斗争,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中都有数量众多的神仙法术、神鬼怪异的故事。如唐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名篇,作者将思维拓展到视觉所不能及的意识深处,借短暂的梦境将人置身另一时空。通过现实世界与异空间的对比,反映现实人生的荣辱得失。这种思维模式,源于刘义庆《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离魂记》中倩娘为追求幸福,离魂私奔王宙的爱情故事,也是受《幽明录·庞阿》石氏女神魂投奔意中人庞阿的启发。这些作品虽都为神怪不合常理之事,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将其当成实有其事来记录,只简约陈述了事件,人物形象极为单薄。唐传奇以虚构求真实,借怪异的故事外壳,有意运用设置悬念、插叙、倒叙、铺叙等艺术技巧,刻画人物,描述事件,塑造的人物生动形象、跃然纸上,情节耐人寻味,在主题上寄托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作品也因此更具现实色彩。
三、吸收多种文体,形成“文备众体”的文体特征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多为“残丛小语”,篇幅简短,只能“粗陈梗概”。唐传奇的篇幅明显变长,较长的篇幅可容纳更多的内容,使故事的叙述更加细致婉曲。唐传奇扩大篇幅的重要手段是在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吸收多种文体融入小说,形成了“文备众体”的文体特征。关于唐传奇兼备多种文体的特性,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评曰:“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①赵彦卫认为科举士子用唐传奇“行卷”,唐传奇“文备众体”的体制特征,能展现他们“史才、诗笔、议论”的才能。唐传奇是否用来“行卷”,学界尚有争议。不过,经详细统计,唐传奇融入了史传、诗歌、辞赋、骈文、公牍文、碑铭文、祭诔文、判文、祝祷文等十多种文体,确实体现了士子诸多方面的才华。众多文体的融入,不仅使唐传奇融“史才、诗笔、议论”为一炉,形成“文备众体”的文体特征,而且充实了作品的情节内容,完善了叙事技巧。
以人神爱情为主题的志怪故事都有相遇—相恋—分别的固定叙事模式:神女与才华满腹却落魄潦倒的书生相遇,以诗歌酬唱传情。离别之际,神女赠送奇珍异宝、仙家珍馐、修炼秘笈,度脱其入仙籍。而人、神之间的爱情,往往因男子负心、留恋尘世、顾忌神女为异类的身份等以失败告终。
东晋曹毗《杜兰香传》是人神婚恋志怪小说的翘楚之作。小说原传已不传,亦不见著录。李剑国《〈神女传〉〈杜兰香传〉〈曹著传〉考论》对诸书引用《杜兰香传》佚文的情况详加考辨、梳理,从《齐民要术》《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引用的佚文可窥知其概貌。《杜兰香传》类如“传奇”,以“传”命名,篇幅、情节比同时期产生的志怪曼衍,再一次证明志怪对唐传奇的直接影响:
汉时有杜兰香者,自称南康人氏。以建兴四年春,数诣张傅……作诗曰:“阿母处灵岳,时游云霄际。众女侍羽仪,不出墉宫外。飘轮送我来,岂复耻尘秽。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至其年八月旦,复来,作诗曰:“逍遥云汉间,呼吸发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鸡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风波,辟寒温”……言:“本为君作妻,情无旷远。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岁东方卯,当还求君。”[11]
《杜兰香传》叙述神女杜兰香奉母之命降临张硕家与之婚配,后因年命不合分离。故事以史传笔法交代神女的出生、里籍,但神女的具体形貌、性情略而不详。应汉时五言诗歌盛行之风,作品穿插了杜兰香自作的两首五言诗,强化神女作为宗教代言者的身份:第一首出现于杜兰香与张硕初次会面,自告身世,警告张硕顺应天意与之缔结婚姻;第二首于神女与张硕分别前,邀请其同往仙乡。显然,这两首诗为作者刻意之作,意在宣扬道教,与作品意境并未融合无间。张硕与神女之间,不存在真正的爱情。他们奉天命而结合,又因天命而结束。张硕对神女更多的是出于敬畏、膜拜、信奉的宗教式情感,神女对张硕也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恋。
唐传奇吸收多种文体对此加以渲染,改变志怪小说人神婚恋刻意凸显宗教主题而忽略故事人物情感世界的不足,着重表现故事人物的恋爱历程,谱写了人神婚恋故事的新篇章。
如《郭翰》,作品运用辞赋笔法,以如诗似画的笔墨,铺叙织女降临人间风姿绰约的美。周围徐徐吹来的清风,皎洁的明月,馥郁的香气,体态轻盈的、衣着艳丽的仙女,无不炫彩夺目,让男主人公郭翰心荡神摇。文中不止一处用“铺张扬厉”“体物浏亮”的赋体。织女身着世间罕见的服饰、清丽绝俗的容颜、与郭翰的尽兴欢娱等,无不以辞赋作穷形尽相地摹绘。李道和对《郭翰》辞赋的大量使用有评:“作品着力于物色的铺张细描、人性的全面透视,语言修饰华丽,句式骈散相间,节奏张弛有度,应有《汉武帝内传》之类降真小说的影子,自然也该有汉赋笔法。”[12]文中还穿插织女与郭翰往来的书信,以及信末所附之四首诗歌:“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卿?”“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回顾,交作两相思。”“赠枕犹香泽,啼衣尚泪痕。玉颜霄汉里,空有往来魂。”[4]684-685
这四首诗歌,如泣如诉地吟咏恋人之间别离的情愫,细致入微地传达了他们之间的相思离愁,把人仙之间的爱恋提升到心灵与情感真正契合的境界。除此之外,郭翰与织女围绕天上星宿、牛郎等敏感问题的议论性对话,切合人物各自的身份、性情,推动故事情节进展的同时,勾勒更鲜明的人物形象。《郭翰》袭用人神婚恋的叙事模式,借助融入的多种文体,将此类题材的故事推向新的高度:以书信、诗歌传达故事人物的情感,营造出诗情画意俱佳的意境;以辞赋铺写环境、描写人物外貌,为故事人物的上场提供了美丽的背景,形神毕肖地展现故事人物的性情;以论说文说理,给作品增添思辨色彩,拓展作品的主题和意蕴。诸多文体的融入,使故事的篇幅变长,情节节奏变得舒缓。作品在缓慢、悠长的情境中,轻诉人与神仙之间微妙、温婉、令人回味的爱恋。
万物有灵,物我不分的时代,与人最具亲缘关系的当属灵长目猿猴类动物。关于此动物的传说层出不穷,较早的当属志怪小说《博物志》“猴玃盗妇人”: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马化,或曰猳玃。同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然故不免。此得男子气,自死,故取女不取男也。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敢不养也。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皆猳玃、马化之子孙,时时相有玃爪也[8]36。
猴玃盗妇的传说,以《焦氏易林》卷一“坤之第二·剥”为本:“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而独宿。”[13]与《博物志》产生时代稍后的《搜神记》《法苑珠林》《太平御览》等虽均有引录,仅沿袭汉代传说,陈陈相因,无甚新意。故事的重心也不在叙事,情节平淡无奇,所有叙述性文字都为文末杨姓子孙来由的解释性文字作铺垫。
唐传奇将多种文体融入小说,完善了作品的叙事艺术和手段,旧素材从而焕发新意。如《补江总白猿传》:用史传笔法,移花接木,假欧阳纥之名演绎欧阳頠事迹,故事情节发生场景及人物政治化:“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罙入险阻。纥妻纤白,甚美。”[4]28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政治背景,将人事与志怪结合,形成志怪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影射,“《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心怀叵测,把欧阳頠改为欧阳纥,捏造白猿窃掠纥妻‘生一子’之事以诬蔑欧阳询”[14]。作品的主题、寓意不仅仅是《博物志》“猴玃盗妇人”的“记怪”“搜异”,有更多的现实蕴含。以赋体语言铺叙猴玃的人性特征,其形象人情化:“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搜其藏,宝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案几。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4]30猴玃盗妇的情节变为寻妻、救妻。寻妻途中,以赋笔铺叙过程的艰难、欧阳纥的执着:“关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险,咫尺迷闷,不可寻逐……纥尤凄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4]29以诗笔摹绘白猿居所如世外桃源般美好,再以赋笔敷衍人与白猿争斗的精彩场面。书信、史传、赋等文体的融入,将猴玃盗妇的单线情节衍生为猴玃盗妇与欧阳纥寻妻的双线情节,故事结构趋于复杂,体现了唐传奇逐步以现实人事为主题的演进趋势。
唐传奇以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为基础,或借诗、辞赋、骈文等对人物形象、故事环境进行描摹、渲染,或移用辞赋、诗、书信等补充故事情节,或以史传笔法,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或插入论说文说理,深化作品意蕴。多种文体的融入,充分发挥了各文体的功能,使唐传奇呈现集“众体之长”的艺术美。
四、结 语
唐传奇在情节、叙事思维、文体特征等方面,都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进行了改写。这种改写,是唐传奇小说家的一种实质性再创造:题材的移植、组合,增衍、改编了故事情节,使唐传奇小说作品的意境、主题、故事结构等与同类志怪作品都截然不同;唐人有意虚构故事,用一定的艺术技巧借梦境、幻术、神怪等反映社会现实或人生的荣辱得失,以虚幻求真实。在主题寓意上,或寄托人的现实诉求,或暴露社会政治的弊端,相比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实录”“释氏辅教”,叙事思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叙事不再是直书其事,也不仅仅是弘教,而是内心欲望的倾泻,是人自我价值、社会价值的理想显现。叙事思维的变化,是唐传奇逐步脱离史传附庸走向独立、成熟的重要因素;移用辞赋、诗、书信、论说文等诸多文体,扩大了小说的篇幅体制,相应地扩充了作品的内容涵量,形成情节更为跌宕有致、内容更为细致详实的故事。诸多文体的融入,使唐传奇形成“文备众体”的文体特征,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真正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