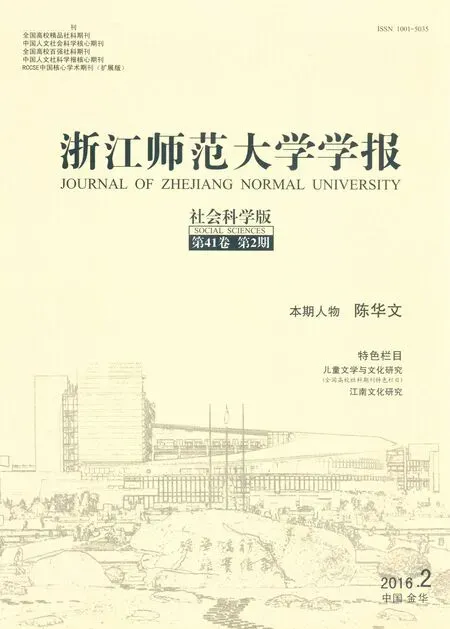马克思哲学批判的两大转向及其存在论筹划
——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存在论解读
2016-02-16周志山张学华
周志山, 张学华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马克思哲学批判的两大转向及其存在论筹划
——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存在论解读
周志山,张学华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批判的两大转向:从对“彼岸世界”的批判转向对“此岸世界”的批判,从“批判的武器”转向“武器的批判”。依循存在论的路径,它预示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存在论筹划:体现在哲学思维上,意味着从知识论的知性逻辑转向生存论的生活逻辑;在哲学批判旨归上,从压迫此在的非时间、非历史的知性关系转向追求此在的时间性、历史性的生存解放。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革命;存在论筹划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创建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学界对该著作的解读成果不少,但从本体论高度解读的并不多。本体论的解读主要表现为两种路径:海德格尔依据《导言》中的某些片段对马克思哲学作了“形而上学化的解读”,①它构成了解读《导言》及其哲学观的主流;少数学者对此作出了回应,认为马克思在《导言》中已经超越了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方式,实现了“实践论转向”[1]与“生存论转向”。[2]笔者认为,这样的回应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仍有必要提升到存在论的高度上来解读《导言》,以期揭示马克思在存在论路径上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及其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估价
马克思的哲学创建在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国内外理论界并无异议。但是,如何评价或评估这一革命性意义,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这种分歧源自人们不同的阐释视角和学术立场。例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等,将马克思哲学革命退行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领袖卢卡奇等,则把马克思哲学革命返回到黑格尔主义的定向上;当代西方有影响的哲学家,如伽达默尔,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置于黑格尔和尼采之间,海德格尔则直接将两者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最终都导回到形而上学之中去了。
因此,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成了当代理论家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了回应和纠正国外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意义的评价上的不足,国内不少学者,如吴晓明、贺来、陈立新等人,在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上,重估了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本体论革命的当代意义,力图指证马克思哲学革命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开启了后形而上学视域,也即存在论的新境遇。
在这里,首先厘定和澄清生存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存在论思维范式和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的本质区别或界限是很有必要的。
所谓“知识论路向”,研究的对象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超验世界,即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第一哲学”,它把哲学规定为“追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以期获得阐释世界万物和一切科学知识的最终根源和最终依据。与此相适应,“形而上学思维范式”是一种试图从终极本体或超感性实体来把握人与世界的思维范式,这是一种迷恋于最终主宰、第一原理和最高统一性的思维范式,具有寻求终极实在的绝对主义、还原主义,以及知性逻辑和概念化思维的唯理主义等特质。其基本做法是: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即感性世界(此岸世界或世俗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彼岸世界或形而上学世界),并设定某一“超感性实体”(如理念、物自体、绝对精神等),作为现实感性世界之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本质根据和最高原则,现实感性世界由此被规定和统摄在超感性世界的阴蔽之中,并以向超感性世界的趋赴和统一为神圣目标。这便是传统哲学知识论路向和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的基本逻辑。海德格尔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中对此评述道:“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如果我们把感性世界称为宽泛意义上的物理世界……那么,超感性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了。”[3]
所谓“生存论路向”,要求理论研究直径达到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的现实生活世界,确立和阐扬现实生活世界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之作为哲学存在论的本质根据。与此相适应,“存在论思维范式”持有生存论的世界观,认为存在只有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才能得以揭示和展露出来,存在的意义并不在超感性的超验实体中,而在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展开和显现之中。这一思维范式要求以生存实践原则取代唯理主义的原则,以现实生活的原则取代绝对主义、还原主义原则,以历史性、时间性取代非历史性原则等。②
如果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置于传统西方哲学向当代哲学转换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的话,不难发现,马克思哲学变革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来自于曾经长期盘踞哲学“至尊地位”的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严峻挑战。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首要任务,就是破除和解构全部形而上学的虚妄性。由于柏拉图哲学是全部形而上学的真正滥觞,而黑格尔哲学则是全部形而上学的巨大渊薮。因此,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味着马克思展开了对以往全部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批判起始于马克思在《导言》中筹划的哲学批判的存在论转向,它体现在哲学批判思维上,从知识论的知性逻辑到生存论的生活逻辑的转向;在哲学批判旨归上,从压迫此在的非时间、非历史的知性关系到追求此在的时间性、历史性的生存解放的转向。
二、马克思哲学批判的两大转向
《导言》写于1843年底,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它是马克思思想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摆脱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影响,并使其转向现实世界与感性生活研究的经典之作。马克思研究的现实性转向主要是通过两个维度的批判来实现的:即对“彼岸世界”的批判转向对“此岸世界”的批判,从“批判的武器”转向“武器的批判”。
(一)对“彼岸世界”的批判转向对“此岸世界”的批判
所谓对“彼岸世界”的批判,就是对宗教世界(超感性世界)的批判;对“此岸世界”的批判,就是对世俗世界(感性世界)的批判。在《导言》中,与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的批判首先也是从宗教批判入手的,认为对“彼岸世界”的批判是对“此岸世界”批判的前提。这是因为,宗教作为一种颠倒了的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它从外部规定着并且掌握了感性现实生活本身,是当时德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是统治阶级统治“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和“包罗万象的纲领”以及“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4]1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和“鸦片”。[4]2面对这种“颠倒”的世界关系,费尔巴哈揭露指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认为“神学的秘密在于人本学”,把问题从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和神学观念引向人的感性世界,从而恢复了感性世界的权威。但是,“谬误在天国为神祗所作的雄辩[oratio pro aris et focis]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4]1由于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仅仅作了感性人本学的理解,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仅仅揭穿了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即人和神的异化关系,而未能揭露此岸世界的“非神圣形象”,即现实世界中人和人之间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更不可能提出现实世界“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的观点。他只看到人在宗教关系中的异化,而没看到人在政治关系中也深受异化之苦,他在瓦解“上帝的宗教”的同时构建起了“爱的宗教”,在批倒天国之神的同时树立起了世俗之神,因而未能找到彻底颠覆宗教的现实道路。
然而,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只是驱逐了彼岸世界的真理,而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才是历史与哲学的真正任务。“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4]2可见,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远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地上,而是超越了费尔巴哈。其超越之处就是,马克思的批判扎根于“现实性”基础之上:一方面,他揭示了人的现实本质,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4]1另一方面,他揭示了宗教的现实根源,认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来建立自己的现实”。[4]2简言之,宗教只是现实的虚幻反映,具有深层的现实社会根源。
于是,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实世界,并向德国现实的腐朽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与英法等国相比,19世纪的德国由于刚刚经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动乱,只能观望国外发生的资产阶级历史性变革,其结果是:在英法行将落幕的事物,在德国才初露端倪;在英法不堪入目的腐朽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的未来;英法的死灰已然熄灭,德国的烈火却正在熊熊燃烧。因此,马克思指出,当时德国的现状和德国的制度是时代的错乱,认为它“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4]3但是,德国的统治者却竭力维护它,“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4]3把农奴反抗鞭子宣布为叛乱。不仅如此,现存的德国制度与国家哲学保持在同一水平之上,现实的人深受着现存制度和观念制度的双重压迫,这意味着马克思要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这一制度得以存在的哲学抽象进行双重的颠覆。“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oeuvres incompletes],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oeuvres posthumes]——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的那些问题的中心”。[4]7
(二)从“批判的武器”转向“武器的批判”
所谓“批判的武器”,是指从理论层面揭示宗教和政治制度对人的束缚和压迫;所谓“武器的批判”,是指从实践层面阐明无产阶级立场和变革世界的历史使命。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出现在的革命要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而德国的国家哲学(集中体现为黑格尔法哲学)是一种纯思辨的抽象哲学,它把“绝对精神”设定为超感性的终极实体,并依循理性之光普照大地,而不去关注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活世界,“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4]9对此,德国的政治理论派“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4]8-9德国的实践派虽然提出了否定哲学的要求,却天真地断言:“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4]8可见,德国“哲学家”只是从理论层面揭示现实问题和提出哲学要求,把哲学批判锁闭在“我思的封闭区域之内”,而不去考虑现实的人的生存解放问题。他们不知道揭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更不知道哲学在完成“解释世界”的任务之后更重要的任务是“改变世界”。因此,“批判的武器”仍然坚持着传统哲学的“知识论路向”。
与之相反,探索“武器的批判”这一“生存论路向”才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当代任务。“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9“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4]8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不可能像黑格尔那样,只是将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引向并消融在概念逻辑的自我运动和自身完满的同一中来加以协调,而是筹划着要与这一哲学批判路径划清界线,将理论的批判与实践的变革相结合。于是,马克思把哲学批判归结为能够根本变革现实世界的“实践批判”。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批判,并非德国模仿英、法等国以实现人的民主自由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4]16马克思实践批判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把德国的革命实践抬高到将来时代“人的高度的革命”水平,即以实现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4]16因此,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心脏”,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变革世界的历史使命决定的。马克思在《导言》中阐明了无产阶级是一个戴着沉重的锁链,遭遇着人的完全丧失,只有在社会得到普遍解放之后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特殊群体,“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4]15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否定私有财产、消除奴役制、消灭阶级并“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4]15如果说,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心脏”,那么,人类解放的“头脑”则是“实践哲学”。只有实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物质武器,同时无产阶级也把实践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使“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才能完成变革世界的历史使命。
三、马克思哲学批判转向的存在论筹划
马克思哲学批判的两大转向,预示着其哲学变革的存在论筹划,它集中体现在哲学思维和哲学批判旨归两个层面。
(一)在哲学思维上,马克思筹划着从知识论的知性逻辑转向生存论的生活逻辑
所谓“知识论的知性逻辑”,是以“知识论路向”来思考存在的一种哲学思维,它坚持从某一概念逻辑或超感性的实体出发,来规定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生存论的生活逻辑”是以“生存论路向”来思考存在的一种哲学思维,它坚持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活动的历史性的展开过程中,来创设人的存在意义及其与世界的存在关系。
我们从马克思《导言》中哲学批判的两大转向,来领会马克思所筹划的哲学思维上的生存论转向,并与费尔巴哈的知识论路向做一对照。
首先,从对“彼岸世界”的批判转向对“此岸世界”的批判来看。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哲学思维是从属于“知识论的知性逻辑”的,他虽然极度呼吁要恢复感性世界的权威,但由于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而只是把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抽象地、外在地对立起来,只是用“爱的宗教”这一新的超感性实体代替了“上帝的宗教”这一旧的超感性实体。因此,费尔巴哈仍然坚持以超感性实体来捍卫他所谓的感性世界的权威,他对宗教的“冒犯”并未能使他摆脱“知识论”的哲学思维窠臼,“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5]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并没有在超感性实体中兜圈子,他对“神学形而上学”的“反叛”也没有返回到形而上学中去。马克思认为,宗教“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4]2就是说,马克思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在击穿宗教这一超感性实体之后又设定新的超感性实体,而是要求废除一切形而上学的超感性实体,并经由现实性地批判,开展出全新的“感性对象性”的生存实践活动,开辟出一条揭示并且切中“社会现实”的道路。
其次,从“批判的武器”转向“武器的批判”来看。德国的历史学派、政治理论派或实践派等“意识形态家”所从事的哲学批判,都遵循着黑格尔主义的“知识论的知性逻辑”。在这一哲学思维导引下,他们把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等视为“不证自明”的哲学前提,其哲学合法性依赖于“理性法庭”的终极裁决。在“理性法庭”面前,他们虽然可以“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但是只会“用词句反对词句”,并天真地以为只要呼喊几句“震撼世界的口号”和“陈腐的气话”,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德国“哲学家”遵循的依然是从终极本体或超感性实体来思考和把握人与世界存在的思维范式。与此相反,马克思所从事的哲学批判遵循着“生存论的生活逻辑”。马克思认为,“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对社会现实的任何不合理性存在的改变,只能诉诸于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践方式。人们只有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从事具体的生存实践活动,才能驱散绝对精神的阴霾、消除宗教的幻影、揭开意识形态的迷雾。正是在生存论的思考方式下,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对象才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使哲学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生存实践。马克思“要求哲学的重心从注目于先验的外在实体,转换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追寻世界的至终究极的解释原则,转换到关注人的具体生存境遇。因此,他的哲学思考自觉地拒斥一切先验的教条和经院的气息,并把现实生活世界作为他从事哲学批判和创造的最重要的根据地”。[1]可以说,马克思在《导言》中确立的以生活实践为定向的生存论思维方式,为其哲学建立稳固的存在论基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二)在哲学批判旨归上,马克思筹划着从压迫“此在”的非时间、非历史的知性关系转向追求“此在”的时间性、历史性的生存解放
所谓“此在”即是人这一存在者的存在,它的本质在于“生存”,时间性、历史性是“此在”的生存论性质及其展开过程。根据人的不同存在状态,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即原初状态下人的自由自在地存在、知性关系下人的被压迫性存在、全面发展下人的自由解放性生存。
马克思毕其一生的哲学努力,就是为了追求“此在”的时间性、历史性的生存解放或解放性生存。这一哲学批判的旨归和历史使命,起始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困惑”而促使他不得不对黑格尔法哲学作出批判性的思考。在《导言》中,马克思揭露了德国人深受宗教和政治统治这双重关系的压迫。而当时的德国人面对这双重压迫,依然遵循着黑格尔神秘主义的知性逻辑思维定式,无论是德国的统治阶级、“哲学家”,还是普通大众都对此抱着默然从之的非批判态度,“沉沦”于宗教幻影、绝对精神等知性逻辑关系之中,没有人提出德国人的解放要求。“无论自己和别人都被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6]根本无力从事变革社会现实的具体生存境况的实践活动。
与其相反,马克思对此持革命性实践的态度。在《导言》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揭示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全人类生存解放”的要求:废除一切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非时间、非历史的知性关系,恢复此在的时间性、历史性、超越性等生存论特性。其“‘解放’的‘根据’,则是……从‘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求索中开辟了本体论的现代道路”。[7]这条解放的道路便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在马克思那里,人类解放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前提。”[8]这意味着马克思把“人的解放”问题置于哲学本体论的原则高度,把它设定为其哲学批判的旗帜和使命,确立为哲学存在论革命之不可遏制的价值诉求和价值旨归,并筹划着在存在论路径上探索它的实际可能性。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性的并且是在存在论原则高度上展开的哲学批判转向的筹划,它为马克思完成其哲学存在论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并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化地把“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依据这一错误断言作出有力地回应。
注释:
① 海德格尔认为,全部马克思主义都是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与费尔巴哈式批判的意义完全一样的形而上学命题为依据的。参见 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也是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意义上理解《导言》的。
②参见吴晓明:《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贺来,刘李:《“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杨学功.超越哲学同质性神话——从哲学形态转变的视角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8-35.
[2]郭艳君.论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变革及其理论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1):158-161.
[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770-77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7.
[6]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6.
[7]孙正聿.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J].学术月刊,2002(9):96-104.
[8]肖小芳.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与旨趣——兼论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0(3):27-32.
(责任编辑吴月芽)
Two Criticism Transformations of Marx’s Philosophy and Planning of Its Ontology: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Introductiontothe“CritiqueofHegel’sPhilosophyofRight”
ZHOU Zhishan,ZHANG Xuehua
(CollegeofLawandPoliticalScience,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bstract:Marx achieved two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transformations i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namely, from criticism of “the other world” into the criticism of “this world”, and from “animadverting on the arms” into “the arms of animadverting”.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Ontology, one can see Marx’s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was planning to convert to Ontology, that is, on critical thinking of philosophy, he transformed from epistemological intellectual logic to existential logic of life; on the aim of critique, he transformed from the oppression of non-time and non-intellectual history to the pursuit of this temporal, historical survival liberation.
Key words:Marx;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planning of Ontology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2-0027-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中的民生问题研究”(11YJA710078)
作者简介:周志山(1963-),男,浙江金华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张学华(1991-),男,浙江丽水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6-02-18